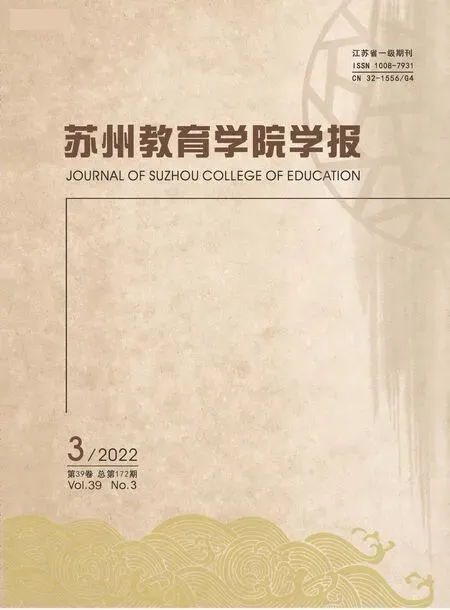小海:偏移的口语诗学
2022-03-18吴投文
吴投文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诗人小海喜欢长跑,被圈里人称为“长跑诗人”[1],这一称号具有双重意味,颇切合他的创作历程。在同代诗人中,小海是早熟的一位,他从中学开始写诗,并和九叶派诗人陈敬容通信,是当时有名头的“中学生诗人”,1985 年被保送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不过,就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来说,他的“文学自觉”还是在大学期间加入“他们”之后才开始逐步确立的。也就是说,他有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小海的诗歌创作几乎未曾停止过,一直处在长跑的途中,至今已出版诗集《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村庄与田园——小海和他的诗歌》《北凌河》《大秦帝国》《影子之歌》《男孩和女孩:小海诗集(1980——2012)》①参见小海:《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出版;《村庄与田园——小海和他的诗歌》,惠特曼出版社2006年出版;《北凌河》,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年出版;《大秦帝国》,文汇出版社2010 年出版;《影子之歌》,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男孩和女孩:小海诗集(1980——2012)》,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年出版。等,此外还有大量的诗论、随笔、对谈等发表和结集出版。当同代的一些诗人从诗坛隐退的时候,他尽管也有过矛盾和犹豫,但始终没有离开诗歌现场,他对诗歌的持守“维持着一种低调却稳定的关系”[2],写诗于他而言,并不只是一种兴趣爱好,更是一种基于内心需要的生存方式。
小海的诗歌创作大体上属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所逐步形成的口语诗阵营,但有与众不同的拓展路径和介入方式。他在一次访谈中说:“‘九叶诗派’的陈敬容先生在我少年时代曾跟我说过,要和自己的同代人、甚至和自己的写作都要保持一点距离。”[3]与时代的普遍风气保持适当的距离,同时也与自我保持必要的距离,是确立写作独特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显然,小海对此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他的创作历程中,拒绝创作的同质化并非是一种创作姿态的张扬,而是艺术自觉的内化,似乎亦带有“长跑”的性质,在持续的竞争中甩开同行者,充分呈现自我风格的可辨识度。在中国当代口语诗的谱系中,他的口语诗具有另开一路的意味,不断呈现出新的变化与突破,从形式到内涵一直处在创新与探索之中。自然,讨论小海的诗歌创作,可能取口语诗这一视角有偏取的意味,并不能完全涵盖小海诗歌在长期的试验与变异中不断叠加的综合性特征,但口语化作为一种基本的风格底色,仍然可以从中透视出小海诗歌创作的一些重要取向,对观察小海21 世纪以来的诗歌创作及其特殊的诗学路径也是一个有效的视角。
不少研究者在谈及小海的创作时,都强调地域因素对小海诗歌创作的影响,认为“在中国带有很浓郁的行政色彩这样的国度里面,实际上小海在苏州从事诗歌写作,往往被忽视,或被边缘化。因为坦白地讲,它不是文化中心,因为你发出的声音跟其他人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在北京,或者在上海,在南京,往往发出的声音会比这里强烈”[4]。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中国文坛,甚至诗坛对小海的诗没有给出应有的评价”[4]。虽然苏州是人文荟萃之地,但到底还是偏离文化中心的。小海长期定居于此,他的创作还是受限于传播中的聚焦效应,因此,对小海诗歌的评价存在预期上的落差,里面确实包含着地域因素的影响。不过,从创作的更深层面来看,可能还牵涉更为复杂的因素,值得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在中国当代的口语诗谱系中,读者和研究者认定的“中心诗人”是于坚、韩东、伊沙、沈浩波等人,他们的诗歌呈现出口语化的整体性风格特征,他们的创作主张与创作实践也有较大的契合性。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后面各自跟随着一支庞大的“影子”队伍,他们对口语诗创作确实具有实质性的影响。相对而言,小海是口语诗创作的“偏师”,虽同在口语诗的谱系中,但他进入的路径和介入的方式却偏离于口语诗的“常道”,他走的是一条通向口语的“岔道”,恰如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中所写的:“但我选择了另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静,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条小路上,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5]罗伯特·弗罗斯特正是小海心仪的诗人。有研究者认为,“小海的诗受西方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弗罗斯特的诗歌对他诗歌意象的捕捉、画面的选择、语言的组合,都有很深刻的影响,甚至断言:小海是‘中国的弗罗斯特’”[4]。尽管把小海称为“中国的弗罗斯特”可能并非是一种确切的论断,但二者在艺术表达的独特性追求上确实呈现出近似于同心圆的涵容。小海对“另一条路”的选择出自自我的艺术决断,他的口语诗在长期的探索中,逐步趋向一种与生活的日常性保持适度“间离”,但又契合于自我性情的圆融与完整,代表了从当代口语诗创作中分化出来的另一路径。
几乎从诗歌创作的起步时期开始,小海就对口语诗性有一种出自天然的敏感,如《狗在街上跑》《老家》《K 小城》[6]3-7这些诗都是通过一个少年的眼睛去看的,看到的却是世界的“反面”,全无一个少年诗人对世界“真实性”的隔膜,反倒有一种在对世界的“陌生化”体察中呈现出来的迷人的气质,如《老家》中这样写道:
他的母亲爱他
往往起得很早
为他采一束春天的花
并且深深吻他
那是个坏天气
在大雨中的街上
他分明听到一个少女
吹着口哨在奔跑[6]4-5
此诗的语言是口语化的,却剔除了口语中的杂质,把一位少年诗人的天真处置得异常纯净,诗中的语调缓慢,把少年诗人的沉思放置在一片恍惚的景致中。此诗写于20 世纪80 年代初期,正是当代口语诗萌芽的时期。小海在出道之初已有如此上佳的表现,说明他有一种敏感的“偏移”能力,能够在当代诗歌的主潮中分辨出一种异质写作的可能性向度。
一般认为小海是“他们”的主力诗人,这诚然是一个可靠的事实判断,但事实后面的逻辑却是模糊的。换言之,当小海被指为“他们”主力诗人的时候,他的独特性是被压抑的,被遮蔽在一个符号的整体性晦暗中。实际上,他对“他们”是一种偏移,是一种补充和修正。小海在《〈他们〉往事》这篇长文里写道,“他们”诗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呈现、共同写诗,向保守的诗坛发起集体冲锋”[7],但这也是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权宜之计,是要在诗坛攻城略地,取得属于他们这一代的话语权。在具体的创作策略上,“他们”诗人大抵奉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为圭臬,使诗摆脱当时盛行的概念语言,摘下“时代面具”,“回复到语言表情达意的本真状态”。[8]161“他们”内部的实际情形却要复杂得多,口语诗创作是“他们”诗人的基本方向,但“只是取个公约数,分子分母是动态的、不确定的”[9]167,作为个体的“他们”诗人还是在相互对照中呈现出丰富的创作样态。对小海而言,他取的是一种“偏移的口语诗学”,是凸显个人创作的可辨识度。实际上,小海对口语诗有相当充分的警觉意识,他并不完全赞同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他对韩东的这一命题有相当辩证的认识,一方面他认为这一命题“既是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崭新的诗学命题,也带有一定的策略性,同时,无疑是针对当下诗坛正确的‘临床诊断’”[8]161,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要承认独特和差异,诗人不是语言的奴隶,要正确对待语言的游戏性质,“把语言降格为取消精神衡量向度,单纯追求语言系统内部操作快感和无序原则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也是有害的短期行为”[8]163。在对诗歌语言的综合考量下,他如此发问并确认自己的判断:“那么,现在由我来发问:诗到语言为止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8]165显然,小海是一位自觉的诗人,他的判断既出自自己的创作实践,也出自他对诗歌创作的总体认知,符合文学史的基本情形。
小海早年开启的口语诗创作,尽管后来也有所变异,但创作的基本走向并未改变,口语化作为一种风格底色始终贯穿在他的创作中。进入21 世纪,他的创作处于持续的爆发状态,在题材视野、主题深度、风格形态上较之以往都有更进一步的拓展。在此,不妨拈取他在2000 年创作的《镜头以外》作为例证:
在坎大哈
看见一个战士
手上的烟叶
和他的吉祥面孔
还不到打仗的时候
半路他可能会死去
许多年以后
也许他会回来
从容地看着我
就像他看着山谷里
金黄的堇菜花[6]177
坎大哈位于阿富汗南部地区,大概小海曾到此一游,有感而作,也可能是一首随性之作,小海未必注入过自己的推敲苦心,但此诗却有其绝佳之处,得之于自然,写得异常凝练,值得反复品味。此诗的前四句(第一节)是镜头里看得见的景象,是一个拉得很远的镜头,里面只有一个看得见的人物,却又近乎特写,有逼真的细节——一个战士在抽烟,他的面孔吉祥。此诗的后七句(第二节)是镜头之外的看不见的心灵风景,却婉转于诗人起伏的情绪,似乎是诗人的画外音,却比画外音低微而多出一份恍惚。此诗的镜头感很强,简约的画面、素描式的人物、空阔的背景,似乎一切都搅和在诗人情绪的暗影里,显得又渺远,又切近,具有心灵的透视性,这就是诗中隐隐透露出来的哀感。诗人写生死与莫名的某种怀念,其中包含着对战争的反思,却不是直接的,而是抑制和抽离内心的悲伤。此诗的魅力源于何处?细究起来,很大程度上源于诗人口语化的表达方式,诗中没有意象的堆砌,没有词语燃烧的华彩,就像平时说话一样自然,却没有一个多余的词句,所有的词句都处在合适的位置上,所有的词句都带着嘴唇的湿润,像词句自己在发出声音。这首诗有它的深邃和丘壑般绵延的层次,是茫然的,也是清醒的;像早晨,也像是黄昏即将来临时的光景。诗人对语感的把握极其到位,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都缠绕在口语的光影上。此诗的口语境界是长期磨砺出来的,像庖丁解牛,小海的手上功夫讲究意到心到,然而又有恰到好处的偏移,正所谓偏而不偏,使口语归于正道。
在小海21 世纪以来的创作中,《镜头以外》似乎包含着其口语诗创作中的某种新变,日常化的生活场景经过高度的提纯和凝练,不再只是作为一个“事实”而存在,往往带有难以言传的心理气味。诗人的主体介入看起来是客观的,实际上诗人处于“假寐”的状态,他始终在静观默察,在悄悄地剔除事物“多余”的那一部分时,往往只保留能够显示事物“精神”的那一部分。小海的诗歌异常简洁,就在于他精于剔除的“手艺”。他的《初雪——浅浮雕》《收音机和公园》《出山》《放生的鸟儿》《蜜蜂》《一九五七》[6]180-203等都是如此,似乎诗人潜伏在诗中的场景里,他之所见都是经过他精心剔除的。同时这些诗歌的口语相当精到,几乎都是日常语言的转化,显示出一种光洁的柔性,这也是他精心剔除的缘故。
在我看来,小海的口语诗是一种“转场”的口语诗——从生活的现场转移到心理的现场,他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也用世界的眼光看自己,与世界进行隐秘的沟通,带有与事物对话的性质。他避免直接倾诉的那种传统化的抒情效果,也有别于所谓的“零度抒情”,尽管他有时候也现身在诗中,却从不喧宾夺主;也不是充当一个观察者,而是把自己融入到事物中去,让事物代替自己说话。因此,他特别讲究简洁,讲究口语的自动呈现,讲究口语的“迂回性”效果。小海的口语诗似乎凝练着诗人主体的沉着,这与他介入生活的方式有关。小海习惯从一个偏移的视角去观察事物,不与现实短兵相接;习惯从事物中发现一种偏移的力量,用一种陌生的姿态焕发生命的热情,拒绝与现实进行等价交换,以此确立自己与世界之间既交锋又媾和的悖论关系。小海的诗歌自有其深度,实际上正来源于这种不无另类性质的追求,这也是21 世纪以来小海诗歌的一个重要转变。
小海在谈到自己的这个创作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个渐进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不是临时的决定或者说一次灵感突袭。”[2]确实如此,他的这个转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他是一位有准备的诗人,“总是想着颠覆自己、寻求突破,尝试各种可能性”[2]。按照小海自己的说法,21 世纪之后,他不想沿袭老路,决计放弃“标签式的主题与创作路径”[2],也因为其个人阅读兴趣的转变,从早年偏重文学艺术而转向历史与哲学,加上工作的变动,个人生活阅历的增加,生命的体验与经验更加真切,自然会带来创作实践上的变化,也对写作的可能性有更进一步的思考。对可能性的尝试与探索是一位自觉的诗人的本能,这也意味着诗人要在不断的自我重塑中完成自我风格的独特性创造。创作的调整与转变不是连根拔起,而是诗人在对自我局限性的审视和修复中建构更丰富、更完整的自我形象。小海说:“创造永远是唯一的。每一位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诗人,只能终老于自己创作的诗歌中。”[10]毫无疑问,小海是一位有定力的诗人,他追求在创造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通过不断的发声来“创造”一个虚拟的自我。小海的长诗创作,正是他着意于写作的可能性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尝试。
在多数读者的印象中,小海是一位擅长短诗佳构的诗人,但他在21 世纪奉献的两部“长调”——《大秦帝国》与《影子之歌》——让读者和研究者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前者是一部诗剧,后者是一首长诗,都是小海匠心独运的突破之作,是21 世纪诗歌的可喜收获。小海说:“写短诗就像短跑,长诗就像跑马拉松。短跑要求爆发力,对起跑、加速、冲刺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要求,短诗再短,哪怕仅仅是一句诗,都要考虑这一句、这一行当中的能量发挥和句子的张力。长诗则要经营,就像马拉松,呼吸和心律都必须调整,要求悠长的吐纳和心律。”[11]长诗的规制要求篇幅有一定的长度,结构上讲究开合度,语言上的经营对诗人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小海的创作进路还是落实在口语上。不过,进一步细究,他采取的还是一种偏移的策略——对口语的偏移,口语与书面语的适度杂糅,把口语的元气辐射到诗的整体结构中。因此,他这两部“长调”的风格底色是口语化的,却又呈现了超出口语的复杂调性。这对小海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冒险,他需要用心处理好长诗内部细节之间的复杂关联,需要对口语进行适度的抑制,同时又得激发口语的原生活力,如同踩高跷一样保持巧妙的平衡。这里不妨择取《大秦帝国》中的一个片段作为例证:
草长在头皮上
草会遭遇北风摧折
草会被马儿啃食
彩绘的脸是寂寞的
嘴巴是寂寞的
颧骨是寂寞的
死亡是我终生的学业
可我知道的越多
学会的就越少
头顶的草皮移动时
从纯粹生物的意义上讲
我们只是搬运一小撮泥土而已
我们不知道出生
泾水、渭水、黄河水
我们知道死亡才是故乡[6]220-221
这是秦国远征将士的一段内心独白。诗中的场景带有死亡的寂静气息,却又隐隐地透出泥土里的声音。“死亡是我终生的学业”,“我们知道死亡才是故乡”,显得多么沉重,在苍凉中透出不甘与无奈,也透出荣耀与骄傲。在此,一切都是历史的记忆,也带有反思战争的意味。这一段的语言是相当精警的,既有常态化口语的自然畅达与流动感,也有剔除口语芜杂因素后的洗练与精确。小海对词语的择取是从整体表达效果着眼的,并不追求词语本身的奇崛,但在诗的整体效果上却不无奇崛的意蕴。口语是一种日常性表达,其主要功能是日常交流的达成,要真正发掘出口语的诗性效果,就必须对口语的表达进行适度的偏移与矫正。换言之,使口语脱去“口水”的外罩,脱去“非诗化”的累赘部分,“朝向诗歌写作自身的发现”[12]。叶圣陶有言,“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13]。应该说,小海的诗在“语”与“文”的处理上大都有恰到好处的平衡,他向口语偏移,但也并不拒绝书面语的衬托,因此,他的诗有时呈现出口语与书面语混融的效果,既有“一种在场的感觉、可触摸的感觉”[14],又有一种“陌生化的语境效果”[15]。诗剧《大秦帝国》如此,长诗《影子之歌》亦如此。
与当代口语诗的主流相比,小海的口语诗总体上呈现出偏移的特征,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究其实,偏移的口语诗学是小海诗歌创作的内在文脉,也是其风格化形态。他的偏移是一种基于口语诗性的艺术节制,他一般极少使用原生态的日常口语,而是注重从日常口语中离析出含蕴诗意的那一部分,一方面克服书面语可能存在的呆板与僵化,另一方面,克服口语可能存在的浅白与粗俗,因此,他的口语诗往往包蕴着绵长的韵味。这是他与口语诗“鹰派”的一个重要差别。尽管小海的创作属于当代先锋诗歌的范畴,却又谨慎地与之保持间距,他回避激进的写作路径,不走极端,讲究节制的美,讲究艺术的圆融之美。他的“偏移”实际上是对当代先锋诗歌的一种矫正,“偏移”是另一种形式的“居中”,有别于那种张扬极端个性的越轨。就此而言,“偏移”的口语诗学对小海而言是一种“中间”的先锋诗学,偏移而保持克制,居中而不自以为大,也就是一种“兼容”的先锋诗学。他的很多诗显得轻逸、自在、敞亮,有一种包容传统底蕴的亲和力,也有一种深度介入现代派诗歌艺术的决断力。这正是“中间”的先锋诗学在小海创作中的体现。
在先锋诗歌的强势覆盖下,中国当代诗歌的本土化路径受制于西方陌生语境的抑制,换言之,我们用汉语完成的诗歌往往没有汉语化的味道,而是弥散出陌生的气息,并不是从我们民族自身的传统中内生出来的。这也是读者远离诗歌的一个重要原因。小海口语诗的偏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陌生语境的偏移,他试图重新把汉语的味道注入诗歌的呼吸中,让读者真正体验到汉语诗歌的汉语味道,这是汉语诗歌的归位。口语诗的一个突出优势是有汉语的味道,但未必同时有诗的味道,而要把汉语的味道与诗的味道综合到高度统一的状态,综合到真正民族化的状态,真正使口语诗成为小海所说的具有汉语味道的“艺术诗”,显然,这个目标并不容易达到,小海却为自己确立了这样的创作方向。在小海的访谈、创作谈和诗论中,反复出现“中国诗人”“民族诗人”“国家诗人”这些与新诗的本土化、民族化联系在一起的名称,从中可以发现长久以来他对新诗创作脱离民族化的焦虑心态,也可以从中发现一种秉持“兼容”精神的本土化诗学。小海认为一个诗人成功的标志,“首先必须是一位‘民族诗人’,具有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的胎记”[16]。他甚至断言,“使自己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诗人”,“要写出真正中国的东西”。[17]他把自己的创作理想奠基于民族化的路径上,恪守一位中国诗人的文化本位意识,这是他出自内心的文化自觉,也是他的口语诗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使命感。往更深层看,“偏移”的口语诗学、“中间”的先锋诗学、“兼容”的本土化诗学,是小海的口语诗创作所包含的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维度,也是他的口语诗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整体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