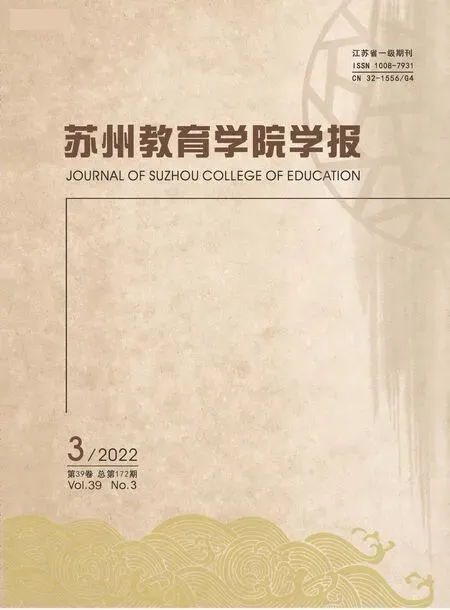江南氛围中的个人气质
——小海为何没有完全成为波德莱尔的第二代中国传人
2022-03-18王珂
王 珂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小海创作的诗歌题材和体裁都比较广泛,从题材的丰富性而言,从乡土诗到都市诗,从现实诗到历史诗等都有涉猎;从体裁的多样性而言,从小诗到长诗,从抒情诗、叙事诗到诗剧等也多有探索;甚至从新诗从业者的多栖性来说,他也是多面手,诗人、编辑和学者集于一身,这些足以证明小海的优秀和其对中国新诗作出的贡献。
一
2013 年,在江苏省常熟市召开的“小海诗歌学术研讨会”上诗人小海被界定为“体制外的自由行吟者”[1],一些与会学者,尤其是非专业研究新诗的学者为他抱不平,认为他没有受到诗界应有的“重视”。“栾梅健教授作为会议主持人介绍了为小海召开研讨会的缘起:其一,小海自身是一名公务员,从事诗歌创作三十余年,作为文学体制外的人进行创作往往不大能受到文坛或者同行诗歌界的关注;其二,在中国这个带有浓郁行政色彩的国家里,苏州作为偏离文化中心的城市,缺乏有影响力的刊物和成熟的诗歌创作群体,这往往导致了诗人创作的外部评论环境和文艺争论平台的先天不足;其三,小海的诗歌与当下倡导的主旋律有所不同,甚至有疏离感。小海纯粹写内心,写自然,写童年,写田野。从非文化中心城市发出的清雅、优美的纤细声音,很容易被强调宏观叙事的洪流所湮没。种种因素导致了当代文学史或者当代诗歌对小海的关注与肯定远远不够”[1]。同时,“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吴俊就小海的非职业化诗人身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古往今来,活跃在诗歌场域与权力争夺发生关系的诗人往往更受关注,而像小海这种远离所谓诗歌权力场域的诗人,往往在批评家和学者的研究里受到某种轻视”[1]。栾梅健和吴俊两位教授所言极是。多年来,我也有这种感受,中国诗坛非“中心”(京城外的“外省人”和省城外的“外城人”)的诗人确实较难得到官方和学界的重视,如20 世纪90 年代发生的“盘峰论剑”事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是以于坚为首的外省诗人与以王家新为代表的北京诗人的话语权之争。在20 世纪80 年代也曾出现过新诗研究界的“上园派”,主要成员是以吕进、叶橹、陈良运等北京以外的诗评家为代表形成的“联盟”,因当时他们在北京参加诗歌活动时住在“上园饭店”而得名。
我从来没有与小海打过交道,仅对其作品有一定的印象。作为新诗的专业研究者,尤其是诗评家,我不愿意受到诸如友情、亲情之类的人际关系影响,如我一旦与某位诗人熟稔,一般就不会写他的诗评,即使写了也决不留情面。因此我在中国大陆有“新诗城管”之绰号,在中国台湾亦有“毒舌”之谓也。曾在席慕蓉、洛夫、牛汉、郑敏等老诗人的研讨会上,我都由温柔的“王珂”变成尖刻的“王珂”。因此很多人不愿意,甚至不敢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作品研讨会,我也不轻易参加。这次受邀参加小海诗歌学术研讨会,并请我写文章,我却高兴地答应了,不仅是因为小海的诗歌确实值得一评,诗界,尤其是新诗研究界对小海的评价太低了,所以我一定要认真地写一篇客观评价他的论文,肯定他对新诗作出的贡献;还因为我有比较奇特的“小海接受史”和以小海为代表的这一代诗人的接受史的情结。近年来,我在从事“现代汉诗”及现代主义诗歌推广的活动时始终强调新诗应该是“现代”的,应该由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演进,甚至主张现代主义应该取代现实主义,如不能取代,就应该让两者和解,或者在内容、题材上走现实主义路线,在形式、技法上以现代主义为主。我在研究新诗史时发现许多优秀诗人完成不了由优秀诗人向伟大诗人的飞跃,这无疑影响了整个新诗的健康发展。
二
近期研究小海及其诗作,我又开始反思为什么国内许多优秀诗人完成不了向伟大诗人的飞跃这个问题,我认为小海如能始终保持“先锋”状态,是能够完全摆脱“苏州诗歌”“江南诗歌”甚至是“南方诗歌”等这些地域性诗歌的文化“束缚”的,是能完成由优秀诗人向伟大诗人的飞跃的。那么这对小海的诗歌创作会不会更好呢?答案是肯定的。由此,我想起了2017 年在兰州采访老诗人高平时的情景。高平在20 世纪90 年代曾任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达十年之久,见证了很多诗人的成长。他感叹地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名言误导了很多诗人,甚至被更为狭隘地理解为越是地方的越是全国的。这是甘肃乡土诗繁荣的重要原因,也是甘肃有优秀诗人,但没有大诗人的重要原因。”高平先生一语中的地点明了地域文化的局限性。这也是我三十年来从事新诗研究所验证的结论之一。
2013 年,我在给诗人陈义海诗集《一个学者诗人的夜晚》写序时说:“我很早就读到义海的诗,将他与诗人‘小海’混到一起。”[2]陈义海和小海都接受过陈敬容的帮助,陈敬容曾向我的硕士生导师邹绛先生和吕进先生推荐过义海攻读他们的研究生,后来他通过考试被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录取。如小海所言:“1979 年底,开始和‘九叶’诗人、翻译家陈敬容先生建立通信联系,在此后的近10 年中,她对我的写作提出了参考意见和建议,教诲和帮助没齿不忘。”[3]11999 年,小海还写了《悼念敬容先生》[4]的诗,以表达他对陈敬容先生的感恩与怀念之情。郭艺在《小海文学年谱》中记载:“一九七九年,十四岁。小海考入海安县中学读书。……同年底,小海在报纸上看到陈敬容的两首诗歌,顿觉耳目一新,于是立即写信给陈敬容,同时还附上了自己写的两首小诗。……在此之后,小海一直和陈敬容保持着通信联系。”[5]陈莎莎也说:“小海的写作具有独立的个人色彩,他一直提到陈敬容对他的影响,敏感的‘距离’使他一直拒绝将某种理论或者口号的标签贴在自己身上。”[1]
张松建认为陈敬容是波德莱尔在中国的三大传人之一,其他两人是汪铭竹和王道乾[6]。小海很早就接受了现代主义诗歌教育,这是他成为先锋诗人的重要原因。但是他与义海一样,最后都没有完全成为波德莱尔的“再传弟子”,反而偏向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尽管他们都成为了优秀诗人,尤其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总是有些遗憾,他们还有能力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小海没有成为波德莱尔的再传弟子,这对于小海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对中国新诗界来说,是幸还是不幸?甚至还可以联想到以下问题:中国新诗,尤其是当下的新诗,是否应该完成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进化”?如何完成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建设?我们首先应该肯定小海是现代诗人,他写的是现代诗,甚至是我近年来鼓吹的“现代汉诗”。我认为:“新诗更应该称为‘现代汉诗’,是采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情感和现代生活的现代艺术,通过倡导现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来让中国人和中国更现代。”[7]1小海抒写的“现代情感和现代生活”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他写出了一个现代人,尤其是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和生活在城市里的“乡村人”的真实生活。他写了很多都市诗、乡土诗和亲情诗,正是这种类型化写作,妨碍了他的现代主义诗歌写作。我们知道诗人大多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也不放弃个性和自由,因而这类诗人的创作除了具有强烈的个人气质外,还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由于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很多处于相同地域的诗人大都具有相似的文化特征,由此形成了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作家群落。当然,才华横溢的小海也自然没有完全跳出这种地域文化的怪圈。
2011 年,《当代作家评论》第5 期“诗人讲坛”栏目推出小海专题,发表小海诗论《关于当代诗歌语言问题的思考》、何平与小海的对话录《“使自己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诗人”》和何同彬的评论《忠实于我的时刻越来越“多”——对小海近期创作倾向的考察》。同年,《深圳特区报》发表小海专访《诗歌原来属于寂寞的行列——专访民刊〈他们〉创始人之一诗人小海》。[5]
不难看出,《“使自己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诗人”》和《忠实于我的时刻越来越“多”——对小海近期创作倾向的考察》的论断与“诗歌原来属于寂寞的行列”的观点是矛盾的。小海提出的要使自己成为“国家的诗人”的观点,使我想到波德莱尔的那段关于诗的功能的名言:“只要人们愿意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中去,询问自己的灵魂,再现那些激起热情的回忆,他们就会知道,诗除了自身外并无其它目的,它不可能有其它目的,除了纯粹为写诗的快乐而写的诗之外,没有任何诗是伟大、高贵、真正无愧于诗这个名称的。”[8]
三
近年来,我一直在做新诗文体学研究,始终坚持将生态、功能和文体三者合一进行考察。我认为:“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文体决定价值。诗教功能和诗疗功能是今日中国新诗最重要的两大现实功能,是由广义的‘诗’、狭义的‘新诗’和特殊的‘现代汉诗’三种文体的文体特征和文体生态决定的。今日中国新诗具有‘诗’‘新诗’和‘现代汉诗’三种文体的各自元素,是三种文体的互相融合又互相纠缠的特殊文体。”[7]4小海的诗也有这三种文体的同时存在,如他的乡土诗,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诗”;他的亲情诗,更多的是现代中国百年以来的“新诗”;他的城市诗更多的是近年来的“现代汉诗”。他的亲情诗和乡土诗并不能称为“先锋诗”,他的城市诗才可以称为“先锋诗”。这里的“先锋诗”是指倡导现代意识和鼓吹现代精神的诗。在某种意义上,“先锋诗”可以与“现代汉诗”相提并论。
作为新诗的编选者,小海具有鲜明的先锋品格。小海、杨克编选《他们:〈他们〉十年诗歌选》(以下简称《〈他们〉诗选》)[9]的独特眼光,让我不禁为之惊叹。如唐欣的《春天》一诗:“春天,忧伤以及空空荡荡/我伸出双手,丢掉了什么/又抓住什么/在寒冷的小屋/像圣徒一样读书/什么也不能把我拯救//长期的寂寞使人发疯/下一个我将把谁干掉/想象中,我曾埋葬过多少赫赫帝王//其实我多么愿意是个快活的小流氓/歪戴帽子,吹着口哨/踩一辆破车子去漫游四方//也许我该怒吼/也许我该冷笑/也许我该躺下来,好好睡一觉”[9]233。1990——1996 年,我在西北师范大学专职从事西部新诗研究时与唐欣熟识,经常与他一起谈诗论道。虽然《春天》这首诗是他的口语诗代表作,但因其口语化和比较颓唐的情绪,很难被当时的正统诗界所认可。21 世纪初,唐欣在兰州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写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口语诗的,论文经过修改后,作为专著《说话的诗歌: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口语诗研究》[10]出版,成为新诗界第一部研究口语诗的著作。1997 年,当小海、杨克编《〈他们〉诗选》时,此时的口语诗正被很多人视为“口水诗”。我更佩服他们选取的韩东的10 首诗。如果从流行的诗观,尤其是从“主旋律”写作的观点来看,这些叙述日常生活的诗确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对我来说,它们却让我有耳目一新之感,如韩东的《来自大连的电话》一诗:“一个来自大连的电话,她也不是/我昔日的情人。没有目的。电话/仅在叙述自己的号码。一个女人/让我回忆起三年前流行的一种容貌//刚刚结婚,在飘满油漆味儿的新房/正适应和那些庄严的家具在一起/(包括一部亲自选购的电话)/也许只是出于好奇(像年轻的母猫)/她在摆弄丈夫财产的同时,偶尔/拨通了给我的电话?//大连古老的海浪是否在她的窗前?/是否有一块当年的礁石仍在坚持/感人的形象?多年以后——不会太久/如果仍有那来自中年的电话,她一定/学会了生活。三十年后/只有波涛,在我的右耳/我甚至听不见她粗重的母兽的呼吸”[9]4。更让我赞叹的是小海、杨克选诗的那种先锋姿态和前卫精神。
20 世纪90 年代,我在先锋诗的研究中也常引用唐欣和韩东的诗,并对他们的诗作了肯定性评价。凭我的直觉,像唐欣的《春天》和韩东的《来自大连的电话》等作品应该是小海编选的。为什么不是杨克?我认为杨克的整体风格是偏向传统的,像唐欣、韩东的诗未见得能入杨克的法眼。由《〈他们〉诗选》引起了我对小海的关注,但是读其诗作,尤其是有关地域性的诗作时又感觉到他的诗风与其编选的《〈他们〉诗选》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究其原因,可能“他们”诗群并不是“江南诗人群”,如唐欣就生活在大西北。正如小海所言,“他们”诗群的诗人对他产生了影响,“少年时代起和韩东等人交往,尤其是后来与《他们》文学圈中一批杰出的诗人、作家们的交往,不仅收获了友谊,更重要是,我的写作变得更加自觉”[3]1。而小海发表的那些地域性诗歌作品是他在苏州完成的,与“他们”文化圈关系不大。
在常熟召开的“小海诗歌学术研讨会”上,林建法认为:“小海从事诗歌创作三十多年,是《他们》创始人和代表诗人之一,代表作有《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村庄与田园》、《北凌河》、《大秦帝国》和《影子之歌》等。从《北凌河》到《大秦帝国》,再到《影子之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深入探讨的诗歌现象与诗歌审美体验。”[11]小海写作的独特性引起了当时与会专家们的注意。吴俊总结了小海创作的三个阶段所代表的三种境界:第一,他认为最早的《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和《北凌河》里的诗,“都源于对人的一种哀悼”,“由此可以理解小海对自己的童年生活,对乡村等在自己诗中安放的位置”;第二,他认为“《大秦帝国》的形式感太强了”,并指出小海“刻意追求了西方古典史诗的气场和做派,有一种用诗歌、乐句和韵律升华历史的宏大感……这部诗剧又最能直观地体现诗人小海的诗艺才华”;第三,《影子之歌》是第三个阶段,他认为小海是“将抽象之思渗透或覆盖到俗世情态之中”,用“非常朴素的方式”将“哲学思考和生活的感受描述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诗人”。[11]傅元峰认为小海的诗歌具有浓厚的“乡村的意味”,但又巧妙地处理了城乡对立的问题;同时,“小海对历史有浓郁的兴趣,历史是他的又一故乡,但小海的历史趣味和面对历史的姿态比较特别”[11],“他将历史抽象为一个又一个诗性时间,在时间之内建立维度,他不在城乡之间、历史的宏大与生活的琐屑之间作简单的二元取舍。最终,小海‘自己通过历史,通过时间,打开了另外的一个维度。他是打破了历史和现实的陈旧诗意的诗人’。小海告诉了我们‘时间’的一种诗歌可能,他赢得了诗歌的尊重”[1]。何平认为“小海的诗作给了他‘兄长带我回家’的感觉,唤起了他许多的童年记忆。他认为在一个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小海的诗歌很容易被简单地读解为田园和都市对抗的寓言式书写。但是作为一个和小海有着共同故乡的阅读者,他倾向于认为小海是一个朴素的行吟诗人,他那民谣般对村庄、田园和河流的吟唱是诗歌最初的源头”[1]。
“乡村的意味”“兄长带我回家”“朴素的行吟诗人”“民谣般对村庄、田园和河流的吟唱”,等等,这些观点都肯定了小海诗歌的乡土性及传统性,而不是都市性或现代性。这种相对保守的写作对个人的情感治疗来说,是无可厚非的,比如在治疗个人乡愁,特别是对都市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不满或抱怨等方面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对群体的启蒙而言,可能就存在不足,尤其是对培养现代国人的正向观念和打造现代中国的精神可能就有些问题。这样的写作会让诗人越来越自恋,甚至自艾自怜,这样的写作是缺乏现代精神的,是缺乏挑战自我和面向未来的现代情怀的。如果以才、胆、识、力四要素来衡量小海的写作,他完全可以成为大诗人,从其写作的时间长度、写作题材的多样性,以及写作技法的多变性来看,他完全能成为大诗人,但小海离这一目标却差了一步,只要他勇敢地跨过去,就一定能破茧而出,涅槃重生。不可否认的是,小海后期的写作确实显得有些保守和传统,缺少了前期的先锋姿态。这恐怕与他低调做人、低调写诗有关,也与他生活、工作在苏州这个园林式城市有关,以及与受邻近的上海的诗人独立性强、不事张扬的处事方式的影响有关。洪子诚曾说:“在诗歌圈外的人看起来上海的诗歌不是太景气,印象里头上海和诗歌好像离得都比较远,好像上海也不重视诗歌……另外上海诗人个性都比较强,都有点自负,不能够成为真正的‘拉帮结派’,而且也拒绝对他们的作品作就像我现在所作的对他们进行整体性的概括,但是在当代中国以运动为主要特征的诗歌环境里头,他们的名声也因此受到损害,影响力也受到一些削弱。”[12]
毋庸讳言,小海的影响力低,可能与他的个人的生存方式、写作方式,特别是写作题材的狭窄有关,甚至还与到他缺乏更为系统的西方现代诗歌教育的启蒙有关。虽然他在中学时期就受到了陈敬容的影响,但作为中学生的小海或许也没有多少能力能完全接受陈敬容的波德莱尔诗学观的滋养。在那个时代,连现代派诗歌的理论家袁可嘉推出穆旦时也不得不强调他是一位“爱国诗人”“现实主义诗人”[13]。20 世纪80 年代大学的现代诗的教育观念还比较保守,也不完整,正如李亚伟在《中文系》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中文系也学外国文学/着重学鲍狄埃学高尔基,有个晚上/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他大声喊:同学们!/快撤,里面有现代派”[14]。
小海是1989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他在大学时没有遇到专门从事新诗研究,尤其是现代诗歌研究的老师,这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一种遗憾。当时北京大学有谢冕和孙玉石、山东大学有冯中一和吴开晋、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有袁中岳和吕家乡、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有吕进、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有吴思敬、北京师范大学有蓝棣之和任洪渊、吉林大学有公木、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有孙克恒、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有孙绍振、复旦大学有吴焕章、武汉大学有陆耀东,等等,这些大学的新诗教育相对较好,培养了一批现代主义诗人。另外,小海工作所在地的大学也长期缺乏新诗研究的教授。这样的诗歌生态环境使小海缺少与来自学界,尤其是新诗研究专家、学者的常态化沟通与交流,缺少专业方面的诤友。当然,也不能因为师资的原因完全否定南京大学的新诗创作,但就整体水平而言,南大诗人群的确无法与北大诗人群、北师大诗人群、山大诗人群、复旦诗人群、武大诗人群等相提并论。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在21 世纪的前十年,江苏乃至上海的新诗研究都较弱,如出席常熟“小海诗歌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除了傅元峰是专业研究新诗的,以及何平、汪政既研究新诗也研究小说之外,其余的都不是专业的现代诗研究者,他们或许对中国诗歌有一定了解,但对外国现代诗恐怕不一定熟悉。2013 年时小海才48 岁,年富力强,如果当时有人对他提出批评性的意见或建议,或许对他今后成为“大诗人”是有益处的,尤其是对他最近十年来的写作会有更大的帮助。我体会过“隔行如隔山”的无奈。我曾在一次有关文艺理论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到现代诗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但没有说是哪位诗人提出的,在座的教授们都认为是我的观点,竟没有一个人赞同。当我告诉大家答案时,教授们仍然不接受它。这个观点就是林以亮曾引述的现代主义诗人奥登的观点:“现代英国诗人,后入美国籍的奥登曾经说过:‘诗不比人性好,也不比人性坏;诗是深刻的,同时却又浅薄,饱经世故而又天真无邪,呆板而又俏皮,淫荡而又纯洁,时时变幻不同’最能代表现代诗的精神。”①转引自林以亮选编,张爱玲、余光中、林以亮、邢光祖译:《美国诗选》,今日世界出版社1976 年出版,第4 页。该观点直到现在仍不被大多数文学教授认同。
四
尽管小海的乡土诗写作是相当成功的,但是这种写作也因为素材简单、题材狭窄、思想简单,有时甚至很偏激而被人质疑,如过分怀念乡村文明,讨厌城市文明等,这也影响了小海的“现代性写作”及“现代汉诗”的写作。罗振亚教授曾批判过乡土诗,他认为:“乡土诗是指乡土人写的诗,还是指写乡土的诗,抑或指乡土人写乡土的诗?迄今仍无定论。我们以为无须在这歧义丛生的称谓问题上纠缠,凡是以乡为方圆、以土为特色的诗皆可称为乡土诗。”[15]他特别指出:“现代乡土诗创作也留下了许多无法逆转的缺憾。如内视点的诗歌一味向大众化民族化及乡土拓进,难免限制了诗人抒情个性伸展,多元风格的形成与新诗现代化的正值生长;其实乡土与现代性决非水火难容的两极,卞之琳的《尺八》、艾青的《手推车》等使其得到了理想结合,可惜这样的诗只是凤毛麟角。‘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理论过度强调,导致大量乡土诗只能做匍伏乡土之‘兽’,而无法盘翔为入乎乡土以超乎乡土的‘鹰’,少现代意识与哲学意识烛照,少言理而多宣情,探究乡土本质——人之存在的作品寥寥可数,这样就削弱了艺术的深厚冲击力;其实乡土生活中并不乏哲理内涵的因子,《三代》对人与土地关系所形成的命运旋律思考就是明证。不少乡土诗只是农民恋土意识的翻版,或只陶醉于传统的清新梦幻里,流露出优越的本土观念,这样就偏离了现代乡土古朴而悲凉的灵魂内核,优美乐观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真正的人间烟火是残酷与优美的交错。另外大量诗作手法陈旧想象泥实,对通感、变形与象征等现代艺术手段借鉴不够……”[15]
谢冕对当代乡土诗的评价也不高。他曾以甘肃诗人姚学礼的诗为例,谈了他对乡土诗的看法:“因为在我印象中我总认为乡土诗是那种比较直接写乡村生活,表现乡村一种生活场景很具体亦难免琐屑的一类诗。另外一个原因是多半的乡土诗都是很传统,都是五言七言体的歌谣式的东西。所以从心底里有些距离。但是一读他(姚学礼)的诗,我发现错了,姚学礼的诗完全不是那种类型。我建议以后应避开新乡土诗这个概念。用陇东乡土诗人称他,是定位不准的,姚学礼应是充分表现了西部生活的现代诗人。从‘五四’运动以来的乡土诗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它总是带着牧歌式的浪漫和激情在原地徘徊。乡土诗作为一种取向,应该寻求新的发展,不应只是一条窄小模式和路子,它不能只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应该和所有的新诗一样,要在大众化、民族化和向民歌学习的基础上而勇敢、敏锐和创造性地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五四’新文学进行对接,以新的生存状态参与世界新诗。……我认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就像姚学礼,他的营养是来自多方面的,可能是一种整合,是一种通融,是一种包容度很大的。如果是一种很偏的东西,或直取现代,或直取古典,或直取乡土,诗就会很狭窄。姚学礼的诗路比较宽广,他是三者兼容。我非常注意诗人和他的土地的关系。我认为海子,他最根本的一点是他的‘麦地情怀’。姚学礼同样有着‘大地情怀’,但他不是表现麦地。我非常注意姚学礼和他的生活本来样子的联系,姚学礼有非常深厚的古典文学的根基,他读了很多书,很多典籍,他是一个学者型的诗人,仅仅说他有乡村生活是不够的。由此我想到现在一些年轻诗人,很聪明很有才情,但缺乏与土地的联系,缺乏和他生活的本来样子的联系。缺少与大高原,大湖泊,大平原,这样一些与大中国绵延不断的土地的联系。另一个缺陷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很少,这往往使他们从一个概念出发敷衍成诗,读了不动人。”[16]
当代新诗创作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这是不争的事实。20 世纪80 年代曾出现了“西部诗歌”的概念,21 世纪10 年代又出现了“南方诗歌”的概念。其间,曾有北京诗人群、四川诗人群、甘肃诗人群、福建诗人群、广东诗人群、江浙诗人群、东北诗人群等诗歌群落交相辉映。对小海来说,地域性诗歌写作或许是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小海曾为自己长期生活在古城苏州而津津乐道,他说:“作为长期生活在苏州这座江南古城的诗人,我也可以略举自古以来吴地广泛流传的一种诗与歌紧密结合的种类——吴歌,来说明两者之间深厚的渊源关系;同时,也能从中窥见古典诗歌中的民间传统及其风格流变。汉语在迁移到吴越地界的江南后,与当地方言融合、杂糅、转化为吴语,唐朝诗人们呼朋唤友游历吴越的同时,也是到吴语区的采风学习之旅。毫无疑问,唐诗得到江南民间艺术——吴歌的鲜活滋养,而呈现出活泼开放、生气灵动、摇曳多姿的气象。”[17]55
我认为:“地域文化对诗人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之前,地域文化,特别是诗人成长和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对新诗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特别是人员流动性较快,那么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诗的影响便有减弱之势,人文地理(文化)的影响渐渐大于自然地理(地域)的影响。同时现代诗歌功能的多元性也会削弱地域文化的影响。今天,当我们在探讨地域文化对新诗创作影响的时候,更需要有现代和开放的心态,更需要有多种预案应对时局的风云变幻。”①2009 年11 月14——16 日,笔者参加了在重庆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上述观点。我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是针对当时出现的地域诗歌热而言的。2008 年,南京一些文艺理论家们专门对新诗创作的“南方精神”进行了专题性研讨,并发表了一些论文。2009 年还出现了两家以“南方诗歌”为主题命名的研究机构,即湛江师范学院的“南方诗歌研究中心”和茂名学院的“南方诗歌研究所”。诗人孙文波对此曾质疑道:“看到网上又有人谈论中国当代诗歌的南方精神。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年头了。不过从发言的人的情况我看到,似乎总是南方出生的诗人更关心地理带来的中国当代诗歌的差异问题。……是不是由于中国诗歌的主要影响力都是由北方传播开来的,因此处于南方的诗人不免在心理上感到在现实中存在着文化的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处于南方的诗人一直在心里有一种对文化中心不在自己生活的地域的焦虑。因此这种焦虑使得南方诗人对地域差异的敏感,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化影响力,成为他们要叙述问题的内在驱动力。……他们所指出的种种不同,除了带有明确的符号化特征外,并没有真正地从文化发展的深层次指出问题产生的关键原因,而更多地只是从地理、气候的差异来谈论问题,譬如一谈到南方诗歌就说它是阴柔的,细腻的,一谈到北方诗歌便说它是粗犷的,刚硬的。但这些真的是中国诗歌南北不同的特征吗?如此简单的划分,在我看来带有机械主义的色彩。……而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诗人,尤其是最好的那一部分诗人,他们的创作实际上对这一文化的所有地域都是有所感知的。他们总能够在非风格化的意义上写出自己选择的题材的最精微感受。因此也就不是在地域的意义上,而是在文化的支配力的意义上达到最有效地呈现作为一种文化的最优秀价值。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南北精神,在这样的诗人身上是贯通了的。”[18]
即使同为“江南诗人”,江苏苏州的小海与浙江湖州的李浔也有差异,这种差异也可能与当年在大学接受的诗歌教育有关。李浔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其诗观是“把诗写得冷静,回到内心,把诗写得凝练,回到诗的本质,把诗写得实在,让诗回到良心。轻松写诗,随心所欲写诗,把诗写得轻松,把诗写得干净,把诗写得清爽,回到诗经时代”②参见李浔:《五年:李浔自选诗二十首》,http://blog.sina.com.cn/u/1280116182。。如他的《早晨的鸟是一滴会飞的露珠》一诗:“早晨你的身体有了淡青的场境/清爽的呵欠湿润的眺望/窗外的小鸟在公共场所调情/这是我梦中无法拓展的细节/杯里有伸着懒腰的春茶/它们惊讶猜疑春是可以冲泡出来的/旱晨的鸟在远处追随旭阳/尽管你已醒了是可以想象了/但梦境中的对话还在/‘是否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是非是磨亮耐心的石头’/这样的早晨是无法安静了/吵吵闹闹的早晨一切都变了/鸟也是一滴会飞的露珠”③同②。。
五
小海对吕德安的欣赏也注定他成为不了波德莱尔的再传弟子。他的亲情诗写作受到了吕德安的影响,他的诗歌的音乐性也是受到了吕德安的影响。我在福建师范大学任教时曾多次与吕德安谈诗论艺。2005 年,我曾邀请他与于坚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作新诗讲座,他讲的正是其代表作《父亲和我》[19]。吕德安的诗歌观念比小海要开放得多,他最早受到朦胧诗人舒婷的影响,舒婷的家座落在厦门鼓浪屿上。吕德安上大学的地方也在鼓浪屿。鼓浪屿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2014 年,舒婷的丈夫陈仲义邀请周伦佑、霍俊明、向卫国等十余位诗评家到鼓浪屿进行文化交流、考察。在这次活动中,陈仲义说到了这样的观点,虽然舒婷没有上过大学,但她读了很多华侨的藏书,那时她接受了比当时许多大学生都要多、要完整的现代诗歌教育。后来,吕德安长年旅居美国,又是职业画家,诗人与画家的双重艺术气质在其诗中得到了交融,如他的代表作《父亲和我》。小海所说的吕德安的“独特的音调”,正是他的中西艺术观念融合的结果:“吕德安从一开始创作,就显示了一种独特的音调,他是‘他们’诗群的重要诗人,可他的诗歌题材与风格、韵致,使得他显得别具一格。他描绘的诸如故乡海滨小镇、旅居海外的曼凯托、福州郊外的山居等朴拙、真实的生活,都有了一种世外感,可能也与他独具的语调无人可以唱和、呼应有关。”[17]58
我近期在阅读小海诗集《男孩和女孩:小海诗集(1980——2012)》的同时,还读了他的诗论集《小海诗学论稿》,尤其是他对吕德安的评论,使我产生了如多年前读他编选的《〈他们〉诗选》时的那种惊喜之感。尽管我不完全赞同他的某些观点,如对吕德安的“隐逸”诗风(传统诗人的处事方式)及“民谣”(传统诗歌的音乐方式)风格造成的“世外感”的过度肯定等,但他的大多数观点还是让我折服的,如“现代汉语诗歌在产生之日就面临着现代汉语生成时产生的同样的问题,就是必须承担回应西方语法挑战和古代汉语转换的双重压力。要有效地挖掘现代汉语的潜力,就要让现代汉语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无论是语法、结构、音韵、拼音系统都在一个动态中不断得到丰富完善,和现代汉语诗歌同样取一个开放的姿态”[17]58-59。宗白华曾说:“近来中国文艺界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新体诗怎样做法的问题……诗的定义可以说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这能表写的、适当的文字就是诗的‘形’,那所表示的‘意境’,就是诗的‘质’。换一句话说:诗的‘形’就是诗中的音节和词句的构造;诗的‘质’就是诗人的感想情绪。……所以我们对于诗,要使他的‘形’能得有图画的形式的美,使诗的‘质’(情绪思想)能成音乐式的情调。”[20]1930 年12 月12 日,梁实秋在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21]1993 年,郑敏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诗歌语言变革与中国诗歌新诗创作》,认为新诗革命者宁左勿右的心态、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及对语言理论缺乏认识给新诗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22]郑敏后来还认为新诗既没有继承古诗的传统,更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2002 年,她在《诗探索》发表了《中国新诗能够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一文,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新诗很像一条断流的大河,汹涌澎拜的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悲的是这是人工的断流。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在创造新诗的同时,切断了古典诗歌的血脉,使得新诗与古典诗歌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同时口语与古典文字也失去了共融的可能,也可以说语言的断流是今天中国汉诗断流的必然原因。……古典汉语是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她极富魅力和个性,如何将她的特性,包括象征力、音乐性、灵活的组织能力、新颖的搭配能力吸收到我们的新诗的诗语中,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23]
如果把以上几段话进行整合研究,就会发现小海这位不在大学从事新诗教学和研究的“民间新诗学者”,在某些问题上的真知灼见,诚可信也。
六
从《男孩和女孩:小海诗集(1980——2012)》的诗集名中也不难看出小海对现代世俗生活的重视,以及对波德莱尔世俗化诗观的继承。于无声处听惊雷,于平凡中显伟大,甚至不需要“惊雷”与“伟大”。在没有英雄的时代只当一个凡人,平静地生活,安静地写诗,只当一片小小的海,眼中只有“男孩和女孩”的诗人,才可能是南方诗人的模样,也是江南诗人正常的“抒情状态”和正确的“书写方式”。小海在《男孩和女孩:小海诗集(1980——2012)》自序中也用了“安静”一词,“相对于其他有成就的诗人,我这几十年基本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写点诗,中间虽有间断,但都不算长,说明我的才能是很有限的,所依靠的可能就是一点耐心与安静。这么说,好像自己有了多少成就似的。其实不然,文学是我终生学习而不可能毕业的一所学校。诗集之所以取名《男孩和女孩》,因为男女是构成人类文明的最基本的一对关系,也是最富有张力,生发与蕴含着极大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一组关系,这也是早期的诗歌中让我迷惑或者说反复琢磨的主题之一,甚至在以后的创作中还衍生出爱与死、生命与影子等等一些有趣有关联性思考”[24]。如这段话所言,他确实有一些英雄梦,如写过诗剧《大秦帝国》和《影子之歌》,等等。在新诗的题材和体裁方面,他都作过大胆而又成功的“尝试”。
作为诗人的“小海”,这种“小”也限制了他的“大气”格局,影响了他的诗的“现代性建设”,他的确有实力能为新诗现代性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写出更多更好的“现代汉诗”。“法国的‘现代’诗无疑开始于波德莱尔。诗人们如英国的艾略特和庞德在他和拉弗格、兰波那里找到了他们正在寻求的现代性。20 世纪的法国诗歌中并没有什么彻底的创新可与艾略特和庞德在1914——1920 年的英国所作的一切进行比较,这一切在数十年前的法国就已经完成了。早在1870 年,兰波就已经宣称:‘应该绝对地现代。’”[25]中国新诗也“应该绝对地现代”,要达到这个宏远目标,需要像法国的波德莱尔、兰波、瓦雷里、布勒东、阿波里耐尔等诗人那样摇旗呐喊,像美国的惠特曼、庞德等诗人那样推波助澜。如果说真要实现“使自己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诗人”的理想,在现代诗歌精神和现代诗歌技法上,应该把惠特曼和波德莱尔作为榜样。如果承认陈敬容是波德莱尔的第一代“中国传人”,那么“根正苗红”,又已“茁壮成长”的现年56 岁的小海是波德莱尔的第二代“中国传人”的最佳人选,完全可以成为新世纪中国诗坛的“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