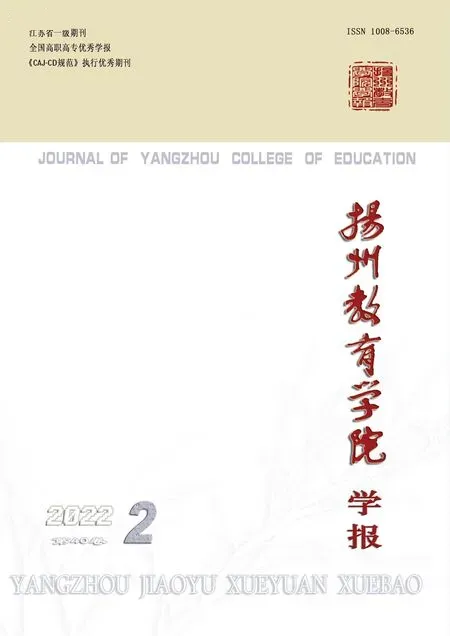“礼失而求诸野”
——艾芜《南行记》的另一个侧面
2022-03-18何晓雯
何 晓 雯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在现代文学史上,总能看到一类特殊的现象,每当知识分子遇到现实或者精神上的困境,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边远地带,形成一种趋同性模式——“礼失而求诸野”。沈从文在湘西世界打造人性的小庙,端木蕻良在科尔沁旗草原寻找民族的血气,周文笔下呈现原始的川康风貌。这类书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奇特的人文景观,使得人们注意到“边缘”的存在,也成为反思中心主体文化的重要参照物。“礼失而求诸野” 的传统思维模式在现代的特殊历史语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知识分子在“边地”追寻着现实出路和精神归宿。艾芜的《南行记》便是这些书写的代表,一直以来,艾芜在困苦与奇特的滇缅地带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归宿,“边地”原始自然的生命形态和强韧的地方气质为他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参照。笔者尝试以“我”与滇缅“边地”的具体关系为背景,以期对“礼失而求诸野”的思维模式有所审视和思考。
一、边缘的知识分子——“我”
《南行记》基于艾芜南行的真实经历,文本中的“我”几乎等于艾芜本人的真实体验和思考。尽管南行的实际处境是艰难的,但是“我”觉得“仍然有味,但这味,需要另一种心情来领略”[1]255,艾芜是有意识地在漂泊。艾芜自己曾直言:“我是逃避包办婚姻出走的。”[2]但更多的还是受蔡元培“劳工神圣”口号的影响,由于北京上海等地的工读互助组织已经没有了,艾芜便“到南洋群岛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3]。艾芜的南行意味着“出走”,即离开原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寻找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去处。
但是到了云南,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最初半工半读的幻想破灭了,几乎变得一文不值,为基本的生存焦虑,自嘲偷吃烧饼的本事都不如叫花子。“我”被生活收购了,精于生存之道成为了必要前提,甚至对知识分子的身份作出了部分妥协。“我”可以为了一份工作,假装熟悉街道,伪造有铺保,谎称精通厨艺,还将白日与野猫子假装夫妻偷东西称为是“新鲜有趣的事”[1]159。在滇缅的路上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读书更是难上加难。诚如艾芜文中所说的:“围绕我们的社会,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本来面目的好人。”[1]15
除了基本的生存危机,“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也被否定了,不同于以往作品中处于启蒙和中心位置的知识分子,“我”在这里被边缘化了,觉得自己“像被人类抛弃的垃圾”[1]26。开篇《人生哲学的一课》,“我”面对墙上的诗句,“提不起闲情逸致来,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作的好东西”[1]12。这句话其实可以映射“边民”对于知识的态度,面对生存的疾苦,知识成了有闲者的专利,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又有何条件去学习知识。同样是面对知识,《三峡中》的小偷们直言:“书上的废话,有什么用呢? 一个钱也不值,……烧起来还当不得这一根干柴。”[1]154而《茅草地》中的洋学堂和店老板即便愿意请教师,“我”在那里也没有获得尊重,而是算计着如何压榨“我”身上的价值。“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价值在滇缅之地没能得到发挥。
即使知识分子的声音较弱,但并非完全失语,触及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时,“我”仍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些独特的声音提醒着人们在这“边地”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世界。《松岭上》中的老人和《三峡中》的老人与小偷们都曾给予“我”片刻的温暖和自由,但是“我”仍选择离开,“他老人家做的事情,是可原谅的,但我却不能帮他那样做了”[1]109;“今天去干那一件事,无非是由于他们的逼迫,凑凑角色罢了,并不是另一个新生活的开始”[1]155。尽管“我”在情感上同情这些生活的受损者,但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与艾芜心中关于“另一个新生活”的设想是相悖的,因此“我”不断地选择离开。
从艾芜对当时云南时局的看法,可以窥得他对于理想的“另一种新生活”的构想:“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全是骗人的,应该变出一个好的环境,能够使我们这类穷人苦人,也会真正得到幸福和尊敬。”[3]336艾芜期待有一场实质性的革命来建设新的社会环境,使得底层受辱者获得平等和幸福生活的机会。同时,艾芜在南行中时刻不忘书籍,其对于“新生活”的追求与知识有关,这必定是基于现代知识建立和维持起来的新社会。这种对社会的展望虽然带有左翼作家阶级话语的痕迹,但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艾芜与“边民”不同的理想,这也是造成两者不同的重要原因。
艾芜借由“新生活”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肯定了自己对于现代新生活的构想和追求,虽然“我”同情并理解他们的选择和遭遇,但无法认同他们关于生活的认识。原本是弱势的、边缘化的“我”以一种曲线式的方式获得了特别的话语权,使得“我”的追求和理想获得了主体位置。
二、启蒙让位于“文野之别”
如前所述,“我”在南行中处于一种边缘的状态,但仍坚持对“新生活”的选择和追求,这就是“我”与那些边民最不一样的地方。滇缅之地的底层人追求的是当下最基本的生存满足,他们很少有关于另外一种新生活的构想,而“我”不断选择离开和出走的姿态就已经呈现出了与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如果说“边地”人民的生活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圆形,那么“我”追求的则是前进的、带有超越性的发展。这种线性的思维与五四以来的进化论史观不无关系,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对此,汪晖曾经说过:“这种进步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中。”[4]因此,“我”南行的意义和追求在更大层面上可以纳入现代性的追求,要完成这一设想,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选择对群众进行启蒙,在民众中普及现代的价值观。
但奇怪的是,艾芜无意像“五四”知识分子一样对群众进行启蒙。或许可以说艾芜迫于生存的压力,暂时放弃了启蒙?但是当野猫子逼迫他留下,他也不做任何解释,只是重复表达自己要离开的述求,而不谈自己关于理想社会的追寻。当他们否定他“读书”的时候,“我不愿同老头子争论,因为就有再好的理由也说不服他这倔强的人”[1]155,艾芜不仅放弃启蒙,连为自己的选择辩解都放弃了。他更多地是在学着如何与这片土地相处,更像一个旅客、过客,而非寄生者、征服者或者教育者。
或许艾芜本人能感受到“野”文化的生存哲学与现代启蒙话语之间存在的裂痕,因此在现实中放弃与小偷们进行对峙。这种矛盾不是源于“族群”,更不是生理上的差异,而是文化,“人的本性,是由文化,即习俗塑造的”[5]。对于文化应当关注其基于环境、内部社会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状态。“边地”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不仅是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构成,更重要的还是文化意义上的“边地”。艾芜南行的滇缅之地,一直以来被视为华夏的边缘。无论是传统的汉文化还是“五四”的现代文明都离这里很远,在滇缅“边地”上流淌的是属于近代云南“边地”独特的生活逻辑。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存原则,“我”不过多地干扰他们原本的世界,更多的是经历着。在《寸大哥》中,“我”曾表示愿意赶马,但是“我就怕,赶一赶的,赶入了迷”,对此,赶马人寸大哥则认为:“你怕赶入了迷,就忘记要做别的大事情了……你们读过书的人,真不好,心太大了!”[1]338很显然,读书人的身份把“我”与他们拉开了距离,他们更关注眼前的现实生活,为基本的物质生活奔波劳碌,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艾芜而言,他们没有以进化为核心的“未来”。
对于艾芜来说,流亡不仅是真实的境况,更是一种不能适应的悬浮状态。他在四川成都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选择“出走”并不意味着切断和抛弃“原乡”。而南行让他感受到了不同于现代启蒙的话语,正是这种“文野之别”,让艾芜明白对话的困难,暂时放弃了启蒙,唯一的方法就是离开。“虽然,他们有着别个友人所没有的最大的缺点,赌钱、走私、吃鸦片、以及迷信命运、屈伏于牛马的生活,但我知道这不能影响我,而且我能像糠皮稗子沙石一样地簸出去,因此,我便不知不觉地原谅他们了。”[1]254“边民”之于“我”都是过客,艾芜在表达自己的态度和选择的同时,也暴露了两种文化存在的横沟和尖锐对立,让“我”频频沉默和离开。
从艾芜与“边地”流民之间存在的尴尬和不和谐的状态可以发现,带着现代启蒙话语的艾芜以漂泊流浪的状态进入“边地”,虽然在现实中与“边地”流民们处于同一层面,但是“我”无法认可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则无法理解“我”对于新生活的渴求。两者存在着难以对话的关系,即艾芜所代表的现代话语与“边地”流民所代表的生存意识之间的隔阂,所谓的“文野之别”在这里强烈地显现出来,粉碎了启蒙的可能性,造成了文本深处的分裂。
三、“礼失而求诸野”思维模式的反思
一般说到“文野之别”时,往往强调的是基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区分出来的“文”和“野”。而滇缅之地长久被视为边缘,相对于所谓的“文”,其往往被定义为“野”,被认为处于较低的文明发展程度。然而在《南行记》里,所谓的“文野之别”却呈现出了相反的形态。“我”欣赏他们生命的强韧,尤其是在《我诅咒你那么一笑》中,“我”讨厌自己的懦弱,而“羡慕勇敢坚毅的人”[1]301,他们是生活的强者,充满了生命的韧性。“我又如同一个淘金的人一样,我留着他们性情中的纯金,作为我的财产,使得我的精神生活,永远丰饶又富裕。”[1]254仿佛我才是那个“被启蒙”的人。在这里,“礼失而求诸野”又再一次发挥了作用,“试图用‘边地’的多元价值去疗救和置换衰朽的主流价值,这种对于‘边地’的发现,某种意义上将边缘文化因子纳入到想象的共同体之中,也是在重新发明和塑造一种新的‘中华民族’文化”[6]。艾芜在“边地”发现了现代社会建设所需要的精神力量,由此顺延,“边地”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参照之一。
这种对于“边地”人民生命状态的肯定,艾芜并非个例。早在这之前,沈从文就致力于借湘西呼唤健康的人性,“他们在进不能兼济天下时,或退于道,或逃于禅,都视山林田园为人的现世的最终家园。这种行止路线、取舍标准发生在文化层面的守护时,则体现为‘礼失求诸野’的思维习惯”[7]。但是,联系当时社会革命的实际情况,他们所描绘充满力量色彩和牧歌情调的乡野生活,不仅不能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反而会有被残酷现实摧毁或者玷污的可能。而艾芜笔下“边地”人民那种强有力的生命血性更有可能演变成社会斗争的实践力量,这不仅是艾芜创作的独特之处,更是“边地”“野”文化的独特魅力。
闻一多来到西南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你们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的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得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8]从这个角度出发,传统的“文野之别”被颠覆了,不再是野蛮被文明征服,而是“边缘文化动力”[9]在现代文明的前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性社会是一种被肯定的构想,而“边地”所拥有的强有力的生命力又是理想的精神资源。
“礼失而求诸野”的思维模式确实重新发现和肯定了“边地”文化,将其纳入中华民族“想象的共同体”中,然而当现代主流价值与“边地”文化并置时,两者存在的裂隙更明显。艾芜的《南行记》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从上述的“文野之别”可以看到,“文”与“野”两者之间存在实际对话的困难,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并非想象中那么圆满。启蒙神话在现实的“失落”,说明了在顽强的“边地”文化价值下,现代话语要想“进入”是何等的困难,“礼失而求诸野”这一路径究竟能在多大意义上实现,是有待商榷的。
同时,当我们循着“礼失而求诸野”的思维模式,强调“边地”作为理想精神存在的价值时,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中心在向“边地”移动,“边地”获得了某种重心,但是从深层看,却是整个“边地”在向中心位移:从“边地”汲取精神力量的中心不是“边地”化了,而是为了中心的发展并且将“边地”同化。艾芜肯定“边地”生命力的强韧和勇气的精神,与其关于“新生活”设想的实现息息相关,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种力量之源,而“边地”也难以摆脱历史赋予的宿命,终将走上中心所追寻的现代化。“礼失而求诸野”在强调中心向“边地”汲取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力量,还需要注意这种对话产生的变体,其在本质上是另一种形态的中心化。“礼失而求诸野”潜藏着强烈的悖论性:一方面它挖掘了“边地”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将其与中心同化,弱化其异质性。
随着“文野之别”的颠覆,一直以来的现代中心主流意识也被解构了。其实,所谓的“文野之别”这种说法也并非没有问题,当承认有一个所谓的“边地”存在时,就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有中心和非中心的存在。王明珂在谈到中国“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时,曾做出一个形象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10]当“边地”脱离中心时,“边地”也有成为中心的可能性,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的“边地”存在。因此,面对“边地”时,应当警惕落入这样的陷阱。无论是所谓的“文”还是“野”都是构成中国现代进程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进程本就没有一个唯一的、统一的内核,而是由许多不同文化组成的。
近代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过程是复杂多重的,其中,“礼失而求诸野”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其涉及到“边地”与“中心”对话问题,“边地”作为“中心”的一部分的同时,也有其独立性。要注意两者是在何种层面上进行对话,在这之间,并非一个简单的“边地”对“中心”的补充,更不是“边地”被同化的过程。总之,“礼失而求诸野”是我们今天在寻求新的多元一体格局中需要去重新思考的一种文明构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