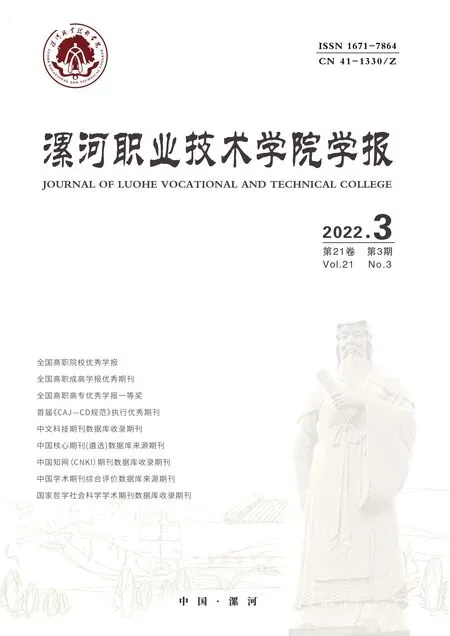徐渭与毛宗岗对“祢衡骂曹”故事接受的比较研究
2022-03-18杜巧云蒋小平
杜巧云 ,蒋小平
(1.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合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范晔在《后汉书》中著有《祢衡传》,记述了“祢衡骂曹”的史实,孔融荐祢衡于曹操,曹操召为鼓吏,祢衡裸衣羞辱曹操,孔融从中斡旋,祢衡假意向曹操认罪,借机痛骂曹操。《世说新语》也记录了这一矛盾冲突,曹操召祢衡为鼓吏,祢衡作《渔阳》一曲明志,曹操不得已放走了他。随着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流传演变,三国人物也变得丰满生动起来,“祢衡骂曹”成为文人创作的素材。明代徐渭与清代毛宗岗都对“祢衡骂曹”的故事进行文本再创作,都是基于对“祢衡骂曹”故事的接受,却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和理解。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并非由作者独立完成,“它的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而意义的实现则是靠读者通过阅读对之具体化,即以读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空白处填充起来,使作品中的未定性得以确定,最终达致文学作品的实现。”[1]4-5可见,徐渭与毛宗岗再创作的文本是对“祢衡骂曹”的故事文本在另一个时代的实现,徐渭和毛宗岗用自己的形式完成了对原故事的接受。
一、徐渭与毛宗岗对“祢衡骂曹”故事接受的比较
《狂鼓史渔阳三弄》为徐渭《四声猿》中的第一折戏,他精思巧构,用杂剧的形式演绎这一传奇故事,成为“猿鸣四声”中的初啼,令人振聋发聩。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徐渭的《四声猿》先后问世,二者皆借“祢衡骂曹”大做文章,将这一传奇故事赋予了别样意义。自此,祢衡凭借着孤标傲世的性格、惊世骇俗的行动以及超凡脱俗的文学造诣成为文人心中的典范。清初文学批评家毛宗岗在批注《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对“祢衡骂曹”这一章节大费笔墨,言语之间爱憎分明:“读徐文长《四声猿》,有祢衡骂曹一篇文字,将祢衡死后知识,补骂一番,殊为痛快。”[2]153赞美之词洋溢于表。同样是以“祢衡骂曹”这一故事为题材,细究之下,罗贯中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徐渭《四声猿》、毛宗岗《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三者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徐渭《四声猿》创作时代相近、内容相似、形式不同,罗贯中在前人基础之上丰富了故事的内容,用小说的形式构建了矛盾冲突,交代了事件的前后因果,祢、曹二人形象也有了更加清晰明了的定位,徐渭则用戏剧的形式创造性地将故事发生的场景设于阴曹地府之内,时间定于祢、曹二人百年之后,事情起因源于判官察幽欲重现当日骂座的景象则“留在阴司中做个千古的话靶”[3]2,可以说,罗贯中与徐渭是将同一个故事用不同方式表达出来,善于文学评论的毛宗岗则对此二人的作品都加以评点。本文旨在分析《四声猿》接受史,故忽略嘉靖本《三国志演义》,仅对毛评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徐渭《四声猿》之《狂鼓史渔阳三弄》进行比较。
首先,对比毛宗岗与徐渭关于“祢衡骂曹”故事的处理,可以看出二人对“阴司审曹”一事有些许观念差异。毛宗岗以祢衡衬托曹操奸诈,徐渭则以曹操反衬祢衡奇绝。毛宗岗自曹操出场,便多用鄙薄之词,称为“曹贼”,在评点本第二十四回中,将原章回名“祢衡裸体骂曹操”改为“祢正平裸衣骂贼”,春秋笔法可见一斑。毛评本《三国志演义》将蜀魏吴三国争斗作为主线内容,将刘备、曹操、孙权作为主要人物,祢衡只是一个起辅助作用的角色,为塑造主要人物的形象而服务。因此,毛宗岗对祢衡着墨并不多,对他的形象塑造也比较片面单一,只是通过抬高祢衡来丑化曹操,祢衡与杨修都是为表现曹操嫉妒贤才、不得人心的“工具人”。徐渭的《狂鼓史渔阳三弄》以祢衡为主角,在阴司连鼓十通,用十一支曲子痛骂曹操虚伪狡诈、篡权夺位,以曹操偷奸耍滑,毫无枭雄形象来反衬祢衡不劣方头、卓尔不群的狂士形象。从剧名《狂鼓史渔阳三弄》就可以看出,祢衡才是徐渭突出塑造的主角,那么作为衬托主角的曹操就不需要多余的笔墨渲染。由此可见,曹操形象的塑造不是徐渭创作《狂鼓史渔阳三弄》一剧的重点,祢衡才是徐渭推崇歌颂的典范,只有这样,他的形象才有血有肉、丰满立体。徐渭、毛宗岗二人刻画的侧重点不同决定了他们在对素材的处理不同,传达出不同的价值观。
其次,阴司审曹并非徐渭《四声猿》所独有,毛宗岗在评点中也提到屠隆所作《昙花记》中“阴司审曹”的桥段,对于这两部剧作中此桥段的运用,毛宗岗都持肯定态度,他赞徐渭《四声猿》“将祢衡死后之事,补骂一番,殊为痛快”[2]153,赞屠隆《昙花记》“古来缺憾不平之事,有欲其事以补之矣”[2]146。毛宗岗将曹操未得恶报视为憾事,与“邓伯道父子团圆”“荀奉蒨夫妻偕老”“屈大夫重兴楚国”“燕太子克复秦仇”“王明妃再入汉关”“侯夫人生逢炀帝”“岳武穆寸斩秦桧”“南霁云立灭贺兰”八件事并列,认为世间不平事须得弥补以慰人心,可见他心中秉持善恶有报的原则,希冀阴间能惩恶扬善,一泄胸间怒火。然而,徐渭善恶有报的观点并未贯穿全剧,他复杂深刻的宗教观念在《狂鼓史渔阳三弄》中初见端倪,剧中祢衡在阴司复现当日骂曹情景,语言犀利,句句在理,似有报仇雪恨之意,曹操迫于判官察幽威势,奴颜婢膝、形容猥琐,丞相之威荡然无存,徐渭将二人地位颠倒,读之令人痛快至极,可是祢衡在一舒怨气后,却道出“大包容,饶了曹瞒罢!”[3]10被曹操迫害致死的祢衡原本充满怒火,可痛骂之后反替曹操求情。“戎想眼前业景,尽雨后春花”[3]10解释了祢衡愿意尽释前嫌,替曹操求饶的原因,“若没有狠阎罗刑法千条,都只道曹丞相神仙八洞”[3]11,如此因果报应的结局给徐渭和对曹操、严嵩此类奸臣不满的群众带来心理安慰,长吐一口恶气。
二、徐渭与毛宗岗对“祢衡骂曹”故事接受差异的原因
德国接受美学学者姚斯将接受过程分为理解、阐释和应用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在阅读过程中密不可分,理解是阐释的基础,应用是在诠释过程中完成对读者所寻找问题的回答。徐渭、毛宗岗二人接受结果的差异就是在这三个接受阶段中形成的。
(一)二人期待视野的差异
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由于自身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形成了独有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情趣,这种由文学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称之为“期待视野”。初级接受阶段便是由期待视野去掌握文本意义的过程,徐渭与毛宗岗生于不同的时代,长于不同的环境,自然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在对“祢衡骂曹”的接受过程中形成了同而有辨的理解差异。徐渭、毛宗岗都是古代封建制度中的文人,他们生不逢时,都未能在仕途有所成就。徐渭年少便久负盛名,诗文书画无一不通,与解缙、杨慎并称为“明代三才子”,被时人敬重,年少中举名扬天下,然而屡进科场都名落孙山,接连遭受横祸,家道中落,年近四十才被浙闽总督胡宗宪赏识,召入府中成为幕僚。好景不长,随着胡宗宪的倒台,徐渭整日惶恐不安,生怕受到牵连,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精神恍惚,九次自杀未遂后苟延残喘。坎坷的命运不仅毁掉了徐渭的身体,更是摧残了他的精神意志,冥冥中竟产生了幻觉,疑心妻子张氏不贞,挥刀将其杀害,在狱中度过了七年。明神宗即位大赦天下,徐渭出狱,此时的他已然耗尽气力,晚年游学交友,最终潦倒离世。徐渭一生颠沛流离,纵然才高八斗却没有建立一番功业,这与毛宗岗的经历颇为相似。毛宗岗生于明崇祯五年,与其父同为文学评论家,父子才学过人,将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增删修订、整理回目,形成了后来盛行于世的一百二十回目的《三国演义》,深受民众喜爱。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毛宗岗未能得到一官半职,毕生致力于文学批评。“学而优则仕”是历朝历代文人终身追求的目标,科举考试也是文人改变命运、证明才学的最好方式,毛宗岗虽然曾参加由监察御史李嵩阳主持的科试,被录取为长洲县第三名,但却和其父亲毛纶一样终身未仕,毛纶一生致力于文学批评也给了毛宗岗很大的影响,在《第七才子书》中,他提出了“补世说”的创作理论,在作品内容上,主张追求“文意之妙”,即提倡教化[4]。毛宗岗同徐渭一样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布衣文人,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使得他们对“祢衡骂曹”故事有着别样的共鸣。祢衡之意气、胆魄都让他们为之折服,“骂曹”的痛快、酣畅都让他们心潮澎湃,对祢衡的欣赏是他们在初级阅读过程中最直接的接受。
(二)在故事中寻找不同的现实答案
反思性阐释阶段建立在审美感觉阶段之上,接受者“赋予文本以一个超出意义视野之外的意义或曰文本的意向性”[1]178,此时读者需要让原故事脱离原定的时空,确定文本的具体意向性,将其作为某些问题的回答。“理解意味着将某种东西作为答案去理解”[1]179,对“祢衡骂曹”的故事人们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理解,反思性的阐释接受是在初级接受之后,读者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形成的对问题思考的答案。那么,徐渭和毛宗岗在“祢衡骂曹”中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得到的又是什么答案呢?徐渭一生命途多舛,他的不幸大多是冥冥之中的阴差阳错。《狂鼓史渔阳三弄》是他的中期作品,此时的他还未经历太多的挫折,对人生充满斗志和希望,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祢衡与青年徐渭的形象隐隐重合。此外,徐渭与同时期义士沈炼相交甚笃,并称为“越中十子”,两人是知己好友,沈炼为奸臣严嵩所害,徐渭痛心不已,这与“祢衡骂曹”故事竟有异曲同工之处。沈炼死后,徐渭多次写诗悼念,将沈炼与祢衡并提,夸赞沈炼不畏强权、刚正不阿。徐渭对“祢衡骂曹”故事的接受重点在才子祢衡宁折不屈、不劣方头上,也借此表达读书人对才子的欣赏。毛宗岗生活于明清之交,身为汉人,面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自然心有不平,他在意的是民族气节、纲常伦理。“祢衡骂曹”故事中的曹操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篡权者,他虽为丞相,实则大权在握,形同皇帝,为天下人所不齿,祢衡绝不事曹的原因便是如此。毛宗岗一面欣赏才子祢衡的刚正不阿,一面将历史中的曹操与现实中的统治者形象重合,他接受的重点在曹操的篡国行为之上。
(三)“祢衡骂曹”故事再创作的实践
历史的阅读早已不再局限于文本的时间与空间,在第二阶段读者在阅读中寻找现实的答案,在第三阶段读者认识文本对现实的指导价值,这使得原文本超越历史,凌驾于时空之上,应用于现实。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曾说:“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5]因此,徐渭、毛宗岗都将对“祢衡骂曹”故事的接受化为再创作的内容。正如前文所述,曹操形象的塑造并不是徐渭创作《狂鼓史渔阳三弄》的重点,祢衡才是徐渭推崇歌颂的典范。他借祢衡死后升天慰藉自己仕途坎坷的凄凉之感,咏出“文章自古真无价”[3]9之句,抬高祢衡身价也是对自己未来的期许与肯定。《狂鼓史渔阳三弄》以祢衡为主角,让祢衡痛骂曹操,塑造祢衡的狂士形象,以曹操奸诈反衬祢衡卓尔不群。此外,徐渭生活在嘉靖至万历年间,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严嵩独揽大权长达十七年,百姓怨声载道,其中不乏有识之士上书弹劾,沈炼就是这些心系国家的义士中的典范。只可惜严嵩权势倾天,沈炼被迫害致死。“祢衡与沈炼皆是因言遇害,且曹操借黄祖除掉祢衡与严嵩借杨顺、路楷之手除掉沈炼这一行为相似。”[6]《狂鼓史渔阳三弄》借骂曹操之名痛骂严嵩,借歌颂祢衡之名纪念沈炼,徐渭用犀利笔法寄托对友人的欣赏与哀思,毛宗岗则借祢衡骂曹以抒不平之气,宣扬正统思想。毛氏父子在评点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将自己的价值观赋予原书也是二人评点的目的所在。毛氏父子在评点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时,通过对嘉靖本的增补删改,以强烈的“拥刘反曹”思想倾向为出发点,以民间道德伦理评判为准绳,删掉了嘉靖本中赞誉曹操的文字,增加了一些情节和评点加强对曹操批判,曹操也由嘉靖本中性格复杂、形象丰满转变成了毛本中活脱脱的奸雄典型[7]。毛宗岗在评点中对蜀汉人物大加赞扬,对魏晋人物冷眼相待,态度鲜明,丝毫不掩喜恶。在对祢衡的评价中,毛宗岗又别出心裁地做出两组对比,一是将祢衡与杨修、孔融对比,三人皆被曹操所迫害,唯独祢衡刚正不阿,既不事曹亦不与曹周旋,桀骜不羁,品性最高,因此最先被杀。曹操阴险狡诈,毫无容人之度,接连害死英才。二是将祢衡与陈琳相比较,陈琳以笔骂曹终又降曹,祢衡以口骂曹绝不事曹,以证明曹操借黄祖之手杀祢衡是有意为之,并非是为挫其锐气的无心之失。毛宗岗赞誉祢衡愈多,反衬曹操奸恶愈明显,在他眼中,曹操固然谋略过人,但多用于虚伪阴险之处,他为不落人口实,博得爱才的名声,即便祢衡多次羞辱他,他仍假装大度,假他人之手杀祢衡,“奸雄”之称实至名归。
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接受的结果也是千差万别,将接受的过程细分的三个步骤探究徐渭、毛宗岗二人创作差异的原因,同时也在更深入地研究后世对“祢衡骂曹”故事的接受。不同的期待视野造成了徐渭、毛宗岗二人的不同困惑,面对不同的人生困境,徐渭、毛宗岗在历史典籍中寻找答案,分别对“祢衡骂曹”故事做出了解释。他们对“祢衡骂曹”故事的接受同而有辨,既一致“拥祢反曹”,希望曹操阴间受到严惩,又因为秉承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徐渭站在不得志的文人角度,对于恃才傲物的祢衡既钦佩又向往,借着戏剧创作寄托着人生理想[8];毛宗岗则是站在民族大义的角度上,将祢衡塑造成威武不屈的忠贞义士,用小说创作承载家国情怀。对于结局的处理,受到佛学思想影响的徐渭不再坚持对曹操来世报应;毛宗岗以小说反抗现实,必然针砭时弊,对篡权夺为者的惩戒不留余地。因此,徐渭创作突出祢衡的锋芒万丈,也愿意宽恕曹操,毛宗岗更关注曹操的奸恶奸诈,借虚构的阴司受刑情节以泄心头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