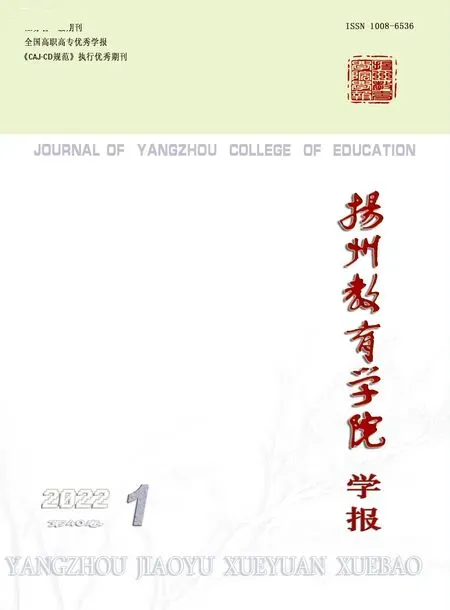“官与私”记录视角下北洋政府修约外交再考
2022-03-18夷宸昊俞嘉懿
夷宸昊, 俞嘉懿
(1.辽宁大学, 辽宁 沈阳 110136; 2.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宿迁市委员会, 江苏 宿迁 223800)
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活动,主要指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基于一战后的国内外政治环境所带来的优势条件开展外交行动,尝试摆脱不平等条约的运动。逐渐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的长期侵害,社会各界利用当时日益兴盛的大众传媒——报刊,针对“改订新约”展开思考与实践,进而对当时进行中的修约外交活动产生影响。
早期学术界也关注到报刊等媒介形式对北洋政府外交情况的影响,着重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并受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北洋政府无力真正维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对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总体持否定态度。
近年来,学界开始辩证看待这一时期北洋政府受到的舆论影响,既认识到北洋政府在时代潮流下顺应民意外争国权的努力,也对舆论压力左右政策、阻碍外交工作的情况施以关注。
总体看来,研究者惯于使用商业报刊的批评视角切入研究,史料的运用还是以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出版物为主,对原始资料的发掘相对欠缺,尤其是对政府刊物的利用明显不足。本文将充分调用“官与私”两种视角,将北洋政府外交部的直属刊物《外交公报》与同时期知名商业名刊《大公报》进行对比分析,重考其修约外交时期的相关工作。
一、修约外交中“官与私”的话语概况
关于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活动在《外交公报》和《大公报》的相关报道,其话语声浪伴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波动态势。
(一)《外交公报》中的修约外交
《外交公报》创刊于1921年7月,正值华盛顿会议(1921.11—1922.2)筹备期间,停刊于1928年北洋政府被南京国民政府取代之时。《外交公报》由北洋政府外交部图书处发行,由当时的外交官员撰稿,是北洋政府外交部的直属刊物。
《外交公报》中关于修约事件的记录主要以三种形式呈现:其一是以新闻稿的形式描述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这种形式的篇目数量较少;其二,即大多数情况下直接刊登围绕着某一事件或条约产生的系列公文,以外交部为收、发文的主体,常用文种包括呈、函、照会;第三种情况是将修改或新签订的条约全文直接刊登以作公示,例如华盛顿会议期间签订的《九国公约》[1]、此后签订的《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2]等都能够在《外交公报》上找到原文。
(二)《大公报》中的修约外交
《大公报》自1916由王郅隆接手后,政治倾向于安福系,1920年段祺瑞政府下台,《大公报》的政治倾向渐与中央政府不和,其代表的知识界意见与外交部门代表的文官团体的矛盾逐渐显露。1926年《大公报》整顿改版,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理念,其社评、星期评论、新闻通讯、副刊四个栏目合称“四绝”,在当时的新闻界居于领军地位。《大公报》由此成为观察在野舆论反对派对中央政府意见的窗口。
华盛顿会议期间,大公报总计刊载了28篇报道;自1925年北京政府照会八国商讨修约起至1928年,《大公报》总共刊登153篇文章涉及修约事宜,排除其中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全中国合法中央政府后发布的45篇,讨论北洋政府修约外交的文稿为108篇,其中1925年为10篇,1926年为37篇,1927年为38篇,1928年北洋政府颠覆前为13篇。
二、典型事件中“官与私”的话语碰撞
20世纪20年代的北洋政府,一批拥有共同留学经历和外交经验的外交官员们,化外交资历为政治资历,进而进入内阁,在文官系统中居于要职。其政治资源不以武力为背景,因此也不随军事力量的兴替而转移,政治资源的稳定保障了他们政治地位的相对稳定和“超然”的地位。不同于传统政治派别,他们没有明确的领袖、组织、政治纲领,因而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心目中政治理想的承担者。
然而也正因为外交系官员的政治资源缺乏军事力量的保障,在当时军阀政治的背景下,其政治表现软弱,其政治理念和外交手段,与知识分子乃至社会各界的期望不尽相同。这一矛盾在几个典型事件中均有所表现。
(一)“有条不紊”中的“斤斤微利”——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作为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修约外交活动的起点,各方对此次会议普遍抱有较高的期望。
《外交公报》中记录华盛顿会议期间相关事宜的篇目近50篇,从记录中可以看到北洋政府对这一重大外交事件的重视:事前设立太平洋会议筹备处,制定筹备处章程,联络各国获知美、日等列强之态度;会议期间将会议实况尤其是涉及中国的内容呈报总统;会后则记录了会议各项条约,成立善后委员会落实会议议定事项。围绕会议开展的各项工作看起来都有条不紊。
《参与太平洋会议中国全权代表恭报该会议大概情形呈(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大总统)》中不难看出中国在会议进程中的被动地位。一战后远东地区国际关系的核心矛盾是美日矛盾,凡尔赛会议外交失败,国民多归罪于皖系军阀政府的亲日外交政策而对美国抱有善意,国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的极度亲美。外交不能独立自主而依赖列强必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戏称美国国务卿修斯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最高全权代表”[3],中国的诉求实际上只能顺应美国的国际战略;另一方面在华盛顿会议中,中国外交官也确实成功地利用了国际均势和世界同情,让中国取得了超越当时国力的突出外交成果,成功收回了包括山东主权在内的许多在晚清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权力。
但这种暂时性的外交成果背后存在隐忧:自袁世凯死后,北洋势力群龙无首,直皖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其内部愈发分崩离析,北洋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正在不断丧失。中央政府的衰败意味着对于列强干涉的抵抗能力的削弱,也就意味着外交对国内政治影响力的增强,这直接导致了外交系官员在此后的北洋政府中身居要职。但正如《大公报》所指出的:各国代表必须“以开明之态度,互相让步,力矫前非……奠世界于磐石之安。否则徒效利用之故智,捭阖纵横,斤斤于目前之微利,华盛顿会议将成为一种滑稽,而各国外交政策之愚昧,将益暴露于世矣”[4]。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未能真正解决列强纷争、构筑世界和平,该体系仍然是各国争夺自身利益碰撞妥协的产物,是列强从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走到谈判桌前最终达成的短暂平衡。在国内既无强大国家力量的支持,国际上则仍要面对列强各怀心思、暗流涌动的局面,华盛顿会议上所取得的外交成果缺少了稳定的根基,也影响了后续外交工作的开展。
(二)“容受”抑或“软弱无能”——激进化的中比修约
1926年,《中比条约》期满,外交部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商讨修约事宜,该约至“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止一律失效并应缔结新约,以代旧约”[5]。按照中比条约第四十六条规定,比利时拥有单方面修改条约的权力,但比利时作为一个小国,又在一战中损失惨重,并无威胁中国的军事力量,选择了联络英国共同对中国施压。按照《天津条约》,中英双方都有修改条约的权力,若按照此案类推,英国唯恐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6],为此英比联合向北洋政府施压。九月二日,外交部向比利时政府提出“临时办法”五条为缓冲,其要点有三:第一,施行期以六个月为限;第二,承认彼此关税自主,以中国享受比利时最低税额为条件交换比利时享受“通行税率”;第三,缔结新约应抛弃领事裁判权,现行领事裁判权“暂予容受”[7]。
此时的美英列强认为一味地指责中国提出的临时办法,不但“正在削弱比利时的地位”,而且使列强各国陷入“窘境”,这种状况将“有利于中国”[8],这是列强不愿意看到的。而比利时在华工商业代表同样认为通过高压解决中比争端将不利于比利时的在华企业,因而向比利时外相施压。国内外的压力迫使比利时政府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临时办法”,但中比双方对是否限期订立新约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1926年4月,段祺瑞通电下野;5月,颜惠庆内阁上台,列强借机拖延正在开展的关税会议等修约会议。5月中旬,颜惠庆询问各国驻东郊民巷公使代表团的领袖公使欧登科各国对关税会议的态度,欧登科答复:“关于关税会议,外国代表决议,如中国方面不提议开会,各国代表则不要求开会,其意无他,不过俾摄政内阁可以从容布置一切。”[9](1)此话载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和馆会晤问答》,出自1966年的《外交档案》,档案号03-41-009-03-004。此后关税会议迁延日久,北京政府对中比修约的态度则愈发强硬,可以看作是在政局动荡中通过外交手段显示中央政府权威的一种手段。
伴随着《中比条约》期满,国内外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声浪日益高涨,旅欧侨民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全国学生总会、全国工商联合会、上海总工会一致通电发函反对临时协定;各地报刊也纷纷报导社会各界的废约运动,《大公报》毫不留情地抨击北京政府的外交工作“软弱无能,令人发指”,其他报刊杂志也一致要求北京政府采取强硬态度。舆情已经从呼吁变为抨击,外交磋商仍未见进展,国内政局仍处动荡之中,最终多方面的矛盾合力迫使北京政府选择了单方面废止《中比条约》,公布《中比条约终止宣言》[9],提出:中国人民对于列强“不满及纠葛之原因”,源于“近百年来,中国受压迫而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屡次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希望缔结“以平等相互主义,及彼此尊重领土主权为原则”的新约,对于现行不平等条约,“于期满时通告终止”,对于比利时政府提出要将此案诉诸国际法庭一事,《宣言》中如是解释,此次废约“实出诸中国对外欲达同臻平等关系之志愿,夫一国人民之志愿,焉能认为可付法律裁判之问题耶”。
《宣言》既出,很快在国内收获好评,《时报》评论:“政府此举,可谓为破天荒之大英断。”《申报》报道称:“外交界视取消中比条约为中国多年来最重要之事。”[10]《东方杂志》高度评价此事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第一声”[11],主办此事的外交官顾维钧个人声望水涨船高,而停滞的中法、中日之间的修约谈判也再度启动。
讽刺的是,对于废除条约之后理应实行的关税自主,北洋政府并未有任何准备,没有颁布国定税率,而对于各租界内的领事裁判权,此时的北洋政府也无力收回。次年初,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占领了长江流域,国民政府以武力接收了武汉的英国租界,此事令比利时政府大为震动,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称“愿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改定新约,并终止了在海牙国际法庭的诉讼,此后又在修约谈判的会议中表示准备将比利时在《辛丑条约》中获取的天津比租界内的一切权力交还中国,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北洋政府日薄西山,比利时方面再次搁置了谈判议程,中比之间的条约问题最终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来看,激进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并拒绝向海牙国际法庭应诉,并不符合顾维钧等北洋政府外交官员一直以来谋求的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行事的主张,顾氏在1922年担任外交总长时曾对苏俄特使越飞说:“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政策。中国政府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谈判,以期有关各国乐于同中国合作,实现中国所欲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12]而在1926年单方面废除《中比条约》则可以看作是外交系官员在1926年国民革命如火如荼、北洋政府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受时势所迫无可奈何的激越之举。
(三)拒绝缄默——北洋政府末期的外交困局
北洋政府末期的政治困局和外交困局,在《大公报》的报道中尤为明显。1925年开始,北洋政府在开展中比修约之外,陆续照会各国商讨修改不平等条约事宜。1925年7月3日的《大公报》刊载了颜、王、蔡三位交涉专员就职时向总统发布的呈文;7月14日刊登采访“王正廷博士左右某君”得知关税自由为修约谈判之要点;对于修约照会的进程也只有少数无关痛痒的跟踪。至1926年,中比修约在顾维钧的主持下,单方面宣布废除了与比利时的不平等条约。这一消息固然振奋人心,但《顺天时报》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国因比国海军力弱小,遂择比国为其废约运动之第一个牺牲品。”[13]
面对军力强盛的日本,北洋政府在废约问题上变得畏首畏尾,自1926年10月17日外交部宣布将于明日送出照会起,《大公报》几乎每日一文对此事保持着高度关注。1926年11月15日刊中评价当下外交局面是 “外交受政局影响,比日修约交涉沉寂,顾维钧亦意兴阑珊”[14],难掩失望之情。直至11月22日,并无进展。转年自1927年1月21日再开修约谈判会议,然至2月22日,“中日外交当局之宣称,均谓‘双方意见甚接近’、‘进展颇顺利’”,而此新闻标题则异常讽刺——《中日修约无实际进步——开幕一月之成绩》[15]。至五月,又爆出双方因最惠国待遇问题意见相左,日方甚至意图扩大最惠国待遇范围以获得更优待之条约,而北洋政府无力拒绝,只得搁置争议,导致谈判旷日持久难以达成共识。直至12月26日,中法、中比、中日、中西修约交涉“俱在延宕中”[16]。直至1928年4月,最后一条关于北洋政府与日本修约的消息是修约专委会“本星期内或将开会”[17],此后北洋政府垮台,最终仅有中比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在北洋政府罕有的强硬态度下得以废除,其余修约事宜多半搁浅。
三、北洋政府修约外交的困境
(一)自身弱点难以承受舆论压力
北洋政府由于受到军阀控制,最高领导人是各方势力角逐妥协的结果,而政治架构又采用了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府院结构,因此在面对舆论压力时呈现极端的两面性。在面对危及政府统治根基的社会运动时采取军事手段残酷镇压,而当其需要行使中国合法政府身份开展外交活动时又无法避免地受到舆论左右,外交活动领域的决策过程相对开放。1920年外交官王正廷在凡尔赛会议结束后从欧陆回国,他在会议上力争主权的形象使其成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偶像。好景不长,1922年王在督办中方对日收回山东主权一案中,遭到山东上下一片声讨,甚至被斥为“卖国贼”。从日本新闻界斥责日本驻华大使“屈辱外交”中,可以侧面窥见中国舆论对王的声讨有过甚之嫌。
伴随着五四运动的落幕,青年知识分子迫切地希望在外交活动中展现其政治声量,《大公报》日益成为知识分子品评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一切政府工作的传声筒。知识精英通过大众传媒引导舆论风向,表达政治主张,吸引支持者。而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各界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强烈诉求、仇视长期压迫中国的各列强的民族情绪,与北洋政府的实际能力所能达到的主权限度和外交谈判中不得不采取的妥协斡旋等手段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外交官员“外交救国”的政治理念实际上与当时的社会局势格格不入,缺乏施展的土壤。因此《大公报》在品评这一阶段的外交工作时,论调显得十分尖锐。从这一视角回顾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活动,可谓是旷日持久而所得寥寥。
(二)自身的合法性危机束缚修约外交工作
根据哈贝马斯关于政府合法性的理论,政治系统需要大众忠诚的维护,当政治系统无法将社会大众的忠诚度维系在一定水平时,就产生了合法性危机。当受到从舆论压力到社会运动在内的各种外来力量的冲击时,一旦合法性危机这一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将最终导致民众对现行政治秩序丧失信心,转而采取革命手段重构新秩序,这就是北洋政府的独裁和专制统治脆弱且不得人心的根源。
20世纪20年代的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军阀混战,一步步削弱了北洋集团内部的力量。北洋政府受军阀控制,而军阀由列强扶持,这样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尽管认识到列强施加的不平等条约是造成苦难的根源、束缚国家之枷锁,北洋政府也无法响应人民关于革命的呼声。五卅惨案之后,国民革命的火种几乎一触即发,然而北洋政府只能通过修约谈判巩固自己作为被列国所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一身份以弥补其日益衰微的政权合法性,这种将自身命运寄希望于他国的行为实属本末倒置。在谈判的过程中,北洋政府也没能在表面上表现出为国为民的胸怀与能力——谈判进程迟滞令人失望,对内武力镇压反帝爱国运动更让军阀政府与社会最广大的人民离心离德。在一次次外交会议的迁延和国内革命的浪潮下,北洋政府的力量被消耗殆尽,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结语
“官与私”记录视角下的北洋政府修约外交工作,固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但仍然暴露出了很多弊病。作为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个开始,在后期出现激进、迁延、准备不足等种种问题,究其原因,是北洋政府自身的局限性束缚了外交工作。北洋军阀之间冲突不断,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权力内耗和内部战争,没能构建政治开明、权力集中的强大中央政府,面对境外列强的干涉和国内的舆论压力与革命力量均表现出手足无措,注定了其修约外交工作的失败结局和自身覆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