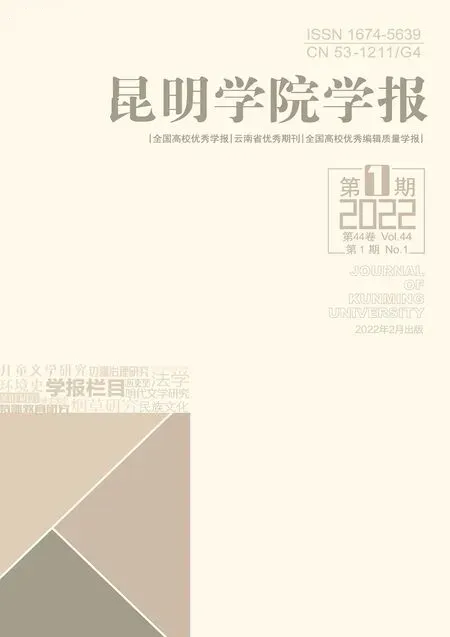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活动情形述论
2022-03-17朱映占
朱映占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人员的迁徙、流动是民族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助推力。特别是双向、多向的人员流动是彼此所属群体进行了解、认知、建立互信关系的重要前提。以此观照中华民族在近代发展的相关情况,我们发现研究者大都聚焦于中华民族成员当中由内地去往边疆地区的人员的活动与感知,很少有人关注从边疆地区赴内地观光、求学、经商等人员的踪迹,以及这些人由此产生的感知与其产生的影响。有所侧重的单向度研究,对于完整、全面探讨近代以来内地与边疆、不同民族间交流与互动的实情是有所欠缺的,也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近代各民族的中华民族一体化认知的自觉过程。因此,有必要把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从西南边疆地区去往省会城市、沿海地区、中原地区,乃至国都观光、参访、求学、就业和从政等人员的体验、感受及其由此带来的对民族、国家的认知与认同等进行深入研究,以此来探讨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认知加强、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在西南边疆的实践过程。
一、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的背景分析
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国人期盼的和平与安宁并没有随之而来。现实的情况是列强环伺,边疆危机依然突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剧,国土沦丧。面对山河破碎、被侵挨打的局面,国人更加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各个成员只有团结起来,形成合力,才能赶走来犯之敌,恢复国家的独立,实现民族的富强。无疑,促进内地与边疆之间人民的多渠道、全方位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一体关系形成及中华民族一体意识自觉、中华民族独立与自强的必要前提。对此,有人提出“对徙汉番,调正情感”。[1]223倡导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双向迁徙流动、交往和融合。对于内地民众去往边疆地区工作、生活,参与边疆开发与建设,当时国人有诸多宣传和倡导,如“到普思沿边去”“到松潘去”“到青海去”“到西北来”等呼吁即是其体现。同样,对于边疆民族去往内地或与内地同胞加强接触的呼吁,也是当时关注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人们之重要倡议。并且,对于边疆民族赴内地之事,无论是关注边疆的学者、官员,还是边疆民族群体都认为是很有必要的。
曾在边疆地区调查和担任治边工作的人员,均感到当时边疆民族的国家观念淡薄,为了民族团结和进步,需要进行引导和激发,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边疆民族到内地亲见国家的伟大。“若以口舌文告宣传威德,固莫若使番民自行宣传之为愈也。”[1]232云南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柯树勋在病重之际“乃决趁一息尚存之际,躬率各土司叭目等赴省垣观光,使彼等开拓眼界,增进见识,知中国之伟大,以泯其夜郎之念,而奠沿边于磐石之安,则死当无憾”。[2]24-25并且,时人意识到,西南边疆民族虽然是中华民族构成之一分子,然而,由于地域之险阻、历代政策之消极等原因,他们“大都固守旧习,未加改进,在文化方面,更未能与时推移,接纳新知。晚近潮流急变,绝非固守原始社会之生活,缺乏近代文化之民族,所能自存。故今日西南夷苗同胞,首须接受内地同胞文化上之启迪,多与内地同胞接近,增益新知,使本身之生活渐趋于近代化”[3]。
从边疆方面来看,随着边疆民族学校教育的开办与发展,边疆民族地区接受现代教育的人逐渐增多,他们中有一些人渴望并且也有机会走出一隅,去了解更为广阔的世界。同时,西南边疆民族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解除苗夷痛苦最基本,最切实,最能彻底而且可以维持永久的方法,就是夷苗青年本身的觉醒和努力奋斗了”。[4]因此,他们渴望走出西南边疆,去了解和掌握新知识,进而促进和唤醒自己所属的西南边疆民族群体的意识。并且,从长远来看,边疆的开发与建设“一方面固要厚其薪给,选拔优秀而有决心毅力的青年去边疆;一方面也得在政治、经济、教育诸方面下手,减低边民困苦,培植边地人才,然后方能收到统一向内的功效”。[5]
可以说,民国时期无论是从边疆的研究者、管理者的视角出发,还是从边疆地区民族自身的视角来看,我们都认为边疆民族赴内地进行交流与活动是迫切的,也是必要的。
二、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的类型及特点
(一)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的类型
民国时期,随着阶序化朝贡时代的结束,边疆民族赴内地不再受限于人数、渠道等方面的制度化规约。在商贸、朝贡之外,赴内地就业、从政、游历、求学之人逐渐增加。也就是说,边疆民族去往内地的人不再限于特殊阶层、特殊行业。总体来看,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的方式,具有一定影响并有所持续,且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观光。民国时期不断有人前往内地旅行和考察的同时,从边疆去往内地进行观光、游历和访问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在云南,就先后有多地的土司、土目和边民代表赴省城观光的事情发生。如1924年夏,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柯树勋率领十二版纳大小土司、土目、团首120余人,前往省会昆明谒见唐继尧,并参访观光。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观光团于(1924年)7月20日抵达昆明附近的昆阳镇,8月9日,唐继尧在省公署召见柯树勋。8月19日,各土司至省公署敬献土特产礼品,省公署收下礼品并送博物馆收藏陈列。8月20日,唐继尧接见观光团代表,并向各土司、土目、团首赠送奖章、照片和礼物等。8月21日起,参观团先后参观访问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东陆大学、省立第一中学、高等师范学校、军队射击场、飞机场等部门、机构和场所。11月9日参观团启程返回,至12月28日回到车里,[6]观光访问结束。1935年2月底,滇西边境葫芦王地班洪等十七土目,派代表赵子福、甘别等十人,赴省城谒见省主席龙云,痛陈班洪被侵略经过和率兵抵抗的情形,以及葫芦王地在中国的历史等。[7]1936年5月中旬,普思沿边土司代表又赴昆明参观省会建设,受到省政府机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土司代表感到非常欣慰和激动。[8]1937年5月,滇西南甸、陇川、遮放、盏达等五土司至省城昆明观光。此次五土司来省城,“因感到伊等世袭土职,服务边疆,责任綦重,惟因途程遥远,交通不便,下情不能上达,近年龙主席主持省政,百废俱兴,各项建设,突飞猛进,对于边疆尤为关怀,因此相约来省谒龙主席请训,顺便观光,俾日后各返原治,为改善边政之助”[9]。并且,滇西土司此次“除拜聆主席训示外,主要目的在边子弟七八人到省入南青(菁)学校,并作全国周览,拟由滇黔公路,经湘、赣、浙抵沪,再到京平平然后由牛汉路达粤,经香港绕南详,过缅甸返故乡预计以半年时间为游历云”。[10]在西康省,宁属和康属的彝族和藏族,也分别组织观光团赴省城、首都和沿海等地参观。如1948年3月,西康宁属边民组成观光团,准备由西昌赴成都、南京、上海、华南及华北一带大城市参观。观光团由彝族人靖边司令、昭觉县国大代表孙仿(子汶)任团长。团员有夷务团长罗大英、罗镇江、罗木呷、罗铁哈、何镇雄;夷务营长罗畸湘,夷务大队长何玉发,边民立委候选人余文成,普雄整理处处长王济民等。并且《边疆通讯报》对蒋介石接见西南苗夷代表的情况进行了报道。(1948年)5月13日观光团一行20人抵达上海,受到上海市市长的接见,观光团向上海市市长赠送土产银制酒器、木制盒子等工艺品。观光团在上海逗留3日,参观了工厂和一些现代设施。[11]1948年4月,西康省国大代表邦达·多吉三兄弟在南京国民政府官员的资助下一起到上海、杭州、北平等城市游览。游览结束后,邦达·多吉返回西康任义敦县县长,并兼任蒙藏委员会调查专员。[12]94-95
第二,请愿。请愿作为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一直贯穿于整个民国的中后期。
在1931年1月,四川凉山彝族曲木藏尧在南京求学时向中央政府发起请愿,就“夷族”的身份、地位等问题向中央提出了五点建议:“一、请明令承认夷族为三危之后,与康藏同种。二、请明令夷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与汉人享受同等地位。三、请明令汉夷婚姻平等。过去夷人之女,汉人可娶,汉人之女,夷人则不能娶,此为汉夷不相合之一大原因。四、请沿中央待遇蒙藏青年求学办法,于京中设立夷人教化学校,教育夷族中能通汉文之青年。五、请于京中设立夷务办事处。”[13]43-44曲木藏尧的请愿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实质性回应,于是曲木藏尧牵头,在南京成立“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联络西南地区四川、贵州、云南在南京求学的夷族青年阿弼鲁德、王济民、岭光电、安腾飞、王奋飞等人,“本三民主义原则以共谋改善夷族生活促进夷族文化为宗旨”[14]开展活动。1932年7月,西康旅京民众救省请愿代表至南京国民政府各部门请愿呈文,陈述解决康藏纠纷的办法。1936年,来自西南边疆云南、贵州、西康等地的喻杰才、高玉柱、王奋飞、岭光电等人组成“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族来京请愿团”向中央政府请愿,就西南“夷苗”民族的地位与待遇,“夷苗”的经济、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夷苗”的组织与训练,以及边地官吏的任用与奖惩等方面表达了他们的期望与心声。此后,1938年9月至11月,在陪都重庆的西南边疆的“夷苗”精英们,包括云南北胜土司高玉柱、西南“夷族”代表喻杰才、四川土司代表岭光电、四川宁属边民代表曲木藏尧、四川宁属“夷族”代表王济民、贵州土司代表安庆吾和杨砥中,以及云南的土司陇甫臣、贵州土司安亮清等,共计100多人,分头或联合先后向国民政府主要领导人、中央各院部委发起了多次请愿活动。[13]125-1281947年,担任西康省边务专员的凉山彝族土司岭光电代表150万“夷胞”组织“西康省夷族参政请愿代表团”经成都赴南京请愿。在拜会党政军相关领导人后,提出了“夷族”参政的三项请求:“(一)在省参议会中列入名额,(二)将来省参议会产生监委时,希望有夷族名额,(三)立委一名似嫌太少,请增加一名或二名”[15]。
第三,慰劳。民国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内地和沿海国土沦陷的情况,西南边疆民族自发组织慰劳团,向政府表达慰劳抗日将士和请缨杀敌的心愿和决心,有的慰劳团还直接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如格桑泽仁于1938年6月组织“西康僧俗民众慰劳代表团”至汉口一带献旗慰劳。“汉口三日电,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一行十二人,于上月廿十九日抵汉,该团为西康各界民众举行大会选举出之代表所组成,自西康出发,经滇川在蓉渝等地时曾受各该地团体之热烈欢迎,该团此行并携有大锦旗一面,上绣‘再造亚洲’四字,拟敬献蒋委员长,同时德格土司泽旺登登亦托该团带来狐皮豹皮药康茶壶经典摇铃马鞍等物九件,敬献蒋委员长,该团拟敬献锦旗后,即赴前线分向各长官献旗致敬,并慰劳各将士云。”[16]1938年,拉卜楞寺及所属各部落组织“藏族僧民慰劳抗敌将士代表团”至重庆向国民政府领导、军队将领献旗,表示崇敬和慰劳之意。代表团到达重庆后,“备受各界之热烈欢迎。充分表现我民族团结,容(融)合无间之气象”。[17]1939年3月,川青交界地区,滨黄海、松潘县境的三峨落西番部落在日寇侵略加剧之际,推举土官、活佛、大小头目二十余人为代表赴省城谒见省主席,表达同仇敌忾、请缨杀敌之决心。此次外出是该部落二百余年来首次派代表赴省城。3月3日,省政府主席在省府接见了该部落代表,在接见过程中“首由代表申述来意,敬服中央及省府当局之德威,愿倾诚服从指挥,决驱强寇,并于目前抗战形势及政府驱寇决心,详为训示,接见约一小时,摄影后辞出,王主席复于午间在省府大礼堂设宴招待各代表,并赏赐蜀锦川缎子茶叶等纪念品,且各赐林主席蒋委员长暨王主席照片一帧,下午一时,各代表于极度兴奋感谢之情状中离出省府”。[18]
第四,经商。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许多深居山中,传统上多无专门的商贾和商业,仅在其居住的周边地区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来互通有无。然而,随着近代以来封闭状态逐渐被打破,西南边疆民族中原来擅于经商的民族,把他们的商业贸易活动发展到了更远的地方,即使在不擅长经商的民族中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商贾和商队。可以说,西南边疆民族中的一些人,他们的足迹不再局限于边疆村寨,有的把生意做到了西南省会城市、内地大城市,甚至国外。如以邦达·多吉为首的康巴商人,就在内地与西藏贸易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邦达·多吉家族的“邦达昌”商号,分别在上海、南京、北京、成都、西宁、兰州等地都设立了商行。特别是抗战时期,“邦达昌”的商行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发往康定、丽江之后,转运至昆明、成都经销,这些商品对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整个抗战时期,“邦达昌”运送支援抗战物资价值达1.5亿美元。[12]71-72民国时期大理的“民家”(1)“民家”为民国时期白族的称谓。同外地的商业贸易也很频繁,其马帮商队常年为四川叙府与缅甸八莫之间的商业贸易服务,这条商路从昆明到大理下关、腾冲的运输通常由民家马帮负责。另外,从云南普洱经大理下关、滇北维西等地至西藏的商路,也通常由民家人负责运输。滇西“古宗”(2)“古宗”为民国时期云南迪庆藏族的他称。商队也经常往返于丽江、鹤庆、大理,乃至昆明。
第五,求学。民国时期,在西南边疆地区逐渐出现了现代学校教育,一些当地民众也开始走出自己世代生活的地方,到所属省会甚至内地求学。并且,在南京等地的一些学校也设置了专门招收边疆地区学生的特殊班级,如中央政治学校的附属西康班、附属蒙藏班、附属蒙藏华侨特别班等。民国初期,川西北卓克基藏族土司索观瀛从老家前往成都读书,他习汉字、讲汉语,具备了阅读汉文书籍的能力。1916年从成都学习返回土司官寨之后,索观瀛不但重视民族文化、改造农业和发展商业,而且注重加强民族间的友谊,[19]在思想上表现出开放和进取的面向。四川小凉山地区雷波彝族杨土司之女杨代蒂于1936年至1937年间在宜宾读书。1941年雷波县长送她至重庆国立边疆学校上学,在当时当地“夷人”(3)“夷人”为民国时期彝族的他称之一。认为她单独到外面上学是很不体面的,都反对她去。“但她认定要把夷人领导起来,向进步方面走,非求得高深知识不可,乃排除众议,单身前往。在渝一共住了四年,去年他母亲死去,她方才回来,这一二年来,她开导夷人,整理家产,深为社会人士所尊重,大有恢复旧有声望之概。”[20]在西康,边地教育于赵尔丰时期已开始筹办,在此基础上走出西康继续求学的人逐渐出现并不断增多,特别是1930年西康特别行政区在南京设立了“西康民众驻京办事处”,积极发动康区青年赴南京、北平求学。由此,一批康区青年考入南京等地学校就读,其中最为有名的为“巴安十西”[21],他们成为较早一批接受现代化教育的康区精英。在云南,大理民家“有钱人到省城去求学或者去谋职”[22],丽江纳西族当中也有赴内地求学的风气,如方国瑜、李群杰等赴内地求学,并成为各自领域的一代名家。民国时期在云南边地考察教育的人士注意到边疆民族群体多样、语言不通,在边疆办教育,师资问题的解决根本上有赖于在边疆民族中寻找和培训,因此他们认为除了在边疆民族分布地区就地开办学校、推进教育之外,“尚须在省会地方,开办边地民众教育师范若干班,惟此项师范班的开办须在边地启蒙师资训练班毕业以后,除将启蒙师资之一部派回本乡服务外,更由各地分配选出若干名,视其智慧足资上造者,派到省会使习民众教育师范科,此项师范科教育完成以六年至八年为限,其程度以能教授高小学生为止”。[23]贵州省雷山县的苗族梁聚五先后在贵阳师范中学、湖南大学上学,在经历过多次政治和社会运动之后,走上了调查、研究苗族的道路。在省会和内地求学和就职的过程中,他“基本接受中华民族所代表的族群融合为一体的理念。他一生对中国政治热情投入,对新中国成立的热望,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备受帝国主义的欺压,特别是对日本侵略所表现的沉痛与愤慨,充分反映他有深刻的国族认同”。[24]另外,贵州石门坎的杨汉先等多人到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求学,成为贵州苗族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第六,任职(就业)。民国时期,随着西南边疆民族中的一些人陆续到内地求学、参军等,渐有留居在西南各省会城市或内地就职者,其中有一部分人还身居要职,甚至对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政局发挥出重要的影响。如滇东北的龙云、卢汉等人到昆明陆军讲武学校学习毕业后,参军入伍,后来逐渐步入云南省政事中来,形成了控制滇政实权达20多年的彝族统治集团。[25]格桑泽仁、江安西、刘家驹等西康藏族曾任职于政府部门,活跃于南京、重庆、成都等地,并曾发起“康人治康”的自治运动,对民国时期康藏地区的政局产生了不小影响。当然,除了龙云、格桑泽仁等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外,还有不少来自西南边疆民族的普通人,就职服务于不同行业,成为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活动的特点
分析民国时期以不同形式赴内地的西南边疆民族的行为、人员构成和规模等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其以下特点:
第一,仍沿袭古代朝贡的一些特征。如边疆民族组成的观光团或请愿团,通常都要谒见政府首长,敬献地方特产或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无论是云南普思沿边土司赴省城观光,还是西康“夷民”代表至战时陪都重庆观光,都有上述谒见和敬献礼物的行为。大有古代边疆土司赴朝廷朝贡的意味。
第二,边疆赴内地者仍然多为土司、头人等少数阶层较高的人。特别是观光和请愿的人员多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世袭首领或政府任命的掌握实权的地方首领。普通民众仍鲜有机会离开本土,他们中只有极少数因求学、参军等而得以前往内地。
第三,赴内地途径和方式渐呈多样化趋势。在朝贡式的观光之外,请愿、经商、求学、就业、参军、婚嫁等都是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的可能方式。在组织方式上,边疆民族自发组织的占多数,但也有各级政府组织和计划安排的。前者如西康夷族观光团、滇西土司观光团等,后者如普思沿边行政总局长柯树勋组织的十二版纳土司观光团、任乃强在西康倡导的政府招“番民”(4)“番民”,民国时期对川西藏族的他称之一。观光等。
第四,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无论是短期观光,还是长期的就业居住,其人员在数量上总体而言仍然是有限的。
三、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的意义探讨
西南边疆各民族,在民国时期通过不同方式赴内地进行或短暂或长期的游历参观、工作生活,于其自身、各级政府及内地民众和社会各界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具有诸多社会意义。
第一,对于西南边疆民族而言,通过赴内地观光、游历、求学、经商等事项,西南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对其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自身在国家中的地位、本民族的教育等问题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如《申报》于雅安的报道就称:“西康的夷族观光团,自从到京沪等地观光归来后,各个团员对于夷务已经是发生极优良的影响:各团员在归家以后,把这次出行的经过与观感与乎元首各院部首长所赠给他们的照片、画片、武器连同在上海所灌制的留声片这类东西,分别向他们的亲友,并深入大凉山的夷巢里去宣传,阐扬政府德意,简述人类进化的情形,这些夷胞深受感动,思想也因之转变,倾心向化了。最近由团员罗大英、罗镇江、罗木呷、果鸡马达等率领窪里、巴哲、瓜别、普雄等地,从来莫有到过西昌的夷人首领罗洪长等数十人,纷纷的自动到西昌去,表示绝对拥护政府,安定边区。夷胞认汉夷是一家,已经莫有彼此的区分,他们并觉悟要想把夷胞进步的话,应该从文化教育方面着手,他们在西昌组织一个夷族文化协会分会,推孙仿、王济民为正副会长,广大夷区现在已掀起兴学的热潮,各地夷人的首领,最近汇集在西昌,要求政府指导协助他们开办边民教育,业已决定划夷区的巴哲、普雄、北山、宁东这四个地方为教育区一共筹备设立边民小学十八所,推定专人负责筹办,定于明春开学,现在所有的校舍已经修筑完成了。他们又请政府发展交通,自己愿意出力修筑,使夷胞的文化经济发达起来,造成一个繁荣的区域。”[26]并且,边疆民族赴内地活动,还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如“边疆地区随着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内地的先进思想文化,对傣族社会也产生了影响”。[27]此外,西南边疆民族通过赴内地观光、求学等活动,增进了对国家的认同。1924年,十二版纳“各土司叭目由昆明归来后,乃渐体会中国幅员之广大,民物之众庶,并深感各机关长官,对边民一视同仁,优礼有加,不复作‘两广孰与车里大’之问难,亦不再作驱逐汉人之想,而唯共存共荣,为最高之标的矣”。[2]25可见,十二版纳各土司通过到省城观光,对国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知,正如有学者所言“柯树勋带领边疆土司头人到昆明谒见唐继尧和参观,就是‘边陲’对‘中心’的一次主动打通,加强了双方的联系和土司头人的国家认同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6]
第二,西南边疆民族去到省府或中央呈献其土产,表达其心声,介绍其民族,经此对于各级政府而言,西南边疆民族不再是模糊的形象,也不再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能够轻易忽略的群体。如针对来自云南、贵州、西康等地区边疆民族请愿的要求,在官方媒体进行报道的同时,国民政府内政部也对他们的请愿事项进行了答复。对于“夷苗”子弟的升学问题,行政院明确指出可以参照《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的规定,给予优待。对此,许多报刊都进行了报道和刊载:“苗夷学生在中央及各省求学者(得比照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办理):苗夷各族,同为边疆民族,散布区域,至为广泛,其文化程度,较之蒙藏各族,尤为低落。在此推行边疆教育之际,所有苗夷学生在中央和各省求学者,自宜格外优待,以示提倡。教育部已准予比照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办理。并命令知照云。”[28]对于西南边疆民族的参政、监察、开发建设、民族身份确立等其他请愿事项,国民政府则都做出了否定的答复或模棱的处理。故而一直到民国后期西南边疆民族的请愿活动仍在持续。如1937年苗夷代表高玉柱在上海某广播台演讲时就声称:“这次我们是表现我们苗夷人民拥护中央的热忱,同时希望中央能够关心我们的一切幸福,而能够帮助我们。”[29]显然,通过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的相关活动,政府在得以了解其动态的同时,对于其呼吁也不能完全视而不见了。
第三,对于内地社会各界及民众而言,与边疆同胞的近距离接触,使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构成、西南边疆民族的实情等都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如1937年来自西南边疆的高玉柱、喻杰才等抵达上海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接待。《民报》《大公报(上海)》《益世报》《时事新报》《时代报》等各大媒体都纷纷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当时的报道称高玉柱十分健美, “她的肌肉的结实,江浙一带的女子,恐怕是不能相比的,至于她的汉语说得十分顺口流利”[30]。并且,参与接待西南边疆民族代表的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声称“四海之内皆兄弟,非常高兴,四海是指中国各地,但大家还是兄弟,夷族的二千万人民,当是都是中华民国的人民”[30]。显然,边疆民族前往内地的活动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的相互认知。同样,“邦达昌”藏族商人正是在边疆与内地之间频繁的商贸往来中,“使藏、汉族深切体会到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与汉、藏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共同的命运把藏、汉民族与全国各族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更加加深了民族间互助了解,促进了民族团结与协助”。[12]72特别是,西南边疆民族多种形式的赴内地活动,在潜移默化间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如滇西土司到内地之后,把内地戏曲的内容和形式带入了滇西,并将之融入本族的戏剧文化之中。“摆夷民间有戏剧——这也是西南民族中稀有的文化,发生时间不很早,三十年前始创于干崖土司衙门中,这因为几位土司贵族,曾经到过汉地的,于是模仿云南民间旧戏的唱做场面而以摆夷语演出。云南戏俗称‘滇戏’,大概其源也出于汉调,故与平剧是姊妹花,扮相、做作、服装全和平剧同,场面小有差异,铉琴唱调另成格,行腔吐字则全用昆明语音。”[31]416
四、结语
长期以来,对于汉人去往边疆民族地区的情况有大量文献记载,如正史和地方志当中有关于汉人迁徙到边疆地区生活居住、流官赴任等。同时,民间的口述资料也有诸多流传,如在滇西民间走夷方的传统,就成为人们对汉族深入边疆地区的一种认知模式。“邻近夷区之汉地内的汉人,每年在霜降节以后,结群走入夷区,次年清明节前后又回到汉地,那便是所谓的‘走夷方’。”[31]433无疑,无论迁徙到边疆民族地区生活的汉人,还是那些走夷方的木匠、泥水匠、货郎等,他们都为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样,生活在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或短暂或长久地离开故土,去往内地开展活动,他们在把自己展现给内地同胞的同时,还把更为直观的认知与感受带回其所属的民族群体,也为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整个民国时期从西南边疆走出来赴内地求学、观光、就业等的民族人士还属少数,因此,其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依然是有限的。边疆与内地之间大规模的交往交流交融还有赖于交通的改善,更为畅通、更加有保障的人员流动与迁徙的社会机制的建立,也有赖于现代教育的发展。正如滇西边区土司对考察人员所言:“将来边地教育普及,夷民智识开化,有谋生之技能,明乎礼义廉耻,有爱国思想,化盗贼为善良,以无用为有用,则不但边地之幸福,抑或国家之保障也。”[31]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边疆与内地一体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彼此间双向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前提,这个前提的建立有赖于包括内地和边疆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共同参与。因此,虽然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的人数、方式等依然有限,但是西南边疆民族主动走出封闭的村寨去往内地交流的实践,却也展现了其参与国家建设、和祖国命运与共的一面。这是我们今天研究边疆与内地各民族全方位、多层次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途径和方式等问题时,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