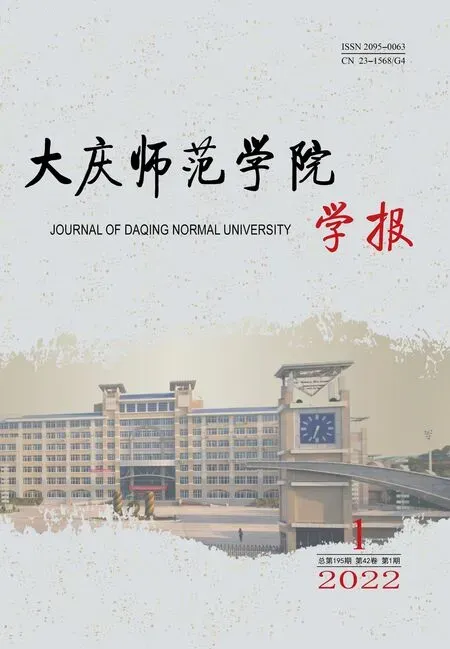论基兹尔巴什及其对伊朗萨法维王朝的影响
2022-03-17冀开运章琳珠
冀开运,章琳珠
(西南大学 1.伊朗研究中心,2.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萨法维王朝(1501—1722年)是伊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的建立结束了伊朗几个世纪以来外族入侵造成的动荡局面,形成了伊朗历史上第三个独立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而萨法维王朝得以建立和实现统一是基于以土库曼部落为代表的部落联盟的支持,特别是由土库曼部落构成的基兹尔巴什军队,他们是开创萨法维王朝主力军,也是王朝建立初期维持统治的核心力量之一。然而,随着基兹尔巴什军队和土库曼部落权力的膨胀,王朝与部落关系的日渐复杂化、王朝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恶化最终致使萨法维王朝走向衰亡。在萨法维王朝自兴至亡的漫长历史当中,基兹尔巴什及其背后的土库曼部落曾担任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都与之兴亡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说,这支英勇善战的军队既辅佐萨法维家族开创了最好的时代,也致使其跌入无尽的黑暗后一蹶不振。
一、基兹尔巴什的概念
基兹尔巴什(Qizilbash)一词源于突厥语,(1)参见Peter Jackson and Laurence Lockhar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The Timurid and Safavid Perio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95-207.初期主要指由土库曼部落构成的追随萨法维家族的军队,后来随着萨法维家族和萨法维教团影响力的扩大,一些非土库曼部落的人也被囊括其中,最终与土库曼部落的士兵共同构成了一支协助萨法维教团进行征服运动并建立统一王朝的强大军队。从祝奈德(Shaykh Junaid)到海达尔(Shaykh Haidar)时期,萨法维教团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和实力,(2)参见贺婷:《萨法维王朝时期土库曼部落与国家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历史系,2016年,第70页。以基兹尔巴什为核心的军事力量逐渐壮大,为此萨法维教团第五代谢赫海达尔为军队设计了统一的军帽——帽子呈深红色,根据这一特征基兹尔巴什又被称为“红帽军”。帽子周边还附有十二条流苏,代表着十二伊玛目,在波斯语中这款军帽被定义为“海达尔之冠”(Haidar’s Crown),(3)参见Moojan Momen, An Introduction to Shi’i Isl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01.象征着他们对教团首领海达尔以及十二伊玛目的尊敬和忠诚,也有译者将其解释为“红头军”或“红帽军”。(4)参见刘昌鑫:《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的外交关系探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4期,第91—105页。尽管基兹尔巴什词源与奥斯曼人有关,最初具有一些讽刺轻蔑的含义,但随着这支骁勇善战的顽强军队横扫战场,带领萨法维教团走向胜利建立新王朝之后,基兹尔巴什则成为标志着他们英勇善战的代名词。
二、基兹尔巴什军队的发展历史
(一)基兹尔巴什的建立背景
基兹尔巴什的历史要追溯到萨法维教团(Tariqa Safawiyya)时期,可以说萨法维教团兴起和扩张的同时也促使着基兹尔巴什成长和强大。萨法维教团自兴起、扩张至最后的征服运动共经历了三个阶段,两者在此过程中维持着相互促进、相互扶持的关系。
萨法维教团的兴起得益于两个条件——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首先,萨法维教团发迹于今天伊朗西北部阿尔达比勒省的首府阿尔达比勒市。阿尔达比勒省临近阿塞拜疆共和国,在吉朗省和东阿塞拜疆省之间,海拔较高,且处于高纬度地区,气候相对恶劣。阿尔达比勒市四面群山环绕,最高的萨瓦兰峰(Savalan)高达4810米,常年积雪,地势险峻。(5)参见Laurence Lockhart, Persian Cities, London: LUZAC& COMPANY LTD, 1960, pp.51-52.该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成为孕育和滋养宗教运动的沃土。其次,13世纪动荡的伊朗为萨法维教团的兴起创造了机会。从萨珊王朝之后至萨法维王朝完成统一前,伊朗高原不断受到来自游牧部落政权的冲击,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曾先后征服和统治着这片区域,割据与动乱充斥着伊朗社会。阿拉伯帝国衰败以后,伊斯兰教逊尼派失去正统和主导地位,什叶派、苏菲派等其他伊斯兰教派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6)参见希提:《阿拉伯通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07页。伊朗民间宗教团体开始蓄势待发,企图借宗教之力控制伊朗高原。在众多宗教团体之中,苏菲派教团之一的萨法维教团最终脱颖而出。
萨法维教团兴起是在萨菲·丁(Safial-Din)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在首领的宣传和影响下,七大土库曼部落中的部分成员便开始归顺于萨法维教团,在这其中就形成了以土库曼部落士兵为主力的基兹尔巴什军队,但是当时土库曼人依附萨法维教团的时间不尽相同,教团中具体的土库曼部落的人数也无法做出确切的统计。按照当今伊朗社会的人口现状,伊朗8000多万的人口之中,土库曼人只占2%,(7)参见王珂:《伊朗地理人口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历史系,2009年,第1页。至今仍属于伊朗的少数民族。据此推算,13世纪刚建立起来的萨法维教团所能吸纳的土库曼部落人口也并不会很多。但是,谢赫萨菲·丁以及萨法维教团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据记载,仅三个月的时间内,从马拉盖(Maragha)和大不里士(Tabriz)两地前往阿尔达比勒拜见萨菲·丁的信众就达13000名,(8)参见Roger Savery, Iran under the Safavid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0.来自各地区土库曼部落的信众也积极加入到基兹尔巴什的队伍当中,成为教团征服战争中不可或缺的精英力量。
从萨菲·丁的儿子萨德尔·米拉·丁·穆萨(Sadr al-Milla val-Din Musa)到易卜拉辛(Ibrahim)时期,萨法维教团迅速崛起,受到众多民众和部落的支持,基兹尔巴什的核心力量也得到更大的扩充和巩固。在父亲萨菲·丁的基础上,萨德尔继续扩大萨法维教团的影响力,广泛收纳信徒。当时很有权势的蒙古贵族埃米尔库班(Chuban)曾询问萨德尔究竟是国王的士兵多还是信徒多,他讲述了从阿姆河流域到埃及边境以及从霍尔木兹海峡到打耳班的游历经历,所到之处遇到了许多萨法维教团信徒并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款待。(9)参见Roger Savery, Iran under the Safavid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8.实际上,在这一时期教团的传教网络已经拓展至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叙利亚地区,土库曼部落加入支持萨法维教团基兹尔巴什军队的积极性也极大提升。对于萨法维教团来说,这无疑为其实现征服和重现伊朗高原统一提供了重大支持。
最终,到祝奈德、海达尔和伊斯玛仪统治时期,萨法维教团已具备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完成了从单一的宗教团体向集政治、宗教、军事力量于一身的历史过渡过程,这其中所包含的军事力量指代的就是基兹尔巴什军队。在萨法维家族政权和萨法维教团宗教信仰的号召指引下,基兹尔巴什的规模和实力已相当强大,不仅是萨法维教团的核心军事力量,也成为萨法维教团进行军事征服运动的主力军。据史料记载,伊斯玛仪担任萨法维教团领袖时,土库曼部落的基兹尔巴什人数达到了七万人。(10)参见Vahid Rashidvash, “Turkmen Status within Iranian Ethnic Identity (Cultural, Geographical, Political),” Research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3, no. 22, p.12.1500年,伊斯玛仪带领以基兹尔巴什为主的军事力量与白羊王朝在沙鲁尔(Sharur)进行决战,这场战役最终以七千名基兹尔巴什战胜白羊王朝的三万军队而告终。(11)参见Kishwr, Rizvi, The Safavid Dynastic Shrine: Architecture, Religion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Iran,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11, p.17.尽管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基兹尔巴什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给伊斯玛仪的军队极大的鼓舞与支持,最终辅佐教团开创了萨法维帝国。
纵观基兹尔巴什的兴起历程,由于前期主要吸纳的是土库曼部落的成员,加之土库曼部落人数在伊朗人口中占比较少,导致基兹尔巴什在萨法维教团征服战争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作为游牧民族突厥人的一个分支,(12)参见秦屹、陈凤、王国念:《部族文化与土库曼当代社会》,《世界民族》2016年第6期,第95—101页。土库曼部落的战斗力自然不弱,并且萨法维教团所宣扬扩张和统一的信念与土库曼部落联盟建立基兹尔巴什的观念契合,因此这种精神凝聚力在战斗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也是基兹尔巴什在沙鲁尔战役中实现以少胜多核心因素之一。
(二)萨法维王朝建立前后基兹尔巴什的发展历史
萨法维王朝建立前后基兹尔巴什的地位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转变:第一阶段伊斯玛仪一世统治时期——军队与王权的稳定时期;第二阶段塔赫玛斯普一世(Tahmasp I)至穆罕默德·胡达班达(Mohammed Khodabanda)统治时期——军权与王权矛盾激化,军权发展达到巅峰时期;第三阶段阿巴斯大帝统治时期——基兹尔巴什的地位受到遏制,新生军事力量诞生取而代之;第四阶段萨菲一世至阿巴斯三世统治时期——基兹尔巴什和土库曼部落权力的衰落。
伊斯玛仪一世统治时期,王权与基兹尔巴什处于相互依赖、相互制衡的状态,总体而言两者关系相对稳定。1501年,萨法维王朝的缔造者伊斯玛仪一世在大不里士宣布王朝的建立。这一新生政权的诞生仍然面临着来自周边残余势力的威胁,因此,基兹尔巴什作为开辟新王朝的主力军继续支持王权,而统治者也需要借助这支忠诚而强大的军事力量开疆扩土、巩固政权。1502—1510年,在基兹尔巴什军队的协助下,伊斯玛仪一世完成了一系列旨在巩固萨法维王朝统治的军事行动,先后铲除了在哈马丹(Hamadan)附近白羊王朝的残余势力,将戈尔甘(Gurgan)、马赞德兰(Mazadaran)、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亚兹德(Yazd)、巴格达(Baghdad)、希尔凡(Shirvan)、呼罗珊以及伊朗中部和南部等大部分区域囊括至萨法维王朝的版图。(13)参见Andrew J. Newman, Safavid Iran: Rebirth of a Persian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06, p.11.在王朝初期的军事行动当中,最能证明基兹尔巴什军事实力的一场战役乃是与昔班尼王朝争夺呼罗珊地区的战争,这是继沙鲁尔之战后基兹尔巴什又一次以少胜多的重要战役。萨法维王朝以17000人的军队最终击败了拥有28000人的昔班尼王朝军队,重新夺回呼罗珊地区。(14)参见哈全安:《伊朗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第112—113页。伊斯玛仪一世在位时期,萨法维王朝在基兹尔巴什军队的支持下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大疆域,涵盖了自西部的叙利亚、东部的阿姆河流域、北部的高加索地区以及南边的波斯湾等广大区域,真正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大国概念。(15)参见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97页。
在征服波斯后,伊斯玛仪一世将王朝西北部的草场和土地分配给土库曼部落及基兹尔巴什:一是为了奖励军队和部落在建立王朝过程中的贡献;二是企图将实力强大的基兹尔巴什安插在靠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边境地区,维护边疆安全。驻守这些地区的土库曼部落逐渐成为该地区的实权统治者和管理者,掌握基兹尔巴什军队的土库曼七大部落甚至在中央政府担任着重要的职务,拥有较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随着部落和军队权力的膨胀,土库曼部落逐渐背离对萨法维家族忠诚的道路,进一步威胁到其权力中心的地位,同时也影响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由于萨法维王朝的建立与土库曼部落以及基兹尔巴什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日渐扩散的社会舆论会导致政权不够稳定,不少民众认为以基兹尔巴什为代表的土库曼部落才是真正缔造王朝的开创者。伊斯玛仪一世也意识到这种“基兹尔巴什建国论”的危险性,并且萨法维王朝是在波斯土壤上建立起来的,若希望维持长久的统治,必须实现自身统治的本土化——去土库曼化融入波斯本土文明。因此,伊斯玛仪一世采取了限制土库曼部落和基兹尔巴什权力的措施,设置全新的行政机构瓦基勒(Vakil-i nafs-i kamil)和维齐尔(Vazir)以及宗教事务负责人萨德尔(Sadr),并指派波斯文官担任这些中央或地方重要的职位,削弱基兹尔巴什和土库曼部落在政府机构中的影响力。
然而,掌控基兹尔巴什的土库曼部落也在积极为自身谋取权力,不仅迫使国王妥协将瓦基勒的职位交给土库曼七大部落首领之一的侯赛因·贝格·莱拉·沙姆鲁(Husayn Beg Lala Shamlu),(16)参见Roger Savory, Iran under the Safavid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4.同时还掌握了王朝最主要的军事力量。萨法维王朝最高的军事职位——埃米尔乌马拉(Amir al-umara)和古驰巴什(Qurchibashi)均由土库曼军事贵族指派担任,特别要注意的是埃米尔乌马拉是当时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也就是基兹尔巴什军队的最高统帅。土库曼部落既掌握了行政机构瓦基勒,也拥有在军事上的强大支撑,而统治者失去自由指挥军队这一国家机器的权力,无法从根本上保障其统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至此,萨法维王朝王权与基兹尔巴什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
查尔迪兰战役成为萨法维王朝与土库曼部落和基兹尔巴什关系的转折点。1514年的这场战争是萨法维王朝与其宿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宗教和领土问题上引发的,伊斯玛仪一世率领着包括基兹尔巴什在内的六万余名土库曼部落骑兵与奥斯曼帝国对抗,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伊斯玛仪一世的“精神领袖和世俗权威”地位开始受到基兹尔巴什和土库曼部落的质疑,军队和部落企图争夺更多的政治权力。
在塔赫玛斯普一世至穆罕默德·胡达班达统治时期,基兹尔巴什的地位随着土库曼部落权力的扩大而达到顶峰。塔赫玛斯普一世在位的前十年,土库曼部落内部陷入了混战,间接引发萨法维王朝的动荡。土库曼部落的“十年内战”主要围绕着拉姆鲁部落、塔卡鲁和乌兹塔基鲁之间争夺塔赫玛斯普一世的阿塔贝格(Atabeg)一职展开的。(17)参见Peter Jackson and Laurence Lockhar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The Timurid and Safavid Perio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33.阿塔贝格是指“太傅”,即主要负责培养和指导即将就任的萨法维王子,一般由土库曼部落的首领担任。当时出任塔赫玛斯普一世“太傅”的是拉姆鲁部落贵族迪夫·苏尔坦(Div Sultan),成为王朝最有权势的“大维齐尔”,代替年幼的国王处理国事,独揽大权。他联合塔卡鲁和乌兹塔基鲁两个土库曼部落摄政,但三个部落因各自的利益而开始自相残杀,塔卡鲁部落的楚哈·苏丹代替迪夫·苏尔坦短暂地成为国家权力的操纵者,之后这一权力又转移到沙姆鲁家族的赫拉特总督侯赛因·汗(Husain Khan)手中。(18)参见阿巴斯·阿马纳特:《伊朗五百年》,冀开运、邢文海、李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20年,第19—23页。最终,土库曼部落的“十年内讧”在塔赫玛斯普一世开始亲政后落下帷幕,但十年内乱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首先,土库曼部落之间多次争权夺利的斗争使得基兹尔巴什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军队的凝聚力也随之下降;其次,内乱导致部分基兹尔巴什叛国投敌的局面,助长了外族的入侵。例如,三大土库曼巨头部落的混战导致乌兹别克汗国的入侵,而之后在围困乌兹别克汗国的行动中基兹尔巴什军队得不到援助,最终只能向乌兹别克汗国投降。
综上,在塔赫玛斯普一世统治前期,王朝面临的“内战”问题与基兹尔巴什对待王朝政权的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从伊斯玛仪一世在查尔迪兰战役中经历惨败后,基兹尔巴什包括其背后的土库曼部落对王权的轻视日渐加深。基兹尔巴什建立的初衷既是为了维持和扩张部落的影响力,也是为了追随萨法维教团所宣扬的苏菲派思想和少数什叶派的极端主义思想。查尔迪兰之役溃不成军的结局致使土库曼部落不再相信萨法维政权的权威,加上此时的塔赫玛斯普一世年幼,王朝内部又没有其他可以制衡或替代基兹尔巴什的力量,所以基兹尔巴什及其背后的土库曼部落势力更加肆意妄为。
1524—1576年,塔赫玛斯普一世正式掌权后重塑国王威信,暂时制约了基兹尔巴什的权力。首先,他通过迁都,将首都从西北部的大不里士迁至中部的加兹温:一是远离奥斯曼帝国,削弱其造成的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影响;二是政治中心远离西北部地区土库曼部落的发源地,遏制土库曼军事贵族的势力。其次,塔赫玛斯普一世开始扶植第三方势力,企图摆脱以基兹尔巴什为主力的土库曼部落的军事控制。从高加索地区俘虏回来的信仰基督教的战俘,主要由格鲁吉亚人(Georgian)、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和亚美尼亚人(Armenian)组成。塔赫玛斯普一世将他们培养成为效忠于国家军事和政治机构服务的人员,以削弱对基兹尔巴什和土库曼贵族的依赖。
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基兹尔巴什受到强有力的牵制,新生军事力量逐渐取代其位置,王朝基本摆脱了基兹尔巴什军事力量的控制。阿巴斯一世继位后针对基兹尔巴什问题提出了改革措施。第一,阿巴斯一世创建了新的军事力量“古拉姆”(Ghulams)。古拉姆具体是指由奴隶出身的军人组成的军队,其兵源主要来自于皈依伊斯兰教的格鲁吉亚、塞加西亚、亚美尼亚和切尔克斯的奴隶,他们构成效忠萨法维国王、领取薪俸的新军势力,以扭转基兹尔巴什战士和土库曼部落贵族造成的政权离心倾向。1589年,阿巴斯一世在英国使者罗伯特·谢尔利(Robert Sherley)和安东尼·谢尔利(Anthony Sherley)的帮助下组建了一支由一万名古拉姆组成的骑兵力量。(19)参见Monika Gronke, Iran-A Short History,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7, p.85.1604—1616年,阿巴斯一世还招募了两万名亚美尼亚人和一万三千名格鲁吉亚人加入古拉姆,(20)参见Peter Jackson and Laurence Lockhar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The Timurid and Safavid Perio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65.扩充了军队人数,壮大了军队实力。除此之外,他还专门挑选三千名古拉姆战士作为自己的贴身侍卫,保障自身安全。据史料记载,在阿巴斯一世统治期间,领取薪俸的古拉姆新军达到了3.7万人,其中包括御林军3000人,骑兵1万人,使用传统兵器的步兵1.2万人,以及使用新型火器装备的射手军1.2万人。(21)参见Laurence Lockhart, The Persian Army in the Safavid Period, Der Islam, vol.34, no.1, 2009, p.89-98.在组建新军的基础上,阿巴斯一世对传统的基兹尔巴什军队采取了削减人数的措施,传统的基兹尔巴什由原先6万人被削减到3万人,空缺的部分由古拉姆填补。基兹尔巴什力量在人数上已经被古拉姆压制,其地位也逐渐被新军所取代。
阿巴斯一世牵制基兹尔巴什的措施之二是重用古拉姆和波斯文官,取消基兹尔巴什在各种行政机构中的特权。(22)参见冀开运、邢文海:《伊朗史话》,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年,第106页。阿巴斯一世在中央建立起由各部落的埃米尔、高层官员以及伊斯兰教的乌莱玛组成的御前会议,该会议的成员由国王亲自指派,必须对国王效忠。同时阿巴斯一世在地方上设置了限制总督权力的副总督,避免部落总督在地方上一家独大。另外,在军政事务方面,阿巴斯一世启用波斯文官和古拉姆。一方面,扶植波斯文官是为了促进萨法维王朝与本土波斯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在统治阶级内部提拔古拉姆则是考虑到其出身背景主要来源于战俘和奴隶,自身地位低下,只能通过效忠国王以获得政治权力。有史料记载,在阿巴斯一世统治的中晚期,古拉姆担任埃米尔的人数较多,而萨法维王朝最出色的89位埃米尔中,出身于古拉姆的占据15位之多,(23)参见David Morgan, Medieval Persia 1040-1797,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1988, p.137.古拉姆作为制衡基兹尔巴什及部落的重要力量开始发挥作用。
第三,阿巴斯一世建立王室直辖领地,进行土地改革,以削弱部落经济基础。以基兹尔巴什为基础的土库曼部落因建立萨法维王朝时立下功劳而获得大量封地,这些封地主要以“提乌里”(Tiyul)和“索尤加尔”(Suyulghal)两种形式存在,(24)参见Peter Jackson and Laurence Lockhar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The Timurid and Safavid Perio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555.前者是作为薪俸或维持军队开支而形成的土地制度,后者是指在无任何附加条件下获得的永久性封地。在此条件下,土库曼部落贵族不仅将土地的大部分收入占为己有,而且利用领地进行养兵练兵的活动,形成以土库曼部落为中心的地方行政中心。阿巴斯一世即位后针对这一现象实行了土地改革,建立王室领地,占有或扩大王室领地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以王权的权威性压迫土地持有者将土地以低价出售给王室。据纳斯里·阿拉·法尔萨菲(Nasr-allah Falsafi)在《阿巴斯一世时代的起居》(Zindagani-yi Shah Abbas-i avval)中的记载,在纳坦兹(Natanz)为阿巴斯一世效忠的税务官员就以专断的态度对待当地居民,企图将整个纳坦兹收归皇室领地,引起当地居民的抱怨和不满。(25)参见Peter Jackson and Laurence Lockhar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The Timurid and Safavid Perio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522-523.其二,对外实行军事行动直接吞并附庸国的领地,如1591年吞并吉兰地区,1596—1598年吞并马赞德兰地区,1597年吞并鲁尔地区等。(26)参见Peter Jackson and Laurence Lockhar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The Timurid and Safavid Perio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69.其三,国王要求基兹尔巴什归还封地,由国王直接统一管理,以扩大王室掌控领土的范围。同时,阿巴斯一世也顺利地将各地的税收权力控制在中央,这些收入直接用于王室以及新军古拉姆的军饷、物资等方面开销。由此,阿巴斯一世的土地改革改变了王朝土地制度的旧有格局,为国王直接掌控全国的领地提供了物质保障;但另一方面这也直接撼动了基兹尔巴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削弱了其在地方的政治地位和军事权力,加深了中央与地方、王室与部落之间的矛盾。
阿巴斯一世上任以来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有效地抑制了基兹尔巴什及土库曼部落的权力,加强了对地方政权的管理和控制,这位被称为“能够任意主宰国家臣民生死和命运”的君主在王朝遭到基兹尔巴什破坏之后从困境中闯出了一条改革之路。(27)参见J.Foran, Fragile Resisit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44-45.
萨菲一世至阿巴斯三世统治时期,基兹尔巴什随着王朝内部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而逐渐衰败。萨菲一世在位时期基本维持了王朝的稳定,并继续推行阿巴斯一世时期的政策,遏制基兹尔巴什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力。在阿巴斯二世统治时期,造就了萨法维王朝最后的繁荣时期。他继续整治国内分裂势力,加强对基兹尔巴什的控制。在土地政策方面,一方面继续扩大王室领土范围;另一方面采取政策限制王室土地的分流。阿巴斯二世亲政后,要求本属于基兹尔巴什管理范围的哈马丹、阿尔达比勒、克尔曼直接纳入王室领土的管辖范围,并且基兹尔巴什只有在王朝发生战争时期才能够征用上述地区。(28)参见贺婷:《萨法维王朝时期土库曼部落与国家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历史系,2016年,第84页。实际上,基兹尔巴什在萨法维王朝统治后期已经从昔日王朝的军事主力沦落为中央集权统治之下的傀儡。阿巴斯二世对禁卫军进行内部改革,更换禁卫将军,普遍任用波斯官员或古拉姆进入行政管理系统当中,只授予土库曼贵族一些小官职,将土库曼部落作为中央集权下的编外力量。(29)参见Najafi karim Barzegar, Intellectual Movemenys During Timuri and Safavid Period(1500-1700 A.D.), Indian Bibligraphies Bureau, 2005, p.235.阿巴斯二世的离世标志着萨法维王朝辉煌时代的正式结束。随后继位的萨菲二世至阿巴斯三世统治时期,王朝内部政治斗争激烈、军队乱象丛生,中央集权逐渐弱化,王朝外部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矛盾纷争日益加剧。这不仅导致萨法维王朝丧失大量领地,也损害了不同利益集团在土地政策当中的权益,特别是由基兹尔巴什和古拉姆组成的王朝军队土地薪俸问题,引发军队对王室的不满和抗议,加上对基兹尔巴什的限制也削弱了军队的整体实力,这也是导致萨法维王朝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
三、基兹尔巴什对萨法维王朝的作用及影响
基兹尔巴什是研究萨法维王朝兴衰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兴盛和消亡与萨法维王朝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萨法维王朝产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论及基兹尔巴什对萨法维王朝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第一,基兹尔巴什协助萨法维教团开创了伊朗历史上繁荣的萨法维王朝,再次实现伊朗高原的统一,促进了游牧部落本土化、波斯化的发展。对伊斯兰世界而言,基兹尔巴什是建设伊斯兰世界第三大帝国——萨法维王朝的主力军,辅助伊斯兰教完成了伊朗化的进程,建构起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宗教体系。在人力资源和意识形态两种力量的支持下,萨法维王朝将帝制制度和帝国政治文化体系扎根于伊朗高原。萨法维王朝是在伊斯玛仪一世领导的萨法维教团经过艰辛战斗和扩张的背景下而建立起来的,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取代白羊王朝的统治,而基兹尔巴什军队作为教团最主要的军事力量不仅没有因频繁的战争而削弱士气,反而吸引了来自叙利亚和中亚地区的1500名士兵加入其中。(30)参见Kishwr, Rizvi, The Safavid Dynastic Shrine: Architecture, Religion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Iran,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11, p.59.后来伊斯玛仪再次回到萨法维家族的发源地阿尔达比勒时,一批来自土库曼巴哈鲁(Bayburtlu)的士兵也加入到基兹尔巴什当中,(31)参见Roger Savory, Iran under the Safavid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5.进一步加强以基兹尔巴什为核心的萨法维教团的军事力量。土库曼部落在加入萨法维教团之后便皈依伊斯兰教,但其部落英勇善战、热衷扩张和掠夺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并且在萨法维教团征服运动当中充分展现了这一特点。最终,在与白羊王朝的决战中,由7000名土库曼部落士兵组成的基兹尔巴什军队战胜了敌军的30000人庞大军队,(32)参见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李铁匠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88—89页。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极大地增强了军队和萨法维教团的士气和信心。1501年,伊斯玛仪带领基兹尔巴什直接攻破了白羊王朝的政治中心大不里士,从此结束了伊朗高原漫长的分裂割据时代,再次建立起伊朗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第二,基兹尔巴什与萨法维教团在王朝建立初期共生共存,作为利益共同体共同面对敌对势力。萨法维王朝主要的宿敌是位于西部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东部的莫卧儿帝国,其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矛盾尤为突出,战争冲突也十分频繁,基兹尔巴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与奥斯曼帝国的察尔德朗之战中,伊斯玛仪一世率领以基兹尔巴什为主的六万名土库曼部落骑兵,配备以弓箭、长矛等落后的冷兵器前往应战。(33)参见黄维民:《奥斯曼帝国》,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66—70页。基兹尔巴什在这场战争中,武器装备无法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相抗衡,但基兹尔巴什还是凭借其骁勇善战令敌人畏惧,察尔德朗之战最终虽然以萨法维王朝失败而告终,但双方签订的《阿马西亚合约》暂时结束了与奥斯曼帝国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也迎来了两国关系短暂的“春天”。(34)参见蔺焕萍、王平:《论萨法维王朝与莫卧儿帝国的交往特点》,《商洛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13—18页。1576年,塔赫玛斯普一世还派遣250名基兹尔巴什士兵和使臣携带大量礼物前往奥斯曼帝国祝贺苏丹穆拉德三世继位。(35)参见黄维民:《奥斯曼帝国》,第95—97页。16—17世纪,萨法维王朝与莫卧儿帝国之间也存在着交往与冲突。伊斯玛仪一世时期,萨法维王朝派遣两名基兹尔巴什将领率军前往莫卧儿帝国协助攻打帖木儿帝国的都城撒马尔罕,夺回其领地。(36)参见李文业:《印度史:从莫卧儿帝国到印度独立》,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页。塔赫玛斯普一世时期,派出一支基兹尔巴什援助国王胡马雍平定阿富汗人舍尔·苏尔的叛乱。(37)参见彭树智:《阿富汗史》,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115页。
第三,从基兹尔巴什过渡到古拉姆新军的建立,标志着萨法维王朝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火器)时代。在阿巴斯一世掌权时代,他从历次对外战争中汲取教训,意识到古拉姆在武器装备和战术层面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因此他计划组建由奴隶军(Qullar)、射手军(Tufangchis)和炮兵军(Tupchis)构成的新军。(38)参见刘继豪:《论萨法维王朝合法性的建构》,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历史系,2020年,第69—79页。新军的人选大多从非土库曼部落当中招募,奴隶军主要来源于战俘。射手军本由步兵组成,但后来逐渐向骑兵部队发展,这支部队多由波斯农民组成,包含少量的阿拉伯人、土库曼人,仿照奥斯曼帝国耶尼切里新军的训练模式,并且培养他们使用火器的技能。在阿巴斯一世时代,这支射手军总数约为12000人。(39)参见Laurence Lockhart, The Persian Army in the Safavid Period, Der Islam, vol.34, no.1, 2009, p.89-98.炮兵军的发展也很迅速,在谢尔利兄弟的帮助下炮兵军队伍也达到了12000人,同时拥有几百门火炮。但是当时的萨法维王朝不具备制造火炮的技术和能力,大部分都是从西班牙和托斯卡纳公国进口购买的,在引进欧洲技术人员后在当地兴建火炮厂。(40)参见Laurence Lockhart, The Persian Army in the Safavid Period, Der Islam, p.89-98.由此可知,在古拉姆新军建立之后,统治者加强军队先进武器装备,仿照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配置和训练模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既加强王朝自身军事实力,也利于逐渐推动伊朗与欧洲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论及基兹尔巴什对萨法维王朝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基兹尔巴什权力逐渐扩大致使其严重威胁王朝的稳定。查尔迪兰战役成为萨法维王朝与基兹尔巴什关系的转折点,战争的失败打破了伊斯玛仪一世在基兹尔巴什心中的神圣地位,军队内部分崩离析,土库曼部落贵族借基兹尔巴什之力开始干涉国家大政,抢占王朝领土。伊斯玛仪一世限制基兹尔巴什的权力时,引发了他们的不满和抗议,甚至在1523年谋划刺杀波斯文官伊斯法哈尼(Mirza Shah Husayn isfahani)以向王朝示威。(41)参见Charles Melville, Safavid Persia: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an Islamic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I.B. Publishers, 1996, p.79.塔赫玛斯普一世在位的前十年,王朝内部形成了三大土库曼部落为争夺摄政权力对峙斗争的局面,这代表着三大土库曼部落的基兹尔巴什军队彼此之间开始因利益而有分裂的趋势,面对塔赫玛斯普一世,他们更是表现出对王权的蔑视。土库曼部落在掌握基兹尔巴什的情况下各自为政,造成帝国分裂割据的局面,王朝经济的恶化。第二,基兹尔巴什是加速萨法维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阿巴斯一世继位改革前,萨法维王朝在基兹尔巴什的内讧中虽几近灭亡的局面,但最终得以幸存。阿巴斯一世之后的统治者过分削弱基兹尔巴什的力量,甚至建立新军以替代其地位,撼动了王室与军队之间的平衡点,反而激起了以基兹尔巴什为主的土库曼部落的反抗情绪。因此在萨法维王朝末期,阿富汗部落威胁王朝安危后便得到了基兹尔巴什和土库曼部落的支持。
四、结语
基兹尔巴什的成立对萨法维王朝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且具有两面性。萨法维王朝正是依靠基兹尔巴什军队的力量打败白羊王朝,建立起伊朗新政权,并维系统治220年;基兹尔巴什协助萨法维教团建立了强大的萨法维王朝,再次统一了伊朗高原,重新实现了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以基兹尔巴什为主的土库曼部落皈依伊斯兰教,无疑为萨法维教团的征服运动增加了新生力量。我们既要肯定基兹尔巴什在伊朗历史中积极的一面,也要反思其最终与王室之间产生矛盾并愈演愈烈的原因。因此,如何处理国家与军队、王朝与部落的矛盾与冲突,是当时萨法维王朝乃至中东地区以部落联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都需要面临和解决的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