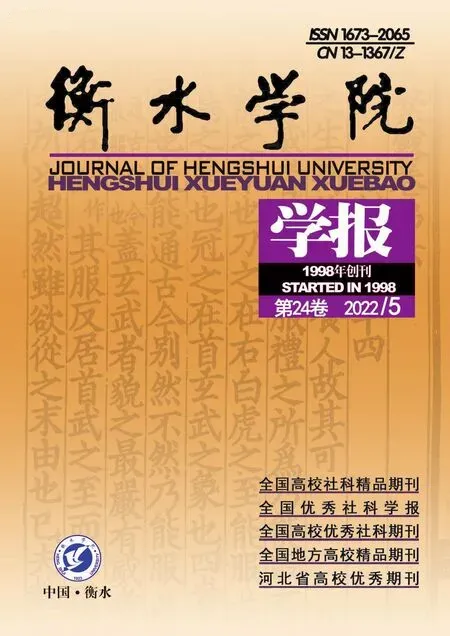“史实”:董仲舒以及苏舆的春秋公羊学
2022-03-17刘芝庆
刘芝庆
(湖北经济学院中文系,湖北武汉 430205)
《春秋》之书,公羊学者多认为是部拥有庞大寓意的经典,虽然不是全部文字段落都可以含有密码,可是许多寄托喻义,言此事而意在彼,表面是说某史事,却是借由论述史实而展露微言意旨,微言大义,以古改制。换句话说,将《春秋》视为一个完整的寄托系统,表面是讲齐桓晋文与鲁国诸公之事,其实多是象征,比事属辞,另有其他蕴含所在,此即孔子之旨①《春秋》三传,探察微言,觅求史义,皆重叙事,所谓书法,即事显义,寻绎微辞隐寓,都以属辞为重。相对于西方叙事学,强调情节推动、形象塑造、情节穿插,各有侧重点,颇有异合。三传互较,则《左传》更以叙事解经见长。可见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16年版)。张素卿《叙事与解释——〈左传〉经解研究》(台北书林出版社1998年版)。。
当然,以上只是原则性的说法,因为《春秋公羊传》并非事事寄托,句句微旨,字字都有深意,虽说公羊学家多把《春秋》的托寓意符,视为解经的关键,却不代表他们都认为这些史实全部都是假的,都是重构,都是意在言外,都是虚拟现实。公羊学者间,彼此论史事的差异,以及他们各自的“历史性”立场,颇值得注意。
从这角度来看公羊学,来看董仲舒,就有许多值得讨论之处。武帝即位之后,曾下了一份诏书,以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之后在元光元年又诏贤良察策。在两次诏问之中,最著名的响应就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故董仲舒论治道,以《天人三策》与《春秋繁露》最为重要,都跟他的立场有关,也源自他的经学,特别是对《春秋》的理解。《史记·儒林列传》:“唯董仲舒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就董仲舒看来,经学是他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资源,他以公羊学的角度,在学术与政治交涉中,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里,擘划政策,企图开物成务,以经学论政,以经学改制更化。但是,从经学世界到国家社会,言政论道,董仲舒是怎样解读《春秋》?《春秋》经传的差异,他又如何看待?微言大义,通于改制,他到底要怎样厘清?这是本文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近代以来,《春秋繁露》以凌曙、苏舆二种注本,最广受引用,而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又是以凌曙注本为底稿,参酌史料,多加发挥而成。关于《春秋繁露义证》的研究,学界多聚焦在他对康有为的批评,目前已有专门的博士论文,处理这个问题[1]。也有多篇论文①关于苏舆的研究,丁亚杰曾有《台湾地区研究苏舆的概况》(《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4年第1 期)。,讨论他与康有为的差异,综合这些说法,大多是指出:康有为以今文经为主,苏舆则是今古文并取;苏舆并非反对改革,但他批评康梁式的做法,也不认可革命;《春秋》是立义之书,不是改制之书②相关论点,除前引书之外,另见姜广辉、李有梁《晚清平实说理的公羊学家──以〈春秋繁露义证〉的诠释风格为例》(《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 期)。姜广辉、李有梁《维新与翼教的冲突和融合——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读》(《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 期)。卢铭东《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 期)。。
本文主要指出,苏舆等人的现实环境,与董仲舒不同,他们那时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也与汉代颇有差异,而公羊学经过何休之后,颇有转折。只是述古与立义,经世与改制,康苏二人依此解董,循此解经,都有所见,也有所偏。关键就在于董仲舒到底怎么看待《春秋》?如何解释史事?其实董仲舒的经学,本就通于史,文史通义,如两束卢,互倚不倒。本文的研究,即是回到董仲舒的公羊学,重探其说,然后顺流而下,比较苏舆的批注,旁及康有为。参酌比较,述其相同,显其差异,说明并解释他们公羊学的特征。
一、史义并重,经世致用的《春秋繁露》
继往开来,解释经典中的典章制度,古为今用,一向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环节。在古人的认知里,经典并非束之高阁的图书馆书籍,而是斟酌损益,因应人情之后,旧瓶装新酒,可以因应于时代,切合于社会,复古而开新的。《春秋》一书更是明天人相与、通阴阳五行,是治国的大经大法,董仲舒自己便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③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台北宏业出版社1996 版,第2523页)。西汉公羊学,特别强调大一统,并主张崇让观,显然与西汉从分封功臣,到分封诸王的历史有关。武帝时期,诸侯王多有骄恣,武帝胞兄胶西王,便是其中之一,所以特地命董仲舒为胶西相,此所以有《春秋繁露》其中《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之作。可见张端穗《西汉公羊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版,第12页)。根据陈苏镇的研究,他就认为在士大夫与儒生的推动下,《春秋》是汉代立法与推行政制的主要经典之一,极为重要[2-3]。
董仲舒身属其中,也不例外。董仲舒与《春秋》的关系,正如林聪舜所言:“西汉的尊儒运动不始于董仲舒,董的独特贡献在于替‘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做出新诠释。在理论的步骤上,董首先提高《春秋》的权威,他神化孔子和《春秋》,再透过对《春秋》的诠释,使他能效法孔子托乎《春秋》以改制,作为建立帝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据。在对‘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新诠释下,董仲舒有关尊君、大一统、改制、受命、三纲、阴阳五行宇宙图式等一整套建立帝国意识形态的理论,都可在经典,特别是‘《春秋》之义’中,找到立论的根据。”[4]
董仲舒的解经学,在《春秋繁露》有更完整的说明。《春秋繁露》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在此之前,并无董仲舒撰《春秋繁露》的记载,故历代不乏质疑非董氏著作的声音,经过学者考证,现在大致可以做这样的判断:《春秋繁露》全篇不一定就是董仲舒亲自著作,但即使是由后世弟子或后人编著,仍可代表董仲舒的思想④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宋人程大昌,稍晚的黄震也提出类似看法,他们大多认为《通典》《太平御览》等书都有转引文字,但查今本《春秋繁露》却皆无记载,而且此书文意浅薄,不似董仲舒所为,加上有些篇幅混杂难分,因此断定非董仲舒著作。对此疑案,近人徐复观先生已有考证,他认为这些质疑最多只能说明此书有残缺,但并非伪书,而且文辞并不肤浅,总之,《春秋繁露》固然可能是由后人整理而成,但仍可代表董仲舒的思想。近人戴君仁亦提出董仲舒不讲五行的观点,他认为《汉书·董仲舒传》只讲阴阳,未言五行,将《汉书》与《春秋繁露》比照,当然应该是以《汉书》为主,徐复观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天人三策》的中心内容是刑德之说,以刑德配合阴阳,这也正是《春秋繁露》的讲法,因此董仲舒没有在《天人三策》中讲五行的必要。邓红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衍,他认为《天人三策》确实有类似五行的说法。除此之外,日本学者如庆松光雄、田中麻纱已、近藤则之等人也对《春秋繁露》的一些篇章(特别是有关五行的篇章)提出质疑,但这些说法已有学者驳之。可参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194页),邓红《董仲舒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195、264-276页)。。
大体来说,董仲舒的理论,主要的对象是君王。他以公羊学解《春秋》,《春秋》寓涵了王者改制之道,因此破解圣经,就成了他所发现之秘,但是解经法,事实上又是为世立法,必有赖君者实践。他将修身治国的原则性带入其中,修身立道,就是法天而行,具有参化天地的神圣感体验,表现在对礼的各种实践中,“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5]275。形式即是内容,法天尊天,一循天道,就包括了改制更化。
因此,政教散布,移风易世,以圣转俗,启文明,开国运,教化行而习俗美,有节,有度,有制,有教,有序,有美,有质,有文,王道政治方成,这也是董仲舒的真正的理想,皆源自他的经学世界,所以他主张要重视《春秋》。《春秋》之所以成为君王治国的方针,就是因为上探天端,奉行天道:“《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循规矩,不能正方员。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①董仲舒的春秋经世,其具体运用之法,参看刘芝庆《王道、经学与身体——重探董仲舒的春秋学》,收于氏著《从指南山到汤逊湖:中国的知识、思想与宗教研究》(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19年版)。
顺着这样的观点,在董仲舒看来,《春秋》奉天法古,是部经世之书,却非人人都能体会其义,与其欲托之空言,不如深切著明之于行事。因此,该如何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观其人,察其物,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透过事,看到义,就成了重要的关键:“《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渺者乎?故案《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5]56董仲舒谈更化、述无为、论六科十指、讲绌夏亲周故宋,自然是要从经学谈到政治,以经学来改变世界。但这样的观点,都非胡思瞎想,或是纯粹抽象的道理,而是在具体的过往之事中,在这些力透纸背的文字叙述之中,真理乍现,发挥而来。
所以董仲舒在谈《春秋》之事时,他的所谓改制,并非真的去假设、建构一个曾经的存在,更不觉得史事都只是工具,求得义理之后,就可抛弃,丢到资源回收桶。他是透过不断地辨析问难,澄清相关的历史事件,建立某些观点。对他而言,托古其实就是溯古,挖掘曾经,重建情境,这样的史事复原,述往事,思来者,必定包含着解释,还有价值判断。他在试图理解过去时,也常常自设辨敌,故意提出质疑,虚设主客与往复问对,执经问难,其实也是两汉经师常见的研讨形式②这种方式,也表现在汉代辞赋,并影响后来的玄学清谈。可参唐翼明《魏晋清谈》第二章(台北东大出版社1992年版)。。
例如他分析齐顷公家世出身,以至于影响他性格。这些记载,在《春秋》只是寥寥数语:
(宣公)十有二年,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师伐陈。卫人救陈。
(宣公)十有三年。春,齐师伐莒。
(宣公)十有七年。己未,公会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断道。
(成公)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
《左传》对此经文,说:“十七年,春。晋侯使郄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郄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献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郄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齐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会。及敛盂。高固逃归。”[6]717-718“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6]771-772《春秋》经文,条列而已,前因固然不知,后果尚也未明,《左传》则是叙述清楚,史事畅达。董仲舒则不一样,他是要在这些事件中,看出端倪,发现意义的,于是他既要说明历史,更要评判论衡:
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于诸侯。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晋、鲁惧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卫、曹,四国相辅,大困之鞌,获齐顷公,斮逄丑父。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5]143
齐桓公之后有孝公、昭公、懿公、惠公,然后则是顷公。齐顷公自以为名门之后,得霸主余荫,骄傲自尊,自以为是。他曾率兵攻打鲁、卫,二国向晋国求援。郄克带领援军,讨齐以救鲁、卫。结果鞌之战,齐顷公大败,身辱名羞,几乎亡国。幸好部下逄丑父代君而死,齐顷公才逃过劫难。董仲舒论史记事,还要发挥一番议论,才说:“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以史为鉴,事实在经书中,需要析论而后大明,故《春秋》大义,得失、是非、贵贱、尊卑之类,都由史而见,我们引以为训,见贤思齐,不贤则自省,然后运用在当下,这才是春秋经事的关键,“《春秋》,大义之所本耶?……然后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故志得失之所从生,而后差贵贱之所始矣”[5]143。至于逄丑父,他自然也有见解: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5]59-60
董仲舒自问自答,逄丑父代君而死,自殒而存君,为何仍不算权?他以祭仲与逄丑父作比较,分析二人行事史迹,逄丑父所为,其实更难于祭仲,但后者见许,前者为非,这就是《春秋》难读,又具有深义的地方,知人论事,是非难别,由此可见。
因为行为相似,理有不同。相似之处,存君;相异之点,则是辱君。祭仲先是驱逐郑昭公,扶位郑厉公,后又重立郑昭公,《春秋公羊传》称许为知权,原因是知权而反经,“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7]。君王退位废立,祭仲出突(郑厉公)入忽(郑昭公),“少辽缓之,则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表面上来看,违反君臣之礼,可是郑昭公去而复返,前枉而后义,结果是对大家都好的,“然后有善者也”。董仲舒的解释,却非如此。他并非以收场答案,而是以行为的属性与内涵来看的:
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至尊为不可以加于至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故难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然方获而虏邪。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当此之时,死贤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以为不然?复察《春秋》。《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日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5]60-62
逄丑父欺晋获罪,又让齐顷公免辱于宗庙,此事虽难,但仍不被认可,因为他的行为欺而不中权,前正而后枉,忠而不中义,导致君王“获虏逃遁”。董仲舒从这件事中得到的启示与意义,境况不同,在那当时,死贤于生,与其辱而生,不如死以荣,所以逄丑父人虽死,但行为处置不恰当,仍不能算是大义,不算权变,行为导致的结果,“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但就这件事来看,辱大于荣,原因就是天子至尊,或是最高领导人,不可以受到至辱大羞①《春秋公羊传》称赞祭仲,是因为知权,导致有好结果;但董仲舒称许,原因则有不同,是因为他认为祭仲让国,使他的君王具备了让德。张端穗《西汉公羊学研究》,第162-163页。关于对祭仲评价与公羊学的问题,可见蔡长林《从对祭仲评价的转变看公羊学经权说的历史际遇》(《汉学研究》2017年第2 期)。。
毕竟,义藉事而显,事也因理而明,空谈哲理,虚说史事,都是没有意义的,所谓的托古,其实是述古,或者是说古,在董仲舒“历史性解读”的春秋公羊学中,历史事实与价值理念是合一的②此处所谓的历史事实,并非全是我们现今所谓的真相。历史当然是有真相的,但真相是否一定是客观而绝对的,颇可多论,当代后现代史学对此,多有分述,因非主题重点,故不赘述。可参古伟瀛、王晴佳《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8页)。本文所指的是“历史性解读”。董仲舒解释史事,以求大义,显然有其“历史性”的刻意解读。所谓的“历史性”解读,根据黄俊杰的看法,是指解读者因身处时代的历史情境与历史记忆,以及其思想系统所致,都会影响解读者以自己的“历史性”,进入文本的思想世界。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46-48页)。。这种名实相符的观点,表现在他的《深察名号》,过往学界多将焦点放在“名”本身,已有许多深度研究,其实董仲舒由名号谈及性情问题,看起来都是谈论符征与符旨,本身内在理路却饶有深义。首先,董仲舒强调“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5]260,名真不分,故名号,代表真实,有其称号,往往也有相应的价值理解。我们观看古今世界,从过去到现在,从理解到实践,就要循名责实,以名来探究其真。这个名与真,其实就是另一种的大义,释名以章义,就像董仲舒从齐顷公、逄丑父、祭仲等人看到的道德意义,名实事理,是不可分也不必分的,所以他说:“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也,犹绳之审于曲直也。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已。”董仲舒批评逄丑父,称赞祭仲,就在于他以君王之名实,来审核逄丑父之行为性质,脱离大义,名实离分,“名者,大理之首章也”[5]285。
正因为这类的述古,并非借托,空言其事,甚至是向壁虚构,虚拟故事,而是他真的去探究过往,研究史迹,做出历史性的解读,并深察名号,将君子夫妇父子尊卑之类,正其名,定其真,而大义是非曲直,常常就在名实离合之间,决定取舍。但是我们又该如何做?才能循名责实,由名而知真,进而理解并实践大义呢?将价值理念体贴到古今世界呢?董仲舒说,名号出于天,《春秋》奉天法古,因此解读体知《春秋》,自然是必行的步骤——其实更广泛地说,阅读经典,本就是一种修行,循天道,修身而行:“循天之道以养其身,谓之道也。”[5]444于是《深察名号》,笔锋一转,谈起了性情:“今世闇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试反性之名?……性之名不得离质,离质如毛,则非性已,不可不察也。”[5]291“身之名取诸天……;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5]293
以经学而通天人,明治道,这方面的看法,董仲舒的性情论,以及法天而引起的修身问题,与柏拉图的“模仿”之说,颇有异同③本文重在讨论董仲舒如何解释过去,至于他如何改变当下,可见刘芝庆《王道、经学与身体——重探董仲舒的春秋学》,收于《从指南山到汤逊湖:中国的知识、思想与宗教研究》。。因为,就董仲舒看来,王者循天道,修身而行,都不是简单的比附而已,他认为在这个世界里,人与天是息息相关的,联类共感,气化相应,学者或称为“联系性思维方式”[8],或以“引譬连类”为主[9],又或是讲成“同源同构互感”[10],其意大多类似。但这种联系引譬,互感联类,很多都是由身体触发的。这种触发,正是人有感于外在环境变化的深切感受,人要理解外在环境,才可能因应外在环境,做出比较好的选择,董仲舒的“法天”,即是指此。如果就柏拉图看来,天人关系,可以说是一种“模仿”,他主张人类应当效法天体的运动,天上的秩序正好就是人间城邦最好的模型,因此要和谐,避免冲突,法自然四时,弗雷德(Drothea Freda)感到难以理解,说如果这是比喻,或许还可,但如果真的要效法,究竟该怎么做,才不至沦为空谈?人到底要学习天上的什么东西?又该怎么学习?他的回答是:“因为他的目的也许不仅仅是要将宇宙秩序投射到地球上或是按照天体秩序塑造人类的灵魂,而是想要永恒的灵魂与永恒的身体之间设计出一种理想的关系,并且展示人类在这一方面所能学习的东西。”①多罗西娅·弗雷德著,刘佳琪译《柏拉图的〈蒂迈欧〉:宇宙论、理性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值得注意的是,陈昭瑛从神话思维与原始分类的角度,来分析董仲舒天人思想,并与荀子做比较,有很深入的讨论。可见陈昭瑛《荀子的美学》(台湾大学出版社2016 版,第318-329页)。
由此可见,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谈史事,并非全把史事认为是孔子寓托,而是视为实际发生的事情;过往之事何其多,邻猫生子,鸡毛蒜皮,难以尽记,故孔子写上某事,又如何写,笔锋浓淡,取舍之间,便大有可说。于是透过言内之事,来探求言外之意,就成了董仲舒非常在意的问题,借用钱穆的书名,这就是“中国历史精神”,只有精神,没有历史,是不够的,更不能有了前者,遗忘后者,躯体存有,灵魂欠缺,也不行。所以言内与言外,史事与义理,是相辅相成的,他才又有六科十指之说,金针度与,示人门径,告诉我们该以何种原则,解读《春秋》,六旨(六科)并非要把《春秋》大义分为六类,而是指出《春秋》义法的彰显目的与效用[11],所以才就得失贵践、法诛罪源深浅,又或是君臣尊卑之道而论,用意在于说明“幽隐不相踰,而近之则密矣,而后万变之应无穷者,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再者,董仲舒也认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涉之事极为广博,但大致有十点要义,此即“十指”。董仲舒以十指之论,对《春秋》义法发凡起例,而《春秋》又隐含王者改制之说,因此十指不但是事之所系、属辞比事,但同时也是王化所流,所以十指是解译的方法,要从《春秋》史事中,明《春秋》大义。
二、立义而微言的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但是,董仲舒这样的看法,由苏舆解释起来,却颇有差异。如前所述,关于苏舆的注疏研究,学界多强调康苏之异。确实,苏舆反对康有为等人的公羊学,他在《翼教丛编》中的序言就说:“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至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12]21托古改制之说,也是他不赞成的,因为他认为孔子并非素王,改制一事,只能由君王来办,儒生只能是建议,无法担任第一人,更不可虚构名号,以己意行之。所以《春秋》是立义,不能是改制之书(芝庆按:为方便说明,区别董仲舒原文,下引苏舆注语,批注自将标明):
《春秋》为立意之书,非改制之书。制非王者不议,义则儒生可立。所云“参酌”“中制”,亦祇是立义耳。[5]112-113
孔子虽然伟大,毕竟只是儒者,不是君王,不能越位,更不可能有《孔子为改制之王》《孔子为新王》《孔子为素王》《孔子为文王》《孔子为圣王》《孔子为先王》《孔子为后王》《孔子为王者》之类的讲法②这些都是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八的标题。。他对近来许多说法感到不满,特别是康有为:“余少好读董生书,初得凌氏注本,惜其称引繁博,义蕴未究。已而闻有为董氏学者,绎其义例,颇复诧异。乃尽屏诸说,潜心玩索,如是有日,始粗明其旨趣焉。”[5]自序,康有为著有《春秋董氏学》,其公羊家改制说,名满天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影响当时学术甚巨①据钱穆所言,在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前,学界弥漫其说。之后才由他摧陷廓清,影响所及,甚至很多大学都不再开设经学课程。钱穆此文,贡献自然很大,但其实经学课程仍有许多,而讲课者也常偏向公羊学。车行健《现代学术视域中的民国经学:以课程、学风与机制为主要观照点》第一章(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11年版)。。故“改制”与“立义”之分,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他认为那些人的说法,过于凿空,义理也有问题:“光绪丁戊之间,某氏有为《春秋董氏学》者,割裂支离,疑误后学。如董以传所不见为‘微言’,而刺取阴阳、性命、气化之属,摭合外教,列为‘微言’,此影附之失实也;三统改制,既以孔子《春秋》当新王,而三统上及商周而止,而动云孔子改制,上托夏、商、周以为三统,此条贯之未晰也;鄫取乎莒,及鲁用八佾,并见《公羊》,而以为口说,出《公羊》外,此读传之未周也。其它更不足辨。”[5]3
就他看来,《春秋》是不住空言,深切著明于行事的,“空陈古圣明王之道,不如因而着其是非得失,知所劝戒”。他解释董仲舒“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在董仲舒提及宋襄公、晋厉王的基础上,说:“因成知顺,桓文是;因败知逆,鲁庄、晋厉是;亦有因败而得其顺者,宋襄是也。假位号,因成败,此圣人作《春秋》之意。因故是以明王义,事不虚而义则博贯。”[5]163所以不能跳过这些史事,空言道理,甚至穿凿附会:“《春秋》之文,非徒为讥刺而已,将使后之王者观其效以审其原,察其文而修其实,有以得存亡之枢要也。”[5]129-130
可是,董仲舒明明也有改制的文字,《楚庄王》《符瑞》,甚至《三代改制质文》,还刻意标明,苏舆又该如何处理?他认为改制,其实就是立义,是儒者相传旧说,更是汉初儒者通论,为董仲舒所援用。改制用意在于改末流之制,后人误会,还以为董仲舒开端起例,发明改制,实乃大误:“故余以为董子若生于太初后,或不龂龂于是。”因此这跟孔子没有什么关系,当今妄者误以为王即是指孔子,就是荒谬:“妄者至谓王者即孔子,谬不足辨。”[5]16至于董仲舒原文“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苏舆也特地解释:
制可改者也,惟王者然后能改元立号,治礼作乐,非圣人所能托。道不变者也,周德既弊,而圣人得假王者以起义而扶其失,俟来者取鉴。[5]28
夫《春秋》立义,俟诸后圣。后圣者,必在天子之位,有制作之权者也。汉之臣子尊《春秋》为汉制作,犹之为我朝臣子谓为我朝制作云尔,盖出自尊时之意,于经义无预也。[5]29
制是可以改的,但道不变,只有天子才有制作之权,只有王者才能改元立号。王者、天子、皇帝都是真实的存在,不是圣人虚构伪托。周德既弊,圣人只好取譬连类,借题发挥,以王者之名,来谈这些立义改制的问题,供后者取鉴参考,但改制者只能是皇帝天子,所以《春秋》立义制作,有待后圣,而后圣必须在天子之位。儒者只能议,不能立,这是大义所在,不能变通的。
若然“假王者以起义而扶其失”,则苏舆必要面对的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人事物,哪些是真的史述,哪些只是圣人夺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也因如此,他连董仲舒的三代改制说,都要否认,认为非有其事,不是事实。书中所言,只是师说,敷衍推展,不是经文本身。既然无事实可据,三代制度又言人人殊,读者只要知道“义”,不必拘泥于“史”。因为道是不变的,制是可以改的,所以真的弄不清楚条制科表,也没关系,并非重点,他指出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的问题:
三代殊制,见于……诸篇甚多。……皆师说所传异制。学者质文随习,不必尽合。本篇所记,但述师说。制于以《春秋》当新王诸义,不见于传,盖为改正而设,与《春秋》义不相属。此云改统,自是一时师说,与《春秋》不相蒙也。[5]184
苏舆论改制差异,目前学界的研究,多聚焦在以口说之《春秋》,发挥微言之《春秋》,上头引文的师说祖述,不见经传云云,皆可由此理解。正如郭晓东所指出:康有为的公羊学,强调“口说”一脉,虽颇为切合董仲舒之学,不免过度发挥,诠释太多而证据太少[13]。
但是,本文要另外指出的是,苏舆与康有为的差异,如果由董仲舒原文看来,两人颇有共同点,即
是认为《春秋》之史,不必求实,也不用完全当真。所以他左一句不相蒙,又一句不相属,学者质文学习,得其微言,知其大义即可,不必尽合。
苏舆又自问自答,说:“本书《三代改制》篇,明以《春秋》为一代变周之制,则何也?”答曰:“此盖汉初师说,所云正黑统、存二王云云,皆王者即位改制应天之事,托《春秋》以讽时主也。”[5]16汉初师说,口耳相传,为讽时主,得其意即可,不是历史,不必在意。因此《三代改制》是当时儒者所言,董仲舒也在其中,是托《春秋》以讽时主罢了。
但是董仲舒显然不是这样看的,如上节所言,董仲舒秉持事理合一,史义不分的原则,文章开头就标明《春秋》“王正月”,又引用传,说王就是周文王,他受命而王,所以应该要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这是《春秋》的微言大义,这种历史记载,充满了丰盈的理念。前人如此,后人亦然,他期勉时主(汉武帝)也该如此做,只是服色礼乐等,要因时而变。后王与前王一样,秉授天命,就应改制作科(制作条规)。首先要在十二种颜色当中选取一种作为正色,然后以黑统、白统、赤统根据寅、丑、子的逆序循环搭配,黑统以建寅月为正月(一月),其中舆服昏冠刑乐都有相应的制度:“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舆质黑,马黑,大节绶帻尚黑,旗黑,大宝玉黑,郊牲黑,牺牲角卵,冠于阼,昏礼逆于庭,丧礼殡于东阶之上,祭牲黑牡,荐尚肝,乐器黑质,法不刑有怀任新产。”“斗”即是北斗星,北斗七星第五至第七颗为斗柄,四季月分即是根据斗柄所指的位置来划分。黑统尚黑,因此朝见服、帽子、路舆、符节、印授、旗子、乐器等,都是以黑色为主。白统则以建丑月为正月(十二月),亦有相应制度:“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舆质白,马白,大节绶帻尚白,旗白,大宝玉白,郊牲白,牺牲角茧,冠于堂,昏礼逆于堂,丧事殡于楹柱之间,祭牲白牡,荐尚肺,乐器白质,法不刑有身怀任。”赤统则是以建子月(十一月)为正月,“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舆质赤,马赤,大节绶帻尚赤,旗赤,大宝玉赤,郊牲骍,牺牲角栗,冠于房,昏礼逆于户,丧礼殡于西阶之上,祭牲骍牡,荐尚心,乐器赤质,法不刑有身,重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文质互补,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正如本文所提出的,苏舆也讲“实”,如前引“察其文而修其实”“事不虚而义则博贯”,但与董仲舒做法大有不同,苏舆多只是强调不可空言,不要随意胡说之类。他对史实的强调,深察名号,远远比不上对道与义的深耕探求:“《春秋》以立义为宗,在学者善推耳。故孔子曰:‘其义窃取。’然而笔削之意可窥事者,落落大端而已,以俟读者之博达焉。”[5]12杨树达为他写墓志铭,也说先生平时持论,说汉儒制经有两体,一是注重训诂名物,二则是重大义,“董生之书实为言义理之宗”“汉儒之学,当首举董生”[12]258。故苏舆批注《深察名号》,就只注重名号背后的实,苏舆说这是名家之学,以综微核实为功,公羊学即与此同。就像凸显史事背后的大义,综微核实,实虽是附名而来,其实比名更重要。他忽略了董仲舒是名实双彰的,甚至可以名来规范实,可以曲直委屈的。更进一步来说,如果这些史文,只是器,只是工具,明道知义,则得意忘言,得鱼忘筌,甚至可以以后者否定前者。他对三代改制的质疑,与其说是对口说系统的不满,对康有为的不认同,也可以说他对于史实的追求,不同于董仲舒,而偏偏就在这一点,他与康有为,颇有相似。
由此可见,苏康之同,都是认为义是第一序,事是第二序。固然理在事中,义在史中,不能离事言理,但他们并非真的都认为事是真的。或寄托,或比喻,或联类,或借譬,皆无不可,第二序对他们而言,因为述说所及,有必要,也有需要,却相较于第一序,其实没那么重要,不必拘泥,也不要完全求真。因此康有为谈史,他的论证,是披着考据的外衣,自己的话多,古人的话少;而苏舆,或资料排比,或训声考字,看似较为稳妥,如姜广辉所言,是“晚清平实说理的公羊学家”,其实也不是要呈现历史真相,他是要钩沉微言大义的,发挥立义之书的。所谓的春秋之旨,很大目的又是为了推翻近来公羊学,特别是康有为之说。所以他才会说董仲舒三代文质,并不可信。
于是,当他们把握到所谓的真理之后,则事可无不可,或得鱼忘筌,历史如何,已非重点;又或是以理限事,义大于事,用他们的研究得来的微言大义,来解释更多的线索或史实。例如苏舆反对康有为,认为孔子并非真的行王事,董仲舒也不是这样解释《春秋》,对所谓的“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春秋繁露》引孔子言),就不厌其烦地说:行事,是往事,而非真行其事,实行其义,因此胡安国称赞孔子著书,行事深切著明:“仲尼以为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5]161他就批评胡安国搞错了,行事不是孔子行王事,而只是孔子假鲁史言王法①胡安国也说孔子改制,只是不在其位,不敢自专,所以只好以特笔微写,尊时王,又希望新王有改制之责,因此孔子“行事”,当然是有改制之实的。但苏舆只强调孔子不能有王者改制,就身分上着眼。关于胡安国的说法,可参蔡长林、陈颢哲《“王正月”解读视角的转变及其意义》,蔡长林编《林庆彰教授七秩华诞寿庆论文集》(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18年版)。。
其实,二人看似复古,都有着时代因素,影响所及,“本意尊经,乃至疑经”,就学术史的内缘观察来看,如果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上承清代今文家的解经、崔述的《考信录》,经廖平、康有为,最后到胡适、顾颉刚,从尊孔——疑经——破古,到“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神话分化说”,因为尊经,导致疑经,进而不信古,重新评估一切价值,考辨伪书、区别伪史、破除伪说,康有为正是其中一个关键[14]。如今看来,苏舆也不会在这个脉络之外。
三、结论
本文指出,董仲舒公羊学的特点,在于即事言理,所以才要深察名号,史义合一。他谈改制,说更化,讲无为,都是从过往历史中,见微知著,发挥挖掘而来,这种历史性解读,颇为明显;康苏则否,康有为“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15],于是孔子改制,孔子为素王,孔子立法,既知如此规律,知义便可离事,不再受限于所谓史的制约:
“缘鲁以言王义”,孔子之意,专明王者之义,不过言托于鲁,以立文字。即如隐、桓,不过托为王者之远祖,定、哀为王者之考妣,齐、宋,但为大国之譬,邾娄、滕侯亦不过为小国先朝之影,所谓“其义则丘取之”也。自伪《左》出,后人乃以事说经,于是周、鲁、隐、桓、定、哀、邾、滕,皆用考据求之,痴人说梦,转增疑惑,知有事而不知有义。于是,孔子之微言没,而《春秋》不可通矣。[16]
康有为认为尧、舜、周公、成、康等所谓先王,皆是所托之古。诸子改制,为当时风气,而孔子为诸子之卓、为制法之王,更亦如是,所以周、鲁、隐、桓、定、哀、邾、滕等,都是托古以立文字罢了,康有为此说,不免以理限事[17]。苏舆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认为《春秋》行事,固然深切著明,不可空言,但首在立义,一旦追寻到微言,则史实如何,又不是重心了,因此义大于事,价值理念与历史事实,未必要一致。康有为引“缘鲁以言王义”,苏舆也有辨明,他说董仲舒之意,并非尊鲁为王,孔子更无此意,都只是一般人论史,以香草美人式的具体性思维,引喻咏事,藉题发挥罢了,只是一则以物,一个以史,“谓窃王者之义以为义也。托鲁明义,犹之论史者借往事以立义耳”[5]280。但董仲舒说鲁言义,明明是要先澄清历史事实:“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于稷之会,言其成宋乱,以远外也。黄池之会,以两伯之辞,言不以为外,以近内也。”[5]280从这些情况中,观看其人其事,说理明义,然后以史为鉴,经世为用的。
本文的研究,即是回到《春秋繁露》本身,分析其公羊学,然后再顺着原文,分析广受学界重视的注本:《春秋繁露义证》。从董仲舒到苏舆,萧条异代,同样解释《春秋》,同样是解读《春秋繁露》,论述却产生分歧,我们并旁及康有为,在学界多强调苏康之异的基础上,也从董仲舒的角度,分析二人的可能之同。论述于此,未及之处,还请学界方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