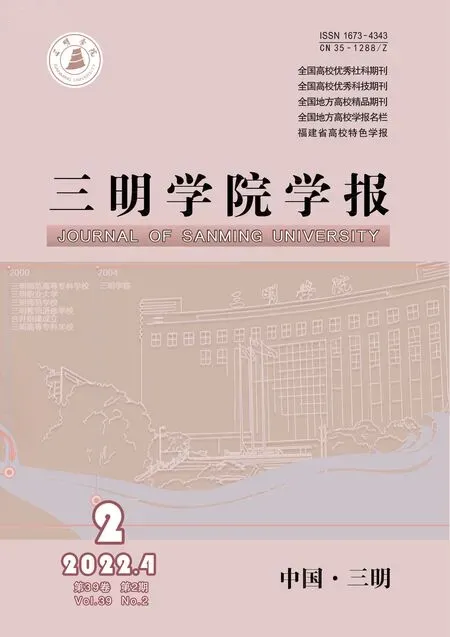包容性文化生态视野中的城镇民俗文化传承
2022-03-17钟福民彭田菲
钟福民,彭田菲
(1.赣南师范大学 客家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2.赣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中国城镇民俗的演变与中国城镇的发展紧密相关。所谓城镇,是指人口相对集中、工商业相对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它反映了人类区别于乡村的另一种生存状态。中国城镇发展的历史悠久。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格局比较规范的城镇。至唐代,市坊分开,城镇功能日趋发达。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繁荣,夜市兴隆,城镇有了很大发展。明清时期,除了大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之外,小城镇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尤其在江南一带,各种职能性的城镇星罗棋布,如以丝绸业闻名的江苏吴江县的盛泽镇,以产棉布著称的浙江嘉定县的南翔镇,以航运业出名的浙江仁和县的塘栖镇,等等[1]46。遗憾的是,从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国内战火不断,中国的城镇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的城镇文化发展中,隋唐之前尽管城镇经济有很大发展,但由于未能形成独立的市民阶层,所以城镇文化仍然带有浓厚的农业文明色彩。宋代以后,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和活跃,真正意义上的城镇文化才得以形成并快速发展。
一个城镇的传统文化既包括那些有形的物质文化,也包括无形的精神文化;既有大传统的精英文化,也有小传统的民俗文化。城镇民俗文化作为生活文化,向外来者传达了城镇文化的独特性,也向当地居民提供了宜居的文化要素和生活方式,并激发着居民的自豪感,产生一种寻求可以共享的城镇精神与文化身份的诉求。
一、当代中国城镇文化建设与认同危机
在当代,中国城镇文化不再像传统时代那样自生自灭地发展,而是进入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发展阶段。当然在中国城镇文化的发展中,也演绎了中国人对现代性的渐进性理解,折射了中国人由重点借鉴西方文化逐渐转向重点关注本土文化的趋势。
客观地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农村的现象,是中国城镇文化衰退的表现[2]76。这是由于城镇无法容纳那么多人口,因而政府动员人口大转移和大分流。从宏观的人口合理分布来讲,这一政策似乎无可厚非,然而具体到个体生命际遇,却成了苦难的记忆,这在“知青文学”中体现得最为突出。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不但中国的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而且中国的城镇文化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当时的城镇管理者普遍认为,城镇文化建设的要义就是建设“现代化”的景观,就是要建设大尺度、大体量的建筑。于是,各地竞赛似地纷纷修建大马路、大酒店、大广场等建筑物,即便小县城也不甘示弱。可以说,这时期以“大”来体现气派的城镇文化建设理念,与当时暴发户的审美趣味如出一辙。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城镇的文化建设理念发生改变,由追求气派转向追求品味,随着各种绿化、亮化和美化工程的展开,园林景观、公共雕塑或音乐喷泉等纷纷出现,城镇形象变得日益赏心悦目。不仅如此,用来展示城镇现代性的公共建筑也得到重视,城镇管理者建大马路、大酒店、大广场的冲动转向建歌剧院、美术馆、博物馆的热情。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城镇开始大张旗鼓地鼓吹“文化立市”或“文化立县”的口号。这种“文化立×”的口号,似乎暗示着城镇文化建设理念的再一次转换:即一个有品位的城镇不仅需要光鲜的景观和优越的物质条件,还需要浓厚的文化氛围和独特的文化名片。然而,究竟什么是文化,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多数人并不清楚。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人们城镇文化意识的增强,城镇文化建设的理念逐渐从关注外观转向关注内涵,“城镇精神”的口号也随之提出。但多数地方提出的“城镇精神”,明显脱离自身的文化个性和历史传统,与以往的社会风尚教育并无二致,如“求实”“文明”“进取”“开放”等等。这种普泛的口号式的“城镇精神”,其实在民间并不具有多少认同感,也难深入人心。
新世纪以来,由于世界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动,以及城镇推介和招商引资动机的驱使,城镇文化建设又有了新的趋向,那就是不约而同地向地方历史传统和民俗文化靠拢,用各种复古的或虚构的手法激发人们的地域想象或思古幽情。一些城镇甚至出现了对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任意的虚构,结果导致各种假古迹和伪民俗的出现,比如很多城镇建有仿古的“明清一条街”。其实,这样的景观与城镇的历史并无多大关联,也很难体现当地的地域特点。
总体上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文化建设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危机。这些问题和危机既表现为人们对城镇历史文化的不了解,也表现为人们在城镇中生活的疏离感,还表现为政府主办的一些文化活动中,民众缺乏参与的积极性,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与危机,无论是外来务工者还是城镇原有居民,往往都有切肤的体验。
可以说,一个城镇是否宜居,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居民对城镇文化的体验反映出来。而城镇民俗是城镇居民体验最为深刻的城镇文化。城镇民俗彰显了城镇的特色和魅力,也为人们提供一种具有亲和感的生活方式。就目前而言,通过激活城镇民俗文化资源,增强城镇的文化氛围,以缓解当下城镇认同危机,建设“人性城镇”[3]3,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
二、作为城镇认同媒介的城镇民俗文化
从本质上讲,城镇是一种积极的、动态的社会结构系统,它总是吸纳着最新的文明成果,从而对传统具有很强的解构作用。但是,城镇的发展又需要强大的凝聚力,需要有保存记忆、延续文化和关联历史的媒介。正是在这些方面,城镇民俗文化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民俗关注的视点主要放在农村,城镇民俗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如今,随着人们城镇文化意识的增强,社会各界日益重视对城镇民俗的保护和传承。在保护和传承城镇民俗时,需要对城镇民俗与乡村民俗的区别与联系有清醒的认识。
城镇民俗与乡村民俗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地理空间观念上:城镇民俗主要存在于一个地区政治的、或经济的、或文化的中心,而乡村民俗主要存在于广袤的乡野僻壤。两者所依赖的经济方式也不同。“稽古之道,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4]593城镇民俗的发展依赖工商百业;乡村民俗的发展依赖农、林、牧、副、渔。此外,两者的参与主体也不同。城镇民俗的参与主体是市民,他们多为迁徙之人,来自四面八方;乡村民俗的参与主体是农民,他们多为聚居于村落的宗亲群体。当然,同时也要看到城镇民俗与乡村民俗内在的联系,特别是在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加剧的社会背景下,城镇民俗和乡村民俗也加速了互动和整合。同样,有些城镇民俗也在乡村盛行开来,比如在以前赣南的乡下,人们都忌讳在婚礼中使用白色物品,但现在,对于新娘穿白色的婚纱拜堂,人们已认为再正常不过了。城乡民俗的互动互化,说明城乡文化之间内在的关系,也说明在建设城镇民俗时,可以从乡村民俗中获取资源。
城镇民俗作为城镇居民生活需要的满足,不是可有可无的城镇赘物,而是不可或缺的城镇传统,它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沉淀下来的,体现了城镇比较稳定的一面。不少延续至今的城镇民俗,不仅激发着居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产生一种寻求共享的城市精神和文化身份的诉求,而且彰显了城镇文化的独特性,为外来者留下深刻的记忆。城镇民俗涉及多方面的资源,为城镇居民包括外来人员对城镇的认同提供了可能和凭借。
在多样的城镇民俗当中,民俗建筑是城镇认同最直观的对象。民俗建筑包括民居、祠庙、商号、会馆、码头、牌坊、街巷等遗址。一个人的城镇意识,很多时候会依赖于对某个或某几个遗址(或地点)的认同,有可能因若干处民俗建筑而更加喜欢这个城镇。换句话说,那些民俗建筑因为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开放的生活空间和共享的生存体验,往往成为最具人气和活力的地方。比如在赣州市章贡区的灶儿巷和建春门,兴国县城的背街和西街等地,因为有不少民俗建筑而成为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可以说,城镇中的民俗建筑是人们勾连记忆、激发想象的媒介,为人们认同城镇提供了最持久、最稳固的空间力量。
作为族群文化载体的城镇民俗语言,也具有很强的认同功能。比如在珠三角地区的多数城镇,无论是在电台、电视节目中,还是在公交、地铁的广播中,会用粤语来播音,从而让人领略到岭南城镇的独特风韵。在江浙一带的城镇,人们所讲的吴侬软语,也为城镇增添了几分秀丽和精致。而东北城镇的一些民俗语言,由于它特有的腔调和含义,竟然成为外地人喜欢这些城镇的一大理由。在赣州市章贡区公交车上报站的客家话,也让乘客感受到浓郁的客家气氛。可以看出,城镇民俗语言之所以成为城镇认同的媒介之一,是由于它为城镇营造了一种有声的氛围。
城镇的民俗饮食不仅仅关乎个人的口味,也关系到人们对城镇的认同。民俗饮食尽管细小而普通,但体现了一个城镇中人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就像生活在珠三角地区城镇的人们,都喜欢腊肠、凉茶、煲汤、沙河粉一样,生活在赣南地区城镇的人们热衷于享受擂茶、肉丸、拼盘、米酒等食物。民俗饮食体现了居民的生活趣味,也反映了城镇独特的文化风韵。有意思的是,民俗饮食不仅对本地居民有很大的自足性,而且对外来人员也有很强的“归化力”[2]191。一些外来人或许一开始很不习惯这里的民俗饮食,但后来却被这里的饮食之道完全同化,不仅接受了,而且喜欢上了,甚至爱屋及乌地喜欢上这一城镇。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所以说,一个城镇的魅力常常体现在它的民俗饮食方面。
作为浓缩了丰富地方性知识的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也是城镇认同的重要媒介。无论是包括传说、故事、歌谣、笑话等的民间文学,还是包括山歌、曲艺、小戏、傩戏等的民间艺术,都可以让本地人娱情悦性,让外来者心旷神怡。比如在赣南不少城镇常常有客家山歌的演唱和赣南采茶戏的表演。在演唱或表演时,观众既有本地居民,也有外来人员。在此,客家山歌和赣南采茶戏为人们提供了解愁娱乐、社会交往、重拾记忆等多方面的契机,并有效地强化了他们对这一城镇的印象和体验。
可以看出,作为城镇文化的城镇民俗,为人们提供了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满足,慰藉了人们内心的焦灼和不安,缓解了人际之间的疏离感,也增进了居民间的融洽感。在以城镇民俗增进城镇认同的过程中,本质上体现了这样一条发展路径:地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城镇民俗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当前,各地在进行城镇文化建设时,不约而同地向民俗文化靠拢,固然是对全球化过程中应对文化同质化危机的一种策略,同时也与近年政府大力扶持地方文化并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是分不开的。此外,很多城镇的地方学者、文人和媒体人,都表现出对所在城镇民俗的关注热情,以城镇民俗的渲染来激发人们对城镇的认同和热爱。
三、城镇民俗文化传承与包容性文化生态的建构
当今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张力作用下进行的。因而,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既要注重城镇景观的建设,也要注重城镇文化的建设。而在城镇文化的建设之中,既要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也要重视地方历史传统的保护和传承,建构具有包容性的城镇文化生态,使来自四面八方的个体都能获得具有归属感的体验。
城镇民俗之所以能够作为城镇认同的重要媒介,是由于城镇民俗具有反思现代性的意义。城镇民俗是最深刻意义上的地方传统文化,可被视为一种阐释现代性的参照之物。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5]34通过与包括城镇民俗在内的地方传统文化的参照,在反思中进行城镇文化建设,无疑会更趋理性和合理。
包容性城镇文化生态的建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它涉及整合社会情感的问题,涉及社会和谐的问题。客观地说,一个日渐多元化与不断变化的城镇,正被越来越多具有不同生活经验与文化背景的个体充塞着。不同个体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往和沟通并不简单,是在存有文化差异基础上的交往和沟通,而城镇民俗正好为这种文化交往和沟通提供了条件。很多民俗活动的举办,有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存背景的主体参与。比如近年在赣州市兴国县城广场举行的山歌赛,既有乡下农民参与,也有县城的公司职员、学校教师、政府公务员等各种职业的人员。还有像近年来在赣州市赣县区七里镇客家文化城举办的“赣县客家庙会”活动中,既有周边村民表演的东河戏,也有学生表演的小合唱,还有自由职业者表演的钢琴独奏等。再比如,赣州市章贡区政府为了打造“端午龙舟文化节”,每年组织龙舟赛,在向社会发出参赛邀请后,不但有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参加,郊区的很多村民也积极参与且多以家族为单位。在龙舟赛举行期间,周边村民和章贡区的城镇居民都来观看,可谓盛况空前。这种“求同存异”的文化活动,表明参与主体内心寻求文化认同的渴望。
包容性城镇文化生态的建构,既涉及“大传统”的精英文化建设,也包括“小传统”的民俗资源的动员。民俗资源因为关系到中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是最有地气、最有生活气息的城镇文化,所以在学者呼吁、政府号召和媒体宣传下,最能得到民众积极的呼应和配合。这是因为沉淀于人们生活和情感深处的城镇民俗文化,是一个城镇“活的历史”,它使冷冰冰的由钢筋水泥建造的城镇变得富有生气和人情味,也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对快速变化的城镇景观更能够保持内心的平和。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的差距日渐缩小,无论是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层面,还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都趋于融合。在城乡文化的融合中,对作为城镇文化最具本原性的城镇民俗加以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在当今城镇文化的建设中,并非用城镇文化来取代乡村文化,而是根据人们的生活需要,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城镇文化。如果说城镇文化以城镇民俗为代表,那么乡村文化则是以乡村民俗为代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镇,他们带去了乡风土俗,促使乡村民俗与城镇民俗趋于融合。其实,城镇化的过程正是城镇与乡村互相影响、城镇民俗与乡村民俗逐渐融合的过程。在此融合的过程中,城镇民俗既吸收了乡村民俗的传统因素,又融入了现代文明的文化因素。
在城镇民俗与乡村民俗的互动和涵化过程中,包含了吸收和创新的环节,城镇民俗既吸收了先进的、健康的因素,又摒弃了落后的、丑陋的因素,如城镇民俗从乡村民俗中吸收了重情义、遵伦理、知敬畏等人文精神,而剔除其封建的、迷信的糟粕,从而有助于避免当今城镇社会人际交往的过度功利化倾向。城镇民俗在吸收乡村民俗的文化因素和精神特质时,又与时代精神和世界潮流有机结合,如城镇民俗形成了以人为本的道德观、保护生态的自然观和重商兴业的致富观等观念。这些观念成为城镇居民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的支配性观念。城镇民俗吸收乡村民俗的文化因素,不是两类民俗的简单叠加,而是人们根据生活的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也是城镇民俗吐故纳新和创新发展的结果。通过对乡村民俗文化因素的吸收,城镇民俗才植根于地域历史传统,并有了个性特色和生命力。
城镇民俗吸收乡村民俗的文化要素,并为城镇居民所接受和传承,缘于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对民族精神认同的一致性。无论是乡民还是市民,都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继承了共同的民族精神,比如与人为善、爱国爱乡、勤劳节俭、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等。这些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源泉。民族精神属于中华民族的全体,它可以超越城乡、地域、职业、阶层,并促进内部成员的文化认同,也将塑造着每个居民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
当然,城镇民俗也因为满足城镇居民日常的物质、精神和社会交往需要而得以可持续传承。在当今城镇的许多商业活动中,因为带上了民俗文化的成分而激发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如节假日期间的花卉市场,增添了节日的氛围,给人们带来愉快的心情和美的享受,甚或激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城镇中的鱼鸟市场,荟萃了各种异鱼珍鸟,成为丰富多彩的鱼鸟大观园,更是孩子们流连忘返的游乐空间。还有像宠物市场中的各种动物,也会引起孩子们的好奇和兴趣。城镇中的各类古玩市场,是城镇居民寻古探幽的好去处,甚至成为文化人和老年人最喜欢溜达的免费博物馆。还有像花灯市场,是城镇春节期间最富艺术气息的欢乐海洋,居民在灯市中赏灯、买灯、猜灯,花灯市场也成为城镇居民最喜爱的游乐场所之一。可以说,城镇居民在这些文化与经济有机结合的场所里,既得到了文化的熏陶,也放松了身心,从而感受到了城镇的美好生活。
在城镇民俗的传承中,既有传承也有变异,在某些方面缩小了城乡差别,融合了城镇文化与乡土文化、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上层文化与中下层文化,形成了具有包容性的文化生态。如原来只在乡村流传的打社火、扭秧歌、舞龙灯、踩高跷等民俗活动,如今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城镇居民的娱乐活动方式。比如在赣南地区的城镇,原来在乡间演唱的客家山歌和表演的采茶戏,如今已成为城镇居民喜爱的休闲娱乐方式。
人们在进行城镇文化建设时,总有对现代性的追求,但现代性并非与传统的彻底告别,现代性本身就意味着选择的多样性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城镇民俗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力量,可以让城镇中的居民感受到传统的温情。城镇民俗作为城镇居民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关系到城镇居民情感的皈依。城镇居民的情感凝聚力往往寄托于那些稀松平常的民俗生活之中,无论是茶楼、会馆、牌坊、花市、灯市、古玩市场等有形的民俗文化,还是扭秧歌、舞龙灯、挑花篮、踩高跷等无形的民俗文化,都成为滋养城镇居民情感的基础。实际上,在一个城镇里,往往是那些拥有深厚民俗文化传统的地方,才是老百姓最愿意去的地方,也是城镇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这些地方既充满活力又自然和谐,并增强了城镇的内在凝聚力。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需要一种内在的凝聚力,没有内在的凝聚力,就没有城镇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对绝大多数城镇居民来说,这种内在的凝聚力不是来自经史子集等历史文献,也不是来自官方和媒体的宣传口号,而是主要来自隐性的文化传统,存在于人们的祭祀、饮食、审美、人际交往等活动中。这些传统和民俗之所以如此富有活力和吸引力,就在于它们是广大的普通居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人们在传承和参与这些民俗活动中感受到了生活的快乐,也体认到生命的意义。可以说,一个拥有蓬勃兴旺的民俗生活的城镇,就意味着在居民生活中具有更多共享的活动、习惯和趣味,就更易于形成社会各文化群落之间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因而也更容易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
城镇民俗同乡村民俗一样,是无形而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源,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以自觉的意识促进城镇民俗的保护与传承,不仅是彰显城镇文化特色的需要,也是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需要。当年那句流传甚广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宣传口号,似乎寄托了人们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愿望,而对于当今中国许许多多的小城镇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说“城镇民俗让城镇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