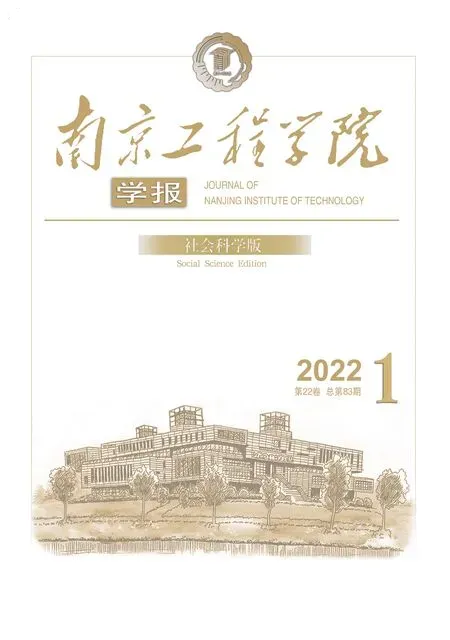权力视角下《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的双重叙事
2022-03-17程婷婷
程婷婷
(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211171)
当代苏格兰女作家缪瑞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28—2006),以“对文化过程和文学传统的敏感性,与精准的说故事技艺结合在一起,在20世纪成为最重要的文学人物之一”[1]。其代表作《布罗迪小姐的青春》(ThePrimeofMissJeanBrodie, 1961)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爱丁堡的一所女子教会学校里,处于“盛年”的小学教师布罗迪小姐用她独特的教育方式,满怀信心地要将她精心挑选的姑娘们培养成人杰中之人杰,却遭到最信任的学生桑蒂的背叛告发。早欲将其铲除的学校迫使其提前退休,她最后抑郁而终。这个经典的校园故事是斯帕克诸多作品中苏格兰性最为浓烈的一部,糅合了典型的爱丁堡地域特征以及民族认同、宗教矛盾等诸多苏格兰元素,是当代苏格兰小说的典范之作。尤为显著的是,小说贯穿了苏格兰文学突出的“双重”写作特征。双重叙述是苏格兰小说的重要艺术手法,应和了“苏格兰人格分裂和信奉黑暗力量的古老黑暗的苏格兰特征”[2]。
斯帕克出生于爱丁堡,18年后搬离故园四处漂泊,并于1960年代定居意大利。尽管被誉为“来自苏格兰的最欧洲化的作家”,斯帕克在创作生涯后期更强调自己“苏格兰人”和“天主教徒”的双重写作身份。一方面,悠久的苏格兰文化传统和对家乡挥之不去的记忆,已然深植于她的创作中。虽然斯帕克“并不刻意地去书写苏格兰,但苏格兰书写在她的小说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她的小说似乎总是在若隐若现地书写苏格兰”[3]256。尤其是苏格兰文学中爱与恨、崇拜与毁灭的传统主题,在斯帕克的创作中得到了传承与延续。另一方面,斯帕克的作品始终笼罩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苏格兰宗教氛围复杂,派别林立,加尔文教与天主教势均力敌。斯帕克受教于爱丁堡女子学校,幼年浸淫于苏格兰长老会教义。其叙事手法特有的“预叙”形式,与加尔文教“控制和预知”的宇宙观极为相似。也就是说,全能的上帝无所不知,通过预先注定的命运体系,对人类的命运有绝对的控制权。斯帕克于1954年皈依罗马天主教后,其小说的虚构模式深受中世纪天主教的文学观影响,即阐释的最高境界归属于上帝。由此,加尔文教令人敬畏的积极掌控与天主教对世界消极神秘的回应再现,构成了斯帕克作品“奇异而自相矛盾的特质”[4]。在斯帕克看来,“两面性”(nevertheless)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属性,“我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两面性’为基础。它指导了我的行为。”[5]这种被斯帕克定义为“思维模式核心”的“两面性”原则贯穿了斯帕克文学创作的始终,凸显了她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
在《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斯帕克隐蔽地描绘了一幅纵横纠葛的权力关系图谱,不仅投射出现代社会权力机制的错综复杂,亦隐喻了英格兰与苏格兰民族关系的微妙平衡。权力视角的解读,为研究斯帕克“两面性”的美学思想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手段,也为重新认识小说苏格兰叙事中的“双重叙事”开拓了有价值的研究路径,构建了文本不断再生的意义阐释空间。
一、双重叙事中的“双身”
“苏格兰小说中的双重叙述并非现代主义作家惯用的用双重视角来叙述同一个故事,它所指的是双身,即一个人能分裂为两个躯体。”[3]12如苏格兰著名作家史蒂文森的经典小说《化身博士》(1886)中的哲基尔,詹姆斯·霍格《罪人忏悔录》(1824)中的罗伯特,斯帕克《派克汉姆·莱的歌谣》(1960)里的道格尔·道格拉斯,都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征。《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双重身份”的书写,集中体现在布罗迪小姐和桑蒂“互文性”的主体塑造上。作为最受布罗迪小姐器重的学生,桑蒂身上处处可见布罗迪小姐的影子。两人形影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颠覆和消解。为了反抗布罗迪小姐对“上帝”的僭越,桑蒂通过背叛的方式终结了布罗迪小姐的教师生涯,扮演了操纵她命运的“上帝”,成为布罗迪的翻版。
布罗迪信仰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和“选民”说,崇拜上帝无所不能、掌控一切的权威,将对这种权力的渴望内化为强烈的自我意志。“她以为她就是天意,她就是加尔文的上帝,她预见到了太初与终结。”[6]195“她自己坚信也让所有的人相信,无论她做什么事上帝都与她同在。”[6]161福柯认为,知识、真理与权力之间存在不可或缺的紧密联系,“没有知识,权力不可能行使,知识不可能不产生权力。”[7]52知识、话语与权力交织所产生的真理效应传递并强化了权力,成为权力斗争的组成部分。布罗迪把自己看成上帝和真理的代表,踌躇满志地要在“事业鼎盛期”大干一场,代替上帝培养精英。“只要给我一个处在可塑年龄的女孩子,那她一生都将是我的了。”[6]85在知识的主导和操控下,个体依附于权力主体成为知识的对象。在传统的教会学校里,依赖一整套知识和话语体系衍生出的权力机制,布罗迪小姐用她信奉的“真正的教育”对女孩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成为其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然而,布罗迪对待加尔文教的态度却是自相矛盾的。她罔顾谦卑、克制的教会律条,崇拜法西斯的独裁主义,“以难以理喻的方式违抗上帝的旨意”[6]184,坠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深渊。她支使尤妮丝到极其危险落后的地区去当一名先驱传教士,教唆乔伊斯去西班牙参战致其惨死,安排罗丝代替自己去做美术老师劳埃德的情人。“当她一边做礼拜一边与音乐老师上床睡觉的时候,她并不会为有可能被视为伪君子而不安。恰如极端的思想会导致极端的行动一样,布罗迪小姐的行为就是因为她极端缺乏负罪感。”[6]161
如果说布罗迪的双重人格体现为个人意志与超自然力量的搏斗,桑蒂则是在虚实的转换之间实现了自己的双重生活。她出生于传统的苏格兰加尔文教家庭,经常幻想与小说主人公的对白,想象布罗迪小姐的爱情故事,编撰她和情人的书信,并在皈依后撰写了成名作《普通人的转变》。无论是虚构的默想、记录、写作,还是现实中对布罗迪毁灭性的背叛和对天主教的皈依,桑蒂一直“用自己特有的过双重生活的方式才能使自己不厌倦”[6]97。一方面,桑蒂无法根除家乡爱丁堡对她深入骨髓、伴随一生的影响,“只有爱丁堡才有的而别的地方都不具有的特殊生活,在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一直存在着。她渴望得到这与生俱来的权利,可是她又一直在拒绝这一权利。”[6]183另一方面,桑蒂对布罗迪小姐的忠诚也从未完结。她因为背叛了一生中“最最无法背叛的人”而被折磨得心烦意乱,布罗迪“在世的最后一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桑蒂的”[6]132。
小说似是而非的开放式结局将斯帕克的“两面性”美学原则推向高潮。桑蒂离开美术老师劳埃德的怀抱,却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改信天主教,进入修道院成为海伦娜修女,与过去身份彻底断裂。然而在接待访客时,她“紧紧攥住铁栏杆,好像要从这个阴暗的会客厅里逃出来。总是将身体探向前方,眼睛盯着外边,两手抓着窗户上的铁格子”[6]111的意象反复出现。斯帕克曾说,从爱丁堡的彻底逃离是她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并多次提及自我的流放。桑蒂辗转纠结的情感转向和信仰抉择,正是她对待故乡爱丁堡和加尔文教的“双重”情感的真实写照。
二、双重叙事中的“规训与反抗”
在《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斯帕克不仅具体细微地描绘了规训权力在社会机构与日常生活中的运作,也揭示了权力关系图谱中布罗迪小姐与桑蒂权力“主客体”双重身份的转换。
不同于封建君主制自上而下的权力压迫,在现代社会自下而上的权力模式中,权力的运作往往“跻身于社会主体最隐蔽的事物中”[8]。福柯将这种新型的“局部毛细血管状的权力形态结构”称作“规训权力”[7]39。随着时代的更迭和演变,规训权力在整个现代社会机体中迅速崛起、弥散、流布。小说中纪律分明、井然有序的布莱恩女子教会学校正是这一典型环境的缩影。学校通过一整套策略、程序、行为和强制性的治理方式,对师生的个体行为进行深入到一切细节的管理和塑造。校园采取全景敞视结构和封闭配置形式,校舍楼宇的空间布置和严格限定的等级结构体现了权力的分配。诸多控制手段的运用“使每个个体屈服,权力得以轻松地运行”[9]。此外,学校里施行“同一性”规范,违反标准的个人和群体被排斥和边缘化。“总显得与众不同”的布罗迪小姐在学校里遭到同事的质疑和校长的发难,布罗迪帮的女生们则因为学习了大量脱离学校大纲的科目而备受讥讽。在这个类似“圆形监狱”的校园环境里,借助精密的权力结构,以女校长麦凯小姐为代表的传统教学势力,对布罗迪帮的监视和审查无处不在,以整体性的稳定机制压制着对立性反抗的自由。
与此同时,在布罗迪帮内部,处于权力中心的布罗迪小姐也加紧了对帮内成员的支配和控制,实现了权力主客体“双重”身份的交叠与转换。通过对个体的改造和驯服,规训权力转化为庞杂而持久的精神控制,无休止地渗透和实践着,其目的是通过自身规训自身。布罗迪细致入微地检查训练女孩子们的着装和仪态,严格盘查其行为举止和思想动态,以防止灵魂的逃脱和迷失。视觉权力的压制迫使“自为”的人在自我审查中异化成“为他”的存在,在内化他人的价值判断过程中不自觉地将自我“物化”。“只需用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10],逐渐丧失主体性,从而产生自我认同。在布罗迪小姐“严峻和充满占有欲的眼神”注视下,娄赛先生被迫配合她疯狂的增重计划,大量进补到厌食的地步。即使在自己诞生的房子里,他也“总显得不是在自己家里似的,干什么事都要看看布罗迪小姐以征求她的同意,好像没有得到允许他就什么也不可以干。”[6]165借助这种强大的控制模式,布罗迪建立了以她为中心的“真理的政权”,隐秘地操控着个体的行为,却遭遇视为心腹的学生桑蒂的致命背叛。
在布罗迪帮的成员中,桑蒂对布罗迪小姐最为崇拜,她用那双“不易被人看见的小眼睛”主动关注着布罗迪小姐的所有举动和变化,“听讲时透过那双小眼睛盯着她,就像听圣女贞德讲话一样。”[6]87她的“悟性”深得布罗迪小姐赏识,成为她精心调教和规训的对象。然而,有权力运行的地方就必然有人反抗,权力所产生的冲突和裂隙促成了对自由意志的坚守,对立关系最终转化为反权威的抗争。布罗迪种种过分的行为导致了桑蒂认知的转变和态度的波动,她内心的抵触和愤怒外化为“一种叛逆的欲望,一种对抗性凝视”[11]。同时,布罗迪“可怕”的权力控制也引发了桑蒂心底无法言明的恐惧,她“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在这种生活里生活的权利,无论它多么叫人不愉快;她迫切地想弄清楚这种生活的真实内容,并且不想再由别的什么开明人士来保护自己”[6]183。福柯在《性史(第一卷)》指出,个体绝非权力的接受者和被动的傀儡,而是作为能动主体的行动者,是权力被确立或抵制的“场域”[12]。桑蒂对自我身份的迷惑和强烈的关注自我的愿望,生发出与布罗迪小姐相抗衡的反制约力。“为了夺回自由,把自我从他人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主体需要注视他人,并反过来控制他人。”[13]桑蒂打破了布罗迪的精心安排,勾引老师劳埃德成为他的情人,并向校长告发了布罗迪的法西斯思想,彻底铲除了她的权力控制,成功地从权力客体转换成为自身行动的权力主体。
三、双重叙事中的民族关系隐喻
在权力运作愈发隐蔽的现代社会,权力与反抗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角力关系。以布罗迪小姐和桑蒂为代表的权力话语场与反权力话语场之间的对峙,正是英格兰与苏格兰民族关系的真实隐喻。英苏之间的权力竞争长达数个世纪,在不同时期相互冲突,相互交织,也相互扶持。在海外殖民扩张时期,苏格兰为大英帝国的辉煌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分享了不列颠共同体的胜利果实。正如布罗迪小姐对布罗迪帮一再强调的那样,“我在我的盛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只要你们真听我的话,我就会把你们变成人杰中之人杰。”[6]99,90“你们将会得到我辉煌时期的果实,这将使你们一生受益。”[6]123“你们必须成长为有献身精神的人,就像我为你们献身一样。”[6]139由此,权力主客体之间建立了彻底的效忠和服从。布罗迪帮的姑娘们坚信,她们是“为布罗迪小姐的命运而团结在一起,上帝让她们来到人间似乎就是为了这个目的”[6]107。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苏格兰历史是一部见证大英帝国的衰落、重新认识英国性和苏格兰性的关系、重新发现民族身份的历史。”[3]248“二战”后英国在与美苏的抗衡中渐失世界霸权,如同小说中留恋青春又寄望盛年的布罗迪小姐,“电车来了,我敢说上面没有我的座位……骑士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我事业的鼎盛期过去了。”[6]86,132战后的不列颠既有对昔日霸权的眷恋和盛世不再的感喟,又冀图通过对帝国内部成员的掌控重返辉煌。“她让帮里的所有成员都要在斗争进入关键时期团结在她周围,并使她们明确认识到,这样做是她们义不容辞的责任。”[6]187“二战”后苏格兰的经济支柱遭受重创,社会问题丛生。相较于对政治宰制和经济剥削的抗争,反对主体屈从化、摆脱个体化管制的抗争变得更为重要。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民族矛盾突显,独立的呼声再次高涨。桑蒂对“爱丁堡特有的生活特质”的诉求正是彼时苏格兰思想气候的具象,投射出苏格兰对独立自主的民族身份的追寻。“你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背叛我。事实上你从我这里得到的最多,最受我信任。”“如果你不背叛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有人背叛你。”[6]201布罗迪小姐临终之际与桑蒂的对话,正是战后英格兰与苏格兰民族关系的注解,斯帕克美学原则中的“既/又模式”则生动地诠释了二者权力关系微妙复杂的“双重”特质。
福柯认为,在流动变化的权力关系中,主客体并不完全是两败俱伤的交互冲突,相反表现为恒久性的互相激发和螺旋式的缠绕渗透。权力关系只有放在两个相互依赖的元素中才能得以阐释。这两个个体彼此诱导、相互牵制,呈现出相互吸引、永久关联又彼此对立的关系。布罗迪帮的成员们“既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相互之间又没有共同之处,唯一相同的是她们都对吉恩·布罗迪小姐忠贞不渝。”[6]82她们与布罗迪小姐既相互对立又生死相依,形成了长久的难以摆脱的束缚。“这一关系已深入她们的骨髓,所以除非她们把自己的骨头拆散,这个团体是不会土崩瓦解的。”[6]190尽管桑迪最终摆脱了布罗迪小姐的控制,却无法否认布罗迪小姐对她的影响,“哪怕那些影响起到了相反的作用。”[6]111
成年后的布罗迪帮恰似“二战”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的大不列颠共同体,各民族抱团取暖却又心生嫌隙。自1707年合并以来,苏格兰始终处于英格兰的钳制之下,成为大不列颠版图中的“他者”。苏格兰曾经数次发起民族独立运动和全民公投,却仍然选择留在不列颠共同体。从历史上看,苏格兰的政治命运和大英帝国休戚相关;从经济上看,联合王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分离的代价太过高昂;从情感上看,强大的宗教力量及根深蒂固的帝国意识是他们联系彼此的纽带。因此,既要求独立,又寻求家园的精神依托的“双重”苏格兰,对英格兰的抗争不会消解,对英格兰的依恋也不会断裂。二者共同谱写的权力之歌将继续演奏着争执、盘旋、往复的乐章,在英伦岛的上空回荡。
四、结语
作为当代苏格兰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几乎完美呈现了王佐良先生总结的苏格兰文学的特点:“矛盾,自我折磨,不忘历史旧恨;有宗教感,但又憎恨诺克斯传下来的教义;有面向群众的创新,却又往往结合了最古传统的重新发掘;民族主义情绪浓厚,但又有重要作家越过它而走向国际主义。”[3]252在《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权力这一古老的主题,如苏格兰威士忌一般历久弥新,在爱丁堡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里持续发酵,成为解读苏格兰现代社会权力机制以及斯帕克的“两面性”创作原则的经典范例。麦凯校长对女子学校的“监视”和布罗迪小姐对布罗迪帮的“规训”,折射出现代社会丰富多样的权力支配技术和隐蔽的治理艺术。布罗迪与桑蒂这对人格一致的“双身”在权力主客体身份中的转换,应和了苏格兰民族的双重性,也深刻反映出苏格兰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身份认同困境。布罗迪与桑蒂之间控制与反抗的权力互动,不仅观照了英格兰与苏格兰矛盾统一的民族关系,也折射出斯帕克对爱丁堡和加尔文教复杂而深沉的情感。在权力视角的解读下,斯帕克创新的“两面性”美学原则赋予了小说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彰显出权力话语与苏格兰“双重叙事”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