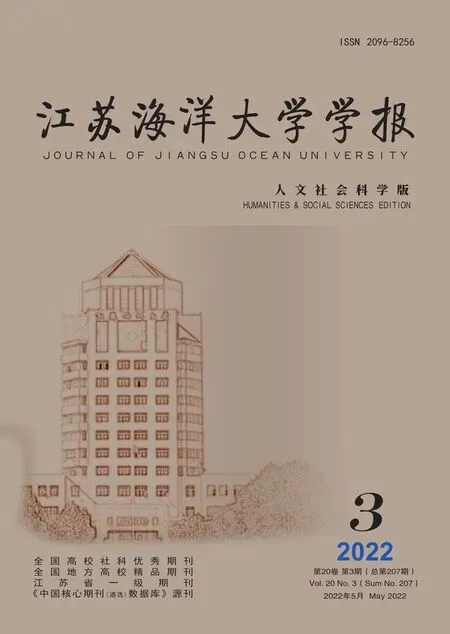清初至民国《长生殿》传播与接受路径的嬗递*
2022-03-17饶莹
饶 莹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自乾隆中后期始,折子戏演出日盛,花部乱弹勃兴,二者兴盛的阶段正是清代文字狱以及官私合禁、审查戏曲如禁毁或删改曲本、饬禁演剧等最盛的时代,《长生殿》演剧形态的转变也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晚清与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时代剧变,战乱频仍,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昆曲一道身处如此变局之下曾一度濒危,《长生殿》遭此境遇却从未停刊辍演,其传播与接受进程处处可见嬗变迹象。
一、《长生殿》演剧形态的转变
清初剧坛创作承前代余绪,势头尚存,至康熙年间《长生殿》《桃花扇》的出现已是昆腔传奇创作史上最后的绝响。然戏曲文本创作的相对沉寂却伴随着梨园演出的兴盛,且自乾隆中后期始,昆腔折子戏逐渐取代全本戏的演出,迎来折子戏的全盛时期。
《长生殿》全本演出多见于康熙年间,至乾隆初期仍然存在。自此剧脱稿至洪昇逝世的十几年间,全本演出形态几乎皆为文士富吏阶层主持。康熙四十三年(1704)洪昇逝世后直至乾隆初年,有关《长生殿》的全本演出记载依然零星可见于史料文献之内。乾隆中叶之后,尤其嘉道以降,《长生殿》全本演出基本在舞台上销声匿迹,全面代之以折子戏的演出形式,流传至今。
《长生殿》一经问世便受到各方的追捧,不独勾栏争相竞演,“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1)徐灵昭:《长生殿序》,《汇刻传剧》第二十八种,清末民初刘世珩暖红室重刻本。,文人宴会也是时时青睐此剧,“于燕会之间,时听唱《长生殿》乐府”(2)朱襄:《长生殿序》,《汇刻传剧》第二十八种,清末民初刘世珩暖红室重刻本。,“梨园子弟,传相搬演,关目既巧,装饰复新,观者堵墙,莫不俯仰称善”(3)尤侗:《长生殿序》,《汇刻传剧》第二十八种,清末民初刘世珩暖红室重刻本。。更有甚者,如《柳南随笔》卷六记曰:“《长生殿》初成,授京师内聚班演唱,圣祖览之称喜,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王称之。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4)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六,借月山房汇钞所收本。
由是,《长生殿》的演出从内廷、亲王阁部乃至文士大臣府邸、酒社歌楼,一时蔚然成风。除康熙四十三年(1704)明确记载关于曹寅府上《长生殿》的全本演出之外,其余史料中虽也多次提及演出全本,具体演出形态是否果真未加删减,仍有待考察。究其原因,“伶人苦于繁长难演,竟为伧辈妄加节改”(5)洪昇:《长生殿·例言》,《汇刻传剧》第二十八种,清末民初刘世珩暖红室重刻本。,民间戏班演出过程中不加删改几乎不可能。即便是大吏豪富阶层的家班或职业戏班,目前明确记载真正演出《长生殿》原真全本的也只有曹寅家班。加之折子戏的艺术形式于明末清初时期已经越发成熟并逐步盛行,问世于清初的《长生殿》处在这样一个折子戏不断发展的历史时期,且《长生殿》的全本演出皆须在特定场合下,其演出群体与观众在表演技艺以及欣赏水准、耐力等方面都需达到一定层次方能完成,绝非随意想演就演、想看就看,此间牵涉雅与俗、戏班与剧场、伶人与观众等诸多问题。《长生殿》演剧形态的转变与此诸多因素息息相关。
首先,清廷谕令官员禁养优伶,禁止官员进出戏园,如康熙十年(1671)明令禁止内城开设戏馆,官员禁养家班,民间草台班与职业戏班成为演出主体。古代传统戏剧的演出场所大体分为神庙剧场、文人厅堂、戏园茶楼三大类,其间各自对应的观演群体有所不同。神庙剧场演出多在乡间庙台,以仪式性祭祀演剧为主。当然,随着娱乐性戏剧的发展,宋元之后的乡间庙台也时常有民间草台班社演出的娱乐性戏剧。厅堂以及戏园的演出则以娱情为目的,尤其戏园的演出还具有商业性,显然文人厅堂演出艺术涵养最高,其演出虽多聘请职业戏班,但也不乏文人自己培养的家班,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曹寅邀请洪昇并筵集江南名士观演《长生殿》全本,即是出自其家班的演出。由此可见,清廷虽明文禁止官员私养家班,然终究是屡禁不止。
李渔《闲情偶寄》“缩长为短”有云:“观场之事,宜晦不宜明……然戏之好者必长,又不宜草草完事,势必阐扬志趣,摹拟神情,非达旦不能告阕。然求其可以达旦之人,十中不得一二,非迫于来朝之有事,即限于此际之欲眠。往往半部即行,使佳话截然而止。(6)李渔:《闲情偶寄》,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77页。”由此看来,昆腔传奇搬演大多要受“腰斩之刑”,以适应观演实际。
《长生殿》全本五十出,清初虽有关于全本演出的记载,然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曹寅家班那般不加任何删减进行搬演极为罕见。随着清廷禁止官员畜养家班以及折子戏演出形式的全面盛行,厅堂演出也逐渐以职业戏班为主体,演出形式上与民间庙台、酒社歌楼趋同,点戏之风日盛,最终“只索杂单,不用全本”(7)李渔:《闲情偶寄》,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78页。。“清康熙以后,由于演出环境方面发生的许多重要变化,以及折子戏自身艺术上的优势,使得折子戏在整个戏剧演出中的地位日趋重要,至迟在乾隆中叶折子戏开始取代全本戏,成为最主要的演出形式。”(8)解玉峰:《从全本戏到折子戏——以汤显祖〈牡丹亭〉的考察为中心》,《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
其次,昆腔传奇创作历来存在剧本与搬演彼此脱节的矛盾,而在剧本创作案头化趋势越加明显的同时,舞台艺人却在表演上精益求精,在有限的优秀剧作中充分发挥潜能,使昆曲演出形态由全本戏向折子戏转变。“折子戏时代”来临的标志在于折子戏表演形式的日渐稳定和规范,随着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行的宝仁堂本《缀白裘补编十二集》、“乾隆时期的昆曲演出实录”《审音鉴古录》、乾隆五十七年(1792)叶堂《纳书楹曲谱》等戏曲选本的出现,梨园场上的折子戏在唱、念、做、打等演唱层面上达到约定俗成,最终形成“歌唱出现‘定腔’(如《纳书楹曲谱》)、演出出现‘定本’(如《缀白裘》)、身段出现‘定谱’(如《审音鉴古录》)”的局面(9)解玉峰:《从全本戏到折子戏——以汤显祖〈牡丹亭〉的考察为中心》,《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
《缀白裘》与《审音鉴古录》几可作为清中叶场上昆曲演出盛况的实录,前者选录《长生殿》“弹词”“絮阁”“定情”“闻铃”“醉妃”“惊变”“埋玉”“酒楼”八出,后者选录“定情”“赐盒”“疑谶”“絮阁”“闻铃”“弹词”六出。除此之外,清代戏班演出剧目、戏单以及私人观剧日记中记录的戏目等,也多有《长生殿》折子戏。
这些折子戏的生成大体符合两种情形:一是自洪昇原本各出内容改编成的梨园演出脚本折子戏如“弹词”“絮阁”“定情”“闻铃”等;二是由原来剧中演出情境相应添加或者分离出的情节形成另外的折子如“赐盒”“酒楼”“醉妃”等,这两类折子戏的生成,前者偏雅,后者偏俗。如洪昇《长生殿·例言》所言:“伶人苦于繁长难演,竟为伧辈妄加节改,关目都废。吴子愤之,效《墨憨斋十四种》,更定二十八折……分两日唱演殊快,取简便当觅吴本,教习勿为伧误可耳。”(10)洪昇:《长生殿·例言》,《汇刻传剧》第二十八种,清末民初刘世珩暖红室重刻本。这是针对梨园艺人对《长生殿》进行删节改编的现象而言,从言语中可以感觉出文人与艺人即“雅”“俗”二者之间的对立。
好在《长生殿》“选择宫调、分配角色、布置剧情,务使离合悲欢错综参伍,搬演者无劳逸不均之虑,观听者觉层出不穷之妙。自来传奇排场之胜,无过于此”(11)王季烈撰,周期政疏证:《螾庐曲谈疏证》,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页。,如诸多戏曲选本中将“定情”一出分为“定情”与“赐盒”两个折子,“密誓”一出分为“鹊桥”与“密誓”,而“赐盒”实乃原本中“定情”一出的后半场内容,“鹊桥”则是原本“密誓”一出的前半部分。叶堂在制订《纳书楹曲谱》的过程中,凡“有与俗伶不叶者,或群起而议之”(12)叶堂:《纳书楹曲谱·序》,《纳书楹曲谱》,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其所选各出“俱遵原本,概不妄增名目,其有俗名与原本异者,亦姑从众以便披览”(13)叶堂:《纳书楹曲谱·序》,《纳书楹曲谱》,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冯起凤《吟香堂曲谱》在“惊变”一出之后附上时俗通行的“小宴”宫谱。凡此诸等,在一雅一俗之间,无不体现出了昆曲作为雅乐融入民间并被俗化的过程。
传统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样式,《长生殿》演出形态的转变既是昆曲发展历史的必然,同时也受到诸多偶然性因素的驱使。洪昇《长生殿》“百馀年来,歌舞场中,传为佳话,流播人间”(14)石韫玉:《长生殿曲谱序》,冯起凤:《吟香堂曲谱》,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其“定情”“絮阁”“闻铃”“弹词”等折子戏至今盛演于舞台,既是《长生殿》内在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使然,而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长生殿》演剧之祸以及梨园艺人对此剧进行删改加工,对演出形态的转变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总而论之,《长生殿》全本演出逐渐为折子戏所全面取代,进而被更广大的群体所欣赏接受,实属大势所趋的必然性转变。“从全本戏到折子戏是中国民族戏剧演进特有的规律,折子戏较适于有时间限制的厅堂演出和剧场演出,艺术上更有全本戏所不及的长处,故最终在乾隆中叶取代全本,成为民族戏剧最主要的演出样式。”(15)解玉峰:《从全本戏到折子戏——以汤显祖〈牡丹亭〉的考察为中心》,《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
二、《长生殿》刊印技术的转型
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长生殿》稗畦草堂原刊本刻成,至清末民初已有两百余年。二百余年来《长生殿》清代刊本众多,清晚期以前的《长生殿》多以雕版之法刊印,发行所费周期较长,全本的梓行历经了康熙二十八年(1689)国丧演剧之祸、清中晚期印刷技术的革新等社会变局,加之有清一代在制度上对戏曲实施一以贯之的禁毁政策,在如此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下,《长生殿》的刊印由其所处不同历史时期而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随着清末版刻由传统雕版、活字印刷向近代印刷技术转型,《长生殿》的石印本、铅印本相继出现。晚清民国时期《长生殿》版籍书面的刊印与发行,地域上集中于上海地区,印刷方式上以石、铅印技术为主,同时兼有刘世珩暖红室刻本以及全本《长生殿》曲谱抄本的行世,整体上呈现出地域集中、方式多样、技术更替的时代特色。
在《长生殿》的诸多清代刊本中,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蜚英馆石印本《增图长生殿传》、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文瑞楼四卷二册铅印本《绘像全图长生殿》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群益书社四卷一册铅印本《长生殿传奇》均得益于清末石、铅印技术的传入与应用。清末《长生殿》石印、铅印本的出现,展现了《长生殿》版刻由传统雕版、活字印刷向近代印刷技术的转型,《长生殿》版籍书面逐渐形成以铅、石印为中心的刊印形式,这一技术转型直接促成了民国初年扫叶山房石印本以及之后新式标点排印本的出现。
光绪八年壬午(1882)古吴扫叶山房主人《扫叶山房书目序》述曰:“迩来铅板风行尤为简捷,昔之宏儒硕彦著述等身,因卷帙繁重绌于赀而未克付梓者,今则一校理之劳而已……斯固剞劂氏之一大变局也。”(16)扫叶山房主人:《扫叶山房书目序》,《扫叶山房书目》,民国十三年(1924)重订本。自清末年间西方印刷技术涌入中国起,石印技术由一开始之未占一席之地,到光绪年间科举废除,活板印刷兴起,再到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因石印技术成书之速且可久传而开始兴盛。扫叶山房即是在此种局势之下“曩因锓板不便,易以精本石印行世”(17)《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民国十二年(1923)重订本。。
自庚申之乱后,苏州遭劫,扫叶山房于上海重整规模,其“烬馀板片修补重刊不遗余力,虽未遽复旧规而精华略备,且上自京畿下逮闽广通达无间。苟为宇内所有之书,咸力致以应官绅贵客需用,古今书籍旧本亦搜罗甚富”(18)《扫叶山房书籍发兑》,《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2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加之“良由海通以来,上海一隅几为全国之中心点,淹通之儒、博雅之士与夫豪贾巨商,凡欲购贩书籍者,无不以沪渎为挹注之资”(19)扫叶山房主人:《扫叶山房书目启事》,《扫叶山房书目》,民国十八年(1929)重订本。。如此,上海成为扫叶山房等书坊与书局刊印出版与发行的重镇。
光绪十三年(1887)李盛铎在上海创办蜚英馆,并于当年发行《长生殿》石印本,同年九月何瑞堂于上海开设鸿宝斋,此二者均属石印兴起之后所设的石印书局。自鸦片战争港口开放海运通商以来,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几乎成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点,清末民初印刷业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表现为由传统雕版到石印兴起再到以铅印为主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在彼时的上海表现得尤为明显。民国时期《长生殿》铅印本馆藏最为集中之地当属上海图书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映射出上海在近代印刷史上的特殊地位。
自古趋易避难是人之常情,譬如刻书之业,自传统木刻雕版技艺兴起后,以手抄书者渐少,同样随着铅、石印技术的应用,选择传统雕版刊刻者也自然减少,尤其铅印技术,排版迅速简捷,铅印书价低廉,极易流通推广,如此版籍书面最终以铅印为主,此既是时势所趋,也是人情使然。
首先,这一转型带来的最直观的变化莫过于《长生殿》绘像版画的兴起。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长生殿》刻成,至清末西方印刷技术引进,在这二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先后有《长生殿》清代刊本如下:(1) 康熙四十三年(1704)原刻本(稗畦草堂藏板、本衙藏板等);(2) 嘉庆十九年(1814)李钟元刻本(从溪静深书屋藏板);(3) 道光三十年(1850)小琅环山馆刻本;(4) 小巾箱刻本;(5) 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蜚英馆石印本;(6) 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文瑞楼铅印本;(7)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群益书社铅印本等。
康熙四十三年(1704)《长生殿》稗畦草堂原刻本最初并无绘像,之后从国家图书馆所藏三种“本衙藏板”本以及郑振铎藏《长生殿》巾箱本收有一幅“太真遗像”或“太真小像”的清代刻本,逐渐发展到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蜚英馆石印本与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文瑞楼铅印本中所收图像增至五十幅,即每出各附一图。郑振铎所藏清末平装石印本《长生殿》目录题“绘像全图长生殿传奇”,书衣题“绘图全本长生殿”,全本有插图五十幅,且直接冠以“绘像全图”“绘图全本”的题名。
除此之外,清末民初刘世珩《长生殿》重刻本在暖红室《长生殿》初刻本基础上也补画了二十四幅绣像。民国时期,扫叶山房本石印本《长生殿》绣像二十五幅,上海鸿宝斋书局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绘图长生殿》插图二十三幅,上海书坊石印本《长生殿》也是绣像绘图本。尤其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绣像绘图长生殿》插图五十幅,为蜚英馆石印本图像缩印版,近代石印技术以拍照、摄影为基本原理,其刊印时可将手绘图像随意缩放而不失原态。
其次,石印、铅印技术克服了传统雕版木刻刊印周期漫长、过程繁复的不足和缺陷,推动了发行的数量升级与快速流通,版式规格趋于统一,使《长生殿》的印刷出版更为便捷。自清初《长生殿》问世到泰西石印、铅印技术尚未广泛应用的清晚期之前,《长生殿》全本主要以传统雕版木刻以及传抄的方式行世,如:(1) 康熙四十三年(1704)原刻本;(2) 嘉庆十九年(1814)李钟元刻本;(3) 道光三十年(1850)小琅环山馆刻本;(4) 乾隆十五年(1750)沈文彩抄本;(5) 同治九年(1870) 孔宪逵抄本;(6) 光绪六年(1880)宜兴徐臻寿抄本等。
二百余年间传世的《长生殿》刻本以及抄本,包括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剧初刻本与重刻本在内,其版本不外乎以上数种。而自清末石印、铅印技术的引入至民国时期,《长生殿》大致有以下版本:(1) 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蜚英馆石印本;(2) 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文瑞楼铅印本;(3)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群益书社铅印本;(4) 民国间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5) 民国上海书坊石印本;(6) 民国六年(1917)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7) 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本;(8) 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泰东图书局铅印本;(9) 民国十九年(1930)上海大中书局铅印本;(10) 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新文化书社铅印本;(11) 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启智书局铅印本;(12)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铅印本;(13)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新文化出版社铅印本;(14) 民国二十六年(1937)国学整理社上海世界书局铅印本;(15) 民国二十八年(1939)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再加上扫叶山房等各大书局重印本,如:(1) 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扫叶山房重印本;(2) 民国十四年(1925)上海扫叶山房重印本;(3) 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扫叶山房重印本;(4) 民国十九年(1930)上海扫叶山房重印本;(5)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新文化书社重印本;(6) 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大中书局重印本;(7)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重印本;(8)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启智书局重印本等,数十年间刊印达数十种,且刊印模板渐趋统一,使再版重印快速迅捷。与传统木刻相比,铅印、石印技术所带来的出版印刷速度的飞跃,势必将《长生殿》剧作的传播接受范围推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最后,近代刊印技术的转型也同时促进了出版经营模式的升级,众多新式书局在西学渐进潮流之下应运而生,使《长生殿》的传播接受更具时代变革特色。尤其是上海作为时代变革的先遣之地,由刊印技术的转型引发上海各大、中、小型出版机构经营规模的转变,出版发行趋于集中一体化。
自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蜚英馆成立至民国年间,各书局、书坊、书社如暖红室、扫叶山房、鸿宝斋等,其刊印与发行销售已集中为一体。刘世珩《聚庼丛书》收有《贵池刘氏所刻书价目》,当中包含了《暖红室汇刻传奇》书目及其标价;扫叶山房设有南(上海彩衣街)、北(上海棋盘街)、苏(苏州阊门内)、松(松江马路桥)、汉(汉口四官店)五个号,其总发行所位于上海棋盘街的北号;何瑞堂于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在上海开设的鸿宝斋,其总发行所位于上海英租界四马路,印刷所则在当时的英租界威海卫路;民国铅印书社在封底通常会注明版权归属与出版发行等具体信息,如新文化书社《长生殿》封底标明总发行所位于上海四马路中市,大中书局《长生殿》封底标明总发行所位于上海白克路九如里七号等。
晚清民国时期刊印技术的升级以及出版发行经营模式的集中,超越和克服了传统刊刻周期繁杂与发售地域分散的缺陷和不足,加之上海作为出版发行的重镇,晚近时期《长生殿》的刊印发行地域上也集中在上海,如此得以辐射发散至全国各地。
三、《长生殿》传承模式的新变
昆曲发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案头、场上流传着诸多经典作品,昆腔剧种得以传承至今,离不开明清两代昆班如文人家班、职业戏班的曲师伶工以及文人曲家等人倾注的心血。一方面,明清众多文人曲家在进行昆腔传奇文本创作的同时,注重本色当行,以使剧作适应舞台搬演;另一方面,梨园伶人根据场上实际,将剧作原本改编为舞台演出的脚本,生成许多为人称道的折子戏剧目,得以保留、传承至今。
洪昇《长生殿》非但文律俱佳,“其选择宫调、分配角色、布置剧情,务使离合悲欢错综参伍,搬演者无劳逸不均之虑,观听者觉层出不穷之妙。自来传奇排场之胜,无过于此”(20)王季烈撰,周期政疏证:《螾庐曲谈疏证》,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页。,既可供文人案头清读,亦为曲家清唱所青睐,加之关目排场冷热合宜,搬演者与观听者各得所需,自清初至晚近时期二百余年未曾辍演,其艺术体制之胜可见一斑。
二百余年间,昆腔剧种历经盛衰波折,《长生殿》面对晚近时期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其传承模式也在时代潮流之下求新求变。
其一,近代文人群体有别于前代文人仅作为昆曲艺术参与者的身份,其对昆曲的援助与扶持成为晚近时期昆曲传承的主要力量。昆曲之盛衰,关乎新旧文化之进退,即如俞平伯《论研究保存昆曲之不易》所云:“溯‘皮黄’之兴不过数十年,而昆曲唯馀一线矣。非皮黄足以亡昆曲,即皮黄足以亡昆曲,亦不必如此其骤也,不必如此其骤而今竟如此其骤者,则社会缔构变迁之急遽有以使之然也……在今日而欲言保存昆曲,如何而可乎?曰无他,先存伶工之传耳……昆曲之亡是必然也,其幸而不全亡者,则在有此癖好者之努力及社会上之扶植耳。”(21)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二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456页。清末民初的新式院团、曲社机构、专科学校、研究学会等,无一不是成立于社会巨变的时代背景之下。
国家和民族遭受亡国灭种之患,救亡图存成为每个华夏儿女的心声。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昆腔剧种曾一度濒临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雅好昆曲的文人志士同样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民初建立的昆剧传习所即是在此局面下创立的,昆曲余势得以借此尚存。随着民国十年(1921)秋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创立,全福班部分老艺人被延入传习所从事教职,使昆曲雅乐得以传承。
昆曲内在文人雅化的艺术特质决定了文人阶层在昆曲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主体地位。就《长生殿》而言,自其问世之初即为文人名士所推崇,上至清宫内廷下至民间戏台皆盛演此剧,文人名士更将其奉若瑰宝常演于时。《长生殿》折子戏搬演于清代文人厅堂红氍毹之上,文人或品评文藻、或雅正伶人曲唱。《长生殿》问世至清末民初二百余年,歌舞场上流播如新,与文人提升《长生殿》表演艺术之功分不开。
自清末至民国数十年间,雅部昆曲虽濒临危局,然“《长生殿》几未辍演”(22)周传瑛口述,洛地整理:《昆剧生涯六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文人群体在此变局动乱之下,致力于对昆腔剧种进行救亡扶持。自昆剧传习所于20世纪20年代筹建始,先后重改组建为“新乐府”“仙霓班”,期间以新的演出形式在舞台上推出了《长生殿》的串折戏。如传字辈艺人周传瑛,自进入昆剧传习所,先后经历了“新乐府”“仙霓社”“国风苏昆剧团”以及“浙江昆苏剧团”等名称更替。《传字辈戏目单》中留存的《长生殿》折子戏目“定情”“赐盒”“絮阁”“舞盘”“鹊桥”“密誓”“进果”“小宴”“惊变”“埋玉”“闻铃”“迎像”“哭像”等,既反映出民国时期《长生殿》的演出形式,同时也体现出文人知识群体对昆剧传习的扶植之功。
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笑舞台新乐府昆戏院曾于十二月演出《长生殿》,演员顾传玠、朱传茗、张传芳均为昆剧传习所传字辈伶人,顾传玠工小生,在《长生殿》中扮演唐明皇,朱传茗工五旦兼工正旦,在剧中饰演杨贵妃,而张传芳工六旦,擅演《长生殿·絮阁》。这次三人合演的《长生殿》折子戏曾被誉为“璧合珠联之拿手戏”(23)《申报》1927年12月14日增刊。。舞台上流传至今的昆曲《长生殿》折子众多,集折串演起来甚至可与全本媲美,这与当时知识分子以支持演出、大力宣传、组织授课等方式积极扶持直接相关。
其二,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四大昆班相继解散,加剧了昆曲传承的迫切性,由此激发了新的戏曲教育模式,为昆曲传承酝酿了新的文化生态。昆曲传统职业戏班如清末全福班解散,昆班零散,若以这一时期的传统职业戏班、伶人为着眼点,当时昆班凋零,艺人沦落各地,甚至有后继无人之状,则确如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所言,清末民初昆剧极度衰弱,“但如果我们把20世纪前期文人阶层对昆曲各方面的深度参与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20世纪前期的昆曲史则可能完全改观”(24)解玉峰:《文人之进退与百年昆曲之传承》,《戏剧艺术》2016年第4期。。
民初时期,苏州张紫东等一批文人领导并创立了昆剧传习所,逐渐演变成后来的“新乐府”“仙霓社”等新式昆班院团,并涌现出诸多曲社机构、专科学校、研究学会等,“各地文人组织的各种类型的数量过百的曲社,大量曲谱、曲学著述的问世,各种戏剧学校、班社、协会的组织创办以及高等院校普遍开展的曲学授受等——20世纪前期毋宁视为整个昆曲史极为‘繁荣’的一段时期”(25)解玉峰:《文人之进退与百年昆曲之传承》,《戏剧艺术》2016年第4期。。
这一时期《长生殿》的戏曲选本,侧面映射出这一“繁荣”景象,如民国十九年(1930)顾名任教于暨南大学所编的《曲选》、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出版的顾震福所编《曲选》、民国十年(1921)上海戏曲学校新编《戏曲四十二种》、民国十五年(1926)杨荫浏为上海南洋大学学生会游艺部国乐科同学课余学唱昆曲印制的教本《昆曲掇锦》、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年(1938—1941)北京国剧学会昆曲研究会刊印的《昆曲谱二十六种》、由民国时期怡志楼昆曲研究社李福谦主持编印的《怡志楼曲谱》、民国二十八年(1939)天津一江风曲社编印出版的《昆曲汇粹》、成立于1923年的肄雅社所编《肄雅社剧本》等;再如吴梅自民国六年(1917)秋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曾在北大任教,教授戏曲专业课程,后推荐许之衡接替戏曲教学;钱南扬于民国八年(1919)入学北大,先后受教于吴梅、许之衡,《曲律易知》即为许之衡任教时所用,书中多处论及《长生殿》的曲律精严与排场之胜;吴梅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作《〈长生殿〉传奇斠律》,正值其任教于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之时。凡此种种,若非前辈文人的曲学授受,亦无今日《长生殿》乃至昆曲雅乐的薪火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