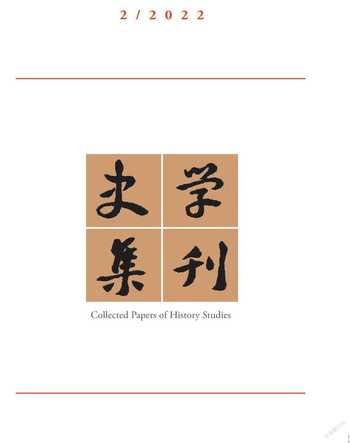叙述与记忆:朝鲜半岛文人的徐福东来记事研究
2022-03-17金洪培冯英盾
金洪培 冯英盾
摘 要: 徐福东渡一直在中日韩三国广为流传。朝鲜半岛人民对徐福东来的叙述与记忆,依其本土文献记载至少可回溯至新罗时期。关于徐福的传说、民谣至今仍在朝鲜半岛南部区域广泛流传,或称“徐市过之”的摩崖石刻痕迹也保留至今。无论是充满想象的叙述,还是遗址遗物中的记忆,都深层次反映了汉字文化圈内独有的文化现象与逻辑。通过对朝鲜半岛文人“徐福东来”记事叙述与朝鲜半岛民间记忆——传说、民谣等资料的研究,勾勒出徐福一行在朝鲜半岛的可能行迹,并进一步揭示徐福研究的当代文化学意义。
关键词: 徐福东渡;朝鲜半岛;文人记事;汉字文化圈
徐福东渡一事首见于《史记》,其作为古代东亚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一直以来是东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学界主要从中日关系或文化交流的视角研讨这一问题,围绕徐福东渡原因、次数与人数、路线等展开。①
近年来,随着国内海上丝路研究的兴起,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徐福东渡途经朝鲜半岛的问题。②
事实上,早在朝鲜王朝时期的史书中就已经记载了有关“徐福入海求神”的故事。在韩国民间也流传着不少与徐福相关联的民谣和传说,此外,在韩国济州道和庆尚南道也发现了多处疑似“徐福过之”的石刻遗址。在朝鲜半岛有关徐福东来的记事中,无论是充满想象的叙述,还是有关遗址遗物传说的记忆,都深层次反映了汉字文化圈内独有的文化现象与深刻内涵。综观国内学界,尚未发现对韩国有关徐福的文献记载、口头文学、遗迹分布等进行基础性的收集与整理,对徐福及其船队在朝鲜半岛的活动轨迹的推测仍不够充分。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朝鲜半岛历史上有关徐福东渡记事的整理与研究,对相关疑似历史痕迹与民间传说进行梳理,在为国内学者提供相关研究素材和视角的同时,深入揭示中国大陆文化对朝鲜半岛的深刻影响及其现实意义。
一、朝鲜半岛古代文人笔下的徐福
朝鲜历史上有关徐福事迹的记载相当丰富,据统计,从新罗时期崔致远至朝鲜末期金允植的57位历史名人文集中,有关徐福的记载有138条之多,
[韩]洪琦杓:《韩国古文献所载“徐福记录”研究》,韩国古典翻译院编:《民族文化》第48辑,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6年版,第74页。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朝鲜半岛有关徐福事迹记载历史源远流长。新罗末期文人崔致远曾吟唱道:“挂席浮沧海,长风万里通。乘槎思汉使,采药忆秦童。日月无何外,乾坤太极中。蓬莱看咫尺,吾且访仙翁。”
(新罗)崔致远:《孤云集》卷一,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版,第152页。 诗中谈到了徐福带领童男童女采药的事情。高丽时期,文人们对徐福东渡日本的印象已具有普遍性,自高丽后期起,有关文集开始出现日本有徐福祠的记载,
[韩]洪琦杓:《韩国古文献所载“徐福记录”研究》,韩国古典翻译院编:《民族文化》第48辑,第73页。以至于把徐福当成是日本的一个文化象征。郑梦周曾于1378年前往日本,在其所作的诗中出现了日本徐福祠的记录。
虽然在朝鲜半岛有关日本徐福祠的记录首见于高丽末期郑梦周的诗中,但对徐福前往日本的轨迹有详细的记载则最早出现在朝鲜前期文人申叔舟的《海东诸国记》中,“孝灵天皇、孝安太子,元年辛未,七十二年壬午,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福遂至纪伊州居焉。在位七十六年,寿百十五。……是时,熊野权现神始现,徐福死而为神,国人至今祭之”。
《日本国纪·天皇代序》,(朝鲜)申叔舟:《海东诸国记》,首尔:国立中央图书馆1976年版,第19页。 朝鲜王朝时期的李瀷(1681—1763)坚定主张徐福、韩终都曾来到朝鲜半岛。他在“答安百顺”一信中写道:“辰之为秦,据《左传》辰嬴可证,吾故曰:‘避秦来而韩人先之也’,据《谷永传》,韩终与徐福同来又可证。”
(朝鲜)李瀷:《星湖全集》卷二六《答安百顺(丙子)》,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版,第518页。 朝鲜末期文人李圭景(1788—?)对徐福东渡则持怀疑态度,他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三韩始末辨证说》就曾写道:“始皇初并天下,遣徐福、韩终之属,重载童男女,入海求神仙,因逃不还。则福外有终,终必韩之后裔,而与良同仇者也。其弁辰亦从后至,而秦人故名辰也。此虽无可考,可以意度。”
(朝鲜)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三韩始末辨证说》,首尔:明文堂1982年版,第17页。
朝鲜中后期,随着朝日两国使臣交流的日益频繁,不少文人对日本的徐福祠进行了实地考察,因此,在此时期不少朝鲜文人的意识中,徐福不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姜沆(1567—1618)在其《看羊录》中就有“徐福,载童男女入海,至倭纪伊州熊野山止焉。熊野山尚有徐福祠,其子孙今为秦始,世称徐福之后”(朝鲜)姜沆:《看羊录》,首尔:西海文集2005年版,第68页。的记录。姜沆曾在壬辰倭乱期间被掳至日本,被俘期间游历日本各地,对当时日本国情有较深的了解。此时期朝鲜文人文集中对徐福的认识,已经渐渐摆脱了“三神山”“长生不老药”等神秘主义传说形象。朝鲜后期,朝鲜文人们对徐福研究的范围与深度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
我国宋代文人欧阳修曾作《日本刀歌》,写道:“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肥沃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玩器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66页。《日本刀歌》记录了“传闻”中的徐福在秦始皇焚书之前携带先秦古籍前往日本的事情。朝鮮文人张维(1587—1638)则通过对海域、航路等地理条件的论证否定了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他认为黄海海域宽阔异常,若“徐福、卢敖迂怪之士,往来惝怳者,极其所至,要不出我国西界外”。
(朝鲜)张维:《溪谷集》卷六《送谢恩兼奏请副使吴肃羽朝京师序》,首尔:曹龙承发行1977年版,第98页。此外,金就文(1509—1570)写过一篇《徐市论》,推论徐市带领3000名童男童女入海求药的动机其实是为齐国报仇。金就文认为“盖市齐之人,而齐之灭,在于始皇之手,则秦其雠也。为齐报仇,市之意也”。且分析徐福由于“势孤力弱,不可以独立,故其与童男女入海者,亦勾践生聚十年之意也。而意成事立,则为齐报之”。
(朝鲜)金就文:《久庵集》卷二《徐市论》,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0年版,第351页。此说亦不无道理。
通过朝鲜文人的相关记录,还可以发现朝鲜半岛本土的徐福记忆由来已久。首先关于三神山的位置,李瀷曾记录了在朝鲜半岛民间流传的说法,“朝鲜人云,三山在国中,以金刚、智异、汉拿当之”。
(朝鲜)李瀷:《星湖僿说》卷二○《经史门之徐市》,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79年版,第125页。朴趾源(1737—1805)也采择了“或曰枫岳为蓬莱,汉拿为瀛洲,智异为方丈”
(朝鲜)朴趾源:《燕岩集》卷三《孔雀馆文稿》,首尔:景仁文化社1974年版,第79页。这一民间流传的说法。“枫岳山”为“金刚山”的别称,因此李瀷与朴趾源所采集的民间说法实为一致。不过李象靖(1711—1781)对这种说法持否定态度,曾主张“智异山亦名方丈,即徐福所称三神山之一,其说固荒唐不可信”。
(朝鲜)李象靖:《大山集》卷四五《书权上舍季周游智异录后》,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年版,第371页。除了朝鲜半岛民间的三神山传说以外,济州岛上流布的徐福传说也是由来已久,朝鲜中期文人郑蕴(1569—1641)和朝鲜后期文人朴泰茂(1677—1756)都曾提到过徐福来济州采集山药的事情。
(朝鲜)郑蕴:《桐溪集》卷一《七言绝句》,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版,第12页;(朝鲜)朴泰茂:《西溪先生集》卷三《答郑济州》,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4年版,第587页。
二、近代朝鲜半岛流布的徐福痕迹调查
朝鲜半岛自古就有文人对徐福东渡一事展开过议论,近代以来韩国学界又注意到了韩国民间流传的与徐福相关的传说、民谣和遗迹。随着视角的转换,“徐福东渡”也成为半岛文人眼中的“徐福东来”。
1.朝鲜半岛徐福记忆——传说、民谣
近代以来随着民俗学专业研究的发展,较古代而言,近代文人对民间口头传承更为重视,对其研究也更为系统深入。韩国学界自20世纪后半叶开始对韩国民间传说、民谣等口头传承文学进行系统性的搜集调查。这其中包含了很多与徐福相关的传说、民谣。通过对这些调查材料的梳理,使得韩国有关徐福的传说、民谣的分布区域也变得明晰起来。
最早秦圣麒曾于1956年3月,在济州岛西归浦市好近里搜集过“徐市和不死药”的传说,故事梗概是:“从前,秦始皇时期曾有过一位名叫徐福的人游览济州岛。徐福受到秦始皇的宠信,想要前往海外旅行,就告诉秦始皇如果服用在三神山采摘的不老草的话将会长生不老。希望长生不老的秦始皇就命令徐福立刻前往采摘。徐福就用昆仑山上生长的千年大树造船出发前往三神山,并带领了500名童男童女。徐福一行经黄海到达济州岛的朝天浦,在此处收获了被称为神仙果的岩高兰之后,经西归浦前往日本。最后徐福到底有没有采到长生不老草,则无从知晓。但是朝天浦和西归浦正房瀑布的岩壁上留下了‘徐市过此’的刻字。”
[韩]秦圣麒:《济州岛传说》,济州:白鹿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此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分别于1979年、1980年、1982年、1985年在韩国民间搜集到《老人歌》《海女歌》《秦始皇歌》《秦始皇和不老草》等涉及徐福东渡内容的民谣与传说。
《老人歌》是1979年由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采集于庆尚北道月城郡甘浦邑(今庆尚北道庆州市甘浦邑)的民谣,其内容中有一段谈到秦始皇遣徐福领500人去三神山采长生不老药,结果杳无音信。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语文研究室编:《韩国口碑文学大系》7-1,首尔: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0年版,第633页。《海女歌》是1980年由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采集于济州市三徒洞的民谣。其穿插有秦始皇遣徐福带领500名童男童女到耽罗国(今济州岛),从西归浦上岛寻找长生不老草未果,然后又前往日本的相关内容。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语文研究室编:《韩国口碑文学大系》9-2,首尔: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1年版,第486页。《秦始皇歌》是1982年由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采集于庆尚北道金海郡上东面(现属于庆尚南道密阳市)的民谣。其中有关于秦始皇派遣徐福带领500名童男童女前往三神山寻找长生不老草,虽然找到了长生不老草并装满船送给秦始皇,但秦始皇吃了之后依然未能长生的内容。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语文研究室编:《韩国口碑文学大系》8-9,首尔: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3年版,第340页。《秦始皇和不老草》是1982年由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采集于庆尚北道军威郡孝令面的一则传说。故事中有徐福欺骗秦始皇率领500名童男童女前往三神山没有返回,并在日本留有后裔等内容。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语文研究室编:《韩国口碑文学大系》7-11,首尔: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4年版,第347页。
还有一个秦始皇和不老草的传说于1985年由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收集于全罗北道井邑郡泰仁面(现井邑市泰仁面)。故事讲述了徐福带领童男童女跟种子前往日本。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语文研究室编:《韩国口碑文学大系》5-6,首尔: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7年版,第363页。全罗北道井邑市德川面也流传有涉及徐福带领童男童女前往三神山故事的民谣《青春歌》。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语文研究室编:《韩国口碑文学大系》5-6,第830页。1980年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在庆尚南道居昌郡居昌邑搜集的《不老采药歌》,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语文研究室编:《韩国口碑文学大系》8-5,首尔: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1年版,第482页。以及2012年在全罗北道高敞郡新林面采集的,强调方丈山是智异山,蓬莱山是金刚山,瀛洲山是汉拿山的《高敞的三神山》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高敞的三神山》,2012年3月21日,
https://gubi.aks.ac.kr/web/VolView2_html5.asp?datacode=07_00_FOT_20120321_KEY_JYG_0011&dbkind=2&hilight=%EA%B3%A0%EC%B0%BD%EC%9D%98%20%EC%82%BC%EC%8B%A0%EC%82%B0&navi=%EA%B2%80%EC%83%89;%EA%B3%A0%EC%B0%BD%EC%9D%98%20%20%EC%82%BC%EC%8B%A0%EC%82%B0(%EC%A0%9C%EB%AA%A9),2021年1月26日。故事,這些都与徐福东渡主题有关。
韩国南部地区至今依然广泛流传着与徐福相关的传说与民谣。就这些传说与民谣口头传承人所在的具体地点来看,基本散布在济州道济州市三徒洞、庆尚北道军威郡孝令面、庆尚北道庆州市甘浦邑、庆尚南道密阳市上东面、庆尚南道居昌郡居昌邑、全罗北道井邑市泰仁面、全罗北道高敞郡新林面、全罗南道和顺郡寒泉面、全罗南道金海市上东面,以及接下来将会谈到的庆尚南道南海郡良阿里、庆尚北道巨济郡河清面、庆尚南道南海郡尚州面尚州里等地方。考虑到民间口头传承的特性,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传说与民谣在其周边地区也应广泛流传。直到今天与徐福相关的传说、民谣仍流传于庆尚南北道、全罗南北道,以及济州道等韩国南部的广阔区域。
与此同时,还应关注与徐福在朝鲜半岛的活动区域等内容相关的传说。韩国学者洪淳晚就曾对济州岛上的“朝天浦”和“西归浦”地名由来的传说进行了考察。
[韩]洪淳晚:《徐福集团的济州渡来说》,济州岛史研究会编:《济州岛史研究》第2辑,济州:济州岛史研究会1992年版,第30页。传说中称,徐福一行来济州岛寻找瀛洲山的时候,首先到达朝天浦,徐福一行在此看到日出,便在石头上刻下“朝天”二字,这块石头也被称为“朝天石”,不过这块石头如今已经无从寻找。然后徐福一行到达西归浦,又在此处的正房瀑布处留下“徐市过此”刻字离开。在济州岛的地名由来的传说中,一北一南的朝天浦与西归浦两个地方皆与徐福有关。
这种与徐福相关的地名由来传说并不仅仅限于济州岛,周永河在《徐福,事实和传说历史》中介绍了全罗南道求礼郡“徐市川”地名由来的传说。“徐市川”地名传说中提到“从前修筑万里长城的秦始皇听闻智异山上有长生不老草,就派徐市去寻找。徐市率领3000名童男童女分乘九艘大船,经过南海,沿多沙江(现蟾津江)而上,然后顺着多沙江支流进入智异山。但是一行人并未寻到长生不老草,就又沿着这条支流返回南海前往耽罗(现济州岛)。由于徐市沿着蟾津江这条支流来回两趟,因此当地人称这条支流为徐市川”。
[韩]周永河:《徐福,事实和传说的历史》,济州学会编:《济州岛研究》第21辑,济州:济州学会2002年版,第339页。求礼郡除了“徐市川”传说之外,还有马山面的冷泉里地名由来的传说,郑守一曾介绍过这一传说,内容大意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想要长生不老,就命令徐福带领500名童男童女前往三神山寻找长生不老药草,徐福在前往三神山路上途经此村,喝了这个村子冰凉的泉水,惊叹泉水之凉,便称这个村子为‘冷泉村’”。
[韩]郑守一:《徐福渡韩考》,济州学会编:《济州岛研究》第21辑,第118页。冷泉村与徐市川都位于智异山山麓,这两则传说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流传的三神山中方丈山是智异山的说法相互映照。
在与求礼郡南部相邻的南海郡锦山也有与徐福有关的传说。李昌植(音)就曾于2004年1月前往庆尚南道南海郡良阿里找到当地居民徐圣泰(音)(时年81岁),从他那里搜集到在当地流传的徐福传说。故事情节大概是,“秦始皇派遣徐福前往三神山寻访神仙以求得长生不老药,徐福带领500名童男童女、五谷,以及种子、药材、工人、生活必需品等从山东琅琊出发,到达庆尚南道南海郡尚州面锦山下面的碧莲浦、豆毛浦,由此上锦山寻找长生不老草,但是却未能如愿登到山顶。为此,徐福一行便举行三神祭和天祭,但是一行人在锦山上仍未寻找到长生不老草。寻长生不老药未果的徐福便向秦始皇汇报虚假情报,告知在住着神仙的蓬莱岛上虽然有长生不老药,但是岛周围有鲨鱼群,请求能派遣射杀鲨鱼的弓箭手,秦始皇答应了徐福的请求。随后徐福以锦山为据点形成部族集团,维系着在南海周边海域势力的同时,派出数艘船前往蓬莱山、方丈山、瀛洲山以寻找长生不老草。后来徐福以为锦山离秦国太近地形又狭小,就决定带着一行人离开锦山前往济州岛”。
[韩]李昌植(音),《徐福传承的正体性和文化信息产业利用方案》,东亚细亚古代学会编:《东亚细亚古代学》第12辑,首尔:东亚细亚古代学会2005年版,第61-62页。
同样也是在南海郡,洪淳晚曾根据曾任南海女子中学校长的河英秀(音)讲述,对当地一个名叫“雪里()”的地名由来传说“徐离串传说”进行了研讨。大意是“在南海岛东南端有一个名叫雪里的小村子,那里把往海延伸的地方叫做‘徐离串()’。据河英秀(音)介绍这个‘雪里’其实就是徐福离开的意思,即‘徐離’”。
[韩]洪淳晚:《徐福集团和济州道》,济州市:济州文化院2002年版,第298-299页。在韩语发音里“雪里”和“徐离”都一样,都是“(seori)”,而“徐离串”也可以理解为“徐福离开的地方”。因为在韩语中“”的发音近似于“徐离”,而“”正是中文“地方”的意思。河英秀(音)本人也认为徐福从此处离开前往济州岛,后由济州岛前往日本。这种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把以上几个传说关联地点用线连接的话,可以发现能形成一个合乎逻辑的路线,即从求礼郡南下到南海,在南海诸岛徘徊,继而去往济州岛。如果说传说带有主观性的话,那么将这些地点连成线后,就变成了一个较为客观且合乎逻辑的路线图。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
除此以外,与徐福和秦始皇的不老草有关的地名还有仁川市德积岛国守峰、仁川市白翎岛仙岱岩和大青岛、古群山群岛的仙游岛和蓬莱九谷、全罗南道珍岛郡的徐市址()、全罗南道高兴郡的徐市墓()和蓬莱岛、求礼郡智异山芝草峰、全罗北道南原广寒楼的三神山、全罗南道的白岛等,
[韩]郑昌元(音):《对徐福东渡说和中国史书东传的关联性探索》,历史实学会编:《历史和实学》第51辑,大田:历史实学会2013年版,第186页。以及全罗南道丽水市的鸢岛。
[韩]数字化丽水文化大展:“”词条,
http://yeosu.grandculture.net/yeosu/search/GC01300842?keyword=%EC%84%9C%EB%B6%88&page=1,2021年1月26日。这些都为我们深入了解徐福一行在朝鲜半岛可能的活动轨迹提供了线索。
综上所述,涉及徐福传说发生地的朝鲜半岛具体地点主要有:济州道济州市朝天浦、济州道西归浦市、全罗南道求礼郡徐市川、全罗南道求礼郡马山面冷泉里、庆尚南道南海郡尚州面锦山、庆尚南道南海郡雪里,以及仁川市德积岛国守峰、仁川市白翎岛仙岱岩和大青岛、古群山群岛的仙游岛和蓬莱九谷、全罗南道珍岛郡的徐市址、全罗南道高兴郡的徐市墓和蓬莱岛、求礼郡智异山芝草峰、全罗北道南原广寒楼的三神山、全罗南道的白島和鸢岛等。就其分布区域来看,主要集中在朝鲜半岛西部与南部沿海,以及全罗南道智异山一带。
而与之相应的是,目前已知的有关徐福传说流传分布区域也都集中在今天韩国的全罗南北道、庆尚南北道、济州道等南部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单一的传说不具有可信度的话,那么将这些关联地点相连接,会发现这一连线能形成一个合乎逻辑,且存在一定可能性的徐福一行在朝鲜半岛的行迹路线。
目前韩国学界部分学者对这些传说的真实性持怀疑的态度,如郑昌元(音)提出根据现今的研究成果来看,只能得出徐福到过朝鲜半岛的结论,但是他具体到了哪里就不得而知,甚至连到过济州岛都不能完全确定。他推断这些传说是中国史书流传到朝鲜半岛后对此区域的意识产生影响后的结果。
参见[韩]郑昌元(音):《对徐福东渡说和中国史书的东传的关联性探索》,历史实学会编:《历史和实学》第51辑,第204页。 笔者以为,如果说这些传说是无中生有或是随意揣测的话,那为何传说的关联地或流传区域会如此集中地分布在朝鲜半岛西部、南部海岸地带,而不是流传于今天的平壤、开城、首尔等古代朝鲜的政治、文化中心区域?况且中国史书中并不涉及徐福一行在朝鲜半岛的具体活动情况,因此,朝鲜半岛西部、南部徐福传说的出现也不能断言就是受到了中国史书的影响。因此,韩国有关徐福传说的分布区域所呈现的合乎逻辑性的现象依然值得学界做更进一步探讨。
2.朝鲜半岛徐福记忆——石刻
除了传说、民谣等口头文学相传外,徐福东渡后在韩国的活动轨迹线索在韩国南部相关石刻等历史遗迹中也可以发现端倪。济州道西归浦市正房瀑布的摩崖石刻、济州道金塘浦的朝天石摩崖石刻、庆尚南道南海郡锦山的岩刻、南海岛上的摩崖石刻、庆尚南道巨济岛上的摩崖石刻、庆尚南道统营郡小每勿岛上的摩崖石刻等都是传说中与徐福有关的刻字遗址。不过在这六处遗址中,目前尚存的只剩下位于南海郡锦山的“尚州里石刻”。
[韩]郑守一:《徐福渡韩考》,济州学会编:《济州岛研究》第21辑,第 114页。
济州道西归浦市正房瀑布的摩崖遗迹虽然已经消失,但是对它的文字材料介绍却较为详细。
据韩国《济州新报》2011年2月22日的报道,济州道政府打算对正房瀑布摩崖刻字进行系统调查,即通过岩壁扫描和岩壁落石调查等方法试图找到传说中的摩崖刻字。同年4月6日,韩国《联合新闻》也报道了济州道将要开展确认摩崖石刻是否存在的调查计划,并引用了时任济州道文化政策科科长的李奎峰
(音)的话“如果摩崖刻字确实存在的话,将成为很好的旅游资源”。参见《(秦始皇使者的正房瀑布峭壁摩崖是事实吗)》,《联合新闻》,2011年4月6日。但从后来没有相关跟踪报道的情况来看,这些实证性质的寻找活动最后也是无果而终。有关正房瀑布摩崖石刻消失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由于正房瀑布上游的淀粉工厂排出的废水损坏了摩崖石刻;二是岩壁的脱落导致刻字的破损消失。而消失的时间被初步判定为20世纪50年代,
济州东洋文化研究所编:《济州道摩崖铭》,济州:济州东洋文化研究所2000年版,第136-137页。因为洪淳晚曾就此摩崖石刻对生活在正房瀑布附近的10余名老人进行过走访调查,据这些老人们说最迟至20世纪50年代还见到过刻字。
[韩]郑守一:《徐福渡韩考》,济州学会编:《济州岛研究》第21辑,第113页。
朝鲜末期在济州岛生活过的文人金喜正研究了正房瀑布刻字的拓本,以及拓本下段由朝鲜末期书法家丁鹤乔写的说明。通过丁鹤乔的说明可知拓本内容为“徐市过之”,这也是目前西归浦市“徐福展示馆”所展示的“徐市过之”的依据。
塚原熹:「済州島にある秦徐福の遺跡考」、『朝鮮誌』、1910年第4巻6号。韩国官方的韩国旅游发展局在1985年出版的《韩国观光资源总览》也收录了在济州岛西归浦市正房瀑布处有“徐市过此”摩崖石刻的信息。
南海岩刻据李东先(音)的说法,共有五处。
[韩]李东先(音):《神秘的徐福过此》,全国文化院联合会编:《全国乡土文化研究发表会受赏集》,首尔:全国文化院联合会2003年版,第313-356页。尚存的南海锦山岩刻分布在7m*4m的岩石上,刻字大小为1m*0.5m。
[韩]张明守(音):《对韩国岩刻画的文化相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仁荷大学,2001年,第43页。其拓本曾在朝鲜末期被朝鲜学者吴庆锡带往中国,请当时的清朝学者何秋涛解读,解读结果为“徐市起礼日出”。但就这些刻字的判读上,不仅我国学者王盛美不认同,
王盛美:《韩国尚州里锦山刻石初读》,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编:《徐福文化交流》总第19期,2013年。韩国学者文治雄(音)也判定南海石刻的内容与徐福无关。
[韩]文治雄(音):《南海石刻和徐福关联说的问题点》,东亚细亚古代学会编:《东亚细亚古代学》第35辑,首尔:东亚细亚古代学会2014年版,第89-90页。
尽管如此,韩国民间一直流传着“徐市过此”刻字的传说。洪淳晚曾在《徐福集团和济州道》中介绍过一则传说,大意为徐福带领500名童男童女来到锦山,在此地打猎,过得很愉快,离开的时候为了给后世留下自己曾来过的证据就刻下“徐市过此”字样。
[韩]洪淳晩:《徐福集团和济州道》,第298-299页。1979年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在庆尚南道巨济郡河清面(现巨济市河清面)采集的有关传说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语文研究室编:《韩国口碑文学大系》8-1,首尔: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79年版,第320页。中也同样谈到徐福一行在经过全罗道的时候留下了“徐市过此”的摩崖刻字,在经过海金刚时留下了“徐市过此”的摩崖刻字,在经过东山时也留下有关“过此”的刻字。据传巨济岛海金刚峭壁上曾有“海东汉国”字样的石刻,在它附近的小每勿岛也流传着徐福的传说。
[韩]尹明喆:《对徐福的海上活动的研究——以航路为中心》,济州学会编:《济州岛研究》第21辑,第 25页。但如今都已无从查证。
传说丽水市鸢岛村海边的绝壁上也曾有过“徐氏过此”四个朱红色大字。
[韩]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金鳌岛”词条:
http://yeosu.grandculture.net/yeosu/search/GC01300873?keyword=%E5%BE%90%E6%B0%8F%E9%81%8E%E6%AD%A4&page=1,2021年1月26日。相传这几个字是徐福带领500名童男童女前往三神山采集长生不老药时路过此地留下的。而且在丽水的一个名为“Nongol
()”的沿海峭壁上也曾有过类似的字体,但由于年代久远已无法识别。除此以外,传说还谈到徐福一行为寻找长生不老草路过了今庆尚南道南海郡二东面良阿里,并留下了象形文字。但由于1959年的Sarah台风,刻字的岩石脱落消失。无独有偶,据传在庆尚南道巨济市距海金刚西边500米远的雨祭峰上也有过“徐福过此”的摩崖石刻。根据现场设置的景点说明介绍,徐福一行曾在雨祭峰的峭壁上留下“徐福过之”的刻字,随后徐福经南海锦山、济州的西归浦前往日本。而其消失的原因与南海郡二东面良阿里的石刻消失的原因一样也被解释为在1959年9月的台风sarah中脱落,如今只能用肉眼看出脱落的部分与周围石头颜色的不同。
目前所知的朝鲜半岛最东边的徐福传说刻字遗迹集中在巨济岛,而巨济岛与日本对马岛的直线距离不过60公里,结合在日本也有不少徐福相关的传说和遗迹这一事实,徐福一行或部分成员由巨济岛跨海经对马岛到日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不过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在目前韩国有关“徐福过此”石刻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质疑的声音,如文治雄(音)就对现存的南海石刻以及西归浦石刻的内容提出质疑,其将这些现存的刻字视为篆字,并将“徐市起礼日出”几个篆字一一与南海石刻拓本字样做对比后,得出这些刻字并不是“徐市起礼日出”,继而否认石刻与徐福具有关联性。
[韩]文治雄(音):《南海石刻和徐福關联说的问题点》,东亚细亚古代学会编:《东亚细亚古代学》第35辑,第107 页。关于这些字属于哪种字体,中韩学者间的意见也并不一致。我国学者何秋涛将这些字理解成籀文,将内容解读为“徐市起礼日出”;
方毓强:《韩国庆南是徐福东渡的重要一环》,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编:《徐福文化交流》总第19期,2013年。王美盛则将这些文字看成是钟鼎文和殷商契文,判读成“午蜃(辰)风以(已)丁亥”,并解释其是中午时分出现海市蜃楼,风停了下来的意思;
王美盛:《韩国尚州里锦山刻石初读》,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编:《徐福文化交流》总第19期,2013年。赵鸣的论文对济州岛刻字内容阐发了新的解读,虽然也认为南海郡石刻内容为“徐氏起,礼日出”,但却认为归浦摩崖石刻内容为“齐臣徐市,迁王过之”。
赵鸣:《海上丝绸之路与徐福东渡的意义》,《大陆桥视野》,2019年第11期,第94页。因此就目前来看,中韩学界虽然都已经出现了否认刻字内容是“徐福起礼日出”或“徐市过之”的研究,但是这些否定意见不能被看作是对徐福一行曾来过朝鲜半岛的否定。况且,对这些字的判读结果目前尚没有被中韩学界普遍接受。因此,对这些文字的解读仍然是学界尚待解决的问题。南海郡与西归浦地理间隔很远,而刻字内容却具有相似性,考虑到古代东亚社会刻字的意义与航海条件,这一现象本身就告诉我们,在这一区域曾发生过有组织的船队活动。至于是否与徐福一行有关,还需要学界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三、徐福一行在朝鲜半岛的行迹推测
目前关于徐福一行在朝鲜半岛的航线研究方面,除了前面介绍的我国学界的研究之外,韩国学界对徐福船队在朝鲜半岛的行动轨迹也同样有所关注。
如尹明喆根据济州岛流传的相关传说,得出了徐福从山东半岛出发,直接到达韩国南部海岸然后前往济州岛进行修整与物资补给,搜集信息,然后去往最终目的地的结论。参见 [韩]尹明喆:《对徐福的海上活动的研究——以航路为中心》,济州学会编:《济州岛研究》第21辑,第55-56页。除此以外,赵源一与金钟圭也赞同这种直达韩国南部的主张。两位学者根据相关史料,论证了徐福一行确实到了日本,并结合对中国古代航海装备与航海技术、气候规律等的分析,主张徐福一行可能从成山头出发向东直接经过朝鲜半岛南部海域途经济州岛,再穿过朝鲜海峡抵达日本。除此以外,他们还给出了另一条可能的航路,即从黄海北上,在黄海和渤海湾之间荣成湾的成山头顺着黄海暖流的东部支流再次北上到达朝鲜半岛,然后沿着朝鲜半岛的西海岸一路南下,经南海途经济州岛向东穿过朝鲜海峡,借助对马岛水域暖流到达日本,并根据实际的地理气候条件,得出此条路线是最安全也是成功率最高的一条海上路线的结论。参见[韩]赵源一、金钟圭:《对古代中国的航海先驱问题的小考》,国民大学校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编:《中国学论丛》第28辑,首尔:国民大学校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2009年版,第42页。综观韩国学界关于徐福船队在朝鲜半岛活动轨迹的研究,可归纳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山东半岛直达朝鲜半岛南部济州岛,然后经济州岛向东到日本;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由半岛西北部,沿岸而行,先南后东,最后到达日本。这基本上与我国学界目前已有的意见相一致。所不同的是韩国学界已经出现了关于徐福一行经过朝鲜半岛时所途经具体地点的推测。
如韩国学者郑守一根据当时的航海技术、地形、海洋的自然条件、航海目的和任务等多种条件进行综合考察后主张:徐福一行从鸭绿江江口沿着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经过乌牧岛(现平安北道身尾岛)和氵贝江(现大同江)江口的椒岛到达黄海南道长口镇,从这里再经过秦王石桥(现壅津半岛附近岛)、麻田岛(现开城西南的乔洞岛)、古寺岛(现江华岛)和得物岛(现德积岛)到达位于汉江江口位置的唐恩浦(现京畿道南阳),然后从这里继续向南经过韩半岛西南端的扶南岛和大、小黑山岛到达耽罗(现济州岛)。又根据求礼、巨济、南海等地相关遗迹,作者继续推测徐福一行从济州岛向东北方向沿着南海岸航行,或者从朝鲜半岛西南端不经济州岛直接沿着南海岸向东航行。但由于对半岛上散布的徐福记忆——传说、民谣、石刻等考察的尚不够充分,导致对徐福一行的活动轨迹的推测仍有不够详尽之处。参见[韩]郑守一:《徐福渡韩考》,济州学会编:《济州岛研究》第21辑,第124-125页。
结合朝鲜半岛有关徐福传说、民谣、石刻的分布点的梳理与徐福一行东渡目的的探讨,可以描述出一条可能的徐福一行在朝鲜半岛的行迹。徐福一行自山东半岛出海以后,循岸而行至朝鲜半岛西北部,然后再依次经今韩国仁川市白翎岛、仁川市大青岛、仁川市德积岛、全罗北道古群山群岛、全罗南道珍岛郡,然后再由此入济州岛朝天浦后再到济州岛南端,最后经今济州道西归浦市往西折返,此为徐福一行的第一次行迹。当时朝鲜半岛北部属箕氏朝鲜,这已经被地理发现所证实,而朝鲜半岛南部的情形史书记载不详,推测徐福一行当时为求神山仙药重点搜索了半岛南部区域,但遇到当地土著势力阻挠后,徐福回到齐地向始皇要求武装力量,“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3页。托言大鲛鱼,似为掩其“止王不来”之心。秦始皇在徐福第一次东渡求长生药不果后曾十分震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徐福第二次东渡时做流亡准备的可能性。
第二次徐福一行或遵循前次航海路径或直接穿越黄海到达朝鲜半岛南部,亦即今天的韩国全罗南道一带,因为有武力可恃,深入内陆进行了细致的搜索。根据目前韩国传说分布等线索可以推测其路径,即在全罗南道白岛一带进入全罗南道高兴郡、全罗南道求礼郡徐市川、全罗南道求礼郡马山面冷泉里、全罗南道求礼郡智异山芝草峰,再由此南下至海岸处,后经全罗南道鸢岛、庆尚南道南海郡尚州面锦山、庆尚南道南海郡雪里到庆尚南道巨济岛,巨济岛与日本对马岛隔海相望,直线距离不过60公里,徐福一行由此入日本列岛。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由巨济岛往东的朝鲜半岛南部地区没有任何有关徐福的传说或遗迹的分布。
作为此时期唯一见于史籍记载的大规模大陆人口出海向东移动的历史事件,不可能不在相关区域留下丝毫线索,且朝鲜半岛东南部存在秦末流民也是歷史事实。据《后汉书》记载:“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
《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19页。早期马韩在朝鲜半岛南部,主要人口为当地土著,
“马韩在西,其民土著。”参见《三国志·魏书》卷三○《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49页。且势力最大,
“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濊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参见《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2818页。在这般环境中能使马韩在其东面单独辟地使之生存,足见当时秦末流民流入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单次人口数量众多,以至于须单独辟出一块地来;二是流民具有一定的武装,但势不足以压制马韩,仅能维持自卫。这也是“辰韩常用马韩人作主,虽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为马韩所制也”的原因。
《晋书》卷九七《辰韩》,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34页。马韩为秦末移民单独“割东界地”,想必这批秦末移民者先到达的不一定是朝鲜半岛南部的东部,而是先到达了半岛南部的中部,再由陆路往东迁徙。因朝鲜半岛有关徐福叙事的记忆——传说、民谣、石刻分布地点只局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西部与中部,所以这一推理也不悖逻辑。本文并不主张构成辰韩的秦末流民主体来源都与徐福东渡事件有关,但是不能排除两者间的关联性。
迟至隋炀帝大业四年(608),隋炀帝遣文林郎出使倭国。在日本列岛裴清经过秦王国后说:“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州,疑不能明也”,
《隋书》卷八一《倭国》,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25页。可见秦末流民在东亚分布之梗概。而目前能将这些现象合理联系起来,且见于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徐福东渡一事最为合适。
由于以上推测囿于史料匮乏,不免有重逻辑推理,缺乏史料印证之感。因此,此方面的推论将来还应有赖于考古发现来印证或纠正。目前韩国学界已有学者通过论证坟丘墓形式在中韩之间出现的时间顺序,从而认为徐福一行确实存在曾到达朝鲜半岛南部的可能性。
[韩]林永珍:《韩·中·日坟丘墓的关联性和其背景》,《百济学报》第14辑,2015年。林永珍提出此观点的依据是中国的坟丘墓历史至少能回溯到公元前20世纪,而在朝鲜半岛,坟丘墓这一墓葬形式只能回溯到公元前2世纪,因此得出韩国坟丘墓的出现与中国本土人口向朝鲜半岛迁徙有关的结论,并且将公元前2世纪的这个节点与徐福东渡这一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不过,这也只是一种基于现象的猜测,尚缺乏决定性的考古证据证实坟丘墓在朝鲜半岛的出现确实是徐福东渡的结果。
如刘凤鸣通过对韩国南部出土的青铜剑与水晶珠等文物与在山东半岛出土的齐国时期的相应文物对比后,得出最晚在战国时期两地就已经开展了文化交流活动的结论。同时作者通过对现有材料的整理,发现了齐国的文物主要集中在朝鲜半岛南部这一独特现象。参见刘凤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0页。我国学界已出现了以考古资料为线索,来开展早期朝鲜半岛南部与大陆文化关联性的研究。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徐福东渡可能抵达朝鲜半岛南部这一猜测的可信度。不过,这些考古发现只能作为秦末有移民到达朝鲜半岛南部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此集团与徐福一行的绝对关联性。本文所推测的徐福一行的可能行迹,只能视为一条有力的线索,未来学界可依据此线索,做更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更好地揭示徐福东渡之谜。
徐福东渡推动了早期大陆文化的向东传播,促进了东亚整体的文化交流。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徐福东渡一事依然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在当代中韩文化交流方面,正以新的面貌呈现出其所蕴含的当代文化意义。当前,中韩学者对徐福的认识从“合作友好”与“和平”
如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的周永河曾建议把徐福视为东亚文化中相互理解的文化象征。参见[韩]周永河:《徐福,事实和传说的历史》,济州学会编:《济州岛研究》第21辑,第341页。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永先也将徐福当成是和平的使者。参见李永先:《徐福是和平的使者》,济州学会编:《济州岛研究》第21辑,第18页。这些积极的象征意义出发,对如何利用好这一中韩文化交流象征进行诸多有益探索。责任编辑:孙久龙
Narration and Memory: Research by the Literati of Korean Peninsula on Xu Fu’s(徐福)Eastward Sea-voyage Records
JIN Hong-pei, FENG Ying-dun
(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133002,China
)Abstract: The story of Xu Fu’s(徐福)sea-voyage eastward has been widely spread in China, Japan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narration and memory of Xu Fu’s deed by the Korean scholars can be traced at least back to the period of Silla. Legends and folk songs about Xu Fu are still widely sprea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Peninsula, and
the trace of the known as inscriptions on precipice carving Xu Shi Guo Zhi (which means Xu Fu once has been here) has been preserved to this day. Both the imaginative narration and the memory in the relics reflect the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logic in the cultural circl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Korean literati’s narration and folk memory of the Peninsula such as legends, ballads and other materials,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possible track of Xu Fu on the Peninsula, and further reveals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on Xu Fu.
Key words:Xu Fu’s sea-voyage eastward; Korean Peninsula; literati’s records; the culture circle of Chinese characters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2.0021
收稿日期:2021-07-29
作者簡介:徐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欧中世纪史。
① absolute monarchy后来通常译为绝对君主制,类似概念还有新君主制(new monarchy)和绝对主义(absolutism)。
② [法]查理·V.朗格索瓦著,莫玉梅译:《要关注英法历史的比较》,《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年第1期。
1360501705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