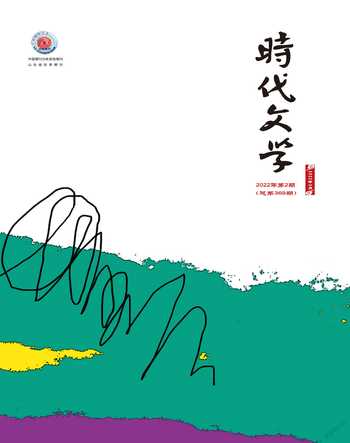读碑阅史听廉声
2022-03-17孙栗
孙栗
京杭大运河滔滔不息,见证着神州大地的千年沧桑;它如一条永不飘落的绶带披挂在广袤的原野,献礼春夏秋冬的风情与浪漫。在这条温婉绶带上,镶缀着一颗玲珑又璀璨的明珠般的小城——山东临清。据史载,明清时期,南来北往的商船在这里聚集,依靠繁忙的运河漕运,临清迅速崛起,成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被誉为“小天津”。她盘坐在河畔,像一位不饰自丽的风韵仕女,以水为镜,拢首顾盼着俏美的身影,向南来北往的客官诉说着春朝秋夕的月华露浓;甫一低头,就会看见曾经芳华远播的临清运河钞关那窈窕的身段。这是全国唯一的一处钞关旧址,是临清重要的历史文物,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筑遗址。临清钞关于明宣德年间设置,至明万历年间,税收居运河八大钞关之首,迄民国时废除,风雨六百载,其风华虽已湮没在历史云烟中,那依稀模糊的身影仍在娓娓讲述着临清欲说还休的故事,听闻大运河的繁华与兴衰。在此建筑遗址上漫步,抚摸着一块块碑石,感受着时代的波涛,在漫漶的文字中,探古思今,思绪无穷……
公与私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齐鲁漫游,临清寻古,抚碑闻政,阅史听廉,在时代的清风中寻觅历史的足音,无不是寻访者澄怀静虑的初心。
临清运河钞关位于老城区会通河南支西侧,现存建筑系户部榷税分司之遗址。院内存有明清时期的碑刻 13 通,最早的1通碑是《重修户部分司公堂记碑》。
此碑刻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碑身高 170厘米,宽 80厘米,厚 18厘米。原碑额、碑座莫知所归。碑文楷书,14 行,行 40-50 字不等,记录了临清置炉铸币的历史。该碑原立于户部榷税署衙,民国年间临清县政府进驻署衙,被埋入地下。1988 年发掘出土后存临清钞关院内。
碑由明正德九年(1514年)一甲一名进士唐皋撰文,同科进士、临清户部分司主事林春泽立石。碑文记道:
“户部分职其分署临清……于宣德间主事刘君澄所创。阅岁既远。春泽莅堂,日就颓敝,将新焉,绌於时。今年春度时,少 □□□□□□有,堂之旧者新之,移堂后庐其前欤,辟其左右各若干庑,足以容众。凡吏庶之趋而立者,伏而听者,進之可進,退之可退也。址之洼陷实之土而加崇焉。堂之前为嶂,稍远地为廊,堂成匾曰“经国”。左右翼以廊序,以栖谞卒之。在公其后有堂,以便退公以款过宾,则依趙君文载之旧而增,右厢梁柱耳加之匾曰“浣心”。其西则为公帑,设重门案牍之度,藏泉布之委顿咸於斯,而匾曰“敬事”,而又置炉,以司煆植其庇物。门垣驰道斥於其旧,髹垩藻饰焕然一新。堂之弗弗以烦民,弗病於有司,一匿税之罚所取资焉。堂之抅始事於旦夕之后,而落成於祓禊之前。役不患巨民,不告劳将垂之久,不可以弗识也。予惟天下之事成於志,而废於志之弗恒也。况事有非可以己者而兴之、废之又可以觇志也。是举,他人视之若迂缓两可,己而不知经□□□□□□□/□渊使宰昭号令、剔奸蠧咸於堂乎?莅位焉,而况兹堂之新,地增而高,座厂而明,庭辟而广,道砥而直,则其功又不徒饰者,尙以驭下德之崇也,明以烛幽知之用也,广以容物仁之俗也,直以履正礼之经也,兹堂之新,子之志益可觇矣。周书礼崇,惟志先王之所以明饰百工者先焉。余闻德敷之政,舟者悦、贾者怀,远迩归颂焉,则兹可埝捻之一节,推而广之又大焉者矣。书此以俟……” (因年久失修,碑文受损致部分字迹模糊难辨,文中以“□”表示。)
读碑文可知,碑关公署由刘澄任钞关主事时发起建造,林春泽履职时已日久失修。因时机不成熟,资金短缺,即“绌於时”,未及时修缮;后林春泽达权通变,“匿税之罚所取资焉”,即用正税之外罚没的商户偷税逃税款项,修葺此堂。“右厢梁柱耳加之匾曰‘浣心’。其西则为公帑,设重门案牍之度,藏泉布之委顿咸於斯,而匾曰‘敬事’,而又置炉,以司煆植其庇物。门垣驰道斥於其旧,髹垩藻饰焕然一新。”公堂所嵌匾额,一为“浣心”,其意乃洗涤心灵,警示上下“洗濯杂念,淡泊名利,清廉治税”;二曰“敬事”,其意为认真做事,告诫官员“严谨法度,敬慎处事”。
凡立石,不唯記事,且寓训政之意,更见葺堂者之初心。其规模形制之作,皆以精神训导为旨归,即所谓“觇志”——“驭下”“烛幽”“容物”“履正”之意。这对历任临清钞关官员廉洁行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是为公之心,倡廉之意。从明代成化到崇祯年间, 临清管关官员计 146 人,其中进士 125 人,官员的文化素质较高,颇多能臣贤吏。许多官员在钞关主事任上及以后的宦途中,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浣心”以修德,“敬事”以执政,“舟者悦,贾者怀,远迩归颂焉。”由此可见,修葺固为小事,因能寓政风政德,官员敬事体国,恤民勤谨。泽被后世,其功非一。事实也确实如此。不唯碑文所记,刘澄、林春泽等人事迹于史亦有记载。
广东人刘澄,字端本,明天顺四年(1460年),以户部主事督理临清关税,稳重忠厚,沉默少言,刻苦自励,好学孝亲,因德行被举荐而登进士第。在钞关任上,在户部郎中任上,在知府任上,皆清正廉洁,不以私情而干公事。清阮元修《广东通志》,称刘澄“朴厚寡言,事亲尽孝。家贫力学,手不释卷。景泰癸酉乡荐,天顺庚辰登进士第。历官户部郞中,督收粮草,人莫能干以私”。蒲田地方志也记载,“刘澄出守,以‘三事’(清、勤、慎)自励,蔬食布衣,澹如也。”
无独有偶,福建侯官县人林春泽(1480-1583年),字德敷,明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正德十四年(1519年)督理临清关税,商民德其名为“林佛”。明陈文烛在《程蕃府知府旗峰林公墓志铭》中记其事,“宽征疏滞,行旅德之,呼为林佛。”(《二酉园续集》卷十七)尤为可颂的是,明武宗朱厚照南巡,官员进谏受杖责,罚跪午门。林春泽刚直不阿,以公理为盾,犯颜直谏,上疏数千言,据理力争,解同僚之困。明武宗临清逗留期间,侍从江彬等仗势作威,林春泽威武不屈,江彬也颇忌惮其刚直。林春泽历明成化、正德、弘治、嘉靖、隆庆、万历六朝,享寿 104 岁,被誉为“人瑞翁”, 重宴琼林,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卒世。朝廷先后敕建“人瑞坊”“六朝大老坊”。
如刘澄、林春泽这般清正廉洁的官员代不乏人,明代有赵瑺、刘焕、徐琏、曾璵、李义壮、孙继鲁、刘玺、王尚学、莫如善、何东序、张祥鸢、邹廷望、詹彬等;清代有李基和、噶尔萨、阿锡鼎、王协灿、张蔼吉等。
封建社会,为官公,则造福一方;为官私,则祸国害民。百姓之福祉系于为官者大矣,故历代统治者无不以简官任吏为大事要事。然事有不谐,投机钻营之流、假公济私之辈混迹官场,鱼肉百姓,令人观史兴叹。
钞关乃“渔猎之薮”、逐利之所,一些人如听事官、书吏、书手、算手、巡捕、总甲、管事等一众角色,“竟趋司榷”,钻营投机入职钞关,利用手中的权力,玩弄手段,极尽勒索之能事。明天顺二年(1458年),江西省建昌府南城县考满回京知县陈升就沿途所见奏言道:临清等处钞关,“其诸处量船之人,于船户有所贿者,减其船之丈尺,钞虽腐软亦收无嫌疑;于船户无所贿者,则增其尺寸,钞虽坚完亦择不受。甚至上下串同,侵欺盗卖,为弊多端。”胥役互相勾结,厚贿管官,“任恣侵渔之利,苛索行商未已”,安享不劳之利,“莫敢谁何”。加之统治者不惜涸泽而渔,原税外,又有“辽饷、新饷、助饷、练饷、剿饷种种名色,于正额之外,税增两倍”。其结果是,“弊端莫指,徒令奸胥肥蠧,商困民穷,而于国用无所补。”
这一现象在明代文学巨著《金瓶梅词话》有着生动的表现。该书故事即以临清为背景地,形象地描述了临清钞关主事钱龙野徇私枉法的伎俩,是当时不法税吏的一个缩影。
作为豪强西门庆府上的座上宾,钱龙野对西门庆的货船出入钞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其偷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因为钱龙野的“关照”,西门庆的手下往往偷梁换柱,把绸缎当成茶叶、马牙香等报关,甚至两箱并成一箱、三停报两停,蒙混过关。十大车货,纳个三十两五钱银子,“少使了许多税钱”。这边钱龙野放水,那边西门庆自然也少不了钱龙野的好处。如此官商勾结,偷税漏税,无疑是割国家的血脉,动国家的基石。
虽则是小说,却有着现实生活真实的影子。西门庆是《金瓶梅词话》中一个典型人物,是富商巨贾,也是一个墨吏,他以钱为通关手段,以权为借路符节,打通临清钞关税使而偷税营私,这是当时地方豪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而故事中的临清钞关主事钱龙野徇情枉法以谋私利,是当时不法税吏的典型代表人物。
有太阳就有阴影,有清廉难免有贪渎,有刚正自不绝谗佞。正与邪的对立,公与私的较量,善与恶的交锋,有时如暗流涌动,有时似惊涛裂岸。当正大碾压邪祟,则大快吾心;值恶丑遮掩美俊,则扼腕恨噬。每每晨光熹微夜阑人静之时,研读临清钞关官员史料,詹彬的善行大德令人心如清风拂煦,旭日临窗;又情似波涛,恨不能手刃奸佞。
为了整顿吏治,加强中央税收,朝廷煞费苦心,简选能吏清吏主政临清等沿运河钞关。詹彬是其中的典型。詹彬,字汝宜,福建安溪人,清嘉庆三十八年(1559年)進士,以户部主事督理临清关税。临清居河运要津,历任榷关者对工商业者征税额无常。詹彬上任后,宽厚以驭民,公平以处事。在认真观察、考核商贩数量、所收税额后,将税额固定下来,并使之成为常态,由是经商秩序井然,商民纳税自觉有序。年终结算时,钞关征收的税银非但不少,而且比朝廷定额多了“数以万计”,詹彬悉数上交。然而,此种正义之举断了一些经纪人和官吏勾结以权谋私的发财之路,使“前后榷关之人交口唾骂”,户部尚书也因不能得到好处大为不满,将詹彬贬为凤阳府通判,詹彬因此郁郁而终。“卒之日,葛衣为敛而已。”(清庄成修《安溪县志》卷八,“人物”)
如此清廉人物,却是这般人生结局,怎能不让人唏嘘叹惋,又如何不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想吏治之于国家之重要。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治国理政,关键在人。施之于今,又何尝不发人深思。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济私者或得逞于一时,而为公者将留名青史,垂光后世。
省与烦
苛税一直是百姓的痛。税烦则民怨,税省则民欢。取税于民,用税于民,则国家安,否则国家殆矣。一税可知天下兴衰,信矣!
《计部李公德政序碑》是一通颂扬户部(又称计部)钞关税使李梓德政的碑刻,记述李梓为政与临清商业兴败的事迹,以此兴论,揭橥钞关赋税与国计民生、市场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法省而商至”“法烦而商离”的恤商思想,值得深思。
此碑于1993 年在原临清钞关仪门前出土。撰文者秦大夔,篆额者曹楷,书丹者汪应泰,3人均为临清人、进士、显宦。故亦称“三进士碑”。碑,额、身联体,高 204 厘米,宽 94 厘米,厚 25 厘米,书体行草,50行,行 49 至 51 字不等,刊刻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碑文开头即称李梓为“君子”,为“公”,颂赞他为“望重海内”,皇帝“下命以国计属大夫,出督清源关”。
清源,临清之别称。碑文记述李梓“厘弊剔蠹、悬鉴以照”,实施“简法便商”举措,各地客商纷至沓来,“内外大通,去往两利”的盛况。撰文者感而兴叹:“昔人酌盈计虚以足国计,故入征而出复征,其谁不以为此匮彼昌,以值之无忧常□而卒告匮,何者?法烦而商离也。今严入而宽出,狡昔之法灭其反,金帛聚而用饶,何者?法省而商至也…… ”
李梓,号养宇,陕西泾阳人,以御史监理临清钞关,整理吏治,重法绳赃,剔奸厘弊,竭尽“辑濯之官,侦巡之率”之责,使 “狼贪者、鼠窜者与夫泽糜而蒙虎者俯首揖志。” (《创建阅货厅碑记》)临清钞关“市行其便,货流其通”,商民安市,国库帑金日增,临清关税年盈达十一万两之多,约占全国七大税关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一。“法省而商至”“法烦而商离”的简政措施,受到了商、民及朝廷的欢迎。碑文热情洋溢地赞叹:“商曰:盖归乎来,有吾大夫。民曰:货囚不售,有吾大夫。大司农曰:国计易盈,有吾大夫……其贻惠百姓,当不在子产下矣。”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须以民生为本,以休养生息为务,而非残民、害民。天下如此,一国如此,一省一市一县一乡莫不如此。古今虽殊,理亦如此。知之者众,知之而犯者亦不乏其人。
万历中期,明神宗向各地派遣税监,临清成了重灾区,李梓推行的恤商、惠商思想受到冲击。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几乎在李梓致仕的同时,税监马堂榷关临清,横征暴敛,很快引发王朝佐反税监斗争,史称“临清民变”,朝野震动。
起因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天津税使马堂兼任临清税使,雇用社会闲散人员充当打手,敲诈勒索,任意抽税,肆意罚款,中饱私囊。据载,每年山东课税十五万两白银之多,而上交朝廷的税额仅二分之一,其余税款全部被分赃,揣进个人腰包。马堂在山东七年,就私藏税银一百三十万两(《明神宗实录》卷四一六)。为逼人纳税,马堂及其爪牙私设公堂,凌辱商人和手工业者,甚至草菅人命,工商业者遭到严重摧残。黑云罩顶,市场萧条,“中产之家,破者大半。”
一时间民怨沸腾,激于义愤,王朝佐挺身而出,号召 1 万多名临清市民到税署请愿,抗议重税。马堂下令兵丁向市民射箭。这激起百姓强烈不满,冲击并纵火烧了衙署,杀死马堂爪牙 30 多人。事件发生后,官府不分青红皂白予以镇压,到处抓捕百姓,受株连者甚多。在“人人自危”的关键时刻,王朝佐挺身而出,慷慨陈言:“首难者我也,请独当之,勿累无辜。”遂英勇赴死。为纪念王朝佐,临清民众为他建立了“王烈士祠”。矗立在钞关院内的《王朝佐烈士碑》,碑高 175厘米,宽63厘米,厚 20厘米,记录了烈士王朝佐“慷慨殉义”之事和立碑修建始末。读之唏嘘,慕烈士之气概,感好义君子之善行。
碑文如下:
王烈士者,明末人也,姓王讳朝佐,平素仗义。万历末年,太监用事,中官马堂者,收税临清,百端骚扰,地方被害。人心痛恨已极,焚其衙署,毙其党三十七人。事闻,株连甚众,人人自危。王朝佐慨然出首,一人承当。阖郡人民赖其保全,载在州志。当时州尊陈一经,嘉其义,为之立祠。其祠倒坏三十余载,士民过其地者,知其慷慨殉义之事,莫不唏嘘悼叹。今者,惟赖四方好义君子同心捐助,因其旧址,廓而大之,鸠工庀材,不数月工程告竣。庶几微显幽闻,而烈士义气之概,永垂不朽,以符有功德于民,则祀之之意云。大清道光三十年岁次庚戌仲夏阖郡士民公立。
临清市民反税监斗争是我国历史上较早的一次新兴市民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政治事件,它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税简则民安,税烦则民乱。它也又一次印证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临清民众的反税监斗争也是新兴阶级维护自身权益的正义之举,在中国历史上放射着灿烂的光彩。
限与放
“日暮秋声乱,津楼夜雨时。舟船泊岸久,商旅入眠迟。”漫步钞关,今人徐舒的诗不觉跃入脑海。
“津楼夜雨”曾被清代钞关官员李基和评为临清十景之一。津楼指临清钞关玉音楼,户部榷税分司置署之初建之,楼上刊刻明宣德皇帝朱瞻基专为各地钞关颁布的圣旨,户部主事郭应聘《重建玉音楼记》记云:“丝纶之命则载以方屏,饰以金璧,绕以龙纹,巍然兹楼之中焉。”玉音者,王言也。钞关建玉音楼,以为妥崇玉音之所。
李基和在《津楼夜雨》诗序中写道:“清源关当南北要津,往来经商及宦游人出此者,必以封榷是索。榷西岸有前朝建玉音楼,风雨中宵,旅航系缆,自楼上听之,泪三声下。时有弹水调龙吟者,叶彼潇潇,愈添愁思。”
傍船河岸,系缆中流,中宵独立,听风声飒飒,听雨声敲船篷,听琴挑水龙吟,念百姓之苦,心中自然生忧添愁。这首诗不是自悼嗟叹,而是对景伤怀,“哀民生之多艰”。
临清居运河冲要,“帆樯并集,百货流通,商贾操厥奇赢,趋利若鹜”,封建王朝在此建钞关,不是为了发展商业经济,而是强化对商人的威慑力,限制商业经济的发展,即“籍而税之,以寓逐末之意”(《临清直隶州志》卷九 “关榷志?附临砖”)。 这与封建统治一贯奉行的“崇农抑商”的国策一脉相承,它阻碍了中国资本经济的发展,损害了商人阶级利益,甚至威胁到百姓的安身立命之本,自然使本就艰难的商旅之人愈添愁思了。
披阅史料,我们看到,从 16 世纪起,明王朝商品经济空前活跃,显示出由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过渡的转型。放眼全球,东西方强弱的转换也正是从此一时期开始。然而,商品经济最终没能在大明的国度里蓬勃兴起,更没有实现革命性的变革,专制主义皇权对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和私人工商业的摧残,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日渐减弱。
自明万历时期起,封建王朝对商人实行严格的控制,向他们征收难以承受的税赋,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掠夺,受害最深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即市民阶层,不但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创造性更是受到打击摧残。自派驻税监征税以来,“临清向来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二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至矣。”(户部尚书赵世卿奏疏,见《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封建王朝“重农轻商”,工商经济受到严重制约,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而同一时期,欧洲如英、法、荷等国家,垂涎于海外贸易高额利润,向外扩张殖民的势头日益强劲;随着世界市场的拓展,反过来又刺激国内商品生产的发展,旧的封建领主逐渐被新兴的手工场主取代,货币作为资本显现出越来越大的力量,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政治影响的扩大,使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统治成为可能。1640 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制,确立了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拉开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开启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而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的1644 年,失去经济和政治活力的明王朝被农民起义的风暴掀翻。恃武力一统天下的清王朝,画地为牢,闭关锁国,不能睁眼看世界,以致越来越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大潮。大运河波澜不兴,船来船往,临清钞关又恢复其收税功能,对商业资本的限制仍在继续,仍在强化。清乾隆时变本加厉,实行一系列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增加钞关征税、扩大征税范围、提高商税税率等。商税繁重,各级官吏敲诈勒索,有的钞关征收的商税甚至比规定税率高出数倍。表面繁荣的运河城市的背后,是死而不僵的社会危机、经济停滞,是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列强的差距日益加大,落后就要挨打成为历史的必然,鸦片战争以来百年屈辱实则滥觞于此。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中國共产党的领导下,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经过不懈奋斗,我们不但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而且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能力,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的节点上,抚今追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昂视阔步,勇毅前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清运河钞关虽然“廉颇老矣”,但风骨犹存,精神依旧。它大睁着双眼,深情地注视着这奔涌不息的运河,年年载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焕颜长城内外……
2411501705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