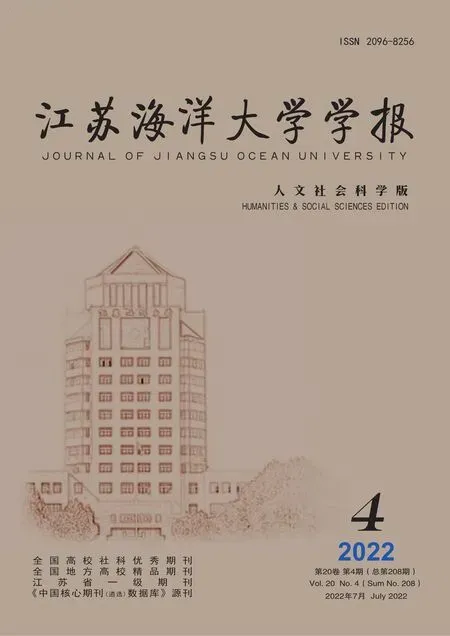异托邦、身体与僭越的文学
——论《一座幽灵城市的拓扑学结构》
2022-03-16于锦江马汉广
于锦江,马汉广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在《一座幽灵城市的拓扑学结构》(以下简称《幽灵城市》)这篇小说中,作者阿兰·罗伯—格里耶表现出了极具先锋性的写作姿态,他对文本空间进行了独特的处理:拓扑学方法构建出来的文本空间让时间失去了对叙述与内容的根本的规定性。这是一种怎样的空间?这种空间和空间中的种种“身体”有何种关系?它们如何构建出一个先锋的文本?巴尔特曾指出,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以简单过去时给出的文本秩序仿佛在与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合理秩序遥相呼应,从而使它成为了资本主义秩序之神话的合谋者[1]27。在对传统书写秩序进行抗争的意义上,我们看到了格里耶与福柯相遇的可能。福柯所谓的文本“异托邦”理论也给了我们审视这一文本的新的视域。
一、异托邦空间与拓扑空间
文学文本的叙述往往需要一个能将其语言内容展开的空间,作者设置这空间的方式或有意或无意,但总归表现了某种关于叙述“秩序”与人物存在方式的思考。首先的问题是,“空间”,对人意味着何物呢?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思想界关于空间言说的几个代表性看法。首先是牛顿物理学,这种看法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具有不可思议的宰制力:它把空间当作既定的、均匀不变的、等待物体放置的场所,并以它去理解人在世界所处的状态;空间就意味着一种先在的、等待物进入的稳定之秩序,人也不过是一个死板的、被合理性规定的客体对象。在哲学领域,康德开启了以先验观念论和经验直观的方式去思考空间的道路,可他仍和牛顿一样把空间当成“单一、同质、无限、连续、各向同性的统一整体”[2]42。到了20世纪,胡塞尔的现象学给出了新的空间视野;其弟子海德格尔以存在论解释空间,换言之,他将人的在世理解为“此在”,世界由“此在”开出,空间伴随着对“此在”具有组建作用的在世而展开,空间就不是一个先在于主体的静止封闭的场所,而与“此在”的在世密不可分[3]129。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同样接受空间与人之在世的关系,但他更强调具体知觉的肉身与空间的关系;人之肉身与空间彼此紧密相联,肉身也参与了对其处境的“空间性构建”[4]。福柯作为梅洛—庞蒂在巴黎高师时期的学生,其“异托邦(heterotopias)”理论一方面继承了庞蒂对空间与身体的思考,另一方面也较庞蒂更进一步,它来到了各种具体的权力场域中;在这基础上,福柯去思考“主体”何以在力的角逐中被生产,去回应实际的人的生存体验。这里是现实而非逻辑的抽象,是历史与现时、概念与实体的杂糅,它以完全扭转时间性主导的叙述方式阐述一个空间主导的现实。异托邦就是要表明,现实的人所处的是充满了异质性的场域,是权力网络下的具体人所生活的另类空间;它的构词形式也提醒我们,空间以复数的样态参差交叠,使得我们在世之肉身体验到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其实,传统的、已然僵化了的空间正是在如此意义上,被20世纪的这些理论家们视为一种理性主义的关于秩序的整体性想象——在其独断的规定性中已经偏离了现实,表现出了对人的伤害。
格里耶在《幽灵城市》这一文本中,与福柯的理论不谋而合。《幽灵城市》的空间设置将这种新的异托邦空间以文学语言的方式构建出来,我们可以在小说文本的内容与形式两个大方面去把握福柯在《另类空间》《词与物》序言等文本中所涉及的异托邦特征:一是拓扑的文本结构、叙述方法以及戏拟、互文、并置等艺术手法构成的文本形式,二是内容上对异质性材料的表现,例如隐喻的意向表达的多样化所指,抑或是碎片化的关于谋杀故事、历史神话、梦呓般的独白等故事内容的组合。我们将在下文具体分析文本空间的异托邦性质。
首先,格里耶运用了拓扑方法在小说中构建出了多维的空间,这也是文本最重要的结构方法,一个另类的文本空间由此打开。在小说文本标题中,“拓扑学”就已直接表明了小说所使用的特殊叙述方式。作为数学中的几何原理,拓扑学的研究展现了几何物体在不同空间维度中变与不变的状态;这也使之成为与传统欧几里德几何学相对的一种空间或图形观念,例如著名的“莫比乌斯带”“克莱因瓶”。在这种拓扑学中,几何图形不再是不同视角得出的观测的统一,因为事物的秩序不是以整一的有序性表现,图形的表面处于一种褶皱般的朝向自身的可逆的状态——这种褶皱“根本不是断裂……而是仍然缠绕着自身”[5]192。正如美国学者莫里塞特所界定的,“拓扑”是“基本的智力的(intellectual)操作,能够揭示表面、体积、边界、接触、孔洞的形态,且最重要的是关于内部、外部的观念”[6]。如此,格里耶在小说创作中积极借用了这种方法,整个小说的五个空间就是如此建立了一个不断折叠变换的空间。其中的故事情节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空间进行叙述,但正如拓扑几何的物体,它保持了“不变的部分”在文本中重复、互文。值得一说的是,拓扑空间往往是一种非深度的空间,它在几何上表现出物体的表面与表面间相连相交又相分离的样态,所以,拓扑空间就被以一种特殊的、失去深度的开放性空间引入了小说文本。小说文本中的“第一空间”是一个典型的呈现,在前三节它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废墟城市中的多个细致场景,尤以第一节的标题“繁衍的房间”为重点。从其叙述方式来看,潜在的叙述者是从第一节的平面化视觉观察开始,以“我”作为静态的视点细察一个封闭房间中几个女性的活动。从第二节开始,叙述进入动态化的描写,仿佛是从绘画的二维进入了动作的三维空间,这一节里,“我”慢慢隐去了,动词的使用开始频繁起来。第三节里,画家的笔变为雕刻家的刀,实际上也暗示了这种写法上的转换,这一节雕刻的刀刺中作品,却给了模特伤口,这个情节随后到第三空间的第二节再次被以拓扑的方式回应,即观看戏剧的女子也是被刀刺死。在第四节与第五节,格里耶拉开了观察的视角,把前三节封闭房间的一切叙写放入了少女正在阅读的书本中,前文的描写就与庙宇铭文记载的历史/神话的维度联系起来(又是一次拓扑);作者以此为切入点,继续叙写了因城市被入侵而在暴力中诞生的阴阳同体的“大卫”神话。第六节则是一次大的反转,前五节的内容变为“我”正在观看的一出戏剧,于是严肃瓦解了,整个第一空间终于在这多次的置换中构建了自身。
这种拓扑空间与异托邦空间有何关联?其实,拓扑空间结构有鲜明的异托邦特征,正如福柯所说:“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7]文学的文本空间是在语言的层面上基于叙述而面向自身的空间样态。我们在上一段重点讨论的拓扑空间在《幽灵城市》中就是一个既面向自身、也面向读者的开放的空间。这种空间包含了“打开和关闭的系统”[7],在或敞开或封闭的空间中,可疑叙述者“我”成为了一个具有揭示性的存在。从“前言”开始,“我”不断打开空间,不断延续文本,在睡梦的交迭里游荡在这个幽灵的废墟,“我”作为一个观测的形式又不构成这个故事的内容,仅仅是作为一个人称代词游离在各个空间。空间是绝对开放的,第三空间第一节的“我”甚至知晓作为作家的格里耶曾经写作过的小说,但无内容的“我”本身却也为叙述所排斥,“我”永远无法真正进入到任何一个空间成为实在的、有内容的主体。拓扑文本作为异托邦,向“我”开放着,却始终有一扇门对“我”关闭。“我”恰如一种刺眼的异质性存在,把拓扑空间的非整一的存在方式揭露出来,这就为异托邦打开了道路,其中有着鲜明的反乌托邦的意义。
二、文本空间的异质性
在上文的分析中,小说的文本空间是以拓扑学的方式被构建起来,在这种复数形式的多样空间里,其“异托邦”性质就表现为文本空间中“异质性”的揭露。文本中的种种异质性内容与空间自身已然互为表里,相互纠缠;一种令人惊诧的艺术特质以反乌托邦和开放性(在想象力的意义上)的文学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其一,拓扑空间作为“异托邦”,何以与乌托邦的空间对立呢?在福柯看来,乌托邦空间与异托邦有一种暧昧的关系,既是同类又是他者[8],但就两者的差异而言,前者意味着虚拟与假象中不实存的地点,当“乌托邦”落到实处,落到具体的人所在的空间,“差异性”或“颠覆性”的异质性内容慢慢被我们察觉,我们就面向了异托邦的空间。空间在格里耶的塑形当中就呈现出上述的异托邦形态;整个第四空间宛如作者设计的一个不断变换的“梦境”(大标题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点),第一节的标题以“等待”与“游荡”为中心词,具体又分为了十个小段,仿佛就是十个破碎的梦境片段一般把“封闭空间”的少女的种种臆想化为文学语言,意识似乎拉开了与身体的距离,但又回过头来重塑了身体,并生成了一个个新的空间,真实与虚幻在这里以纠缠不清的方式呈现。典型的例子就是第四空间频繁地提及了的“镜子”意象:“囚室的另一面有镜子,把她一个人的影子返照过来,她慢慢地观察自己的倩影。”[9]101
虚假的镜像自然是一种不可触及的乌托邦,但返照的旅途就不是一回事了,镜子若是能让人看到自身肉体的实在,那就是从异托邦的维度让人意识到了真实的空间所在。然而,格里耶的处理没有这么简单。在“双影”“还原为两个人”这两节,镜子向这里的“她”(被囚禁的少女)提示了表现“两极分布”(从封闭的小屋到殖民地)功能的虚幻空间[7],“她”在镜子里分裂出了“我”,“我”又在持续的文体的变化里被指称为不同的所指,分布进不同的文体形式。镜子开出的幻想空间之所以是反乌托邦的,恰恰是因为它在展开异质性的内容,而非沉沦在抽象的形式之中。换言之,当文中的“我”追问自己是否在梦里,实际是把自己持续地置于镜子异托邦的拷问之下,流动的主体性要展开的是对绝对特殊的(与合理性秩序相对)内容的承认,这空间就成了福柯意谓的船舶。
其二,这种船舶伴随的是想象力的扬帆起航,是试图开拓出人对自身生存方式的新的梦想。梦想的枯竭与桎梏的发生是同时的,而异托邦打开了新的可能。这就带出了异托邦在文本空间中的第三个特点,即多个具有差异的场景的并置。福柯在《词与物》中同样提及了关于文本异托邦的概念,他引用了博尔赫斯一部小说中“中国字典的条目”为例子,试图表明整体性系统中,差异性事物对某秩序的冲击所带来的惊讶感[10]3,这在小说中以两个方面去表现。第一个差异性的表现在于,作为构成文学文本的整体单位而言,是由前言、五个主体部分和结语的并置得以完成小说文本的,而这一“整体”处在根本性的危机中,它是不稳定的,这种危机表现在以空间命名的五个组成部分在其内容构成上的断裂。在第一空间到第二空间之间,叙事就有了一次断裂;第二空间(按标题提示)作为一个静态的上升运动,既取消了第一空间神话/历史的维度,也离开了现实的维度。大卫H与女性们之间是一种纯粹静态的看与被看的关系,眼睛、镜子与相机镜头都给出了关于“被看者”的表象,在大卫H为中心的叙述过程中,他自己也在看的过程中“被看”(成为被看者)。这里没有深度本质的揭露,只是单纯表象与表象的集合,是一个关于幽灵的叙述,由此才构成一个静态的居所,一个上升运动的空间。到了第三空间,突兀的“断裂”感再次出现,段落的开头,文本第一次表现出来自叙述者的强烈的主观情感,这导致了该部分的语言风格类似于通俗小说的谋杀故事(这也是一种差异)。这种关于有差异之文本的并置对读者阅读的感官造成的效果是直接的。所以,小说的各组成部分以“异质”的危险姿态挑战着看似稳定的整体。第二个差异性的表现在于,文本中各个部分的内在内容也存在着不稳定。在上一段所述的拓扑方法开出来的文本空间里,被填充在空间中的文本内容(第一空间的六个小节)就是典型的例子,不同的空间维度本身就变成了异托空间中所提示出来的异质性。第一空间里,读者经历了不断地置换,尤其是第六节的转折,让本来读者似乎已经习惯了的稳定空间突然崩溃,异质性内容就在其突然的消解之时被释放,由此,读者们才释放了福柯的“笑”。
其三,小说文本的异质性也体现于对时间的处理,它将文本空间与时间的片段化关联起来。在《幽灵城市》中,匀质的、线性体验的时间观念完全失去了效应,时间完全失去了对故事情节的规定性作用,因为在拓扑空间的变换中,文本的叙述由空间开辟。这种开辟也带来了所谓的“异托时”,福柯提出了“无限积累的时间异托邦”和“节日形式的异托邦”[7]。整个幽灵城市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无限时间的空间组合,随着第五空间里描述的最后一次谋杀(在文本的叙述顺序中)结束,结尾当中“我”重新置于一个空荡的幽灵城市;森林包裹了城市,海洋带着关于宗教或神话的、暴力或情色的种种隐喻性的物象,一切都环绕在那个幽灵般的“我”身边。文本似乎是要收尾了,但对于这个拓扑的空间而言,时间远没有结束,它还将不断拓扑下去,在这个过程里,时间既是永存,也是毫无意义。“我再一次向前走,走过一连串关闭着的门,沿着没有尽头的空荡荡的走廊走,走廊永远不变地干净和清洁。”[9]156
同时,在几个拓扑空间的内部,时间的操作以节日形式的异托邦来表现。福柯刻意提及了节日与度假村,它们将来人带入了一个搁置了历史的空间;在这一空间里,历史重新介入现时,人们处于异质性体验的漫长的狂欢。《幽灵城市》的第五空间的第四节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展露出一个设计出来的历史被拽入当前的文本叙述时所打开的异托空间。高墙内的建筑直接呼应的是第一空间的活动空间,大卫H来自第二空间,金币与浮雕则回应了第三空间的文本。这种回溯是双重的,文本的“人物”从内容上回溯城市的历史,文本空间从形式上也回应了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一个人物与读者双重的“狂欢”。
总之,格里耶正是以上述的拓扑学方法建立这一另类的文本空间,这一拓扑空间作为一个文本中的异托邦空间打开了种种异质性的内容。在《幽灵城市》里,读者穿过的每一个空间都向他们提示这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的存在之所——读者与那些幽灵相遇,与那些悖论的场景相遇,与过去与永恒相遇。我们也与“自己”相遇,尽管这个自己已然是以身体的方式带来一种惊愕与讶异。这个身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三、文本空间中的另类身体
在这个文本异托邦里,人是如何安放的?在上文的论述里,福柯意谓的另类空间绝不是一个无人的场所,是切实而具体的人所生活其中的社会构成了所谓的异托邦。其实梅洛—庞蒂对法国思想中空间/人的关系的阐述是极具参考性的,在庞蒂看来,“空间是异质的……是和我们身体的各种特点有着紧密联系的,是和我们这样一种被抛在世界中的存在者的处境有着紧密联系的”[11]25。作为法国哲学脉络的继承人,福柯的异托邦空间理论、身体理论在前辈的基础上进一步与力的场域联系起来,在福柯看来,身体总是在某种权力场域的规训当中,这种身体所在的力与力角逐的场所就是一个具有异托邦性质的空间。这在《幽灵城市》中可以进行具体的分析。
没有“人”是不以身体的方式存在于世的。在《幽灵城市》打开的异托空间里,既然人所在之处所已经不再是以广延的方式去规定,既然空间已经以如此异质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么此一在世的“人”就相应地有了新的特质。《幽灵城市》中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被囚于建筑内的女性,在这里没有了笛卡尔以来承载思维同一性的那个作为“我思”之主体的理性抽象的“人”,他们也不同于尼采所高呼的强大的肉身,这些“身体”在文本中表现出了一个近似幽灵又非幽灵的两面的性质。
这种身体一方面是近似幽灵的,表现出了开放性与平面性。这就是说,他们不再受到匀质规律的时空间的束缚,这种永恒性以类似物的方式表现,即他们剥离了一切作为主体的特殊性。他们不像传统医学、20世纪前的心理学学科话语中所构建出来的那种封闭的身体,相反,小说中的这些身体,全然保持自身的流动与开放。这体现于《幽灵城市》里,身体伴随着拓扑空间的折叠变化也在变化自身,它在各个空间似乎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变形,它绝无可能是封闭式的。但这种身体在一开始也失去了深度性,没有性格,没有主体意识,甚至没有主观情感。他们的一切意识活动或实践行动都是以被规定的方式给出。他们或是无意识的延续,或是历史/神话的一个载体,就像是文物展览品或是某个临床观察对象一样“被看”。文中唯一具有延续性的姓名是女神“瓦纳德”(以及其变形),但即使是这个“名”,也没什么具体的内涵,只是在拓扑空间里作为不断变动的“点”,从而成为文字空间的一种游戏形式。另一方面,这些身体看似超脱了时间和某个封闭的空间,但又不是不受物理之影响的纯粹的幽灵(纯粹的形而上),他们也在持续地成为被操作的肉身,无时无刻不被“监视”与“规训”着。少女们所在的建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训诫身体的场所,这里是疗养院,是监狱,也是处刑台。处刑(对身体进行施力)这样发生:可见的叙述场景与不可见的文本空白隐性地关联,这显然表现出了拓扑空间的特点,身体在其中一个空间的受力在另一个空间的身体上产生了反应,这表明他们所在的每一处空间都是处在力与力的关系中。这些“身体”不断地被各种形式的“力”所侵害:有第一空间中雕刻人的刀、少女躺着的处刑台;第二空间里凝视身体的眼睛、镜子与相机;第三空间中代表“谋杀”的匕首。这里没有澄明的灵魂,只有空洞的物的运动,身体褪去一切修饰,变成了赤裸的动物性的肉身,同时在被不断施加“力”的作用。第二空间与第五空间的对位像是一种隐喻:两个空间都描写了在封闭的房间里的女性,前者似乎是被平静地凝视,后者就是面对带着杀意的行凶者,然而两者实际表达了同一回事,不过是不同形式的对身体的暴力。身体是完全被动的,等待着“力”的降临。“力”就成了生成文本的要素,空间就整个的在“力”的作用下生产自身,神圣的仪式(宗教和神话式的)赋予身体,再用丑陋的暴力将之亵渎。格里耶在本文中钟爱着这种张力,第一空间的静与动之间,第二空间到第三空间由静态的看转到行动的暴力,第四空间戏拟文体之间,最后是第五空间的宗教的形式与暴力的隐喻(罪恶的发生)之间,身体所在的空间是力的场域。
上述关于身体的这两大方面特征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前者成为了后者的基础。但是前者得以可能的前提是拓扑方法的使用,即这种身体是与文本异托邦同时在场。这样,我们才能看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一个身体如何能够被一个整体性的秩序所操作是有条件的,福柯关注的权力制约下的身体何以可能呢?这就需要将身体塑造成动物性的样态,抛弃具有主体性生命意识的部分,成为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的生命(bare life)[12]24。《幽灵城市》的女性身体被先天宣布为有悖道德(被规定为妓女),那么对其进行训诫或处罚就是文本自身内含的一个对位性的暗示。而对一个身体的现代性的驯服首先要把其做成是无特殊性的,这就意味着可以将之纳入一个齐一的训练的模式。文本的这些身体除了视觉上分布方位的不同、样貌描写的不同以外,对其区分是及其困难的(甚至可以说不可能),因为这些身体毫无作为一个主体生命的特殊的内容,真正意义上是一个赤裸着的生命形式。文本空间与之有着极其暧昧的匹配,它们同时在场,即身体的存在随之开出了一个与之同在的空间。这个空间里密布了毛细血管式的权力场,身体的规训紧随其后——“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3]27。
这种福柯式的解读显然表现了批判性的立场,但从作者意图来看,似乎格里耶自己只是在文本中追求一种纯粹的、暴力的美学[14]144。在此先搁置关于这种说法的价值判断,我们想要继续追问的是,如此的一个纯粹先锋式的文本里,在此种关于空间与身体的表达当中,如果仍然将这个文本视作“文学语言”所发生的场所,艺术的维度是何以展开的呢?
四、空间、身体与文学中的僭越
可以看到,文中的诸多身体与种种“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它们以自身肉体性的、赤裸生命的样态展现了其异质性。在异托邦空间里,身体的肉体性让别人、也让身体自身看见了关于毁灭的预言。如此一来,一切温情脉脉的关于身体的乌托邦想象就被颠覆了,用于构建稳固匀质的不变之虚假乌托邦空间的想象破灭了。对身体以及自身存在方式的种种危险的试探,使我们对存在界线的体认才得以可能。毁灭的肉身俨然成了一种象征。肉身的毁灭与生命的消亡两个维度被包容在死亡这个概念中。在这里,“先锋”显示了何谓先锋。先锋艺术是要试图去抵达关于其言说的极限。身体与空间同在,身体的极限也是空间的极限,一个身体离去,一个生命离去,一个世界转身而去,此身体开出的空间也追随而去。《幽灵城市》这个文体就以身体与空间的极限完成了一次关于文学的僭越。我们将试图把这个过程展开来。
就神话与宗教而言,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与神之维度的拉开很大程度上在于有限与无限的差距。正是因为作为人的身体无以可能企及生命的无限,死亡这一概念才能在人这里爆发出巨大的张力,于是焦虑与恐惧便诞生了。害怕面对结局而又不得不面对结局,宗教的神圣之物被硬生生地变成为人神关系的中介。“神圣之物是死亡和情色的处所(locus)。”[15]如果说神圣意味着一种宗教式的神秘与超越,神的维度正是代表了那无限的存在;而祈求于神性,这一行为实则暗含了人类对个体消亡的恐惧。在消亡与神的永恒之间,“性”又被介入其中,它使生命得以延续的繁衍活动成为可能,并体现了人类身体中古老的原始自然性。文明的规训使它自西方中世纪以来就成为了言说的禁忌,成为言说身体的某种底线,“性”作为一种言说就转变为一种情色。神圣、死亡与情色在上述意义上得以彼此纠葛。那么,这种关系是如何在文本中发生的呢?
《幽灵城市》开篇前言对这一“城市”的描述就预先给我们带来了破败与被毁灭的场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种种象征性的意向:没有声响的街道、烧毁的墙垣、被遗忘的少女,等等。通过这些场景,事物的毁灭与消亡成为了一个值得审视的对象。这种消亡是何种消亡?似乎是一种暗示,物的自身规定性的极限已然到来,废墟之为废墟不是物的消失不见,而是一物在消亡与结束的极点。“我”入眠俨然成了与之相应的一种隐喻,一切景象都在我入睡“以前”,入眠之后是无可叙写的绝对的未知,一如无法经验的死亡。第一空间中,第一节的标题就以“繁衍”一词把“性”的环节给了出来,这一封闭的房间回应了一个毁灭的城市的古老历史。这个历史在第四与第五节中展现,庙宇女神的城市因被入侵而覆灭,幸存的女性在神庙中被异族施暴,在血水参杂的海中分娩阴阳同体的大卫,繁衍的历史在文中一开始就与暴力联系起来。第二空间我们看到“性”如何在“力”的作用下转化为情色,这在于“性”的压抑。身体,被毁灭的身体一直在被凝视,无论是文本中那个神秘的“我”,抑或是作为现实的读者,这些身体在格里耶那——几乎涉及视觉的每一细节的——冷静而细腻的描写里展现出色情的意味。格里耶大量使用关于身体的静态的细致描写,他没有迫切地在语言中展露欲望,只是像影像镜头一样给出了一种凝视。平静的凝视是一种安静的施暴,“性”被压抑了,情色发生了。从第三空间开始,“暴力”以更社会化的形式,即现代社会里对身体的谋杀来进行表现。警察机构是现代的社会规则里用以应对犯罪的身体的一种策略,是把社会带进某种稳定秩序的尝试。可是,它在格里耶的文本里变得徒劳,匕首终归在拓扑空间的作用力下,一个空间的施力造成另一个的结果,它刺穿身体,将一个一个的身体带入毁灭。
上述的过程里,身体以两重关系表现其极限。其一是身体与死亡的关系,我们看见了身体的肉身在场并且直观其毁灭,宣告了无限存在的身体与超越肉体而在的乌托邦身体不过是一种幻象,借以身体存在的人,毁灭的肉体是一种刺眼的异质,它迫使我们去打破乌托邦塑造的神话的秩序,人的生存界线在此浮现。其二是身体与情色的关系,在诸多预先有罪的身体中(文本作为妓女的女性)去暴露情色,实际上就是把那空间里密布的权力网络暴露出来——“性”就被放置在身体的表面,在权力的驱使下熠熠生辉[16]232。
《幽灵城市》提出了这般可能,即在身体之现存规则的底线处去越过那界线所在。正是某种极端的文本体验让我们得以在这种处境里回过头来,去确证它、审视它、考验它。这种对人之生存的最根本的试探是双重的考验,它既在内容上是一种越位,即试图达到文学语言能言说的身体的极限,也是拓扑空间带出的文本中的异托邦空间中关于形式的极限,这种极限意味着一个文本如何在几近分裂中维持一个使得读者可以进入的开放空间。从这两者就可以看到福柯僭越理论在文学语言中的呈现,它标示着语言艺术对自身可说之物的极点的试探,我们在这种极点处将一个异质文本放大到极限,在这种差异性的揭露里展开一种美学的力量。这里很容易让人想到福柯关于眼球的比喻:只有在眼球被剥离之时,它在这种毁灭中反过来看见了自身,“他被暴露出来,去面对他的有限,并在他的每个词下都被带回到他自己死亡的现实上”[17]73。意义在这里仿佛被做出了一种现象学的悬置——描写或是言说,是非肯定与非否定的,文本不是要给出一个价值判断的态度,甚至不是要给出一个合理的文学话语的秩序言说,它无意去否定界线,只是将之收归眼底,不断地在注视中剥离掉那种似乎完备的合理性。它只是在把这个异托邦的空间打开,让读者在差异中发笑,去看看关于人存在的那界线何在。于是,这时候才可以回到格里耶言及的美学,在我们看来,那恰似一种危险试探。《幽灵城市》的先锋性就在这儿,他让“文学”入眠,再将其唤醒。
总之,《幽灵城市》以独特的结构文本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拓扑结构的空间。这个空间以其异质性颠覆了虚幻的乌托邦空间,并表现出了异托邦空间的特质。此空间也使得这样一种身体的言说成为可能,它被格里耶暴露在权力的场域中,并以毁灭与情色将这种差异的身体逼到极限处。这种极限就转变为一种僭越的发生。《幽灵城市》的文本给出了这样一种关于文学的先锋性的回答,即让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去抵达言说自身,言说生活的极限之处,让那些界线就在这语言的极点处被掂量着。那是一种关于僭越的语言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