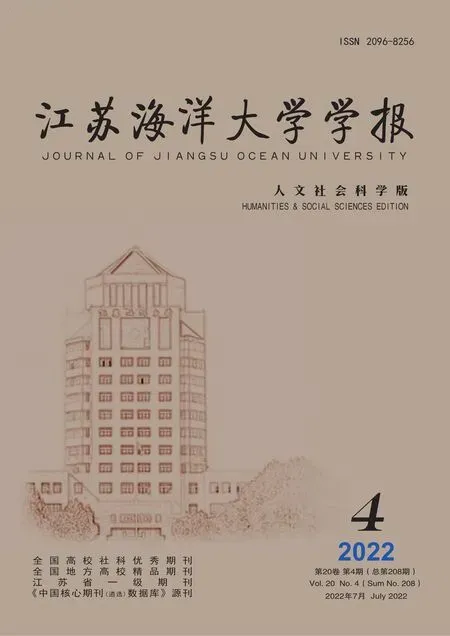《文心雕龙·时序》篇“质文”及相关问题释考
2022-03-16王广州
王广州
(安庆师范大学a.人文学院; b.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安徽 安庆 246011)
《文心雕龙》的写作与文本呈现出强烈的互文和复调特征,这既表现在《文心雕龙》自身一篇之内或诸篇之间的语用实践上,也表现在《文心雕龙》与之前历史上其他各类经史子集文本的关系上。此种所谓互文性或复调式写作,不仅仅是简单的用典与引用,而是如罗兰·巴特所言,是各种既有文本的话语在写作活动中的交织,其中响起的有时是刘勰所认同的前人的声音,有时则纯粹是刘勰本人的独特声音。
近现代以来,《文心雕龙》的注本繁多,研究成果显著,却很少有注本以分辨这些语汇的声音指向与实际意义为主要旨趣,冯春田《〈文心雕龙〉语词通释》、周振甫《文心雕龙辞典》与胡纬《文心雕龙字义通释》一类的研究著作可以视为对这一方面工作缺憾的补充。不过,几乎《文心雕龙》每一篇中都存在此类互文或复调现象,通观全书则数量更是庞大,所以冯、周、胡的此类工作虽说已经颇有规模,但毕竟尚未穷尽,或对有些关键语词未曾涉及,或有所涉而未曾尽善。“质文”一语即属于此类工作“所剩之义”中的一个。在这个自春秋时代以来就酬唱交织的语汇中,刘勰本人在《文心雕龙》中、尤其是在《时序》篇中关于“质文”声音的指谓,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从“社会用法”到“文学用法”:“文”“质”话语的“刘勰转向”
无论如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都可以视为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谓的“终极语汇”之一,而“文”与“质”的对举,尤其是二者的连文“文质”,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化中一个现象级的语汇,其相关研究也已颇有成果(1)自20世纪80年代起,王运熙就开始对“文质”问题进行探讨,撰写了数篇颇为细致的论文,参见其《中国古代文论管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4月版)。21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又有所增进,如夏静的论文《文质三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文质原论——礼乐背景下的诠释》(《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李春青的论文《文质模式”与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山西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吴小锋的专著《古典诗教中的文质说探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上述研究主要是对千余年“文质”话语历史的梳理,而对《文心雕龙》中相应语用现象及其内涵的的辨析则较为简略。。“文”当然也是《文心雕龙》统贯全书的核心关键词,“文”与“质”的对举或连文运用在其中也同样颇为丰富。仅就连文而言,既有已经“熟化”了的“文质”形式,也有不太为人所关注的“质文”形式。刘勰对它们的互文与复调运用也同时体现在上述一篇之内、诸篇之间与古今文本三个层次上。本文主要目的是考察《时序》篇中“质文”概念的声义指向,以及由其所规定的该篇的论题内涵。
“文”“质”对举与连文运用的文化原典,各注本与研究者一般都追溯到《论语》,其中《雍也》《颜渊》《卫灵公》等篇中直接或间接记载了孔子关于“文”“质”的言论或观点,又尤以《雍也》篇的“文质彬彬”说为核心。此后到刘勰之前,“文”“质”及其连文结构“文质”“质文”的意义也经历了各自相应的流变,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大体稳定的语义场域。下面在整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再作稍许补充,演绎式地从四种意义上描绘这个场域的基本构成,尽管这四种意义的得出乃是归纳的结果。
第一种是用以品评人物。这是“文”“质”话语的最初语用场域,又分作两种不同的维度。首先,是指人物生活或处世风格的文雅或质朴。如《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之论即是这种用法(2)关于此处的“文”“质”是指风格的质朴与奢饰还是指内在本性与外在文饰,目前尚有争议。钱穆、杨伯峻持前一立场,本文也暂取前一立场。。其次,主要是指人物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的素质,相当于内容与形式的范畴。如《论语·颜渊》中孔子认为“士”之“达”的标准之一是“质直而好义”,《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同样认为君子的标准之一是“义以为质”;东汉王充《论衡·书解》将人与物相比较,“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然后说“人有文,质乃成”,“人无文,则为仆人”;范晔《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西晋陈寿《魏书·傅嘏传》中说刘劭“该览学籍,文质周洽”,等等。
第二种指政教治理之道。此一用法受到天地、阴阳二元对立范畴与模式的影响,或者可以将其视为前二者的次生范畴[1]。如《礼记·表记》中孔子说:“虞夏之质,殷 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 周之质,不胜其文。”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王者之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西汉桓宽《盐铁论·错币》:“汤、文继衰,汉兴乘弊。一质一文,非苟易常也。”又《盐铁论·遵道》:“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所由不同,俱归于霸。而必随古不革,袭故不改,是文质不变,而椎车尚在也。”东汉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又班固《白虎通德论·礼乐》:“圣人之道,犹有文质。”又《白虎通德论·三正》:“王者,必一质一文何?以承天地,顺阴阳……帝王始起,先质后文者,顺天下之道、本末之义、先后之序也。”王充《论衡·实知》:“文质之复,三教之重,正朔相缘,损益相因,贤圣所共知也。”西晋陆机《五等诸侯论》:“成汤亲照夏后之鉴,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质相济,损益有物。”
第三种是指一般事物的本质及其表现形式,尤其是指礼乐风俗等形式风格的质朴或奢侈。前者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又《春秋繁露·楚庄王》:“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桓宽《盐铁论·毁学》:“学以辅德,礼以文质。”班固《白虎通德论·三正》:“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质……事莫不先有质性,乃后有文章也。”班固《汉书·礼乐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又《汉书·艺文志》:“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东汉《东观汉记》:“且礼有损益,质文无常。削地开兆,茅茨土阶,以致其肃敬。”后者如王充《论衡·齐世》:“文质之法,古今所共。一质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独今也……故周之王教以文……上世朴质,下世文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夫阴阳之气,相扶而行,发动用事,各有时节。若不当其时,则物随而伤。王者虽质文不同,而兹道无变。”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九·夏侯尚传》:“文质之更用,犹四时之迭兴也……时弥质则文之以礼,时泰侈则救之以质。(今)世俗弥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车舆服章,皆从质朴,禁除末俗华丽之事……朴素之教兴于本朝,则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
第四种是辩言、奏陈、史传等实用语言在风格上的质朴与文华。如《韩非子·难言》“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又《后汉书·班彪列传》:“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在刘勰之前,此类用法虽然已经涉及到语言层面,但尚未关涉文学性语言,而且数量也并不为多。
由上可见,刘勰之前的“文”“质”话语,就其讨论的具体主题或论域而言,可概括为五种形态:一是关乎天地阴阳的宇宙论,二是关乎政教王道的政治论,三是关乎风俗世情的伦理论,四是关乎素质行状的人物论,五是关于辩陈奏史的语言论。显然,所有这些都囿于天地、政治、人伦三位一体的宏大文化主题之内,虽然偶然涉及实用性活动与文体的语言维度,但尚未全面进入到真正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微观领域(3)王运熙认为《韩非子·难言》中“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云云是“以文质二字论文学”,只能说庶几近之,严格说或不能立,因为韩非子的主题只是作为实践活动的辩言,而非纯粹的文学语言。此外,王运熙还提到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有“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之论也是文学论,实际上前一句中“文”字显然是指文章作品,非“文质”之“文”,《文选》李善即注曰“言始将情意以纬于文”,参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218页;而后一句中的“文质”似乎指一般意义上的形式与内容,非专指文学之文质,即便是文学论也是偶发运用,未成惯例,参见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1987年,第45-46页。夏静也认为最早在文学领域讨论文质问题的是扬雄,尽管扬雄在《法言》中讨论了文章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但是扬雄并未明确使用文质话语,他说的是“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参考夏静《文质原论——礼乐背景下的阐释》,《文学评论》2004年2期。。这主要是因为此前的诸时代还不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有意为文”的观念尚未完全确立,文学作品的语言性也没有普遍地成为理论思考的对象,大部分作家对之“曾无先觉”,甚至“去之弥远”[2]2220。由于这几种主题都可以纳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范畴之下,我们暂且把“文”“质”话语的这四种用法称之为“社会用法”。
到了南朝齐梁时代,文坛盛行的绮丽浮艳的形式主义潮流固然反映了某种空虚贫乏的病态浪漫,但同时也预示了“有意为文”的纯粹文学意识的成熟。所以当“文”“质”话语到了刘勰手中的时候,便被他引入到文学这个全新的论域中,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上进行了数量可观的语用实践,或许也直接引领了稍后的钟嵘、萧统、萧纲、萧绎等人的同类批评话语(4)刘勰与此数人对于“文”“质”话语的运用情况,王运熙已有举证,参见其《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1987年,第46-48页。 但王运熙对刘勰的语用类型并未进行归纳分类,所以本文接下来将结合《文心雕龙》文本语料略作归纳说明。,使其成为此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中的经典范畴。我们把这种在数量或频率上足以构成一种现象的新用法称之为“文”“质”话语的“文学用法”。概言之,《文心雕龙》中此类用法的“文”“质”话语主要讨论了文学的两个几乎是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向度,以现代的理论话语来说,一是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二是文学语言或风格的取向。
其一,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如《原道》篇“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曰新”,《铨赋》篇“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颂赞》篇“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情采》篇“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灭质”,《知音》篇“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才略》篇“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等等。此类的“质”“文”即分别是指文学内容与形式。很显然,刘勰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认为文学还是以内容为本的,“文虽新而有质”,不管“文”怎么新,还是要有“质”的底子在,这也可以说是“原道”“征圣”“宗经”观的实际贯彻。因此,刘勰接下来的言说逻辑就很自然了,他主张作品的形式只是对内容的承载与呈现,不能超越内容之上而成为目的本身,为了形式而形式,以致于“弄文而失质”,相反,必须做到“文不灭质”;同时,为了真正能承载与呈现内容,文学形式还必须与内容表里圆融,“文质相称”或“文质辨洽”。时间上先“质”而后“文”,逻辑上重“质”而轻“文”,因此可以说刘勰是一个偏颇的二元论者,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天然的辩证论者,因为他主张所有真正的作品都应该是一个“质文交加”的有机存在物。
其二,讨论文学语言或风格的取向。如《奏启》篇“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议对》篇“至如吾丘之驳挟弓,安国之辩匈奴,贾捐之之陈于珠崖,刘歆之辨于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书记》篇“或全任质素,或杂用文绮,随事立体,贵乎精要”,《通变》篇“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养气》篇“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等等。此类的“文”“质”即分别是指文学语言或风格的文华与质朴。在此问题上,从历时维度看,刘勰持有一种宏阔的文学史观,总体上他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质”,其取向如果说不是由其所属的特殊时代所决定,那至少也是与这个时代相映照的。而在共时维度上,当涉及不同的文体或文学内容时,刘勰也持有一种务实而灵活的“通变”立场,创作者在语言或风格上“斟酌乎质文之间”时,无须拘泥于某种时代风气或成法规则,“随事立体”即可,只要“得事要矣”,那么就可以“质文不同”。就此而论,刘勰仿佛又突破了上述那种机械的映照史观,为某个时代形成“质文”错采的文学世界预设了巨大的空间,此一时代也就可以超越其作为历史纵切面上线性节点的狭隘身份,从而成为一个社会横切面上具有丰富文学性格和面孔的普遍性文学时代。
二、《时序》篇“质文”义辨:文学之“质文”,抑或时代之“质文”
关于《文心雕龙》中“文”“质”话语的“文学用法”,上文已列举了不少例子,但也许读者未必留心到,我们故意回避了《时序》篇中的例子。这主要是因为《时序》篇中的“文”“质”话语到底是“文学用法”还是“社会用法”尚存疑问,有待考定,而这正是本文接下来的任务。不过,读者也无须担心自己错过了太多,《时序》篇中“文”“质”的典型用例只有两处,都是以“质文”的连文形式出现的:一为篇首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一为文末的“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
宽泛意义上,《时序》篇的论题实为“时代与文学”。具体而言,刘勰的观点颇近于一千多年后马克思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他用了大量的古代文学史材料作为论据,论证了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这一命题,该命题被表述在“质文代变”“质文沿时”两处句子中,但这两个“质文”指的是文学的“质文”还是时代的“质文”,对于理解这两个关键句以及整个《时序》篇的主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分歧也就由此而出:要么是“文学用法”,是说“文学的质文情况是随时代变化的”;要么是“社会用法”,是说“时代的质文情况是随时代变化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持前一立场者称为“文学派”,而将持后一立场者称为“时代派”。
关于这两处“质文”,刘永济、范文澜、詹锳等现代先行研究者都未加解释或说明,周振甫的译注本中虽然翻译了两处“质文”的意思,但是却回避了“何者之质文”的问题[3]393,406。而其余的当代译注者,自然也就主要分为“文学派”与“时代派”。
“文学派”译注者又可以分作两类。第一类对《时序》篇中两个“质文”的共在性有明确的认识,而且认为它们的内涵具有同一性,都是指文学(或文章和文风)之“质文”,而非时代之“质文”。例如吴林伯即认为两处“质文”是“相应”的,而且都是指文学作品的“质文”,但他却将“质文”解释为内容与形式意义上的“情思和辞采”[4]839,884,而非“质朴和文华”,这与其他译注者迥异,不过吴林伯将同一文本内的同一术语前后进行照应对齐来做解释的做法,已经成为他的方法论,在他对《文心雕龙》中“文情”等概念的解释上也有体现[5];同样,陆侃如和牟世今二人的合译本也将两处“质文”都解释为“文风的质朴和华丽”[6]530,546;祖保泉和张灯各自都将两处“质文”解释为文章或文学作品的质文[7]875,896,[8]873,885;戚良德也将两处“质文”都解释为“文章的质朴或华丽”[9]509,513。第二类译注者似乎没有意识到两处“质文”的共在性,只解释了其中一处而忽略了另一处。例如黄侃弟子李曰刚在《文心雕龙斟诠》中只将“质文沿时”之“质文”解释为“诗文之朴质或华丽”[10]1724;王运熙在对《时序》篇进行题解时只提及“质文代变”之“质文”是指各代文风的质朴或文华[11]438;穆克宏仅将“质文代变”之“质文”与文学和文风而非时代关联起来[12]89,284;张光年也只认为“质文代变”的“质文”说的是历代的文风[13]81;向长清将“质文代变”解释为“文章的质与文”,但对“质文沿时”的解释则比较含糊[14]378,392;张长青也仅将“质文代变”的“质文”指向了历代的文风[15]533。此外,有的文学研究者如童庆炳也意识到此一问题上“文学派”与“时代派”的分歧,但他明确地选择了“文学派”的立场[16]334,但如同几乎所有的译注者一样,这种选择是未经言明的选择。
“时代派”同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也是意识到两处“质文”的共在性,也承认其内涵的同一性,从而作出同步解释的,此类译注者目前所见只有赵仲邑一人,他将两处“质文”都解释为“时代风貌的质朴和文华”[17]367,373;另一类似乎未能前后对应对两处“质文”作整体性的处理,例如杨明只将“质文代变”译为“时代在变化,有的时代表现出‘文’的特征,有的时代则表现出‘质’的特征,是互相交替的”[18]183,对“赞”中的“质文沿时”之“质文”则未置可否。
在这两派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的译注者,他们对两处“质文”的共在性和同一性也许是全无意识,也许是意识到了其共在性却不承认其同一性,把它们视为两物,从而对其一作“时代派”之解释,对另一作“文学派”之解释。例如郭晋稀将“质文代变”之“质文”归结为“时代风尚的”,而将“质文沿时”之“质文”归结为“诗文的”[19]186,207;徐正英、罗家湘二人合译本也将前者视为是“时代的风气”[20]408,将后者视为是“诗文”的风气[20]425。
由上可见,“文学派”的译注者显然是主流,而真正有意识的“时代派”只有赵仲邑一人。“文学派”的占比之所以如此畸重,原因或许有三:首先,刘勰在《文心雕龙》全书中的“文”“质”话语大半都属于“文学用法”,见上文所举诸多例子;其次,刘勰在论证过程中确实描述了一些时代如齐楚两国与西汉等在文学风格方面的“文”(文华)的特征,而且在篇末的“赞”的总结中也言及“蔚映十代,辞采九变”;再次,对《文心雕龙》的译释主要始于20世纪中叶以后,此前尚以校注为主;而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语境中,本来是后起的、而且主要就是起于刘勰的“文”“质”话语的“文学用法”成为主流,而其原初的“社会用法”几乎被前者所淡化与遮蔽,所以现代的普通读者乃至译注者会很自然地首先从“文学用法”的角度进行解释。
但我们不能单纯地根据“文学派”与“时代派”双方人数的多寡来判断其主张的是非。退一步说,从现代解释学或解构诗学的立场看,所有阐释本无是非,都是一种特定视域下的重构。因此,我们暂且把这两派的主张都悬置为一种中性的重构,然后结合《时序》篇文本,尝试考察它们各自可能的理由,来寻找更切合篇章语境的理解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来考察《时序》篇名中的倾向。除了“文之枢纽”“论文叙笔”部分以及《序志》篇之外,《文心雕龙》其余各篇的篇名中实际上都省略了另一个关键词“文学”,如《程器》实际是“程器与文学”,而不是单纯的人物德行论;《物色》实际是“物色与文学”,而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的博物学;《才略》实际是“才略与文学”,也不是单纯的心理学或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禀赋论。其省略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全书的论域就是文学,“文学”已总括在书名“文心雕龙”中了,各篇无非是谈文学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已。如此之后的情形就如同“文学”是舞台的一幕布景,各篇的主题“程器”“物色”“才略”等是不同的角色,一个个不断地登场上来;观众注意力的中心不是那同一幕舞台布景,而是这些个活动在舞台中的各个角色。同样,《时序》篇实际是“时序与文学”,刘勰的基本观点是:存在一个如此这般的时代,则就会产生一个如此这般的文学,这个如此这般的文学作为“逻辑后承”已然蕴涵在这个如此这般的时代中,欲了解一文学只须了解其所属时代即可。要处理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刘勰的首要任务就是先把作为“前件”的时代刻画出来,因此《时序》篇的优级话题是时代而非文学,篇名本身已透露此点。
其次,从《时序》篇结构来考察。宏观上,篇中尽管只有两处“质文”,但其一在开篇,揭开话题,另一在结尾,重申立意;显然,两者前后呼应,虽二实一,是贯穿全篇论证的实质性主命题,又因为《时序》篇的优级话题就是“时序”,所以“质文”应该是时代的“质文”。微观上,从尧舜到南朝齐,刘勰的论证结构都是先论时代再论文学,其句法结构又以骈文为主。所以,开篇的第一“质文”句,即“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中,前两小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则以时,一则以代,是合说时代的变化如此(5)《文心雕龙·议对》篇也有“究列代之变”之说。;后两小句“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是继说文学的反应可求。结尾的第二“质文”句,即“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中,前两小句“枢中所动,环流无倦”是先说作为原因的时代情况(“枢中所动”),后说作为结果的文学情况(“环流无倦”)的结构;后两小句“质文沿时,崇替在选”也是相同因果结构的重复,“质文沿时”在先,说的就是时代的情况,“崇替在选”在后,说的是文学的情况。
因此,《时序》篇两处“质文”皆宜视为时代的“质文”,属于“社会用法”;那么刘勰在《文心雕龙》其它篇目中是否也有“文”“质”话语的同类用法呢?同样不乏其例。例如《书记》篇“上古纯质,结绳执契”,《铨赋》篇“秦世不文,颇有杂赋”, 《才略》篇“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等句中的“文”“质”都是指社会时代的或“文”或“质”,可以旁证这两处“质文”的“社会用法”。
再次,现在回到《时序》篇中来考察刘勰是否是从“质文”角度讨论各代情况的,以作验证。战国时代,六经扫地,兵、法诸家兴起(6)吴林伯认为此处“诸子飙骇”是专指兵家和法家等,大体符合实际,见其《〈文心雕龙〉义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44页。,秦韩燕赵魏等国都崇尚武力、权术与苛法,斯文不再,《才略》篇称之为“战代任武”;只有齐楚两国重视文化建设,任用孟子、荀子等大儒来引领时代思想潮流,于是,齐国稷下和楚国兰陵的文化学术风清气正,刘勰谓之以“颇有文学”。章太炎曾将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大致分为“尚武之世”与“尚文之世”:秦汉尚武,东汉与六朝尚文;唐代尚武,宋代尚文,等等[21]211。此处刘勰所谓“任武”与“有文”,就是“尚武”与“尚文”之别,而“武”实乃是“不文”或“质”之极致状态,“武”“文”之别就是“质”“文”之别,所以刘勰是从“质文”角度来论证战国时代的。到了西汉,由“高祖尚武,戏儒简学”到文景二帝“经术颇兴”,由汉武帝“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到昭宣二帝“驰骋石渠,暇豫文会”,再到汉元帝“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谈”,百年风气由“尚武”渐至“尚文”,也就是由“质”到“文”的过程。而东汉,先因光武帝“深怀图谶,颇略文华”而“其时质”,又因明章二帝“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而“其时文”;汉末“文学蓬转”,失“文”而近“质”。
曹魏父子三杰“雅爱诗章”,“妙善辞赋”,“下笔琳琅”,不但自身爱好文学,擅长创作,而且“体貌英逸”,尊重英才,所以有了“俊才云蒸”的盛世文雅;其后也都延续了这种重“文”的传统,“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也形成了英才俊杰“迭相照耀”“并驰文路”的局面。刘勰在《才略》篇中曾称汉魏之际的建安时代是“崇文之盛世”,所以有魏一代当然是他眼中的“文世”。西晋的几代帝王或“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或“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都不重视教育和学术,尽管承魏余韵而“人才实盛”,但终究“人未尽才”,因此刘勰认为西晋是“不文”的。而东晋前期帝王“披文建学”,“雅好文会”,“孳孳讲艺”,创造了风雅华彩的文化局面,其后虽有消长,但自西晋以来的玄学风气一直流行,所以大体仍是“文世”面貌。南朝“宋武爱文”,“文帝彬雅”,“孝武多才”,所以人才“霞蔚而飙起”,“不可胜数”。南朝齐是刘勰本人所在的时代,出于某种心理,他难免有溢美之词,谓其帝王们“文明自天”,“文思光被”,创造了超越周汉的典章学术与比肩尧舜时代的礼乐制度,“鸿凤懿采”,“其鼎盛乎”,将宋齐两代都推为礼乐文华之世。
可见,刘勰历数各代之变基本上是以其“质文”情况为依据的,他对西汉到南朝宋的时代风貌的描述与章太炎“尚文之世”与“尚武之世”的粗线条判断大致吻合。不过,刘勰还是以每个朝代的帝王赓续为线索,从各朝代内部具体而微地勾勒了“质文”情况的动态消长。
综上,“时代”作为《时序》篇的优级主题,刘勰主要是谈时代的“质文”情况。那么作为“时代与文学”中另一个后承主题的“文学”,刘勰是要谈它的什么情况呢?刘永济抓住“赞”中的“辞采九变”一语,将其定位为“文章风气”方面的情况[22]134,童庆炳则认为刘永济此说尚未挠到痒处,继而将“文章风气”具化为“质文”的情况,主张并分析了刘勰的“质文代变”“质文沿时”就是“文学”之质文的情况[16]334-335。
然而,结合《时序》篇文本分析,情形也许并非如此。例如,刘勰举陶唐时代“‘何力’之谈”与“‘不识’之歌”的例子只涉及文学的内容,并不能说明当时歌谣的“文风”之“质”,反而恰恰说明了作为其原因的“世风”之“质”,即其所谓“德盛化钧”。刘永济所谓的虞舜时代“薰风”“烂云”诗的“雍容之美”,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心乐而声泰”之“泰”字,所显示的也不是文学风格的质朴或文华方面的情况,而是文学风格的平和或激烈方面的情况,恰恰也同时说明了“政阜民暇”的“世风”之“质”。至于由大禹商汤时代“九序”“猗欤”等作品的“咏功”与“作颂”,到周代《诗经》中作品的“勤而不怨”“乐而不淫”,再到“怒”“哀”等,也都不是文学风格的“质文”之变,而是文学内容或功能方面的变化,最终表现的是各种君王治下的“德盛”“化淳”“厉”“微”的时代风气之变。
西汉自武帝之后,人才鼎盛,刘勰罗列十四五位贤才,其中主父偃、公孙弘、倪宽、朱买臣、司马迁等人或贤德或奏对或史传,皆非关纯粹文学;所言的真正文学之士只有枚乘、司马相如、扬雄,都是赋体大家,所以刘勰说“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实际上是以偏概全,忽略了汉代散文,李安民的批点“除赋外,不得谓祖述屈子”[23]146可谓准确。东汉明章二帝后儒术重兴,虽然“才不时乏”,但多是班固、蔡邕类的“磊落鸿儒”,使得文学的发展渐趋鄙陋,刘勰之意非在文风的“质文”问题,而恰在刘永济本人也意识到的盛衰问题,此点下文将再论及。
对于曹魏文学,刘勰论证的重点一是帝王对文章与人才的重视,二是文学内容方面的“斐然之思”与“翩翩之乐”,三是“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的文士风度,四是志深慷慨、梗概多气的主体精神,五是玄学余风对文学体例的影响,前四点都与文风的质文无关,即便是第五点,也只能说有稍许的关联。
刘勰对西晋文学的描述确实涉及到其风格的“质文”,但他的真正目的却在于强调“人才之盛”。对东晋文坛的描述多集中在“文思”“微言精理”与玄学“澹思”之上,至于“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云云,更是非关文风之“质文”问题。刘勰对南朝宋文学的描述确实偶尔论及“龙章”“风采”,但重点也在强调人才之盛。对南朝齐,如上文所言,刘勰主要论述的是其文章典故与礼乐制度。以上或未言及文学“质文”问题,或旁及而不以其为目的。
三、文学:“崇替于时序”
至此,我们肯定了刘勰的“质文”话语谈的是时代之“质文”,而非文学之“质文”。那么,作为《时序》篇次级话题的“文学”,刘勰到底是用哪种话语来谈的呢?其实就是上文已提及的“崇替”话语,也即盛衰或兴废问题。
首先,《序志》篇在概论相关篇目要旨时说“崇替于时序”,即已直接点明《时序》篇的主题,即文学盛衰与时代的关系。由此可知刘勰在篇中讨论“文学”的情况时,其立意重心是文学的盛衰之变,而非文学的“质文”之变。
其次,从全篇论证层次看,通过开篇对远古到周代文学世界的描述,刘勰首先点出时代与文学的一般因果关系:“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继而考察了由汉到晋的文学世界,将时代与文学之间的一般因果关系具化并推进为全篇的核心命题:“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与世推移”之“世”具化为某种特定的“世情”,“歌谣文理”之“文理”推进为“兴废”;更关键的是,此句中的“文变”与“兴废”是互文的,可以合而观之,就是“文学的兴废之变”,即盛衰之变。最后在“赞”中总结为“质文沿时,崇替在选”,再次将“世情”之“情”字具化为“‘质文’之‘情’”,也回应了开篇首句中的“质文代变”,而且这种回应是一个经过论证而充实了的“质文”对一个空泛的“质文”的回应,如同一个被兑现了的诺言对最初被许下的诺言的回应一样;同时,将“兴废”重申为“崇替”,再度明确了关于“文学盛衰之变”的次级主题。
再次,从刘勰对各个朝代文学的描述看,除却为了点出时代与文学一般因果关系而进行的对上古到周代文学的分析之外,刘勰对此后各代文学的分析重点,不是其“质文”之变,而基本是一幅幅的文学人物群像图。清谨轩本《文心雕龙》评曰:“古今人才,不能出其范围。”[23]149如齐楚两国的孟子、荀子、邹衍、驺奭、屈原、宋玉,陈仁锡批点曰“一时名士风流”,李安民批点曰“滔滔衮衮”[23]145。西汉所论人物更是多达十四五位,文学由汉初的消沉达到了“莫与比盛”的繁荣;东汉则经历了由“才不时乏”而“辉光相照”再到浅陋俳优之徒“余风遗文,盖蔑如也”的衰退过程。汉魏之时重新出现了“俊才云蒸”“迭相照耀”,“高贵英雅”“并驰文路”的文学盛世。承魏余韵,“晋虽不文”但“人才实盛”,玄席之上,文囿之间,流光溢彩,也是一时灿烂。所以,黄叔琳说“文运升降,总萃此篇”[24]262,刘永济亦附和此论[22]134;刘咸炘也认为此篇“但论文运之盛衰,世主之轻重,才人之多寡”[24]262。总之,在各代不同的“质文”世界中,刘勰确实勾勒了一部以人才为其风向标的文学盛衰兴废史。
四、“质文”译释的时代之见
《时序》篇的实际论题是“时代与文学”,而刘勰论证链上的两个关键词是“质文”与“崇替”。“崇替”显然是说“文学之崇替”,如果同时也把“质文”解释为“文学之质文”,那么似乎就产生了两个逻辑失序:一者,本来是“时代之质文”的“质文”就被剥夺了,“时代”就是失去了自己逻辑谓词,空无着落;二者,如果将“质文”与“崇替”都视为是文学的逻辑谓词,那么二者之间似乎应该具有一种因果关系,比如说文学“质”则“崇”,文学“文”则“替”,而实际上这种因果关系并不必然成立,“质”的文学可“崇”可“替”,“文”的文学亦可“崇”可“替”,文学史上不乏此方面的例子。所以,有的译注者如吴林伯既谈文学的“质文”,也谈文学的“崇替”,却无法将二者圆洽关联。因此,“质文”说的是“时代之质文”,“崇替”说的是“文学之崇替”,“时代与文学”的主题实际上就是“时代之质文与文学之崇替”。刘勰在一般意义上论证了时代的“质文”情况与文学兴废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他也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例如,他曾论及“晋虽不文”而“人才实盛”的错位现象。
与此相关,在《时序》篇的译注史有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明清到近现代的先行者们如黄叔琳、刘咸炘等,只言“文运之升降”“文学之盛衰”而不言“文学之质文”;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大多译注者们却与之相反,大多将“质文”视为“文学之质文”。一代有一代之视域与阐释,这在解释学上是常态,并不值得奇怪,只是需要我们谨慎对待各种“时代之见”。“质文”在明清到近现代的视域里也许是不言自明的,尚未成为一个问题。“文学之质文”,差不多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时代之共见”;而“时代之质文”,也许只是我们的“时代之偏见”。但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时代之见的错杂存在时,也就更接近于我们的理解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