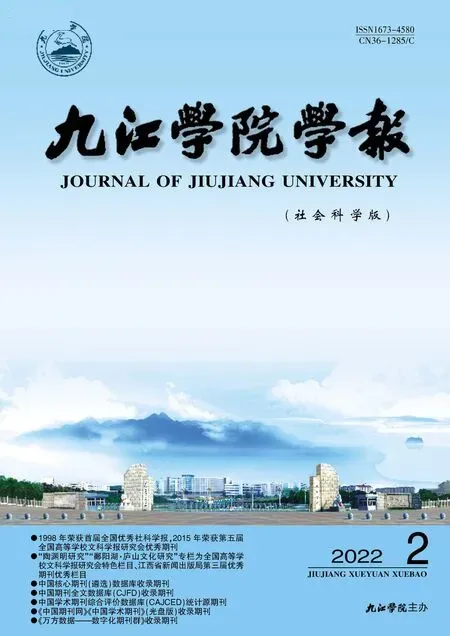论陶渊明的隐士哲学
2022-03-16邓青
邓 青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如果说哲学关乎良善的生活,即什么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那么隐士的取舍行藏无疑提供了一个别致的范本。让天下之巢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庄子以及辞官归去的陶渊明,皆堪为隐逸之流的标格。所谓隐者,乃损之又损,剥落尘俗,逃名幽栖,独往独来,乃或时处困穷;然其落寞自甘,一往孤诣,都无悔改,乐以终身。寻其志意所在,实不同于悠悠凡俗。梁萧统于《陶渊明集序》起首便发问曰:“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其故何也?”[1]此即索问隐沦之志:当人从得失荣辱、名利声色等尘想之中解离出来,而或处于绝对幽独之中时,尚复何求?又作何观想?
渊明卓为隐中大贤,如钟嵘《诗品》便赞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2]。且陶公平生所慕尚与其诗文所咏歌者,亦多安贫乐道之古贤,如孔子、黔娄等。故读陶之诗文,即可想见隐者的志趣与生命,并可藉之以思一己之出处潜跃,不啻为一入道的契机。观其诗文,想其人德,虽不能尔,至心慕之。此文即以渊明诗文为主,一窥隐者之生命真趣。
一、君子固穷
陶之诗文中充盈着对于人生有限性的揭示与感慨,如《形影神》即云:“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3]生唯一遭,死不能复,乃不如天地草木周尽而复始。于其百年之内,或者驰骛功名,但如《饮酒》其三云:“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一生倏忽易逝,专意于此,虚名又有何益?况且荣华并不常存,如《饮酒》其一云:“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或云人生当积善,然则《饮酒》其二云:“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善行未必有善报,恶行未必有恶果,此亦人间常态。渊明在其《感士不遇赋》中对此颇多慨叹,乃至对天道的清明公正亦产生怀疑:“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有德才者命途多舛,遂使人疑心“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教诲不过虚言而已。
总之,生年短促,且盛衰无定、善恶不应,甚或长处潦倒,然则究竟如何安顿人生?或曰,生此变动不居的世间,是否仍有坚实、确定、永恒之物即所谓常道者以供人栖止?渊明《饮酒》其四云:“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此无所定止的失群独飞之鸟,照写出徘徊歧路不知所向、却又有所省觉与追问的游魂。所幸的是,它终究觅得了永恒的托依之所——傲霜贞秀之孤松,乃前诗“固穷”之节的隐喻。“固穷”者,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4],进德修业,尽其在我,至于寿夭祸福等则有所不恤而委之于命,故求仁而得仁,可以无恨而不怨。《咏贫士》曰:“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道者,即为人生之栖止,乃决定人之所以具有人格而异于禽兽者。
《荣木》诗曰:“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渊明以孔子为先师,其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此遗训为孔门精义:在飘忽短暂的人生中,人所能把握者,非外在不定之祸福,而是自身道德人格的修炼和砥砺,故求其在我而已。“贞脆由人”之“贞”,即谓依于道、敦于善,贞定不移,而不为外在境物所动,如《五柳先生传》所云“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依止于此常道,则有持守之常,以应对万事之变。因之人所应关切者,乃使自身足以配得幸福,而不专止是幸福而已。渊明所撰《感士不遇赋》,虽然满腔愤怨不平之气,而其归旨则在乎“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一语,其卒章亦曰:“苍旻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昧,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知或不知,遇或不遇,都不介怀:一者,以仁义行身,光明磊落,可以无愧于天人;二者,疏食饮水之中,确乎可有自得之乐。渊明能会于此,故其孤昂肃洁之操,宛若云间之龙鹤。
二、饮酒真意
渊明“性嗜酒”(《五柳先生传》),常顾影独尽,期在必醉;从萧统《陶渊明传》载其种秫公田、留钱酒家诸事,亦可想见其酒兴。然其饮酒,自有意趣寄托其间,非如俗夫买醉浇愁而已。萧统《陶渊明集序》云:“有疑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5]斯言得之。然则其意如何?
渊明有《形影神》诗,其中《形赠影》言人之生必有死,倏忽而已;形之应对则以酒,借醉酒而忘死,故诗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影答形》则曰:“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影之应对则为行善,欲将恩惠遗留人间。神则对此两者皆有所疑,《神释》云:“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据神观之,“甚念”“多虑”无非人对一己生命的执著。影之立善遗爱,从而为人称道追怀,是形体生命的延伸和存留,然而终究不可期必。且如上文所论,人唯行善尽己而已,又何须顾及身后称誉?形之醉酒,则不过假借外力暂时遣忘生死忧惧,且酒虽能极乐消忧,亦可促龄损生。《形影神》诗序云:“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辩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形影之苦,皆源于内外之矛盾:内则营营惜生,外则究竟无可奈何于“物久人脆”(《祭从弟敬远文》)之事实。神则以自然委运开释之,此便是醉酒真意所在。
自然者,自然而然,任随变化。神之所以能自然者,在于超脱形影之念虑,而至于忘机无我之境地:消解主体自我之思虑或意欲,无目的、无意图,不期求、不粘滞,从而任随运化之自然,来者不喜,失之不惧,而永葆心神的清虚寥廓、和乐平易。在此无我之境中,主体(以形影为喻)消泯,其所固执之得失、是非等皆不结体于胸臆,故一片清通浩荡。萧统赞渊明之语曰:“论怀抱则旷而且真。”旷者,清远虚旷;真者,率性自适。心灵清虚,并无一物障塞,既不意图建构自我,亦不执著或趋向于某物,而后能率其真性,自得其乐。
此忘机无我的太虚心境,往往可于饮酒中得之。渊明曾记其外祖父孟嘉“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桓)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酒中之趣,正在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既卸下自我矜持,又暂时解除人事牵缠,故可渐近自然,率性自在。渊明又有《饮酒》诗云:“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酒之迷醉,能使人不知物,复不知有我,于是所有思虑与机心皆被洗白无遗;任其狼藉杂乱无行次,一切礼仪矜束便都被打破了。《连雨独饮》复云:“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饮酒之中,无有机谋智巧,淡远尘想百情,任其真率,可曰得仙入天;入天而不辨天人物我,一切浑然都忘,是为忘天,即此“悠悠迷所留”之境。于是便如同云中之鹤,其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心神入于透脱空阔、真实无妄之境,此乃为饮酒成仙之真意。故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饮时之欢与醉后之乐。渊明能会此真意,《饮酒》其五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心远”一语正见其志趣与境界所在,陶公之生活与其诗文,皆从此二字流衍而出。其心旷远清虚,融然远寄,至如造化之太虚,虽处人境之中,自不以功名利禄为意,故其所居之地亦因心境之高远而偏远。他不意图去建构什么,不去知解、思议与谋划,而惟纵任自己与周遭之物的当下契会。本来自在采菊,初不有意望山,举首而适见南山;甚至不是人去看见,而是南山自在呈现,而“我”与之适然感会而已。主客对立在“现”与“见”之中消失了,于是“我”便是采握之菊,现于眼前的云山与飞鸟。其心悠然,所见之南山亦悠然,各个自得。“我”便于此间存在,所遇之物无不构成生命的真实内容。“我”在此间消融了,亦无须再与谁辨。冥忘物我,和气周流,真可谓极致的幽独;然而沉浸其间,悠然自得,亦是极致的充盈。
此中真意,乃在心远而浑忘物我,故醉酒实是醉心。每于醉后见天真,没有“简发而栉,数米而炊”的斤斤计较,不严肃,不紧张,无心忘机,任真自得,始能脱樊笼而返自然。此真意为陶公其人其心之止泊处,亦即“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其一)之所隐喻者。饮酒可得此真意,却不必然由饮酒而得。苟能具此无心任真之自然意趣,则饮酒可忘,玄酒可作酒豪饮,无弦之琴亦可鼓奏入神,自不必拘泥形迹。
三、即事之乐
渊明《饮酒》诗云:“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己酉岁九月九日》亦曰:“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枯槁者,不止物质生活之贫苦,亦是心境之老洫、单调与无聊:或专注于名利而不省察生命的意义,徒然养其形体而已,即所谓“客养”者;又或焦心于未至,执念于已往。而生命或生活,其意正与枯槁相反:肆志称心,以得今朝及时之乐,从而见出灵动活泼之生机,同时又虚心迎向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乃可称为生命或生活。心无期必与执著,而常虚闲无机;以之即事应物,则每多目下之欣乐与美感。
渊明曾自述云:“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疏。”(《与子俨等疏》)渊明少而穷苦,辞官后躬耕自养而常不足;于此饥寒困顿之中,其持之以为人生之依保者,在于即事而每有欣乐,如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云:“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诗中所谓“未量岁功”,乃“机巧好疏”之一端,即不计量产出或成果,而排遣了目的性的期求。唯其如此,方能“即事多所欣”,在当下行事之陶醉中得其所乐。于是平畴广野,时雨和风,亲戚之情话,奇文与疑义,皆具足美感而令人心生悦喜。《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唯在“委心任去留”,亦即不愿富贵、不期帝乡之后,方有此间种种乐事。
《杂诗》其一云:“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此中之欢乐,并非单纯物质上的享乐,而为一种审美生活之意趣:恰须荡涤意欲以至于空虚无我,方能即事有乐;否则,汲汲于目的达成与手段谋划,此心何能洒脱无缚而体味眼前之真趣?渊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曰:“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发岁始俯仰,星纪奄将中。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神萍写时雨,晨色奏景风。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时光飞速如空舟快棹,人生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且其间时运之夷险窊隆变换无定。渊明之诗意,要须此心常居冲和,以待此人理必然之变。冲和者,澹泊于名利之奔竞与功果之图谋,无它顾虑、杂念与偏执,直任其志意性情之所行,而后能将心神收摄投注于当下之周遭,以见林木之丰荣,“善万物之得时”(《归去来兮辞》)。
此即事之高明,源于虚明之“素心”。具之者,则其目光眷注于近小平凡之事物,而每能于平淡之中感会得其可爱之处。《杂诗》其四曰:“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渊明之志,迥异于世俗之悠悠奔竞,而沉浸于目下即时之欢娱,了无谋图,都不远虑,全情贯注,与物一体,忘乎所以,不知老之将至。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又云:“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飔。不驶亦不迟,飘飘吹我衣。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且先搁置诗中在盛思衰之感,而留意五月光景之“可爱”。其中所谓“流目”者,并非有意探察,而乃闲散无目的地纵目游观,任物跃现于眼前,如“悠然见南山”之意境。景物与无我之心境相互应会,于是雨乃闲雨,自在洒落,从容不迫;云乃行云,任意东西,变化游移;风乃和风,不疾不徐,温和清润。人与景各任自然,而相谐相契、浑融无间。
渊明又好游于山水丘壑之间,《归去来兮辞》曰:“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移居》其二亦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天气澄和,风物闲美”(《游斜川》诗序),三五同志,衔觞赋诗,言笑晏晏,以终其日;又或琴书为伴,稚子戏侧,种豆采菊,舂秫作酒——“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其一)。《读山海经》其一亦曰:“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泛览流观正如“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随意翻检,不疲乏伤力,不为任一事物羁绊,但又沉浸其中。他尽心捕捉生活中的每一分美意,故其随兴并非草率含糊,倒见出生活之郑重与认真。而从中获得乐趣即是人生最胜之理与最高理想。
人与周遭物事的互相亲近,须以人之心境的简淡忘机为先决:淡然无我,而后能神思清明,心怀敞亮,任风物自在涌现,而全情领受其中之意趣与大美。此心是为虚静之玄心,排遣计量分析之理性,而呈现为前意识或前理性的感性状态。因行事之间并无机心目的,不假觉思,无一毫勉强作态,故能纯粹真切地投入自己的全幅情感去感知契会当下事物,至于心物一如,外内无间,自然浑合,则每多洞见、深情与妙赏。事物之未至,则并无预谋或期必,而迎纳一切可能性;及至事过境迁,情随之尽,冰心素白,都不淹留执滞。盖其宅心于无限的大化流行,而后能自在出入于世变之中。然则入必深情,出则透脱。渊明之至性深情,尤可见于其《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等诸诗文中。
又复遥想精卫衔石填海,夸父与日竞逐,孔子知不可为而为之,荆轲毅然刺秦而不反,其所以能如此者,唯行其志意而已。各从其志,自得于心,全情贯注于行事之间,至于成败生死,则一概置之度外。唯如此,故有悲壮慷慨之风力,令后人于千载之下犹能想见其凛凛生气,所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者也。
四、纵浪大化
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曰:“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渊明息交绝游,其心境之淡远澡雪,已入于洁净精微之境地,无声雪白,了无人迹,斯可谓幽人高士。虽无尘俗之悦,却有固穷之乐:衡门栖迟,独对琴书,尚友千古,坐究四荒。
与渊明相形,好陶的东坡则对此绝对的幽独心怀恐惧,其《后赤壁赋》曰:“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6]东坡亦有入道之梦,但对尘俗尚有不可斩截之留恋,故而当其置身于此绝对的虚静与虚静的绝对之中时,难免心生悲恐,不能久居,遂落荒而逃。于是那作为道之象征的孤鹤与道士,倏忽掠之而去,杳然不见其处。是虽有道心,而不敢入道,亦终不能入道者。
但东坡却时有仿佛见道之语,《前赤壁赋》言“变者”与“不变者”[7]:天地之间举为变动之物,而“不变者”唯是一切变动的整体,亦即绝对。如陶诗云“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虚明之心自合于绝对而敞向无限可能性,对于天地之间的有限之物及其变动具有超越的整体观照,故不执念于既往,亦不期必于未来,而后能任随形迹迁转而闲淡自若。如此则心不为物使,而能使物,如古井之无波。然后萧然忘机,而纵意用情于每一种当下的可能境遇,肆志于眼目之下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于是在与物的瞬间契会间,即有无限与永恒的当下呈现。
此则可谓“观化”,表明开阔心灵与造化整体的契会如一。但此心又非绝然高蹈,而恰寄寓游走于殊物之间,与之感会融通。渊明《读山海经》其二有“天地共俱生,不知几何年。灵化无穷已,馆宇非一山”之句,本写西王母之仙寿与神灵变化,然而亦未尝不可读作对无我神游之状态的描摹:其心入于无限,故与天地俱生;其心又随在而适,寓于万物,故天地之间皆其所居之馆宇。“观化”者也常喜浮云之无定,亦爱讽咏“浩浩洪流”,因为云水不执定形,而即呈现出活动流转的无限可能,于是便成为见道者的寄托与写照。云行水流,游戏自在,此为风流逍遥之真意。渊明撰《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起句便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以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无来处,故无端倪;无姓字,故不受虚名拘系。其间既有幽独,亦可见其逍遥于无垠之境。从而所在皆可寓居,所适无不安乐。
隐者得道并非易事,他须对宇宙及生命实有洞见,且能经受住生活的诱引摧迫和幽独煎熬,而真正乐在其中。一己行其宿志,以清高自持,则生活之寒苦尚能勉力克受。但人生世间,绝非赤条条无牵挂,而尚有不可逃脱的人伦义务,故不能决然弃绝人事而专顾一身出处。于是在个人志趣与现实生活之间,每有冲突与熬煎。渊明《咏贫士》其七曰:“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渊明虽率性固穷,但因此而不能为儿女创造优裕的生活,亦感忧心惭愧。此是固穷之难。
渊明亦曾做官,亦躬耕自给,过着人间世的平凡生活,而非“形隐”者隐遯深山、避世不出。鲁迅在其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说渊明并非真隐者,因为真隐者超出人间世,自不必作诗为文予人看,也不应用情俗务;然则渊明既有诗文流传,亦有许多牵缠愁苦。此中亦或有辩:一者,渊明并不有意以诗文自鸣,其作诗为文,直是聊发性情、自得其乐而已,他人之看与不看,后世之传与不传,则初不经心;二者,所谓超出人间世之隐,亦有“形隐”与“心隐”之分:“形隐”者决然弃世,得隐者之迹,虽为人所称高,却也固僻偏执,行之亦实难;“心隐”者,形寄人间,而心神淡远幽独,得隐者之意。生身不可逃于天地人伦之间,然则即事而心远,固可游乎方外,遁入无垠的虚静;而后能以幽独之心过群体的生活,以淡远之心做人间的事业。
渊明实为“心隐”者,虽则悠然心远,却不自标清高、谢绝尘事,而只平淡郑重地过着寻常的生活,从老得终,悠游卒岁。如其《自祭文》所述,他自忖度过了极美好的一生,故其临终言曰:“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对于人生当归止何处,渊明有着清醒的知解。若非如此,则不能写出“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之句。唯神思清明而心知所向,而后其从吾所好者方能坚定不移。不光如此,他亦非单纯的旁观者或叙述者,而是以切实的生命行动来践履其志意与性情。以自觉、郑重、欣乐对待生活与生命,凭此即可谓陶公为真隐者。
隐者之在世,譬如秋菊幽兰,虽无人而犹芳。萧统于《陶渊明集序》对隐者之志有所隐括,其文曰:“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盈虚,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8]隐者明达,韬光遁世,不自矜夸,不自张大,以至于忘机无我,以纵放虚明之神灵契会宇宙万化,由之获得真切自足、怡乐悠然的生活与生命体验。隐者“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9],含贞养素,求志达道,以天地之心为心,乃与天地上下同流,此其所以殊异于一般渔樵村夫者。虽说隐者似乎专于成己,寡能成人,然则不能成己,又焉能成人?故必先成己,于人生之意义思索明白,而后始能以其昭昭发人之昏,使之成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