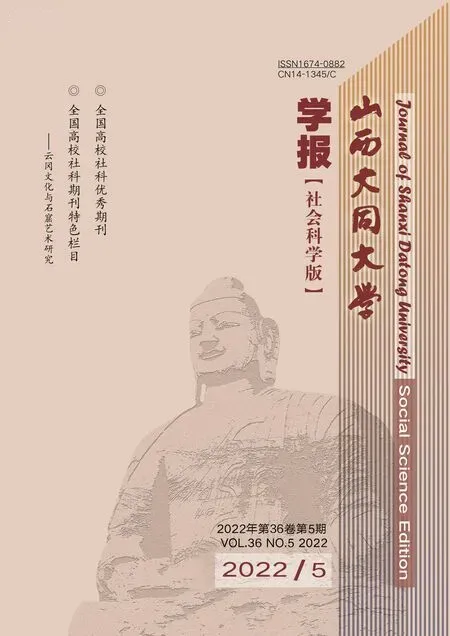浅析沈曾植行草书用笔特点
2022-03-15文津
文 津
(晋中学院美术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沈曾植(1851—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他以章草笔意嫁接行草书,创造出了生拙、野逸、险峻的书法作品。纵览沈曾植的书法作品,篆、隶、行楷、行草均有涉及,其中篆、隶、行楷作品数量不是太多,篆、隶多为临习作品,行楷则多以对联形式出现。相比之下,沈氏的行草书作品出现频率比较高,无论是立轴、对联、还是扇面、手札,沈氏行草书都能很好的驾驭。行草书可算是他的典型书体,也代表了他书法的最高水平,所以笔者下文欲以沈氏的行草书用笔为典型展开具体分析。
一、运笔方法——“转指”、“运腕”、“卧笔”
王蘧常对沈曾植作书这样评价:“先生作书,速度极快,笔力奇重。曾云:‘作字须胆大’,执笔在手,盘旋飞舞,极其灵动,甚至笔管卧倒于纸上,厚如玉版宣亦常被打去一大片。他作书主转指,转指时最用力,要求笔笔送到。”[1]可见,沈曾植主张作书时要“转指”,因为手指转动才能将笔送到位。这明显是受到碑派提倡者包世臣的影响,包世臣提倡书写时要转指用腕,因为“转指用腕”可以使书写更加灵活。同时,沈曾植认为书写时只有运腕才能得势,而运腕要视情况而定。“写书写经,则章程书之流也。碑碣摩崖,则铭石书之流也。章程以细密为准,则宜用指。铭石以宏廓为用,则宜用腕。因所书之宜适,而字势异,笔势异,手腕之异,由此兴焉。由后世言之,则笔势因指腕之用而生。由古初言之,则指腕之用因笔势而生也。”在此他指出章程书与铭石书的用笔方法不同,精细的作品宜用指,宏大的作品宜用腕,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掌握了“转指”、“运腕”的用笔方法,笔势也就相应而生了。另外,沈曾植在作书时笔管与纸面不仅不垂直,甚至还将笔管卧倒于纸上,他的“卧笔法”在常人看来极为不合法度,但以沈曾植清季大儒的身份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来看,他是非常遵循传统的。我们可以从他对一个学生关于笔法的回答中一探究竟,“先看《书苑菁华》。从唐人议论研究则知古,从宋人研究则知今。以唐碑证唐人议论,以汉碑证汉人议论。笔法所由来,了然可观。”由此可见,沈曾植认为用笔有“古”、“今”之别,唐代碑刻与唐人用笔的议论可以互相佐证,汉代碑刻与汉人用笔的议论可以互相佐证。沈曾植认为对笔法的追究不仅要从古人理论中找到依据,还要以时人的书迹做验证。沈曾植正是致力于书法经典,顺应时代潮流,在古人传统用笔的基础上融入时代特色,这才导致了他“卧笔”的独特用笔方法。当然,对流沙坠简的细心钻研和学习也是导致他用笔盘旋飞舞的一大原因。
从书法用笔演变来看,沈曾植“转指”的运笔方法源于帖派,帖派多书写小字用笔精细,另外加之秀妍流畅的特点,故主张“转指”,认为“转指”可以使笔画更灵活生动。沈曾植“运腕”的用笔方法则受到碑派的影响,当时碑学书家为追求苍茫、遒劲的笔道和金石气,热衷书写大尺幅作品,这就客观要求运笔方式的改变,“运腕”的用笔方法使大尺幅书笔画更有力。沈氏在书论中谈到“指腕兼用之妙,实董发其端”。“转指”虽为帖派运笔方法,“运腕”虽为碑派的运笔方法,但“指腕兼用”实际从董其昌就已经开始使用了。王蘧常在描述沈曾植书写状态时用到一个词:“卧笔”,“卧笔”其实是“转指”与“运腕”的综合运用,“卧笔”使笔画盘旋飞舞,恣意生动。
二、笔画形态
笔画是构成汉字书写的基本单位。用笔的中侧锋和笔画取势直接影响了笔画形态,沈曾植行草书中典型笔画形态具体表现为方圆笔和波磔的使用,笔者以下欲具体分析。
(一)取逆 清代包世臣认为帖派用笔注重起笔、收笔与牵丝连带,而忽略了笔画的中端部分,造成笔画“中怯”。他进而提出“取逆”的用笔方法,具体就是笔管的倾斜方向与笔画书写方向相反,用笔逆锋顶着纸面走。沈曾植受到包世臣的影响,认为笔画“中实”是对帖糜弱流滑的改进。“取逆”的用笔方法使笔锋在运笔过程中得以调整不易失去控制;“取逆”使点画更加丰富,笔画“取逆顿挫”、“中锋行笔”改善了帖派用笔“薄”、“流”、“直”的缺陷。纵观整个书法史,我们可以发现,章草强调横势,今草强调纵势,自改章草的横势为今草的纵势后书法中的顺势增加,逆势减少,这是因为逆势要求“断”,顺势要求“连”。沈曾植认为“断”和“连”是“古”、“今”之间的差别。“断”从汉代书写时就有,是古法,“连”是唐代开创的新法。他强调古法,借用章草的元素侧锋取逆来弥补帖派流畅轻滑的蔽习。那么,沈曾植是如何将这种“逆势”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呢?
1.横画內擫,竖画外拓
所谓內擫就是力量从外向内压迫,笔画的边缘线向里收缩;所谓外拓就是力量从内向外扩散,笔画的边缘线向外扩张。內擫多见于汉魏碑版,这也许是由于碑版刀刻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外拓多见于唐以后的法帖墨迹。沈曾植同时吸取了碑派內擫的特点和帖派外拓的特点,需要注意的是沈氏并不是将內擫与外拓简单相加,而是在寻找到內擫与外拓的组合秩序上加以运用,具体表现为横画內擫,竖画外拓。在书写內擫笔画横时手腕需要微微翻侧,产生逆势,书写外拓笔画竖时手腕顺势而下,这一“逆”、一“顺”就使得书写节奏发生变化,改变了帖派书法的流滑,增加了几分持重。內擫笔画让我们不禁想起早沈曾植一百多年的张瑞图,张瑞图的书法锐利刚劲,就是多用內擫笔画使然,他不仅将横画处理成內擫,就连竖画也同样使用內擫用笔,过多的內擫用笔在使其书法坚韧挺拔的同时也对书法的高古浑拙有所损伤。沈曾植在內擫的基础上加入了外拓,竖画的外拓柔化了內擫横画造成的锐利芒角,使整个字变得坚韧挺拔而不失古拙。
2.模糊笔画间的牵丝连带
一般帖派的用笔都是在前一笔的末端提笔虚化,顺势下行,在下行过程中慢慢增加笔画力道,与下一笔的起笔形成连带呼应,这样做使得笔画之间连带性很强,增加了“顺”势,而沈曾植一改上承下接的生理习惯,反其道而行之,改“顺”势为“逆”势。他将笔画之间的连带模糊处理,具体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模糊上一笔的末端连带,强调下一笔的起笔连带;二是模糊下一笔的起笔过渡连带,强调上一笔的末端连带;三是完全舍弃笔画牵丝连带,用“笔势”将笔画联系起来。沈曾植采取这种方法使得笔画“生拙”,打破过往的书写习惯和节奏,给人们的视觉造成了冲击。
(二)中、侧锋互用 沈曾植在《护德瓶斋涉笔》中认可包世臣的“中画圆满”说,但又提到自己书写时却很难做到,直到看到刘墉的书法,才明白要做到“中画圆满”需从笔画稍左开始求得,这就需要我们注意藏锋。杨守敬认为:“所谓‘藏锋’者,并非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2]其实,在明代之前,书家没有“中锋”这个明确的概念,当时的书家对中锋、侧锋的使用意识不是很强,虽然我们在书论中会看到米芾“刷字”等字眼,但这里的“刷字”可能并非我们理解的“侧锋”。“中锋”概念的明确提出是在明代以后才出现的,到了清代由于碑学的兴起、篆隶的复兴,“中锋”这个概念开始大量使用。沈氏追求“中画圆满”,却认为如果不知“中锋”之实,固守“中锋”之名,就是教条主义,如果只为“中锋”而“中锋”,不能将其运用到书写实践当中去,“中锋”就毫无意义。他提到“笔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尝无兼用侧锋处,总为我一缕笔尖所使,虽不中亦中”。他认为中锋是运动变化着的侧锋,在书写静止时用笔表现为中锋,在书写运动时用笔表现为侧锋,中锋是侧锋的实质,侧锋是中锋的表现形式,所谓“八面出锋”也谓之中锋,中锋并非只能使用笔的一两面。他不赞同碑学家“笔笔中锋”的主张,他认为中锋、侧锋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是事物的两个方面、两种状态。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中侧锋互用,他认为两者互用能表现出书法的阴阳、向背、轻重变化。他还进一步提出“侧锋取妍”的用笔理念:“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余裕。”“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就是说用笔要四面出锋,注意起笔收笔的提按顿挫和点画之间的回环顾盼;“偃亚中间,绰有余裕”是说要逆锋行笔,使笔画中段坚实饱满。沈曾植认为书写时既要注意笔画与笔画之间的纤丝萦绕,又要避免笔画中怯,他用帖派用笔来克服碑派主张的“笔笔中锋”,又用碑派用笔来改善帖派容易出现“直”、“流”、“弱”等缺陷
(三)方、圆兼施 清代碑学大炽,康有为认为六朝碑版气象宏大、用笔浑厚的审美价值远远高于帖派书法。他在包世臣用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方、圆兼施,顿笔为方、提笔为圆,方笔用翻、圆笔用绞的学书主张,他认为方笔使笔画沉着凝练,圆笔使笔画萧散超逸。沈曾植的书法作品受到“方笔”、“圆笔”说的影响,方圆互用。这里笔者欲重点强调方笔,方笔的使用一是指直接的方笔使用,即笔画形态为方形;二是指间接的方笔使用,即笔画形态不一定为方形,但所呈现的整体感觉较为方整。细观他的笔画多呈圆笔,但是为何整体会给人方整的感觉?这是因为他在圆笔的基础上突出了锐角的使用,锐角使得字的尖角突出,给人尖锐激进的感觉。
(四)波磔的使用 东汉、魏晋时期,章草盛行,但由于社会发展对快速书写的要求及章草自身的局限性而逐渐被今草取代。王世镗在《论草书今章之故》中对章草和今草的特点做了概述,他主张学习今草应该先学习章草,章草喜“断”、“顿挫”,今草善“连”、“流畅”,但二者都以功夫为基础而不失天然。纵观章草演变史可以发现,它是从古隶、小篆发展而来,所以它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书写的草化,由于快速书写的要求使得在隶变过程中出现很多字形部首的省略和变形;二是波磔笔画的运用,波磔是隶书的主要标志,章草将隶书的这一主要特征经过改进保留了下来。元明书家以传统章草《急就》、《月仪》、《秋凉》、《豹奴》等为范本,糅合今草、章草,这样既发展了今草又使得章草笔意得以流传。元明书家在使用章草笔意这一点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章草的书写,比如邓文原、宋克、俞和等人就是按照传统的章草范本进行临摹学习,以致将波磔作为作品的典型笔触来使用;另一类就是将传统章草和今草进行糅合创造,比如杨维桢、徐渭、傅山等人,他们对章草的波挑和草化笔画进行借鉴,巧妙的融合在今草创作中,这样的作品可以概括为对波磔的节制使用。沈曾植属于将章草、今草进行糅合创造的书家,他主要通过强调单字的横画出锋或捺笔波磔以示章草笔意,横画出锋与捺笔波挑显示了主笔的分量,突出了笔画的力量感,同时强调了笔势走向,这也许就是书家喜用波挑的原因。王晓光将沈曾植的一部分作品统计后发现:“其中立轴作品含波磔笔的单字约占总字数的17.6%,相邻(字)磔角同时出现时,则同时予以弱化(形小、短促),另一种情形时,对联中波磔频度有所提高,对一些八言联作一番统计后显示,波磔笔字数约占总字数的31%。”[3]由此可见,沈氏书写时喜用波磔,但他是在一定范围内有节制的使用;另外,不同的作品样式使用波磔的频率不同,对联中波磔的使用高于立轴波磔的使用,可见,沈曾植对其笔画使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波磔的使用按使用范围可以分为楹联作品中波磔的使用、立轴作品中波磔的使用和扇面、手札类作品中波磔的使用。在楹联作品中,由于字数少、字的半径大的缘故,波磔类笔画往往起到主导、支撑的作用,这就要求在书写波磔笔画时要强化突出,但是作为主笔,波磔又不宜过于显眼。在立轴作品中由于字数较多,字与字、行与行之间需要互相错位呼应,这时的波磔就起到一个调节作用,波磔的使用在调整书写节奏过程的同时也利用“势”加强了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在扇面、手札类作品中波磔的使用比前两类要频繁的多,这时波磔作为一种标志性笔触出现,类似汉简、章草类作品。
结语
沈曾植早年从帖学入手,临习二王、米芾、黄庭坚和各类阁帖,他提倡包世臣的碑学运笔理论,经过自己亲身实践探索后,修正完善了包世臣的运笔方法。在清季碑学运动的热潮中,他受到了碑派“中段圆满”、“五指齐力”、“崇尚碑版”、“篆隶复兴”等书学理论的冲击,他同意碑学的一些学术主张,但在他看来,南北本来就是互通的,二者皆可通二王书风。他主张南北同源,所以他在积极学习北朝碑版的同时也在探索帖学的用笔方法,他以碑看帖、以帖审碑、纳碑入帖、以帖补碑。笔者认为可以把沈曾植行草书的用笔特点概括为以下几点:一、糅合碑与帖的运笔方法。帖的运笔方法主要是“转指”,这与帖派多小字及其精细流畅的审美要求有关。碑派则主张“运腕”,这是明清大尺幅作品对运笔方式的改变提出的客观需求,“运腕”扩大了笔的活动范围,使书写更灵活自由。沈曾植在“转指”、“运腕”的基础上甚至提出了“卧笔”,“卧笔”的运笔方式是沈曾植生、拙、涩书法风格形成的关键。二、以碑的迟涩克服帖的流滑,以碑的强劲改善帖的糜弱。传统帖学用笔注重起收的提按顿挫,中间部分容易一带而过,造成空怯、流滑。碑派书家讲究“中段圆满”,他们认为笔尖顶着纸面走,通过增加笔与纸之间的摩擦可以改善帖的糜弱流滑。沈曾植认为中锋是侧锋的实质,侧锋是中锋的表现形式,二者并不对立。沈氏认为中锋立骨、侧锋取妍,他主张中、侧锋互用。现在大多书家一味的认为沈氏书法多侧锋,忽略了中锋在其作品中的作用。三、横势与纵势的处理。沈曾植借鉴六朝碑版中宽博开张的结体,注重了横势,因此字与字之间的纵向联系相对减弱,为了保证通篇的连贯与完整,沈曾植通过加强点画呼应、调整字形大小与倚侧等方法把看似独立的字联系起来。四、六朝碑版由于刀刻的缘故,多棱角分明、锐利圭角,加之刻手的水平高低不同造成碑版的优劣,这就为书家挑选学习造成困难,沈曾植早在学习阁帖时就意识到刻手是影响版本优劣的因素之一,因此他没有盲目的跟从碑派书风,而是进行理性的选择。另外,碑版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棱角容易模糊,碑派书家可能将原来刀刻的方笔视为圆笔,所以追求碑刻的苍茫、圆浑,而沈氏则“透过刀锋看笔锋”,以笔墨来表现碑刻,并主张方、圆最终都是为书法风格服务的。
沈曾植身处碑、帖二元对立之际,却不囿于碑、帖。他的出现使得章草在清末民初得以复兴,沈曾植在传统章草的基础上加入时代风气的创作方法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大胆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