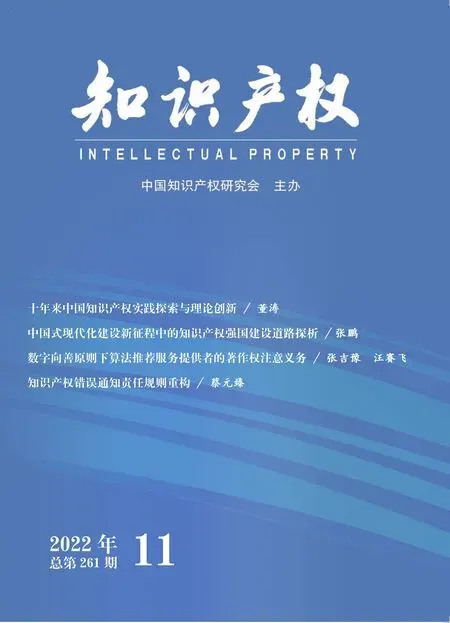知识产权错误通知责任规则重构
2022-03-14蔡元臻
蔡元臻
内容提要:围绕知识产权错误通知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的签订以及国内相关司法文件的陆续跟进,打破了立法与司法之间的默契。利用《民法典》第1195条第3款之例外规定所带来的契机,知识产权错误通知责任规则有望迎来灵活、合理的开放性重构。该重构工作应当因循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不同知识产权客体在侵权判定层面的方法论和专业性差异,通过纳入和完善“错误通知情节”这一考量要素,完成对错误通知归责原则的多元化设计,同时合理安排平台审查义务,最终实现避风港规则的利益平衡本旨。
一、问题的提出
避风港规则于21世纪初被我国正式引入,并在此后经历了一段发扬、勃兴和完善的时期。具体说来,避风港规则不仅在适用场景上逐渐延及了知识产权网络保护的主要领域,且较之美国等率先启用该规则的国家和地区,其在我国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学界的热议随着2013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修改等工作达到白热化,在近十年后的今天依然留有余温。大量的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已经厘清(甚至解决)了有关避风港规则的大部分概念和制度安排,如今尚待深入研讨的议题则以特定产业下的规则适用①参见兰昊:《电商领域知识产权“通知—删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4期,第53-65页。、特殊客体的规则适用②参见詹映:《“通知—移除”规则在专利领域的适用性分析》,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第176-187页。、不同法律文本的协调适用③参见徐伟:《网络侵权中错误通知人的归责原则——兼论〈民法典〉第1195条第3款的适用》,载《法学》2022年第6期,第114-127页。以及平台义务④参见蔡元臻、白睿成:《云计算服务平台适用避风港规则的局限性及其破解》,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4期,第42-52页。为主。
避风港规则下的错误通知责任和平台审查义务原本并非该规则最受关注的问题。然而,实践中愈发普遍的错误通知现象已经对平台的运作模式及用户的权益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并逐渐升级为负担。一次得逞的错误通知在效果上如同“免费赠送”的诉前禁令,能够导致相关内容和商品在短时间内遭到删除和禁止。在违法性方面,错误通知不但侵犯了被通知人的财产权利,倘若在具有竞争关系的主体之间被使用,意在对对方形成商业打击,也可能构成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错误通知由此同恶意通知一并属于“利用违法通知滥用避风港规则”的不法行为,亟需得到规制。
目前,围绕我国错误通知责任规则完善的核心争议既非构成“错误”的判定标准,亦非规则细化的其他具体方案,而是明显属于基础理论范畴的错误通知归责原则问题。遵循侵权法一般原理,侵权行为应当以主观过错作为构成要件之一。但是考察我国相关规范性文件可以发现,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8号)到《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再到《电子商务法》和《民法典》,我国在该问题上始终坚持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些规定是与侵权法理论存在直接冲突,还是立法者选择将错误通知作为一种严重而又特殊的侵权行为对待?随着司法实践对过错责任原则的坚持适用,这些疑难问题原本逐渐淡出了理论研究的视野。然而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以下简称《中美经贸协议》)第1.13条明确要求我国“免除善意提交错误下架通知的责任”,再次突出了现有错误通知归责原则问题的矛盾性。该条款后续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法释〔2020〕9号)等司法解释文件中,进一步促使错误通知责任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迫使我们必须重视错误通知责任问题,近期已有研究试图通过法律解释方法消解冲突,重拾体系的一致性,同时针对恶意和善意的错误通知责任构成,在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之间作出抉择。本文对此类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深表认同,但亦想指出其过度的法教义学化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或许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尽管知识产权错误通知责任在我国立法和理论构建上存在诸多不足,但是否也因此使得制度完善具备了充分的开放性。知识产权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开放性重构应当以知识产权客体的差异性为基础,以错误通知归责原则的灵活性为表征,以合理分配网络平台的审查义务为目的。基于这一构想,本文第二部分将对我国现行规则及其冲突加以梳理,并阐释制度完善的开放性思路;第三部分基于知识产权客体差异,提出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多元化重构思路;第四部分则具体论证多元化规则及其合理性。
二、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现有困局与破解路径
(一)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立法变迁
2000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8号)第8条第2款曾规定:“著作权人指控侵权不实,被控侵权人因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遭受损失而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由提出警告的人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我国立法上最早带有错误通知责任意味的条款,采用的也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过,直至该司法解释于2012年被废止,援引这一条款的案例屈指可数,让人无从判断条款中“不实”之意涵。从我国后续相关司法解释的立场来看,“不实”应指通知本身存在错误的“内容不实”,亦即在实际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主观认定他人侵权并且发出指控,而非蓄意捏造错误内容的“行为不实”。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4条在归责原则上回避了主观要件,通常被认为是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重申,此后的《电子商务法》也作此处理。至此,我国立法在无过错责任立场上一以贯之。不过,《电子商务法》首次明确区分了错误通知与恶意通知,在通知人的主观状态层面作了区分。其第42条第3款次句规定:“恶意发出错误通知,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失的,加倍承担赔偿责任。”从中也可以看出,这里的两种违法通知并非两个平行的概念。此处的恶意通知采狭义,仅指在明知存在权利瑕疵或者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仍然发出错误通知的情形。至于重复通知等滥用通知规则以达到骚扰对方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不属此类。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虽然该款勾勒出了“恶意发出错误通知”的责任,但并未进一步区分恶意、善意与过失错误通知。尤其是,该款在细化主观认知状态之余,一来仍没有将主观过错视为错误通知责任的构成要件,二来恶意发出错误通知的法律后果在性质上与“非恶意的错误通知”无异,只是加重了赔偿责任。总之,《电子商务法》在谨慎探索和有限完善的同时,没有改变我国坚持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贯态度。
《民法典》第1195条第3款在归责原则上沿用了以往的规定,⑤但是该款选择将“权利人”作为错误通知主体的做法值得探讨。通知人往往以权利人自居,错误通知人有时确为真实的权利人,只是由于错误地判断了侵权事实而发出通知。但也有通知人是在自知不享有诉争知识产权的情况下,故意侵害他人权益。此时的通知人并非权利人。根据立法机关的陈述,之所以在此处特别明确通知主体,是为了“使这一规定更有针对性”,但这一做法可能使得该款的错误通知丧失周延性,故值得商榷。有关立法商议内容,参见《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0年5月26日。但新增的保留性规定非常值得注意。该款次句,即“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仅呼应了前述《电子商务法》中有关恶意通知加倍赔偿以及《中美经贸协议》中善意通知者免责的特别规定,也为我国整个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开放性构建提供了依据。事实上,针对错误通知责任的例外规定在《民法典》的多次审议稿中都未出现,直至2020年5月草案临近通过之际才得以正式确立。这进一步说明了该条款在前文中的两层意义。
尽管我国司法实践并没有严格遵循立法上一贯恪守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对其的“三令五申”仍然使得无过错责任至少在错误通知责任的理论领域占据了一定优势,论证者多有之。⑥参见程啸:《论我国〈民法典〉网络侵权责任中的通知规则》,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47-148页;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关于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调研报告》,载《人民司法(应用)》2020年第7期,第72页。这种矛盾与和谐交织的微妙局面直到《中美经贸协议》第1.13条的出现,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法发〔2020〕11号)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第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法释〔2020〕9号)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第5条。等司法文件的发布,才让各界重新开始重视其中的理论余味。
(二)立法矛盾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因素
有学者指出,美国与我国签订《中美经贸协议》,意在通过更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构筑新的贸易壁垒。⑨参见易继明:《后疫情时代“再全球化”进程中的知识产权博弈》,载《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5期,第173页。该协议第1.13条要求免除善意通知人责任,目的是为活跃于中国的美国知识产权权利人营造更为宽松的维权环境,同时也促使我国立法在错误通知责任问题上向美国的做法靠拢。前者为私,后者则多少彰显了该协议第1.36条所约定的双边义务一致性。《中美经贸协议》第1.13条对我国造成的冲击是不能忽视的,其间接导致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之间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矛盾。
《中美经贸协议》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国内立法与司法之间的默契。法律文本反复强调的无过错责任立场与司法实践大规模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之间的抵牾,说明国内立法并未吸收司法实践相关经验。在本文的语境下,这种现象在十余年前的立法政策与司法实践衔接之中既已存在。⑩参见苗炎、叶立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政策反思——以立法修改背景下的司法解释为例的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6期,第76-83页。我国立法与司法在错误通知归责原则问题上的脱节,赋予后者过多的自由裁量空间,可能导致放任个别司法主体的价值偏好和能动倾向,⑪参见杨铜铜:《论立法目的司法适用的方法论路径》,载《法商研究》2021年第4期,第94页。或将前者的目的置于虚位。
曾有研究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基于国际经济政治的变动性及其与双边协定的关系,论证对《中美经贸协议》予以“冷处理”的可行性。历史表明,大国政治矛盾(尤其在有可能发生权力转移的时期)往往以经贸摩擦的形式展现,⑫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Alfred A. Knopf, Inc., 1958.但经济上的博弈也可以经由政治磨合而逐渐得到解决,后者便是将本协议加以边缘化的一条路径。目前我国与美国的知识产权博弈,同日本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因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经贸摩擦非常相似,产业的自主干预有限,由国家主导。变动不居的政治关系意味着双边协定往往缺乏稳定性,这也是美国曾经“敲打”世界列强过程中的普遍规律。⑬参见[日]大矢根聪:《日美经贸摩擦的政治解决过程——兼论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叶琳译,载《日本学刊》2020年第5期,第145-152页;赵晨:《走向“贸易新世界”的美欧关系——“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美国研究》2016年第5期,第65-67页。正因此,或许在我国彻底解决错误通知归责原则问题之前,中美经贸关系已有新发展。本文认为,基于历史经验的分析确有其说服力,但诚如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丁·洛克林所提出的,“政治与法律越来越呈现出正式的分化趋势”且能够“有效共存”,⑭[英]马丁·洛克林:《剑与天平——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省察》,高秦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法律应当以现行法为素材而追求自洽和进步,其余则不足为道也。
(三)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开放性构建
既如此,无论《中美经贸协议》关于错误通知责任的规定是否源自一场误会,⑮同注释③,第124-125页。纠结于过错与无过错责任之间,为了消解规则层面的矛盾而投入大量的法律解释技巧的做法,既值得商榷,亦非当务之急。事实上,美国自身在错误通知归责原则上也经历了一个从无过错责任到过错责任的纠偏过程,⑯Playboy Enterprises, Inc. v. Frena, 839 F. Supp. 1552 (M.D. Fla. 1993); Rossi v.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Inc.,391 F.3d 1000 (9th Cir. 2004); Lenz v. Universal Music Corp., 801 F.3d 1126 (9th Cir. 2015).其学术层面的讨论跨越三十余年。一如前述,尽管我国立法多年来坚守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司法裁判却似乎从未对错误通知人适用无过错责任,相反,近乎所有判决都适用过错责任”⑰同注释③,第116页。。这种现象虽于理不明,却从实践角度验证了该模式的可行性,而《民法典》第1195条第3款的例外规定又为该模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并且已经在理论层面发挥作用。有观点在论及《中美经贸协议》和相关司法解释所带来的规则冲突时曾指出:“无论中美经贸协议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适用范围都仅限于电子商务领域。”⑱姚志伟:《〈民法典〉网络侵权条款评释》,载微信公众号“电子商务法实务圈”2020年5月29日,https://mp.weixin.qq.com/s/ADS5KQlzpSCTeq_v10szUQ.其言下之意,《民法典》的规定在电子商务领域之外仍有广阔的适用空间。这一思路确有可行之处,但在本文看来,即便是主动排除电子商务领域而将其他网络产业交由《民法典》安排的做法也未免过于谨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电子商务的概念和边界至今未能得到清晰阐释和廓清。
首先,《电子商务法》第2条将电子商务定义为“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3条的表述亦类似。文义上,电子商务的界定取决于“信息网络”“商品和服务”和“经营活动”三个要素,分别对应技术环境、行为客体和行为属性。对于技术环境,信息网络的传统涵义包括计算机网络、电话网络和广播网络。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外延的扩张和内涵的细化,尤其体现在移动客户端和移动社交网络的确立。而严格来说,这些“新概念”同样尚未得到足够清晰的界定。
其次,电子商务法治语境下的“商品和服务”遵循着网络环境的特殊性,直接套用商标法理论对其加以解释的做法很可能有失严谨。尽管许多类型的电子商务可以在商标制度的相关文件(如《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觅得踪迹,但在表述和概念上都缺乏对应性。例如,有些短视频平台在提供分享短视频渠道的同时,会为一些主播人员构建额外的网络经营空间,即“线上小店”。这种撮合交易和发布商业信息的服务,⑲赛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08民初6194号。似乎与《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分类)第35类下的“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广告”“通过网站提供商业信息”以及“为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双方提供在线市场”相近。但该分类极其庞杂,而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只能调整普遍性、一般性的商品和服务交易。
最后,“经营”一词在我国多个法律规范中使用,对此司法实践和学界多有分析,在区分某个平台是否确为电子商务平台的过程中,“经营”要素的权重最高,其争议性也较之另外两个要素更大。易言之,对“经营活动”要素的判定,往往会影响《电子商务法》的适用。理论上,任何有能力帮助用户完成经营行为的平台都可以被视为电子商务平台。这是基于功能主义思维所形成的观点。网络技术的快速创新强化了平台的功能性,由此模糊了平台类型的边界,也打破了原本更为主流的平台类型化观念。在李美群、易小陆等买卖合同纠纷案⑳李美群、易小陆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1民终22171号。中,当事人双方曾就微信平台是否属于电子商务平台问题展开辩论。对此法院认为:“因李美群在微信朋友圈售卖案涉物品,且微信朋友圈显示其长期在微信朋友圈进行货物交易,故应认定本案买卖合同属于电子商务交易”。可见,功能主义思维扩大了电子商务及其平台的认定范围,并且已在司法中获得认同。㉑类似司法观点,参见北京森悦腾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靖远志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平川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甘04民终388号;王朋飞、许剑涛买卖合同纠纷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6民终2241号。
上述分析的启示在于,电子商务的边界之广阔不仅远超人们的一般理解,而且在法律后果上具有不确定性。若是接受电子商务领域的“规则圈地”,只在余下的空间里做文章,这种不必要的审慎不利于我国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全面构建。任何可实施网络行为的产业领域和主体范围,都应当依据《民法典》第1195条第3款的例外规定而得到灵活、合理的制度设计。
三、从知识产权客体差异切入:一种多元化思路
在错误通知的归责原则问题上,我国早期立法采取了回避和搁置的态度,近期则是在外部压力下有所调整,二者皆非完全因应国内现实需求而为之。正因此,我国应当开放性地看待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构建问题。开放意味着灵活和多元,在知识产权领域,可以因循知识产权客体类型之间的差异加以落实。申言之,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应当分别采用符合其客体特征,尤其是侵权判定特征的错误通知归责原则。
(一)多元化思路的制度目的
任何有关网络主体的义务责任分配都必然牵涉到利益平衡这一知识产权领域的经典趣旨。错误通知责任规则原本并非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规则下的核心内容,但其关系到权利人、平台和一般网络用户的权益。尽管众口难调,但我们应当承认避风港规则自始便具有一种原生性的利益倾向。具体来说,通知删除规则为通知人提供了一种极其简易、高效且低成本的维权途径。也许避风港规则的初衷是为了尽可能免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责任,避免苛求其义务,从而保障该主体的良性发展。但从规则运行多年的实际结果来看,愈发依赖甚至滥用避风港规则的却是权利主体,并非平台,更非不堪错误侵权通知反复骚扰的被通知人。既如此,错误通知责任规则构建的考量基础就不应当是通知人的权益,而是应侧重平台和网络用户的权益。
基于客体特点而差异化地构建错误通知责任规则,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减轻平台因为规则单一而担负的不必要、不合理的注意义务,并非只为单纯缩减平台的工作量。随着内部通知处理机制的完善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平台已经能够高效应对绝大多数的侵权通知。以国内“阿里系”平台为例,其有能力在24小时内将98%的通知处理完毕,㉒《2021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载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网站,http://aaca.alibabagroup.heymeo.net/publications,2022年9月3日访问。至少在效率层面足以对标其他世界级平台。㉓参见蔡元臻:《论合理使用对滥用通知现象的遏制——美国“跳舞婴儿案”的启示与反思》,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1期,第27页。同时,平台为了因应著作权间接责任而推出的各项配套措施也进一步提高了避风港规则的运行效率,其中以谷歌的标准化线上投诉系统、YouTube的“内容身份识别”(Content ID)主动审查系统、Vimeo的“著作权对比”(Copyright Match)过滤系统和我国某平台的主动防控智能算法技术较为知名。主动防控智能算法技术能够实现对平台内容的不间断巡视和分析,并将疑似侵权内容主动发送给权利人,提醒权利人发起通知。㉔同注释㉒。至少在侵权判定相对容易的著作权领域,这一模式颇有“转守为攻”的意味。谷歌公司方面,其在2016年便已有能力应对10亿件涉及著作权的侵权通知,㉕See Google, Request to Remove Content Due to Copyright, http://www.google.com/transparencyreport/removals/copyright/#glance, 2022年9月3日访问。该公司旗下的YouTube平台仅在2021年就收到通知逾15亿件。㉖See Google, YouTube Copyright Transparency Report, 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transparencyreport/report-downloads/pdf-report-22_2021-7-1_2021-12-31_en_v1.pdf, 2022年9月1日访问。在信息处理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海量通知本身并非平台所面临的主要挑战,重构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主旨仍是平台责任与义务的合理安排。
(二)被通知人利益的定位
错误通知往往会对被通知人的利益造成直接损害,立法上基于这一情形确立了通知人与被通知人之间的债之关系,即要求通知人对被通知人遭受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过,在错误通知责任规则重构的语境下,本文认为可以暂且搁置(并非忽略)被通知人权益的考量,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被通知人处于避风港规则的末端,仅受到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间接影响。严格来说,尽管通知人与被通知人在侵权行为上直接对立,但在网络的特殊环境中,侵权行为由网络服务提供者优先居中调停。也就是说,被通知人的权益保护不仅取决于通知人发送通知的行为,还与平台的审查以及必要措施的执行有关系。
其二,被通知人的权益与平台利益存在同一性。对于平台而言,避风港规则的意涵是以大幅提升注意义务为代价,换取责任的减免。理论上,错误通知归责原则越严格,平台的审查义务和侵权责任越小,反之亦然。而当我们尝试梳理被通知人权益与错误通知归责原则之间的消长关系时,会发现二者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平台义务的合理安排能够间接地惠及被通知人,使其更加自由地使用他人的知识产权。
其三,实证研究表明,现阶段的错误通知对被通知人权益造成的损失总体尚小,这一点主要表现为反通知机制常年来的不启动。例如,美国推特平台在2015年共转发侵权通知53,494件,收到反通知148件,比例为0.28%;2021年转发侵权通知329,442件,收到反通知20,057件,比例为6.09%。[27]See Twitter Transparency, Copyright Notices, https://transparency.twitter.com/en/reports/copyright-notices.html#, 2022年9月10日访问。推特平台上的反通知数量在2021年下半年较之上半年暴涨两百倍,创历史新高。但这仅是个别核心用户的偶然行为,无法佐证反通知机制正在逐步变得普遍。虽有明显增长,但时至今日,反通知机制在整个避风港规则下依然扮演着比较轻微的角色。诚然,被通知人抗拒反通知机制的原因是多元的,除却法律资源和财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外,一些权利人在通知中的强势表达和威胁性用语也是用户遭到震慑从而退却的原因之一。[28]Jennifer M. Urban, et al., Notice and Takedown in Everyday Practice, UC Berkeley Public Law Research Paper No.2755628,22 March 2017, p. 41.若是从网络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网络内容的快速消费特征和瞬时性(Ephemeral Nature of Internet)限制了网络用户对其传播内容的情感依赖和记忆黏性,促使其逐渐接受和习惯了内容遭到删除的事实。[29]Jessica Vogele, Where's the Fair Use: The Takedown of Let's Play and Reaction Videos on YouTube and the Need for Comprehensive DMCA Reform, 33 Touro Law Review 589, 632 (2017).但对于理性用户而言,反通知机制的有限性终归源于其带来的额外交易成本。[30]Gideon Parchomovsky & Philip J. Weiser, Beyond Fair Use, 96 Cornell Law Review 91 (2010).用户由于顾虑其进行侵权判定、平台沟通、专家咨询等事务所造成的交易成本超过了反通知所挽回的内容价值,从而决定放弃发起反通知。这对反通知机制的经济性提出了质疑,也从侧面说明错误通知本身的经济危害性尚在用户的容忍范围之内。
(三)平台视角下的知识产权客体差异分析
围绕三类典型的知识产权客体发出的侵权通知构成了目前侵权通知的绝大部分。实践中通知人提交的初步证明材料通常以权利证明为主,缺少充分的侵权分析。为了避免法律风险,平台须判断侵权事实是否成立。很显然,这通常会给平台的工作造成困难。在审查知识产权侵权通知的合格性的过程中,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临时扮演司法机构或者行政机构的角色,对侵权事实的陈述进行初步核实和判断。平台面临的专业知识壁垒是毋庸置疑的,而壁垒的高低则与知识产权客体类型存在直接联系。我国学界对此率先开展研究,[31]参见吴汉东、胡开忠等:《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第232-236页。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层面后续也有所跟进。司法实践中,201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阐述了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商标权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定细则,是该领域内彰显客体差异意识的司法文件之一。此外,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法发〔2020〕32号)第3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害知识产权的,应当根据权利的性质……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亦即将知识产权权利类型作为评价平台采取的措施是否“及时”和“必要”的一项因素,也是上述意识的一种体现。诚如前述,客体类型对平台义务的影响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未能获得及时而充分的法律回应,相较之下,人身权益网络保护的类型化完善则更为迅速。[3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11号)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是否及时,应当根据……网络信息侵害权益的类型和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
平台在处理针对各类型知识产权的侵权通知时,需要面对不同程度的专业技术门槛。知识产权客体因其信息属性和技术构成的差异而采用了思路迥异的侵权判定方法,曾有研究从该角度切入并给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论述。[33]参见王迁:《论“通知与移除”规则对专利领域的适用性——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3条第2款》,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3期,第29-32页。在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三类主要知识产权类型之间,著作权的侵权判定因其信息比对更为直观而易于专利权的侵权判定,是各界经过多年实践而达成的基本共识。[34]例如,参见贾小龙、梁凯鑫:《网络服务提供者专利侵权责任实证研究——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之相关规定》,载李雨峰主编:《西南知识产权评论》(第八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4页;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何琼于2019年10月24日在浙江省第四届“三知论坛”上的发言。但就商标权的侵权判定逻辑而言,其究竟是与著作权的侵权判定同属直观和相对浅显的信息比对,还是因其对专业性要求较高,而介于著作权的侵权判定与专利权的侵权判定之间,尚存争议。[35]参见李佳伦:《影响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及时性的因素》,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3期,第80页。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起草过程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曾调研发现:与著作权领域中常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相比,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侵权判定专业性更强,平台难以辨别侵权通知的正误,这是错误通知和恶意通知滥发的主要原因之一。[36]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关于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调研报告》,载《人民司法(应用)》2020年第7期,第67页。
从知识产权客体论的角度分析,作为知识产品的知识产权客体本身皆由信息构成,只是不同客体之间的信息样态有所不同。作品中的信息通常表现为具有社会价值的文学艺术内容;商标承载的是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其信息则是商标自身所呈现的图形或者文字;专利所蕴含的信息多为具备工业价值的技术方案等。由于与技术方案等无关,在比较侵权判定难度时,人们通常倾向于将侵犯著作权和侵犯商标权一并讨论,并区别于侵犯专利权。但本文认为,侵犯著作权与侵犯商标权在判定方式及其难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37]著作权与商标权在权利属性、权利边界、侵权判定规则上都有明显差异。参见杜颖:《网络交易平台商标间接侵权责任探讨》,载《科技与法律》2013年第6期,第60-61页。总的来说,侵犯商标权的判定更为复杂,其判定结果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并因此亟需在知识产权避风港规则的制度设计中得到重视。
首先,商标表现形式和侵权样态具有特殊性。如果仅从外部表达来看,绝大部分的受法律保护的作品和商标都由文字、图形等元素构成。而对于作品体系中较为特殊的视听作品和音乐作品而言,尽管在商标领域中并非主流,但亦有动态商标和声音商标作为对应。进入21世纪以后,商标类型扩张极大地丰富了商标的表现形式,与作品类型之间产生了微妙的互动甚至融合。然而一旦来到侵权的语境之下,鉴于作品通常具有的宏大篇幅和丰韵内涵,以及商标所先天具备的简洁性,二者各自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侵权判定方法论。具体而言,即“思想表达二分法”“抽象分离法”“整体观感法”等更具抽象意味的分析方法,与“音形义”“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性”“相关公众”等事实分析之间的迥然差异。诚然,两种侵权判定思维之间本质上难言优劣难易之分,但是在实践中,对作品进行抄袭、剽窃等难度更高的“异态”侵权行为相对罕见,更为普遍的是擅自复制并传播作品的“同态”侵权(例如盗版行为)。而商业标识则必须面对能够更轻易实施的“山寨”等“异态”侵权现象。也正因此,跳出直观信息对比的商标侵权判定具有更高的技术性和专业性。
其次,商标制度设有专门的“商标对象的近似性判定”规则。商标对象是商标所附着的商品和服务,商标侵权判定中需要对广义的商标近似性加以分析。广义的商标近似性分析不仅需要考量客体本身与侵权资料之间的相似性(也就是商标与侵权标志之间的相似性),商品或服务种类之间的近似性也是判断商标近似的一个因素,除此以外还有消费者的混淆可能性证明问题。在侵犯著作权和专利权案件中,对比权利客体与侵权物内容的判定思路分别体现为“实质性相似”和“全面覆盖”的侵权认定规则;而商标保护中将消费者产生混淆——一种具有些许公益色彩的因素——纳入侵权判定的做法,与著作权制度下认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用户感知标准”l以及判断实质性相似的“读者标准”异曲同工。[38]与其他判断方法相比,此处提及的两种标准在实践中尚存大量争议。参见刘家瑞:《为何历史选择了服务器标准——兼论聚合链接的归责原则》,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2期,第25-32页;梁志文:《版权法上实质性相似的判断》,载《法学家》2015年第6期,第43-45页。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技术性使其不适合将公众感知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但对于创新程度更低的专利(例如外观设计)产品及其市场,“一般消费者标准”依然发挥作用。[3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21号),第10条和第11条。也就是说,围绕商品和服务类别展开复杂判断的“商标对象的近似性”问题,适用的是商标法下的专门规则,并且很可能使在商标领域适用目前的知识产权避风港规则缺少合理性。
此外,诸如通过抢注获得商标权继而发出侵权通知的行为,以及商标权与其他民事权利之间更加普遍的冲突性,都为平台妥善处理商标权侵权通知造成了困难,提高了错误通知比例。商标抢注是我国商标使用与注册制度并存之下一个长期的疑难问题,近年来学界更专注于商标抢注的体系化法律规制,多少忽略了抢注行为本身的司法认定问题。事实上,对于抢注事实,以及抢注过程中可能牵涉的“不以使用为目的”“不正当手段”“一定影响”“恶意”等考量因素,平台几乎无从判断。而商标权与其他民事权利之间的普遍冲突,是指由于商标本身所蕴含的市场价值性及其多元化的内容形态,导致商标更容易与其他民事权利客体发生重叠。或许平台可以相对快速地处理有关两个文字商标或者图形商标的争议,但当商标权人通知删除的内容受到著作权、肖像权、企业名称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姓名权等民事权利的保护,平台又应如何决断呢?商标权侵权通知不仅在侵权判定方面具有多样性,且牵涉权利类型庞杂,非平台日常工作所能胜任,遑论技术性更高的专利权侵权通知。故此,我国应当因应知识产权客体的差异性而构建更为完善和细致的错误通知责任规则。
四、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重构
(一)制度重构的基本原则
“本身发端于版权的避风港制度,扩展适用于商标已经难能可贵,但是又将其适用于更具专业性、复杂性的专利实属不能。”[40]司晓:《网络服务商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页。这一评价指出了我国知识产权避风港规则开拓有余但雕琢不足的问题。就错误通知责任规则而言,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错误通知归责原则的选择以及平台因未能准确筛除错误通知而可能面临的连带责任方面。后者虽然不曾在现行立法的措辞中得到明确,但遭受损失的被通知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68条至第1172条的多数人侵权责任条款而加以主张。二者之间,错误通知归责原则的调整显然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因为程序上错误通知的发起先于对其的审查,因而平台义务自始具有被动性和回应性。
在因应上述问题对错误通知责任规则进行系统性调整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并贯彻三项原则。其一是知识产权客体导向下的差异化构建。原则上,对于侵权判定专业性较低的著作权侵权通知,鉴于平台通常能够胜任对侵权通知中有关侵权事实初步证明的初步分析,因此可以在注意义务分配方面稍向权利人倾斜,亦即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专利权侵权通知的实践应用是我国扩张适用避风港规则的直接成果,但或许已成为民事领域网络法治统一制度化建设中的一个适用难点。平台审核人员难以具备就侵犯专利权有关事实的初步证明进行初步核实和判断的能力,但在权衡审核成本与间接侵权责任之下,出于规避责任的目的,只能勉强审核之。在此背景下,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构建,应当尽可能减轻平台的注意义务,而将认真对待侵权通知的义务留给专利权人,也就是对专利权侵权通知人发出错误通知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商标权的侵权判定的复杂性介于著作权与专利权之间,其避风港规则适用的合理性存在一定争议。商业标识对创造性要求低的特点造成了商标权的侵权判定难度较低的假象,但实则不然。除却侵权事实较为明显的“山寨”以外,商标权的侵权认定的专业性不亚于技术特征的对比。出于与市场竞争紧密关联的缘故,错误发出商标权侵权通知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甚至高于其他两类知识产权客体的错误通知,实践中也出现了最为多样化的通知滥用形式。因此,对商标权侵权通知人也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
其二是错误通知归责原则的灵活性与合理性。曾有研究尝试从“权责统一”和“权利风险对等”的角度证成无过错责任的适用,但此举首先未能充分考察善意错误通知的可责性,其次从归责事由下的危险和控制力理论出发,也无法解释为何要将错误通知对经济利益和网络言论自由所造成的有限妨害,等同于带有高度人身危险性的“不幸损害”。[41]See Josef Esser, Grundlagen und Entwicklung der Gefährdungshaftung, München: Beck, 69, 1969.与此同时,相对缓和的过错责任也难以破解通知滥用以及禁令制度遭到架空的难题。因此,带有折衷意味的弹性构建是修正错误通知归责原则的应然方向。
其三是将减轻平台审查义务作为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促使知识产权避风港规则在整体上回归利益平衡。尽管并非重构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逻辑起点,但是平台审查义务正在随着实践中通知人过错责任的普遍适用而不断提高。通知人过错责任加重了平台的连带责任风险,继而转化为巨大的审查成本。应注意的是,一味加重通知人的责任并非为平台改善环境的唯一手段,而且这一做法也有悖于前两项原则。在平台义务不断增加的总体趋势下,本文所谋求的必然是一种“有限减轻”,以及对避风港规则的本旨——利益平衡——的最大化实现。
(二)错误情节的理论意义及其适用
基于知识产权客体的差异性,上文对归责原则的一般适用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细化,但依旧有所不及。归责原则本质上是对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状态所作出的制度安排,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恶意、善意抑或过失,都属于错误通知责任下主观要件的讨论范畴。与此相对,错误通知中的具体错误方式和错误程度,则是错误通知责任的客观要件。两要件共同构成了错误通知责任规则,但二者之间并非平行抑或对等的关系,而是采用“主客观结合主义”,由客观要件的具体内容决定主观要件构成与否。在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认定中,“主客观结合主义”往往超越“纯主、客观主义”而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以及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帮助侵权、专利权间接侵权等领域尤为突出。[4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法释〔2021〕4号)第3条。该条通过知识产权客体类型等一系列客观因素推定主观认知状态。在专利权间接侵权责任认定中,帮助侵权同样采用主客观相结合主义;另见蔡元臻:《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专门化研究》,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第1242页。
错误通知归责原则的重构应当充分糅合错误情节方面的考量,从错误方式和错误程度两个维度切入,对不同情形作出针对性的安排。所谓错误方式,本质上是指通知中存在错误的具体内容,也就是“怎么错”或者“错什么”的问题。严格来说,我国对侵权通知的内容构成缺少统一明确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等曾对著作权和商标权侵权通知的格式内容作出过规范,但未能延及专利权领域。这一空白在近年来电子商务知识产权领域的若干文件中得到了弥补,也就是在前二者通知内容的基础上,要求专利权侵权通知人进一步提交相关技术特征的比对说明,以及个别类型专利权的专业评价报告,[43]司法解释、地方司法文件和地方性法规对此都有采纳,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第5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涉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指南》(浙高法民三〔2019〕33号)第8条和第11条;《上海市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意见(试行)》第9条。以此协助平台理解和审查侵权通知。总体上,侵权通知内容应当涵盖五个方面,即权利人信息、权属证明、侵权内容信息、侵权事实分析以及真实性声明。其中,仅有侵权事实分析属于观点内容,其余四项皆为事实内容。
观点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可责性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可能牵涉复杂的论证和微妙的判断,即便权利人作出误判也往往在情理之中;后者则是客观事实的单纯搜集和提供,其谬误于理不容。近年来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美国“跳舞婴儿案”[44]Lenz v. Universal Music Corp., 801 F.3d 1126 (9th Cir. 2015).的核心争议便在于此。该案中通知人对于侵权内容构成合理使用与否的相关分析如果错误,若其属于具有主观色彩的观点错误则无须承担责任,但若将其定性为事实错误则会因为构成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而导致侵权。[45]同注释㉓,第29-30页。在本文的语境中,事实错误应当构成错误通知的加重情节,观点错误则反之。例如,假设原则上适用过错责任的著作权错误通知系事实错误,司法机关就应当认真考虑判决通知人无条件承担责任(改用无过错责任)的可能性;而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商标权和专利权错误通知,则可以因为构成观点错误而得到免责。
错误程度指错误的严重性,既取决于错误通知的行为性质,也要审视错误通知所造成的后果。由于本文严格区分错误通知与恶意通知,将伪造权利证明、虚报专家鉴定意见、重复发送错误通知[46]我国知识产权避风港规则对重复通知行为的态度莫衷一是,但从恶意通知“明知没有权利或者依据不足但仍发出通知”的主流定义来看,重复发送错误通知的行为更接近于恶意通知。相关地方司法文件和司法实践也间接明确了这一立场。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涉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指南》(浙高法民三〔2019〕33号)第28条;武汉金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与刘鹏飞、杭州务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渝民终1083号。等明知通知存在重大纰漏却仍故意发出恶意通知的行为予以排除,因此从行为性质层面,对非恶意但具备相当错误程度的通知行为,应当结合通知中包含的初步侵权证明加以判断。
我国现行法规普遍要求通知人在侵权通知中对诉争侵权事实提供初步证据,但对初步证据缺少形式和内容上的细致规范。由于平台往往急于寻求免责而疏于对通知内容的严格审查,久而久之,该内容不仅篇幅寥寥,并且逐渐沦为一种“反正就是侵权”的缺乏论证性的追责声明。易言之,对侵权事实的举证和侵权行为的描述替代了侵权构成的证明。[47]参见杨显滨:《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3期,第39页。这一现象显然埋没了初步证据的重要功能——帮助平台理解和判断侵权事实的明确性和客观性。也就是说,初步证据环节背后的理论假设是平台在缺少这一内容的情况下,完全无法自行判断违法行为的成立与否。这是平台所承担的私法注意义务与公法注意义务之间的根本差异之一。对于后者,平台在审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暴力、淫秽等违反公法规定的内容时,无须初步证据而应径直作出判断。[48]参见李佳伦:《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内容的判断义务》,载《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3期,第146页。
2022年新修订的法国《数字经济信任法》(loi pour la Confiance dans l'Économie Numérique)简化了侵权通知的框架结构,但其第6条第1款第(5)项仍然要求通知人详细提供删除他人信息的法律规定和事实解释,较之诸多其他国家的同领域立法,该法对“初步证据”给出了更为准确的阐释。我国应重申初步证据之于证明侵权构成的功能定位:一则符合《民法典》第1195条第1款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的明确要求;二则避免权利人变相推卸规范化通知的法律义务,保证平台与权利人之间权责与利益的平衡;三则契合证据法价值理论对制度效率的重视和追求,[49]参见吴洪淇:《证据法体系化的法理阐释》,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165页。实现避风港规则的有序运行。在我国,通知人有责任在提供侵权证明的同时,对侵权事实进行足够深度的论述。借鉴美国法的经验,该论述无须高谈阔论不绝,[50]Rossi v. Motion Picture Ass n of America, Inc., 391 F.3d 1003, 1005 (9th Cir. 2004).但也不允许只言片语了之。[51]See Disney Enters., Inc. v. Hot file Corp., No. 11-cv-20427, 2013 WL 6336286, at *48 (S.D.Fla. Sept. 20, 2013).侵权分析充分但结论错误的初步证明,属于错误情节中的观点错误,而侵权分析不充分或者明显缺失的情形应当被视为事实错误。一如前述,观点错误与事实错误应当分别作为错误通知责任的减轻和加重情节,对一般归责原则的适用产生影响。
侵权法将损害后果的大小作为衡量侵权行为轻重的重要指标,原则上,损害后果越大,侵权责任越重。正是秉承这一观念,侵权法上发展出了用以惩罚严重侵权行为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通知滥用行为的语境下则体现为《电子商务法》第42条第3款中有关恶意通知发送者承担两倍赔偿责任的规定。在法律规制行为的过程中采用后果导向思维,对于错误通知问题也有相当的启示性。对被通知人造成重大损失的错误通知行为,应当对其适用更为严格的归责原则。重大损失既包含经济性损失,也可以表现为人身性损失,例如被通知人正当使用自己肖像或姓名的内容因错误通知而被删除,还可能造成更为广泛的社会性损失,例如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健康。
作为“权利人损失”的配套概念,“侵权人获利”在知识产权制度中通常只被作为损害赔偿计算的一项标准得到应用。个别地方司法文件将违法获利作为酌定侵权情节严重性的考量因素,[52]其中最为突出者,应是202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强化了这一概念的司法适用,但从相关条款的内容来看,“侵权获利数额”的表述意味着司法仍将违法获利的内涵限定为经济层面的直接所得,忽略了间接获利和非经济性获利。通过错误通知获得的利益可能是间接性的,例如,如果通知人与被通知人之间存在市场竞争关系,那么错误通知在对被通知人造成打击的同时,还会为通知人带来颇具隐蔽性的竞争优势。这一现象在如今视频分享平台的同类别播主之间较为普遍。由于同类别播主上传的视频内容经常“撞车”,原本属于良性竞争的“内容战”逐渐异化为恶性的“投诉战”。错误通知获利也可以是非经济性的,美国政治选举期间的参选人及其团队曾经采取借助侵权通知遏制竞选对手传播宣传短片的策略,谋求的则是一种时效性的政治优势。[53]See Elliot Harmon, Once Again, DMCA Abused to Target Political Ads (17 November 2015), https://www.eff.org/deeplinks/2015/11/once-again-dmca-abused-target-political-ads.故此,本文认为此二者也应当被确立为违法获利的表现形式,并且纳入错误情节的酌定范围。
除却上文关于弹性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论述,还需要明晰的是,无论通知中的错误在本质上属于事实或者观点,遵循善意侵权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基本法理,以及司法解释针对善意错误通知的最新规定,能够证明自身不存在任何过错的错误通知人,既无须向遭受损失的被通知人进行赔偿,也不适用事实错误的加重情节。
(三)错误通知中的平台审查义务
我国早期平台具有强烈的中介性、回应性和被动性特征,尤其在避风港规则框架下,长期以来其义务仅限于在通知人与被通知人之间进行协调和沟通。但是,随着避风港规则近年来的泛化式发展,如今我国立法对平台义务的规范,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公法义务与私法义务的分化趋势。其中前者趋于严格,平台事前监控、事中介入和事后规制的公法义务不断加强。即便是私法属性较强的电子商务平台,也逐渐开始担负数据报送、信息过滤以及食品安全等特殊领域的行政事务和监管工作。[54]参见赵鹏:《私人审查的界限——论网络交易平台对用户内容的行政责任》,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6期,第117-122页。后者相对平缓,例如,《民法典》第1195条第2款允许平台根据自身的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同时未明确侵权通知的审查标准;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涉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指南》第13条规定平台只须审查排除“明显”不符合要求的通知和反通知,并且要求在“明显”的认定标准上,“应考虑电商平台经营者的一般判断能力,不能从知识产权法律专业人员的角度进行评判”,该条第3款甚至将提高通知审查标准的权力交还予平台,由其自行把握。
本文在此不予评价平台公法义务的强化趋势,但至少对上述“公私分明”的平台建设模式表示赞同,同时认为以公权观念约束和干预平台私法治理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即便这种干预只是“适度的”。[55]参见刘权:《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以电商平台的法律规制为视角》,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52-53页。但仅就平台对侵权通知的私法审查义务而言,“一刀切”的形式审缓和有余,但弹性不足。平台对侵权通知进行形式审查抑或实质审查,应当视情况而定。由于著作权错误通知采过错责任,且平台能够胜任大部分的著作权侵权判定工作,因此可以对著作权侵权通知进行实质审。反之,对采无过错责任且专业性更高的商标权和专利权侵权通知,则实行形式审。原则上,除非平台在对侵权通知进行形式审的过程中出现错误,亦即未能筛除明显存在合格性问题的通知,否则对于造成损害的商标权和专利权错误通知,平台不承担损害赔偿的连带责任;而对于著作权侵权通知,理应负有更高注意义务的平台必须承担更大的连带责任风险。
结 语
《中美经贸协议》的签订和国内相关司法解释的发布,在错误通知归责原则的问题上,打破了立法与司法之间的默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的诸多研究试图运用法教义学路径,为立法上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坚持和司法中对过错责任原则的青睐都寻得理据。本文不否认此类研究的现实意义,但若是基于错误通知责任规则(抑或整个知识产权避风港规则)目的的考量,片面地适用某一种归责原则既不能充分回应侵权通知的滥用现象,也难以对平台义务作出合理的安排。不同知识产权客体之间的差异是不容忽视的,也正因此,从行政授权到侵权判定,各类客体都有着专门的制度设计。在此意义上,我国对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绝大多数民事权利的网络保护予以统一化立法,这一做法本身也值得反思。
《民法典》第1195条第3款为我国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开放性构建提供了法律依据,利用这一契机,在充分认识平台对知识产权主要客体的侵权判定工作的基础上,将客体差异思维贯彻于错误通知归责原则的弹性适用之中。这一重构思路的主旨,一方面在于消减平台不必要的通知审查义务,尤其是避免平台为免责而强行审查专业性较高的初步侵权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则是理性地追究错误通知责任,在规制通知滥用行为和保证权利人高效维权之间把控平衡。
错误通知责任规则的重构对于塑造避风港规则的整体品格具有深远的意义。避风港规则本为网络私法治理实现利益平衡而生,由于在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营造环境的过程中过度地将权力和便利赋予权利人,该规则又进一步发展出了“反通知”和“错误通知”等机制,作为“利益平衡失序后的再平衡”措施发挥作用。重构错误通知责任规则意味着避风港规则正在放缓前进的步伐并逐渐走向反思。这不仅有利于立法层面对重大分歧的澄清,以及司法一致性和自洽性的实现,更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私权保护制度迈向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