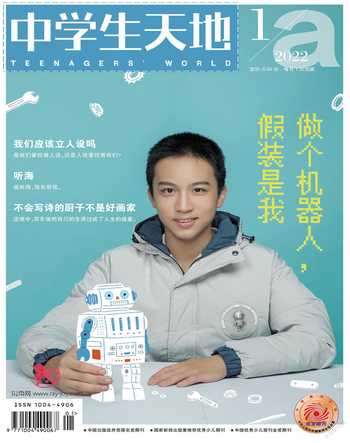我是珊瑚裸尾鼠, 这是我最后的故事
2022-03-14任辉
任辉
我是珊瑚裸尾鼠。你们大概从未听过我的名号,我们之间更没有一面之缘。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只生活在距离你们万里之遥的一座热带珊瑚礁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已经和你们挥手告别多年。
是的,我和伙伴们已经灭绝了。
2019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对外宣布了我们灭绝的消息。他们认定,我们是全球第一种因为人类活动带来气候变化而导致灭绝的哺乳动物。我已经能想象到你们错愕的表情:气候变化对生物的生存环境产生威胁的故事,想必你们都知道一些,比如北极的北极熊因为升温而难以觅食,南极的企鹅因为冰盖的融化被阻挡了前往滩头繁殖的道路。乍看起来,好像只有适应了冰天雪地的极地生物才更畏惧温度的攀升。而我,一种生活在热带的小老鼠居然成了气候变化的牺牲者,这当然超出了你们惯常的认知。
别急,就让我来讲述自己最后的故事吧。
我的故事,要从一只蝴蝶
讲起
其实,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物种灭绝这件事,人类科学家早就有所认识。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北美的一种蝴蝶——季诺格纹蛱蝶就曾遭受过这样的威胁。当时的研究发现,这种蝴蝶的幼虫必须以一种特有的植物——矮人芭蕉为食。随着持续恶化的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高温和干旱,矮人芭蕉的分布范围不断缩小。因此,季诺格纹蛱蝶的未来在当时是不被看好的,人类科学家认为它的灭绝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这种顽强的蝴蝶显示出了惊人的适应性。2015年的研究发现,小蝴蝶不仅改变了自己的食谱,还迁徙到了气候更为凉爽的高海拔地区继续生活。
但你们也能想到,这种看似幸运的故事,其实是不能持续的。蝴蝶或许可以在短期内不断改变自己所处的海拔高度来获取足够凉爽舒适的环境,但山地的海拔总归有限,如果气温持续升高,就连山顶都被热浪吞噬,等待它们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我的故事就印证了这种假设。
频繁的风暴潮,是我们灭绝的丧钟
和小蝴蝶的栖息地相比,我的故乡要矮小得多,在澳大利亚东北部外海的一座小小礁盘上。它的最高处只有3米多,在仅有的0.036平方千米面积中,一半还被沙滩覆盖,能供我和伙伴们栖息的地方只有剩下的一半面积上的零星植被。
许久之前,这片珊瑚礁刚刚露出海面时,我的祖先还生活在几十千米之外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或许是一次偶然的洪水,被冲入河水的祖先只能攀附在一根浮木上漂流入海,意外地来到这里,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历经几十万年岁月,被孤立在小岛上的我们已经在独立演化中变得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近亲们截然不同,我们也成了这座礁盘上独有的特殊生物。
这里并不是多么广阔的家园,而一个栖息地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在大陆上,生物可以不断向周围适合的栖息地扩散,但岛屿上并没有这个条件。很显然,小小的珊瑚礁上养活不了太多的“鼠口”。1845年,人类首次发现我们的时候,我们总共只有数百只。1998年,澳大利亚的人类科学家又对我们进行了一次“鼠口普查”,那时我们只剩100多只。随后的几年里,更多的人类学者来到礁盘上,想对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我们已经越来越难以被他们寻觅到了。2009年,是我们最后一次出现在人类面前。10年之后,人类宣布了我们灭绝的消息。
你或许想问,为什么我们会走向灭绝呢?这座珊瑚礁几乎未被人为开发,现存人类设施只有一座无人值守的灯塔,这里没有受到过外来物种的入侵。把我们推向灭绝的“凶手”,恐怕正是近些年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毕竟在这座制高点只有3米的珊瑚礁上,一次肆虐的风暴潮就能把小小的陆地横扫一通。而由气候变化大背景带来的气候极端化现象,让风暴潮来得更频繁,也更猛烈了。一次又一次的风暴潮扫荡过后,我们终于难堪重负。
气候变化愈演愈烈,
谁能独善其身
我们并不是唯一被气候变化逼上绝路的热带生物。同样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粗卷尾袋貂很可能即将步入我们的后尘。这种只分布于昆士兰北部路易斯山上的有袋类动物非常喜欢在当地凉爽的雨林中昼伏夜出,但近十几年来,这个地区遭受了多次前所未有的热浪袭击,极大地威胁了袋貂的生存。2005年底的一次热浪袭击过后,它们瞬间销声匿迹,直到2009年,人类才又发现了4只幸存个体。此后的几年中,粗卷尾袋貂的数量缓慢恢复。但在最近几年,澳大利亚的热浪越来越强,这些幸存的袋貂是否还能熬过去就很难说了。根据气象监测,路易斯山山顶的温度甚至可能攀升到39℃,而以往的研究认为,当温度超过29℃就有可能导致粗卷尾袋貂死亡。
正如我前面说的,提到气候变化对生物的威胁时,你们总是把目光聚焦于极地的生物。我们这些生活在热带地区的生物的悲惨故事应当能警示你们:在这场全球化的剧变中,没有哪个角落可以幸免,也沒有哪个物种可以独善其身。
这就是我的故事。我和伙伴们已经走完了作为一个物种的一生,这个故事对我们已经毫无意义。但其他万千生物——当然也包括你们人类自己——还会继续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你们的故事是否会和我们截然不同?这需要你们自己寻找答案了。
3825501908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