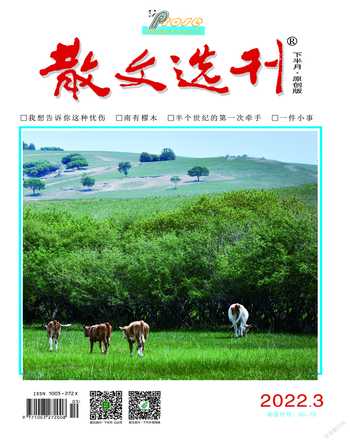外婆
2022-03-12朱晓梅
朱晓梅

被送到外婆家时,我大概有好几岁了。
我认生,就哭。外婆左哄右哄我仍然哭,然后黑着脸说“再哭就把你丢出去”,我非但没有被吓着,反倒号哭起来。外婆抱着我到里屋,把钱放在角落的一个积满灰的坛子里,这才掏出钥匙打开漆黑木柜,摸了一个把把糖给我,我把它含在嘴里还是哭,尽管哭声小且含糊不清。围坐在火堆边的小孩眼巴巴地望着我,眼里全是饥渴,小姐姐嘴角向下耷拉着,好似也要哭起来。外婆说:“别哭,别哭,我给你们砍甘蔗去。”我止住了哭。甘蔗我是知道的,路旁好多地里都有,一排排好似列队的卫兵,颀长的叶子翠白而尖利地向下垂着,就如卫兵的刺刀。母亲说甘蔗很甜,是集体的。外婆拿着弯刀出了门。好一会儿,外婆神神秘秘地回来,还不时回头往身后看,进屋后立马关门,脸色苍白,这才呼口气从围腰里窸窸窣窣地掏出几大截甘蔗来。外婆手脚麻利地砍尖,去叶,削皮,给我三截,其他孩子一个给一小截。我吃得汁水横流,脸上黏糊糊的,最后大家又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
吃完后,外婆把皮、叶、渣全扔进火堆,看着烟雾弥漫的火堆,我心里盼望着明天还能吃。明天当然吃了,后天也吃了,连着几天都吃了,大家的舌头起了泡,于是不愿再吃。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外婆偷砍甘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被逮着是“背时”的,怪不得每次进门都跟做贼一样。也幸亏我们后来不爱吃了。每年甘蔗成熟的时候,我的脸庞总是发红疹,又红又痒,季节一过自然就好,医生说是甘蔗过敏。于是,我不再吃甘蔗。哥哥姐姐说,谁叫外婆偏心呢,每次都给我吃最多,该!
记忆里,外婆很耍赖。有一回放暑假,母亲把我接回家里自己带,我们和外婆家相隔不过两个院子,外婆找上门要五元钱,母亲踌躇着不想给,吞吞吐吐说假期孩子自己带。外婆马上黑了脸,号啕大哭,且边哭边走,引着村里好些人跟着。母亲跟着到了堰塘边,外婆这时停住了脚步,欲跳塘,旁人扯的扯,拉的拉,外婆一屁股坐在堰塘边,叫着“我的命好苦啊——”声音尖厉。母亲脸上挂不住,摸出五元钱递给外婆。外婆接过来,拍拍屁股走了。
外婆很迷信。每回过年给压岁钱,我是五角钱,其他的哥哥姐姐是一角钱。我穿着新衣,拿着崭新的五角钱出门嘚瑟。外婆在门口的井旁打水,我探头去看,脚下一滑,掉进了井里。外婆“哐当”丢了水桶,眼疾手快地把我从井里抓出来,急忙拿小姐姐的衣服给我换上,让我坐在火堆边烤,又熬姜汤给我喝。而我还是发烧了,瑟瑟地抖。外婆叫舅母把那只大红公鸡抓来,反别着它的头掐它的鸡冠,公鸡被捉住翅膀动弹不得,外婆掐出鸡冠血来,给我的额头、手心、脚心涂抹,口里念念有词,朝空中撒了一把米,又带我到木楼上,参拜她的菩萨。那是一碗石灰,上面插着铜钱串的黄玻璃纸,纸上挂有我所看不懂的黄符。我学着外婆的样给菩萨作揖,心里却嘲笑外婆叽叽咕咕地嘟哝着我听不清的话,然后蒙头睡了一觉后,居然好了。
外婆也很固执。后来我们搬进城里了,外婆每每进城卖菜后,总要买点零食来看我。母亲留了她吃饭,无论如何要炒点肉或者鸡蛋,外婆就着喝点小酒,咂摸得有滋有味。母亲的经济大约松动了些,每月都要给外婆零用钱,并且千方百计想留外婆住下来,钥匙都给她。外婆把钥匙丢在邻居家拔脚就走,她留下的话是家里的鸡鸭怎么办,家里的猪怎么办,那些菜怎么办,她还要存钱修房子呢。我问过母亲,外婆为什么一定要修房子。母亲说,外婆一生带过许多孩子,却只有她和姨娘带大了,看到其他人家孩子多,过继了两个男孩子来。外公去世得早,她得想方设法给舅舅置下房产,留个念想。
外婆的人缘好。六十几岁动工修房子的时候,队里的人都来帮忙,外婆像个陀螺似的忙里忙外,可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房子完工了,上梁的时候照例是要请客的,外婆一会儿给人递烟,一会儿与人说话,言语间洋溢着喜气。三外公喝了酒,就爱扯白,他说你外婆厉害着呢,一个寡妇带这么些个孩子,拉扯大不容易。有一回,村里的泼皮欺负她,她扯散了头发,把那个泼皮拖到堰塘里撕扯不休,泥巴糊了一身。队长来劝架的时候,她还扯着那个人的头发不丢(松)手。自那以后,那个泼皮看见她,总是恭恭敬敬地叫声“嫂子”。如今,外婆用两分地换一分,还添上两百斤谷子的条件做了亏本买卖,置换得临马路的土地,第一个在马路边修了房子,以后是要发财了。我寻找外婆的身影,看见她站在马路上,正抬眼看两楼一底的新房,眼里写满了笑意。春天的时候,外婆特意在屋外栽了棵李树。后来李树长得茂盛,年年花开得洁白而热烈。结果的时候,我早已没有吃的欲望,倒是下一辈的几个孩子高兴得不得了。
外婆也是勤劳的。她爱卖菜,一日不肯闲着,不是坡上就是地里。也还是爱喝点小酒,抽她的劣质纸烟,身体也没什么大问题,七十几岁带重孙的时候也卖菜。母亲、舅舅们再三劝说,她总是不听,她说身体壮实着呢,还是吃烟喝酒种菜,只是保证不挑担卖菜了。八十八岁时她还说身体壮实着呢,一日到地里去看她的菜,就摔倒了,摔斷了大腿骨。在床上躺了大半年后,外婆能够下地了,不过,弓着腰,得靠两张条凳帮忙才能行走。夏天,我和母亲去给她洗澡。外婆坐在大的木盆里,我看见她松垮干瘪、下垂到肚皮的乳房,看见她干枯成老树皮的肌肤,看见她皮肤下隐隐凸显如柴样的骨骼,心里酸酸的,外婆老了!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低哑着声音说:“我怕是不行了。我走后,你们要给我做道场,泼血盆,不要让人撒油菜籽,不然我找不到回来的路,一定要记得啊!”母亲红了眼,哽咽着说:“奶儿啊,你身体好着呢,我们还等着给你庆九十岁的生呢。”我望望屋外的李树,葱茏的树叶间,居然有几根枝杈秃着,硬硬地刺向湛蓝的天宇。
冬天我再去看她的时候,躺在床上的外婆已认不清我是谁了,我喊:“外婆,我是梅啊!”外婆没有答话,只流下了浑黄的泪水。看着她蜡黄的小脸,觉得她像冬天的雾霭,游离成一团幻影。我扭过头,屋外的那株李树枝丫一叶不存,为什么我看见了朦胧的水珠?
春天过去的时候,外婆也去了。那株李树没有发芽,它也随外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