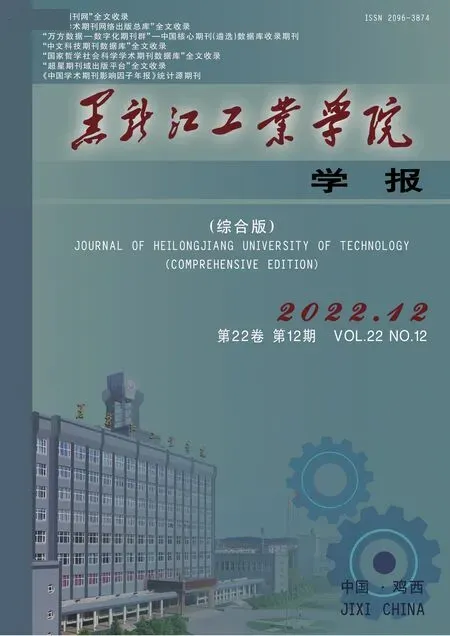从抗日戏剧看东北地域文化书写研究
2022-03-11樊淑玲
汤 惠,樊淑玲
(1.齐齐哈尔市江岸小学校,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2.安阳市新一中学,河南 安阳 455000)
东北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历史发展都比较独特,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艺术家们用富有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映照大众生活,展示自我。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是在东北打响的,最后也是在东北抗战胜利的,因此,东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初期,东北地区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文学界出现了抗日文学活动,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热血青年开始着手组织社团和兴办刊物,爱国的进步作家集结起来发表了许多具有抗争意识的文学作品,其中就包括戏剧。剧作家们利用戏剧这一文学形式将沦陷的东北地区的社会现状呈现在大众面前,试图揭开日军伪善的面目,形成了具有抗争意识的东北抗日戏剧。东北抗日剧作数量众多,但至今对此作出系统研究的较少。其中,主要代表作品包括罗烽的《两个阵营的对峙》《现在晚了》,舒群的《过关》《逃避者》《吴同志》《路》,萧红的《突击》,金剑啸的《咖啡馆》《穷教员》《谁是骗子》《母与子》《艺术家与洋车夫》,塞克的《哈尔滨之夜》《流民三千万》等等。作家们在剧作中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日常生活和乡土风情,通过文学的形式将东北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地域文化精神展现在观众面前。剧作家们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地域文化书写,生活在残暴的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的东北人民的最真实的处境和内心感受被一一呈现出来。剧作家们以此作为与殖民文学相抗衡的强有力武器,渴望用戏剧的形式来唤醒被日本统治的东北人民的反侵略意识。
一、社会背景及剧作家写作初衷分析
1.社会背景
了解东北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背景是我们了解当地特定时期戏剧风貌形成的基础。社会大背景直接影响作家们对创作主题的选择、人物形象的描写和作品基调的敲定,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东北地区的社会环境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1)具有抗争意识的知识分子被残酷镇压
在受日军侵略的东北地区,日寇当局对作家们实施注册等级制度,作家的日常行动轨迹也被跟踪监视,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被捕入狱甚至还惨遭杀害。在东北沦陷区,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被日寇大肆追杀,李季风、关沫南等进步作家都先后被捕,惨遭迫害。因此,沦陷区作家“杀身成仁,未常氏舌,为文氏头”;有些尽管保住了性命也遭遇了非人的酷刑,早已“疮痍满身,永生不愈”[1]。
(2)推行“官制文化”
文化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日本侵略者也深知文化阵地的重要性,因此随着武装侵略的同时还提出了“对支那思想宣战”的口号。在东北沦陷区,日寇所管辖的文化机构操纵着大部分文化宣传,这种法西斯文化专制被日本侵略者称为“官制文化”。日寇当局把文化宣传看得非常重要,于1932年建立了“满洲国通讯社”,并且直属关东司令部。侵略者为了控制沦陷区的新闻、出版和广播还成立了弘报协处和华北武德报社等众多机构,日军侵略者在多个沦陷区都设立了报道部,控制沦陷区的文化,使之成为日寇“思想战”和“文化战”的重要阵地。日寇当局为了获取在文坛的霸权,也建立了全国性或者区域性的文学团体,利用这些文学团体对文艺工作实施有效管理。在东北沦陷区,由于“官制文化”的推行,中国民族文化被打压,各类文艺创作也被严重摧残。但是万幸的是尽管文学被侵略者拉入战争的轨道,企图以政治介入文艺,但是大多数作家并没有屈服,并且在为挣脱这种文化专制做着各种努力和抗争。
2.写作初衷
东北地处祖国边陲,独特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东北地区人民的独特性格特征,东北人民身上的漂泊和流浪的特质也是受到了当地原始游牧和渔猎生活方式的影响。历史上,东北地区因为种种的原因经历了数次移民潮,这也造就了东北地区人民的开放和冒险精神。受到了地域环境以及历史语境的影响,东北的剧作家们在自己的家园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时、民族危难之际四处奔走呼喊,将手中的笔化作尖锐的武器,将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地域文化书写与殖民主义文学相抗衡。剧作家们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统统写入作品中,其中就包含了对故土沦陷的痛心、对迁徙流亡的无奈、对亲人的思念以及对民族的深情等等。
由于受到家园沦陷和迁徙流亡现实处境的影响,抗战时期的东北戏剧常常弥漫着忧郁的情调,在这种现实环境中,剧作家们饱受精神煎熬。东北地区的沦陷以及伪满洲国的存在在当时的社会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某些当局者和某些百姓对家园的遭遇并不在乎,抱有一种无所谓的漠视态度,这种现象大大刺激了剧作家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在国家危难之际,作家们为了寻找生存的意义和实现自身的价值而投身于创作之中,拿起手中的笔杆与敌人抗争,试图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可见作家们的救亡意识。
二、抗日戏剧中典型人物形象分析
1.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家们在物质生活上承受着艰辛与匮乏,在精神世界中也备受煎熬,因此,此时的抗日戏剧总体上的情感基调是忧郁的,表现了知识分子们救亡精神的决绝,这种决绝的精神情调投射在作品中就形成了一个个理想失落、精神迷茫,却不断反思、积极追寻的知识分子形象[2]。例如,萧军创作的《弃儿》就讲述了一名大学毕业生的精神迷茫。主人公晓星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工厂工作,成为一名普通工人,然而工厂倒闭导致晓星失去工作,又身患重病,晓星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危机。在这种惨状下,晓星感到非常绝望,却又无奈和无助,晓星愤怒地将这个父亲用大半辈子积蓄换来的大学毕业证书撕成碎片,在晓星看来这就是一张骗人的证书,证书并没有帮助晓星摆脱贫困,反而让他在精神上备受压迫。然而命运总是如此捉弄人,父亲为了有一口吃的在街头卖报纸,最终却被车撞死,自己的妻子迫于生活的无奈要将婴儿抛到江中,晓星非但没有阻拦,还因“共犯弃儿罪”被捕入狱,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理想的大学毕业生本该拥有完美的生活,然而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却被现实活生生逼迫成了一个阶下囚,表现了一个在东北沦陷时期,精神迷茫,理想失落,生活没有出路的,毫无抗争精神的知识分子形象。
2.普通百姓
东北地区人民内心的顽强的求生意识和强烈的抗争意识是刻在骨子里的[3],当地严峻的生活环境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都造就了东北地区人们特有的顽强生命力,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东北特色的地域文化精神和所蕴含的内在底蕴。
1933年一篇名为《黎明》的短剧在《夜哨》终刊号上被发表,这是一部描写磐石地区抗日生活的短剧。在作者李文光笔下,被日本侵略者扫荡过的村落“被哭嚎、惨叫、叱骂、吆喝、鞭打、放枪、犬吠的嘈杂声浪,可怕地沸腾着”[4]。作者在文中描写了在侵略者压迫之下民众的反抗,其中甚至包括十岁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以及少妇。年仅十岁的小石头跟随士兵送情报;年迈的老太太和少妇在掩护士兵转移的时候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为不退缩,沉着应对。还有宇飞创作的《土龙山》,作者描写了在日本侵略者扫荡后的村落中村民奋起反抗的英勇行为。然而剧本并不是直接描写村民与日寇的战斗场面,而是重点描写了一户普通农家人在面对侵略者强行收缴地照时的思想斗争。日军对路过的村落大扫荡,强迫农民们交出地照,如若反抗便大肆杀戮。作者描述了在这种情况下的一家人的不同行径。面对这种情况,剧中的女人为了保全性命认为只要交出地照就可化险为夷,甚至认为“日军占了东三省跟我们何干?我们不是已经过来五年了吗?”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普通民众的懦弱以及消极应战的心理。然而剧中丈夫的形象就截然相反,他坚持“老百姓们的力量大,土地是百姓们的命,百姓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命,绝不能把土地白白送给他们”[5]。这种反抗行为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反抗,同时也是为了谋求精神世界的独立和自由抗争,这也是东北地域文化精神的属性之一。
萧军的三幕剧《突击》也是一部描写殖民侵略和民众反抗的戏剧,在剧中描写了日寇扫荡过后的惨烈场景,塌了顶的房子,被炮火轰毁了的土墙,打折的树木,死了的牲畜,男女的尸体,这一切被蹂躏的痕迹,还都新鲜地存在着,穿红肚兜的小孩挂在树上摇动着,田大爷的地契凌乱地挂在柴草上。村中百姓对日军的残暴行为愤恨不满,民众们高喊“我们要活,我们要报仇”,通过组织各种游击队与日寇作战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抗争意识。作者不仅描写了游击队员英勇的抗日行为,同时也描写了普通民众一致对外的勇气以及决心。其中就包含十几岁的孩子提刀反抗手持钢枪的日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救下游击队员。失去了孩子的李二嫂被日军残忍蹂躏,她痛骂“鬼子”的残忍行径,展现出当地民众强烈的抗争意识,体现了当地民众身上独有的地域文化精神。
三、抗日戏剧在东北地域文化中的作用
东北地区的地域文化色彩浓厚,抗日戏剧对当地文化的书写和传播都有着重要作用。东北抗战文化历史悠久,具有重大的资政育人的意义。东北抗日战争是一场持续时间最长、环境最苦、抗战也最早的战争,与我国其他地域文化资源相比,历史地位更加突出。在东北抗战时期,抗日戏剧开始,空前繁荣,砥砺了当地民众,同时也鼓舞了士气,对当地地域文化的书写有着重要意义。中国东北地区地处祖国边陲,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严峻的自然条件,东北地区人们的顽强求生意识就是在这种严峻的自然条件中被塑造出来的,东北地区的老百姓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练就了为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反抗压迫的抗争意识。正是这种抗争意识才让东北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得以生存和延续,同时也是这种抗争意识使东北人民在异态时空下抵御外来敌人的强大力量。戏剧凭借着其特有的优势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在特殊的社会大背景下将民族精神与抗战情绪联系起来。戏剧拥有着对时事反应迅速的优点以及方便传播的优势,在战争时期,剧作家们用戏剧作为武器抗衡外来侵略者,他们的作品唤醒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抗争意识。
结语
铁蹄的蹂躏、家国的破灭、生活的窘迫、被践踏的个人尊严以及生命,这就是沦陷区剧作家们所面临的真实境遇[6]。前线的炮火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在逼仄的空间里挣扎着,毫无办法。因此,作家们在面对物质世界感到窒息之时便将写作视为自己的精神避难场所。东北地区的作家们拿起笔杆做武器,通过他们的作品唤醒了东北民众内心的抗争意识,促使民众觉醒,激励人们反抗压迫和屈辱。在创作之时,作家们用心观察百姓们的生活,关注战争中每个人的生存境遇,在作品中融入了作家们对国家的担忧、对故土的眷恋、对现实的抗争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等,真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抗争史。东北抗日戏剧中所体现出来的东北地域文化以及浓厚的地方色彩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对其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对东北地域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