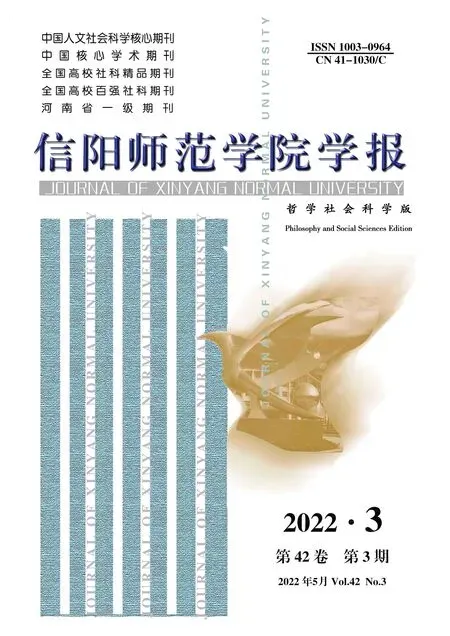《痴心》:家国情怀烛照下的群英谱
2022-03-03郑积梅
郑积梅
(郑州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郑州 450044)
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1],是生命个体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的高度认可,它诠释的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家国情怀已沉淀为中华儿女的内在品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文以载道”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写作传统,拯世救世的社会责任感成为流淌在他们血脉中的印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中国历代无数仁人志士谋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河南作家路程、朱六轩的《痴心》(河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通过描写地方中小企业“鲁阳炭材厂”凤凰涅槃的重生,塑造了一批在家国情怀烛照下为了民族工业发展虽屡遭挫折却痴心不改、以谋求国家富强与民族工业振兴为己任的普通却不平凡的英雄。
一、乡土文学兴盛之下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匮乏
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耕文明比较发达。中国绝大部分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在与土地打交道。费孝通在1947年写的《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乡土”是指中国广大乡村这一基层传统社会,自然村是“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2]5,“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乡土社会是个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2]164。农耕文化深深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土地与故乡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生命存在,正如莫言谈到故乡时说:“故乡如一个巨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两年后,当我重新踏上这片土地时,我的心情竟是这样的激动。当我看到满身尘土、满头麦芒、眼睛红肿的母亲艰难地挪动着小脚从打麦场迎着我走来时,一股滚热的液体哽住了我的喉咙,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那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故乡对于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的祖先灵骨的那片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3]233-234
文学来源于生活,中国作家对于乡土有着内在的精神关联。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文学的拯世救世特质被强力突出。陈晓明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是以‘苦难’作为历史/现实本质而构成文学艺术表达的核心情感。现代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精神向导,拯救国民灵魂,医治心灵创伤则是其根本任务。”[4]407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创作的最早实践者是鲁迅,他的《故乡》以“我”“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的情节叙事,以“我”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感,塑造了闰土和“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人物形象,刻画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萧条、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原本纯真的人性被扭曲,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冷漠。这样的故乡使得“我”选择了最终的逃离。鲁迅的《故乡》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先河。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开始构建乡土文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理论最早提倡者是周作人。周作人认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学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5]15文学理论对文学实践的推动作用巨大。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离婚》《社戏》及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等作品在当时及此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中国文坛上涌现了一大批年轻作家,他们因为比较接近农村生活,创作又较多地受到鲁迅的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乡土文学潮流。如彭家煌创作了《活鬼》《怂恿》《陈四爹的牛》,叶紫创作了《丰收》,鲁彦创作了《炮火下的孩子》《伤兵医院》,许杰的代表作品是《惨雾》《赌徒吉顺》,许钦文则有短篇小说集《故乡》,以及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更是代表了中国乡土文学取得的辉煌成就。杨义高度评价中国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底气深厚,步武结实,不断走着上坡路,一直下接着三四十年代更加繁荣发达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6]429-430
乡土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乡土文学名家名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作品有《三里湾》《山乡巨变》《艳阳天》《金光大道》《创业史》《李双双小传》以及许多中短篇小说等。新时期以来,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厚土”系列、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贤亮的《刑老汉和狗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都是典型的乡土文学作品。综观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作品,可以发现他的大多数作品是以乡土为背景来描写粗粝的、驳杂而又活色生香的乡村生活的,如《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莫言以自己大量的、高质量的以山东高密农村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精心营造了一个“高密东北乡”这样的一个旗帜般的乡土文学世界。
相对乡土文学在现代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显得匮乏、失色。依照一种相对严格的文学标准,长达70余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除了蒋子龙的一系列工业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外,其他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工业题材文学作品非常稀少。洪子诚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工业题材的作品成就不高的现象时说:“这一描写范围被严格窄化的所谓‘工业题材’创作,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它们大多数显得乏味,即使是出自有经验的作家之手。”[7]131洪子诚的相关描述与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王春林分析了导致此种不合理现象生成的原因:“首先,虽然当下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从总体文化传统来看,中国却依然是一个以乡土文化为主体的农业国家,现代都市工业文化的匮乏乃是导致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从中国当代作家的基本文化经验来看,他们大多来自于广大的乡村世界,乡土生存经验的丰富与工业部门生活经验的相对贫乏,乃是中国当代作家所拥有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精神特征。第三,更为根本的一个因素当然还在于从事于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小说家个人是否拥有足够的艺术天赋的问题。”[8]176-177
二、《痴心》:家国情怀烛照下的工业题材的创作探索
随着中国工业的长足发展,中国当代文学也在期待着优秀工业题材的涌现。考量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应该从“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三个层面入手[9]。“写什么”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题材问题。从题材的角度来说,河南作家路程、朱六轩的《痴心》当然应该被归到“工业题材”的范畴之中。作品通过描写地方中小企业“鲁阳炭材厂”的凤凰涅槃般的重生,塑造了一批为了民族工业发展虽屡遭挫折却痴心不改的平凡英雄,《痴心》可谓是一部家国情怀烛照下的群英谱。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深广,家国情怀便是其基本要义之一。我们通常所谓的家国情怀就是指个体人对国、对家的一种思想心境和情怀。千锤百炼、浴火重生的近代的家国情怀带有很强的积极、正面意义。这种超越民族、意识形态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社会建设、国家统一、展现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痴心》全书充溢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作者有过在地方中小企业长期的工作经历,热心实体经济,对工业、工厂和工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痴心》在扉页上注明“谨以此书献给我国痴心于实体经济的人们”,就表明了作者的赤子之心。小说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洋溢于全书的激情澎湃的家国情怀。作者路程在“后记”中提到自己“一辈子在企业埋头苦干,从一名普通的工人到厂长、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一干就是五十年,至今还在企业东奔西忙,见证了鲁山炭材业由小到大、从小高炉到至今我国最大的炼铁高炉用上自己的产品,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和自豪。作者对企业、对员工这份难以割舍的深情厚谊,以及刻在心灵深处的家国情怀”,决心创作一部反映痴心于实体经济的人们生活的作品。“他们痴迷于企业发展,他们所遇到的艰难和困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付出也是常人难以承受的。他们有顺风顺水时的欢笑,但更多的是胶着、煎熬中的无奈和困顿。他们是民族工业发展的拓荒牛,是中华民族的脊梁!”[11]756-757单单看看目录中的一些小标题:“风雪上任路”“责任重于泰山”“追逐梦想”“炼狱”“家国情怀”“没有硝烟的战场”“走出国门”“负重前行”“真金不怕火炼”“新的突破”“艰难的接轨”“铁肩担道义”“赤子之心”等都满含着一种激情澎湃的“家国情怀”。作者在一种宏阔的社会背景中刻画了以季健中为代表的一批饱含家国情怀的时代拓荒牛形象。他们临危受命,突破重重困难,承受着身心的双重压力,使得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而且取得骄人的业绩。
作为英雄的季健中,从临危受命之时就有远大志向,作品展现出了他的非凡气概。他有信念,即使遇到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甚至在遭受陷害等不利的形势下,在四面楚歌、难以自拔的艰难境地中,他秉承“诚信”和“道义”,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应变,始终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群众。他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愈挫愈勇,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当代企业家铁肩担道义的大爱情怀,最终使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成功突围、浴火重生。因此,评论家何弘在“代序”中认为:“《痴心》再现了中小企业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奋勇搏击、不畏沉浮的英雄气概,生动地展示了时代拓荒者‘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凌云壮志,深情抒发了企业家们‘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报国热忱,真切描绘了敢为天下先的英才们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怀揣英雄本色,破万重危局’的艰难跋涉,读来令人心潮起伏,不胜感怀。”[12]1
《痴心》是一部英雄“传记”,也是一部英雄史诗,小说塑造了一批积极创业的英雄群像。全书上下部共42章70余万字,既刻画了人生百态,书写了季健中遭受的苦难,更多的是展现季健中们的战斗史和创业史。毫无疑问,季健中是英雄,漫长的人生历练让他百炼成钢。他的成功,有他自身不屈不挠的奋斗,还有同志们的帮助,更离不开上级党组织和领导的关怀。经过一次次战斗实践的千锤百炼,成就了季健中的人生辉煌,成就了鲁阳炭材厂的辉煌,也成就了这部英雄史诗。这种英雄形象,不是人为的塑造与拔高,而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个革命战士在社会实践中的自觉养成。季健中那种临危受命从容不迫的风度,是由他那长期的艰苦生活磨炼和严峻复杂的工作环境决定的,也是由他担任的职务和责任感所决定的。他心中有人民,在他的心里,人民群众始终占据至高无上的位置,他除了安置本厂下岗工人,还帮助其他国有企业的大龄和残疾员工实现再就业。这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品格。
主人公季健中是一个有着崇高人格的文学审美形象,也是一个体现我们中国文学正大气概的英雄形象。这种形象可以概括为“四有”:心中有阳光、心中有组织、心中有群众、心中有智慧。这种英雄特质,不仅体现在主人公季健中身上,也体现在小说塑造的其他英雄身上。大学教授郑寒光、材料专家杨逸涵、高炉专家张铁山、县委书记刘振国、党总支书记奚道强、工会主席何百松也是这种形象。
应当看到,这种英雄形象的塑造,虽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是依然是作家坚持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创作原则,代表的其实是一个时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三、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的紧密结合
文学是以审美情感为中介来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钱中文指出:“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情感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的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具有广泛的全人类的审美意识的形态。”[13]136
当作者准备动笔创作《痴心》的时候,正如其本人在“后记”里所说,为了能够胸有成竹地从事《痴心》的写作,“披星戴月,翻阅了大量与作品有关的文章、记录、史料、文献等,数易其稿”[11]758。作品的篇幅从最初的100多万字修改、提炼为70余万字。
在写作《痴心》的过程中,已经有过多年文学创作经历的作者,为了作品能够在情节上的推进和细节上的描述更加符合内在逻辑,他们将初稿交给书中叙述事件的亲历者和其他相关人等,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工友,有20多岁的大学生、研究生,也有冶金界的老前辈、高级工程师,有县委书记、科局长,也有学校教师、专家教授,还有法律工作者、文学爱好者,甚至还有海外侨胞,目的就是让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初稿提建议、挑毛病。随后数易其稿,最终写成7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在当下这样一个人心浮躁的时代,已经拥有数十年创作经验的作家,仍然对文学抱有一种敬畏之心,仍然能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精益求精地潜心打磨这部长篇小说,单是这种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的举动,就应获得我们充分的敬意。在很大程度上,《痴心》之所以能够以如此一种成熟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与作者这种精益求精的打磨和修改密切相关。
与以往的那些工业题材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相比较,《痴心》最为突出的叙事特征表现为作品的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的紧密结合。对于这一点,作者在“后记”中已经不经意间有所提及,“山沟里的一家小企业,竟然是我国钢铁界的长子——鞍山钢铁公司大型炼铁高炉内村材料的供货商,而且它的产品一举使鞍钢高炉鹿衬一代炉役平均寿命由四点六年,提高到十三年零八个月无大修的记录……鲁山碳素厂已经发展为旗下拥有八个公司的河南方圆碳素集团,是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炉用碳砖生产基地,产品出口欧美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开创了全国行业多个第一”[11]756。小说围绕地方品牌的创立这些骄人成绩而展开的工业叙事,实际上属于我们所指认的宏大叙事的范畴。在《痴心》中,宏大叙事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客观事实。地处偏僻之乡的濒临破产倒闭的“鲁阳炭材厂”,后来发展成为旗下拥有八个公司的河南方圆碳素集团,是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炉用碳砖生产基地,是鞍山钢铁公司大型炼铁高炉内村材料的供货商。在这个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是杨逸涵、张铁山等这样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凭借自身的智慧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是季健中这样的厂领导想方设法地战胜各种困难,积极组织劳动生产,才能使工厂最终浴火重生获得长足发展。所有这些描写与叙述,全都可以被看作是长篇小说《痴心》中的宏大叙事部分。
此外,作者还把相当多的笔墨,花费到了以季健中为突出代表的一批劳动英雄的日常生活的展示上。举凡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乃至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作者都以非常细腻的笔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生动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工业题材小说作品,之所以乏善可陈,一个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作家们在写作过程中过分地或者说只是一味地进行所谓的宏大叙事,而忽略了更能够见出人情冷暖的日常叙事。我们都知道,与工业题材小说的备受冷落形成鲜明对照的,乃是乡村题材小说创作的骄人成就。乡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的日常叙事。因此,一条切合艺术规律的表达就是,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要想获得相应的思想与艺术的成功,首先必须做到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更进一步说,还必须使得日常叙事成为文本的主体部分)的有机结合。《痴心》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相当不错。
四、结语
米兰·昆德拉在强调小说的意义时说:“从现代纪元初始,小说就不间断地、忠实地陪伴着人。正是胡塞尔在考虑欧洲精神本质时所讲到的‘求知欲’抓住了小说,并引导它仔细考察人类的具体生活,抵御‘存在的遗忘’,将‘生活世界’置于不灭的光照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并赞同赫尔曼·布罗赫反复坚持过的观点:小说之‘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发现那些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如果一部小说未能发现任何迄今未知的有关生活的点滴,它就缺乏道义。”[14]4世界多彩多姿,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吃、喝、拉、撒、睡);安全需求(健康、不失业等);社交需求(亲情、友情、爱情,归属感);尊重需求(荣誉);自我实现需求(自己的理想)。人的具体生活离不开这些方面,当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它必然会以独特的形式产生艺术审美召唤力,使读者领悟到文学形象背后的意义,获得关于人生和存在的启示与思考。《痴心》的社会学价值在于作品描绘的真实历史图景,留下了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做大、做强的珍贵记忆。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工业题材小说作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于沸腾的生活,创作接地气的、富有中国工业气息的、能够体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作品,为工业题材写作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与努力。草明在创作《乘风破浪》时曾经长期深入基层生活,多次采访孟泰、王崇伦、张明山等模范典型,与工人打成一片:“她深入生活的方式,主要是直接参加工作,通过工作来取得对生活的更深切的体验……从1954 年起,她下了更大的决心,把户口也迁到鞍钢落户,并被任命为第一炼钢厂的党委副书记,而且一蹲就是十年。”[15]17草明最终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对工业题材小说具有滥觞意义的作家。 2016年3月16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火热实践,倾情服务人民,倾心创作精品,热情讴歌全国各族人民追梦圆梦的顽强奋斗,弘扬崇高理想和英雄气概,奏响了时代之声、爱国之声、人民之声。”[16]《痴心》中的人物源于作家自身的亲身经历,有着最真实的生活原型。《痴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学表达,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深入生活,是作家在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与真切的生命体验的基础上完成创作的,这一点对当下作家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