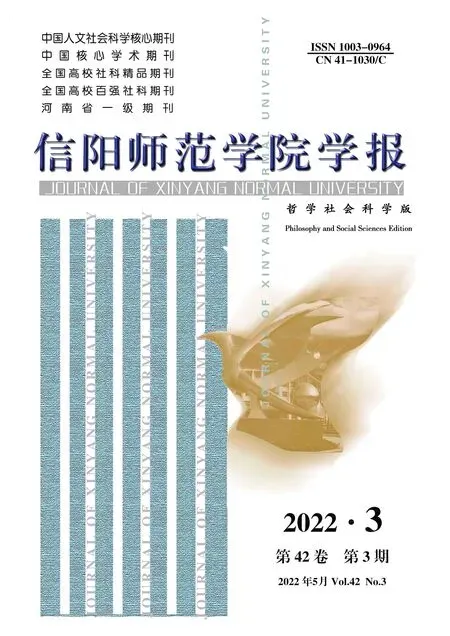温馨燃情的“芳华”
——电影《芳华》价值探析
2022-03-03周强
周 强
(信阳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2017年12月15日,冯小刚导演的情怀力作《芳华》在全国和北美地区同步上映。影片在国内上映79天,票房总计14.23亿,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文艺片。影片以刘峰、何小萍、萧穗子等人物为聚焦点,讲述了他们在文工团青春之会的聚合与离散,从正青春的风华正茂时到后青春的烽火芳菲尽,展现出美好青春的流变与伤逝。《芳华》制造了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话题,产生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力,堪称新时代开局之年的现象级华语电影。《芳华》的成功,凸显出走进新时代的中国电影,在艺术创意力、审美创新力以及文化影响力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变化、新态势与新问题,值得总结与反思。
一、艺术创意力:从形式到内容
(一)生命之舞的视觉呈现与意义变奏
著名艺术理论家苏珊·朗格曾说:“舞蹈是一种形象,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幻象。它来自于演员的表演,但又与后者不同。事实上,当你在欣赏舞蹈的时候,你并不是在观看眼前的物质物——往四处奔跑的人、扭动的身体等;你看到的是几种相互作用着的力。正是凭借这些力,舞蹈才显出上举、前进、退缩或减弱。”[1]4他的经典阐释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舞蹈理解为仅仅是在舞台上演出的具有主题性的舞蹈形态。在宽广的生活场域中,人之力爆发所产生的动态形象,皆可视为舞蹈。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芳华》无疑是一场舞之盛宴。既有成熟完整、精心呈现的主题性舞蹈,也有融入整体叙事链条的舞蹈片断;有展现时代新风的摩登轻舞,有拨动心弦的复苏之舞,有绽放少女之心的追爱之舞,更有与死神较量的英雄战舞等。舞蹈里有时代的印痕,有青春的足音,有爱情的悸动,有灵魂的涤荡,有搏击死亡的呐喊,有爱与美的交响,还有对青春际会和人生际遇的某种象征与隐喻。
电影《芳华》主要呈现了两个典型的舞剧:一个是《草原女民兵》;另一个是《沂蒙颂》。它们的呈现,不仅具有视觉叙事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在叙事结构上形成了前后呼应的对称性。
《草原女民兵》的排演,是在电影的初始阶段。这一叙事段落形成了多重意义交织的艺术效果。一是烘托了时代氛围和具体环境。《草原女民兵》是一支具有鲜明的红色文化内涵的舞蹈,而歌舞技能是文艺兵的身份标识和价值所在,加之他们具有时代感的军队装束,使歌舞的意义大大超越了本身的奇观性与欢乐感。这场歌舞排演在与内外景的有机结合下,折射出“文革”后期的大时代氛围与文工团小环境的特殊性,正式开启了文工团青春之会的序幕。
二是呈现剧中人物与铺设人物关系。萧穗子作为画外音讲述人,已经在电影开场通过声音显示了她在影片叙事中的重要性。在接踵而至的歌舞排练中,导演将她设置为领舞人,既展示了她优美舒展的舞姿,又为之后的叙事赋予了足够的人物权重。郝淑雯、陈灿等人物也在此处多次亮相,为接下来表现他们与刘峰、何小萍与萧穗子的关系,埋下伏笔。三是映衬主要人物与推进剧情发展。在这个舞蹈的前后,导演通过刘峰与大家之间的热情互动,突出了刘峰的好人缘、好性格,为这位欢情英雄的形象塑造奠定了基础。影片以多机位、多景别的运动摄影和流畅的无缝剪辑,将萧穗子领衔的舞蹈排演表现得荡气回肠、美轮美奂。文艺女兵的曼妙舞姿和青春群像,顿时跃然幕上,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观者的眼中,这道风景线恰恰与接下来何小萍的首次舞技展示,形成了美与丑的鲜明对照。何小萍以紧张笨拙的踉跄跌倒,完成了她在文工团的黯淡出场,也开始了她成为集体笑话的历史,为接下来剧情的发展,留下了故事的话头。
如果说《草原女民兵》的舞蹈之美,象征了文工团青春之会的华丽开场,那么告别演出上的《沂蒙颂》,再次以文艺兵们擅长的舞蹈艺术形式,以酣畅淋漓、壮怀激烈的抒情方式,为青春之会的散场画上了悲壮的句号,与前者构成了一种叙事上的审美呼应关系。这种呼应的复合性,进一步体现在与何小萍这个角色的勾连上。不难看出,随着《沂蒙颂》演出的展开,因战争而失忆的何小萍仿佛受到感染而产生了精神共鸣,来自记忆深处的艺术情怀在悄然萌动。导演将写意化的亮光打在她的脸上,以光线的明暗对比将她从观众群中超拔出来,打开了一个只属于她的艺术之境。何小萍旁若无人地走出剧场,在空无一人的户外草坪上,上演了一场象征灵魂复苏的生命独舞!她的这段场外之舞与剧场里战友们的群舞,形成了交相辉映、相映成趣的审美效果,彰显了扣人心弦的叙事引力和舞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包含着怎样的内涵呢?是在强调何小萍与文工团集体之间融合而又疏离的复杂关系?是在给出一个她如何挥去精神阴霾实现自我救赎的理由或者方式?是在强调舞蹈乃至整个艺术对人的心灵疗救与审美解放作用?是在言说青春记忆之于人生命成长的深远意义?还是揭示人的怀旧情结以及电影怀旧之美的艺术需要?也许都包含其中且又不止于此。
(二)剧中人的声音叙述:游走在虚实之间的故事缝合
对历史往事的客观化钩沉,尚不足以亮出一个艺术文本的怀旧腔调。如果意图渲染影片的怀旧特质,就需要在叙事时间上标识出过去与现在的分立,彰显出怀旧作为人的一种心理活动的回忆之境与反思之态。为了更好地营造怀旧的氛围,《芳华》在声音之维上,构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叙述人形象,而这个叙述人正是剧中的女二号人物——萧穗子。
那么,萧穗子的声音叙述具有哪些积极作用?表现出怎样的艺术特征?又存在哪些问题?她的声音叙述在片中出现了十余次,主要具有介绍人物形象与时代背景、预叙人物命运与关系、评说人物的心理与行为等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介绍人物与时代背景及其变化。电影一开场,她的画外音先声夺人,将故事发生的时代、环境以及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并提示了刘峰与何小萍的主人公地位及其未来的命运纠葛。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影像书写之后,她的画外音,接续交代了这一年中国发生的大事件以及主人公刘峰抗洪抢险受伤后的角色转变。“画外音在更大范围里发挥一种结构的作用。叙事的画外音可以随意地附着于开头的形象序列,解释形象和启动情节,此后便完全为视觉形象腾出空间”[2]213。
二是对人物命运与人物关系的预叙。在何小萍沦为文工团笑话和军装照引发冲突之前,萧穗子的画外叙述,都起到了预先知会观众、铺垫情节发展、引导心理期待、点化叙事重点的艺术效果。从后来的剧情发展来看,军装照事件是何小萍对文工团生活美好想象的跌落点,在影片中起着承前启后的叙事作用,不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萧穗子的预叙,在一定程度上提前吸引了观众的审美注意力,也分解了影像在这个事件上的叙事难度,为更加清晰明了地表达这个事件的前情后事以及何小萍的心理动机,起到了积极的审美作用。
三是对人物行为及其命运的反思与评说。这里边包括对刘峰、何小萍、林丁丁等人心境的推测和理解,对他们命运的暗示与评说,对文工团解散时的情感追思。不可否认的是,从表面上看,萧穗子的叙述是一种主观化的内视觉视角,但是细加探究,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着全知性的视角。这些叙述既有来自记忆深处曾经感受过、体验过或是听闻过的事实,也有无法确知和难以求证的大胆虚构。这种虚构可以看作是她事过多年之后的推知、忖度和想象,也可以看作是导演为了避免叙事的分裂感和叙事声音的杂陈,赋予她的话语权力。在刘峰冒着死亡危险看护战友遗体的那个长镜头处,萧穗子的画外音解读了他的内心世界,而在这段话语中出现了一个“也许”和三个“可能”,这样的语气和措辞无疑证实了它的虚构性。而导演对这个镜头的营造,运用了大摇移的跨时空转换,以镜头内的蒙太奇手法,将伤残的刘峰和正在歌唱英雄的林丁丁进行了穿越时空的缀接缝合,刻意突出两人的意义关联。画外音对影像发挥了补充解说的功能,成为导演全知式艺术把控的化身。
这样一来,萧穗子以真实的主观性和拟仿的主观化,彰显出双重叙述功能,在实与虚之间跨越和游走。但无论怎样,她都以剧中人的身份,带给观众一种不同于纯客观化叙述的情感基调。这份情感会一点点地打开观众的心门,引领观众一步步地从感动于身,走向情动于心,走向思动于魂。
(三)主人公形象:欢情、悲情与深情的立体化塑造
如果说电影对各种事件的叙述是艺术情境展开的延长线,那么鲜活而丰满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主人公形象)则是这条线上彰显故事魅力、拨动观众情思的闪光点。叙事的关键在于塑人,展现人情冷暖,表达人性冲突,突出形象的艺术感染力。
刘峰是导演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在文工团特殊而优越的环境中,刘峰一直是以热情助人、扶弱济困、无私奉献的“活雷锋”形象示人。他吃苦受累甘愿发挥“万金油”的作用,对何小萍、炊事班班长等人倾情相助,为了追求林丁丁而放弃进修提拔的宝贵机会等。严歌苓在小说中给他取了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雷又锋”。“雷又峰”的称呼很明显地体现出时代英雄人物对他的精神引领,不过,他的个人奉献行为更应该被看作是来自于阳光奔放的青春生气和善良柔软的人性之光。在发生“触摸”事件之前,在文工团青年男女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个和他们一起洋溢青春、同呼吸共命运的伙伴,又是一个值得他们学习甚至崇敬的“欢情英雄”。
从叙事逻辑上看,刘峰的命运裂变与林丁丁有着直接关系,而何小萍做出的命运抉择又深受刘峰命运变化的影响。三个人形成了富有戏剧性的命运锁链。如果说刘峰对何小萍的关心和抚慰,主要是源自人性之善的战友情,那么他对林丁丁的关心则夹杂着更多的私人化爱恋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导演书写这位“欢情英雄”的叙事明线,其实又是一条为他走向悲情之途而做铺垫的叙事隐线,因为这条线上每一次表现两人互动的剧作节点,正是刘峰最欢情的奉献时刻,也是他逐步接近悲剧命运的时刻。所以说,在文工团生活的叙事板块中,导演对刘峰形象的塑造,是在欢情的表象下孕育着悲情的内涵,具有在肯定中否定的哲性叙事深度。
在林丁丁眼里,刘峰是一个“好人”,却不是一个“爱人”。刘峰向林丁丁表白,并冲动地拥抱她,这给予对方的却不是爱的甜蜜而是突如其来的震颤。当林丁丁被指责腐蚀活雷锋的时候,女人的自尊和虚荣导致了她对刘峰的检举揭发。刘峰的典型性格使他走上英雄的道德制高点,也在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感中向女性屏蔽了个体的爱欲,注定了他在关乎身体之欲的情爱追求中一败涂地。自此,刘峰离开欢情的文工团生活,悲情地走向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前线。
影片对刘峰悲情之途的书写,主要分为浴血战场和海口受辱两大叙事板块。从第一个板块来看,为了更好地表现青春风云的变幻,为了凸显战争的残酷性与死亡色彩,电影用冷峻暗沉的影像风格,刻画了刘峰在突如其来的战斗中与死神的搏杀。战争内容的加入,展开了刘峰从平凡走向崇高的叙事界面,形成了他从“欢情英雄”向“悲情英雄”转化的分水岭。
刘峰形象的立体化展现,离不开何小萍这个女主人公的映照。与林丁丁迥然不同的是,对于何小萍而言,刘峰在她心中完成了“好人—恩人—爱人”三重递进式的价值升华。文工团里的刘峰是热血喷涌的欢情英雄,而何小萍却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悲情少女。在何小萍深陷孤独悲情的深渊之时,只有刘峰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去拥抱她被其他男性厌恶的身体,去抚慰她因父亲去世而伤痛的心灵。她从刘峰给予的战友情和温暖的救赎之中,感受到他身上的人性光辉。她对刘峰的感激之情也向着笃定而深沉的异性之爱蝶变。当刘峰离开之时,她那标准而纯正的军礼是对战友的感恩与祝福,那一句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可不可以抱抱我”的情感诉求,是想爱却不敢爱的羞怯,多年以后她对这个诉求的重提,更是在两人历经沧桑之后,痴心不改、此爱不变的深情与坚守。何小萍与刘峰在人生的舞台上、在欢情与悲情交织的节奏中独自舞蹈,于冥冥之中遇到彼此,或早或晚地将深情地投向对方,最终走向白首不相离的生命共舞。
(四) 时代变迁中的军旅青春消亡史
《芳华》讲述的是一代人青春怒放与消亡的历史。故事从“文革”结束前夕男女主人公刘峰与何小萍通过接兵而相识讲起,表现了他们在30年间经历的种种美好、欺侮、冤屈、苦难以及分离聚合,以二人在21世纪初最终走到一起、相濡以沫为结局。电影在历史的真实性和宽广度中,表现出一代人的青春流逝与命运转折,凸显了时代的沧桑巨变与人的悲欢离合之间的互文性关系。
影片第一个镜头通过整屏的巨幅毛主席画像,将观众的观影体验拉回到三四十年前。然后随着镜头从右至左的摇移,引出电影的两位主人公刘峰与何小萍。与镜头配合的是萧穗子的画外音,告诉观众20世纪70年代她在西南地区部队文工团服役,并交代了刘峰作为英雄是他们学习的榜样。至此,电影所指涉的年代可谓一目了然。而刘峰叮嘱何小萍政审表关于“革干”的身份,更强调了“文革”年代特殊的政治需要,强化了时代的氛围。
为了更好地凸显文工团生活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导演通过刘峰这个人物的塑造,起到了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艺术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刘峰扮演着时代讯息的传递者、文工团命运的预示者和时代大事件(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亲历者的形象。甚至可以说,刘峰是文工团这场青春之会的聚合者,也是它最终散场的拆解者。当刘峰带领文艺新兵何小萍回到文工团,这是他第一次象征性的“归来”。虽然从史实上看,军队并没有介入“文革”,但是,这场运动在当时的中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整个社会的典型性症候。导演借助刘峰归来的外界环境,为观众展现出这一时代氛围。
刘峰的第二次“归来”是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他去北京参加完抗洪抢险英模报告会回到文工团,这一次和上次相似,他又给大家捎来了家里的礼物,更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时代讯息。包括萧穗子在内的一批战友,他们被错划为“右派”的父母解放了,这预示着中国就要迎来新时期的曙光。
在刘峰与何小萍相继离开的前后,大时代的社会环境也正在发生巨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电影通过邓丽君歌曲在文工团的私下流行,含蓄地点出了这一历史性的社会巨变。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这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后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对外军事行动。随着时代的转折与战争的结束,军队以及相伴而生的文工团的命运也在悄然改变。当观众还在刘峰与何小萍感伤的拥抱中,品味青春凋零与伤痛的时候,导演将镜头顺势一转,展现出文工团青春之会的散场。
二、审美创新力:审美突破与审美主调
(一) 青春电影的审美突破
回首青春岁月,展现青春年华,已然成为近年来华语电影的创作热点。对于80后、90后这些观影主力军来说,青春影像更容易与他们的情感对接,引起他们的共鸣。导演冯小刚曾说:“‘芳’指芬芳的气味,‘华’指缤纷的色彩。这个名字充满青春和美好的气息,很符合我记忆中光彩的景象。”[3]这部承载着冯小刚青春记忆的电影,带给我们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
在和平与安宁的时代大背景下,关于青春的影像书写,已经远离了深重的苦难与死亡的逼视。像《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样表现“文革”年代前青春少年派的影片,有意地把年代的沉重虚化成朦胧的远景,甚至倒置为马小军等人展开青春狂欢和情爱狂想的舞台。《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匆匆那年》把表现的重点聚集在象牙塔里的大学生活,而远离世俗尘嚣的校园青春又过多地纠缠于爱与性的得失。情爱的求而不得或是得而复失所造成的错位与伤痛,会进一步弥漫到剧中人后续的社会生活中。一部青春片,似乎就像一部从校园情爱进行时到进入社会情难了的青春荷尔蒙激荡史。不能否认,一场场的青春电影场景里,也有因死亡突降而释放的悲情,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阮莞遭遇车祸,但是死亡的偶然性带来的仅是故事表层上轻飘的悲痛感,缺乏更深彻的艺术穿透力。大多数的青春片是将青春之痛降格为情爱之殇,将青春之美简化为爱情之醉,以追爱的小情调置换了青春的大格局,为观众呈现的不过是“小写”的青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芳华》拓展了青春的生面,以一种具有诗意般的现实主义手法,谱写了一种“大写”的青春。这种“大写”的青春并不是缺乏真实人性的大英雄主义赞歌,而是冰与火交融的青春。主人公刘峰从文工团的温室环境跌入惨烈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战场,体验了同龄人少有的苦难,在死亡的边缘向死而生。何小萍在对刘峰的追随中,主动去承载相似的青春苦难,诠释了爱的大义,在充满泥泞的青春之路上,完成了生命的浴火涅槃。在这种别样生动的青春状态里,我们看到了从生命血肉里流淌出的爱情憧憬与爱欲冲动;也看到了在青春生命融汇的集体里,充溢着真善美并且超越排他性爱恋的战友情;还看到了爱情幻想破灭后的苦难青春;更感受到从战友情升华为相知相恋的真挚爱情。
《芳华》以青春片为主导,糅合了战争片、歌舞片等电影类型的特征与元素,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当下青春片逐渐固化和窄化的内容,产生了丰富立体的审美质感,实现了青春电影的审美突破。《芳华》通过放飞激情的青春故事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老年观众再度唤醒过往的青春记忆,也使年轻观众在青春的共性中获得了审美共鸣;战争场面的精彩呈现,为喜爱战争片和枪战片的观众带来更多的审美兴奋点,更把包括对越自卫还击战老兵在内的特殊观影群体拉回到影院;歌舞内容具有“合家欢”的感染力,有利于激发更多潜在观众的观影兴趣。总之,《芳华》通过对刘峰与何小萍等人物的青春历程的描述,为观众展现了立体多维的青春格局,从正青春的歌舞齐欢乐到后青春的悲欢离合愁,烘托出青春淬火后的沧桑之美。
(二)消费时代的沧桑之美
人间正道是沧桑。沧桑之美萌发于生命的起落之间。沧桑之美生成的最佳起点,是人的生命力最旺盛的青春期。电影用唯美的影像为观众呈现了这段青春伸展、激情张扬的岁月。美好的情怀就像陈灿送给萧穗子的西红柿,鲜红而饱满、朴素而真挚。流淌在她嘴里的汁液,富含着荷尔蒙贲张的青春诗情。但是,如果《芳华》仅仅为我们勾画了文工团生活的优雅多姿和青年男女的明爱暗恋,那么它的审美格调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片并无二致,只不过爱风情雨今又是,换了年代而已。一个事物的内部总是包孕着自身的否定性。热血沸腾的青春终究只是人生大戏中的一幕,当电影把“正是橙黄橘绿时”的青春盛景铺展到极致的时候,刘峰的腰伤预示了以他为代表的文工团青年的命运渐变。从放弃去军政大学进修的机会到冲动地向林丁丁表白拥抱,刘峰的真情暗恋虽让观众同情惋惜,但也会深感于他的青涩与稚嫩。电影里被删掉的众人批斗刘峰的场景,更是无情地昭示了青春世界里的欢情英雄敌不过复杂世事的撞击。刘峰的命运开始逆转,被下放伐木连。青春的一起一落,戏剧的冲突由此加重,沧桑的美感开始皴染。
如果说,青春的感伤只是源于爱欲的陨逝,那这份感伤只是生命可以承受之轻,并不是生命难以承受之重。而唯有那份难以承受之重带给青春的深重印迹,才是沧桑之美的生命底色。青春本不该遭遇的战争苦难以及死亡的威胁,构成了刘峰与何小萍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重。战争的真实惨烈,生动地演绎出刘峰慷慨赴死的悲壮与甘于牺牲的崇高。在这种饱含苦难的战争际遇中,在悲壮与崇高的青春书写中,生命的沧桑之美深深地铸就。与刘峰形成审美呼应的是,承担救死扶伤使命的何小萍,用她奋不顾身的一跃掩护被烧伤的战友,完成了自我蜕变的英雄壮举,也实现了青春生命从青涩走向沧桑的转折。
沧桑的世事经历,也许会损毁蓬勃充盈的青春生命力,就像刘峰被战争夺去了右臂;也许会带给人生无法抹去的心灵创伤,就像何小萍被战争消解的记忆,但这恰恰是沧桑成为沧桑的过程。与死亡对决的终极创伤,通过超越青春承受力、融入青春改造青春性以及最终建构新的生命状态的三个环节,使刘峰与何小萍等人在青春的渐进线上绽放出生命的沧桑之美。“生命通过展示那种此时是被保护、被赞美而彼时又是在岁月的流逝和死亡中被毁灭的两面性,从而超越了自身”[4]31。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在影片结尾处,刘峰与何小萍深情相拥,他们的结合超越了世俗的婚姻与爱欲,是对青春的升华,对生命的重构。也许有人会从这种平淡中读出历经坎坷的无奈,笔者却更愿意相信这是看透世事的安详与渡尽劫波的超然,也是沧桑之美生成的最终归结点。
《芳华》的沧桑之美,不仅为局限于爱欲表达的青春电影注入了鲜活的审美生气,而且为怀旧文化增添了新的审美景观。在小鲜肉充斥文化场域的不良态势下,在平均雷同之美、矫饰炫亮之美大行其道的审美风潮中,《芳华》的沧桑之美以抗拒庸潮、抵制媚俗的强力反拨之势,为大众呈现了新的文化样本和审美样态,提供了更高层级的审美感动与文化感召,是一股积淀着情感厚度和生命深度的文化清流。对于种种文化偏失与审美乱象,沧桑美所代表的审美旨趣,虽不能说起到力挽狂澜的文化救赎作用,但它所凝结的文化情怀,值得珍视和推崇。
三、文化影响力:怀旧的文化印迹与文化助燃
影片通过多种视听元素的呈现,留下怀旧性的文化印迹。芳华小院、对越自卫还击战战场等主要场景以及剧中人的生活状态,明显地凸现出电影故事的年代感。特别是绿意葱茏的65式军装,展现出飒爽英姿的青春芳华,引发了强烈的怀旧联想。此外,电影还通过字幕的形式,标识了1976、1979、一年之后、1991、1995等时间点,进一步强化了怀旧的代入感。怀旧是一种守望美好记忆的情感留恋和心灵跃动,而音乐是最具有直击人心力量的情感艺术。所以,影片中大量歌曲音乐的巧妙运用,也成为调动观众怀旧情绪的亮点,比较恰切地体现出影片的青春怀旧主题。《芳华》先后使用了《绒花》《草原女民兵》《侬情万缕》《英雄赞歌》《送战友》和《沂蒙颂》等经典歌曲音乐,烘托出温婉动人的怀旧情调。邓丽君的歌曲《侬情万缕》,既含蓄地暗示了1978年,又以这位流行歌曲天后的声音召唤力,掀起了大众的怀旧心潮。韩红演唱的片尾曲《绒花》,是对影片主题的音乐诠释,更是对全片怀旧意蕴的凝聚与升华,令观众沉醉于怀旧感伤的情感之海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正如张颐武教授所说:“对《芳华》,我最喜欢的是韩红唱的片尾曲《绒花》,那曾是李谷一的名曲,也是电影《小花》的插曲。当年李谷一的歌声让我十分触动,但那声音今天听来简单纯朴,高亢中透出真情。而今天韩红的演唱却让人感慨无限,那种感伤中的依恋和难言的微妙,让人无语,让人沉迷。”[5]一位活跃在大众文化场域中的著名文化学者,毫不吝啬地表达出对今日《绒花》的偏爱,不应该被简单地看作是抒发个体好恶的私人话语,而是意见领袖代表大众发出共同心声的集体性文化认同。
诗意的怀旧不仅传递了繁复的美感,而且助燃了当下的文化怀旧潮。在2017年末,即将迎来2018年之际,“晒18岁照片” 的文化热潮,在微信朋友圈蔚然兴起。这种大众的怀旧性自嗨,最初的缘起,很可能是最后一批90后献给自己年满18岁的成人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活动在大众中的扩散流行,生动证明了它契合人心的青春怀旧表达,彰显了大众的怀旧天性。“一代代人绵延不绝地在心灵世界中回望昨天和重温旧情, 早已证明怀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存在,是人类如影随形的情感原型”[6]。2017年12月15日上映的《芳华》,在经历了国庆撤档的风波之后,于岁末重新登陆各大院线,虽然在出现的时间上早于这股怀旧潮,但我们却不能武断地将后者出现的根源归因为《芳华》的上映。不过,电影的青春怀旧气质确实助燃了怀念18岁的自媒体事件,为这个怀旧的冬天增添了一把熊熊之火。反过来看,自媒体的怀旧活动,明显受到《芳华》的启发和触动,而将18岁和“芳华”的意义关系,紧紧黏合在一起,无形中提高了电影的市场热度和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度。“芳华”一词迅速在媒体上蹿红,成为跨年流行的时尚热词。在我们举目可见的各种新闻、报道与社会话题中,“芳华”的符号能指及其意义所指,已然渗透到教育、旅游、财经、服饰、饮食、美容整形、家用电器等各大领域。毫不夸张地说,民众们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似乎都能发现“芳华”的魅影。这一切也许是机缘巧合的天注定,也许是恰逢其时的文化共谋,也许是宣发高手的营销妙计。无论原因为何,两者之间确实形成了一种奇特而真实的互动关系。
“社会通过话题关注的蔓延,于一部影片的市场影响如此巨大,正在一再被电影市场印证。……而这一影响之深,又说明电影真的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社交媒体”[7]。在媒介变革的时代,《芳华》的话题传播,鲜明地凸显出电影对媒介社交功能的催化效应。“芳华”作为时尚热词,仍在以高曝光率的态势,发挥着它的社会影响力。可见,《芳华》的意义已经大大超越了电影本身,正在以广泛的文化影响力,深深植入大众的文化思维,建构着当下的文化生态。所以,对一部话题电影的话题性及其影响的全面认识,应该融入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前瞻思考中。
四、结语
作为一部情怀电影,《芳华》以表现特殊历史时代的方式、怀念青春的角度和风格、塑造英雄的故事逻辑以及焕发出的整体美感,触及不同圈层观众的心灵痛点和敏感点,最终创造了中国文艺片的票房新高。在娱乐至死、资本狂欢和IP喧嚣的文化态势下,《芳华》再次证明了一个朴素的艺术道理:艺术应该到最真实和独特的人生体验中去寻找感动生命而无法忘怀的情感记忆,这份具有情感原动力的生命记忆是艺术原创性的保证,因为只有让自己感动至深的故事,才能揭示生命的真谛,才有可能去感动他人。而这份由己及人的生命共情,有助于激发褒扬抑或批判的冲动,成为话题蔓延和市场热卖的引爆力。《芳华》作为现象级电影,不仅反映出导演冯小刚的个人转型,而且昭示了中国电影文化与市场的新变化。关于它的言说,将伴随中国电影走进新时代的步伐而继续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