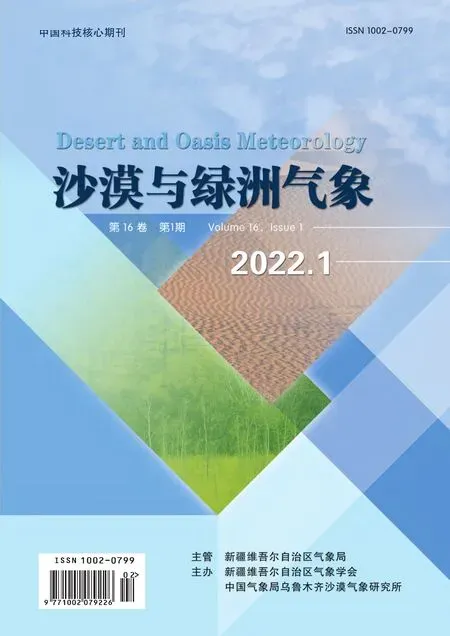博斯腾湖流域气候变化及其对径流的影响
2022-03-03吐尔逊哈斯木张同文尚华明喻树龙姜盛夏石仁娜加汗王兆鹏郭玉琳
郭 冬,吐尔逊·哈斯木,张同文,尚华明,喻树龙,姜盛夏,刘 蕊,石仁娜·加汗,王兆鹏,3,郭玉琳
(1.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中国气象局树木年轮理化研究重点实验室/新疆树木年轮生态实验室,新疆乌鲁木齐 830002;2.新疆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3.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4.阿勒泰地区气象局,新疆 阿勒泰 836500;5.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水资源是保障人民生产生活、保护生态环境及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性资源[1]。其中,河川径流是人类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末,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干扰,塔里木河流域出现了径流量减少、下游河道断流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2]。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地表径流产生显著的时空变化,进而影响流域水资源总量[3]。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21世纪末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在1986—2005年基础上将升高0.3~4.8℃[4]。我国西北干旱区处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5],气候变化对域内的影响更为显著。干旱区内陆河流域产流主要集中于山区[6],山区产流大小直接影响下游绿洲可利用水资源的多寡。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区域性内陆河径流演变规律与机理研究,已成为当前气候变化和水文水资源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7]。
新疆水资源80%以上形成于盆地周围山区[8],其中气温和降水量的变化对河流主要补给源有重要影响[9]。博斯腾湖流域是中天山南坡主要水系之一,其入湖径流主要来自开都河、黄水沟和清水河等。同时,该流域也是塔里木河“四源一干”[10]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开展博斯腾湖流域气候变化对径流的影响研究,对域内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11]、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绿洲农业[12]及塔里木河下游生态环境保护[13]等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围绕该流域的主要入湖河流已经开展了一些气候水文研究。研究发现,开都河上游径流呈明显增加趋势,其年径流量的大部分集中在夏季[14],并且径流变化与降水量的相关性强于气温、潜在蒸发等因子[15]。流域内夏季气温变化所导致的冰川融水变化也是影响其年径流量的重要因素[16]。基于对降水、地下水、河流、冰雪融水的同位素分析,结果证明分别处于天山南北坡的黄水沟和乌鲁木齐河流域在不同季节径流组成成分表现出较大差异[17]。对黄水沟径流变化的相关研究,还发现了黄水沟径流量季节间的不平衡性[18]。周京武等[19]通过对天山南坡黄水沟与清水河寒区流域的极端水文事件进行了分析,发现年内最大径流与夏季降水量关系密切,而最小径流与冬春季的气温关系密切。李玉平等[20]开展的清水河和阿拉沟流域径流变化气候响应研究,表明冰川的调节作用使得径流对气温变化具有一定滞后性。
考虑到降水和气温是气候变化的主要体现,气温的作用主要是加速山区冰川融化和影响流域蒸发量,而降水的作用主要是增加整个流域水资源总的补给。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博斯腾湖流域入湖径流和山区气候资料,探索不同气候因子对流域内主要河流年径流量的影响,并计算河流径流量对气候因子的响应模拟方程,以期为流域水资源规划利用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博斯腾湖流域地处中天山南坡的焉耆盆地,位于82°52′~88°23′E、40°44′~43°48′N[21],东部和南部为荒漠戈壁,北部和西部为天山山脉、那拉提山、霍拉山,流域地势是北高南低、西高东低,高山、峡谷和盆地交错,地形复杂(图1),是南疆地区重要的水资源区之一,流域面积4.54×104km2,海拔856~4 798 m[22]。博斯腾湖主要入湖河流有开都河、黄水沟、清水河等,流域内河流补给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及降雨。

图1 研究区示意图
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资料
本文气象资料选取了巴仑台气象站(42°40′N,86°20′E,1 738.3 m)1958—2012年和巴音布鲁克气象站(43°02′N,84°09′E,2 458.9 m)1958—2010年的逐月平均温度和降水量,数据来源于新疆气候中心;水文资料选取大山口水文站(42°15′N,82°44′E)1972—2010年、黄水沟水文站(42°27′N,86°14′E)1955—2013年和克尔古提水文站(42°25′N,86°53′E)1956—2013年的逐月径流量,数据来源于新疆水文水资源局。
2.2 研究方法
气温、降水量和径流量变化采用一元线性回归进行趋势倾向率估计。Mann-Kendall突变检验具有明确指出突变开始时间点的优点[23],运用Mann-Kendall突变检验对气温、降水量和径流量的年际变化进行突变检验。通过对气候因子和域内主要入湖河流径流量之间进行相关分析和偏相关分析,筛选出主要影响因子,并建立气候因子—径流量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3 结果与讨论
3.1 气候水文要素年际变化特征
巴仑台站和巴音布鲁克站年内最高月均温出现在7月,最低月均温出现在1月(图2a,2b);年内最大月降水量出现在7月,最小月降水量出现在12月。说明博斯腾湖流域山区气候夏季雨热同期,冬季寒冷干燥。巴仑台站全年和四季的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增温速率为秋季>冬季>全年(0.337℃/10 a)>夏季>春季(图2c、2d,表1)。巴音布鲁克站全年和四季的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春季和冬季气温变化趋势不显著;增温速率为秋季>夏季>春季>全年(0.231℃/10 a)>冬季。巴仑台站和巴音布鲁克站全年和四季的降水量趋势变化中,仅有巴音布鲁克站冬季降水量趋势变化达到显著性水平,并呈上升趋势,增加速率为1.48 mm/10 a(图2e、2f,表1)。博斯腾湖流域山区气候变化主要以气温上升为主,秋季气温增幅快于其他季节;而降水量增加趋势不显著,这与Xu等[24]1957—2002年开都河年径流量和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而年降水量变化不大的结果相吻合。由于年际降水量变化经历湿润—干旱—湿润的过程[16],因此其线性增加趋势并不显著。
博斯腾湖流域主要入湖河流年内最大月径流量出现在7月;开都河和黄水沟最小月径流量出现在2月,而清水河最小月径流量出现在4月(图3a、3c、3e)。结合图2a、2b可知,3条入湖河流的年内最大月径流量与其流域最高月均温和最大月降水量同步发生在7月,开都河和黄水沟最小月径流量发生时间相较于其流域的最低月均温滞后1个月,清水河最小月径流量发生时间则滞后于最低月均温3个月。除开都河和清水河春季径流量、黄水沟夏季径流量在线性趋势变化上不显著相关外,博斯腾湖流域3条河流在全年和其他季节的径流量变化均呈上升趋势(表1)。其中开都河春季径流量变化不显著是受上游春季气温变化较小,导致冰雪消融补给量无显著变化;清水河春季径流量变化不显著是由于最小径流量主要受冬春季气温影响,而清水河流域的冰川面积小于开都河和黄水沟[11,19,20],造成冰川融水在年径流量中贡献较小,使得其春季径流量变化不蒸发量增大从而抵消夏季降水量增加对径流量增大的作用。

图2 巴仑台站(a、c、e)和巴音布鲁克站(b、d、f)月平均气温和降水量的年内分布及年际变化

图3 开都河(a、b)、黄水沟(c、d)和清水河(e、f)月径流量的年内分布及年际变化

表1 博斯腾湖流域主要入湖河流四季气温、降水和径流量变化趋势系数a及相关系数平方r2
3.2 年代际气候水文要素变化特征
显著;黄水沟夏季降水量增加不显著,而冰川补给占比较低[17],所以可能存在流域内因气温升高导致的以当年4—10月为暖半年,11月—次年3月为冷半年[25]。由表2可知,巴仑台站年均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变冷,直至到达最低点(70年代为6.1℃),随后气温变暖至最高点(21世纪初为7.8℃);巴音布鲁克站年均温先变暖,然后变冷至最低点(20世纪80年代,-4.3℃),随后气温变暖至最高点(21世纪初,-2.6℃)。两站在暖半年均温从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持续变暖。巴仑台站冷半年均温20世纪50年代开始变冷,直至达到最低点(20世纪70年代,-4.9℃),随后气温变暖至最高点(21世纪初,-2.5℃);巴音布鲁克站年均温先变暖,然后变冷至最低点(20世纪80年代,-19.6℃),随后进入偏暖时期。博斯腾湖流域(两站)冷半年变暖趋势大于暖半年,符合新疆、甘肃等区域在冬半年气温上升快于夏半年的特征变化[26]。并且其年代际年均温和冷半年均温冷暖变化趋势一致,所以认为气温年代际变化主要受冷半年均温影响。从降水距平年代际可以看出,巴仑台站和巴音布鲁克站年降水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偏干时期,到80年代结束,随后进入偏湿时期,与我国内蒙古中西部20世纪80—90年代降水量恢复上升[27]、新疆西部暖湿化[28]等干湿变化趋势相同。

表2 巴仑台站和巴音布鲁克站气温和降水量年代际变化
采用多年平均径流量±10%浮动量作为判别年代径流量丰枯的标准。较多年平均径流量偏小10%定义为枯水时段,偏大10%为丰水时段,其间为平水时段[25]。如表3所示,博斯腾湖主要入湖河流在20世纪70—80年代处于枯水期,并在80年代达到最低值,随后年均径流量上升并进入偏丰时期,并与同时期天山北坡精河径流变化具有相同趋势[29]。结合表2,博斯腾湖流域主要入湖河流径流量年代际变化与其流域降水量变化趋势表现一致,说明降水量年代际变化是影响径流量年代际变化的主要因素。

表3 开都河、黄水沟和清水河年代际年平均径流量变化
3.3 气候水文要素突变检验
由图4a~4j可知,巴仑台站全年和四季气温突变年分别为1996、2000、2002、1996、1991年,巴音布鲁克站全年和四季气温突变年分别为2000、2004、1982(不显著)、1993、2005年。通过对巴仑台站和巴音布鲁克站全年和四季的突变检验,发现两站春季气温突变年均晚于全年气温,其中巴仑台站夏季气温突变年晚于全年气温,而冬季气温突变年则早于全年气温;巴音布鲁克站冬季气温突变年晚于全年气温,而秋季气温突变年则早于全年气温。巴仑台站全年、夏季、秋季、冬季降水量突变年分别为1986、1991、2001、1993年,巴音布鲁克站春季、夏季、冬季降水突变年分别为1982、1998、1992年,其中巴仑台站春季、巴音布鲁克站全年和秋季降水无显著突变年,巴仑台站夏季、秋季、冬季降水量突变年均晚于全年降水(图4k~4t)。博斯腾湖流域地处天山东部“暖干”中心和西部的“暖湿”中心[30]之间,气温突变检验均较为显著,但降水突变检验普遍没有气温变化显著,同时也说明研究区的气候变化以增温为主,增湿为辅。

图4 巴仑台站(a~e、k~o)和巴音布鲁克站(f~j、p~t)全年及季节气温(a~j)和降水量(k~j)突变检验
由图5可知,开都河全年和四季径流量突变年分别为1993、1993、1991、1996、1991年,其中夏季和冬季两季径流量突变年早于全年,春季径流量突变年与全年变化相同,秋季径流量突变年则晚于全年径流量;黄水沟全年和四季径流量突变年分别为1988、1984、1989、1992、1993年,其中春季径流量突变年早于全年,其他三季径流量突变年晚于全年;清水河全年和四季径流量突变年分别为1987、1988、1986、1988、1990年,其中春季、秋季、冬季三季径流量突变年晚于全年,夏季径流量突变年早于全年。结合图4,降水量突变年基本在各条河流径流量的突变年之前,而气温的突变年在年际变化和季节变化上普遍晚于各条河流径流量的突变年。表明博斯腾湖流域20世纪90年代之前径流量增加主要受降水量增加的影响,随后受气温上升导致冰川冻土加速消融,也加速了年径流量的增加,有研究表明夏季降雨量和气温变化是开都河径流量变化的主导因素[16],暖季降水量是其源区湿地的主要水源[31],也说明夏季气候变化是径流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3.4 年径流量与月气候因子相关性分析
为探讨开都河、黄水沟、清水河流域河流的年径流量与不同月气候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利用相关分析方法对开都河、黄水沟和清水河年径流量与当年、上一年中不同月份气温、降水因子进行分析。由图5a、5b可知,开都河年径流量与上一年6、9月、当年8、10月的气温因子和上一年7月、当年1、4、7、8月的降水因子呈显著正相关;黄水沟年径流量与上一年2、9、11、12月、当年1、11、12月的气温因子和当年4、6、7、8月的降水因子呈显著正相关;清水河年径流量与上一年1、2、9、11、12月及当年1、9、11、12月的气温因子和当年4、6、7、8月的降水因子呈显著正相关。

图5 开都河、黄水沟和清水河年径流量与月气候因子的相关分析(a、b)和偏相关分析(c、d)
年径流量由于受气温和降水量的共同影响,所以通过将年径流量和气温/降水因子作为相关变量,同降水/气温因子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排除其他气候因子的影响。通过偏相关分析(图5c、5d),发现与开都河年径流量变化呈显著正相关的气候因子增加了上一年8月及当年11、12月的气温因子和上一年8月、当年12月的降水因子;与黄水沟年径流量变化显著正相关的气候因子增加了上一年6月的气温因子和上一年7、8月的降水因子;与清水河年径流量变化显著正相关的气候因子增加了与上一年6、7月及当年10月的气温因子和上一年7月的降水因子,但与当年9月气温因子之间的相关性不再显著。结合相关分析和偏相关分析结果,开都河年径流量变化主导因子为当年8月气温(TC8)、4月降水(PC4)、7月降水(PC7)、8月降水(PC8),表明开都河年径流变化主要受4月及夏季降水、8月冰川融水影响;黄水沟和清水河年径流量变化主导因子是PC4、PC7,表明黄水沟和清水河年径流变化主要受春季4月和夏季7月降水影响。其中有研究表明开都河流域的中低山区(3 500 m以下)积雪在5月初基本融化[32],说明4月降水基本转化为当月的径流。综合博斯腾湖三条入湖河流主导因子,开都河受TC8影响是由于冰川融水补给的影响大于黄水沟和清水河。开都河、黄水沟和清水河出山口前的集水区面积分别是18 827、4 311和1 016 km2[11,19,20],冰川面积分别为4 384、23.8和5.64 km2[11,19,20],集水区中冰川占比分别为2.36%、0.55%和0.56%。冰川在开都河流域的面积和集水区占比都远高于黄水沟和清水河,这表明冰川融水补给在开都河占比较大。
3.5 年径流量与气候因子的模拟
为表征气候因子对年径流量的综合影响,选取相关分析和偏相关分析与博斯腾湖流域主要入湖河流年径流量均呈显著相关(P<0.05)的气候因子,使用后向剔除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式中,QKDH、QHSG和QQSH分别代表开都河、黄水沟和清水河的年径流量(108m3),TP2、TP11、TC8、TC12分别代表上一年的2、11月和当年8、12月的月平均气温(℃),PP7、PC1、PC4、PC6、PC7、PC8分别代表上一年的7月和当年1、4、6、7、8月的降水量(mm)。方程(1)的R2=74.5%,R2adj=69.7%,F=15.567,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方程(2)的R2=75.4%,R2adj=72.2%,F=23.998,通过0.001的显著性检验;方程(3)的R2=78.6%,R2adj=75.9%,F=28.832,通过0.001的显著性检验。由图6可知,模拟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

图6 开都河(a)、黄水沟(b)和清水河(c)年径流量模拟值与实测值
4 结论
基于气象水文观测资料,对博斯腾湖流域的气候变化及其对径流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博斯腾湖流域年际气候变化以气温上升为主,其中秋季气温增幅大于其他季节;降水量增加趋势不显著;同时期域内主要河流径流量持续上升。域内年代际气温变化主要受冷半年气温影响,年代际径流量与降水量具有同步变化特征。
(2)通过突变分析,研究区径流量20世纪90年代之前增加主要是降水量增加的影响,随后受气温上升导致冰川冻土加速消融也加速了径流量的增加。
(3)博斯腾湖3条入湖河流年径流量变化主要受4、7月降水影响。其中开都河还受8月气温和降水影响,同时开都河流域集水区冰川的面积和占比均大于黄水沟和清水河流域,表明冰川融水补给对开都河影响大于黄水沟和清水河。
(4)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建立的开都河、黄水沟和清水河气候因子—径流量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其径流变化过程,证明了博斯腾湖流域水文变化受气候因子的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