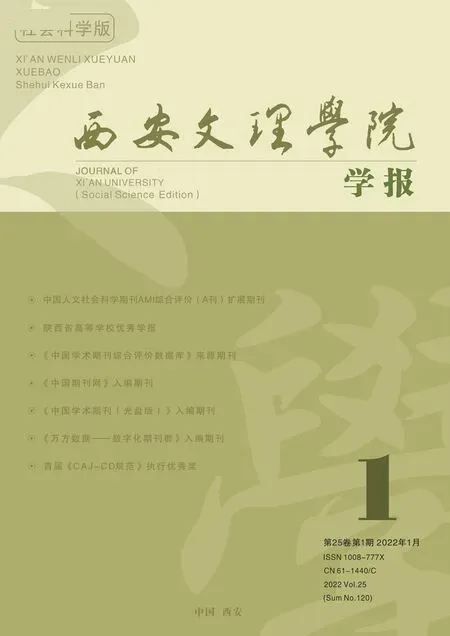西方《诗经》研究中的讽喻之辩
2022-03-02廉鹏
廉 鹏
(西北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068)
在跨文化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中,学者们都倾向于找到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诗经》中是否存在讽喻,成为《诗经》海外汉学研究中的巨大议题,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抑或是海外学者之间,甚至是中国学者之间意见也不相同,争论之势愈发激烈,因为“讽喻”并非中国本土文学研究的术语,而是取自翻译学,因此能否将外来术语与本国经典相结合,是海外汉学家和中国学者论证的关键。
一、《诗经》在西方的传播概述
(一)《诗经》在欧洲的传播
《诗经》在欧美的传播源自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学习汉学(遂僦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子五经皆通大义。《蒿庵闲话》),这是历史上西方人有记载的首次学习《诗经》,并且利玛窦以《诗经》为传教工具,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和阐释《诗经》。1626年,比利时人金尼阁首次用拉丁语翻译《诗经》,《诗经》的首个西译本诞生。17、18世纪以来,对中国《诗经》的研究主要在法国,法国成为了汉学研究中心,主要学者有马若瑟、白晋、赫巷璧、宋君荣等,并且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图像主义者”,用图像的方式宣传和阐释《诗经》。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研究达到顶峰,孙璋的《诗经》译本经汉学家莫尔(Julius Mohl)编辑成书,成为了西方第一个全译本《诗经》。随后,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也根据自己的想象,在不懂汉语的情况下转译了孙译本,虽然与原著大为不同,但却受众广泛,对《诗经》在西方的传播大有裨益,其受众从学术界扩大到了民间。1871年,理雅各的英译本出现,代表了《诗经》传播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事件,理雅各的英译本不仅用词准确,还带有完整的序言,成为了西方学术界对《诗经》研究的重要文本。之后,克拉默(Joham Cramer)的德译本(1844)、波蒂埃(M.G.Pauthier)的法译本(1872)、顾赛芬(S.J.Gouvreur)的法译和拉丁译本(1892)也受众广泛,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进入20世纪后,《诗经》传播和翻译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当属亚瑟·韦利的英译本和高本汉的《诗经注释》。尤其是亚瑟·韦利的译本,十分雅致生动,很多人认为其译本完全可以当作优美的文学作品来读。但是20世纪的《诗经》研究相较于前几个世纪发展比较缓慢,因为此时西方汉学家将研究重心放在了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上,开始转换维度来学习汉学,不急于一时阐释经典。总体而言,《诗经》是在西方传播最为广泛的中国经典之一,西方汉学家对《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俗学研究、语言研究、诗体研究以及政治学阐释这四个维度上,自16世纪至今,海外汉学对《诗经》的研究从未停止,并且一直在推进。
(二)《诗经》在北美的传播
《诗经》在北美的传播也很广泛,不过相较于欧洲要晚几个世纪,20世纪初期,美国才开始研究《诗经》。虽然美国研究《诗经》时间开始较晚,但因其强大的国力和学术资源,短短几十年便后来居上,成为西方汉学研究重镇,并且《诗经》的海外汉学研究重心也从欧洲转移到了北美。就译本而言,最为关键的译本是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孔子颂诗集典》(1954),以及麦克诺顿( Wenaughton)的全译本。就研究角度而言,北美的《诗经》研究主要分为语言研究、诗体研究和诠释研究三大类。首先,语言研究方面,代表学者是美国学者金守拙(G.A.Kennedy)和加拿大学者威廉·多布森(William Dobson),尤其是多布森的《〈诗经〉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Books of Songs),为《诗经》的语言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多布森创新点在于重虚词,其选取了几组近义词,如“言”“爰”“焉”等,研究其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含义。同时,多布森还通过不同时代、不同语体的变化来确定《诗经》中各篇的成书时代。其次,从诗体上分,代表学者是美国的苏源熙(Haun Saussy)和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苏源熙在《〈诗经〉中的复沓、韵律和互换》(Reception,Rhyme and Exchange in the Book of Songs)一文中,从《诗经》的篇章结构切入进行深层研究。同时,苏源熙也从“兴”的角度对《诗经》的隐喻进行探讨和研究。最后,从《诗经》的诠释学角度,代表学者是柯马丁(Martin Kern)。柯马丁的《毛诗之后:中古早期〈诗经〉接受史》(Beyond the Mao odes:Shijing Recept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从古代仪式的角度对《诗经》进行诠释。总之,《诗经》在北美的译介和研究以诠释学和文化分析为主,资料完备且成果丰富。
二、《诗经》与政治隐喻
《诗经》被认为具有讽喻色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具有政治隐喻,带有意识形态符号色彩。并且这种意识形态符号性是跨文化的,具有一种普遍性,是所有文本中都存在的问题,因此张隆溪先生在考察《诗经》的跨文化研究时,便尝试将《诗经》中的“兴”与讽喻联系起来,并写道:“讽喻,许多人认为对于希腊和西方而言是本质性的,可以成为跨文化知识的可能性的试金石。讽喻,即一个具有双重结构意义的文本,是否可以像在西方一样,有效地讨论和阐释中国的文本,换种方式说,它是否既可以在语言中翻译,也可以作为概念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1]。张隆溪先生为了寻求这种对等概念,采用了共时性研究方法,将中国文学中的“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的方式与西方的隐喻结合起来,在政治隐喻的维度肯定了《诗经》的这种讽喻性。政治隐喻即讽喻是张隆溪先生和苏源熙先生的基本观点,在他们看来,这种能指滑移的符号性是《诗经》构成讽喻的直接证据。
詹姆逊也将政治隐喻与讽喻结合起来,将所有的第三世界文学都归为“民族寓言”,从寓言性的角度来肯定这种政治隐喻,即讽喻,其言:“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必然性地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语言来阅读,特别是当它们的形式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2]。基于此,冯红也补充道:“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表面上关乎个人欲望(private libidinal dynamic)的文本——必然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出一种政治维度。”[3]60,并认为所包含“有意识的公开化的结构特点”[3]61-62。因此,从隐喻的角度看待文本,文本的空白指出才是文本真正含义的隐藏之地,这种文本空白之处的真正含义是排除了其他因素、消除了对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的依赖和关联而形成的。在文本的字里行间里,每行字都受到了来自符号系统的抑制,当我们进行文本细读,并关注于文本的空白之处时,便会发现这种症候,这种症候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泛化的指向。因此《诗经》中的“兴”是有固定指向的,是存在政治隐喻性的,是具有文本意义的双重性的,故讽喻不言自明。张隆溪先生继续补充道:“因为寓言的词源意味着‘谈论他人’,在阅读这篇文章时,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它。”(As allegory etymologically means "speaking of the other," in reading this we should then understand it as that.)[4]因此正是这种“谈论他人”,《诗经》中的指向意义是明确的,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符号性。如德勒兹所说,语言的共同体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的。[5]在德勒兹看来,每一条语法规则的本身就是权力话语的体现,是意识形态下所规定的符号模式,语言从不是用来使人沟通的工具,而是一种让人服从的命令式工具。所以,这种强制性和指向性打破了《诗经》中“兴”的泛化指向观点,强烈的意识形态符号性使《诗经》具有强烈的讽喻色彩。而这种讽喻色彩是《诗经》成为外交辞令和统治者之统治工具的根本条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精神的存在方式就是语言,他在《单向街》(GesammelteSchriften.7Bde.,in14Tl.-Bdn.)中写道:“精神存在中可传达的东西,就是其语言……精神存在中可传达的东西,并不最清晰地显示在其语言中,正如其于言说中‘过渡’;而是,这种可传达(Mitteilbar)径直是语言本身。”[6]本雅明认为,语言可以“传达”任何所思所想,是思维方式的直接体现,也是唯一体现。但本雅明忽略了语言的有限性,随后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开始研究寓言,并将寓言比作“底本”,开始探究语言背后的隐喻,这种隐喻即意识形态的另一种体现。可以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对此詹姆逊提出了其元批评(Metacommentary)理论,认为“每一个单独的阐释都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都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每一个评论都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元评论”[8]。詹姆逊旨在通过揭示这种意识形态无意识,来对权力话语进行祛魅。《诗经》也是如此,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其“兴”中的寓指不仅仅是文学上的余音绕梁和意义回味,是有明确的政治隐喻的,语言是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因此,《诗经》作为意识形态的经典文本,它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文化根本,代表着有固定指向的政治隐喻。所以在这一点上,《诗经》可以被认为是讽喻作品,可以套用西方的“讽喻”术语。
三、“美刺说”与讽喻之辩
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即《诗经》中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究竟是否具有先在性?即这种有固定指向的寓指是早就存在,还仅仅是统治者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捆绑阐释?刘毅青对此持否定观点,他从“美刺说”的角度和张隆溪进行了学术辩论。张隆溪对“讽喻”(Allegory)作出了定义,从古希腊词源的角度进行了阐释:“意为另一种(allos)说话(agoreuin),所以其基本含义是指在表面意义之外,还有另一层寓意的作品。”[9]苏源熙也赞同此说,认为“讽喻即说一个事物而意味着另一个事物,而不管这个事物说了什么以及意味着什么”[10]。但刘毅青不同意此论,其言:“有意将讽喻泛化,将其视为文学语言的根本特性,这等于说文学就是讽喻,实际上消解了讽喻自身的特性”[11]。刘毅青认为,语言文字本身具有复义性和游离性,这种语义的游离不能全部归为“讽喻”,这种泛化的“讽喻”是没有意义的讽喻。《诗经》的隐喻和讽喻是西方《诗经》研究的重点,如葛兰言在《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将《诗经》中的山川看作是最大的隐喻,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山川是人们心中的圣地,是一种神圣化的象征,故古代重大节庆都在山川举行,“山川之德只有靠君主之德发生效力”[12]。但这种隐喻是否等于讽喻,一直也没有定论,二者也不可化为一体,隐喻代表着一种多重阐释之下的意义,而讽喻是一种政治性极强的固定所指。而《诗经》恰恰是多重意义下的复杂文本,即使它有政治隐喻,但这种政治隐喻不占全部,甚至不能占据主体地位,完全是由第三方(统治阶级)来阐释的。并且《诗经》的隐喻,不仅出自他人的阐释,还出自文学性本身,是一种审美上的意义延伸,并非主观上的政治隐喻,所以把《诗经》的隐喻当作讽喻是略有牵强的。
如果将“兴”与西方讽喻作品的“讽喻”作直观比较,那么“讽喻”的本质可以理解为罗钢所言的“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13],是一种指向意义;而“比兴”的本质则是生发意义,即一种言之不尽、余音绕梁的独特意境,是一种“意味”的生发。从这一点来看,《诗经》中的“兴”是不能用讽喻来替代的,因为这种“余音绕梁”的独特意境如雅各布·霍温德(Jacob Hovind)所评价的那样:“留下简单的没有来由的话语和声音,无论文本哪里,都是道不清的,并且无人称化的‘叙述声音’”( Leaving simply words without source and voice without origin,the nameless and impersonal‘voix narrative’that speaks whenever literay texts happen.)[14]。这种无人称的叙述声音是对《诗经》中“兴”的巧妙评价,而“讽喻”是要一种直观的意指,否则将失去讽喻的意义。
脱乐性的出现是《诗经》政治化的标志,也是《诗经》具有政治隐喻的最鲜明证据。早期的古代宫廷礼乐,乐舞的重要性是高于诗的。[15]但《诗经》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开始具有脱乐性。《诗经》经过长时间的人为阐释,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象征,而不仅仅是一种礼乐之果。如毛宣国所言:“《诗大序》提出‘美刺说’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在于,在《诗经》 中本身就有一些诗歌,如变风、变雅,这一类诗歌所表述的情感与行为是在《诗大序》所强调的礼义规范之外的,是不符合《诗大序》所确立的道德教化主旨的。”[16]133显然,《诗经》很多作品已经不再完美地符合传统礼乐制度,但它本身的价值性不减反增,因为《诗经》更大的价值就在于它自身的阐释性,即上文所述的“意味”的生发。正如毛宣国所言:“《诗经》意义生成本身就离不开《诗经》阐释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规定性。离开了《诗经》阐释的历史,离开了《诗经》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经典文化体现的神圣性、符号性,《诗经》丰富的意义世界也不可能产生。”[16]134因此,作为意识形态下所被诠释的文本,不能简单地将其言外之意归为讽喻,可以说,这种美学作品可以看作是政治文本的一个附属品,任由统治者阐释,仅仅是一个带有美学色彩的工具。因此余宝琳的论述非常具有客观性,其将《诗经》的讽喻色彩概括为“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可见余宝琳的观点是一种折中状态,认为《诗经》在特定的语境之下具有讽喻性。
四、争论背后的原因反思
首先,争论的根源在于社会背景所发生的变化。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儒学在西方的传播,对《诗经》的阐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太宰春台《朱氏诗膏肓》对朱子的三大批判:第一,对“劝恶惩善”说的批判。太宰春台认为《诗经》所志者,乃“人情”而非“教义”。在《读朱子诗传》中言:“夫人情无古今之殊,则诗所以达之,亦乞有古今之殊哉。宋儒之于诗也,可谓谬矣。”[17]可见“诗道人情”是太宰春台对于《诗经》最本质的看法,太宰认为诗歌之源皆为言思言情,其极力还原《诗经》的文学本质,而非政治功用。并且太宰春台的学说也掺杂多种学说,例如其《经济录》里也包含道家、法家等思想,并非独尊儒学;如韩东育认为,太宰之思想含有“脱儒入法”之意[18]。第二,对朱子“弃序说”的批判。朱熹废弃《诗经》之序,令太宰大为不满。朱熹在《式微》中解释,认为序无可考,故可不论。太宰驳斥道:“虽有可疑者,然舍此而无所他考。”第三,对“淫诗说”的批判。新儒学除了主张经世致用,还有一个重大的思想主张,便是对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反驳。朱熹以“灭人欲”为利器强解《诗经》,将存有男女之情的几十篇诗歌归为“淫诗”,这是太宰春台所不能忍受的。因此,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时期阐释的主体会发生很大变化,所以阐释的结果也会大不相同。从这里可以看出《诗经》中的意识形态性及其隐喻的阐释多样性,这种隐喻是由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统治者所决定的,因此能否作为讽喻才有这么大的分歧。
其次,因为中西方传统语境不同,所以才会有此争论。《诗经》经典化的确立,实际上就是“讽喻化”的结果,但是一种断章取义式的讽喻,仅仅是纪廉(Claudio Guillén)所认为的“潜在可能性的机会”[19]。《诗经》的政治性在古代远大于其文学性,从汉代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诗经》的讽喻色彩必不可免。但由此将“兴”与讽喻混为一说,实在过于牵强,因为讽喻必须是主体的主观寓指,但《诗经》中的“兴”是意识形态下的权威阐释寓指。经学博士对《诗经》的阐释开始成为一种“绝对权威”,齐鲁韩三家权威皆为经学博士所致,皇帝诏书、群臣奏议中大量援引诗经,已经成为一种断章取义式讽喻,所想之言为了“礼”,必须有诗学出处。因此这种只重表面文本,忽视内涵的援引方式使《诗经》大量篇章至今仍有歧义,《诗经》的阐释并非具有主观性,而是根据需要而阐释。《诗经》的“兴”不能简单地与“讽喻”混为一谈,因为《诗经》的“兴”更多程度上是读者的解读,并非作者自己所想,完全是根据场合需要来解读,而西方传统讽喻作品则是作者主观上的讽喻。并且,如多布森(W.A.C.H.Dobson)所说:“另一种可能性,从歌曲本身的性质来看,一方面是礼拜圣歌,另一方面是求爱诗等,语言差异可能是由于古代汉语的等级和通俗形式造成的。”(Another possibility,suggested by the nature of the songs them-selves liturgical hymns on the one hand and courtship poems andthe like on the other-is that the language differences might be due to a hieratic and demotic form of Archaic Chinese.)[20]19-20因此,《诗经》中的“言在此而意在彼”形成原因庞杂,不能一概而论,很多寓指都不明确,都来源于主观的阐释。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诗经》的“内传性”。《诗经》的“内传文本”概念由柯马丁最先提出来[21],指《诗经》是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代代相传的,这种群体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这种内传性使《诗经》的解读具有两个鲜明特征:其一,这种师徒相传的内传性使《诗经》的解读单一化、意识形态化,其意义受正统政治观念影响;其二,这种内传性是由师徒相授,这就意味着是一种由老师到学生的单向传授,不能进行讨论,所以其意义更具有强制性。如葛兰言所言,这些注解都是强加硬塞而成,早已非《诗经》本意。[12]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诗经》背后的讽喻之争,不同的文化背景将概念强硬地照搬照抄,一定会出现排异和争论。
五、结语
国与国之间文化背景是不同的,若将外来术语刻意地与本国经典相匹配,就容易造成争论甚至是谬误。但不可否认的是,《诗经》中的很多篇目确实符合讽喻的标准,因此对于西方《诗经》研究的讽喻之争,我们要做的不是急于对此下定论,而是从总体化、辩证化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虽然《诗经》并不属于讽喻性作品,但其含有讽喻性质,“兴”与“讽喻”的区别不是质的区别,而是意义的外延程度的区别。虽然“兴”与“讽喻”并不相同,区别也很大,但《诗经》带有强烈的讽喻性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