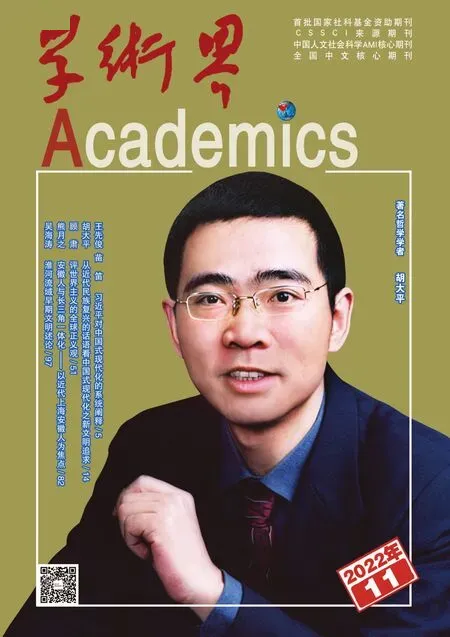北极公海保护区的治理模式与体系构造〔*〕
2022-03-02杨显滨
杨显滨
(上海大学 法学院, 上海 200444)
201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UNCLOS”)为基础,制定一项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以下简称“BBNJ”)的国际法律约束文书(以下简称“BBNJ协议”,也称“BBNJ协定”),以保护海洋的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1〕时至今日,关于BBNJ的政府间会议已召开五届,第五届会议已于2022年8月27日在纽约闭幕,〔2〕其对悬而未决的公海保护区治理等问题展开谈判,以求尽快颁布BBNJ协议。此外,国际海底管理局第27届会议第三期理事会已于2022年11月11日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闭幕,深海采矿涉及的生物多样性议题受到与会各国的广泛关注,但是否取得相关成果尚未公布。在此背景下,北极公海保护区作为公海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纳入BBNJ协议的谈判过程加以考虑,充分保护、利用北极海洋生物。但前提是,北极地区公海保护区的设置与治理是否因其独有的法律属性与其他地区公海保护区存在差异,从而须作出不同的制度设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具体路径为何。北极地区地缘政治复杂,各国权利主张交叉重叠,全球性、区域性与国内立法纷繁交错,选择何种恰当的治理模式来衡平各方利益,值得考究。此外,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关乎不同层级、不同海洋区域及沿海国与非沿海国的利益,如何剖析现有治理体系,取其精华,推陈出新,建立契合北极地区公海保护区自身特点的治理体系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亦是本文的难点。据此,BBNJ协议下北极地区公海保护区的治理模式与规范构造切中时弊,理论与实践意义可见一斑。
一、问题的提出
在BBNJ协议的政府间谈判中,公海保护区的法律制度构建等新议题不断涌现,相关讨论如火如荼。〔3〕因北极生态系统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该地区生物多样性养护与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尤为尖锐,建立公海保护区至关重要。然而受制于UNCLOS,北极地区与公海保护区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罅隙,主要包括北极公海保护区设立与治理两个方面的困境。
一方面,北极地区设立公海保护区存在障碍。一是遵照UNCLOS第87条,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各国在公海范围内有开展航行、捕鱼、科研等活动的自由。实现公海保护区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势必会限制各国的公海自由,进而引发“公海保护区的管辖权与公海的传统自由之间的潜在冲突”;〔4〕二是依循UNCLOS第76条第5款与第77条,沿海国可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三百五十海里的大陆架享有主权权利。然而公海保护区设立范围及于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二百海里外的海域。公海保护区与沿海国享有主权权利的大陆架存在海域重叠,公海保护区治理与沿海国主权权利行使之间可能相互掣肘;〔5〕三是审视UNCLOS第234条“将冰封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权和执法权从船旗国转移到了冰封区域外的沿海国”,〔6〕即北极沿海国可以通过国内立法制定北极地区的航行规则。北极沿海各国就北极地区公海的管辖权主张存在重叠与交叉,公海保护区的设立举步维艰。上述矛盾与冲突产生的关键在于,UNCLOS等国际条约尚未对公海保护区的属性作出明确规定,进而引发保护BBNJ与沿海国权利行使之间的冲突,其核心是权利位阶问题,主要体现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何者优先的问题。若前者位阶高于后者,旨在增强全人类的福祉,彰显的是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性;反之,公海保护区具有区域性,意在保护某个或某些国家的利益。有鉴于此,明确公海保护区的法律属性乃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北极公海保护区的治理面临困境。BBNJ虽进行了多轮谈判,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各国、组织、机构就公海保护区的治理模式问题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时至今日,战火仍酣。以欧盟为代表的组织与国家为避免区域治理模式下公海保护区治理陷于各组织、机构各自为政的囹圄,赞成全球治理模式。〔7〕以美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以全球治理模式下公海保护区治理难免流于政治化之弊为由,支持区域治理模式。〔8〕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国家出于对区域治理模式的兼容性与全球治理模式的协调性考量,支持混合模式。〔9〕各国对上述三种治理模式的主张均未着眼于北极独特的生态环境与地缘政治,无法契合北极的特殊需求。因海洋治理具有复杂性,且“北极在生态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10〕治理模式的选择应有别于一般海域。此等境遇下,单一治理模式恐难切合北极地区公海保护区的实际治理需求。我国应当集各家之所长,结合北极地区的“特中之特”情势,寻求合理、可行的治理模式。在中俄两国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可以BBNJ相关的政府间谈判为基础,协调UNCLOS关于国家管辖权的相关规定,明确公海保护区的法律属性与治理模式,尽快建立北极公海保护区,兼顾北极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二、北极公海保护区的法律属性定位
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保护区类似,公海保护区旨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有学者认为,公海保护区是“位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保护区,包括公海水体和国际海底区域”。〔11〕随着地中海、东北大西洋以及南大洋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海洋保护区突破国家管辖权的射程范围,延伸至公海,与公海保护区相混淆。BBNJ会议的召开将公海保护区再度置于风口浪尖。
(一)北极公海保护区具有全球性
“各国为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纷纷将目光投向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这就使得公海保护区的设立成为必然。”〔12〕与全球现有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保护区不同,公海保护区的范围仅涉及除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沿海国享有主权权利)之外的海域与国际海底区域。自2004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CBD”)第七次缔约方大会呼吁设立公海保护区至今,公海保护区的法律属性在国际社会层面尚未达成共识。在BBNJ谈判过程中,有部分国家指出,公海保护区作为区划管理工具,是规范某一特定区域的法律机制,强调公海保护区的区域性。其实不然,公海保护区的设立目的、法律基础以及合作方式均具有全球属性。
首先,公海保护区的设立目的是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2006年BBNJ工作组第一次会议报告指出,“公海是具有科学价值的区域和自然保护区,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13〕人类共同遗产理论“将人类作为一个单独的主体,在法律上认可了人类共同利益”。〔14〕为维护公海所承载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公海保护区应运而生。CBD第2条规定,可以为了“特定目的”设立保护区,如依据该法第8条(b)项、(c)项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由设立保护区。保护区作为公海保护区的上位概念,其设立目的同样适用于公海保护区,即为达到保护海洋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人类共同目标可以设立公海保护区。公海保护区有特定的边界与范围,但其养护海洋生物,实现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却惠及全人类。以渔业为例,海洋环境污染可能导致大量的鱼类死亡,渔业产量锐减,必将对赖以生存的渔民、地区、国家造成重创,这无疑造成全球鱼类市场的震荡。此外,“极具破坏性及不可持续性的捕鱼活动、来自船舶的航运污染及船舶撞击引起的海上航运事故、陆源污染……均导致海洋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海洋生态环境形势严峻”,〔15〕进而影响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公海保护区设立目标在于秉持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理念,以应对这些日趋严重的海洋问题,保护海洋环境、生物资源,造福全人类。因此,海洋保护区保护海洋生态、生物多样性的设立目的是全球性的、共益性的。
其次,公海保护区设立的法律基础是国际公约。BBNJ协议拟定伊始,即被视为“根据UNCLOS制定的一项关于养护和可持续利用BBNJ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16〕其规定的管辖、治理、监督等规则均应以UNCLOS这一全球性国际公约为基础进行构建。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大使在第61届联大全会上就BBNJ机制提出,养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和手段应该在UNCLOS和其他相关国际公约的框架内确定,需要充分考虑现行公海制度和国际海底制度,力争实现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利用之间的衡平,而不是简单地禁止或限制对海洋的利用。〔17〕公海保护区作为BBNJ机制下的划区管理工具,源于国际公约的授权,主要履行养护海洋生态的职能。〔18〕其作为BBNJ的重要措施和手段,理应受制于UNCLOS和其他相关国际公约,并在其框架下推进。UNCLOS第192条、第194条关于海洋环境保护与保全的规定以及CBD第8条关于设立保护区的规定均为公海保护区的设立奠定了法律基础。以国际公约为基础设立的公海保护区,对加入该公约的缔约国具有法律拘束力。与此相对的是设立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区域性海洋保护区,如1999年建立的地中海派拉格斯海洋保护区,其设立的法律基础是法国、意大利和摩纳哥于1999年11月25日签署的《建立地中海海洋哺乳动物保护区协议》。作为区域性协定,其效力仅及于此区域内的缔约国。“关于第三方遵守上述保护区管理措施的国家实践仍然相当有限”,〔19〕因而无法发挥公海保护区所具有的全球作用与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建立公海保护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最后,公海保护区合作方式的国际性。现有国际公约未直接规定公海保护区的治理方式,借UNCLOS关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可以窥见一二。UNCLOS第197条规定,“各国在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而拟订和制订符合本公约的国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时,应在全球性的基础上或在区域性的基础上,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此外,UNCLOS第199条、第200条以及第201条分别对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就海洋污染应急计划的发展和促进,海洋污染研究方案及情报和资料的交换,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规章的科学标准的拟定等事项的合作进行规定。面对UNCLOS规定的全球性与区域性合作方式,公海保护区应如何抉择,值得思索。对此,在关于BBNJ政府间会议第一届会议中,协调人Revell指出,公海保护区可以依靠“一些旨在合作与协调的全球一级决策”,〔20〕通过建立一个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全球性机构,实现公海保护区治理的有效性和一致性。我国学者亦指出,“由于公海处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公海保护区的认定、专设和管理不能被置于某一国家的管辖权之下”,〔21〕以避免集权化治理的弊端。由此,摆脱区域性合作下“专制”的藩篱,采取全球性的合作方式,顾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方为上策。故公海保护区防止海洋污染、养护海洋生态目的的实现仰赖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其合作治理方式正是公海保护区全球性的内化与昭彰。
(二)北极公海保护区具有区域性
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设立公海保护区的倡议提出前,区域性海洋保护区作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重要手段,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域性的海洋保护活动比全球性的活动更加可圈可点,在东北大西洋、地中海、南太平洋以及南极洲与南大洋都有相应的国际组织在负责区域的海洋管理与保护,这其中尤以OSPAR和CCAMLR的工作最有成效。”〔22〕与上述区域性海洋活动相似,设立北极公海保护区同样具有一定的区域性,主要体现在公海保护区的地理位置、管护主体与现实影响等方面。
一是公海保护区的地理位置处于特定区域内。随着传统海洋保护区突破国家管辖范围,其与公海保护区之间的界限被逐渐打破,外延相互交叉,在性质、特征等方面具有共通之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保护区定义为‘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手段,明确界定的地理空间’”。〔23〕“海洋保护区则定义为‘任何通过法律程序或其他有效方式建立的……区域’”。〔24〕保护区、海洋保护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位于明确的“地理空间”或“区域”。实践中设立的海洋保护区无一不限制于特定的区域内,例如2016年设立的罗斯海海洋保护区即位于罗斯陆缘冰之北,维多利亚地与玛丽伯德地之间(西经158°—东经170°)。有鉴于此,公海保护区可定义为在国家管辖范围外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栖息地或生态系统的特定海域。公海保护区亦限于特定海域之内,并非无界限。2009年设立的全球第一个公海保护区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海洋保护区亦位于南极半岛西部特定的凹形区域(Western Antarctic Peninsula-SouthScotia Arcdomain,WAPSSA)内。据此,有学者甚至采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保护区”这一表述,〔25〕以凸显公海保护区的区域性。
二是公海保护区的管护主体包括沿海国或区域性组织。“随着公海保护区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出于便利和成本的考虑,管护措施的落实将主要依靠地理相邻国家或者区域性国际条约的域内国家,即主要依靠沿海国。”〔26〕以南极海洋保护区为例,其“直接法律依据是《养护公约》第2条以及第9条第2款(f)与(g)项”。〔27〕其中,《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9条规定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针对生物资源养护的管制措施,包括确定捕捞区域和禁捕区域、区域和分区域等。南极海洋保护区内,生物资源养护等目的的实现仰赖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这一区域性组织以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缔约国采取具体的管制措施。无独有偶,作为大西洋第一个国家管辖海域以外的公海保护区,东北大西洋公海保护区的管护主要依靠《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以下简称“OSPAR公约”)。该公约设立了由15个缔约国政府的代表和欧盟委员会组成的东北大西洋环境保护委员会,意在凭借上述沿海国与区域性组织实施的管护措施,实现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的目的。〔28〕“从这个角度看,公海保护区的管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沿海国管辖权的体现”,〔29〕故公海保护区的管护措施的适用范围、实施主体等均限于公海保护区及其相邻国家范围内,无一不体现其区域性。
三是公海保护区的影响范围具有区域性。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指出,公海保护区是“区域生态系统规划和适应性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0〕公海保护区在实施上述生态系统规划、适应性管理措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着毗邻公海保护区的沿海国。以地中海派拉格斯海洋保护区为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涵盖公海海域的海洋保护区,其设立之初意在保护地中海海域内的海豚、鲸鱼等“海洋哺乳动物免受各种形式人类活动的干扰,其目标是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和谐发展与对生境和物种的保护”。〔31〕随后,派拉格斯海洋保护区设立的法律基础——《巴塞罗那公约》于1995年将其功能区域扩展至了缔约方内水。随着《巴塞罗那公约》适用范围的扩张,其影响范围亦呈现出扩大趋势。然而,时至今日,其影响范围仍旧局限于缔约国之内,具有区域性。此外,作为大西洋第一个国家管辖海域以外公海海洋保护区网络,东北大西洋海洋保护区网络的设立意在保护包括米尔恩海山复合区等7个区域内大西洋中脊的海山、脆弱的深海和物种以及生物栖息地等区域。〔32〕其治理多采取双边协调与合作模式。受制于该合作模式,公海保护区的治理直接影响着沿海国的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有一定的区域性。
三、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
自2015年联合国正式启动BBNJ谈判以来,各国就公海保护区治理模式的问题争论不休,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现有公海保护区治理模式主要包括:全球治理模式、区域治理模式以及混合治理模式。〔33〕其中,无论是多数国家所提倡的区域治理模式,抑或部分国家所主张的全球治理模式,均以现有海洋保护区为基础,探讨全球范围内公海保护区治理模式的应由之路,并未结合北极地区生态、政治等特殊因素对症下药。因此,北极公海保护区的治理模式仍有待明确。
(一)全球治理模式与北极公海保护区的区域性相冲突
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治理模式要求“建立一个全球决策机构,授权其确定、协商和采取保护性措施,这些措施由缔约方通过对其管辖和控制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管制来执行”。〔34〕全球治理模式排斥区域或部门机构建立公海保护区,而以缔约大会(以下简称“COP”)为决策机构,确保治理标准、手段、措施的一致性。王勇教授认为,公海保护区全球治理模式的构建须有尽可能多的缔约方加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只有数量足够多的缔约方加入,才能使缔约方大会更具有代表性,从而真正代表全体人类行使共同管理公海环境事务的权力。”〔35〕据此,公海保护区全球治理模式具有治理标准统一、决策主体众多以及治理手段模糊等特征,这与北极地区现有生态治理模式存在如下冲突:
一是统一的治理标准无法适应北极地区独特的生态系统。北极地区因积年冰雪覆盖、地广人稀等特征,并受全球变暖等因素的影响,其生态系统具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脆弱性与敏感性,“是世界上最脆弱的地区之一”。〔36〕该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对生物多样性养护提出了较高要求。以渔业资源的养护为例,UNCLOS第119条第1款(b)项规定,在对公海生物资源决定可捕量和制订其他养护措施时,各国应考虑到与所捕捞鱼种有关联或依赖该鱼种而生存的鱼种所受的影响,以便使这种有关联或依赖的鱼种的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其繁殖不会受严重威胁的水平以上。此规定为养护世界范围内的渔业资源提供的统一标准过于模糊、抽象,难以适应北极地区鱼类种群保护的特殊需求。2017年正式通过的《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Agreement to prevent unregulated high seas fisheries in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在UNCLOS构建的全球性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北冰洋中部沿海国家在养护和可持续管理北冰洋中部鱼类种群方面的特殊责任和特殊利益”,细化UNCLOS关于渔业资源养护的规定,以匹配北极地区生态系统的特性。此外,1991年签署的《北极环境保护战略》(Arct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亦在考量北极动植物群落的特殊性、当地居民与北极的特殊关系等因素的基础上,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采取预防和其他措施,保护北极地区的海洋环境。可见,全球治理模式下,为兼顾全球范围内公海保护区治理的共性,COP往往制定普适性的公海保护区治理措施。由此形成的统一的治理标准难以适应北极特有的生态环境。
二是众多决策主体致使北极公海保护区的治理效率低下。现有反对全球治理模式的国家认为,受制于全球治理模式对缔约国数量的要求,公海保护区的治理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统一的决议并执行。在BBNJ第一次预委会期间,挪威呼吁关注现有结构所带来的成本效益,例如海事组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区域海洋组织,而不是建立新的机构。〔37〕相较于依靠现有的区域性组织驱动的自下而上的治理方法,全球性治理须组建囊括众多国家、组织、机构的COP。上述利益攸关方追求的多样化利益使得谈判的难度陡然升高,从而导致统一的合作性行动难以形成。此外,全球治理模式下,北极公海保护区决议的作出受繁复、琐碎的表决程序与反对程序的影响,各国与各地区间就养护手段、标准等问题难以达成一致。以UNCLOS关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规定为例,UNCLOS第159条第5款至第10款规定了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的表决程序。其中不乏“过半数成员”“三分之二多数作出”“过半数成员”等表述。全球范围内签署并批准UNCLOS的国家高达152个,其中三分之二也已过百。协调各方利益,达成一致决议困难重重。全球治理模式要求众多缔约国参与决策,以确保决策的兼容性的诉求与实现北极公海保护区高效治理目标之间的矛盾不言自明。故北极公海保护区采取全球治理模式势必面临众多缔约国因各国之间的利益而导致决议难以形成的困境,治理效率低下在所难免。
三是北极地区公海保护区的治理手段由全球性的公约或协定等进行明确,难免流于抽象、模糊之弊。在公海保护区相应的国际法制度尚未完善的当下,UNCLOS与CBD等一系列现有的涉及利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为北极地区公海保护区的建立提供了法律框架。〔38〕以UNCLOS与CBD为例,其就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养护海洋生物资源所作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的概括规定,以适应全球不同地区海洋保护的多样性。CBD第8条、第9条关于就地保护、移地保护的规定,多为“促进保护生态系统、自然生境和维护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种群”;“最好在遗传资源原产国建立和维持移地保护及研究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设施”等倡导性、建议性的概括规定,缺乏具体明确的治理措施。“在订立协定时,缔约国之间总是存在着强烈的政治联系,因此不宜采取笼统地概括这种做法。”〔39〕为此,CBD第6条规定,各缔约国为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应按照其特殊情况和能力制定国家战略、计划或方案,或为此目的变通其现有战略、计划或方案。可见,全球治理模式下,具有普适性的公海保护区治理规则,难以兼顾北极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特殊性。
(二)区域治理模式与北极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性相冲突
相较于全球治理模式而言,北极地区公海保护区的区域治理模式着眼于区域组织在公海保护区治理方面发挥的决定性作用。BBNJ协议“仅为区域提供一般性的政策指导并且排除全球层面对区域的监督”,〔40〕具有去全球层面中心化决策、强调区域自治以及维护区域现有制度等特征。公海保护区区域治理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为区域治理主体闭锁、治理组织职能单一、治理对象有限等。基于此,我国部分学者通过分析公海保护区区域治理模式的局限性,指出区域治理模式难以实现公海保护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目的。〔41〕
一是北极地区治理主体的闭锁性致使利益攸关国难以参与公海保护区治理。现下北极地区的治理主要依靠以北极理事会为主导形成的区域治理机制。“以北极理事会为主体的区域治理模式充分体现了北极理事会在北极区域治理中的核心主导地位,其现行机制的成熟性也保证了当前北极地区的诸多权益争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可控的地位。”〔42〕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北极的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生物养护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仅依靠北极国家的单边和区域治理已不能有效应对上述北极问题”。〔43〕北极地区承载的全球性利益提出了适当平衡北极理事会和促进其与非北极地区国家(利益攸关国)广泛合作的问题。〔44〕然而,受制于北极理事会等北极区域治理主体(组织)的封闭性,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限于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环北极八国。中国等在生态、经济、政治等方面与北极地区存在密切联系的利益攸关国,难以直接参与北极地区的区域治理活动。这不仅违背了北极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性特质,更与公海是人类共同遗产的理念相背离。
二是北极地区区域治理组织的单一职能窒碍公海保护区多元化目的的实现。法学家Alex G.Oude Elferink指出,“区域模式意味着(几乎)没有来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初始安排,其执行将取决于现有的区域、部门框架”。〔45〕作为北极治理的政府间论坛,北极理事会在北极区域治理中起决定性作用。北极理事会成立宗旨之一在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此,自2011年以来北极理事会接连颁布《北极海空搜救合作协定》(The 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on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in the Arctic)、《北极海洋石油污染预防与应对合作协定》(The 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on Marine Oil Pollution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in the Arctic)等协定。然而,上述协定仅限于北极地区的海空搜救、石油污染等主题,并不关涉海洋生物养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公海保护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目的的实现不仅体现在如石油污染等海洋污染防治方面,也彰显于海洋生物养护等方面。随着北极理事会特遣组、北极经济理事会等工作组的成立,北极理事会机构的职能进一步完善与丰富,〔46〕但仍与海洋生物养护无涉,难以实现公海保护区的治理目标。
三是北极地区区域治理对象的有限性妨碍公海保护区设立目的的实现。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34条、第35条以及第36条的规定,未经非国际条约缔约国的第三国书面明示接受或表示同意,条约不对第三国生效。相较于UNCLOS“在海洋划界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上具有最普遍的效力”,〔47〕北极理事会颁布的各项文件“能否对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发生效力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选择”。〔48〕Torbjorn Pedersen指出,“北极理事会不是由条约设立的,也不是一个可以采取在法律上对其成员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或措施的机构”。〔49〕以北极理事会为主导形成的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体系尚且存在无法约束其成员国的可能,成员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自不待言。可见,在北极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区域性治理对象的有限性表现为,区域性治理相关的协定除约束缔约国外,对区域治理组织的成员国及其他国家均无法律约束力。如此有限的区域治理对象实难促进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目的的实现。
(三)混合治理模式兼顾北极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性与区域性
以日本、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国家率先提出公海保护区的混合治理模式。〔50〕公海保护区的混合治理模式强调区域性治理与全球性治理并行,由全球性组织与区域性组织共同参与公海保护区的设立与治理,并受全球性组织制约。〔51〕与单一的全球治理模式、区域治理模式不同,混合治理模式的提出结合了上述两种模式的优势与长处,弥补了全球治理模式难以兼顾区域特殊性,区域治理模式难以统筹各区域治理组织等短板。其可通过系统化的治理体系、多样化的治理方式以及全面化的治理主体,兼顾北极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性与区域性。
一是系统化的治理体系兼顾北极公海保护区的全球参与性与北极地区的特殊性。因北极公海保护区兼具全球性与区域性特质,单一治理体系已无法满足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的多样化需求,亟待构建多元、系统的治理体系。全球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实现仰赖多层级治理体系,〔52〕具体表现为,“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和广泛的协商合作来共同解决全球海洋问题”。〔53〕这正与混合治理模式加强现有区域治理组织的合作、协调,并强调全球机制的监督、管理的手段相契合。混合治理作为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折中办法,在维持现有区域治理体系稳定性的基础上,〔54〕回应了UNCLOS第197条在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基础上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规定,强调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双管齐下。混合治理模式中,全球性、区域性组织的介入,为北极公海保护区多层级治理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性组织,可借BBNJ协议对设立北极公海保护区的基础性规定进行明确;以北极理事会为代表的区域性组织实现北极公海保护区的特殊化治理;北极地区的各主权国家在现有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法律体系下,以国内法约束可能影响北极地区生态环境的行为,实现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体系的系统化。
二是多样化的治理方式统筹北极公海保护区的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以北极公海保护区系统化的治理体系为前提,不同治理体系下涌现出多样的治理方式,其中包括以国际公约具体规定为依托的刚性治理、以集体磋商为依托的柔性治理。有学者认为,国家域外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治理应当具有刚性,然而,相关国际谈判至今仍然步履维艰,各方立场严重冲突,难以调和,以至于诸多基础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柔化是大势所趋”。〔55〕全球治理模式下,公海保护区的治理通常采取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等刚性方式,难免受制于拟定协议的超长周期;区域治理模式下,通常采取集体磋商等柔性治理方式,却欠缺法律约束力。上述治理模式的缺陷与生俱来,难以避免。混合治理模式集各家之所长,力图充分发挥北极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性与区域性功能。作为全球治理模式的变体,〔56〕混合治理模式可取全球治理模式下协议的强约束力,补区域治理模式的柔性治理之漏;取区域治理模式下政府磋商的可变动性,补全球治理模式的刚性治理之缺。
三是全面化的治理主体兼顾北极公海保护的区域利益与全球利益。相较于区域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全球治理模式中的治理主体更为广泛、全面,二者各有利弊。因区域治理模式中治理主体的局限性,使得其在区域治理过程中,往往着眼于区域利益。以采取区域治理模式的东北大西洋海洋保护区为例,OSPAR公约的序言部分指出,缔约国在区域或次区域一级进行合作的原因之一在于实现同一海洋区域有关国家的共同利益。为兼顾北极公海保护区所承载的全球性利益,全球治理不可忽视。然而,一味强调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治理亦不可取。如前所述,全球治理模式下的公海保护区无法兼顾特定区域的特殊需求,难以因地制宜地实现特殊化治理,因而不能实现公海保护区所承载的区域利益。以联合国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为例,“《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鼓励各国在现有机构内采用指导原则和方法,而不参与系统或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制定”〔57〕的原因即在于此。混合治理模式下全面化的治理主体,既包括与公海保护区治理密切相关的沿海国,亦包括沿海国以外直接享受海洋治理红利的利益攸关国。全面化的治理主体有助于兼顾北极公海保护区所承载的全球利益与区域利益。
四、北极公海保护区的治理体系构建
北极公海保护区兼具全球性与区域性。因受多元主体、多重利益、多种手段等因素的约束,单一的治理模式难以兼顾北极公海保护区的双重属性,采取混合治理模式实属必要。在此等模式下,亟待构建合法、有效的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体系,“必须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提供充分的空间保护,并通过其他工具提供充分的保护,以确保世界生物多样性,并确保维持关键的生态系统结构和进程”。〔58〕
(一)建立以UNCLOS、CBD与BBNJ协议为中心的全球性治理体系
涉及公海保护区设立、治理的现有规定散见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巴塞罗那公约》等区域性公约、双边协议中,统领性的规定暂付阙如,系统化的治理体系尚未形成。对此,时任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马新民认为,“BBNJ国际文书在不影响现有区域性、部门性机构的职权和运作的情况下,……要确保BBNJ国际文书不能与现行国际法以及现有全球、区域和部门的海洋机制发生抵触和冲突”。〔59〕随着BBNJ协议拟定进程的推进,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面临的上述困境可以解决。构建以BBNJ协议为中心的公海保护区治理的基础性规则,应受现行全球性、区域性公约等的制约,尤其是UNCLOS与CBD。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以UNCLOS与CBD为基础构建公海保护区全球性治理体系。UNCLOS与CBD为当今海洋环境保护与生物资源养护提供了整体框架。〔60〕依循UNCLOS第192条、第194条,各国应采取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审视公海海域,UNCLOS第七部分第二节(第116条至第120条)就“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作出规定,主要涵盖各国公海上捕鱼的权利、各国为其国民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措施的义务等内容。CBD第2条、第8条分别就保护区的定义、设立以及治理措施等内容作出规定。前述规范覆盖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的原则性规定、公海生物资源养护与管理的具体规定,构成了由简至繁的法律体系,为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建立海洋保护区提供了国际法依据。〔61〕此外,UNCLOS附件八第5条第1款规定,涉及渔业、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海洋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争端可通过特别仲裁法庭予以认定。“由于前三类争端与未来执行BBNJ协定的目标的特殊关系……这些由专家组成的仲裁庭可以成为处理有关未来BBNJ协定的解释或适用的争议的专门主管机构。”〔62〕可见,为维护公海环境保护与生态养护标准的兼容性与协调性,公海保护区的设立与治理须在以前述规定为基础所构建起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我国在《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国际文书草案要素的书面意见》中亦指出,BBNJ协议是在UNCLOS框架下制定的国际法律文书,应符合UNCLOS的目的和宗旨。可见,以UNCLOS等国际公约为基础建立公海保护区全球性治理体系具有正当性。
二是发挥BBNJ协议在公海保护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已有国家依据国际公约在其管辖范围外建立保护区的先例,但无论是UNCLOS,还是CBD,都只是为公海保护区的建立提供原则性的精神导向,无法直接充当法律依据,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在全球适用的公海保护区法律规范。〔63〕在此背景下,“联合国大会于2004年通过第59/24号决议,成立了‘研究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通过在《公约》框架下缔结一份BBNJ国际多边协定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64〕在BBNJ国际协定谈判预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指出,“新国际文书可围绕养护和可持续利用BBNJ的总体目标作出规定”,具体包括“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应有明确的保护目标、确定的保护对象、具体的保护范围、适当的保护措施以及合理的保护期限等”。〔65〕此前举行的BBNJ政府间会议在充分关注BBNJ协议统领性作用、强调维持BBNJ总体目标的基础上,就公海保护区治理的范围、合作与协调、不损害邻近沿海国的措施、属于沿海国管辖范围的措施等核心内容展开充分讨论与协商,彰显了BBNJ协议在公海保护区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部分国家甚至指出,“BBNJ协议应反映对国家管辖范围外产生影响的活动的全球最低标准。”〔66〕作为UNCLOS的补充与完善,BBNJ协议对公海保护区的保护措施、后续监督审查程序等内容应作出充分、完整的规定,切实保障公海保护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与生物资源养护目标的实现,发挥其在公海保护区治理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二)借鉴波罗的海模式与OSPAR公约创设区域性治理体系
受制于海洋的一体性、流动性以及海洋边界的模糊性,〔67〕单个国家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充分应对、妥善解决流动性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为此,联合国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区域海”概念,“以生态为基础而不是以国家边界为基础的海域划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国家管辖范围限制”。〔68〕区域海洋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以区域国家间的合作为基础”。〔69〕“目前部分区域海项目已经将其活动范围扩展至公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也开始重视与BBNJ交叉议题的处理”,〔70〕地中海、东北大西洋以及南大洋三个区域海项目已经建立起的包含公海在内的海洋保护区便是例证。现有海洋保护区在区域海洋治理上已先行一步,可为北极公海保护区区域性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经验。
一是采用波罗的海模式构建北极公海保护区区域治理体系。“在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约的体系构建模式上,业已形成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体系、赫尔辛基公约体系和巴塞罗那公约体系这三种类型”。〔71〕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体系、巴塞罗那公约体系分别采取的由分立向综合渐进的趋势以及公约兼议定书的模式均无法回避北极的划界争端。赫尔辛基公约体系展现出由概括规制向具体规定演变的路径,具体表现为由《保护波罗的海海洋环境的赫尔辛基公约》作出原则性规定,再通过增加附录实现治理规则具体化。〔72〕相较于其余二者,赫尔辛基公约体系构建的背景与北极海洋环境治理现状最为相符,理由如下:北极海洋治理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是北极海域外大陆架划界争端。现有外大陆架治理模式无法妥善化解划界争端,北极各沿海国的外大陆架权益之争愈演愈烈,内水化治理之声此起彼伏,难以调停。在此背景下,北极BBNJ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赫尔辛基公约体系下,由概括规制向具体规定过渡的治理经验可为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提供借鉴。通过概括性规制回应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的原则性问题。解决划界争端后,再通过增加附录的方式对前述问题的具体解决方式进行规定。此举在有效解决北极公海保护区区域性治理体系缺失问题的同时,也为日后治理方式的细化留下解释空间。在BBNJ的政府间会议第四届会议中,确定公海保护区标准的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各国普遍承认需要设置明确的海洋保护区标准,但对设立标准的存在形式有不同看法。部分国家提出,“这些标准应列在指示性附件下,并由缔约方会议以决定的形式定期更新”,〔73〕得到众多国家的支持。此种凭借附件对原则性规定予以细化的模式与波罗的海模式不谋而合。从原则性规定到具体性规定的波罗的海模式契合北极公海保护区区域治理的现状,故可采用波罗的海模式构建北极公海保护区区域治理体系。
二是借鉴OSPAR公约中涉及公海保护区治理的相关制度,具体化BBNJ协议关于污染防治、环境质量评价、能力建设等方面的规定。OSPAR公约第1条规定,适用本公约的海域范围包括大西洋、北冰洋及其附属海洋位于北纬36度以北,西经42度和东经51度之间的部分。中北冰洋向大西洋延伸的部分亦受其规制。可见,北极海域治理与东北大西洋海域治理存在相似性。此外,作为建立全球第一个公海保护区网络的区域性公约,OSPAR公约将国家管辖外海洋保护区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74〕其关于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养护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国家管辖权外的公海。由此,借鉴OSPAR公约制定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的区域性公约具有可行性。OSPAR公约主要涉及缔约国的一般义务、海洋环境质量评价、防止和消除陆地等其他来源的污染、科学和技术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涉及污染防治、海洋环境质量评价以及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的规定对具体落实BBNJ协议谈判中产生的公海保护区治理、环境影响评价以及能力建设、技术转让等议题,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以海洋环境质量评价为例,BBNJ政府间会议第四次会议在制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全球最低标准或准则的过程中,亦呼吁缔约方会议与现有机构、框架、公约等法律文件协调,制定这些标准。〔75〕由此,北极公海保护区区域治理体系中环境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可参考OSPAR公约附件四第1条至第3条关于海洋环境监测内容、方式等规定,以统一国际公海保护区环境影响评价标准,实现公海保护区治理标准的一致性。
(三)遵循公海自由、适当顾及原则建构国家治理体系
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除上述全球性治理体系与区域性治理体系外,亦存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76〕通过由全球层级向区域层级,再向国家层级逐级递进的方式,细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规则,因地制宜地实现北极公海保护区的治理目标实属必要。UNCLOS第117条规定,“所有国家均有义务为各该国国民采取,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由此,各主权国家有权在UNCLOS与CBD等国际公约构建的法律框架下颁布公海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完善北极公海保护区的治理体系。北极公海保护区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北极公海保护区国家治理体系应依循公海自由原则,不得随意限制其他国家的公海自由。UNCLOS第87条规定,所有国家在公海均享有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方面的自由。各国对公海享有的自由是一种广泛的自由。然而,依据UNCLOS第117条与CBD第8条(b)项,于必要时,各国可制定准则据以选定、建立和管理保护区或需要采取特殊措施,构建公海保护区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养护公海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各国为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国家治理体系势必会对公海自由形成挑战。因为无论各国采取何种措施参与公海保护区治理,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他国家对公海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如何化解严守公海自由原则与公海生态环境养护之间的矛盾是构建北极公海保护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脱胎于海洋自由理论的公海自由原则,吸收了海洋自由理论中符合现代国际法理念的内容,又发展了海洋自由理论,是现代海洋法的重要支柱,不得随意变更或突破。在BBNJ协议的拟定过程中,针对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部分国家认为应以公海自由原则为基础充分利用公海生物资源。〔77〕部分学者亦指出,“UNCLOS规定的公海自由原则不仅是国际海洋法的基础,也是BBNJ谈判的基础”,〔78〕严格遵循公海自由原则与限制公海自由原则滥用,二者不可偏废。北极公海保护区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亦不得突破公海自由原则的限制,以防止国家管辖权的任意扩张,维持公海活动的稳定性。
二是北极公海保护区国家治理体系可以适当顾及原则合理限制公海自由,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公海自由作为一个因时而变、顺势而变的概念,自提出至今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从1958年《公海公约》规定的公海自由仅包括航行、捕鱼、飞越以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到UNCLOS增设科学研究以及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从二战以后海洋法的发展来看,无论是海洋自由内涵的扩大还是通过消极自由约束缔约方过度利用公海自由原则,公海自由从绝对自由走向相对自由,最终都显示出与现代自由理论一致的发展方向”。〔79〕公海绝对自由难以适应当今海洋治理的趋势,公海相对自由理念逐渐深入人心。UNCLOS第87条(c)(d)(e)(f)项对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建造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捕鱼以及科学研究活动的限制正体现了公海自由的相对性。此外,UNCLOS第87条第2款规定,这些公海自由应由所有国家行使,但须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公海自由,并适当顾及本公约所规定的同“区域”内活动有关的权利。Fernando Labastida亦指出,各国行使以上各项自由及国际法一般原则所承认之其他自由“须服从于《公海公约》第2条所列举的适当顾及其他国家在行使公海自由时的利益的原则”。〔80〕在适当顾及原则下,公海自由的相对性展露无遗。以此为前提,南极南奥克尼、南极罗斯海等海洋保护区的治理均对缔约方的捕鱼、航行等活动作出限制,同时为非缔约方规定了软法条款。可见,在适当顾及原则下,公海自由受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限制。前述国际条约、协议以适当顾及原则充分贯彻了公海相对自由理念。作为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最为直接、具体的手段、措施,国家治理体系须严格遵循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内立法细化与昭示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的基本原则,实现国际法的国内化与国内法的国际化。〔81〕故北极公海保护区国家治理体系可在不违反UNCLOS与CBD等国际公约的前提下,通过适当顾及原则合理限制其他国家在公海保护区内的活动自由。
五、结 语
作为北极治理的新命题与新挑战,北极公海保护区承载着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国家层面的海洋权益。各国、组织、机构在享受北极公海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养护所带来的红利的同时,亦应受到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体系的约束。世界各国以北极公海保护区为联结点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与中国所倡导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契合。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各国在北极公海保护区的利益错综复杂,其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北极公海保护区设立、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作为利益攸关国应以平等、互惠、发展为宗旨,切实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北极公海保护区治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积极参与拟定BBNJ协议的政府间会议,建言献策,助推BBNJ协议的尽快出台。充分发挥中国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国的作用,为北极公海保护区区域性治理体系的建构贡献中国智慧。在现有公约、协定的基础上,以国内立法回应北极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性与区域性治理体系,实现北极地区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生物资源开发的良性互动。
注释:
〔1〕See Revised estimates resulting from the decisions contained i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92,entitled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5/353/58/pdf/N1535358.pdf?OpenElement.
〔2〕中国绿发会:《BBNJ IGC5在第60次全体会议中胜利闭幕|绿会代表团讯》,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2290036491173520&wfr=spider&for=pc。
〔3〕参见杨泽伟:《中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40年:历程、影响与未来展望》,《当代法学》2022年第4期。
〔4〕〔78〕Yong Wang,“Reasonable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of High Seas by ‘Marine Protected Areas on the High Seas’:An Empirical Research”,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2019(2),pp.245-268.
〔5〕参见杨显滨:《“冰上丝绸之路”倡议下北极外大陆架的治理困境与消解路径》,《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6期。
〔6〕Kraska, James,“Governance of Ice-Covered Areas:Rule Construction in the Arctic Ocean”,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2014(3),pp.260-271.
〔7〕参见黄玥、韩立新:《BBNJ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问题》,《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8〕参见郑苗壮:《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谈判与中国参与》,《环境保护》2020年第Z2期。
〔9〕〔20〕〔34〕See Summary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4-17 September 2018,https://enb.iisd.org/events/1st-session-intergovernmental-conference-igc-international-legally-binding-instrument-12.
〔10〕A.R.Thompson,“The Arctic Environment and Legislation”,Alberta Law Review,1972(3),pp.431-439.
〔11〕付玉:《欧盟公海保护区政策论析》,《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2期。
〔12〕赵融:《公海保护区与沿海国外大陆架主权权利的冲突与协调》,《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13〕Summary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13-17 February 2006,https://enb.iisd.org/events/1st-meeting-bbnj-working-group/summary-report-13-17-february-2006.
〔14〕许健:《论国际法之“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5〕周江、徐若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项下海洋环境治理规则体系演变及中国应对》,《中国海商法研究》2022年第2期。
〔16〕Natalie Y.Morris-Sharma,“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Issues with,in and outside of UNCLOS”,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2017(1),pp.71-97.
〔17〕参见《刘振民大使在第61届联大全会关于“海洋和海洋法”议题的发言》,http://isa.china-mission.gov.cn/chn/xwdt/200701/t20070131_8200400.htm。
〔18〕参见邢望望:《划区管理工具与公海保护区在国际法上的耦合关系》,《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9年第1期。
〔19〕〔35〕〔40〕王勇、孟令浩:《论BBNJ协定中公海保护区宜采取全球管理模式》,《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5期。
〔21〕邢望望:《公海保护区法律概念界定》,《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年第2期。
〔22〕〔61〕何志鹏、李晓静:《公海保护区谈判中的中国对策研究》,《河北法学》2017年第5期。
〔23〕Reeve,Lora L.Nordtvedt,et al.,“The Future of High Seas Marine Protected Areas”,Ocean Yearbook,2012(26),p.265.
〔24〕〔32〕朱建庚:《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洋法律制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第101、116页。
〔25〕王金鹏:《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保护区的实践困境与国际立法要点》,《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9期。
〔26〕〔29〕张磊:《论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的关系》,《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0期。
〔27〕陈力:《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国际法依据辨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28〕参见桂静、范晓婷、公衍芬、姜丽:《国际现有公海保护区及其管理机制概览》,《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3年第5期。
〔30〕Donald C.Baur,W.Robert Irvin,Darren R.Misenko,“Putting Protection into Marine Protected Areas”,Vermont Law Review,2003(28),p.504.
〔31〕王琦、桂静、公衍芬、范晓婷:《法国公海保护区的管理和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环境科学导刊》2013年第2期。
〔33〕马金星:《欧盟参与南极海洋环境治理的路径及趋势》,《欧洲研究》2019年第6期。
〔36〕Jennifer McIver,“Environmental Protection,Indigenous Rights and the ArcticCouncil:Rock,Paper,Scissors on the Ice”,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1997(1),p.148.
〔37〕Julien Rochette et al.,“The Regional Approach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Marine Policy,2014(15),p.109.
〔38〕参见罗猛:《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的国际立法趋势与中国因应》,《法学杂志》2018年第11期。
〔39〕Yurika Ishii,“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the Repression of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 under the UNCLOS”,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2014(2),p.350.
〔41〕参见袁雪、廖宇程:《基于海洋保护区的北极地区BBNJ治理机制探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2期;王勇、孟令浩:《论BBNJ协定中公海保护区宜采取全球管理模式》,《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5期。
〔42〕章成、顾兴斌:《论北极治理的制度构建、现实路径与中国参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43〕〔48〕白佳玉、王晨星:《以善治为目标的北极合作法律规则体系研究——中国有效参与的视角》,《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2期。
〔44〕See Natalia Loukacheva,“Developments in the Arctic Council”,Yearbook of Polar Law,2014(6),p.347.
〔45〕〔54〕〔56〕〔57〕Alex G.Oude Elferink,“Exploring the Future of the Institutional Landscape of the Ocean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Review of European”,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2019(3),pp.240,241,241,242.
〔46〕参见夏立平、谢茜:《北极区域合作机制与“冰上丝绸之路”》,《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47〕秦树东、李若瀚:《新时期中国参与北极治理:身份、路径和方式》,《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49〕Torbjorn Pedersen,“Debates over the Role of the Arctic Council”,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2012(2),p.148.
〔50〕IISD:Summary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http://enb.iisd.org/oceans/bbnj/igc2/.
〔51〕“Earth Negotiations Bulletin IGC 1 Final”,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ttp://enb.iisd.org/oceans/bbnj/igc1/.
〔52〕〔76〕全永波:《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多层级治理: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政法论丛》2019年第3期。
〔53〕王琪、崔野:《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6期。
〔55〕张磊:《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柔化——以融入软法因素的必然性为视角》,《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58〕Kevern L.Cochrane,Jessica S.Sanders,Alexis Bensch,“MPAs:What’s in a Name”,Ocean Yearbook,2014(22),p.215.
〔59〕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研讨会专家观点集萃》,http://www.ysfri.ac.cn/info/1111/31503.htm。
〔60〕杨泽伟:《国际法史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25页。
〔62〕Eduardo Jimenez Pineda,“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of the Future Third UNCLOS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on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A Preliminary Analysis,Paix et Sec-urite International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21(9),p.16.
〔63〕桂静:《不同维度下公海保护区现状及其趋势研究——以南极海洋保护区为视角》,《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5期。
〔64〕施余兵:《国家管辖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谈判的挑战与中国方案——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研究视角》,《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1期。
〔65〕郑苗壮等编:《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国代表团发言汇编(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3页。
〔66〕〔73〕〔75〕See Summary of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7-18 March 2022,https://enb.iisd.org/marine-biodiversity-beyond-national-jurisdiction-bbnj-igc4-summary.
〔67〕张卫彬、朱永倩:《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构》,《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5期。
〔68〕全永波、叶芳:《“区域海”机制和中国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69〕李建勋:《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启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
〔70〕参见李洁:《BBNJ全球治理下区域性海洋机制的功用与动向》,《中国海商法研究》2021年第4期。
〔71〕韩立新、冯思嘉:《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以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为视角》,《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72〕参见刘天琦、张丽娜:《南海海洋环境区域合作治理:问题审视、模式借鉴与路径选择》,《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74〕李洁、张湘兰:《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规范的完善》,《中国海商法研究》2016年第2期。
〔77〕姚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意涵: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当代法学》2019年第5期。
〔79〕梁源:《论公海自由的相对性》,《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80〕Fernando Labastida,“Continental Shelf and the Freedom of the High Seas”,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1970(2),p.135.
〔81〕参见王建廷:《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新发展》,《当代法学》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