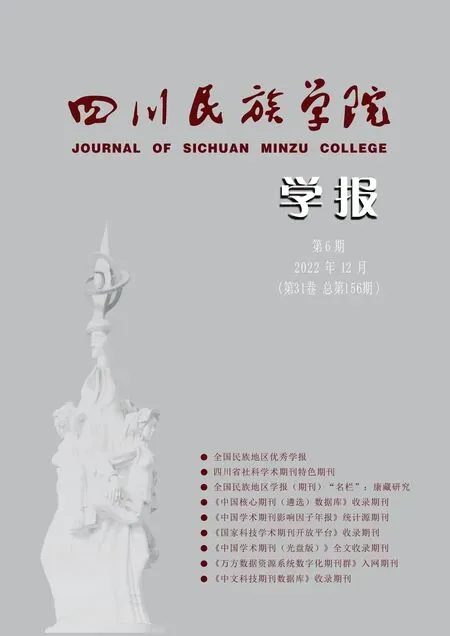西南局时期云南民族工作的历史考察
2022-02-27魏烁豪
魏烁豪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 400041)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大区一级行政区划建制。为加强大区领导工作,并推进西南地区的解放和建设,中共中央于1949年7月决定组成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对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和重庆四省一市实行全面领导。西南大区是一个多民族区域,而云南的民族关系更为复杂多变,其民族问题直接关系着社会转型、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1950年,邓小平在批复云南省委关于边界地区的工作方针时指出:“云南面前摆着三个重大问题:即国防问题、民族问题和土匪问题 ,但核心是民族问题,只有解决了民族问题,才能解决国防问题和土匪问题。”[1]389云南省委在西南局的领导下,坚持“谨慎稳重、长期工作、切忌性急”的工作原则和“民族和睦、民族团结,工作稳步前进”的方针,基于云南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成功地指导了云南民族工作的开展,促使云南各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日益改善、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民主政权得以巩固、经济状况持续好转、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从而初步奠定了云南民族工作基础,铺开了云南民族工作新篇章,并为日后云南民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笔者通过查考文献得知,郎维伟主编的《邓小平与西南少数民族》系统回顾和研究了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和思想,但对云南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提及较少;李东红等则从民族团结的角度,系统展示了新中国以来云南民族团结工作的实践经验和重要成果[2];马喜梅等从各民族互助发展、互惠共荣的维度,论述了新中国云南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实践与经验[3];方素梅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以云南和广西为例考察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的民主建政。[4]可见,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民族工作的研究侧重于民族关系、民族团结、民族文化、民主建政等某一方面,相对缺乏全面系统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民族工作的历史研究,而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下云南民族工作的研究涉及较少。因此,本文拟以西南局时期云南民族工作实践为考察对象,并从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视角,系统梳理展示云南民族工作的历史图景,力求揭示和探寻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实践轨迹与基本规律。
一、疏通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团结
处理好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地区的团结和稳定,是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是开展土地改革、巩固国防、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等工作的基本点。云南解放初期,各民族之间尚存多重矛盾。一方面,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深如鸿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少数民族土司政权与国民党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如在云南保山区,“土司对摆夷族(1)摆夷族,今傣族。实施‘愚民政策’以对抗国民党的侵入,国民党统治阶级通过伪政治局的种种活动夺取土司政权,造成土司与政治局之间的尖锐冲突。”[5]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地位和自我利益,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解放前,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纠纷。如“同饮一江水的傈僳族与白族、哈尼族与白族之间的民族纠纷”[6]208,使得民族之间相互戒备,甚至相视为敌。
因此,缓解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的任务迫在眉睫。邓小平与西南局高度重视民族关系问题,并把搞好民族团结视为西南民族工作的开端。1950年7月,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同时强调“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工作也就前进一步。”[7]164-165为此,云南省制定了“首先是联络感情,搞好关系,十分谨慎稳重,长期工作,切忌性急”的原则,确立“民族和睦,加强民族团结,消灭历史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工作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8]389,并通过培养民族干部、争取民族上层、组织民族参观访问团等举措贯彻执行。
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为各民族的团结与进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云南省通过组建云南民族学院和民族学院分院,培养一般区县的民族干部;在各专区开办民族干部训练班,并要求区县的领导机关把培养民族干部作为经常性任务,从而实现各地民族干部培育机制的专业化和长效性。在民族干部的任用上,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指出:“要大胆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不要要求过高,要耐心帮助提高,任何歧视性或打击的政策都是有害的。”[9]326这就决定了在实际工作中,不仅要稳妥,即不轻易调动少数民族干部中已经与群众取得联系的干部,而且要积极帮助和引导,促使民族工作干部树立长期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思想。为深入边疆农村开展民族工作,云南省委先后派出大量干部,“统一组织3000人的民族工作队,分赴保山、普洱、丽江、临沧、蒙自等地”[10]100,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深化党和各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疏解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步消除其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恐惧和戒备。
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对联系少数民族群众、安定社会秩序具有“牵头”意义。民族上层,是指各少数民族的土司、王子、山官、土司属官、大小头人、奴隶主和宗教领袖[10]100,在少数民族地区影响很大。为加强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云南省委采取“通过上层,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团结上层”的工作方针,并通过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而达到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的目的。为此,宋任穷特别指出:“参加代表会议的代表在开始时就是只有上层人物和土司头人参加也是好的,这对团结各民族只有好处而无坏处。”[9]320此外,云南省还号召曾受挑拨离间而流亡国外的少数民族上层回国,使其中一些民族上层担任高级干部,致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事业。
组织和选派参观访问团,为深化民族之间的感情、增强各族人民的爱国意识提供了契机。1950年6月,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祖国各地选派各民族代表,以组成代表团的形式参加北京国庆盛典。为尽可能争取具有重要影响的云南民族上层参加西南代表团,云南省各级人民政府和当地驻军通过大量的动员工作,使得西南局领导组织的西南代表团中,“云南代表最多,有53人,占全区代表总数的80.3%。”[8]233少数民族代表经过数次参观访问,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逐渐发生改变,这些变化日益影响到他们身边的成员,并由此带动整个民族观念的进步。
由此,随着民族关系的日益改善,历史上积淀的各种民族矛盾逐步化解,民族隔阂得以逐渐消除,民族团结大好局面基本形成。这极大地增强了各族人民对党和国家的拥护、热爱与政治认同感,为各项民族工作的实施和民族事业的发展打开了崭新局面。
二、清除残匪势力,安定社会秩序
近代以来,云南的封建势力和土匪势力根深蒂固。云南解放初期,人民政府的征粮征税工作直接触动其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加之当时国民党特务的煽动和利诱,他们同当地的旧军政人员、流氓恶霸和不开明的土司头人等混搅在一起,组成各种旗号的反动武装。这些反动势力在省内各地谋划和发动不同规模的土匪暴乱,严重时“全省土匪发展到250股4.5万人”[6]137,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造成极大损害。“1950年以后,帝国主义和逃亡国外的国民党残余军队通过各种方式,拉拢少数民族上层,挑拨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各族群众间的团结,向境内频繁进行武装窜扰,斗争十分尖锐。”[10]98其中“流窜云南中越边境马关、河口、金平等地的股匪与越南土匪周光禄合伙,组成‘滇南剿共救国军’,人数达2000余人”[8]357,并得到越南境内法国侵略军的支持,屡次窜回中国边境,骚扰破坏。在边境多股土匪的不断拉拢和挟持下,部分少数民族上层和群众加入土匪队伍,严重破坏民族团结,威胁国防安全。
因此,消灭土匪在内的反动势力是云南乃至整个西南民族工作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正如邓小平所强调:“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11]100为彻底消灭土匪,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剿匪委员会,建立起一元化的剿匪领导体制,并采取“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剿匪方针以及“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授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11]119的剿匪政策,为西南各省的剿匪任务提供了基本遵循。
云南省委按照西南局和邓小平的剿匪指示,制定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联防自卫,防匪保家”[1]389的剿匪方针。为坚决打破土匪和封建势力的各种抵抗行为,宋任穷提出“土匪应积极剿灭”以及“对土匪投诚、回头、立功者要宽大,坚决破坏抵抗则坚决消灭之”[9]137的剿匪策略。从1950年5月起,云南军区对滇西、滇南及昭通三大区域的大股土匪展开大规模围剿,先后剿灭“滇西人民义勇自救军”“云南反共救国军滇中独立师”“西南人民革命军尹武纵队”“反共救国军教导师”等土匪势力和封建武装。云南省采取“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9]365的方法,由军区部队和各族民兵相结合,组成联防武装,对流窜于中越、中缅边境的股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逐步进行清剿。
从1950年到1956年,同国民党残匪进行大小战斗4363次,歼敌约13万人,捕获特务1689人。[1]389西南局时期云南的剿匪工作,为云南匪患问题的彻底根除起着重大作用,使各民族地区基本实现社会安定,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革和民主建政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实行土地改革,促进社会变革
“土地改革是最后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最剧烈最残酷的阶级斗争”[9]412,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革命性转变,是一项破旧立新的社会变革。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特殊复杂,针对在民族杂居区是否开展土改的问题,邓小平于1950年11月明确指出:“在云南沿越南、缅甸、印度的国境边界各部落都不存在,在那些地方肯定是不能做的。”[11]2701951年6月20日,西南局特别指示云南省委,在民族杂居区实行土改绝不能采取群众斗争的方式,也不实行清算违法赔偿,而是通过召集民族代表会议讨论解决,采取协商调解、法院判决等方式进行。由此,云南采取先内地后边疆、先坝区后山地的改革步骤,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各项土改政策。
内地平坝区和低山区多为汉族居住的地区,其中少数民族有白族、回族、纳西族、壮族、蒙古族和部分彝族在内共约150万人。在这些地区存在坚实的封建地主经济基础,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汉族地区大致相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大纲》,在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的基础上,基本上实行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步骤。但对少数民族地主处理相对宽松,并按照 “当地培养出各民族自己的干部,通过他们去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土改”[8]395的前提条件进行,谨慎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始终注意民族团结,防止因政策或工作的操之过急而导致民族纠纷。截至1952年7月,内地坝区土改工作基本完成。
相对于内地坝区而言,内地山区则多为各民族杂居的地区,其中少数民族包括彝族、哈尼族、苗族、瑶族、傈僳族及部分白族、纳西族等在内约200万人。这些地区虽为封建地主经济,但由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政府工作基础非常薄弱;加之山区土地贫瘠,导致少数民族之间居住分散,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甚至还存在封建领主经济和农奴制残余;此外,由于恶霸、匪首等反革命势力在此盘踞,更是加重了土改难度。1952年7月中旬,在云南省委的组织下,内地山区土改采取比坝区和低山区更为宽松的政策,并“从解决政权问题入手,实行本民族地主由本民族农民斗争的方式,防止阶级敌人挑拨民族关系”[12]。在土改进程中,坚持先反汉族恶霸,先斗汉族地主。1952年底,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约500万人口的山区土改基本结束。
在总结内地土改经验的基础上,缓冲区土改也被逐步提上日程。所谓缓冲区,是在实行土改与不实行土改的民族地区之间划出交错地带,采取温和的斗争方式,从而避免因土改的阶级斗争引起民族纠纷。1952年5月,云南省委根据西南局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土改的指示精神,对缓冲区采取特殊的土改政策,从宽对待少数民族地主,只没收他们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禁止动刑或变相用刑等。随后,云南省委在划定出缓冲区具体范围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土改试点,并相继在全省的缓冲区推开。
最后,云南省委继续遵照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指示精神,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自上而下、和平协商的土改方法。然而,边疆地区尚有一些少数民族还处于原始公社末期,或处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1953年11月6日,云南省委向中央和西南局提出在这些地区不实行土地改革,也不划分阶级,而是在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政治上,妥善安排民族上层,建立健全乡村政权,设立“生产文化站”作为一级党政领导机构,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开展各项工作;经济上,率领直接过渡区的各族人民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努力发展生产,如“1954年,云南省最先在德宏区的景颇族聚居区试办了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0]104。从而使他们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
云南民族地区的土改工作,使得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关系实现了根本性变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分得了土地,摆脱了经济上的剥削和盘夺,消灭了几千年落后反动的剥削制度,彻底挖掉了剥削的根子。土改工作的完成,也使得民族团结空前增强,各族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开展其他各项民族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各族人民当家作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9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明确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并被视为解决西南乃至全国民族问题的钥匙。而云南民族种类之多,分布特殊,如何在云南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摆在西南局面前的一大问题。1950年7月,邓小平嘱咐云南省委:“区域自治应速实行。”[1]391鉴于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各民族地区普遍缺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邓小平鼓励各地干部要实事求是,大胆试验。云南省委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关于目前少数民族工作问题的指示》,“要求在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在民族杂居区要尽快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4]
分等级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和区域自治政府。针对各族人民普遍要求参加政权和在政府中的发言地位,云南省人民政府作为立法上和实际上的云南各族人民的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之下推行实施小的区域自治,即在民族杂居区的专区、县、区、乡均组织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划定各地方的行政单位时,“一般仍以习惯上的区域为宜,不必勉强以民族区分。”[9]320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推进,1951年5月12日,峨山彝族自治区正式成立,成为云南省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地方。随后,相继建立西双版纳傣族区在内的5个专区级民族自治区,边疆一线还先后建立了9个县级民族自治区和384个民族乡。截至1953年,全省共建立了普洱、蒙自、玉溪、保山、丽江、宜良等6个专区级联合政府,还相继建立了23个县级、33个区级、148个乡级联合政府。[8]397
按比例决定政府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各地政府根据各民族的人口状况,在各民族中物色和培养代表人物,由各族代表组成政府委员会,并参与政府工作,使其真正有职有权。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现行政治制度,人民政府则不予变更,并保留现有土司、头人的地位和职权;而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土司、头人,还可参加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在专属的政府委员会尚未成立之前,即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一些县通过组织民族事务委员会,以此保持和加强政府与各民族的联系,进而不断加强党和政府对边疆各民族地区的领导和治理。
云南各级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和区域自治政府的成立,政治上的平等,使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使人数较少的民族能够参与到政权管理中,体现了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原则,真正实现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
五、加强贸易工作,发展民族经济
在政治秩序得到巩固、少数民族民主权利逐步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强化民族贸易工作,构建民族经济新秩序,成为改善各族群众生活、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刚解放的云南,由于边疆地区工业品供应不足,其大部分民族地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贸易方式,交换中的不等价现象十分普遍。而汉族商人与少数民族群众不等价交换的情况尤为严重,如在云南怒江贡山县,一些汉族商人在少数民族群众不识戥子(2)戥子,学名戥秤,属于小型的杆秤,是旧时专门用来称量金、银、贵重药品和香料的精密衡器。也不识秤的情况下实施欺骗,傈僳族老人反映:“背一背贝母只算我们5-6斤,或者7-8斤只顶1斤”,“借汉人1块钱,每年要给5斗粮食,可能20-30年都还不清。”[13]69这些极不合理的商业关系和交换比例使少数民族的生活困苦不堪,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因此而倾家荡产。同时,这些贸易乱象进一步加重了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戒备和敌视心理,使得民族关系更加紧张和敏感。
为了彻底改变这些不合理的交易现状,邓小平于1950年7月提出:“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7]167-1681951年,西南局制定了“在增强、巩固民族团结,服从民族政策的前提下,积极稳步地发展民族贸易,扶持生产,保障供应,等价交换”的方针,以及国营民贸机构“有赔有赚,不赔不赚,不上交利润”的原则,[14]193从而为云南民族贸易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根据西南局历次关于少数民族工作方针的指示,云南省在具体贸易工作上因地制宜地制定计划,坚决贯彻。先是按照“要从吃盐、吃肉等小问题抓起,首先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的要求[1]393,应急供应少数民族普遍需要的食盐、针线、布匹、火柴等,并大力收购少数民族的茶叶、烟、麻布、皮货、药材等土产品;同时,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少数民族的贸易工作,在各地成立贸易机构,执行合理的价格政策,取缔不等价的交换比例和不合理的商业关系;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各级政府还通过举办物资交流会、建立贸易集市的方式,进一步搞活民族贸易。如在云南省昭通专区举办的土特产品展览交流大会,效果颇丰。为发挥干部在各项贸易政策和举措中的关键作用,宋任穷指出:“应号召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干部,学习贸易工作,结合群众组织供销合作社,去流通物资交流,贸易机关给予帮助和指导。”[9]324这些举措无疑为构建民族经济新秩序、实现民族经济新发展起到极大的助推作用。
在西南局的民族贸易方针指引下,云南民族贸易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商品的交换价格日趋合理,民族贸易秩序更加稳定有序,少数民族群众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实惠。民族贸易不仅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的经济联系,还从根本上改善了民族关系,大大增进了民族团结。同时,各项贸易举措使党和政府的各项民族贸易政策得到贯彻和落实,也为日后发展民族贸易积累了丰富经验。
六、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素质
旧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而一些民族的文化习俗直接影响着卫生进步,加之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人口健康和民族生存面临着巨大挑战。为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健康水平,1950年7月,邓小平提出:“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去那里办学校。”[7]168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的重要性。随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也特别指出:“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保障其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其风俗习惯,并帮助其发展医药卫生工作。”[15]这些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指明了根本方向。
医疗卫生方面,由于缺乏基本的科学医疗意识,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存在严重疾病威胁。在云南潞西县(3)潞西县,今芒市。1996年10月,设县级潞西市;2010年7月,潞西市更名为芒市。,摆夷族人民因笃信佛教,生病后只想出钱请佛爷念经,很少有人愿到卫生院诊病[13]196,导致患病后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疟疾、痢疾、温病、霍乱、天花、痧疹等各种疾病流行,缺医少药又是常态,无法治疗后便顺其自然,造成少数民族人口大量下降。另外,少数民族聚居区医疗卫生人员和机构严重缺乏。如云南省芒市卫生院地址狭小而污秽,只能容纳10个病人,全院仅1个医师,药品和医疗器具十分紧缺[13]197;永平县第三区第三行政村中,白家人约40户,土家族约1600余户,但仅有土家人草药医生1个和白家人草药医生1个[13]287-288。
从1950年到1952年,西南局和云南省委相继组织各级民族工作卫生队开展巡回免费医疗。针对云南边疆医疗卫生条件差的状况,邓小平亲自派西南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率200余名医学院学生和5名专家,赴德宏进行研究治疗和预防热带流行病。[8]397云南省在派出巡回医疗队的同时,还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卫生干部,提高他们的医务水平。为彻底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面貌,减少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各级医疗工作队积极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引导少数民族人民改变不卫生的陋习。如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人民消除了竹楼下边的粪便和污水,刈除竹楼周围的野草,消灭了疫病主要传播者蚊蝇繁殖的窝巢[14]196,从而有效控制了疟疾和其他严重危害少数民族群众身体健康的传染病,使发病率大为降低。在西南局的领导下,云南各民族地区还相继建立起县一级卫生医疗机构,开办卫生人员训练班。由此,各民族地区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逐渐完善,医务人员数量不断增加。
文化教育方面,刚解放的云南,少数民族的现代教育几乎是一张白纸,一些民族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也无保障可言。在云南鹤庆县,“入学的儿童全是民家族(4)民家族,今白族。民国时期大理地区将说白语的少数民族称“民家”,1956年确立称为“白族”。、汉族中农以上的儿女。其他兄弟民族的儿童普遍都不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13]108随着云南民族地区新政权的建立,少数民族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深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积极争取受教育的机会。然而,云南民族地区人才稀缺,从事民族教育的教员更是少之又少。加之多数民族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而有文字的民族,一般只有少数的上层头人和宗教人士会使用,少数民族群众文盲率很高。可见,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亟需发展现代教育。
1950年至1952年,云南各民族地区陆续兴建学校,并重点恢复原有的中心学校,而“一般学校则以民办公助的方针维持与恢复。”[9]324同时,在少数民族中推行巡回教育和半工半读的文化教育方式。各地在建校的基础上开设多种课程,如在普洱区民族教育中,小学课程各类课程所占比率为:文化课、卫生课、民族政策各占20%,地理课、历史课、自然课各占10%,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及共产党一般情形的介绍,占10%。[16]随着新建学校数量的增长和课程类型的日益丰富,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初步形成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体系。文化教育的普及使少数民族的教育观念也开始改变,如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人民也一改过去的做法,把子女送到政府办的学校去学习[14]197。1951年至1952年,云南省陆续专设初等和中等民族师范学校、师训班、技术学校,着力培养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和中等技术人员。经过培养后的各民族各年龄段的学员大多数回到基层工作,为推动民族教育进步、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云南各民族教育事业不断迈向新的坦途。
综上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对西南民族工作的领导下,云南省以“谨慎稳重”的各项民族工作实践,促使云南民族团结空前加深,民族地区社会总体稳定,各项民族事业稳步前进,各族人民生活日益改善。这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云南民族地区的良好形象和威信,增强了各族群众对党和新中国的向心力。西南局时期云南的民族工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中国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乃至全国民族工作的推进和民族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