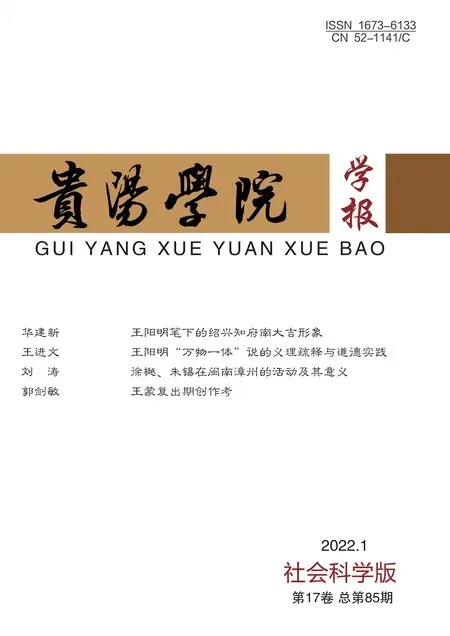王蒙复出期创作考
2022-02-26郭剑敏
郭剑敏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一、“复出作”:《诗,数理化》与《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
1963 年12 月,王蒙举家离开北京远赴新疆,一去就是16 年,这期间从乌鲁木齐到伊犁巴彦岱公社,再到乌拉泊五七干校,都留下了王蒙在新疆改造的身影。在1976 至1977 年的一段时间里,已从伊犁回到乌鲁木齐并在文联创作研究室工作的王蒙甚是清闲,只是做一些带有政治宣传色彩的工作,如编连环画、修改剧本,任务不重,闲暇时间较多,王蒙便将游泳作为主业。不过,1976 年以来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也使得王蒙看到了命运发生变化的可能,“都说1976 年把四个人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意义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但多年右派分子的身份及政治运动的冲击,使王蒙的处世态度变得十分谨慎。王蒙小心而忐忑地等待着命运转变时刻的到来,在后来所写的自传中王蒙记录下了当时自己的心境:“真正的日子渐渐来到了,我从一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然而我必须夹紧尾巴,我必须格外小心,我相信还有反复,还有曲折,还有坎坷……再不会以为从此天下太平,顺风顺水啦。我好像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一件娇嫩的宝器,我生怕由于自己的不慎而将宝器打碎,与宝器失之交臂。我已经痛感一切美好都是那样脆弱,而一切横蛮与困厄都是那样顽强纠缠乃至貌似威严。我不当出头椽子,我必须若无其事。但是我还是流露了我的压不住的快乐,以至于一些和我要好的亲朋好友,都善意地告诫我:天道无常,上心难测,慎重,慎重,第三还是慎重。”[1]2
带着对可能发生的转变的期待和判断,更是因着压抑多年的创作欲望在这种转机出现时的悄然而动,王蒙终于又一次提笔开始了他的创作。1977 年12 月,王蒙在乌鲁木齐写下了一篇千字散文,题为《诗,数理化》,文章主题是歌颂高考的恢复,他把这篇文章投给了《新疆日报》,文章很快在《新疆日报》副刊上刊登出来,这篇作品算是王蒙的复出作,它距上一次王蒙发表作品已过去了13 年。“我试探地写了一篇小文《诗·数理化》,歌颂高考的恢复。这篇文章在报纸副刊上刊登出来,时为1977 年12 月,距上次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春满吐鲁番》的1964 年5 月历时13 年多,加上1958 至1962 年的封杀期,1962 年至1964 年的半封杀期,我前后被冻结17年,半冻结4 年。”[2]这里用了“试探”一词,的确折射出了王蒙以及很多重回文坛作家彼时的创作心态。
《诗,数理化》是一篇千余字的短文,文章是围绕1977 年高考恢复这一事件而写的,作品起笔写道:“星期天我看到两个年轻人,一个在写诗,一个在做数学题,忽然感慨万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诗被戴上了‘黑话’的帽子‘枪毙’了,数理化也挂上了‘白专’的牌子被打入了冷宫。”在描述了“文革”中诗与数理化被抛弃、贬斥的命运后,作者着重书写了“文革”后那种诗意的生活的回归,以及在新生活来临之际对知识的渴望。小说结尾处作者写道:“诗和数理化,这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硕果,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们创造的人类文化的奇葩,在清除了‘四人帮’那几条蛀虫的祖国的沃土上,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阳光照耀和雨露滋润下,已经绽开了新花,万紫千红。幸福的年轻人,展开你为革命而学的金色翅膀吧,高声朗诵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伟大诗篇,向着四个现代化的明天,勇敢地飞翔吧!”[3]王蒙在其自传《大块文章》里这样谈及当年的这篇文章:“歌颂高考的恢复,指名道姓地歌颂当时的领导人华与叶,批判‘四人帮’的一切已被揪出示众的谬误,政治上没有一句自己的语言,没有独到的见解,如果说此文有任何可取之处,应在于我长久以来对于诗歌和数理化的兼收并爱。”[1]4但就是这样一篇短文,虽无独到之立意,但对王蒙个人而言却是意义非凡,因为它标志着沉寂已久的作家王蒙又回到了文坛。
《向春晖》是王蒙继《诗,数理化》后发表的又一篇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王蒙复出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该作发表在1978 年1 月号的《新疆文学》上。从内容上看,小说《向春晖》写的是清水县花园公社种子站技术员向春晖指导当地少数民族农民开展农业生产的事迹,故事的时间背景是1976 年初至1977 年。小说着重表现了向春晖这名汉族技术员如何扎根基层,在公社种子站带领当地农民抵制各种“左”的干扰,历经三年成功地繁育出了双杂交玉米良种,从而赢得了当地农民的信任,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小说采用不同身份、不同立场路线的人分别发声辩论的方式对当年的政治气候进行了直观的图解,故事的展开紧紧契合着当时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而进行组织。王蒙后来对这篇小说曾有这样的总结和评价:“作品有筋骨脉络,却没有肌肉神情,没有细节,没有丰满的生活情趣,没有气韵生动。但仍然符合当时的潮流,酷似当时的许多作品,意在笔先,大树先进,斗争激烈,合图合谱合辙,绝对不越雷池一步。”[1]4的确,历经多年的政治运动,王蒙深知写出“安全的”作品是最重要的,丰满的生活情趣、气韵的生动等等,这些都是次要的。可以说,王蒙彼时的创作心态颇具代表性,他的表述真切地反映了从“文革”结束到真正获得平反之前,那些头顶右派分子帽子的知识分子的微妙心态。王蒙在自传中曾记载了一件事,就是在那段忐忑不安地等待平反的日子里,一位右派作家口袋里装了两篇小说来到北京打探情况,这两篇小说一篇是批“走资派”的,一篇是批极左的,根据政治风向的情况,择机而动。这个细节颇有意味,文学创作在这里成了投石问路的道具,也成为政治动态的风向标,等待复出的右派作家的微妙心理,以及历经运动后的复杂的政治心态从中可窥一斑。经过多年的政治运动,右派作家们大多在政治上变得敏感而成熟起来,这种成熟表现在待人处世上的慎重,在政治上的谨言慎行,在写作上对中心政治的自觉迎合。
因在《新疆日报》和《新疆文学》上连着发表了两篇作品,王蒙受到了时任《人民文学》编辑向前的注意。1978 年的一天,王蒙收到了《人民文学》编辑向前的约稿信。在《王蒙自传》里,王蒙特意记述了当时收到这封约稿信时自己的感受:“那个年代,能不能上《人民文学》,能不能得到《人民文学》的约稿,竟然成为行情,不,甚至是等级与身份,是命运的通蹇祸福的标志。”[1]5正因如此,王蒙深知这次亮相的重要性,对应该将一篇怎样的作品投给《人民文学》有着慎重的考虑:“对于《人民文学》,应该写点什么,才能表示出王某仍然宝刀未老,仍然不辜负所谓‘有文才’的‘最高’点评而毕竟又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的王蒙,很有些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呢?”[1]5历经多年的运动,王蒙深知当然不能再像当年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那样锐气锋芒,而是已经历练得老到成熟了。王蒙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想法:“与五十年代的写作相比,这时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样的了,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不是艺术的酝酿与发酵在驱动,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以政治的正确性为圭臬,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为第一守则乃至驱动力,把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形象记忆视为第二原则,视为从属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这样艺术服务政治,应能充分运用自己前后十多年在新疆的体验,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与维吾尔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写出又‘红’又专的新作来。”[1]5经过反复的斟酌,最终王蒙向《人民文学》杂志呈上的新作便是小说《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而这篇作品被王蒙自己视作复出作。
小说《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写的是新疆一个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的故事,表现的是“文革”后期乡村基层政治生活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从而对极左路线的危害性予以揭露和批判。小说主人公铁木耳(维吾尔族)是生产队的队长,他作风踏实,不搞浮夸风,不弄虚作假。而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谢力甫专营权术,热衷搞阶级斗争。小说开篇从1975 年春写起,围绕到州里开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报材料的情节,引出了谢力甫和铁木耳之间的分歧。天性幽默、正直的木匠莱提甫给自己收养的一只凶悍野猫取名为“吕后”,讽刺的正是谢力甫等人所竭力推崇的法家代表吕后,实则是对当时所搞的尊法批儒运动的嘲讽。而“半截筷子”的典故来自流传于维吾尔族民间的一个笑语,讽刺的是那种不务正业、喜欢背后搬弄是非的人的卑劣行径。作品虽然有着主题先行的痕迹,但能在对特定时代路线斗争的叙述中融入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的描写,显得较有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作品的政治色彩。这篇小说的发表对王蒙个人而言意义非凡,虽然当时作家还远在新疆,但作品在《人民文学》刊登出来,已有着全面回归文坛的意味。王蒙的妻子崔瑞芳在其《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一书中记录了这篇作品发表时给他们夫妻俩所带来的那种激动与兴奋:“1978 年6 月5 日,我在办公室随手翻开第5 期《人民文学》,上面竟赫然印着王蒙的名字,《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发表了!我马上放下正在批改的作业,抱起那本杂志就往家里跑。天正下雨,我把杂志揣在怀里,浑身上下淋成了落汤鸡,杂志却安然无恙。离家门还有八丈远,我就放开喉咙大叫:‘王蒙,你看,你的作品发表啦!’……王蒙正包饺子,拿沾满面粉的手一把把杂志抓过去,嘴里念念有词:‘真快!真快!’20 年了,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兴奋——他终于回归了他的本行!”[4]
上述作品《诗,数理代》《向春晖》《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构成了王蒙复出之际第一阶段的写作。这个阶段王蒙的处境有两个特点:一是身处新疆,二是“文革”虽已结束,但王蒙还没有获得平反。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王蒙写作的特点在于紧跟政治形势,作品在取材上把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是一种典型的主题先行式写作。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情节展开中所涉及的尊法批儒、反击右倾回潮、农业学大寨、高考恢复等等事件和运动的书写,其故事的时间背景锁定在1975 年至1977 年“四人帮”下台前后这一段时间,而其中又将对毛主席思想的歌颂作为主线,将在华主席领导下打倒“四人帮”作为故事的结局,所写所述都凸显当时的大政形势,并不做更深远的历史追溯,也不在政策形势的表现之外做更深的探讨。另一方面,在政治主题为先的写作理念指导下,作者自身也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基本处于隐身状态,可以说是一种“无我”的写作,所谓的知识分子话语、主体意识、历史反思等在这一时期的写作中无从谈起。总体上来看,评价这一时期王蒙的创作,艺术上是否完美、作品内蕴上是否丰富都还是其次,最为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又开始写作,开始发表作品了,这种回归,这种重新被文坛认可和接纳是最为重要的,这构成了王蒙在复出期第一阶段最为显著的创作心态。也因此,在迎合时政的主题先行式的叙述中,我们依然能够读到王蒙内心深处的那种压抑不住的欢欣,因为一切都预示着新的转机的开始,无限的生机正在蓬勃展开。
二、复出期第二个阶段的创作:从《最宝贵的》到《布礼》
小说《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的发表,既标志了王蒙向中心文坛的回归,同时也可以说是他在复出期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之后,他开始从最初的那种政治主题先行的“无我”式写作,逐渐向敞开心灵、言说自我、审视历史、凝视现实的方向转移。这种转移带来王蒙复出后创作上的一个喷发期。
1978 年6 月,王蒙应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邀请赴北戴河团中央疗养所去写作,虽然还未获得平反,但此时对于王蒙而言生活已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等三个月疗养结束回到北京后,已是“八面来风,五方逢源”[1]23。这一年先是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2 月5 日,由《文艺报》和《文学评论》主持,文艺界在北京新侨饭店开了一次会,为许多人的作品落实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转年春天,王蒙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的改正。很快,北京文联负责出面联系,把王蒙调回北京,夫人崔瑞芳也调回北京崇文区109 中学任教。1979 年6 月12 日,时隔16 年,王蒙举家由新疆迁回了北京。回到北京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王蒙陆续创作发表了《最宝贵的》《布礼》《蝴蝶》《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春之声》等作品,其中既有伤痕反思类的小说,又有开始将目光投向变化中的新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集中地发表于1979 至1980 年间,体现了王蒙复出后第二个阶段的创作走向,同时也构成了王蒙复出后的第一个创作高峰。
小说《最宝贵的》写于1978 年的清明节,是王蒙复出后创作的第一篇真正有伤痕文学意味的作品,而这篇作品也是王蒙在读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后受到鼓舞而写下的。“我已经受到《班主任》的鼓舞,敢于写到滴血的心,写到例如‘文革’,例如‘四人帮’。”[1]10《最宝贵的》截取了一个生活片断,写刚刚参加完老领导追悼会的市委书记严一行,得知当年正是自己的儿子向专案组供出了老领导老陈藏身的地址,从而导致老陈被“四人帮”的爪牙抓走后遭迫害致死。在严一行的责问下,儿子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进行辩解:10年前,自己年仅15 岁,是接受着革命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个中学生,当专案组的领导找到自己时,他觉得自己的做法只是在配合着上级领导的工作和要求,小说中儿子对父亲说:“那时,我是多么诚实,多么轻信啊。我相信名义、旗号和言辞,胜过了相信自己。” 所以,在儿子看来,自己当年只是相信上级领导,配合上级领导的工作而说出了老陈的住址,自己不该负有什么责任,更何况一个15 岁的少年当年也不知道供出地址后会导致怎样严重的后果。随着那场浩劫的结束,受迫害致死的老陈也平了反,冤案得到昭雪,逝者的家属也得到了温暖的关怀和妥善的照顾,正义得到了伸张,那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文学的思考不应结束,小说恰恰是要借严一行对儿子的追问来表达这样的思考:就算是被欺骗、被利用而无辜犯下的错,作为个体难道就不应该有所担责,有所自责吗?小说借严一行之口,面对过往:“你总应该觉得终生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为了陈伯伯的不幸,也为了你最宝贵的东西的失去。你总应该懂得憎恨那些蛇蝎,他们用欺骗和讹诈玩弄了、摧毁了你少年的信念和真诚。”[5]106在这篇小说中,王蒙不再简单地对时局大政作亦步亦趋的书写,而是对刚刚过去的历史进行人性的追问与反思,而这种追问无疑极具理性的深度与现实意义。
小说《夜的眼》在王蒙复出期创作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从这篇作品开始,他将目光从“昨天”移向了当下那种鲜活的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小说讲述了被下放边远小镇二十多年的陈杲于“文革”结束后又回到了自己之前所在的那个大城市,受人所托到去找一个大领导求情办事的经历,呈现了这个城市“今天”的面貌,以及这种面貌带给自己的种种陌生和新奇。首先呈现在陈杲面前的是这个城市的全新的生活景象:“大汽车和小汽车。无轨电车和自行车。鸣笛声和说笑声。大城市的夜晚才最有大城市的活力和特点。开始有了稀稀落落的、然而是引人注目的霓虹灯和理发馆门前的旋转花浪。有烫了的头发和留了的长发,高跟鞋和半高跟鞋,无袖套头的裙衫,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城市和女人刚刚开始略略打扮一下自己,已经有人坐不住了。这很有趣。”[5]197在这样的都市生活景象的叙述中,很难想象这里昨天还是一片火热的政治运动的场景,转瞬间,城市生活已变得如此五光十色。这里变化的不仅是生活的色彩,还有人们的观念。公交车上穿着工人装束的青年,正情绪激动地谈论着关于民主的话题。城市新建的居民住宅区大得有如迷宫,通过开着的窗子可以看到电视上正播送着国际足球比赛。小说一下子把人们的视线带入到鲜活的当下都市生活中去,虽然离“文革”的结束刚刚过去三年,但昨天的一切似乎已遥远得如同传说,已然没有历史的纠结。读者透过作品,能够强烈地感觉到新生活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推动了王蒙在这一时期写作重心上的快速调整和转向。继《夜的眼》之后,王蒙一鼓作气地写出《风筝飘带》《海的梦》《深的湖》等作品,都是把这种“当下的”鲜活的生活内容和其中的滋味作为自己作品表现的重心。而这种创作重心上的调整,也使得王蒙从伤痕文学的框架中跳了出来,寻找到另一种感知并表现新生活内容的叙述手法与方式,正如王蒙自己所说:“这是在我七十年代喷发式写作过程中突然出现的一个变数。它突然离开了伤痕之类的潮流或反伤痕的潮流。……它用一种陌生的,略带孤独的眼光写下了沸腾着的,长期沸腾永远沸腾着的生活的一点宁静的忧伤的观照。它写下了对于生活,对于城市,对于大街和楼房,对于化妆品与工地,对于和平与日子的陌生感。”[1]48王蒙要写下那种走出政治生活后对生活的那种很纯粹的感觉。
《布礼》是王蒙这一阶段创作的第一个中篇小说。谈及这篇小说题目的含义和来源,王蒙说:“我当时以此作为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的标题,包含了弘扬自己的强项: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经历与曾经的职业革命者身份的动机。我相信,到了这个年代,除了我已经没有太多的人怀念互致布礼的岁月了。革命成功弘扬了革命,却也消解了、褪尽了革命的浪漫色彩。”[6]43《布礼》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我们可以把这部作品看作是王蒙后来写的自传系列和季节系列的最初写作。小说以选取特定时间点人生片断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随共和国成长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钟亦成从1949 至1979 年的人生经历,其中重点呈现的是主人从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被错划为右派到平反复出的心路历程。新中国成立时,钟亦成是P 城省立第一高中的学生,年仅17 岁的他已是两年半的候补党员,那是怎样一种豪情壮志!但1957 年的风暴使钟亦成跌入人生的谷底,曾经的少年共产党员却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文革”中钟亦成再次受到冲击,红卫兵小将更是以革命名义将他作为阶级敌人进行批判。“文革”结束后,钟亦成终获平反。回首这20 年的沧桑岁月,钟亦成想要表达的并不是创痛感,也不是时代巨变下对自己曾经的那种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困惑,反倒是一种历练之后的更为成熟坚定的信念:“二十多年的时间并没有白过,二十多年的学费并没有白交。当我们再次理直气壮地向党的战士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的敬礼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我们已经深沉得多、老练得多了,我们懂得了忧患和艰难,我们更懂得了战胜这种忧患和艰难的喜悦和价值。而且,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也都深沉得多、老练得多、无可估量地成熟和聪明得多了。”[6]102这部作品直指王蒙自己,这是他敞开心扉、书写自我的作品。从《诗,数理化》到《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再到《最宝贵的》,王蒙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紧跟时局,书写极富时代感的主题,而回避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那种历史体验的书写。而在《布礼》中,王蒙有了第一次的释怀,他真正地、完全地面对自己,书写一个与新中国同步成长起来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心路历程,通过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的遭际进行回顾,对经历了20 多年沧桑历程的忠诚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内在情怀进行反思。在这部作品中,作家透过主人公这20 多年“低头认罪”的沧桑经历感悟到了与自己当年作为一个满怀豪情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内在联系,找到了30年间党员与组织那种共历风雨、共同成长、共经磨难的“宝贵”人生经历,从而使得“布礼”成为自己数十年人生成长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与信念,这便是一个经历运动沧桑的共产党人的信念宣言。可以说,这篇小说对王蒙个人而言,以及那一代有着少年布尔什维克经历和体验的知识分子而言,都有着标志的意义,刘绍棠、丁玲在复出之际,也在作品中表达过相同的情感。因此,这部作品不仅是王蒙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还是一代经历过运动波折的党员知识分子平反后政治心理的表达。
三、一部延宕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
2013 年4 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王蒙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后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从发表时间来看,这部作品与王蒙的复出时隔久远,但实际上这是王蒙在复出期创作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只是由各种客观原因,作品迟至30 年后才出版。据学者郜元宝的考证,《这边风景》动笔于1972 年,“从1972 年‘试写’部分内容,1976 年底完成初稿,到1978 年6 月去北戴河,这中间如果因为忙碌不再有任何改动,则1976 年底的初稿可算是《这边风景》真正的原始样态,它的创作始于‘文革’后期的1972 年,大约完稿于‘文革’结束的1976 年底”[7]。而据王蒙妻子崔瑞芳在《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一书中所记,王蒙是在1974 年10 月15 日40 岁生日那天决心恢复写作,从1974 年底开始,加上整个1975 年都在写《这边风景》。从上述情况来看,1972 年王蒙应该是动笔试写了与《这边风景》有关的部分内容,而小说正式全面铺开来写是在1974 年10 月。可以明确的是,王蒙时隔多年再次提笔写作正是从创作小说《这边风景》开始的,而小说初稿完成的时间是在1976 年底。
小说初稿完成后,王蒙暂时将它放在了一边,将主要的精力转向创作《诗,数理化》《向春晖》《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等作品,构成了王蒙重回文坛后发表的第一批作品,也正缘于这些作品,王蒙引起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注意。1978 年初,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黄伊给王蒙去信,邀请他去北戴河团中央疗养所去写作。1978 年6 月上旬,王蒙坐了3天的火车从新疆来到北京,与中青社的其他同志在北京站会合后,乘车来到北戴河。从6 月16日到8 月31 日,王蒙在北戴河呆了46 天。这期间,王蒙主要的工作便是对《这边风景》的初稿进行充实、修改,“我在这里写新疆后期所写的《这边风景》,上午与晚上写作,下午去海上游泳”[1]18。但这一写作过程并不顺利,这与彼时急剧变化的政治气候和文艺思潮有关。对于当时自己那种左右为难的状态,王蒙曾说道:“写作当然是去北戴河的主要目的,但是写得糊里糊涂,放不开手脚,还要尽量往‘三突出’、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上靠。我想写的是农村一件粮食盗窃案,从中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的风情文化。但毕竟是先有死框框后努力定做打造,吃力不讨好,搞出来的是一大堆废品。”[1]18小说动笔的时候还是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岁月,又是文艺上大力倡导“三突出”“主题先行”的时期,王蒙在这样的氛围下写作《这边风景》,不论是在人物刻画、情节设置、结构安排还是主旨立意上,都不可能不受到时代政治气氛的影响以及主流文艺观念的拘牵。待小说初稿完成之际,已经时过境迁,曾经在写作中应予着力表现的政治主题及内容开始烟消云散。时至再次面对这部手稿的1978 年,已是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轰轰烈烈兴起之际,所以1978 年6 月至8 月间,在北戴河写作的王蒙面对这样的一部手稿,真切地感受到无从下手。这不是小小的修改、润色就可以完成的,需要伤筋动骨,需要推倒重来,这无疑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对于彼时刚刚复归文坛的王蒙而言,显然无法抽出足够的时间去重写作品,最终这个作品就停留在初稿阶段,没有出版。“由于此稿大情节是以批判‘桃园经验’与制定‘二十三条’为背景的,最初以此来做‘政治正确’的保证,在形势大变以后,原来的政治正确的保证反而难以保证正确,恰恰显出了政治不正确的征兆。出版社觉得难以使用。”[8]7041979—1981 年间,王蒙曾试图对书稿进行修改,但修改得仍不顺利,“终于死了心,原作已经成型,体量太大,六十余万字,八十多个人物,推倒重来,已不可能。我本人承认无计可施:此稿因政治可疑而被打下另册”[8]704。1981 年,王蒙在浙江《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作品中的一些片段,从此以后这部小说的手稿就被束之高阁,随着时间的推移,连王蒙自己也逐渐淡忘了这部小说的存在。直至2012 年,王蒙的儿子王山和儿媳刘珽打扫旧屋时偶然发现了这部小说的手稿,才使作品重见天日。在家人的动员下,王蒙对手稿进行了重新校订,“基本维持原貌,在阶级斗争、反修斗争与崇拜个人的气氛方面,做了些简易的弱化”[8]705。小说最终于2013年4 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计60 余万字。
关于小说《这边风景》的思想价值,有学者这样评述道:“王蒙从伊犁农村生活的切身经验出发,通过对跃进公社爱国大队两条路线斗争以及生产生活的描写,立体地全景式地向人们展示了20 世纪60 年代初,新疆伊犁农村的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是一部描写新疆伊犁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9]应该说,这样的概括是较为中肯的。《这边风景》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置于1962—1965 年间,着重围绕伊犁跃进公社爱国大队七生产队如何开展四清运动而展开叙事,作品在情节结构及人物塑造方面有着鲜明的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作品的风格和特点,但却并不显得生硬和说教,也并没有图解政治的感觉,因为在这部小说里,由浓郁的新疆边地风情和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及日常生活场景的展现构成作品叙事的主体,让人们看到六十年代中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情形。小说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上虽然也有着依从阶级斗争叙事的需要而进行刻画的痕迹,但并没有将人物置于路线斗争中而作简单的脸谱化和观念化处理,而是将人物放置在新疆民族文化土壤中来进行塑造和开掘,因而显得个性鲜明、立体丰满而又有着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小说中人物众多,从民族成分上来看,既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锡伯族、东干族,也有汉族、俄罗斯族等,不同人物身上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格特点的一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小说中刻画了一个具有极左色彩的基层干部—公社书记库图库扎尔:“库图库扎尔就是这样的不可捉摸。他一会儿正经八百,一会儿吊儿郎当;一会儿四平八稳,一会儿亲热随意。有时候他在会上批评一个人,怒气冲冲,铁面无私,但事后那个人一去找他分辩,他却是嘻嘻哈哈,不是拍你肩膀就是捅你胳肢窝。不过,下次再有什么机会说不定又把你教训一顿。伊力哈穆和库图库扎尔打交道也不是一年半载了,总是摸不着他的底。听他说话吧,就像摆迷魂阵,又有马列主义,又有《可兰经》,还有各种谚语和故事,各种经验和诀窍,滔滔不绝;你分不清哪些是认真说的,哪些是开玩笑,哪些是故意说反话。”[10]34在这样一种多维性格性情的剖析与审视中,作家已一点点地摆脱了那种脸谱化、概念化地刻画人物的局限,有了从生活出发的意蕴和色彩。小说中这种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风情色彩不只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在对当地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习俗的描述中更体现得淋漓尽致,真正呈现出“这边风景”的韵味。如小说开篇写主人公伊力哈穆时隔多年后由外地返乡回家,年迈的外婆按当地古老的习俗在家门口迎接他:“在伊力哈穆家的木栅栏门口,八十岁的巧帕汗嘤嘤哭泣。维吾尔族的风习就是这样:妇女们乃至男子们和久别的(有时候也不是那么久)亲人相会的时候,总要尽情地痛哭一场。相逢的欢欣,别离的悲苦,对于未能够一起度过的,从此逝去了的岁月的饱含酸、甜、苦、辣各种味道的回忆与惋惜,还有对于真主的感恩—当然是真主的恩典才能使阔别的亲人能在有生之年获得重逢的好运……都表达在哭声里。”[10]13在这个场景的叙述中,不仅有着关于当地民情风俗的书写,也包含着对人与人之间真情挚爱的呈现,这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更显得难能可贵。再如小说中关于维吾尔人打馕的场景描写:“土炉烧好了,院落里弥漫着树叶、树枝和荆蒿的烟香。面也揉好了,米琪儿婉和雪林姑丽都跪在那块做饭用的大布跟前,做馕剂儿。做馕,是从来不用擀面杖的,全靠两只手,捏圆,拉开,然后用十个指尖迅速地在馕面上戳动,把需要弄薄的地方压薄,把应该厚一点的地方留下,最后再用手拉一拉,扶一扶,保持形状的浑圆,然后,略为旋转着轻轻一抛,馕饼便整整齐齐地排好队,码在了大布上。最后,她们用一只鸡的羽毛制成的‘馕花印章’,在馕面上很有规划地、又是令人眼花缭乱地噗噗噗噗地一阵戳动,馕面上立刻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有的如九曲连环,有的如梅花初绽,有的如雪莲盛开……新打好的馕上面,充满了维吾尔农妇的手掌的勤劳、灵巧与温暖的性感。”[8]609由打馕作者又引发出对维吾尔人生活哲学的感悟:“打馕能引起这么大的兴趣,不能不联系到维吾尔人生活哲学的某些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第一是重农主义,他们认为馕的地位十分崇高,有人甚至说在家里馕的地位高于一切。第二是唯美主义,他们差不多像追求一切实用价值一样追求各种事物的审美的价值。”[8]609可以说,这样的劳作场面的诗意的描绘,既是对美好生活的礼赞,也是对维吾尔民族那充满诗意生活的赞美。小说更为动人的是对当地美丽善良的少数民族姑娘们的描写,不论是狄丽娜尔、雪林姑丽,还是爱弥拉克孜,她们不只有着美的容貌,更有着纯真善良的心灵,她们的爱情故事也都真挚感人,呈现出一种热情奔放、炽烈真诚的美。对于她们,作家常常用诗一般的语言去描述:“雪林姑丽,你丁香花一样的小姑娘,你善良、温和、聪明而又姣好的维吾尔女子。笔者在边疆的辽阔的土地上,第一个见到了的,第一个认下了的,不正是你吗?那是在终年白头的天山脚下,在湛蓝湛蓝的孔雀湖边。湖水里映照着洁白的雪山和墨绿的云杉、蓝天、白云。湖边有几棵发黑的大柳树,许多深绿和嫩绿的枝条正在摆拂。有一行白鹅,在蓝宝石般的湖面上缓缓地浮游。有一团小蜢虫,在湖面上嗡动。这时候,你来了。”[8]559这种诗化的语言烘托和呈现的是人物的纯真和美丽,又与新疆沁人心脾的自然风光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小说特有的别样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