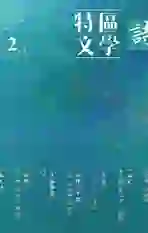动物杂记(三篇)
2022-02-26刘向东
蜉蝣记
如今,很少有见过蜉蝣的孩子了。偶然见了,也不认识,说是小鱼儿。水塘越来越小,水越来越少,河流多有干涸,偶尔一场洪水,可以漂起石头,不等迎来蜉蝣,紧接着开始抗旱了。最主要的还是孩子们没空儿玩耍。你想,一个小小蜉蝣,从卵孵化至幼虫,又在水中蜕十次甚至二十次皮儿,费时三年,才生存几个小时。一个生命,就这么完了。也有说蜉蝣活一整天的,俄国作家普里什文就说蜉蝣的寿命有一天—唯一的一天,我想这可能是不同的品种。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才知何止是不同品种,蜉蝣,竟然有两千一百多个品种呢。书上还附有一组图画,介绍蜉蝣的生活简史。甭管它是什么品种,是活上一天还是几个小时吧,总之是生命短暂。这时孩子在作业堆里,在补习班里,碰巧和蜉蝣打个照面儿的机会实在太小了。
说起来我格外幸运。我家老屋西边百米,有一古潭,因我父亲喜欢文墨,看古潭形似石砚,便将它命名为“石砚潭”。我们小孩子家,不管它石砚不石砚,叫它大石井子。大石井子中的水,止水一般,深得发黑,静得让人害怕。实际上下面有细细的泉眼,让那水总是活的,适合蜉蝣生存。夏天的黄昏,水面上有一缕缕的霞光和香油(老家人认识蜉蝣,却常常形象地叫它“香油”,是时香油金贵,有时用筷子头蘸一星儿入汤,蜉蝣一般恍兮惚兮)。蜉蝣的翅膀薄到了不能再薄,却居然可以收拢并竖立起来,展开时,其状若蝶,尾巴拖着三根上翘的小须儿,或飞、或跳、或舞,曼妙啊!
儿时我以为蜉蝣可以活一个夏天,天天见它们飞来荡去,兴致来了就动手,猛地一把,把它们抄上岸来,看它们在石头上蹦蹦跳跳。有时把它们捧回家,放进水缸,看它们着急的样子。至于它们在什么时候消逝了,则全然不知,要是转眼不见了,还以为飞了呢。如果我打小就知道它来这世上是那么难,而活着的时间又是那么短,我有可能不忍心碰它,我将专注地看着它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用几个小时,或整整一天的时间。
过了三十岁才知道,人怕过年,一个接着一个,飞快,蜉蝣一般。浮来游去,有时也立志,下决心少睡一会儿,多读几页书,多写几个字。读着,写着,累了,躺在床上,头大身子轻,床若潭水,眼前发黑,觉得自己也是蜉蝣了。“姑娘,姑娘,你为什么皱起眉头,莫非你遇到整日阴雨绵绵?而那边那只小蜉蝣该怎么办啊,它的一生都遇到阴雨绵绵!”迷迷糊糊中,眼皮儿外好几次浮现这诗意,待自己渐渐变大、变薄,大到不能再大,薄到不能再薄,成为一片梦。
生命原是这样,满百者不能说长,几个钟点儿说不得短,因是世代绵延,给人以不息的感觉。
有一次我二大爷出远门,路过北京站,见人山人海,以为大集,回家跟乡亲说:真巧真巧,我去时见了那一大拨儿人,回来又见了那一大拨儿人。乡亲们问有多少人?我二大爷說:“跟蜉蝣似的。”
二大爷,您说得对,人啊,蜉蝣似的。只是您不知道,您见到的“那一大拨儿”,是分了这一拨儿和那一拨儿的,天天变换,蜉蝣似的。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听我念到诗经里的蜉蝣,女儿忽然问:“啥是蜉蝣?”那时她还不大,我答应抽空儿带她到水边走走,花几个小时,或者一整天,去寻找蜉蝣,见识蜉蝣,看那些不知皱眉头的短促的生命,在温暖的水里,如何长出美丽的翅羽。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白答应了。
2011年7月22日,陪伴父母回到故乡,次日一大早去看大石井子,黑乎乎止水一潭,但见蜉蝣依旧,我暗暗祝福。当天下午,跟老爷子上山,到水湖子寻找先前的记忆,居然在山楂林里再次见到三只蜉蝣。为了给山楂树打药取水方便,果农在树林里挖个坑,铺上塑料布储存雨水。水坑边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农药瓶子,水都蓝了绿了,飘着黄叶,蜉蝣竟然浮游着,奇迹啊!
采蜂记
蜂,尤其是蜜蜂,总是深深吸引诗人。
爱尔兰诗人叶芝写道: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窝棚,筑起篱笆墙
支起九行芸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而在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的诗中,就到处都有嗡营之声了,就连她忘情地描述她梦中的大草原时,也忘不了来这么一笔:
要有一只蜂
一只蜜蜂……
特别感动我的是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与蜜蜂有关的两行诗。那是写给一个困苦中的小男孩儿的。一个苦孩子,巴望一口蜜—
让我尝一口蜜吧,
让我尝一口蜜,我宁愿去死
我老觉着这是写给我的。
小时候,我就是那样地想尝一口蜜。
我不敢说我是苦孩子出身。要说苦,那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事。来这世上的人,谁是直接掉进蜜罐儿里的?还不都是一来到这世上就哇哇大哭。
在我的故乡,早先整个村子有三户人家后院有蜂房,那是刘勤、刘增、刘福春家。蜂房是用空心椴木做成的,大约一篓粗,五尺高,底部有个或圆或方的小孔,供蜜蜂出入,上头,用黄麦草扎顶子。至于蜂房内部结构,我无从知晓。养蜂人家一般不让靠近,怕你挨螫,怕蜂受惊,怕生人气味。待到人家割蜜时,你就更不能靠近,万一流出口水来,丢人现眼。
起先我并不知道为什么管采蜜叫“割”,现在想来,割,有取舍的意思,是想给蜂们留下口粮吧。
待有人家割蜜之时,半大孩子老远张望。蜂房的顶子揭开了,里边是用木条钉的十字,蜂儿依十字筑巢。
春暖花开的时候,偶尔有一群蜜蜂从蜂房中逃离,或是有整窝的蜂背叛了主人,犹如小小的机群,满载花开的声音。这时养蜂人家急了,随手抓一把土向蜂群扬去,看蜂群呼呼地飞,连绊脚的石头都顾不上了,一追老远。有人急,可也有人乐,忙着在远处花树上采蜂,妄图拦住一大群春天。有蜜的人家,往草帽上抹蜜,没蜜的人家,喷一点糖水,吸引蜜蜂过来,一手托着草帽,一手拿着新笤帚往草帽里扫。谁家扫着蜂王了,算是有养蜂的命,他家的孩子,来年就有机会吃一口蜜。说是“有机会”,其实机会很小。扫来的蜜蜂住不惯新巢,说飞又飞了。勉强住下来的,开始闹病,一个个挣扎着爬出门,栽倒再也飞不起来了。
有一年春,我爷爷和我在老娘沟森林里发现一窝蜂,在一个老椴树根部,蜂们出出进进,一片繁忙。观察了好几次,看它们很像蜜蜂,全都带着甜甜的味儿,以为是野蜜蜂呢。
我爷爷说,和谁也别说啊,等到秋天。
为了一口蜜,我和我爷爷苦苦等了两个季节。
苦苦地等。等,其实倒没什么苦,苦的是守着那个秘密,守着那个很想对人说但无论如何又不能说出的甜蜜的秘密。
终于可以去割蜜了。“一定要把蜜蜂也采回来!”我拉着爷爷衣袖说。
悄悄地备下一个蜂房之后,爷爷带上铁镐、木桶、斧头和松明出发了。“草帽儿!草帽儿!还有草帽儿!爷爷!爷爷!带上草帽儿!”我喊着追出门,想跟着去,爷爷不让,怕我挨蜇。
去了大半夜,爷爷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原来那不是蜜蜂,是一窝土蜂。
就在这年秋,我们家特意从增大伯家买了一罐头蜜,谁知,其中竟然兑了一多半儿粳米米汤。
此刻,我无法描述采蜂的趣乐,是因为事非躬亲。有几次我见蜂群落到野地小树上,便跑回家找来草帽和笤帚,蜂群已经扬长而去。
我一定要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实在想说出我对甜蜜的理解—
甜蜜无所不在,但
人们很少能够得到甜蜜
因为命运只把它
赐予理解它的人……
说出要说的话,突然又想起我曾经望见的那些蜂房中的十字木条来,像十字架。偶见一本书上说,相传蜜蜂最初是在天堂,曾以“上帝的小仆人”著称,在有的佛教徒聚集地,人众至今被喻作蜂群,佛塔呢,又曰“蜂台”。
但凡传说,恍兮惚兮,不足信,也不能不信。
忽见《环球时报》上黑体标题:“以色列发现三千年前蜂箱—《圣经》‘奶与蜜之地所言不虚。”
报道说,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北部发现了三千年前养蜂业的证据,包括古代蜂房、蜂蜡和他们认为的最古老的三十个完整蜂箱。希伯来大学考古学家阿光凯·马扎尔告诉记者,那些蜂箱由稻草和未烧过的黏土做成,一头有个洞,以便蜜蜂进出,另一头有盖子使养蜂人可以够到里面的蜂巢。发现的时候,这些蜂箱摆放整齐,三个一摞。马扎尔还说,《圣经》中多次提到以色列是“奶蜜之地”,但人们认为这指的是由椰枣和无花果做成的蜜,因为书里没提到养殖蜜蜂。但是,新的发现表明,“圣地”在三千年前就有那么发达的养蜂业。
再听蜂儿之歌唱,赞美中隐含祈祷。
蝉鸣记
在一家报社主办的“天雄杯全国新诗大奖赛”参赛作品中,有一首诗叫《蝉鸣》,因我偏爱之,一再向其他评委鼓吹、推荐,大伙儿却认定它没有我说的那么好—孤掌难鸣。私下里,我评判一件文艺作品,首先是把握设身处地这一尺度—假如“我”也来操作之,是比人家强呢还是自愧不如?我说《蝉鸣》不错,也正是因了我的自愧不如,因为我也写过《蝉鸣》,费劲巴力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
一只蝉,
曾经有十七年被尘埋
而后放风
两只蝉
为妻者必定是哑巴
脉脉深情默默而终
原来我以为,蝉是每年都要上树歌唱的,谁想它们要在暗无天日的潮湿的泥土中守候那么长时间。科普读物中介绍,蝉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一种昆虫,一生大多在地下度过。幼虫一般要在地下待二至三年,长的要五六年。已知的在地下时间最长的蝉是美洲的十三年蝉和十七年蝉,也就是说它们每隔十三年或十七年才孵化一次,遵循的是一种奇异的生命循环。
我专门到太行山下白鹿泉附近的苹果园看蝉,见它们从地下钻出来时还没翅翼,前腿却坚强有力,很快爬上苹果树,脱掉浅黄色的蝉衣,变成有翼的蝉。蝉衣落到地上变黑,头上两个窟窿,样子像是儿时听大人们描述的“小鬼儿”,怪吓人的。天暖和了,蝉们鼓翅而鸣,有一种“鸣鸣鸣鸣—哇,鸣鸣鸣鸣鸣—哇”,天越热鸣叫越欢,且有金属的音质。本以为是蝉都会鸣叫,谁知只有雄的才叫,它是在呼唤它的哑巴妻子。一个大声呼唤,一个沉默不语,不对等,但对称。受精的雌蝉默默劈开嫩枝产卵。几星期后,雄蝉和雌蝉在完成种族延续任务后,双双死去。受精卵则在枝内自主孵化,新的一代诞生。幼虫从树上掉到地上,又钻进土里进行漫长的隐居,直到它们在地下住到一定时候,才又爬上地面,举行新一代婚礼。有了如上认识,加上原先六行垫底,又过了一年,我拼凑出另外“两只蝉”来:
三只蝉
总有一位正拱破泥土
不顾头上有怎样的天空
四只蝉
在高枝之上鸟雀之下
为谁而鸣
经年得来这么几句,一看,没啥意思,也没出息,借用的是古人说过的话。古人不是说过“乱山秋雨后,一路野蝉鸣”吗,不是说过“黄雀在后”吗,还说过诸如“秋来吟更苦,半咽半随风”之类。可我坚持守护我的诗,这是因为,我有我的发现—你说这世界对蝉们来说多么“那个”我都同意,但总还有另一番情景:总是有拱破泥土的,就像种子发芽,长出小苗。
写了几节,强行收工。某日去《诗神》编辑部,见诗人大解手托一泥丸,有铅球大小。大家议论纷纷,有人问这是什么蛋蛋,有人问这是什么球球,诗人旭宇说,看看不就知道啦,抄过来顺手一扔,泥丸摔在地上扑哧裂开,里面原是一只作古的蝉虫儿。正是这只蝉虫儿,令我为我的《蝉鸣》新添了如下六行:
又一只
永远把自己包在泥里
对心中的秘密守口如瓶
我是另一只
我的嘴唇总是湿的
又有什么能夠说清
为此陶醉一番,陶醉于这世上有许多事情,尤其是诗,美在不能说清。
谁知偏偏另一种美,在于观察仔细、描述准确、说得清楚。如法布尔,在《昆虫记》卷五中如此描述蝉鸣:
在雄蝉的后胸,紧靠后腿之后,是两块很宽的半圆形大盖片,右边的盖片稍微叠在左边的盖片上。这是护窗板、顶盖、制音器,也就是发音器官的音盖。把音盖掀起来,看到左右两边都有一个大空腔,普罗旺斯人称之为小教堂。这两个小教堂汇合起来就形成了大教堂。小教堂前面有一层柔软细腻的黄色乳状膜挡住;后面是一层干燥的薄膜,薄膜呈虹色,就像一个肥皂泡,普罗旺斯语称之为镜子。
这大教堂、镜子、音盖,就是人们通常认为的蝉的发声器官。对一个没了气息的歌唱者,人们就说它的镜子裂了,这形象的语言也用来指没了灵感的诗人。但是,这声学原理和人们普遍认为的是不相符的。把镜子打碎,用剪刀剪去音盖,把前面的黄薄膜撕碎,并不能消灭蝉的歌声,只不过改变了它的音质,响声变小了些。那两个小教堂是共鸣器,它们并不发声,只是通过前后膜的振动增强声音,并通过音盖开闭的程度改变声音。
真正的发声器官在别处,新手是很难找到的。在左右小教堂的外侧,蝉的腹背交接处的边缘,有一个半开的纽扣大小的小孔,小孔被角质外壳限制着,那盖着的音盖又把它遮了起来。我们把这个小孔起名为音窗,它通向另一个空腔。这个空腔比旁边的小教堂深得多,窄得多。紧靠后翼连接点之后,是一个轻微的隆起物,大致呈橢圆形;它那黑得没有光泽的颜色,在周围带着银色绒毛的表皮中显得异常突出。这个隆起物就是音室的外壁。
在音室上开个大的缺口,于是发声器官音钹就现出来了。这是一块干的薄膜,白色,椭圆形,往外凸,有三四根褐色的脉络分布在薄膜上从中穿过,增加了它的弹性。这个音钹整个儿固定在周围坚硬的框架上。试想一下,这块突起的鳞片状的音钹变形了,往里拉,拉得凹下去一点点儿,又在那一束脉络的弹性下迅速地回复到开始的突起状态,于是一声清脆的声音就从这来回的振荡中发出来。
什么是蝉鸣?这才是蝉鸣。我原来还以为蝉是用嘴鸣叫的呢。幸亏是写诗,不然“对心中的秘密守口如瓶”和“我的嘴唇总是湿的”之类,会不会让雌蝉知道了也大声惊叫?
好玩的朋友看了如上文字,说是干巴,太干巴了!什么蝉不蝉的,不就是知了猴儿吗,你听我说(依据记录整理,敬请审阅):
在柳树下挖知了猴儿,要看洞口大小,最保险的是开了一点的、不规则的洞,用小树棍儿轻轻一挑,就看见一点贼亮。这时候千万不能用手挖,一挖知了猴儿就往后退,如果退回去,就再难捉到了。要用很细的棍子轻轻伸进去,逗它,等知了猴儿的腿挠住棍子,再轻轻把它拽出来。很多没经验的小孩儿会用手抠,所以就经常看见憋死在洞里没法完成蜕变的变成绿色的知了猴儿。小时候大家都说知了猴儿看不见,因为外面那层壳包住了它的双眼,于是就打赌,把知了猴儿放在画好的圆圈儿里,一方又是跺脚又是喊叫,一方拿着棍儿在知了猴儿眼前晃,知了猴儿要么一动不动,要么冲着棍儿就去了,所以都说没变成知了的知了猴儿都又聋又瞎又傻。把聋瞎傻的知了猴儿扣在筛子下面,过一夜,就变成知了了。把知了翻过来,一掰,有镜子的能叫,没有镜子的就是哑巴了。把能叫的知了依然扣住,到了中午就能听见它们的叫声了。哑巴知了会被淘气的小子用火烧了吃。小时候曾拿着手电筒整夜观察知了猴儿变知了的过程,怎么看也没啥变化,可是一眨眼,知了猴儿的身子就肿了,然后再一不留神,肿了的知了猴儿后背裂开了一道缝儿,等撒泡尿回来,知了已经拖着皱皱巴巴的翅膀傻乎乎的出来了。看着那个丑家伙,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这团湿不拉叽的东西怎么就变成了白天那个振翅高飞的薄翼。蒙眬睡去,等早晨醒来,听见筛子下面嗡嗡的动静,一看,知了爬在筛子眼儿上正试图高飞呢。有的小孩儿为了证明没有镜子的知了不能叫唤,就拿根小棍儿捅破有镜子的知了的镜子,那知了果然就不叫了。要想逮变成知了并且飞上树梢的十分费劲,于是小子们就用马尾巴上的鬃毛套知了。把弯成细圈儿的马鬃绑在一根细长的竹竿儿上,悄悄接近知了的头部,等知了一惊往前一飞,正好落入圈套。也有用面筋粘知了的,把面粉不断过水冲洗,只剩下一坨黏黏软软的面筋,捏一小块涂在竹竿上,让面筋悄悄粘住知了的翅膀,任它怎么挣扎,也飞不掉了。现在的高楼越建越多,城里鲜见了高耸的笨槐却多了被砍掉树帽儿的洋槐,夏日的晚上再也看不到孩子们拿着手电筒在树下寻觅知了洞的情景了。有一回我弟弟去山东,在高速收费口看见旷野里灯光绰绰以为见了鬼,一打听才知道是男女老幼一干众人打着手电提着水桶在树林捉知了猴儿,而路边,一群一伙的妇女正提着大袋小袋蠕动的鲜活知了猴儿兜售,那场面就仿佛知了猴儿是种在地里等着人收获似的。过年的时候我弟弟在超市冷柜里看见冻成一大袋子一大袋子的知了猴儿,遂买了一袋,回家数了数,一共三百个,一个三毛钱。
刘向东,1961年生于河北兴隆县;诗人,作家,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诗选刊》主编。出版有诗文集《母亲的灯》《落叶飞鸟》《诗与思》《沉默集》以及英文版《刘向东短诗选》和塞尔维亚文版《刘向东的诗》等26部。有作品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文学精华》《新诗百年百首》等两百多个选本,被翻译成英、俄、法、德、日、波兰、捷克等多国文字。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作品奖、冰心散文奖、孙犁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