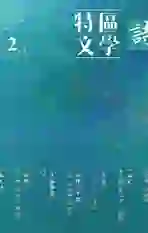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人
2022-02-26拾荒
我承认!为了孩子上学去送礼了
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人
我的骨头里钉入了钉子
铁的硬度让我的骨头很软
我的体内蓄有足够的氧和盐分
我甚至听到了金属浸蚀的滋滋声
人生是否真的需要一场大病来体会健康?
作为农民工我有得是力气
可以瞬间拔出钉子
却要用漫长的后半生来抚摸伤口
承受,骨子里遗留的锈
诗人简介:
拾荒,本名王计兵。生于1969年,江苏省邳州市人,现居于江苏昆山。诗歌散见于国内多种诗歌文学期刊,以及印尼、菲律宾等国家。早期有小说作品发表。近年来因兼职外卖骑手,诗歌作品常在送餐路上完成,而被网友称为骑行诗人。
世 宾:痛感是存在的证明
这是一个自称是农民工的诗人的诗篇。这首诗呈现了一个弱者(为了孩子上学必须去送礼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无可奈何不得不向权贵低头的状态。
低头、妥协对于他来说,自尊心受到极大的羞辱,但他又不得不承受这种命运。可以说,这是一个觉醒了的生命,他在低头和妥协那里感受到了痛感,他的羞辱心也为他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对于麻痹者来说,也许这样的生活很正常,但对于一个自尊、骄傲的人来说,就是钉子敲入骨头的痛。
钉子钉入骨头这个意象是这首诗的核心。钉子就是艰难的生活,他深深伤害了一个想成为有尊严的人的心。他知道他不得不向生活低头,所以他说他的骨头显得很软。但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屈辱的生活对他构成的伤害,他也有反抗。他说,体内蓄有足够的氧和盐分,“氧和盐分”就是反抗的意识、力量、意志,它时刻在反抗钉子对身体的暴力;它也在侵蚀着钉入他的身体的金属。这反抗的意志也是如此强烈,如此不妥协,“滋滋声”就是反抗的持续、反抗的力量的表现。但钉子的这种伤害是持久的,永恒的,纵使钉子拔出来了,骨头里依然会留下钉子遗留的锈,那难以愈合的伤口。
这首诗写得非常有现实感。但从这首诗看,这个诗人的诗歌并不是十分成熟,有些句子是可以去掉的。“我承认!为了孩子上学去送礼了/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我是否真的需要一场大病来体会健康”这样的句子在这首诗中是多余的,去掉会给人更简练、准确的感觉。
吴投文:然而,拔出骨头里的钉子……
为取得一项正当的权利而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获取,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诗中写到的为孩子上学去送礼,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惯不惊。拾荒正是由此出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人”,看起来小题大作,诗中却有颇不一般的力量,矛头直指污浊的社会风气,也指向清醒的自我反思。在骨头与钉子的较量中,骨头是松软的,钉子可以轻松锲入,加之“我的体内蓄有足够的氧和盐分”,致使钉子的锈迹在体内弥散。诗人进而质疑自己:“我是否真的需要一场大病来体会健康?”这是悖论的妙用,亦具有反讽意味。“我”之不纯粹,就像身体里的锈迹,“我”固然有力气,“可以瞬间拔出钉子”,却要在漫长的后半生里承受“骨子里遗留的锈”。这是不甘,亦是自醒,关键还是骨头要硬,让钉子钉不进去。
这是一首接地气的诗,写人之所见、我之所遇,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题材并无特别之处,诗人的主题表达却见出犀利的力度。从写作的角度而言,此类题材的写作实际上颇有难度,不易把生活中的诗转化为可靠的表达形式,不易把生活中的诗对称于恰当的表达形式,诗人拾荒处理得颇为到位。生活中到处都是诗,浮开日常的表层,诗意的碎屑随处可见,既要有发现的眼光,又要找到恰当的表达形式,就需要诗人的聚焦与提炼。细究起来,此诗可能还是有些局促,可以更放开一些,同时更收拢一些;更集中一些,同时更延宕一些。一首高超的诗往往是在矛盾因素构成的合力中取得平衡,在纯粹与不纯粹的张力中形成内在结构的完整性。
向卫国:诗人更应该追问,谁之罪?
这首诗的写作意图非常清楚,我“为了孩子上学去送礼了”,因而心生愧疚,如鲠在喉,以至于觉得“要用漫长的后半生”来忏悔。诗歌的主要笔墨,都是用来描述“送礼”这件事给“我”造成的心理影响,比如说,我感觉好像“我的骨头里钉入了钉子”,还听到了体内的“氧和盐分”侵蚀钉子的“滋滋声”,对钉子在“骨子里遗留的锈”的承受……这种隐喻式的内心状态的描述,也几乎是这首诗的“诗意”的唯一源泉。
但是,“为了孩子上学”而需要给别人送礼,这到底是谁的错?
孩子當然是要上学的,如果不送礼就没有上学的机会的话,那么送礼的“我”有什么不对?真正有错甚至有罪的,是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那些隐身人,应该追责的是他们,应该忏悔的也是他们。尽管我们赞赏一个人对“纯粹”和“高尚”的追求,但世上并没有纯粹的人,也永远不会有。一个人不必为不存在的过错或者在被迫的前提下必须犯下的过错而过度自责,反而放过了那些真正有错或有罪的人。
某种意义上,此类貌似主动担责的行为,反而是对真正的错误和罪过在一定程度上的掩盖。只有追问那些人的责任,才有可能让其他人再也不必“为孩子上学”而去送礼,这是一个诗人应该承担的比个人灵魂的纯粹更重要的责任。作为诗人,也许应该比常人更清楚地分辨一切社会性罪恶的根源。
周瑟瑟:羡慕外卖骑手一边骑车一边写作的奇妙经历
羡慕外卖骑手一边骑车一边写作的奇妙经历。我试着站着写作,但站不了多久就坐下来了,某大师光着身体写作,写出不朽的作品。我深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写作习惯,只要适合自己就好。
这些年来,我国对所谓的底层作者格外关注,还有对残障人士的才华格外欣赏。常识告诉我这类身体或工作的原因形成的标签不可太看重,可以放一边,先看文本后看经历。经历固然重要,经历甚至可以成为文学最重要的内容。
我见过将自己的经历或感受说得天花乱坠的人,引诱我迫不急待地看他的作品,但往往是看后觉得写得不如他说得精彩。这就是“说”大过了“写”,“经历”好过了“文本”的典型案例。
还有一类就是拾荒兄弟这样的写作者,如果这次不看其简介,我并不会知道他在骑行路上写诗的奇妙体验。我对他的写作不陌生,读过他的作品。“骨头”“钉子”“盐”“伤口”,严格说来这些诗歌元素属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年这些词语作为诗歌中心意象出现时,给人带来又狠又好的感觉,现在偶然出现依然又狠又好。
词语与意象是固定不变的,但放到不同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每个人的写作都有自身的命运,词语与意象是公共的,但感受是独特的。当拾荒兄弟想表达“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人”的时候,这些属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词语与意象获得了新的生命与用处。
任何时候的反思与悔恨、无奈与坚挺,都有其价值与意义,只要真实就会闪光。
对于拾荒兄弟,我更想看到他在外卖路上更直接的作品,如果扔掉“骨头”“钉子”“盐”“伤口”这个向度,而写他的脚划过地面的感受,写他在路上奔跑时每一刻的感受,凡是他个人的而不是我的感受,我都想看到,因为我没有像他一样一边骑车一边写作的生活。从这一点来说,我又对一个拥有成熟文本练训的人的经历十分自重,并且将之视为他独有的写作优势。
宫白云:以个我的境遇写出整体的悲凉
这是一首投射力极强的诗,直指一种丑陋的社会现象,写出了做为学生家长“为了孩子上学”不得不去送礼的刺骨之痛,明知“送礼”这种行为令人不齿还不得不为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堪?它透露了一种什么现状?揭示出一种什么样的时代背景?这些都是引起读者深思的问题,而这首诗的深刻也正在于此,它以个我的境遇写出了整体的悲凉,看似细弱的潜流里蕴含着巨大的旋涡,“纯粹”被生生地扭曲,这是对荒谬世界有力地抨击。它的可贵,就在于作者构思之巧,他通过否定自己“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人”进而去否定“送礼”这样的歪门邪气,又一反庸常的平铺直叙,以“我的骨头里钉入了钉子”这样惊人独特的隐喻来坦露自己“送礼”后身心的感受,借用“钉子”这个意象,在“骨头”中的超然联想,去体味其中的锥骨之痛,去达至一种病态的共在,这种以身体的病态去揭示社会的病态的隐性写法,把现实的荒诞、残酷、无奈与痛心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人生是否真的需要一场大病来体会健康?”一句反诘更是把一种荒诞推到了极致,让人陡生出寒凉的颤悸。我个人认为至此戛然而止为好,把一切给予留白更有震撼人心与警醒的力量。当然,我不是作者,作者还是怀揣希望,他希望把那顆锥骨之痛的“钉子”拔出来,尽管“要用漫长的后半生来抚摸伤口/承受,骨子里遗留的锈”,他也将用尽全力去拔除!
赵目珍:作为“存在”的人与成为“救赎”的诗
先谈作为“存在”的人。此处所说“存在”的人,首先指的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人,其次是说在具体生存环境中真实存在而作为社会人的这个人。他为“真实生活”所迫而“折腰”—“为了孩子上学去送礼”,从而认为自己成为了一个“不纯粹的人”。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先于他的本质,其意义就是说他必须先存在,然后才创造他自己。但是存在并不创造他,他是在存在的过程中创造他自己的。”在某种程度上,诗中的“我”也在“创造”他自己,只是“存在的过程”在“创造”他时,使他偏离了他要成为的那个人。这个人成了一个矛盾的存在。然而这不能否认他仍然是一个“存在”的人,因为“矛盾就是人性”(闻一多语),矛盾使他变得更为实在。
再谈成为“救赎”的诗。从背离人格的角度而言,诗中的“我”是“失败”了的。如果没有这首诗的存在,诗中的“我”笃定是失败了。然而因了这首诗的存在,他完成了一个“反转”。诗中的“我”,对自己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做一个纯粹的人,不让自己被浸蚀。然而当他被“浸蚀”之后,他言说自己,将这种“不堪”和种种心迹剖白出来给人看。闻一多曾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等美好“建构”完成了对“不自主的、虚伪的”宫体诗的救赎。作为一个存在的人,真实地呈现自己,至为重要。而“虚伪”是人乃至某种文体“失败”的一种象征。此诗中的“我”在作为人的“诚与真”的层面上,字字有声,层层推进,实现了对自己的另一种“创造”,显然有“救赎”的意义在里面。
高亚斌:我承认!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人
拾荒《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人》,围绕一次令人屈辱的“送礼”事件,以戏剧化的方式,描摹了日常生活极为耐人寻味的一幕。在诗歌里,诗人代言的是一个底层的草根阶层、一位卑微的农民工兄弟,他为了能够让孩子上学,而被迫忍受屈辱,去给别人送礼。诗人选择了一个巧妙的角度,以质朴的语言,触及到了一个社会的敏感话题,用了近乎愤怒和抗争的声音,发出了扣人心弦的灵魂叩问。
在这首诗里,诗人运用了特殊的“身体写作”,诗中出现了骨头、氧和盐分、金属这些关联肉身的意象,具有鲜活的人的在场感。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孩子入校就学,接受教育是天经地义的正当权益,但在一个扭曲的社会环境中,却要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解决,这本身是一个极为荒诞的事情。送礼的行为固然令人不齿,但应该接受谴责的不是当事人,而应该是整个社会,诗歌在平实的叙述中,凸显出骨头的坚硬和钉子的顽强。表面上,诗人是在对“送礼”过错做出反省自责和忏悔,但事实上,却是对于不正之风和人性丑恶的猛烈抨击,在令人愤慨不平之余,深感面对现实的无奈和无力,这更加强化了诗歌的反讽修辞和控诉效果。
诗人拾荒作为一个底层社会的见证者,在生活中他一面兼职做外卖骑手,一面在送餐路上坚持诗歌写作。他的思考和灵感都是“在路上”的状态,是在生活的现场完成的,这使他的诗歌避免了旁观者的无病呻吟,而有了更为真实的切肤之感。弥足珍贵的是,他不仅仅是代表自己一个人说话,他是在为一个群体发声,体现的是一位优秀诗人的良知和勇气,这些都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爱戴。
徐敬亚:中间4行很重要
诗写得清楚、干脆、悲愤!
铁钉入骨,这个凶猛的比喻,是本诗的台风眼。也许这是妙手偶得,也许是诗人心存已久的一个诗核,忽然把它用在了孩子上学的事。东拼西凑是诗人常常使用的小招术。诗在没写来之前谁也看不到,因此这成为诗的永久秘密。
最动人心魄的,当然是结尾。在“送礼”的简短世俗叙事中,诗人突然加入了“我的骨头里钉入了钉子”!最后,靠著这个重量级的比喻,拾荒终于写出了一个人以后半生默默承受内心耻辱的悔恨。这种直抒的手法虽然直露,但对人内心击打的力量太大。
我要着重说的,却是第4、5、6、7行—这四行,太重要。“氧”“盐分”“金属浸蚀”、“滋滋声”……就像事先埋伏好的几束炸药,诗意在结尾才爆发。可以假想,如果没有这四行,诗也仍然完整,但就只剩骨头。可以说这几行正是这首骨头诗中的“肉”。
当下浅白诗盛行。浅白容易,在浅白里埋下钉子不容易。如何用平白的词语写出凸凹的诗意?就像怎样用棉花裹住铁、就像从白云里抽出闪电—这已成为时代难题。
如果从语感的角度读一下诗,会发现首句太硬了!3字后面当头一个惊叹号,又强烈地强化了硬度。从节奏上,第一行也与整诗有些脱离。更细地说,作为支撑全诗的核心事件,“贿赂”之事可再多写那么二三行,以顺应后面的语感。
韩庆成:我与钉子的对立统一
拾荒是刚刚评出的《诗歌周刊》2020“年度诗人”,他的诗以现实性见长,这首《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人》也不例外。
农民工子女上学难是一个存在了很多年的现实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解决渠道,就只能通过旁门左道来解决。托人、花钱、送礼,是常见的几个方式。但农民工有几个能托到管用的人呢?所以最后还是得通过花钱送礼来解决。对于生活拮据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花的不是钱,而是身上的肉。由此,作者更进一步,写到了肉里的骨头。他把违心送礼、不得不送礼,比喻为往自己的骨头里钉入了一颗钉子。
拾荒诗歌的高明之处是善于把现实性融入诗性之中。在这首诗里,体现为钉子和我既对立又统一的微妙关系。
首先,“我的骨头里钉入了钉子”,钉子是入侵者;“铁的硬度让我的骨头很软”,我被迫改变,是受害者;“我的体内蓄有足够的氧和盐分/我甚至听到了金属浸蚀的滋滋声”,因为被迫,我的身体开始反抗;“作为农民工我有的是力气/可以瞬间拔出钉子”,我自信可以打败钉子。写到这里,这首诗似乎有了一个光明的结局。且慢,我真的可以拔出钉子吗?或者说,这个钉子是你能够拔出就可以拔出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者继续写道:“却要用漫长的后半生来抚摸伤口/承受,骨子里遗留的锈。”拔出钉子的后果,很大很大。我与钉子的关系,就从对立转向了统一。至此,诗中那句“人生是否真的需要一场大病来体会健康?”问得就很必要。诗的题旨也超越了简单的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而有了更深的指向。
霍俊明:“纯粹”与“不纯粹”
拾荒的诗《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人》中最容易刺激阅读的兴奋点是“农民工”这个词,这也印证了诗的写作伦理和阅读伦理问题。如果再结合一下作者的简介,“近年来因兼职外卖骑手,诗歌作品常在送餐路上完成,而被网友称为骑行诗人”,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去讨论这首诗之内和之外的社会学话题。在写作的层面来衡量,“农民工”“外卖”往往因为诗人主体的介入而不再是中性的了,而是发生偏移。比如拾荒的这首诗叙述了一个亲身体验的社会问题,全诗也基本上是在“纯粹”以及外界因素侵入的过程中(比如“送礼”“钉入了钉子”“金属侵蚀的滋滋声”)而变得不再“纯粹”(比如“让我的骨头很软”“骨缝里遗留的锈”)的过程展开的,全诗基本上是在“对立”“矛盾”中完成的(比如钉子与骨头、大病与健康),而该诗所要传达的信息因为话说得太满而没有留下余地甚至缝隙,从而也导致诗歌的阅读时间随之变短。
我们可以写“痛苦”的诗,可以写“愤怒”的诗,可以写“不纯粹”的诗,但是其前提仍然是“诗”,仍然要在诗歌的效力和活力的前提下完成。以此来考量的话,这首诗也仍有“未完成”之处,仍有“重写”的空间。
值得补充的是,从写作技术上而言,全诗十一行,而前八行每一行都出现了“我”且句式也大体重复,这就使得该诗在表现方式上因为过于强调主体的介入而变得单一和沉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