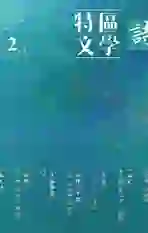我们流泪,听着大海的冲刷声
2022-02-26张高峰
“但是在时代的这种加速度中,谁能留下来和诗歌守在一起?”这是诗人王家新在《饥饿的艺术家》中留下的深切诘问。消费主义兴起与技术时代历史转场,带给个体灵魂存在的是更深的涡流和迷乱的礁石,诗人必须在逼近自我内心的持守之中,回应这一噬心的盘诘。被岁月流转所磨蚀的心灵,也犹如普罗米修斯般,“那被啄食的肝脏/仍在不断地再生!”自八十年代初伊始,诗人王家新四十年诗写的不懈坚守与心路历程,历史的跌宕起伏与时代的巨大变迁,青春的面影与直抵“晚期风格”的上下求索,都使得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代人的生命历练与诗艺探求。那在诗写之中出生入死的求真意志,始终维系于散发光芒的语言锻造中,在时间与记忆宽广的河流里,自过去而向未来敞开。我们看到的诗人王家新,他始终“把写作保持在一种难度里,把人类运转不息的精神保持在一种不灭的光辉里”。每一个时代都会因那些与诗写相依为命的诗人存在而被深深铭记,他们持守着不可剥夺的精神秘密,他们视语言为生命的见证与奇迹,在诗性正义里向我们的灵魂一再发问。
诗集《未来的记忆:王家新四十年诗选》收录了诗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至今近两百首(组)诗作,其中如《帕斯捷尔纳克》《转变》《反向》等名篇,均已在九十年代广为流传,其生命痛感的沉郁之力,强烈而持久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选入的诗人早年的诗作,同样显示出诗人不凡的笔法与独特的感悟,它昭示着一颗诗性的心灵如何成长而来,如《风景》《夜行》《练习曲》《什么地方》等,也预示着诗人在诗性空间内“与世界相遇”而来的体悟。如同雅各与天使的较力无始无终,对于语言的无限倾听,使得被管辖的舌头重新言说,在时代的经验与贫乏中保有了可贵的丰盈,如同诗人在《词语》里所写:“而无论生活怎样变化,我仍要求我的诗中永远有某种明亮:这即是我的时代,我忠实于它。”几十年来,诗人王家新持续不断深入的诗写,源于现实生存境遇与语言变革激流的唤醒,历经着幽暗的强力而朝向着永在的光亮。它们最终连缀成了一位诗人虔诚而执着的生命之域的壮阔景象,那里有着不可磨灭而又令人胆寒的气魄存留。他以语言的不朽来挽留那些心灵的可贵与可泣。在王家新一路诗写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了那些来自伟大诗歌灵魂的聚合和召唤,同时他又倾注心力投入对异域诗人诗作的翻译。诗人曾不无隐喻性地写下,“我从过紧的写作中松开自己,而在别的地方生长起来”。译诗如同换气,是另一种诗性的呼吸,通过了诗人之手的触摸而苏生着无尽的诗性张力。诗人所译的保罗·策兰、叶芝、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等诗人,已然融入他诗歌写作的血骨之中,搅动着一个时代的良知与巨痛。正是通过这样的诗歌和翻译,诗人王家新四十年来日益精进,与“子午线”上那些“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遥相呼应,引领我们进入到“生命的伟大与贫寒”之中。
对于历史生存的省察与个体存在的感知,贯通着诗人深刻的生命体验,王家新的诗成为一种关乎历史的见证与灵魂的辨认。在他的早年诗歌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到夜里/满地的石头都将活动起来/比那树下的人/更具生命”的灵魂风景(《风景》),回想那些青春岁月,“好像我的一生都在走向那个时刻/—海的气息一阵阵涌来/骤然开阔的谷口/一片黎明前的海岸无人来临”(《夜行》)。这些散发着燃烧之蕊的诗行,彻骨而直抵诗性本质,因之而具有了衡度生命的动人力量,它犹如生命之“对视”,“与蝎子对视/顷刻间我成为它脚下的石沙”(《蝎子》)。诗人在打量世界的深度存在,也深知自身的命运,“被冬天的精神充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从不到达”(《什么地方》)。可以说,王家新的诗写自早期开始,便尤为关注对于诗人命运和精神性事物感受力的把握,他那些讓人难忘的诗句,如“把自己稳住,是到了在风中坚持/或彻底放弃的时候了”(《转变》)。也正是源自现实灵魂的深切危机和内在需要,他在三十年前的名诗《帕斯捷尔纳克》,那是“灵魂的颤栗”的悲剧,至今读来仍让人泪涌。
在这部厚重的《未来的记忆:王家新四十年诗选》中,倾听与对话并存,泪与爱被赋予。在生与死的盘诘里,北方明亮的歌声自我们的内心升起,在死亡的高度之中是“山顶的墓石。雪的耀眼的光芒”(《反向》),它来自诗人对于内心的至深拷问与一再重新打量,它源自那“辽阔、伟大、愈来愈急的飞雪”。但是深入体察,这样的雪是“从我的写作中开始的雪”(《日记》),如同诗人所说,“当我想要告诉你什么是真实时,我发现,我不得不用另一种语言讲话”(《见证》),因此诗歌写作也便成为王家新所依持的“内在力量”,诗人以此“来克服外部的痛苦与混乱”。这是他“秘密承受的火焰”,在语言的无垠延展之中,来照亮存在的边界,“存在的只是那在黑暗中发光的声音的种子”(《词语》)。九十年代国外的旅居生活经历,无疑都促使着王家新透过一盏他乡的灯火,在一种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之中,来重新看待母语并思考自我存在的历史根基性。他的诗写也必然随之加深,而发生着内在的变化,“当我在欧罗巴的一盏烛火下读着家信,而母语出现在让人泪涌的光辉中……”“不再是在别处,是在一粒盐的隐忍中,你要经历的是如此巨大……”诗歌的来临不再是其它外在之物,而是诗人深刻意识到的生命被攥住的时刻。
诗人渴望在词语“滞重的阴影”里,书写出那“不屈服于时间的事物”,从而寻回缄默之中永恒的声音。在他的名篇《尤金,雪》里,“一个在深夜写作的人,/他必须在大雪充满世界之前/找到他的词根;/他还必须在词中跋涉,以靠近/那扇惟一的永不封冻的窗户/然后是雪,雪,雪。”在诗歌写作的辨认之中,诗人不断靠近一个灵魂的真实,一个可容呼吸和观看的诗性空间,正如人们看到的,“雪”成为王家新极为重要的核心意象,它指涉的是最为纯粹的语言凝结,但又是十分复杂的情感晶体,一种历尽了冰风严酷之冬的精神性闪耀。这样的“雪”伴随了诗人王家新的一生,“整个冬天他就这样吃着橘子……仿佛/他有的是时间,/仿佛,他在吞食着黑暗;/他就这样吃着,剥着橘子,抬起头来,/窗口闪耀雪的光芒”(《橘子》),“再一次获得对生活的确信,就像一个在冰雪中用力跺脚的人,在温暖自己后,又大步向更深处的雪走去”(《变暗的镜子》)。诗人透过“雪”的意象,朝向了对于整体生存的容纳,它发自“所有那些与寒冷共存的灵魂”,穿织于广阔的精神性存在之中。他通过这样的“雪”,给我们的现代汉语诗歌带来了一种精神性的语言!
诗人王家新的诗总是在滞缓之中,唤起人们生命情感中最为浑厚而沉重的部分,这源于诗人所怀有的那一份深厚的爱,他清醒地意识到正是“痛苦在造就一位诗人”。尤其是在狂欢化的时代喧嚣之下,如同诗人所写,“他在生与死的风景中旅行,/在众人之中你认不出他”(《旅行》),“每年都会有雷声从山头上响起/每年都有这样的雨声来到我们中间/每天都有人在我们之中死亡/雨中的石头长出了青苔”(《八月十七日,雨》)。诗人必须在精神的缺席与在场之中,来深刻地辨认出自我与他者,辨认出宿命的反抗与诗性光辉的永存,这是关于生存真相的揭示与显露,不再仅限于现实的观照,“我相信了这个传说,月亮/就为我徐徐移近。//我们的一生,/都在辨认/一种无名的面容。”(《传说—给杨键》)这种贯穿在王家新近二十年来创作中的“辨认的诗学”,总是给我们带来一种深长的启示。
面对现实的深刻感受和穿透力,使得诗人也曾写下不少充满反讽意味的诗篇,而这些诗作同样来自于诗人生命中沉沉淤积的强烈痛感,它指向外部的批判与剖析,也指向了自我的灵魂审视,诗人的写作也籍此进入到“一阵陡峭的/被刺破的黑暗里”(《写于新年的第一天》)。我们看到《变暗的镜子》里所隐隐郁结的沉痛,“一切都从采石场拉来了,卸下了,而从一台台粉碎机对石灰石的赞美中,出现了我们一生的远景”。语言的悖论中激荡着灵魂的交锋,而在反讽的语式里澄明着现实的幽暗,“葡萄酒沉睡在你的头脑里,而忘却的痛苦有时比一枚钉子尖锐”“活到今天,要去信仰是困难的,而不去信仰是可怕的”。王家新的诗写就这样内蓄着令人不胜唏嘘的喟叹,“不是你老了,而是你的镜子变暗了”“不是你在变老,而是你独自用餐的时间变长了”,这样的惊人之笔,是从时间荒凉的深处而来,它在诗人的笔端寻求出现,也许当一切被时间之锋芒剥蚀了所有色泽,我们方才看清楚了一個人清晰的面影,而它们曾是我们的终生无名的忍受。
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四十年的精神历险与语言跋涉,恍如昨日飞逝,但又似远远走在我们前面。在诗的探索之中,王家新已走得足够深足够远,犹如西行之旅,“他不走,那流动的沙丘就会将他吞没”(《唐玄奘在龟兹,公元628年》)。在王家新的诗性言说之中,往往带给我们令人暗自惊心的感触,这与他深入黑暗深入无名地相互寻找有关,更是命运发生于语言中的刺人呈现,这样的诗语不可更移地捺入我们的心灵。《未来的记忆:王家新四十年诗选》中的最后一首诗是诗人写于2019年6月28日的《在洞头—给王子瓜,一位年轻诗友》,它的最后四句撼人心魄:
“既然生活失败了,诗歌为什么要成功呢?”
我们都不说话了。我们能听到的
唯有大海的冲刷声。
我们流泪,听着大海的冲刷声。
一种巨大的关乎灵魂的痛苦被继承,隐秘的精神联系在恢复,王家新在艰难的历史时空的对话,不仅将我们带入到苦难与爱的墨痕之中,而且将那语言的承受与生命的承受,悉数转化为一个诗人精神的源泉与内在的源涌,从而实现着伟大的生命之树的嫁接与重新生长。在我和许多诗人朋友看来,这是诗人王家新在中国当代诗坛上最重要、也最难得的贡献。
“需要巨大的寒意,来保存我们的火种”,诗人自觉地领受着属于他的天职他的宿命。纵观王家新近些年的创作,一方面他早已进入一个高远的境界,在“时间之塔”上远眺;另一方面又将目光投向了脚下古老的土地,或者用阿甘本的术语来讲,将其目光“紧紧盯在这个时代之上”。历经风霜雪寒,而今那些被诗人所写出的词,依然承受着千年的锈迹,“生长在希望与绝望之间”(《铁蒺藜》)。诗人以其自身的光亮汇入“子午线”上那伟大的精神星丛,成为一种灵魂共同在场的思想受体,使得那些卑微个体生命的尊严得以捍卫得以昭彰。他对于语言的难度与灵魂质地的持守,不因时代的物欲喧嚣、娱乐狂欢而更移。近些年来,他的诗的声音日益内敛沉静,有时甚至是以词语和声音吞咽无尽的悲痛,但却能引领我们进入更为广阔深奥的存在之域。这样的诗已无需关于技艺经验,而是全然容留了泪水的晶体,质朴、孤绝而深厚,迸涌而出于时代幽暗之影中,持久地散发出新鲜动人的光泽。诗歌于此成为诗人终身的存在之家。在他于2019年年初写下的《新年第一首,想起波罗的海,想起一禾》中,他有意引用和改写了诗人骆一禾的诗句:“我们一定要从容地/对必死者说到死/我们一定要从容地/对光荣者说到光荣。”这就是一个诗人历经“四十年”的跋涉最终所从容达到的境界,这同样属于“大海的冲刷声”,足以让我们含泪倾听。
张高峰,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在读。出版有诗集、研究著作多种。文学评论及诗作散见《文艺报》《新京报》《作家》《名作欣赏》《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理论与创作》《星星》《扬子江诗刊》《诗选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