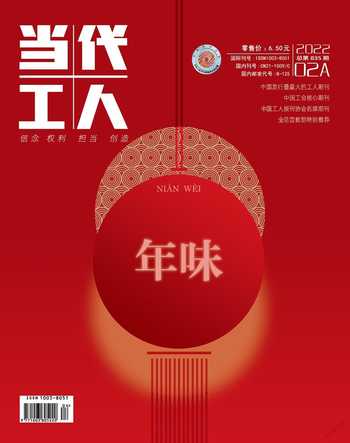在时代的港湾里摇呀摇
2022-02-25麦丰
麦丰
归客千里至
1991年2月7日,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18岁的赵继刚拖着两个大号编织袋,在人潮中踏上回家的列车。
赵继刚是辽宁沈阳沙岭人,初中毕业后只身到广州打拼。当年有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州。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给新建的楼房贴瓷砖,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挣30多元钱,“一个礼拜差不多就能顶沈阳一个月的工资。”如今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赵继刚,回忆当年坐在车厢连接处吃煮鸡蛋的情景,并不觉得辛苦。“没买到座票,但回家过年还是高兴,一年攒了5000元钱,在秋衣缝了个兜揣着,想起来就忍不住挺挺胸。”
直到2011年京沪高铁实行网络售票后,全国铁路才逐步全面铺开网络售票。彼时赵继刚的车票,是他凌晨3点在车站售票处排队,排了13个小时后买到的。如果实在买不到火车票,便只能退而求其次,搭乘长途客车返乡。高速公路修通之前,从广州乘车到河南通常要走两天三夜,如果遭遇拥堵,甚至需要一个星期。河南人刘全富清楚地记得,1993年,他带着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回老家,核定42人的车厢内,生生挤下100多人,过道里摆满小马扎。
临近春节,大部分背井离乡到沿海一带闯荡的务工人员,都会克服车票难求、旅途劳顿的困难,返乡过年。在赵继刚和刘全富看来,过年回家是约定俗成的习惯,不存在“因为孩子太小留守异乡”的选项,“不回去,别人会以为你欠了债、出了事。”
1980年,《人民日报》上首次出现“春运”一词,在随后的数十年中,返乡过年引发的迁徙,如一年高似一年的潮涌,在每年的40天中排山倒海。赵继刚回忆,火车站台上人头攒动,扛着大包小裹的人们往车上挤,儿童和一些身手灵活的乘客干脆从车窗爬进去。小商贩挎着提篮,通过车窗兜售当地的特产和食物,常常火车启动了,还有旅客没拿到应该找回的零钱。车厢里则充斥着各地的方言和复杂的气味,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塞满了人。最拥挤的时候,他整个身体被架在人堆中悬了空,只能趁着火车进站的时候,顺着人流挪动一下,透透气。
20世纪80年代,南京火车站“158”雷锋服务站的李慧娟获评全国“时代楷模”,20年后她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年春运运能极其紧张,有的中转旅客在候车室一等就是一两天,她想了一个办法:为旅客表演快板,让大家藉此消遣并感到温暖。
年夜饭飘香
这一时期,“衣锦还乡”成为不少外地务工人员过年回家的骄傲。1991年,中国GDP不到2万亿,北京月平均工资239.75元,一斤猪肉价格不到2元,赵继刚带回家的5000元,不是小数。
产业结构多元化,带来的不仅是收入提升,亦有物资阜盛。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90年代的年夜饭开始有了明显变化,鸡鸭鱼肉成了重头戏,山珍海鲜和反季的绿色蔬菜,曾经一年到头都吃不到的食物,也已经不再稀奇。1992年,北京西单菜市场推出5种家庭套餐,每套50元至70元,回家一加工就是一桌年夜饭。1994年后,饭店门口“春节休息”的大红告示逐渐消失,在饭店吃年夜饭成了时尚。从涮火锅、涮羊肉,到烤鸭、粤菜、川菜、上海菜,新菜系相继而至,中间还穿插着西餐、自助餐,人们开始追求生活的质量和品位。
辽宁沈阳的何静,家里兄妹三人当年都是端“铁饭碗”的工人,生活条件不错,每年会轮流操办请客。1996年,何静在皇寺广场附近一家新开业的饭店订下了年夜飯,据说大厨是从宝发园挖来的,水熘黄菜是拿手绝活儿。何静说,这道菜听上去像是道素菜,其实是颇有技术含量的荤菜。厨师将鸡蛋打入以鸡架和猪棒骨熬成的高汤中,加以佐料搅拌成高汤蛋液,再把猪油和花生油按照6:4的比例混合,热锅烧到七成,下高汤蛋液,调中火搅拌均匀,使其状态介于鸡蛋羹与豆花儿之间后,最后淋洒上鲜虾仁、鲜豌豆、鲜胡萝卜及鲜蘑菇丁所制的卤汁,入口清淡,稠厚香嫩。“这是咱们家每次聚会必点的一道菜。”
随着改制开始,何静家收入锐减。“大哥下岗了,我和小妹虽然正常上班,但工资一直拖欠着。”何静的大哥下岗后,开了家切面店,做饺子皮成了店里的“支柱产业”,春节期间一天就能卖出去三四十斤。何静和小妹办理了待岗证,在大哥的切面店附近盘了一个小店,专门做手工水饺,可以现点现吃,也可以做成速冻食品卖。三家人的年夜聚餐从饭店挪到家里,但仍尽可能准备丰盛的菜式,熘肉段、锅包肉、炸刀鱼、炸靠大虾、红烧肘子、四喜丸子、凉拌白菜、酸菜血肠……平时节省,过年舍得,“硬菜”仍能摆放一大桌。“过年不能糊弄,要给新一年开个好头,心气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娱乐新风尚
“开个好头”体现在下岗工人浮沉生活的美好愿望中,也体现在女性的新发型上。张荣发是最早“下海”的一批人,原本有着公职的他,不满足于一眼望到头的安稳日子,一个人扛着行李走出家门,先是倒腾了两年录音带和录像带,然后跟着老乡“速成”了美发技术,凭着手艺和头脑挣下了第一桶金。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全国几乎各个城市,哪怕是三四线的小城镇,大街小巷的女性十有八九都顶着像钢丝球一样的烫发造型。赚了钱的张荣发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认准了“当老板才能赚大钱”的道理,相继在河北、湖南开办了职业学校,生意蒸蒸日上。
在赵继刚、刘全富、何静、张荣发的印象中,八九十年代虽然较现在清苦,但不失为一个极富年味的时代,经济发展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生活改善,将丰足、富饶、人人喜气洋洋的年味逐步推至巅峰。时代在摇荡,家庭如小舟,而春节是船上的一个沉锚,让人能够短暂地在浪潮和风雨中暂歇,并得到安宁与快乐。
1997年,赵继刚24岁,第一次掏钱买票进了电影院。这一年,冯小刚执导的《甲方乙方》以开篇“祝全国人民虎年大吉”9个大字,开启了中国内地的贺岁片市场。自此开始,很多影片开始打着“贺岁喜剧”的招牌推出,元旦和春节期间有五六部新片上映,文娱市场一下热闹起来。
人们春节期间的娱乐方式,不再仅仅局限于走亲戚串门,或者待在家看电视。除了看电影,唱卡拉OK、旅游等娱乐方式都成为新兴消遣。数据显示,1997年,北京春节旅游过年的人数在10万人左右,海南全境以及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福建厦门、武夷山等地的旅游路线逐渐火热起来。也正是在这一年,春节期间机票打折优惠的营销手段彻底成为历史,随着更快的火车、飞机取代绿皮车,家人围坐在一起看春节晚会的日子慢慢过去。到了千禧年后,冯小刚凭借“贺岁三部曲”,与葛优一同成为票房的保证,而百姓“过个团圆年”的观念也开始悄然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