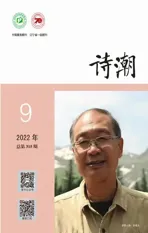当代诗人佳作选读
2022-02-24三姑石赏评
三姑石/ 赏评
三姑石,本名宋心海,70后诗人,生于黑龙江省明水县,现居绥化。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十月》等刊,入选多种诗歌选本。出版诗集《卜水者》《手上香火》等。
恒 河
于 坚
恒河啊
你的大象回家的脚步声
这样沉重
就像落日走下天空
[三姑石赏评] 于坚的诗于我是神一样的存在。想当年,朦胧诗那会儿,于坚、韩东等诗人的诗是我心灵的慰藉,烦躁的缓释,劳累的歇憩,是我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夜,再次与他这首极简的诗行相遇,我忽然想起,帕斯捷尔纳克宣称的才能特征之一,“在白纸面前的勇敢”。
于坚的勇敢在于——
一是超拔的想象力。雨果说,想象就是深度。于坚从寻常水声听出了大象回家的脚步声,表面看似“瞎掰”,细思却极好,有其熨帖与舒服。印度大象数量多,如此庞然大物踏地回声也似轰隆隆,恒河长且宽,排浪本就轰隆隆,且声声撼人心旌。两者有足够大的相似度,有达成比喻的纹理。但这个比喻闻所未闻,可谓大勇。
二是词的灵魂被逼出来。恒河乃印度人的母亲河,是亿万印度人民归属与栖息的源流地,它用宽广博大的襟怀接纳、包容、养育着世世代代的印度人。而“大象回家”,宛如游子回到母亲的怀抱,脚步沉缓凝重,又踏实安稳。瓷白的词的骨骼似瞬间就生出活的思想与跳跃的灵魂。这,不能不说是可嘉之勇。
三是于无形中构筑了天地之间回家之大象。特别是结尾一句出现之后,天地之间,落日回家,大象回家,诗人回家,读者也要回家……而恒河沉默雍容,像接纳他们出生一样,没有任何条件地接纳他们回家。寥寥数语间的气魄,真是神勇。
四是发现了晦暗之光。于坚说,印度那显而易见的历史感沉重得令人窒息,这使得人们的表情呈现出某种尊严,某种自我意识,自信、安详、平静,就像恒河一样。
于坚的诗,大气凝重之象备矣。似有多个进入的入口,而我只是来到了门边,没有更大勇气进入或离开,这等犹疑,似会耗尽一生。
“诗有时就是写一些感受,不一定有那么多意义与价值,意味的发散与语言中的余味更重要”,用林莽老师的话掩饰一下论述之素、词穷之羞。
最软的部位
商 震
已经醉到浑身瘫软
只有僵硬的舌头
还在字字清晰地念着
您的名字:“韩——作——荣”
此时身体里更硬的
是思念
八年了
对您的思念是天火
任何风都不能吹灭
任何黑暗都不能阻挡
念一遍您的名字就喝一杯
念多少遍就喝多少杯
酒是火中浇油
把我的一切烧软
直到声音也软得走不出嘴唇
您却在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鲜活地皱着眉头
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只有您一个人的位置
[三姑石赏评] 奥登说,诗歌通过讲真话来祛魅和解毒。商震借一场酒局搭建造诗的现场,通达斯人与故人对话的航道。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喊出故人的名字,这是在饮泣,也是在嘶喊。
这是生者与死者在一张纸上的故事,是文人与文人在一场酒局里的相遇,是愚兄与仁弟在奈河桥边的别离。是啊——
“八年了
对您的思念是天火
任何风都不能吹灭
任何黑暗都不能阻挡”
八年,时间快到弹指而逝,长到生与死的距离;八年,诗人举着不熄的天火,点亮了思念的天空。“念一遍您的名字就喝一杯/念多少遍就喝多少杯”,一个年已六旬的老人不顾惜状态有失从容,不顾念一把老骨头泡在酒里的酸痛,他沉浸在无限的思念中,似走不出来。
商震在写一篇西行至阳关的随笔中说:“真正的酒应该在阳关喝,阳关才是汉朝以降的酒泉、泪泉。”但诗人又说:“酒大多时候是伴着泪喝的,和泪而饮的才是酒。”喜庆的酒是在锦绣上添了点色彩,痛苦的酒是霜雪中的火盆。喝酒对喜庆氛围的营造作用有限,而对痛苦则是强力的推进器。
在“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诗人忍住没喝,而在念及韩作荣的酒桌上,诗人——
“念一遍您的名字就喝一杯
念多少遍就喝多少杯
酒是火中浇油
把我的一切烧软
直到声音也软得走不出嘴唇
您却在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管理会计人员首先要加强对理论知识的学习,要保证具备一个技术型人才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与素养;其次每一个工作人员要熟练计算机操作技能,要扎实并且熟练的运用各种软件;然后公司要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要确保团队时刻了解社会发展的状况,让他们的技术紧跟时代的步伐,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与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样才能保证团队工作中通力合作,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利益。
鲜活地皱着眉头”
借酒消愁,诗人以酒于霜雪中借念故人之暖而取暖,以酒于痛苦中追思故人之痛而痛彻。大悲,亦是大歌,那是心之荒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壮美。
“我心里最软的地方,只有您一个人的位置”,这个位置是诗人商震于灵魂中搭建的,须仰望的位置,冷酷如白雪的白,酌热如阳光的光,让人望而生痛,心旌激荡。
坍塌时间
玉 珍
在这件事情上时间早已隐身
年岁与年代也消失无迹
只有一种感觉比任何事件清晰
那会儿天空很美,母亲和小姨
在寂静的风声中站立
我很矮,脸挨着母亲某粒扣子
一个老旧的竹篮被拿在手里
将要被拿来盛装香草
我们正准备出发,去幽谷中采摘植物
就在那时死神忽然掠过
屋子在风中展开了裂隙
像一种放弃
坍塌在我们的身上
[三姑石赏评] 诗人写下这首诗,应该是她走出了那个时间,来到了纸上的这个时间。
诗人在开篇写下“在这件事情上时间早已隐身/年岁与年代也消失无迹”的诗句,意在强调无论时间多远多久,痛会一直痛彻;坍塌的阴影、破碎的声音不会消失的执念。
特德·休斯说,任何诗似乎都必须是那些掌控我们生活的力量所发出的陈述,必须是我们的终极痛苦和决定所发出的陈述才能够成为诗。
诗人玉珍就是这样一个陈述人。她放下了肩头的山峰和隐藏于心的凶器,开始平和地讲述一个事件或一次意外,而这件事“只有一种感觉比任何事件清晰”,似乎一刻也没有远离。
多美好的画面啊!“那会儿天空很美,母亲和小姨/刚迈出房门/在寂静的风声中站立”,还有小小的我,“脸挨着母亲某粒扣子”。这是生活真实的画面形象化地回放与定格,是诗人对美好过往的深情聚焦与咀嚼。
透过文字,我们看到“一个老旧的竹篮被拿在手里/将要被拿来盛装香草/我们正准备出发,去幽谷中采摘植物”。彼时的诗人及家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节奏与行走的姿态,是诗人铭刻于心的坍塌时间的开始。
呜呼!“就在那时死神忽然掠过/屋子在风中展开了裂隙”。诗人与读者都被拽入了诗意构建最危险的时段,而那展开的裂隙,张着大口,似要吞噬眼前的一切。
最后的诗意,恰在此时,从最紧张的裂隙间喷涌而出——
“像一种放弃
坍塌在我们的身上”
这是最后一句诗,也是最大诗意的开始一句。诗人在此间,给了这个结尾以足够的宽阔度和开放度,使诗意更加多元与多趣。
死神拿一个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人没有办法,他远远地盯着废墟,看到一个人从坍塌的时间里站起来,只好摇了一下头,转身溜了。
高原上的野花
张执浩
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我愿意将我的祖国搬迁到
这里,在这里,我愿意
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
像那条来历不明的小溪
我愿意终日涕泪横流,以此表达
我真的愿意
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
[三姑石赏评] 张执浩的诗有一种独特的气息,他的绵密、细腻、用情似无人能敌。与他的诗遭遇,往往会有幸福的烦恼,深陷其中,难以轻易脱身。
这首诗选定高原上的野花作为观照对象,必有深深用意。
其一,让人感受到社会人回归自然人的诗意温暖。
诗人、你或者我,投入广袤的自然界或一带高原,从社会人做回自然人,忘记烦忧愁绪,欣赏高原上满野的小花,看到格桑花或蒲公英等竞相绽放,心就会一下子被浸润,由坚硬变得柔软,由防御变成打开,由纷乱变到多趣。心,瞬间变回自然心,人也会回归到自然人。
而满眼满野的花儿又不是花儿了,乃是众多的小美女。诗人不吐不快:“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人性的博大、温暖和芬芳,在高原宽阔的臂弯里似乎一下子就得到充分释放。
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的自然心仅仅是装在皮囊里,关在栅栏中。写在纸上,那往往是诗人才有的奢侈。
其二,雕塑了一尊足以让儿女膜拜的神。
读这首诗,心会有疼痛感,并一点点加剧。诗人用了四个“我愿意”,加一个“我真的愿意”。这让人想起结婚典礼那两声“我愿意”的互为应答。而在此诗中,这是一个父亲,“愿意将我的祖国搬迁到这里,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在对“女儿”起誓,而且他愿意为女儿的幸福“终日涕泪横流”。
允许我傻傻地想到结婚典礼时在一个角落里失声痛哭的那对父母,读这首诗时,我已经泪眼蒙。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这就是一个好父亲的形象,一个五千年文化滋养下隐忍的父亲,伟大而平凡。为儿女付出一切,可以把泪水当成子弹咽下,也可以把自己当成炸弹投出去。
父亲是我们宗教和信仰般的存在,诗人在纸上画了一个我们的父亲,一个让我们想起就想哭出声音的父亲,是儿女顶礼膜拜的神。
其三,让人扑到了一个温暖的襟怀里。
“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这里“为任何人”,恰是诗人的大慈悲、大境界的表达。诗人在这里似乎在提示、告诫自己和世人,要做好自然的、社会的父亲,承载起应有的本分和责任。
这不是诗人的高蹈,是诗人敞开了拥抱世间万物的襟怀。这应该是诗人的良心所在,是作者的终极表达,也是诗意的最后大成。
当然,这首摇曳多姿的小诗,也许诗人别有怀抱。那些野花,它们是娉婷的、芬芳的,在人迹稀少的高地,它们也是纯真的、圣洁的,它们以高尚的品质,让人怜惜、珍爱。所以诗人是多么惊喜,在遇见它们的那一刻,他想到了祖国。他把祖国辽阔的疆域浓缩于一朵花上,他是多么希望生养他的祖国能像这些野花一样美好、明亮。他唯一的目的,只是想像那条自然而生的小溪一样,自然流淌,滋养万物;只是想由衷地、感恩般涕泪横流地做一个把所有的愤世嫉俗变成花的养料的老父亲。野花之于披头散发的诗人,宛若香草之于形容枯槁的屈子……让人陡然思接千载。
蕨的记忆
桑 克
我明白我为什么对蕨一见倾心,
因为它们对称的叶子,因为它们野蛮而不失精致的绿,
更因为对于没有见识过永恒的我来说,
它们的古老几乎就是永恒。
所以我才常常站在它们的身边一遍一遍
单调地重复惊叹词而说不出其他的词来,
而且惊异于同样是对称的叶子为什么每一类蕨对称得
都是这么不同,如果我的诗也是这样……
我不能贪婪地想下去,我不能冒犯
这些年老的长辈,我不能让沉默的呼噜声
触动安静的些微涟漪,我只能仰慕地
看着这些蕨坦然地睡在骄傲的松柏的缝隙
……
[三姑石赏评] 这首诗有明显的桑克缜密之思的痕迹。诗人应该是在一个忙里偷闲的缝隙,回首故乡或者以往经历时想到了可以寄予闲愁以曾经一见倾心的蕨。“因为它们对称的叶子,因为它们野蛮而不失精致的绿”,诗人忘不掉那段生活,那是躲藏在记忆深处的疑问,也是他试图找到的诸多问题的答案。
蕨在诗人笔下已经不仅仅是蕨本身,他是诗人能抓到的时光中的时光,是可以代替不老时光的观照物。诗人似乎执着地选定了它,在每一次抬头的时候,都会发现“对称的叶子”上面,那“野蛮而不失精致的绿”。面对蕨的一笔一画,诗人之思已经切近一个曾经封闭的内核中,他要砸碎核壳,誓要找出“更因为对于没有见识过永恒的我来说,它们的古老几乎就是永恒”的这样之思,诸如核仁儿一般有营养的思之成果来。
面对蕨,诗人是诚实的,似要掏出心来。“所以我才常常站在它们的身边一遍一遍/单调地重复惊叹词而说不出其他的词来”。这是诗人的惊诧,也是诗人的犹疑或迷茫。我不知道诗人是受到了美的震慑,还是面临了思维的危机,我们明显地感受到,诗人眼前的蕨,是谜一样的存在,是神一样的出现。
诗人面对蕨是小心的,充满新奇和热爱的。诗人似在把自己变成充满泪水的海绵一样酝酿他之思,寻找他之诗。诗人在面对蕨时,那样不可抑制地亮出深藏于心,似已久远的最大的底牌:“而且惊异于同样是对称的叶子为什么每一类蕨对称得/都是这么不同,如果我的诗也是这样……”这一刻,我们感受到诗人要把蕨放到一首诗中,也感受到了他视诗如生命的决绝。
在诗人的眼中,蕨已然就是生长在诗中的文字了。“同样是对称的叶子为什么每一类蕨对称得/都是这么不同”,诗人要从对蕨的世界的思考中,找到属于他自己诗的世界的精彩与呈现。
作为用灵魂写诗的诗人,诗就是全世界。桑克内心的谦卑和虔敬一直在,“我不能贪婪地想下去,我不能冒犯/这些年老的长辈,我不能让沉默的呼噜声/触动安静的些微涟漪”。“敬”之大者,乃是人,在诗人这里,是先人,是长辈,可见诗思之奇崛。面对蕨,诗人想到了那些站过的肩膀,那些挺举过他的手掌,那些注视过他的慈祥目光。诗人似不敢想到他的诗了,他的思想似遇到了小小的阻力,他要慎思、慎行、慎下笔。
“我只能仰慕地/看着这些蕨坦然地睡在骄傲的松柏的缝隙”,能明显感受到,诗人非常羡慕蕨的坦然和骄傲,他似乎要在一首诗中找到一道属于他的“松柏的缝隙”,而那缝隙好像是一个愿景,诗人穷其一生也无法企及。
在老虎中间散步
唐 力
我在老虎中间散步
那些老虎,散落在
山坡上,岩石边,草地上,阳光下
或者躺卧,或者蹲伏,或半仰起头
或者站立,或者走动
众多老虎,它们目不斜视
或者顾盼有姿,就是
对我熟视无睹
它们有的细数身上闪电的斑纹
它们有的被自己身上的黄金
所惊动,而抬起头来
它们有的悠闲地走来走去,就像
穿着横纹睡衣的老人一样
我就在它们中间散步
不惊动它们,也不
与它们混为一谈
我的颜色并不比它们鲜艳
但我是站立的,我比它们要高
我的孤独,也因此格外醒目
[三姑石赏评] 这是一首出名较早的新诗,我与其相遇却较晚,但还是有幸成为他的时空伴随者,从暗自关注到今晨的凝视,一首好诗被我筛出来。
读着读着,似有公园、虎园和人园等“三园”于隐秘处从诗境中明晰起来,恰如此刻天光,正欲大亮。
一曰公园。
特别是读诗的前半部分,感觉诗人正在一处公园闲游:“我在老虎中间散步/那些老虎,散落在/山坡上,岩石边,草地上,阳光下”。因为这是一处置放了诸多小品之虎的公园,诗人才敢或才会有机会于此间闲庭信步。从这个层面考虑,似做实诗人是在一堆摆放石造、铜制、土砌的非虎之虎的一处公园里。
诗人似有闲情,似还携妻掖子了,只为于众多似虎非虎之间,采撷一些欢乐。诚如读诗之我,此时亦有入园之乐。
二曰虎园。
哈尔滨有座虎园,多次去光顾,而每次看到“或者躺卧,或者蹲伏,或半仰起头/或者站立,或者走动”的那些老虎,总似有它们已非虎的感慨,总觉得虎啸山林、虎影仙踪于它们是个笑话。诗人敢于此间如此淡定行走,或于想象的栅栏外如此大摇大摆行走,可知其藐视之情备矣。
“众多老虎,它们目不斜视/或者顾盼有姿,就是/对我熟视无睹”。呜呼,这些老虎似无一点野性了,它们的王者气已俨然消弭殆尽,对诗人这一人肉已熟视无睹。或者,还有那么一层理解,人类对其豢养是成功的,使其老实,也使其退化。
虎园于游客不仅弥漫着新奇,也氤氲着遗憾或叹惋,于读者,却感觉诗人笔力沉实毕现。
三曰人园。
诗中之虎,不就是人吗?
“它们有的细数身上闪电的斑纹
它们有的被自己身上的黄金
所惊动,而抬起头来
它们有的悠闲地走来走去,就像
穿着横纹睡衣的老人一样”
忽然让我对天地间有了人园的想象。如果单就我之清浊怒怼这些大老虎,也没有什么理解之高妙,这也有赖对此诗理解之与时俱进所赐。
大凡园者,皆有围墙、栅栏或看管,在虎与人同的大背景下去理解,此诗之神意缓缓而至。人类与虎类确是被管束了,这就有了或有罪或无辜之辨,人类?虎类?
于此台阶去观望,人园之大意义于诗意中瞬间黏稠了许多。
“我就在它们中间散步
不惊动它们,也不
与它们混为一谈
我的颜色并不比它们鲜艳
但我是站立的,我比它们要高
我的孤独,也因此格外醒目”
这是于“三园”中悠然出入的诗人,或诗中之我。可知此人淡定,于虎影中如常散步;可感此人清醒,于卧虎中虽颜色不比虎们鲜艳,却保有站立之姿,高出一头之状;可叹此人寂寞,于众虎之中,多囿于虎屈膝胆破还走之流,“我的孤独”还是寂寞处的风景,“也因此格外醒目”。
诚如朱零点评此诗时说,唐力是孤傲和自负的,与一堆动物为伍时,只有人格独立的人才活得如此低调和孤单。
如此,好诗源头可知矣。
西藏:罗布林卡
娜 夜
它是我来世起给女儿的名字:罗布林卡
它是我来世起给女儿和儿子的名字:罗布和林卡
它是我来世想起今生时的两行眼泪:罗布……林卡
[三姑石赏评] 要学会与一首诗相处,了解它的心地、本质、背景等诸多方面,才能更好地找到进入诗意妙境的可能性。
这首诗的诗题标注诗意的源流地是西藏,因为是西藏,这首诗的纯净和辽阔就是必然的了。人类许多美好的畅想都可以在西藏被寄予。我曾去过那里,看着天空那种大蓝,雪山那种大神,河流那种大美……让人很容易产生如梦似幻的感觉。所以说,诗人娜夜在西藏罗布林卡那一刻,在园林里散步徜徉的时候,特别是罗布林卡这四个字组合所带出来的那种亲切的感觉,触发了她内心的无限温柔与伤感,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母性之伟大,就在于对追求母性成就的热望,那就是成为母亲。
仅仅一个普通的地名,让诗人有了绵绵的情思,联想到女儿,甚至又刻意地强调了一下:女儿和儿子。最后,她想到了两行眼泪。不管诗人是否有女儿,是否有女儿和儿子在遥远的来世,现在,那最珍贵的眼泪如此晶莹且锐利地穿透了一个女人的一切。
深入思量,此诗似还有峥嵘意。把集文化、艺术、宗教等于一体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称为女儿、女儿和儿子,既是奇崛的比喻,又是为人母者最美好的期许。而那两行眼泪却有些复杂,既有叹惋今生未尽之美好的哀愁,又有伤怀来生未达成之爱意的忧患,甚或还有一切圆满的感动与感恩。
而罗布林卡,罗布和林卡,罗布……林卡……这语感节奏又似转经筒发出的诵经之声,更似从诗人身心上溢出的雪莲般的纯净高洁的气息。
无疑,这是一首美好的诗,一首忧伤的诗,在极简省的文字下面,凝结着诗人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种情思,一种温暖。
而我,于这个月夜,正享受一首诗带来的欢愉和洞见。
在开往哈达铺的火车上
杨森君
我辨认着
与我的命运一致的人
我在很多人的
面孔上寻找自己
沉默寡言的
心不在焉的
兴奋的
疲惫的
幸福的
操劳的
我居然在一个小男孩的面孔上
看见了自己小时候的模样
——他在一位年轻妈妈的怀里酣睡
[三姑石赏评] 这首《在开往哈达铺的火车上》所呈现的应该是诗人推定或不得不面对的诗意现场。在一个封闭的、枯燥的、无所事事的但又人群密集的时间与空间中,诗人有机会静下心来,他没有把自己的心思投向窗外,而是于无数的车厢内对应的人与物中,寻找并发现自己,重新审视并确认自己。
我好像发现诗人手中有一架虚无的相机,从远处向近处切入,从宏观向具体推动,从别人的脸向自己的脸转换,最后完成从远拍到近观,从普遍到个案辨识,从他拍到自拍的机智反转,实现诗意的有力构建。
在车体的抖动中,在各色人等的“聚集地”,“我辨认着/与我的命运一致的人”。诗人好像习惯性地呷了一口茶,又慢慢地用大手攥紧了跟随自己多年的大茶缸子,平静的表情下,是一层层动荡的涟漪。
车厢里,小世界,大人生,面目各异的人,命途也不一,但诗人于万千人中发现了形似自己,或确是自己的,深藏着过往、现实,已属于胶片定格的,已经积攒了浅灰的脸。
“我在很多人的
面孔上寻找自己
沉默寡言的
心不在焉的
兴奋的
疲惫的
幸福的
操劳的”
诗人透过镜头在一张张脸上寻找、确认自己,也是在寻找、确认命运。在这些不同的脸上,诗人找到记忆中自己不同的脸,他们在一个荧幕上流动了起来,那一张张脸的变迁中,是凝固的过往,也是定格的时间。当自己在他人的脸上清晰呈现,整个车厢忽然响起同一种命运的旋律。殊途同归的指向,生活的复制与重叠,令诗人似乎无法辨认本应迥异于他人的存在。
然而,寻找终会有所结果,诗意,也终会一步步逼近。
人在旅途,如人在荒野,颤抖的灵魂似无以栖居,于冷暖交替中,于万千矛盾中,诗人似乎弄丢了自己,而孩子却如星辰陡现。“我居然在一个小男孩的面孔上/看见了自己小时候的模样”,我们好像能觑见诗人惊喜的表情,“他在一位年轻妈妈的怀里酣睡”,他找到了自己最初的样子,也找到了那份只属于自己也区别于他人的面孔。
是啊,当孩子在一个温暖的包容的怀抱中时,恰如处于一个皇宫。而放逐般的成长,确如流放、流浪,有他必须承受的悲苦,必须面对的世相,必须在不断放弃中寻找新鲜的自己。
列车没有停下来,诗人心灵的或现实的“哈达铺”还在远方,等待抵达无法选择和确认的终点,既是一种结果,又恰如一次判决。
女 人
康 雪只有你知道,她的里面有星星她的外面有落叶的树。只有你知道她所剩无几的美也足以怜悯天下她的双手粗糙。你一触碰就会流泪。只有你知道她如此特别。她生下的都是君王,以此隐瞒她君王般的命运。
[三姑石赏评] 我固执地认为,康雪写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和母亲的一生。

李小洛绘画作品︽看到风经过的地方︾
“只有你知道,她的里面/有星星。”母亲有朴素的理想,她的眼中有活泼的星星,她的一生本会像银河一样璀璨。然而,理想毕竟是理想,“她的外面/有落叶的树”,有金黄的秋草,有秋风一样的哀愁,有秋雨一样的悲戚啊。
我见证了母亲从年轻到衰老似弹指间的过程。“只有你知道/她所剩无几的美/也足以怜悯天下”。是啊,我的母亲,也是天下人平凡的母亲形象,虽垂垂老矣,却依然有怜悯,有热爱。她似在等待,要把瘦瘦的骨头也点燃了,只为最后释放出所有光与热。
于儿女而言,母亲最具牺牲精神。前几日在哈尔滨,认真抚过母亲的手掌,“她的双手粗糙。你一触碰/ 就会流泪。”是啊,这就是抱着我、背着我、拽着我的那一双手啊。它经历了什么?它经历了什么不重要,“只有你知道/她如此特别”。它,此刻是我手中的宝,也正如我,依然是她手中的宝。
“她生下的都是君王,以此隐瞒
她君王般的命运。”
至此,赞美从诗中显现出来,于整首诗的内敛中喷薄而出,轰然灌顶,使诗意瞬间抵达。
天下母亲的内心都安放着一把大坐椅,她们的孩子就是座上的君王。这是女人心中人人都有的骄傲,但是好像一直没有被谁提及,诗人敏锐地找到,见证了他发现力与创造力的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