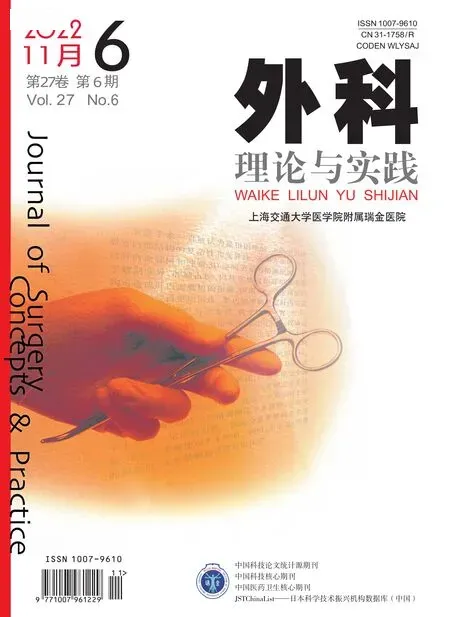腹膜后肿瘤外科的规范及手术质量控制
2022-02-24邱法波曲腾飞
邱法波, 周 斌, 曲腾飞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腹膜后肿瘤外科,山东 青岛 266003)
腹膜后肿瘤是一类包含众多病理类型的罕见肿瘤,其中恶性原发性腹膜后软组织肉瘤年发病率仅占恶性肿瘤的1%左右。虽然手术切除是该类肿瘤治疗的基石,但是腹膜后肿瘤外科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历史并不长远,其相关理论及技术实践仍待完善。
随着近年国内各种腹膜后肿瘤相关学术组织的成立,制定多份专家共识。通过技术推广和专家共识巡讲,使得腹膜后肿瘤外科的国际先进治疗理念和技术迅速推广,我国腹膜后肿瘤外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全国越来越多的医院陆续建立独立的腹膜后肿瘤外科或亚专科,更多医师施行腹膜后肿瘤手术。腹膜后肿瘤外科手术往往横跨多个学科,手术团队需要具备处置普外科、泌尿外科、血管外科、妇科甚至骨科等学科复杂状况的能力。手术创伤大、风险高,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住院时间长是复杂腹膜后肿瘤切除术的公认特点。近年来,随着对腹膜后肿瘤生物学行为理解的加深,在进行手术规划和决策时,外科医师需要平衡生存获益与手术风险制定个体化策略。因此,腹膜后肿瘤外科的规范和手术质量控制显得尤为重要。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腹膜后肿瘤外科领域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已得到显著提高。年手术量100例以上的腹膜后肿瘤中心,也在逐年增多。人口众多和卫生经济水平差异大,直接反映在我国腹膜后肿瘤诊治能力上的区域差异。外科诊疗规范和质量控制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只有加强腹膜后肿瘤诊疗的规范化和手术质量控制建设,才可能实现全国范围内诊疗的同质化,惠及更多的腹膜后肿瘤病人。
腹膜后肿瘤外科的专业化和集中化
目前,在大的医疗中心,随着学科建设的细分,临床专业划分越来越细,有利于解决腹膜后肉瘤这类罕见且异质性高的肿瘤。该类病人的诊治日趋集中化,也促成高流量医疗中心的形成。较多证据表明,在欧美高流量医疗中心,腹膜后肿瘤病人的近、远期预后以及安全性均好于低流量医疗中心[1-3]。
由于腹膜后肿瘤的特殊解剖位置,紧贴背部肌肉、脊柱,周围存在大量神经、脂肪及纤维组织,常侵犯神经及大血管、消化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等脏器,手术中往往需要联合脏器切除。因此,在欧美明确要求,腹膜后肿瘤外科医师要精通、至少掌握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血管外科、疝与腹壁外科、泌尿外科、妇科甚至骨科等专业常用的手术技术或技巧[4]。因此,也只有专业化和集中化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培养出合格的腹膜后肿瘤外科医师。另外也只有集中,才有可能在该类疾病中进行高质量的临床研究,为临床决策提供更好的证据。为了促进腹膜后肿瘤外科持续健康的发展,除加强交流培训外,建立腹膜后肿瘤外科准入制度,也有利于专业化和集中化的发展。
腹膜后肿瘤多学科诊疗团队
腹膜后肿瘤外科手术应在三级综合性医院开展,以腹膜后肿瘤外科专业为基础,采用由多个学科有经验的医师共同讨论决定治疗方式,即多学科诊疗团队(multi disciplinary team,MDT)的诊疗模式。该团队应由掌握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并熟悉腹膜后肿瘤诊治指南、能在临床工作中践行规范的医师组成。腹膜后肿瘤诊疗的专业化团队应包括腹膜后肿瘤外科、肿瘤科、麻醉科、病理科、影像科、重症医学科、营养科等有经验的医师,需要时邀请肝胆胰外科、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妇科等科室的医师参加,共同讨论制定诊疗方案。MDT模式已成为恶性肿瘤诊疗的基本要求。对于腹膜后肿瘤这类罕见异质性高的难治性肿瘤,MDT尤其重要。MDT在术前诊断、手术实施、术后管理、非手术治疗的各个环节都承担重要作用,应体现在腹膜后肿瘤全程化管理中。
腹膜后肿瘤外科医师的规范化培养
腹膜后肿瘤外科是外科领域中复杂而又新兴的学科分支。其专科医师的培训远非目前的医师培训体系所能实现。作为学科,腹膜后肿瘤外科尚未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腹膜后肿瘤外科手术更是在遵循外科基本原则下,借鉴运用多个外科专业的技术技巧。腹膜后肿瘤治疗技术和理念不断更新。这些都是腹膜后肿瘤外科医师培养所面临的挑战。跨大西洋腹膜后肿瘤协作组在成立之初,就开设面向全球的培训课程,值得借鉴。因此,我国的腹膜后肿瘤学术组织和一些成熟的高流量医疗中心,有责任编写系统的专科医师培训教材和开设系统的培训课程。
此外,重视梯队建设,加强对各级医师的培训,严格管理每一个医疗环节,并定期考核,建立退出机制,才能全面控制和提升腹膜后肿瘤的手术质量。
手术质量控制
一、手术适应证
根治性手术切除是目前腹膜后肿瘤有希望得到治愈的唯一方法。除身体条件极差而不能耐受手术、肿瘤广泛侵犯不能切除、不可控制的远处转移外,均应争取手术治疗。对于局部复发的病人经过MDT综合评估后可从手术切除中获益 (包括潜在的根治切除机会、减瘤以便为全身综合治疗争取时间、单纯缓解症状等),也建议积极手术切除[5]。
二、手术入路及关键技术
术前应根据影像学检查结果来确定手术切口、入路和手术方案。由于巨大腹膜后肿瘤常累及邻近器官,可能合并联合脏器切除[6-7],因此,良好的手术切口有助于肿瘤暴露,是手术成功实施的先决条件。最常用的是腹部正中切口。若需联合左右侧脏器切除等额外暴露时,可向两侧横向延伸。骶3以下直径<10 cm的低位肿块可采用经骶尾部切口,术中切除尾骨,必要时甚至可切除第4、5骶骨以暴露术野[7-8]。其他联合及少见切口:盆腔巨大肿瘤经单一入路无法切除时,可采用经腹经骶联合切口;若肿瘤侵及膈肌甚至胸腔,必要时可选用胸腹联合切口。
位于右侧腹膜后的肿瘤可能需要Cattell-Braasch手法以评估下腔静脉、十二指肠、胰头和回肠、腰大肌、肾脏的受累情况,左侧肿瘤可能需要Mattox手法以评估远端胰腺、脾脏、主动脉及其分支和直肠情况[9]。对于肿瘤巨大而侧方暴露困难的,同时为提前控制肿瘤血运,可采用中线入路,由足侧向头侧紧沿腹主动脉或下腔静脉离断大血管进入肿瘤的血管分支,沿肿瘤内侧继续分离至肿瘤基底部[10]。
三、手术切除范围
国内外指南及大量文献都认为首次手术切除是腹膜后肉瘤获得根治的关键[4,11-13]。根治的关键是获得阴性切缘,对于腹膜后恶性肿瘤,以脂肪肉瘤等为代表的肿瘤常与周围正常脂肪组织无法分辨界限。另外巨大肿瘤往往与多脏器粘连紧密或关系密切,依靠术中冷冻病理学检查决定手术切除范围很困难,手术切除范围更多依靠术者的经验来判断和确定。因此,目前的共识是将腹膜后肉瘤的彻底切除定义为R0/R1切除,即由手术者判断彻底切除肉眼可见的肿瘤。近年来随着对腹膜后肉瘤生物学行为及复发转移模式认识的加深,主张依据组织学类型来确定切除的范围,避免手术范围上“一刀切”[4,14]。
无论既往手术是单纯肿瘤切除还是联合脏器切除,对腹膜后肿瘤术后局部复发的病人,再次手术的目标,仍是尽可能获得R0/R1切除。对于腹膜后肉瘤的寡转移,如恶性程度低,可考虑手术切除转移灶。
四、微创技术切除腹膜后肉瘤的适应性评价
随着机器人及腹腔镜微创技术及设备的发展,微创方式切除腹膜后肿瘤的报道越来越多。对于诊断明确而体积较小的良性肿瘤,可行微创手术切除。腹膜后良性肿瘤中,神经源性良性肿瘤最多,因位置深,在脊柱两侧,传统开腹手术暴露困难。此时,微创或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可避免扩大切口,且对神经显露更清楚。本中心经验是肿瘤直径最好不超过10 cm,且与下腔静脉及腹主动脉没有严重粘连,否则,腹腔镜手术操作视野受限,游离困难,增加手术时间[15]。对于腹膜后肉瘤,由于瘤体多较大、与周围脏器关系密切,多需经过仔细探查,特别是用手触摸,才能确定手术方案,且首次根治性切除可能是病人治愈的唯一机会,因此,在现有的技术和设备条件下,不适合进行微创手术[16]。
五、围术期并发症的评价及远期生存预后评价
腹膜后肿瘤手术复杂,术后并发症涉及几乎所有腹部外科的并发症,尤其涉及大血管切除吻合以及多脏器切除的手术,术后并发症更为严重,死亡率较高。腹膜后肿瘤术后并发症以出血、感染、肠漏等最常见,其中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即使在高容量的手术中心仍可能接近20%。术后死亡率2%~7%,死亡原因多为多脏器功能衰竭或严重感染引起的脓毒症[17-19]。
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因肿瘤不同而差异很大,包括组织学亚型、分级、大小和多灶性、病人年龄和合并症等特征;以及治疗变量,包括切除的完整性、诊治中心的专业性等。高分化脂肪肉瘤预后优于去分化脂肪肉瘤[20]。腹膜后恶性肿瘤完整切除及部分切除病人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69.3%、21.5%,仅行活检的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仅为8个月。联合脏器切除的病人5年生存率为73.2%。完整切除术后局部复发率为44.1%,中位复发时间为11个月[21]。完全肉眼切除(R0/R1)与腹膜后肉瘤病人的总生存率提高有关[22]。考虑到高级别腹膜后肉瘤复发的中位时间为根治术后5年,因此,即使5年以后仍需每年进行随访。即使在15~20年后,完全切除腹膜后肉瘤后也存在复发的风险,应无限期地随访病人[4]。
展 望
我国有多个腹膜后肿瘤中心建立了数据库,但格式不统一,难以融入国际主流腹膜后肿瘤数据库。没有有力的数据支持,就难以做出有说服力的高质量临床研究。因此,建立我国全国性的腹膜后肿瘤病例登记制度,可弥补这一短板,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资料共享,为腹膜后肿瘤外科的质量控制和基础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数据化和信息化是大势所趋,建立信息化质量管理平台也是腹膜后肿瘤外科发展的方向和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基础和关键。借助信息系统的建立、评价工具的开发和数据分析等,可加快腹膜后肿瘤外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