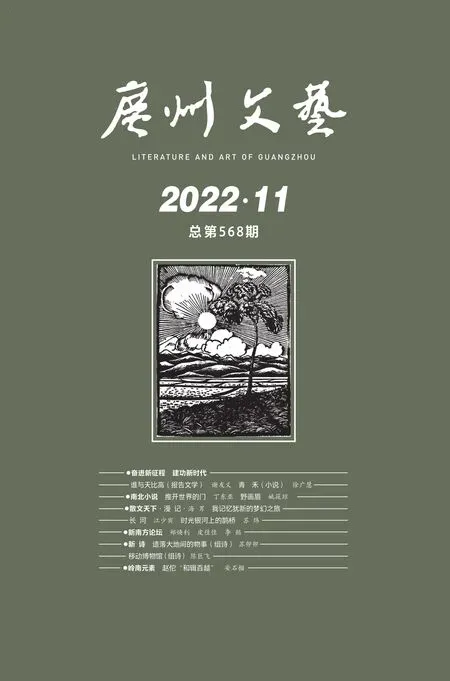遗落大地间的物事(组诗)
2022-02-24苏卯卯
苏卯卯
一些有光的词语
小侄女作业组词。她的声音
枝丫一般指向了春天的另一个方向
“光——
春光、月光、日光、目光……”
多么有趣,这些恬静的词语
每一个都举起明媚的光束,都若
胸怀火焰的智者,那么温暖、通透
而生活中,这些有光的词语
多么生涩。那些读懂的人,有的成了正人君子
少数把自己读疼了的人
成为圣人。我要感谢它们——
在黑暗的时光崖边,在日暮潦草的孤独穷途
曾不止一次将我指引
是我一生的恩人
山居日常
一日:要浣洗白云,梳理门前老柳的头发
唤醒东去的小溪。并告诫其尘世无涯
别只顾急着匆匆离去
一日:要采摘足够的桃花杏花,配以春风春雨
酿一坛美酒,祭祀生我养我最后还会葬我的黄土
一日:整理家谱,修缮记忆和童年
夺回蜘蛛安营扎寨的家。重新把落日、山峦和故人情
一一触遍
榕树情
一个人守住有阳光的下午是幸福的
今天是星期六,女儿和妻子出门。老母亲也去老家种菜。而我呢,喝茶读诗
累了的时候对着屋外唯一的一棵榕树发呆
虽然看不到它的年轮里密集的风声和雷电
也错过了它的青葱岁月和芳华。但它
脉管从容的曲线,以及依旧笔挺劲拔的树干
足以让人钦佩。大半个下午,我们心照不宣
各忙各的。老友般偶尔远远地注视着对方
眸光间善意荡漾。一阵又一阵的风吹来的时候
我和屋外的行人一样抱紧了身躯
只有它挺着腰板在摆动,叶子拍手般作响
那一种声音仿佛在嘲笑我们——
这些面对生活的逼仄低头弯腰的人
水洛河腹地
黄昏美得出奇。我愿意
从这里开始,走向那一座座披着白雪的山峰
麦子地下,曾经埋着月光的地方
此时铺满了大块大块黄金。寒冷的黄金
和雪一起被风吹打着
让人怀疑在北方,有那么一位神灵
从亘古到现在,总是在吹着一只古埙
吹得芦苇弯腰,三五个孩童
迷失了家的方向
沿着水洛河的腹地狂奔。那种
庄严的速度,像是来自中世纪时期的骑士
追逐着落日从史册的尾页
火焰一样寂灭。天空伸出手指
点亮星辰,又替阴云卸下了负重
父亲的遗物
整理房间,无意间碰到
父亲生前的一些旧物。一只褪色挎包
一本革命日记式笔记本,一些书信
那些曾带着父亲体温的物什
冰冷寂静。但面对着时光的打磨宠辱不惊
这符合父亲的性格。在他最后的日子
疼无数次在半夜和他谈话
他却忍受着不出声
翻阅那些俊秀的字迹,一张张
泛黄的纸上。岁月重新回过头来
作为一个无父之人,尘世间艰难跋涉这么多年
本以为自己足够强大,但是那些字符
轻易地就拔出了泪水的根须
尘世如此悲凉,抱着这些
能给我温暖的旧物。和它们的相同之处是
我也是父亲的一件遗物
有些记忆是无法忘记的
有些记忆是无法忘记的。比如
绝望的眼睛。我曾在父亲弥留之际看到过
那带血的瞳孔里,闪现着
不舍的泪光
我一次次看见斜阳,在山峦上
缓慢坠下。那种情景像极了一个人最后的时光
一堆决绝之火,烧红了泥土
又燃疼一颗孤独之心
在秋风萧瑟的车站。薄霜
染白了年轻母亲的睫毛,她背着蛇皮袋
或者说是巨大的蛇皮袋背着她
亲了又亲六岁女儿的面颊
迅速加入了农民工的大军
手术室内。二十二岁的朋友
血肉模糊。半个小时前他从数十米的钢管架上
掉了下来。醒来后他懊恼地捶打着
已经保不住还在流血的双腿,口里念叨着
“媳妇没了,媳妇没了……”
有些记忆是无法忘记的。记起的时候
让人又冷又疼
母亲的粮食
我一直在怀疑着——
母亲,那个一辈子离不开泥土的人
是在大地上写诗的人
她习惯把杂草和麦苗分行,把一块块田地
当作稿纸。她喜欢把清晨第一滴
醒来的露水交还给大地,喜欢把种子
字符一样播撒在温热的泥土
喜欢一个人佝偻着腰身,微笑着面对
自己的麦苗,仿佛那是一群被她宠坏的孩子
给了她伤口、疼痛,也能够
给她快乐和收获
它们和母亲是那样亲,不像我
每一次回乡都是一次攫取之旅。都会用
母亲的粮食将小汽车塞满
然后在高分贝的音乐声中,将母亲和村庄
遗留下来
有次夜里回城的时候,无意间
我看到了母亲头上的月亮,那样安静
像一座庙宇。泪水里那条人生一样漫长的路上
月亮被我仰望了一次,又一次
悲冷的心修行了一次,又一次
日 记
整个下午,我一直陪母亲劳动
田野里新鲜的事物太多了,以至于我忘记了
时间触角一样伸出的指针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
撞击着我、麦苗、小花、小草……
以及在这绿色丛林里探险的蚂蚁、毛毛虫蜈蚣、蚱蜢……
一个微小而未知的世界
被我多少年后在一本旧日记中翻出
我突然又回到了那个被时光打磨得铮亮的童年
回到那半亩薄田之中
泥土依旧温热,小昆虫、小花草们
依旧模样可爱。只不过,这块地里多了
长眠于泥土中间的父亲
正在播种着万亩日落和暮色
风轻轻地吹
唯有风声能抚慰大地吧。在春日
唯有风声能唤醒大地上所有的花朵吧
风那么柔,轻轻推着我登上了
故乡最高的山顶
凝视着落日,我完全把自己
交给了风声。把骨头和肉身交给了空气
把隐疾、疼痛和罪恶交给了
风千万次诅咒过的草滩、山峦
以及沉重的土地
风啊,那神祇的喉咙
一定倾诉过什么,也一定感化过
这片土地上的歌谣和泪水。人生海海
我和风相见时我也一定是风,也有
被风和你触摸过无数次的疼痛
土门祭
颉崖梁上,土路已经不多了
土屋更是少见。我喜欢沿着黄土路游走
看红日爬在几间土屋的墙上
芨芨草摇着尾巴,似乎还在等待着主人回来
我在屋外停留了片刻,两扇木门
那样木讷而忠实地守候着傍晚的光阴
余晖从门缝钻了出来,风也从门缝
钻了出来。只有锁芯为日子和风雨锈蚀
仿佛门涂抹着口红的嘴唇,紧紧关闭着
日子过往。门上的门神脸色惨白
这城市化的村庄,他们不再是人们心中的英雄
而是乡愁的一种,是过往记忆
最后的指认
每一种事物静默如初
相册里,我的童年被那样完整地保存着
凌乱头发、年幼雀斑,以及额头上那一块
被月亮碰到的烙印已经没有疼痛
所有的东西是静好的。阳光朴素
房子们灰头土脸,但不妨碍成为我们的乐园
那时候的花朵只有黑色或者白色
像时光的琴键。弹奏着晨风
演绎出熟悉的第八套广播体操的旋律
整齐的队伍间,到现在还有无限光
从整齐的白鞋子上反射出来
那年夏天,时间的反射弧真长
以至于我们拖着青春期和
疲惫不堪的身体
穿越千山万水,穿过生活的逼仄和风暴
每一种事物仍静默如初
那年春天
那年春天
在水洛河畔,鹰带走了云朵
留下了烟囱和工厂
留下了一个孩子仰望的背影
在我心里,那是工业化涂改不了的乡愁
那年春天,柳哨
最后一次响起。我骑过的黄牛中毒
于漆黑的夜里死后尸体卖给了餐馆
端上了别人的餐桌
在我心里,那是年轮迈不过的门槛
那年春天,我见过的——
鱼儿死了,但水还活着
天空死了,但乌云还活着
花朵垂败了,但芳香还活着
还夹在识字课本的扉页
那年春天,北方大旱
我不止一次提心吊胆,雨点走丢了
黄土坡上大片大片的庄稼死了
生我的养我的,那么多农民
究竟该怎么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