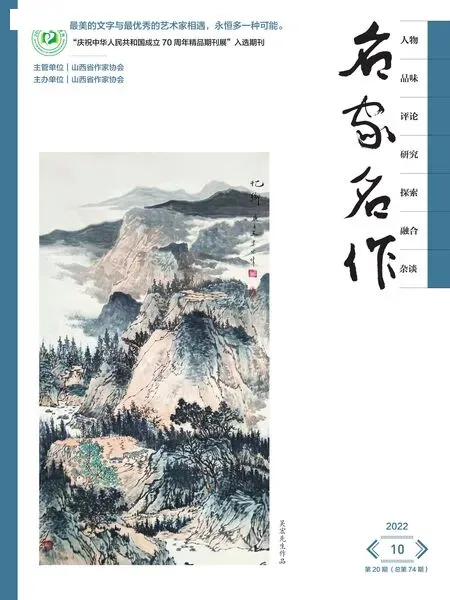笔底秀山水,淡墨隐情思
——探究陆小曼《西山情思》中的画艺诗情
2022-02-24赖伶双
赖伶双
目前对陆小曼书画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近五年来对其文学及绘画作品研究的论文甚至不足20篇。2020年11月,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曼庐墨戏——陆小曼的艺术世界》,全面收录了陆小曼的绘画作品,成为其书画艺术研究的重要文献。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陆小曼书画的论文篇名多出现“烟”或“云”字,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徐志摩笔下的“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事实上,“烟”“云”来自多位画坛老友和书画大师对其画作的题诗和评价,如海派大家孙雪泥为其题诗“腕底云烟笔底山,胸中丘壑意清闲”,钱瘦铁先生曾题“烟瑕供养”,著名美学家邓以蛰评“肯向溪深林密处,岩根分我半檐云”,杨杏佛先生评“手底忽现桃花源,胸中自有云梦泽”等等。陆小曼是如云的,其人生似云卷云舒,绘画清秀苍茫,散文尤见笔底云烟。《西山情思》作为其散文的代表作,是陆小曼于1925年5月11日从北京西山大觉寺休养回来以后所写就的一篇游记。这篇收录于《小曼日记》中的散文,后被单独摘出收录于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经典散文——纯情私语》。作为一篇独立而完整的美文,在当代游记散文代表作中占得一席。陆小曼精工国画,有良好的画艺修养,这是“艺”;受到天性与环境、情感与社会等多重矛盾的影响,陆小曼心生对诗性自然的追随之情,这份情感在西山大觉寺的疗养之旅中被触发,成为山水散文背后汩汩流动的情感底蕴,这是“诗”。本文试图以《西山情思》为例,探讨陆小曼散文中画艺风格与诗性自然观相互交融的“画艺诗情”。
一、构图的散点透视
与西洋画讲究构图透视交汇于一个点不同,中国画更多是“散点透视”,不为求真,只为写意。《西山情思》游记部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画面内容,分别是:乘轿上山,步行穿林,夜游杏林。在每幅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似山水画的构图:在“乘轿上山”画面中,“一连十几个轿子一条蛇似的游着上去”,“上山也没有路,大家只是一脚脚地从这块石头跳到那一块石头上”——画面几乎垂直构图,人物和植物依附在山体而垂直向上,形成单侧垂直的山水图;在“步行穿林”画面中,“回头看见跟在后面的人,慢慢在那儿往上走”“我一口气跑到了山顶,站了一块最高的石峰,定一定神往下一看……从上往下斜着下去只看见一片白,对面山坡上照过来的斜阳,更使它无限的艳丽”“在山脚下又看见一片碧绿的草……”——人物站在高处,山下与远方之景一览无余,画面呈现横向下沉的布局,景物细节聚集在画面下方,而上方多为留白,唯有一斜阳点缀;在“夜游杏林”画面中,“窗外的明月又在纱窗上映着逗我,便一个人就走到了院子里去,只见一片白色,照得梧桐树的叶子在地下来回飘动”“一直跑出了庙门,一群小雀儿让我吓得一起就向林子里飞,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庙前就是一大片杏树林子”——以庙门为分界,庙门以内有明月、院子、梧桐树,庙门以外有宿鸟、杏树林、草丛,画面的两部分各有景致,呈现对称结构,人物可以垂直地往上行走,也可以垂直地向下眺望。此外,正因“散点透视”,文章可以有多个重心,三幅画面也各有叙述的高潮,如“乘轿上山”中对白色杏花的错认、“步行穿林”中对山下奇景的感叹、“夜游杏林”中的“醉卧”花丛入梦,使得游记环环相扣,尽显移步换景的趣味。
二、摹景的明暗着墨
除了构图,陆小曼对景物描摹的明暗轻重也颇含淡墨山水的手法。见下文:
从上往下斜着下去只看见一片白,对面山坡上照过来的斜阳,更使它无限的鲜丽,那时候我恨不能将我全身滚下去,到花间去打一个滚,可是又恐怕我压坏了粉嫩的花瓣儿。在山脚下又看见一片碧绿的草,几间茅屋,三两犬吠声,一个田冢的景象,满都现在我的眼前,荡漾着无限的温柔。
这是轻写。明朝张岱《湖心亭看雪》有“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可以说将山水画的“白描”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读张岱的文字,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更多是无人干涉的冷静之感;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有“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同样以“大道至简”的道家笔法,以冷静的电影全景式视角观望湘西风土;而陆小曼的描摹还是有别,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花瓣是“粉嫩的”,草丛是“碧绿的”,满眼的景象带有“无限的温柔”,这是将人物内心的柔情惬意移情于景,虽然也是以“一片、几间、三两、一个”等数词轻描淡写略过,但为景物留下了情感色彩,文字有鲜活的热度,不是“白描”,而是“洒墨”。
文中也有重写。作者花了较多笔墨渲染杏花之景,杏花的“色”与“香”分别吸引着“我”,并出现在全文的多个角落。文中的两次“错认”都与杏花有关,一是将满山杏花认作白雪,二是将脸颊的落花误认为爱人的偷吻。陆小曼是敏感而细腻的,所写景语皆情语,其清丽文字之下饱含丰富情感,颇有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的主观色彩,然而郁达夫的笔触更多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深沉与浑厚,任凭情感在星空下倾泻,这是油画的叠涂;陆小曼则是笔底烟云,杏花是轻盈的、梦幻的、模糊的,成为画的底色。愁思在落花的牵动下娓娓道来,是收敛而含蓄的,如涓涓溪流。
一幅好画,除了落笔轻重,高手自然还会顾及光影明暗的处理。《西山情思》的第三幅画面“夜游杏林”正是月下之景。明月作为一个自然天体,自古以来便不是一种客观无情的事物,而成为文人笔下绕不开的情结。鲁迅的月,是照破虚无的理性之月:“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狂人日记》)郁达夫也是偏爱月的,尤其偏爱冷峻忧郁之月:“半痕新月,斜挂在西天角上,却似仙女的蛾眉,未加翠黛的样子。”(《沉沦》)“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银灰色的死》)陆小曼笔下的月,则多了几分俏皮,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明月这一意象的两次出现均伴随着一个“逗”字,分别是:
我因为想着你不能安睡,窗外的明月又在纱窗上映着逗我,便一个人就走到了院子里去,只见一片白色,照得梧桐树里的叶子在地下来回地飘动。……
忽隐忽现的月华,在云隙里探出头来从雪白的花瓣里偷看着我,也好像笑我为什么不带着爱人来。这恼人的春色,更引起我想你的真挚,逗得我阵阵心酸……
静态的月光,是照拂和浸润,而此处用“逗”字,点出了光影摇曳、忽明忽暗的动感。然而明月不解风情,殊不知陆小曼最是对“逗”字敏感。陆小曼在日记中曾反复提及自己因众人的取笑而感到痛苦,如“W他们都笑起来,我叫他们笑得脸红耳热,越发得难过了,因为我本来就不好过,叫他们再一取笑,我真要哭出来了”“我们现在是众人的俘虏了,快别乱动,一动就要找人家说笑的”等。陆小曼的婚姻情感已成为压在她生活中的巨石,她在家庭和爱情两个难以平衡的矛盾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煎熬,因此,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中,伴着明月和花香,无处躲藏的愁绪又一番番涌现,像是重新置身于社交场合中被人挑逗和取笑。同样的杏林春色,从白日里的“甜味”变成夜晚的“恼人”,这既是景色的明暗变化,又是心境的明暗变化。
三、私人心境中的诗性自然观
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中,《惊梦》一出经久不衰,杜丽娘一句“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已成经典的戏词。这正是杜丽娘在不顾严格的家教条例,闯入后花园时发出的感叹,也是她第一次亲身面对自然美景而受到的震撼。对她而言的满园春色,却只是他人眼中的“韶光贱”,这是对自然之美的呼唤,是中国文人独有的审美情怀,更是联想到自身悲剧命运而生发的愁思。陆小曼的《西山情思》,正是一个长久禁锢于城市樊笼中的灵魂找到自然归处的写照,面对杏花的白,正如面对徐志摩的真,陆小曼感到无地自容,也由此发现了内心的“真我”,即她的“诗性自然”观。这或许可以借杜丽娘一句自叹来呼应:“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陆小曼在现代性灵派诗人徐志摩的深刻影响下,其自然观被层层激发,二人对田园的无限向往之情与对性灵之真的呼唤,成为千余年后陶渊明田园诗意的现代回声。徐志摩和陆小曼,他们立足于水深火热的现代社交场焦点中,生发出对回归真性情的深刻哲思,以饱含深情的文字召唤出一个个田园梦境,这是现代文人对生存困境的反思和对本性自然的转向,也是“庄老”玄理与“山水”审美相融合的体现。只是相较而言,徐志摩在信中“保全一个诗人性灵”的浪漫追求,还有在《北戴河海滨的幻想》中对诗意栖居于自然家园的渴望,其展现的自然观在与现世的积极斗争中轰轰烈烈地宣泄,这是他对回归自然、恢复个性的强烈意愿和战斗意志;而陆小曼则如一只受惊的小鹿,想要跌跌撞撞地躲进田园,从此避世。她的自然观在其笔下的“月色”和“杏花”中悄然流淌……
也许就能在黑雾中走出个光明的月亮,送给黑沉沉的大海一片雪白的光亮,照出了到达目的地去的方向。
……这样的所在简直不配我们这样的浊物来,你看那一片雪白的花,白得一尘不染,哪有半点人间的污气?
月光与杏花的共同特点是“雪白”,对应性灵的本真与纯洁,然而这里强调的是作为个体的性灵个性,而非普遍意义上的共同性灵。陆小曼对这个社会是依存的,而非抗争,她追求的是自我内心的净化。陆小曼是典型的“以我观物”以造就“有我之境”,物本无情而人有情,“也许到不得已时我就丢开一切,一个人跑入深山,什么都不要看见,也不要想,同没有灵性的树木山石去为伍,跟不会说话的鸟兽去做伴侣”。在她看来,自然并非本身具有灵性,而是有灵性的人的“看见”,才使得自然山水具有审美意义,是人的“思考”让自然具有哲性,正如“杏花”唯有在陆小曼的眼中方能发生误认,呈现漫山白雪的美景。从《小曼日记》来看,与陶渊明在《形影神》中的自我对话相似,陆小曼始终进行着对自我的灵魂苦斗,逃开众人的逗笑与欢乐场,对自己陷于社交与应酬感到厌恶,这种对自我的批判在自然山水的注视下愈发深刻和强烈。可以看出,陆小曼的自然观是蕴含于私人心境中的诗性自然,她并不具有与身世和现实斗争的强大勇气和意志,唯一追随象征爱与自由的田园深情。这样的诗性自然,与19世纪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在《丁登寺》和《古舟子咏》等作品中展现的自然观不同,来自英国浪漫主义诗派的自然观对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进行审视和反思,构造了一个自然生灵与人类文明相互约束的强大隐喻,这是将人类与自然万物的个性汇聚为共性的思考;陆小曼则是从社会共性中抽离,回归个性,成为那只溯洄而上的柔弱扁舟,寻找着水中央的真、善、美。
四、结语
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第四十》中提出的“隐秀”概念可谓中国古代文论“意境”的萌芽,“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而文人山水画的意境,也可以用“隐秀”来说明。中国传统文人无论文章还是绘画,多追求意在言外、浑然天成,沧浪所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是很高的境界。朱光潜谈及创造与情感时提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概念,指诗人于想象之外又必有情感,人情与物理融成一体,产生完美的境界。作为一篇日记随笔,陆小曼能够从布局、绘景、移情等方面一一顾及而并无刻意雕凿之感,将丰富而独到的画艺手法蕴含于内,形成一篇清丽的游记散文,确实难得。而工于山水的背后,陆小曼自我窥探式的、以逃脱般的迫切去追求性灵与真我的诗性自然观成为全文的哲理底色。《西山情思》的锦屏之下除了韶光,更见天然,其中秀的笔法和隐含的情思交融,在文内自化为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