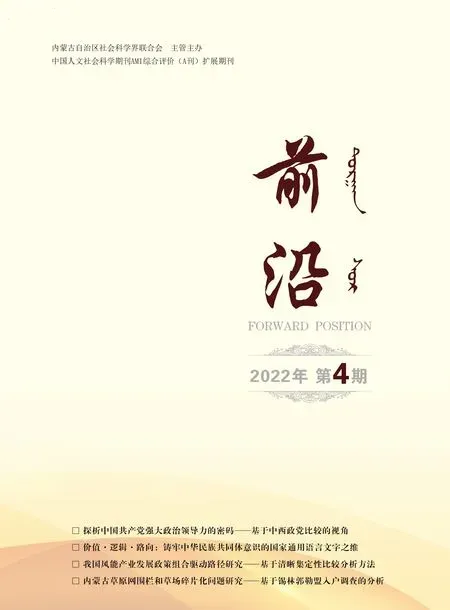清代阿拉善地区草原生态保护研究
2022-02-24包朝鲁门韩云平
包朝鲁门 韩云平
(1.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2.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法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关于清代阿拉善地区草原生态保护问题,前人虽有研究①,但仍有可探空间。阿拉善蒙古于17世纪末正式归顺清廷。清政府编撰《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等法律文件,既是调整当时蒙古地区各种社会关系的依据,也是司法活动准则。与此同时,清政府授予阿拉善札萨克②一定的地方立法权和司法权,允许其自行解决不涉及国家政治利益的地方性案件。从清代阿拉善地区历史文献来看,阿拉善札萨克通过划定游牧封锁区、严惩纵火犯罪、保护珍稀野生植物等措施保护当地草原生态环境的努力,值得肯定。以史为鉴,深入研究清代阿拉善地区草原生态保护制度,对于建设我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划定游牧封锁区
阿拉善地处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虽然大部为沙漠地带,但“沙漠间草原颇多,适于畜牧”[1]1。为保护有限的草原,清代阿拉善札萨克多次颁布谕令封禁了大量牧场,作为游牧封锁区。如在清道光二年(1822年)三月十九日,阿拉善旗第四代五任旗王玛哈巴拉为保障下游苏鲁克绵羊及马群饮水,颁布谕令封锁了乌勒吉木伦河以及和希格图木伦河沿岸土地。道光十三年(1833年)六月二十七日,阿拉善和硕亲王囊都苏布隆颁布谕令封锁了查干乌苏等十七处牧场。道光十四年(1834年)和道光十五年(1835年)又先后封锁了沙拉达布逊等五处牧场,严禁任何旗民放牧。道光十六年(1836年)颁布谕令封锁了色音胡都嘎等四处牧场,但并未要求立即执行,而是给予苏鲁克负责人一定缓冲期,允许其“放牧到明年夏季”[2]9。可见,划定游牧封锁区在清代阿拉善地区较为普遍,牧民只能在特定空间区域放牧。这与清政府“各依界限,毋得越境滋事”[3]274的规定有关,是清政府封禁政策在地方法上的具体化。
道光十七年(1837年)一则判例体现了立法者谋求划定游牧封锁区来保护草原植被的目的,内容如下:
在阿古拉别立③马群牧场负封锁任务的达木勒④副章京嘎拉达宗迪报告说,据值班达木勒昆都⑤达兰台报称,边官达木勒昆都朋什利等擅自来往该封锁地境内的查干乌苏高勒牧场,曾经劝阻不去……即派该苏鲁克拔什库保劳道等前往该封锁地查看,回来报告说:“小人奉命在该封锁地达木勒巴雅尔协同之下,细行查看察干乌苏牧场所有牲畜脚印,概无昆都朋什利牲畜脚印,该朋什利居住于察干乌苏封锁线外。”此外,在封锁线内二里许却有达木勒昆都达兰台及苏鲁克其⑥官布二人的羊群放牧的脚印。即将昆都达兰台、苏鲁克其官布传来审问时供称:“小人等羊群并无在封锁地进出之事,只是本年11月降大雪时,羊群瘦弱,曾在封锁线内一里许放牧过两天。”各该所供一致。查昆都达兰台本应不论自己或别人的牲畜一概禁止进入封锁线区域,但却将自己牲畜放入封锁界并虚报昆都朋什利等迁居牲畜入界等,实属不当。为此将昆都达兰台罚马一匹,箭丁⑦官布责打二十五鞭。昆都朋什利并未进入封锁地,故不议处。此判。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初四。[2]14
这是一起当事人违反禁令擅入封锁区放牧,为掩饰自己违法行为而诬告他人的案件。虽天降大雪,情有可原,但达兰台、官布等无视禁令擅入封锁区,已明显违反了旗札萨克谕令及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旗札萨克自然不会放任此种行为。从处罚结果看,达兰台只被罚了一匹马,看似不重,但在交通工具并不发达的时代,马匹为草原上的重要交通工具,家畜是当时旗民的主要财产,其警告意义远大于一匹马本身的价值。该案从侧面反映出清代阿拉善札萨克谋求以划定游牧封锁区方式来保护草原的尝试。由于封锁区的存在,旗民只能在王爷指定的其他区域放牧,且不得擅自离开,封锁区内的植被得以恢复。可以说,禁止越界游牧是封锁区制度的早期形态,也是清政府封禁政策在地方法中的具体化,它源于蒙古传统习惯法。早在成吉思汗建国初期,就为其母亲、弟弟和子侄等分封了领地和百姓。元代蒙古草原各部落也有各自的游牧界限。其后,1640年的《卫拉特法典》将此项规定予以制度化:“凡人在左、右边界内随其昂吉⑧游牧。从昂吉以四十户往其他地方离去者,罚其四十户长四岁骆驼一峰,令回归昂吉。不足四十户单独分离去的人,罚各和屯四岁马一匹,令其返回四十户。”[4]274到了清代,它成为封禁政策的内容之一,即限制蒙古地区各旗之间的来往。道光九年(1829年)一则判例说明不在指定区域放牧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内容如下:
前曾谕令二等侍卫班迪,箭丁好陶劳、德钦、古尔坦藏布等移居旗之东部边境放牧。但该等违反谕令向里迁移回来。为此将二等侍卫班迪降级一等;好陶劳、德钦、古尔坦藏布三人各罚带犊奶牛四头……各责打五十鞭,仍按前令,迁往东部边境。如再违抗,加重惩处。经请示判决。道光九年四月十一日。[2]13
这是牧民擅离指定游牧地的草原保护案件。班迪、好陶劳等人受罚是因为没有遵照王爷谕令在指定区域放牧。有官职的侍卫班迪降级一等,箭丁好陶劳、德钦、藏布三人因无官职,被罚一定数量牲畜,各责打五十鞭。其出发点是教育旗民严格遵守札萨克谕令,违抗者须承担法律责任。同时,该案的生态保护意义也不容忽视,根据游牧民族传统生产方式,“随季节变迁,逐水草而居”已成为一种习惯。但清廷为了有效分割蒙古各部势力,严禁人们擅自越过旗界,即使在一旗之内,也须服从旗札萨克命令,不得随意离开指定放牧区域。一方面,说明当时草原资源有限,札萨克为旗民划定游牧区域,可预防旗民因争夺牧场而产生纠纷,利于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旗札萨克划定的封锁区类似于当代禁牧措施,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规定,禁牧是指对中度、重度退化、沙化草原以及自然保护区和重要湿地草原实行一年以上禁止放牧利用的保护措施。清代阿拉善札萨克实行的游牧封锁区制度,虽然在内容上远不如当代法律法规详细,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一定的进步性,对清代阿拉善地区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及草原生态保护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严惩纵火犯罪
阿拉善地处内蒙古西部荒漠干旱区域,降水量偏少,气候干燥。草原是草食动物赖以生存的活动场所,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预防草原火灾、保护有限的草原植被,是清代阿拉善地区草原保护重要内容。以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一起纵火案为例,阿拉善旗第四代札萨克亲王旺沁班巴尔与鄂尔多斯札萨克贝勒敦罗布色楞之间往来的四件书信记载了该事件。内容翻译如下:
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鲁特札萨克亲王致伊克昭盟盟长鄂尔多斯札萨克贝勒敦罗布色楞。我旗管理边界事务的台吉纳木亚、侍卫拉苏隆报称,黄河沿岸塔本苏海音吉日格木吉之地苏亥图库伦部分芦苇发生火情。长三百八十阿拉达⑨,宽一百阿拉达。在敖伦敖包库伦也发生火情,长九十阿拉达,宽三十三阿拉达。据查,杭锦旗乌布贵格隆、塔宾沙日班,鄂托克旗毕力格图、萨日本、伊尼等五户人家居住于此。据鄂托克旗毕力格图之女称,杭锦旗赛因毕力格前些年在此放牧,可能是其在空闲时间狩猎致芦苇失火。荒火对人畜均不利,在牧草中放火属重罪。应查清是谁因何放火并严加惩处。故此,望副盟长贝子喇什多尔济调查上述两旗百姓,严惩肇事者,另请复文处理结果。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九。[5](第九卷:187-188)
秋冬干燥季节在牧草中放火,不仅对附近居民生命财产构成威胁,而且有限的枯草也是发生雪灾时牲畜重要的食物来源,此举不利于牲畜渡过难关。该案属纵火案件,案发地点位于阿拉善与鄂尔多斯交界处阿拉善旗一侧。巡逻人员发现草原火情后及时上报了旗札萨克衙门。旗札萨克派人调查附近居民,得知杭锦旗赛因毕力格有纵火嫌疑。因火灾发生在阿拉善旗境内,而纵火嫌疑人是伊克昭盟杭锦旗人,所以由敦罗布色楞调查此案。敦罗布色楞收到来信后立即展开调查,并于三个月后向阿拉善旗做出回复。内容翻译如下:
伊克昭盟盟长鄂尔多斯札萨克贝勒敦罗布色楞来文一件。收到贵衙门来文……本衙门派梅林德力格尔、色凌多尔济,杭锦旗梅林达赉、贡其格等前去调查。据查,鄂托克旗毕力格图并无女儿。毕力格图称,杭锦旗吉日嘎拉的一头牛犊被狼吃掉,吉日嘎拉将野狼追赶至苏亥图库伦芦苇中,发现该处并非放牧之地,遂将其小规模点燃以驱赶野狼。后追赶至敖伦敖包库伦芦苇并点火。吉日嘎拉也承认此事。而赛因毕力格从未放火,毕力格图并无女儿。另外,附近民人周三也称:“去年十一月,听说蒙古人在二库伦部分地区放火后,我与掌柜的前去查看。因我们买下了这片芦苇,发现部分被烧,遂加以收割,以利于明年生长。”而附近其他蒙古人与民人对此并不知情。杭锦旗吉日嘎拉将野狼赶至非放牧点并放火,未对人畜造成损害。此举虽看似无关紧要,但吉日嘎拉擅自在二库伦放火,实属不妥。故此,责打二十五鞭。此判。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初十。[5](第三卷,95-99)
上述内容说明,毕力格图并无女儿,赛因毕力格也从未放火。事实是杭锦旗吉日嘎拉的一头牛犊被野狼吃掉,其追赶野狼至芦苇丛并点燃一部分芦苇。经询问附近民人周三,芦苇丛燃烧了两天,被烧毁的面积也与前述调查结论一致。鄂尔多斯方面认为,吉日嘎拉的行为虽未造成人畜重大损失,但肆意纵火属违法行为,对其判罚鞭刑二十五。然而,阿拉善方面对裁判结果并不满意,要求鄂尔多斯方面重新审断该案。内容如下:
今年三月十八,收到贵衙门来文。称贵衙门曾派遣梅林德力格尔、色凌多尔济,杭锦旗梅林达赉、贡其格等前去调查。……据查,贵盟杭锦旗吉日嘎拉在我旗二库伦狩猎时放火,责打二十五鞭明显过轻。依照律法规定,擅自放火属重罪。望依法惩处肇事者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本衙门。如不按律惩处,本衙门将上报理藩院予以处理。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日。[5](第九卷,198-200)
对此情况,鄂尔多斯方面在一个月后做出答复,依法予以改判:
贵衙门来文称,杭锦旗吉日嘎拉在我旗二库伦地狩猎时两次纵火,责打二十五鞭处罚过轻。依照律法规定,任意纵火属重罪,望贵衙门依法惩处肇事者并告知我处。如贵衙门不依法惩处肇事者,本衙门将上告理藩院等内容。据本衙门调查,杭锦旗吉日嘎拉追赶野狼至芦苇地并纵火一事,虽无重大损失,但此举颇为不妥。故此,本衙门重新审断,虽之前已责打二十五鞭,现重新判罚吉日嘎拉五畜,责打二十五鞭。为此行文。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二十日。[5](第三卷,121-122)
该案发生在阿拉善与鄂尔多斯交界处阿拉善一侧,清代非常重视对纵火行为的处罚,纵火被视为严重犯罪行为,立法中依据不同情节规定了不同处罚规则:“因熏野兽窟穴致失火者罚一九,给见证人;延烧致毙人者罚三九,给死者之家。其余失火者罚牲畜五,给见证人。”[3]166本案中,鄂尔多斯方面起初认为杭锦旗吉日嘎拉虽有纵火行为,但并未造成人畜伤亡等严重后果,所以判令责打二十五鞭。但阿拉善方面认为杭锦旗吉日嘎拉的行为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裁判结果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处罚明显过轻,遂提出交涉,要求依法改判。鄂尔多斯方面认为吉日嘎拉并没有“熏野兽窟穴”,也未“延烧致毙人”,应属“其余失火者”,所以在原判基础上加罚五畜,再打二十五鞭。因此,纵火者吉日嘎拉前后受到鞭刑五十,还被罚了五畜。从本案裁判结果看,不仅依法制裁了纵火者,而且对附近蒙古人和民人均起到教育作用,使其不敢做出类似行为。更重要的是,严惩纵火犯罪行为,有利于保护清代阿拉善地区有限的草原资源,也为我国当代立法提供了一定参考。2009年施行的《草原防火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草原防火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民的草原防火意识。2016年施行的《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条例》也强调开展草原防火宣传教育的必要性。可见,防火宣传教育不仅要为广大群众传授防火知识与技能,同时也要通过对古今草原防火相关事例的宣传讲解,使广大群众切实认识到草原防火的重要性,有效提高草原防火意识,助力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保护珍稀野生植物
阿拉善草原植物数量稀少,种类相对单一。“在阿拉善沙漠上,百十里之内都是一望无际、寸草不生的流沙……即使长有草木的地方,植物种类也极其贫乏,不外乎几种丑陋的灌木和几十种野草,其中主要的木本植物是梭梭,主要草本植物是沙蓬。”[6]161有限的草原植物不仅可以防风固沙,也是广大牧民畜牧业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保护草原野生植物,就是保护畜牧业经济。清代阿拉善札萨克王爷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数次颁布谕令,严禁随意采挖野生植物。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罗布藏多尔济向笔帖式⑩班迪、兵丁布仁颁布谕令,要其确保芨芨草、芦苇等草原植物不受破坏,内容如下:
据悉,我旗北部额尔和哈斯哈、图固日格、乌恩格德、尼伦等地,部分民人擅自越界,于夏季采挖沙鞭、蒙古葱,秋冬季节则采挖芨芨草、芦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致使旗民放牧之草场日益减少。因此,你二人需严格查处随意采挖植物之民人。若民人为谋生而愿花钱购买本地芨芨草、芦苇、蒙古葱、沙鞭的,你二人应与民人友好协商,并详细记录采挖相关情况,及时上报本衙门。如有民人不愿购买或蒙古人怂恿民人惹事者,也将其名字上报本衙门。为此一并告知。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初三。[5](第七卷:23)
罗布藏多尔济虽然禁止擅自采挖野生植物的行为,但对迫于生计而来到阿拉善旗采挖野生植物谋生之民人网开一面,允许其与边官协商,有偿采挖少量植物,但绝不允许盗采草原植物。可随着采挖人数的增加,通过协商解决采挖事宜并非长久之计,官方需要依法规范采挖草原植物的行为。因此,罗布藏多尔济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向本旗边官颁布谕令,允许民人持官方证明文书采挖苁蓉等植物,内容如下:
民人潘嘉报称:“小人在贵旗采挖苁蓉,按每峰骆驼能驮的重量缴纳五钱银子,望贵衙门允许我等十五人采挖苁蓉并颁发证明。”故此,我旗为其颁发了允许采挖苁蓉的证明文书。因此,本旗边官应允许其驮运苁蓉,不必阻止。证明文书须每年一换,否则不得驮运苁蓉。为此告知。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初九。[5](第七卷,511)
“札萨克旗与内属、八旗蒙古及内地省县制度最大的区别是:拥有封建领主性‘君国子民’之权,对本旗的山林、土地、矿产资源有传统所有权。”[7]383民人随意采挖旗内野生植物等于侵犯了该旗自然资源所有权。作为阿拉善旗札萨克的罗布藏多尔济不可能坐视不管。如前文所述,罗布藏多尔济曾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颁布谕令,禁止民人越界采挖苁蓉、芨芨草等植物,只可少量购买。同年六月初三又颁布谕令,严禁在察干哈达等地采挖芨芨草、沙鞭等植物。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三月十六日向宁夏理事司员衙门呈文,请求严加处置擅自越界采挖植物之民人。在短短不到五年时间从“禁止”向允许持证明文书少量采挖苁蓉过渡,说明在无法完全禁止随意采挖草原植物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允许民人凭官方证明文书有偿采挖草原植物,既规范了野生植物采挖行为,也能增加本旗财政收入。同时,考虑到穷苦民人的生计,允许适量有偿采挖行为,减轻了关内土地压力。再次,清政府此前虽施行封禁政策,明令禁止民人擅自越界进入蒙地。但到乾隆时期,明显放松了对擅自越界行为的限制,越界进入阿拉善旗的民人日渐增多,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罗布藏多尔济谋求依法规范此种行为,维护社会稳定,命边官不必阻拦持官方证明文书采挖苁蓉之民人。阿拉善旗札萨克依法规范采挖行为,不仅维护了清代边疆地区社会安定,也保护了内蒙古西部干旱草原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实现了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四、结语
清代阿拉善地区有关草原生态保护的案例表明,阿拉善札萨克已认识到当地草原生态环境先天不足,谋求通过划定游牧封锁区、严惩纵火犯罪、依法保护草原植物等方式,实现对草原的可持续利用。清代阿拉善地区草原生态保护相关规定,为当时阿拉善地区草原生态保护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2019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内蒙古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立足全国发展大局确立的战略定位,也是内蒙古必须自觉担负起的重大责任。有效借鉴清代内蒙古地区生态保护基本制度和传统,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草原生态保护体系,为建设我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必要参考,也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其在本质上需要积极探索和发现草原地区的生态规律,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总结草原生态保护的经验和教训,是发现草原生态规律的有效手段。另外,草原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在制度层面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的生态保护传统文化,不断完善草原生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制度保障。
[注释]
①如朱风:《近代阿拉善社会》,《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金海:《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苏日娜:《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司法档案研究》,2018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黎明:《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扎萨克衙门蒙古文档案种类及其史料价值》,2009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等等。
②清代官名,意为执政官。
③蒙古语,意为山腰。
④蒙古语,意为管理者。
⑤指协助苏木章京管理苏木军事、军械等事务之人。
⑥蒙古语,意为畜群承包者。
⑦指编入丁册之平民。
⑧蒙古语,是卫拉特社会行政单位。
⑨蒙古语,长度单位,一阿拉达约合五尺。
⑩蒙古语,意为书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