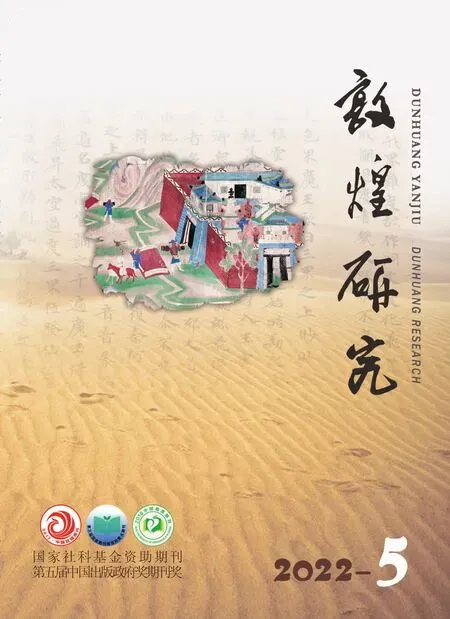从印度到敦煌:祇园布施与舍卫城斗法故事的图文转变试析
2022-02-23魏健鹏
魏健鹏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祇园精舍,即祇树给孤独园,亦名逝多林,由祇陀太子和给孤独长者(须达多)共同敬献于释迦,众多经典诸如《金刚经》《阿弥陀经》和《楞严经》等,皆是在此宣说。佛教文本和从印度、犍陀罗到敦煌等地区的图像中所记录的祇园精舍相关内容,主要集中于祇园布施和舍卫城斗法两大主题,但二者的关联度在不同时期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以往研究多基于《贤愚经·须达起精舍品》和《降魔变文》,关注以劳度叉斗圣故事为中心的祇园精舍建立相关问题,涉及文献校勘[1-3]、历史背景[4-7]和图像分析[8-11]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文本和图像内容的认识。但相对而言,这些研究也较少着意于发生在祇园精舍建立前后的劳度叉斗圣故事和舍卫城大神变的联系, 多将后者游离于祇园精舍主题之外, 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进行关注[12-14],而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可能关系到认识劳度叉斗圣故事的文本与图像的来源等问题。 因此,我们试图从文本分析入手,结合从印度、犍陀罗到敦煌等地的图像资料,梳理祇园布施与舍卫城斗法故事的主要发展阶段及二者的关联, 探讨从舍卫城大神变到劳度叉斗圣变斗法主体的转变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思想的分析考察图像中劳度叉斗圣变的功能, 以期对认识祇园布施和舍卫城斗法故事的源流等问题有所贡献。 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贤愚经》结集以前独立叙述的祇园布施与舍卫城斗法
祇园布施和佛教与外道在舍卫城斗法是祇园精舍建立过程最为关键的两个情节,然而,在《贤愚经》问世以前,佛教经典中关于祇园精舍建立的过程,多将布施与斗法诸事分别叙述,前者重在阐述须达与祇陀太子布施精舍的功德, 后者则侧重于对佛神变和法力崇拜的描绘, 鲜有将二者整合进行叙述的。
(一)祇园布施文本
祇园布施的故事多次出现在《中本起经》《中阿含经》《佛说十二游经》《佛所行赞》《大般涅槃经》《四分律》以及《汉译南传大藏经·本生经》等经典中, 相关叙述的要点都旨在强调须达和祇陀布施的功德,精舍建立的过程相对平顺,并不涉及佛教与外道斗法的相关情节。
以《中本起经·须达品》为例,祇园精舍的建立过程主要包括须达购园、建造精舍、遥跪请佛、佛众游舍卫国等环节。精舍建造完工以后,须达遥跪请佛赴舍卫城:
于是众佑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游于舍卫国,应须达请。……给孤独氏及王弟癨陀,前礼佛足,共上精舍。佛受咒愿故,曰癨树给孤独园。[15]
祇园精舍建立以后, 先后有五百婆罗门和长者瞿师罗闻佛功德,共同皈依释迦门下。在此过程中,并未受到外道的干扰,其他相关经典述及祇园精舍建立过程亦大同小异。
(二)舍卫城斗法文本
和记述须达与祇陀太子建立精舍的相关经典相似,亦有若干经典以相对独立的形态,记录了祇园精舍建立以后,释迦与外道在舍卫城的一次斗法事件,一般称为“舍卫城大神变”。相对而言,该斗法故事最早见于东汉法炬、法立译《法句譬喻经》,在《天譬喻经》①该经最初由英国学者Edward Byles Cowell 和Robert Alexander Neil 于1886 年将梵文转写为拉丁文,2007 年由日本学者平冈聪译为日文。 张同标根据日文译本将其中第十二篇“神变经”译为汉语,见张同标《中印佛教造像探源》,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261—284 页。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等亦有相近内容,主要记述祇园精舍建立以后,由于国王及民众争相供奉释迦,引起外道不满,故而要求由波斯匿王作证,在舍卫城进行斗法。
我们以《法句譬喻经·地狱品》为例,释迦与弟子至祇园精舍以后, 外道首领富兰迦叶嫉妒国王及人民奉佛,之后遂引发斗法。核心事件仅一个回合,由释迦展现大神变,外道即惭愧不堪而投降:
与记述祇园布施的经典中多无斗法场景相似,我们所见记述斗法事件的相关经典,亦基本未出现祇园布施的相关情节。现有早期经典仅《法句譬喻经》叙述舍卫城大神变相关内容,相近的情节在《天譬喻经》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中有更完备的叙述,但此二经可能结集年代较晚,在风吹外道和火烧外道的表现次序上有所调整,相关内容我们将在下文详述。
二 早期图像材料中平行发展的祇园布施与舍卫城斗法
前述关于祇园精舍建立过程的文本梳理,表明在《贤愚经》结集以前,祇园布施和舍卫城斗法的故事, 从未共同出现在祇园精舍建立过程的记述中,甚至未出现在同一经典。 与此相应,早期的有限图像材料中,亦大体反映出类似的特点。
(一)祇园布施造像
祇园布施的造像内容最早见于巴尔胡特佛塔东门和南门之间栏杆上的浮雕, 坎宁汉先生编号第15 号柱[17],画面分为左右两部分,右部绘须达以金砖铺地买园的场景:①坎宁汉对该内容释读为祇陀太子的友人在精舍落成之日前来围观祝贺,但未列相关经典内容,(Alexander Cunningham,The Stupa of Bharhut:A Buddhist Monument,Ornamented with Numerous Sculptures, Illustrative of Buddhist Legend and History in the 3. Century B.C., 1879: 87.)邢逸菲亦遵此说(邢逸菲《印度早期祇园布施图像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20 年第6 期,第136 页。 )但该内容不见于相关经典,结合图像中央持金瓶人物形象,应是呈现释迦及弟子前来精舍的场景。牛车载金砖,②众人搬运金砖并以之铺地; 左侧绘须达迎接释迦及弟子至精舍的场景:③佛及弟子至精舍,由于无佛时代的造像特点,释迦并未被表现出来①,④须达以金瓶倒水准备盥洗释迦手, ⑤人物周围布局有檀香树、芒果树和精舍建筑,以示祇陀太子敬献花园内树木和建造精舍等内容(图1)。

图1 巴尔胡特佛塔浮雕 祇园布施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 图像中的标志性构成要素——须达持金瓶盥洗释迦手的情节, 在涉及祇园精舍建立的多数汉译经典中都未出现,主要见于译自巴利文的《本生经·佛入祇园精舍》中,在释迦到精舍后,须达以金瓶为释迦洗手,以作为敬献精舍的最后礼仪:“长者取金瓶,以水澡十力者之手……佛受精舍,述谢辞并述施此精舍之功德……”[18]北传诸经典中,仅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中涉及:“尔时世尊从室罗筏城中,与苾刍众同至寺所,敷座而坐。 时给孤独长者,金瓶盛水盥世尊手……”[19]
除祇园布施浮雕以外, 巴尔胡特佛塔的南门角柱上还雕刻了一处波斯匿王乘车马率众人来前礼佛的场景(图2),坎宁汉先生根据图像中的题记“Bhagavato Dhama Chakam”(佛的法轮)和“Raja Pasenaji Kosalo”(萨罗波斯匿王)辨识为“波斯匿王乘四驾马车前往佛坛礼佛。 ”[17]90-91法国学者阿·福歇(A. Foucher)认为该图像应当被进一步解释为舍卫城大神变中波斯匿王入斗法场的情景[13]139-140,扬之水先生亦沿袭此说[20]。 虽然该 图像的确有可能表现佛教与外道斗法时波斯匿王前来作证的场景, 但同时该佛塔西门角柱上又雕刻有阿阇世王礼佛的场景,据报告描述,图像内容与波斯匿王礼佛场景接近, 最大区别主要在于波斯匿王乘马车,阿阇世王骑象[17]89-91。 因而就目前所知材料而言, 仅波斯匿王礼佛或出城场景可能并不足以推断其是否与斗法有关。

图2 巴尔胡特佛塔浮雕 波斯匿王拜见释迦
在巴尔胡特佛塔之外, 祇园布施的场景还见于桑奇大塔[20]101-103和菩提伽耶遗址[21],本文不再赘述。 综合考察目前所见相关图像资料与研究成果, 在上述几处印度存有祇园布施图像的早期佛教遗址中, 暂未发现明确表现佛教与外道在舍卫城斗法的有力图像证据。
早期的祇园布施图像大体即如以上所述,相关题材再度出现,即是敦煌西千佛洞北周第12 窟的劳度叉斗圣变,相关内容我们将在下文述及。虽然有学者指出,新疆森木塞姆石窟第44 窟和库木吐喇石窟第23 窟,也存在表现祇园布施中“金砖铺地”的图像(图3)[21]139,贾应逸先生将库木吐喇石窟第23 窟中的该图释为船师请佛渡水因缘故事: 画面中佛座下绘一舟, 左右两边为比丘和船师,正在准备渡佛过水[22],因而就现有内容,仍难判定其与祇园布施的关联。

图3 森木塞姆石窟第44 窟和库木吐喇石窟第23 窟 佛传、因缘故事画
(二)舍卫城斗法造像
表达释迦在舍卫城斗法主题的造像广泛分布于印度到犍陀罗的广大地区,既往关于舍卫城大神变造像的研究,多将表现释迦佛身上出火脚下出水的造像统称为舍卫城大神变或双神变。由于释迦身出水火的事迹在佛教经典中较为常见,诸如《佛所行赞》 记述释迦成佛后生报恩心, 回到迦毗罗卫国, 父子相见后, 净饭王对释迦所修道业存有怀疑,佛为父王施展身出水火等神变,使之欢喜:
佛知父王心,犹存于子想,为开其心故,并哀一切众,神足升虚空,两手捧日月,游行于空中,种种作异变,或分身无量,还复合为一,或入水如地,或入地如水,石壁不碍身,左右出水火。 父王大欢喜,父子情悉除。[23]
又如在《杂阿含经》卷八,佛在摩揭摩陀国的迦阇尸利沙为千比丘做神足变化示现, 入火三昧施展身出水火等神变:
神足示现者,世尊随其所应,而示现入禅定正受,陵虚至东方,作四威仪,行、住、坐、卧,入火三昧……或身下出火,身上出水,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周圆四方亦复如是。[24]
因此,身出水火的造像,主要着意于释迦展现神变的场,不一定与舍卫城斗法有关,以往关于舍卫城大神变图像的认定,可能存在泛化的倾向。根据图像内容, 诸多被认定为释迦大神变的造像大概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释迦脚下出现龙王托举大莲花的情节,以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藏莫哈迈德纳里(Mohhamed Nari) 出土的舍卫城大神变造像为代表(图4),其他还有诸如奥兰加巴德石窟第2 窟、阿旃陀石窟第6、7 窟等, 在释迦身出下方表现有龙王托举莲花,周边有释迦的各种分身等内容,可对应于释迦和外道在舍卫城斗法的相关情节。

图4 莫哈迈德纳里出土舍卫城大神变
二是仅表现身上出火脚下出水场景的释迦单身像, 以法国集美博物馆藏阿富汗迦毕试地区派特瓦寺(Paitava)遗址出土的释迦大神变立佛像为代表(图5),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白沙瓦出土释迦大神变等应当亦属此类, 这些造像在以往研究中多被笼统划入舍卫城大神变, 但由于其指向较为宽泛,且多为独立造像,因而可能是重在对释迦神变法力的崇拜, 与外道斗法则处于相对弱化的地位。

图5 阿富汗迦毕试地区派特瓦寺遗址出土释迦大神变像
玄奘西行求法时,在迦毕试国听闻贵霜帝国君主迦腻色伽在佛加持下,两肩生火焰降伏恶龙的事迹。 孙英刚先生指出,君主双肩出火是一种王权符号, 贵霜帝国钱币上即有国王双肩发出火焰的形象(图6),而双肩出火焰的佛像在时代上又晚于贵霜早期君主的同类形象, 故推测释迦身出水火的表现方式可能与此有关[25]。受此启发,我们或可进一步分析, 由于在表现身出水火的释迦佛造像中,基本都未出现外道归附等内容,因此也可将之视为一种表现佛圣性的符号, 主要作为对释迦神变特质崇拜的象征。沿此思路继续延伸,表现身出水火的释迦像,无论是舍卫城大神变与否,其所表达佛教与外道斗法的内涵都居于次要地位。 因此,大神变及相关图像传到中国后,不论是单独出现的释迦身出水火的形象, 还是释迦与多个分身共同出现的图像, 诸如在新疆早期石窟穹顶天相图中常见的身侧出火释迦像和其他位置的焰肩佛立像或坐像等 (图7),都是重在表达释迦的神变特质,并不涉及斗法相关的内容。

图7 克孜尔石窟第38 窟穹顶天相图中身侧出火的释迦像(左)、第189 窟主室前壁及右壁佛传故事中的焰肩佛(中、右)
至此,梳理《贤愚经》结集前的祇园布施和舍卫城斗法的故事, 因为服务于不同主题, 二者在文本和图像中都大体处于平行发展的状态。 祇园布施以讲述精舍建立的缘由和赞颂须达及祇陀布施的功德为要旨, 而舍卫城大神变或其他释迦神变则以宣扬释迦强大法力崇拜为主旨, 并未置于叙述祇园精舍建立过程的框架。 这应该也是祇园布施和舍卫城大神变的文本和图像始终未出现于同一叙述单元的原因, 而舍卫城大神变造像中多无外道形象, 且与其他释迦水火双神变等造像在视觉区分上相对较弱, 可能也正基于此。
三 舍卫城大神变文本的影响与劳度叉斗圣故事叙述的转变
《贤愚经》首次将祇园布施和舍卫城斗法的故事结合, 祇园布施的基本情节一如此前相关经典所述,唯在舍卫城斗法部分做出重大调整。
首先是在精舍建立前引入外道要求斗法的环节, 将之作为精舍能否建立的先决条件:“六师闻之,往白国王:……听我徒众与共捔术,沙门得胜,便听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26]此处新增内容不见于以往经典,故事虽着意于佛教和外道斗法,但仍密切服务于祇园精舍建立的框架, 且该品名为《须达起精舍品》,一仍此前强调须达功德的传统,因此可以明确,其出现之意图,应当是为了使人更深刻地感受到精舍建立之不易。
其次是将斗法的主角由释迦转变为弟子舍利弗, 并将释迦舍卫城大神变前后的鬼神王和金刚力士降伏外道的情节整合, 转述为舍利弗与外道首领劳度叉斗法的五个回合, 在斗法次序和框架上,始于风吹外道,终于火烧外道,可明显感受到舍卫城大神变斗法叙事的影响。
基于此, 我们将在下文通过梳理舍卫城大神变叙述体系的变化, 分析其在祇园精舍建立相关的文本和图像叙事上的影响。
(一)《法句譬喻经》等经典影响下劳度叉斗圣叙事的第一次转变
若将《贤愚经》 中劳度叉斗圣的故事与前述《法句譬喻经》中释迦在舍卫城施展大神变的故事并置, 可知二者是发生在祇园精舍建立之前和之初的两次斗法事件, 但却从未在叙述精舍建立的相关文本中同时出现, 这表明它们大体是互斥或者互相可取代的关系。对比两个故事的情节内容,其中的矛盾之处显而易见。
以较为明显的斗法结局为例: 在祇园精舍建立前,《贤愚经》 中记述舍利弗和六师外道的代表劳度叉斗法胜利以后,“六师徒众,三亿弟子,于舍利弗所,出家学道。”[26]420表明此次斗法之后,外道徒众尽归佛门;而在《法句譬喻经》等经典中,方才在斗法中败于舍利弗而归附的外道, 又在精舍建立之初,强烈要求与释迦斗法,由释迦施展大神变后,外道代表富兰迦叶“惶怖投座而走,五百弟子奔波迸散。 ”[16]599相比之下,此处富兰迦叶的实力和徒众远低于劳度叉一方, 在悬殊的实力对比之下,选择更强大的对手,显然不合乎常规逻辑。
基于上述对祇园精舍建立前后两次斗法故事的分析,我们认为劳度叉斗圣故事的出现,实际上可能是对释迦在舍卫城与外道斗法施展大神变的改编或再创作。这种改编,也见于两次斗法具体情节的叙述上:《法句譬喻经》 中的舍卫城斗法以释迦施展大神变为核心事件, 在神变前有鬼神王般师起大风吹外道, 神变后有金刚力士以金刚杵火烧外道;而《贤愚经》中的劳度叉斗圣故事,也是始于舍利弗以神力出风,吹倒外道化出的大树,结束于毗沙门天王制伏夜叉鬼。因此,从基本叙事结构上看,二者都以风吹外道开始,以金刚力士或天王制伏外道结束,似乎存在借用的痕迹。
当然,两次斗法事件差异也非常明显,最主要在于斗法主角的不同,限于篇幅,我们主要对佛教一方斗法主体的转变进行分析。 类似的神变主体由释迦转变为弟子的手法并非孤例, 也同样见于释迦成佛后回到迦毗罗卫国与父亲相见的场景。前述《佛所行赞》记载父子相见后,释迦为父王施展身出水火等神变的情节,在《中本起经》中则转变为由弟子目犍连施展身出水火的神变:
佛勅目连:“现汝道力。 ”目连受教,飞升虚空,出没七反,身出水火,从上来下,前礼佛足,却侍于左。 父王见变,心意解悦……便发无上正真道意。[15]155
因此,分析这种转变背后的驱动力,我们认为应当是佛教的发展脱离原始佛教阶段后, 出于升华释迦形象的需要, 将原有相对历史化的叙述进行调整, 以使之更适合部派佛教时期佛陀观念的构建。不同阶段佛陀形象的构建,在佛传的叙述体系中更加显而易见,从《佛所行赞》到《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再到《佛本行集经》,释迦的形象呈现出从相对历史性到神圣性的构建过程。 唐以后, 大乘佛教神圣化的佛陀观念再次影响了劳度叉斗圣故事情节的调整, 内容集中体现在安史之乱前夕成书的《降魔变文》中,通过塑造舍利弗声闻乘的形象和强调声闻乘与大乘的差距等方式,使祇园精舍建立相关的布施和斗法故事, 得以脱离《贤愚经》等经典的部派佛教叙述传统,自然融入大乘佛教的叙述体系[27]。
因此,可能是在《法句譬喻经》等经典的影响下,《贤愚经》 参照佛教与外道在舍卫城斗法的故事,增加了引人入胜的劳度叉斗圣情节,使祇园精舍建立过程的叙事迎来首次重大转变。 这次转变在图像上的影响, 则体现在仅有孤例——西千佛洞北周第12 窟南壁的劳度叉斗圣变(图8)。 图像结构继承了敦煌北朝以来的线性叙事传统, 分为两层呈“>”形分布,祇园布施和劳度叉斗圣的情节在图像空间所占比例大体持平, 同时图像中留存的榜题内容也与《贤愚经·须达起精舍品》原文相合者较多[11],体现出其与《贤愚经》一脉相承的创作关联。 整体而言,敦煌西千佛洞第12 窟劳度叉斗圣变的原创性贡献和历史地位, 应当在于该作品是祇园布施和舍卫城斗法的图像, 自印度和犍陀罗出现以来首次产生人的交集, 紧密的联系在祇园精舍建立过程的图像叙事中。

图8 敦煌西千佛洞第12 窟南壁门东侧劳度叉斗圣变
(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等经典影响下劳度叉斗圣叙事的第二次转变
《贤愚经》之后,劳度叉斗圣的故事再次出现明显变化即是在中唐前后成书的《降魔变文》中,其内容调整除了前述强调声闻乘与大乘的差距以外,还体现在对斗法情节次序的调整上。或是受舍卫城大神变图像早期研究者阿·福歇等先生的影响,后来学者对该图像相应文本的关注,多集中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和《天譬喻经》上,相对忽略了《法句譬喻经》中的简略记载。 对比两处文本关于舍卫城大神变记载的异同, 似乎反映出劳度叉斗圣变从《贤愚经》到《降魔变文》对斗法回合次序的调整,并非横空出世,可能仍然是源于唐代前后的文本中叙述舍卫城大神变的新变化。
正如我们前文多次提到,在《法句譬喻》释迦施展舍卫城大神变前后, 分别有风吹外道和火烧外道的情节,而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中, 对释迦在舍卫城大神变的斗法环节进行了新的调整。 首先是将与用火相关的斗法情节前置到主体斗法活动之前, 将火烧斗法场取代此前金刚力士火烧外道的情节。 其次是将此前鬼神般师在开场前的风吹外道, 转变为金刚手大药叉放猛风雨雹猛吹外道, 而佛教一方并不受影响:“时金刚手大药叉……即放猛风雨雹交注, 彼神通舍随处崩摧, 外道邪徒并皆离散……佛神通舍一无倾动。”[28]在斗法的最后部分对药叉放风吹外道情节的表述, 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晚唐以来敦煌石窟的劳度叉斗圣变(图9),画面中风神持口袋放风吹向外道,外道一方在大风之下慌作一团,或以手遮面,或搭高梯固定斗法高座,而佛教一方则清静无风。 当然,晚唐劳度叉斗圣变中的这种转变,也正是基于《降魔变文》中将原有斗法第一回合的风吹大树, 置于最后并扩大化为风吹整个外道阵营,成为最终击溃外道的尾声:“舍利弗忽于众里化出风神……出言已讫,解袋即吹……外道无地容身,……宝座顷(倾)危而欲倒,外道怕急总扶之。 ”[29]对比两处文本对风吹外道场景的描述,其相似之处不言而喻, 很难想象二者是在独立的状态下, 分别完成各自情节次序与内容的调整。 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降魔变文》对风吹外道情节的次序调整与内容改编,其源头应当是诸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或《天譬喻经》一类经典,对舍卫城大神变情节次序与内容的调整。

图9 莫高窟第196 窟西壁劳度叉斗圣变摹本 李承仙、霍熙亮、李复先生临摹
巫鸿先生指出, 劳度叉斗圣变对斗法情节的调整, 应是图像自身出于表达叙事效果需求的推动,并且这种调整在西千佛洞第12 窟的劳度叉斗圣变中就已开始, 图像虽采用线性叙事的绘制方式,但并非按照《贤愚经》中所述的斗法回合次序在图像中排列相关情节, 而是依据舍利弗所化现为越来越有威力的兽、鸟和神祇的次序重新排列,以造成最强烈的叙事效果[30]。
四 圣地崇拜语境下的祇园精舍图文叙事
正如我们对祇园精舍建立过程中的文本分析和从印度、犍陀罗到敦煌的基本图像资料梳理,祇园布施和舍卫城斗法的故事, 经过早期的平行发展后,最终以《贤愚经·须达起精舍品》为汇合点,将舍卫城释迦与外道斗法的故事转述后, 共同服务于祇园精舍建立过程的叙述。 之后讨论的方向是,通过对叙述祇园精舍建立文本性质的探讨,引入到图像思想与功能的相关思考。
(一)叙述祇园精舍建立相关文本之性质
《贤愚经》之后,祇园布施和劳度叉斗圣的故事作为一个整体,时而出现于佛教文献中,较为重要者当属隋代吉藏撰《金刚般若疏》,在开端部分即先对说法地进行说明,解说祇园精舍建立的因缘:“问何因缘故起立此祇园精舍? 舍卫国主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曰须达,其人居家巨富财宝无限……”[31]随后引入劳度叉斗圣的故事,最后以“须达造精舍因缘事如是”收尾。 类似叙述祇园精舍建立过程的方式,也见于《降魔变文》,以往学者多关注于文本内容的对勘及其对图像内容的解释,相对忽略了开端对《金刚经》的题解:
然今题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者, 金刚以坚锐为喻,般若以智慧为称,波罗彼岸,到弘名蜜多,经则贯穿为义。 善政之仪,故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大觉世尊于舍卫国祇树给孤之园,宣说此经,开我蜜藏。[29]638
此处题解表明文中所述祇园布施及劳度叉斗圣诸事,实际上与《金刚般若疏》相同,仍然是作为《金刚经》解说的引言,这对认识《降魔变文》的文本性质非常重要。首先是该文本虽名为“变文”,但实际上并非独立的变文作品,应是《金刚经》注疏或讲经文的一部分,主要在于解说该经开端“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的内容。其次即是叙述祇园精舍建立的因缘之于经典注疏的意义, 亦经典注疏或解说中强调说法地的作用。
唐地婆诃罗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有较为精到的阐释,指出主要在于拉近佛和众生的距离, 同时令众生知晓后能对说法地产生尊崇:
“在舍卫城”等,说处也。 辩处何义? 利益众生。 云何利益? 令知此地佛曾游止,心净尊崇,种福因故。[32]
另据《宋高僧传》载,南方天王第三子张璵撰《祇洹图经》一百卷,乾封二年(667)春道宣受天人口述, 记为上下两卷的《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33],具体讲述祇园精舍内部院舍的分布规模与功能[34],使人们对祇园精舍的理解更加具象化。
在此思想的影响下,晋唐以来,西行名僧在远赴印度后巡礼祇园精舍在内的各大圣迹, 并有行记留存。 因此,祇园布施和劳度叉斗圣故事,应是作为对佛的说法地——祇园精舍的注释而存在,旨在通过强化受众对圣地的崇敬, 以加深对经典的理解。
(二)劳度叉斗圣变图像功能的再探讨
由于“劳度叉斗圣变”的命名,以往研究多关注于和争斗相关的主题上, 对其所归属的祇园精舍建立主题相对关注较弱, 似乎仅有金维诺先生关注到这一问题,将之命名为“祇园记图”[35]。我们试图重新回到这一轨迹上关注劳度叉斗圣变的主题,在对文本性质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图像绘制位置,简要探讨敦煌石窟劳度叉斗圣变的功能。
印度和犍陀罗地区外, 祇园布施和劳度叉斗圣题材图像主要见于敦煌。 敦煌石窟共18 处劳度叉斗圣变,除西千佛洞北周第12 窟外,其余均为二元对称式的图像结构, 且以正壁佛像后方的壁面作为主要位置, 二元主角在视觉上位于洞窟主尊塑像的两侧, 表明图像的核心功能或思想与主尊密切样关。
图像作为文本内容的视觉性表达, 基于此前的分析,在文本层面,劳度叉斗圣的故事从未以独立形态出现,始终服务于祇园精舍建立过程的叙述框架。 因此,图像层面的劳度叉斗圣变即使以斗法情节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其功能仍与文本表达的思想保持一致,即作为释迦说法地——祇园精舍圣地崇拜思想表达的精彩注脚。我们认为绘于洞窟正壁主尊身后的劳度叉斗圣变(图10),也是祇园精舍的象征, 在文本构建的圣地崇拜语境下,和佛龛或佛坛上的诸尊像一起,以绘塑结合的方式表现释迦在祇园精舍说法的场景。

图10 莫高窟第85 窟佛坛及西壁劳度叉斗圣变
五 结 语
早期印度和犍陀罗地区的祇园布施故事旨在讲述精舍建立的缘由和布施的功德, 而舍卫城斗法则强调对释迦神变特质的崇拜, 可能基于这一原则, 二者在文本和图像中鲜有共处同一叙事单元的情形。 北魏《贤愚经》可能出于升华释迦历史性身份的需要, 参照早期舍卫城大神变相关文本始于风吹外道终于火烧外道的叙事框架, 将斗法事件作为祇园精舍建立前的必要环节, 创作出以弟子舍利弗为代表的舍卫城斗法叙事新形态。 敦煌西千佛洞北周第12 窟的劳度叉斗圣变即是在图像上作为对此次转变的回应。 唐代佛教文本对释迦舍卫城大神变的叙事结构做出新调整, 以药叉放猛风吹外道作为斗法事件的尾声, 可能受此影响, 劳度叉斗圣故事也将风吹外道斗法场作为斗法胜利的终章, 而莫高窟初唐第335 窟的劳度叉斗圣变, 应是对这种转变最早的图像回应。 此外, 劳度叉斗圣的故事始终仅服务于祇园精舍建立的叙事框架,并多出现于诸如《降魔变文》等经典注疏类的文本中, 作为对佛说法地建立缘由的注解,用以拉近受众与佛的距离,并使之建立对说法地的尊崇之情。 敦煌石窟劳度叉斗圣变多位于洞窟主尊后的正壁,这种圣地崇拜思想的投射,意在通过和佛龛或佛坛上的尊像相结合, 以绘塑结合的方式构建释迦在祇园说法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