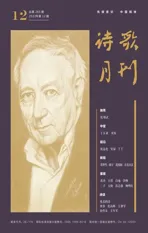中年,或某种心境
2022-02-23唐伟
唐伟
第一次读见君的诗,温婉而细腻,从容舒缓的抒情意味不浓不烈,犹如诗中那杯早先“慢慢变淡的茶水”,似唇有回甘、齿留余味,有一种成熟的“中年意味”。
“中年意味”,很容易让人想起暧昧的“中年写作”,而所有讨论一旦跟生理年龄牵连上,似乎就很难避免滑进浮泛、谵妄的代际纠葛。作为一种浅薄的诗学现象描绘,对“中年写作”的指摘毫无意义。而在见君这里,我之所以指出“中年”,是作为一个客观的事实,而无关乎年龄的限定,意在强调诗人为我们营构了一幅颇具心境意味的诗学景观。进而言之,与其说这是修辞导致的直接后果,不如说是作者的诗艺想象带给我们的一种心理体认。
中年,首先是跟自己的和解,其次才是跟世界的握手言和。或许正是放弃了那种年少气盛的刻意抵抗和拒斥,由衷的欣赏和观照才成为可能。对诗人来说,对世界的观照,重要的不是习以为常,而是如何做到经由语言中介的常以为意。
在见君笔下,“不泛起任何激情”的“平淡”“平静”“回忆” 成为诗人常以为意的抒情锚点——纵使是 “结怨很深”,也是要特意隐藏在“那场大雾”,似乎不明所以。而也正是由此,我们说去性别化或无性别化,才有可能成为某些诗人中年写作的一个典型征候——正如诗人在诗中选定的季节是不温不火、不冷不热的“四月”。
我们看到,见君笔下“陶瓷缸里的荷花”“窗扇”或“孤独的船”并无多奇崛之意,在见君这四首诗里,诗人通过一种高超的诗意把握能力,抒情性地改造“风霜雨(水)雪”等自然意象,从而把内在的心理视景充分具象化,或者说这是一种互文的彼此映照,外在世界的常态常景由此内化为某种心境的剪影。有评论家将诗人对日常即景的摄入和提炼概括为“将日常生活呈现为一种真正的诗歌状态”,实在是再准确不过。
但中年又谈何容易? 见君最见功力的地方即在于,他并没有胶着于中年进退失据的惨淡状态,或聚焦生活一地鸡毛的琐碎和零杂,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管中窥豹,四两拨千斤,写出人到中年的不堪以及某种力不从心。比如诗人将“正在自远方赶来”的雨,“迷失了方向”的风等种种飘忽不定、转瞬即逝的意象营造为一种不确定的诗歌情境——即使是“孤独的船”,也是停驻在四月的“斜坡”上,让我们担心它随时都有可能滑向不知所终的水域。把一个男人“查看自己的使用说明”的那种惊心动魄,化为不动声色的“风平浪静”,可谓是真正做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貌似的平静或平淡,实际上隐含着一种深深的不安和隐忧,这或许才是人到中年的真实心境。
世界对中年并不友好,“危险的钓线,一根根垂下”,诗人甚至都预见到了“未来的日子正在忙乱着”,尽管如此,也依然要“寻找信心”。这是中年的心境,也是中年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