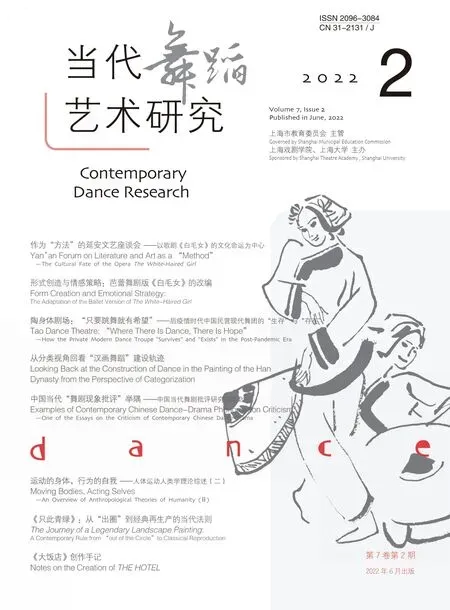中国当代“舞剧现象批评”举隅
——中国当代舞剧批评研究随笔之一
2022-02-23于平
于 平
舞剧现象,不是“现象级舞剧”。后者是指某部舞剧因所引发的关注(包括业内、圈外)而成为一种被关注的对象,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小刀会》《鱼美人》、80年代的《丝路花雨》《奔月》以及当下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等;而前者是指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编导的系列舞剧创作蔚成风气,引人瞩目—而这通常是由舞蹈批评家发现并阐释的,这种“发现和阐释”就是我们所说的“舞剧现象批评”。在中国当代舞剧史的研究和写作中,笔者发现有一些“舞剧现象批评”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故举隅如下与众共赏。
一、 优秀的“战士舞剧”是怎样炼成的?
1959年6月1日至7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在北京举行。演出结束之后,胡果刚发表了长篇舞评《舞蹈创作的丰收—为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而作》,这是当代第一篇值得我们重视的“舞剧现象批评”。我们知道,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又称全军体育、文艺运动大会)于1952年8月1日在北京举行,彼时涌现的最有生命力的舞蹈作品是原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演出的《藏民骑兵队》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歌舞团演出的《轮机兵舞》。那一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举行的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中,舞蹈节目多达114个,而成绩尤为突出的是舞剧的创作。如胡果刚所谈到的,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舞剧作品,既反映了我们时代斗争生活的现实、人民的理想希冀,又有更强的思想性和更大的教育作用,而且通过“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反映现实生活的舞剧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五朵红云》《蝶恋花》《英雄丘安》等,它们具有较强的艺术性,满足了大众对舞蹈艺术的欣赏期待与要求,将我们部队歌舞团舞蹈和舞剧的创作水准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①参见:胡果刚.舞蹈创作的丰收:为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而作[J].舞蹈,1959(10):30.我国当代的舞剧创作之所以会由部队歌舞团“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于新中国的舞蹈事业很大基础上是由部队的文艺工作团从战火中发展起来的。胡果刚曾在1949年协助吴晓邦创排《进军舞》,由此他提出了“战士舞蹈”的理念。他曾谈道,这种“战士舞蹈”从“秧歌舞”的道路走来,又受到了“苏联红军舞蹈”的深刻影响,这是结合当时部队生活的真切感受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它在战士们中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还有效地发挥着团结、教育、活跃部队的作用。②参见:胡果刚.谈“战士舞蹈”[M]//胡果刚.胡果刚舞蹈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5.可以说,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中的优秀舞剧《五朵红云》和《蝶恋花》,代表了“战士舞剧”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时代高度。
作为一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舞剧现象批评”文章,《舞蹈创作的丰收》一文由上述优秀舞剧的出现,论及了“有关舞剧艺术的规律”的认识,提出从我国几部舞剧创作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出发,依据我国公众的欣赏习惯、我国民族艺术的传统、外国舞蹈的经验以及我国舞剧创作成败的具体实践,可见作为舞剧艺术的规律和法则,除了必须符合艺术和戏剧的一般规则,还需具有舞剧艺术特性的东西。具体展开来说:第一,不仅能舞,让舞剧情节能舞起来、跳起来,至少可以用动作表现出来,还一定要有舞,要有古典舞蹈或民间舞蹈作为舞剧创作的基础,例如《五朵红云》的创作基础是五彩斑斓的黎族民间舞蹈,《蝶恋花》的创作基础是汉族的民间舞蹈和古典舞蹈;舞剧的基础是否扎实,编创者所掌握的古典舞蹈和民间舞蹈是否丰富深厚,直接影响着舞剧中人物生活表现是否具体、真实、深沉,如果舞剧创作者的脑海里没有许多具体生动的民间舞蹈或古典舞蹈的形象,那么他不仅无法通过民间舞蹈或古典舞蹈的形象在作品中表现人物和生活,从根本上还会制约他进行舞蹈形象思维的能力;我们习以为常的用来将生活动作、劳动动作和战斗动作转化为“舞蹈动作”的方法,也还存在一个问题,即以什么舞蹈为基础来转化它,假如根本就没有基础,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夸大和“节奏化”生活动作、劳动动作和战斗动作;这种所谓的舞蹈动作,在舞剧中很难表现人物生活,在舞蹈艺术中也很难满足观众的要求,可见民间舞蹈或古典舞蹈在舞剧中不仅能够作为表演舞的需要,还能够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性格特色,它是作为舞剧中一切舞蹈动作和人物性格的造型基础的。①参见:胡果刚.舞蹈创作的丰收:为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而作[J].舞蹈,1959(10):33.我们的舞剧表现要有舞,这是那时最基本的认识,也是我们现在要坚守的认识;这个“舞蹈”不仅是指舞剧中的“表演舞”,更是指舞剧中所有表现剧情、塑造性格的“造型基础”—而这就要求“舞蹈”渗透在编导的“形象思维”中。
在此前提下,文章接着指出:第二,要戏中有舞,舞中有戏……在舞剧《蝶恋花》的二、四、七场里,都选择了适合发挥舞蹈的场景,以适应情节线索发展的需要,如第二场中的“酒舞”“分粮舞”“刀舞”等都与情节的发展直接相关,如果能将表达特定环境所必需的湖南民间舞蹈处理得更加深刻、更丰富多彩,剧中人物的生活特征也就会更加深刻、更加清晰;在第四场中,舞和戏结合得较好之处也有不少,如嫦娥在月宫的“长绸舞”和由该舞引出的、在烈士幻觉中出现的“红旗舞”等;在舞剧《五朵红云》的“归来”“暴动”“初胜”等场次中,也都有着舞与戏结合得很好的部分,尤其是在“暴动”与“初胜”两场里,戏的高潮与舞的高潮同为一处。②参见:胡果刚.舞蹈创作的丰收:为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而作[J].舞蹈,1959(10):33—34.第三,戏和舞中要有人,人要有戏和有舞。③参见:胡果刚.舞蹈创作的丰收:为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而作[J].舞蹈,1959(10):35.概括来说,我们在创作中要通过舞蹈的形象来塑造人物。应肯定舞剧《蝶恋花》和《五朵红云》对主要人物的刻画与塑造。然而是什么原因导致观众认为主要人物在舞剧中的表现不突出?在舞剧《五朵红云》中,阿锦为了救自己的妻子,和朋友去劫笼,后来又为了抢救敌人手中的妻子,即使身中三弹,也依然挣扎着扑向敌人,从编剧角度看,这个人物的刻画是不错的,但在具体的动作编排中,没有充分地以舞蹈形象表现人物的内心激情;在舞剧《蝶恋花》中,编导对杨开慧和柳直荀的人物刻画也是花了心思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但在形式上没有表现这两个人物的独舞,而更主要的是舞剧缺乏能够表现两人性格的具体戏剧行动。④参见:胡果刚.舞蹈创作的丰收:为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而作[J].舞蹈,1959(10):34—35.从《五朵红云》和《蝶恋花》的创作经验来看,“戏和舞中要有人,人要有戏和有舞”应该是统一的要求。若是缺少用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具体戏剧动作,舞剧就无法表现人;但当人物有了戏剧动作,在舞蹈形象中若是得不到充分发挥,那么这些人物在舞剧中给观众的印象也不会很深刻。⑤参见:胡果刚.舞蹈创作的丰收:为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而作[J].舞蹈,1959(10):35.作为一篇“舞剧现象批评”的好文,胡果刚的文章是就一届文艺会演中若干优秀舞剧的成功及不足来进行批评的;文中对于“有关舞剧艺术的规律”的提出与分析,至今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 中国舞剧艺术10年发展的综合考量
胡果刚的舞评《舞蹈创作的丰收》,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舞剧创作现象批评,聚焦于“一届文艺会演”这样一个较短的时段;同期,游惠海发表了《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新花:漫谈舞剧艺术的发展》,从时段上来说,它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0年舞剧艺术发展现象的批评,当然也大大跨越了“战士舞剧”的视野。正如文中所说:作为新生的艺术形式,舞剧从最初以一种完整新型的艺术形式进入革命文艺的行列,从无到有,那10年间,已经组织了一支舞剧艺术人才队伍,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舞剧艺术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⑥参见:游惠海.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新花:漫谈舞剧艺术的发展[J].舞蹈,1960(2):4.“在党的百花齐放的总方针下,几年来的舞剧艺术创作,题材是多种多样的,形式也是大大小小丰富多彩的。到现在,舞剧艺术的花坛上已经有了民族风格浓郁的民族舞剧,有了反映革命历史和斗争的现代题材舞剧,有了经典性的芭蕾剧目,有了民族和芭蕾结合的新创造,也有了在古典或民间基础上创作的新鲜活泼的中小型舞剧节目……所有这些都是10年来在党和国家关怀重视下得来的成就,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舞剧艺术的领域里坚定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所取得的成就。”①游惠海.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新花:漫谈舞剧艺术的发展[J].舞蹈,1960(2):4.游惠海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受业于吴晓邦先生,后又在北京舞蹈学校第二届舞蹈编导训练班(1957—1959)受业于苏联专家古雪夫,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0年舞剧发展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他在文中从五个部分谈了自己的认识:一是从传统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民族舞剧;二是坚持现代革命题材创作的传统;三是继续攀登芭蕾艺术高峰;四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借鉴和溶化;五是坚定地贯彻党的领导和党的文艺方针。第二部分以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中的“战士舞剧”为主,第三部分则是谈《天鹅湖》《海侠》等芭蕾经典剧目的排演。在此,笔者主要举隅该文的第一、第四部分。
关于“从传统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民族舞剧”,游惠海写道:“在脱胎于戏曲的古典舞和丰富多样的民间舞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民族舞剧,是我们舞剧艺术中和民族传统血肉相连的独特的一枝花。回顾民族舞剧的发展,早些年经过整理的戏曲《雁荡山》《三岔口》《闹天宫》等剧目,成了我们继承戏曲中古典舞遗产的最初借鉴。这些传统剧目中表现力很强的舞蹈片断,对于我们民族舞剧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以古典舞为基础的小型剧目和片断的新的创作,像《东郭先生》《盗仙草》《刘海戏金蟾》《碧莲池畔》等就是这方面的初步实践,这样一些小型作品的演出给舞剧艺术带来了新鲜的气息。”②游惠海.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新花:漫谈舞剧艺术的发展[J].舞蹈,1960(2):4.1957年,在苏联专家查普林的指导下,北京舞蹈学校首届编导班齐心协力,舞剧创作迎来了比较蓬勃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舞剧已经扩大了艺术手段,在艺术形式上已经比较完整地具备了把戏剧、音乐、舞蹈(民族的古典舞、民间舞和一部分芭蕾手法)三者结合起来的特点,例如这一时期在创作上比较成功的民族舞剧《宝莲灯》就比较完整地确立了民族舞剧的艺术形式;此后,在这同一的创作基础上,出现了《石义和王恩》《并蒂莲》《刘海砍樵》《小刀会》等剧目,这些舞剧的创作大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和戏曲文学,一般都有着鲜明的反封建、善战胜恶的主题,它们吸取了民族文学、戏剧中富有人民性的内容和题材,从而奠定了这些舞剧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气质的内在基础;从民族文学、民族历史和戏曲传统中继承富有人民性的内容,继承富有思想性的现实主义传统,是我们发展民族舞剧创作的根本的、主要的特点。③参见:游惠海.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新花:漫谈舞剧艺术的发展[J].舞蹈,1960(2):4.“几年来我们所进行的古典舞整理工作的成果—从载歌载舞中脱胎出来的古典舞语汇规律和发展新的组合,已经成了民族舞剧表现的基本手段;古典舞的因素是被当作民族舞剧艺术形式统一风格基础的,这些古典舞的因素在舞剧里已经得到了新的发展,以一种新的面貌和音乐、戏剧结构结合在一起,作为表现剧中人物的戏剧动作和情感的独立手段了。同时,古典戏剧中经过千锤百炼非常精确细腻的表演风格和方法(如哑剧、手势、表情等),也提供了民族舞剧塑造不同人物形象的参考……民族舞剧已经广泛运用了民间舞蹈,它和古典舞共同成为民族舞剧的构成要素……许多民族舞剧中以多彩的民间舞蹈形成色彩对比发展的组舞场面,增强了舞剧的民族风格,同时又以生动的形象把观众引入戏剧所要求的情感和气氛……民族舞蹈艺术的遗产为我们提供了发展民族舞剧的雄厚的基础,它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创作的基础,需要我们今后长期继承、长期学习、发展运用。”④游惠海.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新花:漫谈舞剧艺术的发展[J].舞蹈,1960(2):4.作为10年舞剧现象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该文一是指出我们的民族舞剧都有鲜明的反封建、善战胜恶的主题;二是指出我们的民族舞剧都继承了富有思想性的现实主义传统;三是指出我们的民族舞剧都以古典舞语汇规律为基本表现手段—这一点也就是说,中国古典舞的创建“是被当作民族舞剧艺术形式统一风格基础的”。
关于“在民族的基础上借鉴和溶化”,文章重点分析的是“《鱼美人》现象”,并提到那10年,舞剧艺术的发展是和我们认真学习苏联舞剧先进的经验分不开的。在苏联专家古雪夫的指导下,北京舞蹈学校第二届编导班集体创作了舞剧《鱼美人》,大胆地结合芭蕾舞、民间舞和古典舞的表现手法。“这是一次有成效的具体借鉴学习苏联编导艺术的实践,这个实践的结果创造了一个为群众所喜爱的新鲜的舞剧形式,扩大了、丰富了我们舞剧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创作道路。舞剧《鱼美人》在演出中显示它许多优点:它的情节是紧凑、清晰、易懂的;主要人物的形象是鲜明的;舞剧里有着许多色彩美丽的舞蹈形象,剧中幻想与现实的场景的对比变化和许多有趣的形象—如海底的场景、山妖的迷宫、抒情的尾声等都很引人入胜。整部舞剧在处理上,尽量避免了哑剧手段,使舞剧的舞蹈艺术形象十分严谨和鲜明。《鱼美人》这些优点是我们舞剧全面向苏联学习的结晶,这些优点将对我们今后在编导艺术上起着极大的借鉴学习的作用。作为首创的大胆的尝试,《鱼美人》本身还是存在一些缺点的:主要的是作为一个民族的传说题材的舞剧,在情节发展、戏剧结构上的思维逻辑还缺少民族的特点和民族习惯;舞剧中所选用的某些民间舞蹈形象脱离了戏曲内容所规定的典型环境(如第二幕的‘啰嗦舞’和‘酒舞’);舞剧中不同手段的结合也还存在溶化得不够的情况……学习先进的编导艺术经验用于民族题材的创作时,必须牢牢地站在民族生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认真消化和运用,避免艺术上的教条主义。例如在舞剧的戏剧结构上,我们必须把戏剧结构的规律用来解决富于我们民族气质、民族习惯的题材结构;在选择发展舞剧鲜明的舞蹈形象的方法上,必须牢牢服从戏剧所要求的典型的民族性;在扩大表现手法和外来手段的借用上,必须在民族风格上加以溶化—不是物理性的结合而是化学作用的溶化。”①游惠海.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新花:漫谈舞剧艺术的发展[J].舞蹈,1960(2):7.作为一种“舞剧现象批评”,文章认定在那10年舞剧艺术的发展中要看到“在民族的基础上借鉴和溶化”的巨大作用,而这一“舞剧现象”事实上就聚焦于“《鱼美人》现象”—文章中论及的在舞剧的戏剧结构上、在选择发展舞剧鲜明的舞蹈形象的方法上,以及在扩大表现手法和表现手段的借用上的“三个必须”,就是这方面极具启示性的“现象”审视和“经验”总结。
三、 中国舞剧“新古典舞派”的“扛旗式”召唤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舞剧《丝路花雨》犹如我国民族舞剧的报春花,唤醒了我国舞剧艺术的春天。1979年我国舞剧创作的绚丽景观,会让人忆及1959年《五朵红云》《蝶恋花》《小刀会》《鱼美人》竞芳斗艳的风采,让我们看到中国舞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盛况。面对1979年的“舞剧现象”,丁宁发表了《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我们知道,新中国的第一部舞剧是1950年问世的《和平鸽》。在这部由欧阳予倩任编剧、戴爱莲任编导组组长的舞剧中,丁宁是编导之一并饰演男主角“工人”。丁宁谈道,1979年是个舞剧年,舞剧新作接连问世,这个可喜的现象证明了舞剧创作的潜力是不小的;舞剧可以说是舞蹈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舞剧的创作需要一定的基础和条件,此时中国舞剧的繁荣,正说明我们已然具备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同时,对舞剧的一系列艺术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有着迫不及待的感觉。②参见:丁宁.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J].舞蹈,1980(4):9.丁宁迫不及待地要讨论和研究的“艺术问题”其实就是“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实际上,在他关注或者说他希望舞蹈界关注这一“舞蹈现象”时,“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还处于刚刚萌发的状态。他提及的作品主要有三部:甘肃省歌舞团创演的《丝路花雨》、中国歌剧舞剧院联手北京舞蹈学院创演的《文成公主》以及上海歌剧院舞剧团创演的《半屏山》。不用往长了说,仅在20世纪80年代可归属“新古典舞派”的舞剧,至少还有中国歌剧舞剧院创演的《红楼梦》《铜雀伎》,上海歌剧院舞剧团创演的《凤鸣岐山》《木兰飘香》《大禹》等。此时的丁宁提出“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应该不是“封箱式”的盘点而是“扛旗式”的召唤。
丁宁写道:“中国舞剧有自己的特点,这是得到广泛承认的……我以为,中国舞剧就其总的概念来说,当然不是仅仅以某一种形式所能代表的;因为我国的舞蹈文化,根据历史的发展,是以多民族舞蹈为基础的。中国舞剧无疑应包括各民族的舞剧和古典的、现代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内在联系,才使得各种形式的当代舞剧组合成繁花似锦的中国舞剧的统一体。比如《召树屯与婻木婼娜》,是一部很出色的中国舞剧新作。它的成功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风格纯朴、美妙无比,完全是傣族的。又如《奔月》,也是一部相当别致的中国新舞剧。它的新颖的表现手法,丰富的舞蹈语言,塑造出了新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上的探索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实际的艺术效果也是好的。《文成公主》《丝路花雨》和《半屏山》等属于另一种类型的舞剧。它们各有所长,在艺术上都有以古典舞规律作为塑造主要人物舞蹈形象的基础这一共同点,只是程度不同而已……”③丁宁.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J].舞蹈,1980(4):10.我们可以想想前文游惠海所说的“被当作民族舞剧艺术形式统一风格基础的”,正是丁宁所说的“作为塑造主要人物舞蹈形象基础的”古典舞的法则。只不过为了区别《召树屯与婻木婼娜》那一类舞剧,丁宁才不笼统地提“民族舞剧”而提“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丁宁回忆道:“大规模地向传统舞蹈学习,是从50年代初期开始的,‘古典舞’这一概念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在舞蹈界出现的。戏曲中的台步、身段、做功、武打和毯子功技巧,具有严格的程式和生动而又典型的形象,蕴藏着传统舞蹈的精华。我们学习传统舞蹈一开始从向戏曲老艺人学习入手,理所当然,效果显著;新中国第一代的舞蹈演员几乎都是从这条路上过来的,在她们身上体现出传统舞蹈文化承上启下的光辉例证。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的建立,推动了我国舞蹈事业的发展,从此我国舞蹈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拿古典舞来说,正式在教学中开设了古典舞课程,并由年青的舞蹈教员任课;为了适应舞蹈教学的需要,改革了教学法,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为后来‘民族舞剧’专业的设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①丁宁.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J].舞蹈,1980(4):10.丁宁在此想说的,其实正是“新古典舞派”作为塑造主要人物舞蹈形象基础的“古典舞的法则”的滥觞。
很显然,作为“扛旗式”的召唤,丁宁必须要阐明“古典舞的法则”。他谈道:古典舞,不是古代舞蹈,所谓古典,意思是传统的、代表性的;古典舞与传统舞蹈有着继承的关系,两者之间关系密切;然而古典舞是时代的产物,其基本的规则取决于时代的舞蹈审美发展水平,一旦古典舞与时代的审美理想发生冲突,失去了代表性的价值,必然会带来新的变化,这方面有才能的艺术家会表现出特有的敏感,所以古典舞不是不可改变、不可发展的;古典舞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舞蹈语言的基本规范化。②参见:丁宁.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J].舞蹈,1980(4):10.“舞蹈动作来自生活的意象并具有形象的美感……仅用舞蹈这个概念不足以表示舞蹈的本质,因此借用舞蹈语言这个术语是可取的。舞蹈语言的典型性离不开对某一种传统的继承—继承先于创作,哪怕是部分的继承。不能把舞蹈语言看作随心所欲的东西,而应当看作人类智慧的一种结晶的表现。研究古典舞必须研究舞蹈语言的基本规律,从而形成新的规范化了的舞蹈语言。这样做并不会妨碍创造,除非创作本身缺乏形象思维。”③丁宁.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J].舞蹈,1980(4):10—11.这段话指出了为什么遵循“古典舞的法则”并不会影响舞剧“新古典舞派”的创造性—想想古典芭蕾的舞剧创造就能明白这一点。丁宁进一步指出:“古典舞尤其重视舞蹈语言的典型性。这种典型性往往凝练于一套基本训练之中,因而忽视基本训练就会失去古典舞的基本法则。当然关于舞剧创作所涉及的问题很广,但这并不是不重要。《宝莲灯》《小刀会》等舞剧,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称得上古典舞派的代表作;在现代中国舞蹈史上也是划时代的,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这样完整的古典舞剧出现过。《丝路花雨》和《文成公主》是新的发展。古典舞表现神话题材和历史题材比较容易。但作为新时代的古典舞,必须反映新的生活,塑造新的形象;为此,古典舞的改革已提到新的日程上来了。在目前情况下,古典舞教学的‘教改’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改,会影响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的民间舞蹈极为丰富多彩,真是取之不尽;民间舞蹈语言生动而又形象,古典舞可以吸收民间舞的素材,并且按照古典舞的法则加以规范化……我们有了一批以古典舞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舞剧,有了一套古典舞的教材,也有了懂古典舞的著名舞蹈家,总起来说,在艺术上已构成了一个古典舞学派;古典舞派的革新体现出‘新古典舞派’的产生……我企望‘新古典舞派’在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上繁荣发展。”④丁宁.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J].舞蹈,1980(4):11.很显然,关于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丁宁认为在《丝路花雨》《文成公主》等剧中出现了端倪,因为他指出这两部舞剧是《宝莲灯》《小刀会》“新的发展”。如果说,《丝路花雨》的“新的发展”在于发展出一种可称为“敦煌舞”的古典舞语言法则,那么《文成公主》的“新发展”,恰恰是“吸收民间舞的素材并按照古典舞的法则加以规范化”。因为文成公主这一形象在基本韵律上选择了朝鲜族舞蹈上下起伏的动律及呼吸节奏,结合了敦煌壁画、戏曲和朝鲜族舞蹈的特点形成了基本手势,由此便在基本姿态上形成了垂手、微抬肘的风格;而对于松赞干布这一形象的塑造,主要是以藏戏的造型和姿态为基础。⑤参见:唐满城.舞剧《文成公主》创作的经验和体会[C]//文化部艺术局,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舞蹈舞剧创作经验文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310.当然,就完全意义上的“新古典舞派”而言,中国舞剧界还有待努力—不仅有待于出现更多体现着“新古典舞法则”的剧目,而且有待于出现传授“新古典舞法则”的教材。
四、“心理描写”已构成现代舞剧创作观念的一个支柱
同样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舞剧现象批评”,杨少莆的文章较于丁宁晚了17年—当然,这篇《祥林嫂的人生转折:回顾舞剧〈祝福〉兼谈中国芭蕾创作》,不是“扛旗式”的召唤而是“封箱式”的盘点。文章开门见山: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生百年,芭蕾舞剧《祝福》诞生了,祥林嫂脚穿足尖鞋,袅袅婷婷地走到了人们面前,这一人物形象虽然与鲁迅笔下所描述的那踽踽独行、年迈衰危的老妪有所差别,但这是从中国经典文学名著中翩然而出的主要人物,其具备中国人在塑造自身时的那一份天性,以及那种祖祖辈辈所传承延续下来的思维定式、表达方式以及情感脉络;芭蕾舞剧《祝福》中的祥林嫂尽管有些洋气,但是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她却是十分“中国”的,因此,她曾经在亚非欧美各大洲的剧场频频亮相,并且也被我们的同胞所认可;特别是舞剧中的第二幕,是在全剧很久都没有上演的情况下,延伸并取代了全剧的生命;17年的时光拉开一段距离,会使我们对《祝福》、对中国芭蕾创作历程的认识更趋理性的辨析,从而更客观、深入地谈论它的价值。①参见:杨少莆.祥林嫂的人生转折:回顾舞剧《祝福》兼谈中国芭蕾创作[J].舞蹈,1997(5):22.杨少莆还曾从对历史建构的反思中,对中国芭蕾的美学趋向进行了考量。在他看来:中国芭蕾尽管年轻,却已然确立了一种新的特殊价值的文化存在,“中国芭蕾”的“核”,即“中国芭蕾”必然姓“中”的缘由,便是从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出发,将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等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芭蕾创作相结合;中国芭蕾的完整概念是以芭蕾艺术的固有规律,以其特定的风格以及严谨、规范和高度发展的技艺来传达中国文化的特质,也就是外来形式与中国文化内涵的糅合。②参见:杨少莆.“中国芭蕾”什么样(下)[J].舞蹈,2001(6):24—25.有了这样的视野及思考,杨少莆才能“拉开一段距离”来批评那一“舞剧现象”。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首先推出的一部心理描写的舞剧作品便是《祝福》。该作品延续了国际上心理描写的创作趋向,在第二幕中的重点舞段—贺老六与祥林嫂的双人舞及各自的独舞,便细致入微地以中国式的情感递进上演了一段人物情感和性格碰撞的过程—二人都面临着“去或留”的人生选择,舞台上人物之间的一来一往、一招一式,都是遵循着“抉择”而加以展开的,而这就是编导对于人物心理轨迹的刻画;心理描写之于舞剧的发展历程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其也是舞剧编导家们近几十年来的坚定探索,而中国式的表达是舞剧《祝福》的鲜明特点之一,即用层层剥离、情感递进的方式展示着人物心理的变化,在男女主人公的情理转折中,体贴、同情、体谅对方产生着极大的作用,这是东方的含蓄合着中国的道德观在舞台上泛起了一道雅辉,最终解决了两位主人公的难题。③参见:杨少莆.祥林嫂的人生转折:回顾舞剧《祝福》兼谈中国芭蕾创作[J].舞蹈,1997(5):22.如果只是这样来评说《祝福》,那杨少莆的这篇文章仅是为“现象级舞剧”而发声;而笔者看中该文的价值,在于它的“舞剧现象批评”。正如文章所言:同一时期的中国芭蕾创作不谋而合地注重心理描写,例如同样取材于小说《祝福》的舞剧《魂》是追寻祥林嫂的心理历程,描绘了主人公的精神重负;舞剧《雷雨》则是将一部具有深厚底蕴的话剧搬上了芭蕾舞台,仅用8个登场人物便对性格的对峙和感情的冲突进行了活灵活现的展现,其舞台表演的主要依据是心理活动,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蘩漪这个人物形象,以细密的舞蹈发展,凸显了其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舞剧《家》更是不在故事情节上费尽心思,其脱离了传统戏剧结构和时空艺术观,转而采用了心理结构的方法,即剧情的走向和发展是受人物心理和情感发展的牵动,着意刻画出人物内心活动,进而形成了性格对比、命运交错、心境悖逆的错综复杂的画面。④参见:杨少莆.祥林嫂的人生转折:回顾舞剧《祝福》兼谈中国芭蕾创作[J].舞蹈,1997(5):22—23.我们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还在强调“舞蹈语言的基本规范”之时,中国的芭蕾创作却以“心理描写”呈现了舞剧发展的重要一页。
何以如此,又为何如此呢?杨少莆谈道:什么时代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产生芭蕾舞剧《祝福》的时代,也即《雷雨》《家》《林黛玉》《魂》等舞剧相继诞生的时代,正是“文革”结束不久,整个社会沉入深刻的反省;文艺家们因为对那段时期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反思十分深入和广泛,也因此对于其文艺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在舞剧创作领域出现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即对所谓“样板戏经验”(内容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题范畴,形式上“三突出原则”的表现手法)的反叛;这一时期诞生的舞剧作品,把舞剧创作的视角扩展到现实生活更为深层的角落,从人出发,刻画人的共同本质,而并非从政治概念出发,是这些作品所呈现的新的创作观;然而,对于编导家自身而言,本能和良知的觉醒或许早已萌生内里,所以真正的解释应该是,他们的灵感激发既是其内心的启悟使然,同时也是对时代呼唤的回应,随着新时期而来的另一气象,是艺术家们思想解放、精神昂扬、视野开阔和吸纳能力的空前增长,以及社会宽松的环境氛围使得他们能够广泛地学习各类艺术流派,借鉴世界各国的创作成果,吸取最新的创作经验;20世纪芭蕾以两个全新的因素激动着人心,一是交响芭蕾越发拓宽抽象美的舞台空间,二是戏剧芭蕾的戏剧性向人物内心发展。①参见:杨少莆.祥林嫂的人生转折:回顾舞剧《祝福》兼谈中国芭蕾创作[J].舞蹈,1997(5):23.芭蕾舞剧演进到20世纪中叶,在创作中渐渐出现了心理描写的技巧,舞台上不再只是一些单纯的情绪舞蹈或戏剧动作,而是想方设法用形体来对心理活动进行表述,舞蹈的形体运动成了人物内心活动的投影和外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奥涅金》《村居一月》《曼侬》《梅雅林》以及80年代的《马克白斯》等作品接连出现于世界舞坛,使得芭蕾舞剧创作的美学品格实现了一次跃升,因为它们都是由外部形态的表面化表演转向了对人物内在深层进行探索;一段舞蹈可以把深沉的内心予以外化,揭示性格矛盾,表现情感冲突,展现出人物的精神世界,无限扩大和延伸了身体诠释事物的可能性;戏剧性朝着人物内心发展,扩大了选题范围,突破了形式羁绊,所以心理描写构成了现代舞剧创作观念的一个支柱;总体概括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心理结构舞剧,对于中国芭蕾舞剧创作发展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其意义全不在于如何先进、如何时髦的创作技巧的应用,而是在于其掀开了中国芭蕾历史新的篇章。②参见:杨少莆.祥林嫂的人生转折:回顾舞剧《祝福》兼谈中国芭蕾创作[J].舞蹈,1997(5):23—24.从该文可以看出,“舞剧现象批评”的写作是需要“视野”的,“视野”越宏阔而“批评”越深邃!
五、 把心理写照和戏剧冲突巧妙地结合起来
与游惠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0年舞剧艺术发展较长时段的“现象批评”相似,叶林的《新时期的舞剧问题》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0年舞剧艺术发展的综合考量。叶林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担任多年的音乐舞蹈处处长。他认为,在那10年间舞剧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形成新时期发展的最大特点,不仅仅在于可观的创作队伍和舞剧数量,更在于推陈出新的创作意识—这种“出新”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大家关心舞剧自身的规律和功能,于是在创作理论和实践方面开始了细致探索;另一方面,舞剧的创作日益贴近于当时的文艺创作思潮,开始重视艺术创作的主体精神,明显调整了舞剧与生活、舞剧与人之间的关系,重视舞剧自身的艺术规律与重视舞剧创作的主体精神又是相辅相成的,它们都强调创作主体以及艺术的自身特性。③参见:叶林.新时期的舞剧问题[J].舞蹈艺术,1988(3):36.这一时期舞剧创作的主要特征体现在舞剧形式的更新上。而率先表现在舞剧形式变化上的通常是舞剧结构的变化。此前大多舞剧都采用戏剧性的结构形式,基本上是同戏曲或话剧的结构相接近,有人物、故事情节,有矛盾冲突、高潮、结尾,即情节是按照人物的遭遇来进行铺排的,并按着情节的发展走向来展现矛盾冲突,在结构上能与戏曲或话剧相区分的大概只有依靠回忆和倒叙,或是索性整场运用倒叙的手法,或是在舞台上同时开辟新的表演区域,以此来显示舞剧情节叙事的自由;这种把舞剧建立在戏剧基础之上的戏剧性结构,实际上在处理舞剧的时候仍然是遵从戏剧表现人物和处理生活的故事性行动的原则,这方面的代表作在20世纪50年代较为典型的是舞剧《小刀会》,在新时期的代表作则是舞剧《丝路花雨》,虽然《丝路花雨》舞蹈风格的新颖和舞蹈语言的创新是有目共睹的,但其却依然延续着戏剧性结构的形式;这种结构有它自身的美学功能,当然仍是可以使用的,但如果从艺术上加以推敲,这便会给舞剧带来许多的困难,会相对地失去舞剧的特色。④参见:叶林.新时期的舞剧问题[J].舞蹈艺术,1988(3):39.其后,叶林关注的“舞剧现象批评”,主要集中在“舞剧结构的变化”。
叶林指出:当时的舞剧创作实践是丰富多彩的,编导们对有关“戏剧性结构”问题的解决,有其各自的见解和答案,而舞台上共同呈现出一种可喜的趋势,那便是加强了对剧中人物心理走向和内心感情的刻画,突出一个“情”字,为此,编导们都勇于剪裁戏剧的内容及结构,因此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建构形态;典型的例子便是可以被称为心理结构舞剧的代表作的中型舞剧《鸣凤之死》,该剧以鸣凤作为矛盾的中心,以鸣凤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为结构逻辑,通过对鸣凤精神世界、内心幻觉和思想矛盾的揭示,完成了对鸣凤的描写和刻画,在舞台上,我们所看到的是鸣凤痛苦彷徨的心灵,舞剧的戏剧行动也都直接体现出鸣凤的心理活动,其形象的塑造大多是心灵的外化呈现。⑤参见:叶林.新时期的舞剧问题[J].舞蹈艺术,1988(3):40.值得说明的是,我们与欧洲那些仅仅表现人物纯心理活动的舞剧结构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这种心理结构式的舞剧是社会环境使然,是把人物的心理刻画放置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而并非纯主观的、孤立的幻觉和心理写照;同时,在强调人物心理刻画时,将心理写照和戏剧冲突巧妙灵活地结合起来,从其心理活动中引出戏剧行动和戏剧冲突,这是我们心理式舞剧结构的独特之处,更加符合中国的传统欣赏心理,使其具有较为强烈的社会性。①参见:叶林.新时期的舞剧问题[J].舞蹈艺术,1988(3):41.舞剧《原野》体现出另外一种不同的舞剧结构,是当时又出现的一部佳作。它基本上属于戏剧性结构,但又与一般戏剧性结构相区别,它在戏剧性结构当中融入心理结构的因素,又十分注重心理的描写与刻画,所以可以称之为“具有心理幻觉因素的戏剧式结构”;该舞剧还对戏剧性结构的舞剧如何更加“舞剧化”的问题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与探索—例如,在一些段落中特别注意人物心理刻画,精心设计了符合人物性格和心态的双人舞,这使人物更加有血有肉,更加立体,并且给予人物行动以合情合理的心理依据;总体来说,这部舞剧突破了传统的戏剧性结构,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戏剧性结构能使舞剧更加突出人物形象,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从而强化戏剧矛盾,只要能够更加诗化和舞蹈化,其仍是一种有力的结构。②参见:叶林.新时期的舞剧问题[J].舞蹈艺术,1988(3):41—42.杨少莆关注舞剧的“心理描写”,认为这是构成现代舞剧创作观念的一个支柱。叶林虽然也关注“心理结构”的舞剧,但他看问题更为“辩证”—他不仅主张我们的“心理式”舞剧结构要巧妙且有效地将戏剧冲突与心理写照结合,而且认为传统的“戏剧性”舞剧结构也可以进行更加“舞剧化”的有益探索。
关于新时期“舞剧结构的变化”,叶林进一步指出:那些年,除了上述的戏剧结构和心理结构外,还出现了诸如诗体结构、时空交错式结构和乐章式结构等新实验与探索,其实质都有利于进一步发展舞剧的表现力,有利于突破传统的戏剧式结构;虽然它们有各自的特色,但也有着共同寻求舞剧艺术的潜在功能的趋势,强调舞台时空的超越,力争更加自由地把握舞剧形式,深化舞剧主题的哲理性,因此,这类舞剧并不要求人物性格合乎逻辑的发展和戏剧情节的完整性,不遵循传统戏剧结构的规律,其情节故事往往是跳跃的、不连续的,矛盾冲突也可能是细碎的或片断式的,通常会留下较多的空白,以此让观众运用自身的想象来加以填补;然而,人物的内心世界可能表现得更深邃,舞剧的容量和意念可能更加宽广。③参见:叶林.新时期的舞剧问题[J].舞蹈艺术,1988(3):42—43.上海芭蕾舞团的舞剧《阿Q》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舞团的舞剧《伤逝》可以说是乐章式或篇章式的结构类型。例如,舞剧《阿Q》采用了四个乐章的结构形式:第一乐章表现了阿Q赌博失利后以“老子输给儿子”的精神胜利法自得,为《谐虐曲》;第二乐章表现了阿Q需要爱情,遭到赵老太爷的痛打和吴妈的拒绝,为《圆舞曲》;第三乐章表现了阿Q对于革命的想象,为《进行曲》;第四乐章表现了阿Q悲剧的结束,为《送葬曲》。它是四个“块面”特写式的结构,从四个方面塑造了阿Q的人物形象,虽然在情节上相互之间缺乏一定的联系,但仍可以互相补充,由此刻画了阿Q性格的整体印象,构成了其短暂的、悲剧的一生。④参见:叶林.新时期的舞剧问题[J].舞蹈艺术,1988(3):43.舞剧《伤逝》的结构也可以算是“块面”式的结构,通过“序篇”“出走篇”“幸福篇”“谋生篇”“分离篇”“诀别篇”“悔恨篇”七个篇章,表现出涓生和子君两人的生活悲剧;通过描写几个关键性或侧面的事件来进行舞剧形象的塑造,不强调场与场之间的连贯性,仅仅是在场与场的联结上采取跳跃的方式,避免为交代戏剧情节而带来的束缚,因此基本上仍然是传统舞剧的结构的表现手法。⑤参见:叶林.新时期的舞剧问题[J].舞蹈艺术,1988(3):43.而时空交错式结构和诗体结构可以让主体意识在创作中更加自由,可以颠倒时空顺序,使主观意识和客观现实进行相互交错—例如,在舞剧《黛玉之死》中,在黛玉的病榻旁边竟出现了宝玉和宝钗的婚礼,黛玉可以穿插其间,同宝玉跳着缠绵的双人舞,这其实是黛玉病危时的幻觉景象,是她精神意识与现实情景的结合,这种时空交错的手法常常作为一种补充的手段在其他结构的舞剧中局部性地出现。⑥参见:叶林.新时期的舞剧问题[J].舞蹈艺术,1988(3):43.至于诗体结构的代表,可以《悲鸣三部曲》中取意于曹禺话剧《日出》的舞剧《日之思》为例。舞剧中的三个人物分别以《日出》中的翠喜、陈白露、小东西为雏形,着重刻画三个苦难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控诉,通过她们各自内心情感的表达予以表现;全剧故事情节极为淡化,但却着力诗化人物,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乐章式的诗体结构;新时期舞剧的变化,当然不限于形式,但较为突出的表现显然是形式的嬗变。⑦参见:叶林.新时期的舞剧问题[J].舞蹈艺术,1988(3):42—44.《悲鸣三部曲》创演于1987年,那时中国舞剧即将进入中国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第10年。除《日之思》外,《悲鸣三部曲》的另外两部正是文中先行提及的《鸣凤之死》和《原野》。刘光第曾谈道:《悲鸣三部曲》的大胆创新在于艺术手法上有机结合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戏剧性结构,编导自身鲜明的主体意识在原著的戏剧性结构框架中始终流动着、保持着;这三部舞剧在结合主体意识与戏剧性结构时,其各自的情况又并不相同—《原野》在戏剧性的“大厦”里活跃着人物深层的自我,《鸣凤之死》是在人物的心理潜流中“浮载”着戏剧性的“风帆”,《日之思》则是几乎隐没了戏剧的正面冲突,独辟蹊径。①参见:刘光第.情· 意· 美:观舞剧《悲鸣三部曲》[J].舞蹈,1988(5):17.叶林与刘光第的文章写法不同,但却是“英雄所见略同”—只是叶林的文章是“舞剧现象批评”,而刘光第的文章是“现象级舞剧批评”。此外,“刘光第”在舞评界有点“横空出世”的意味,或是叶林的笔名也未可知。
六、 用人的心灵激情去升华人体动作的格调
与前述某一特定时期的“舞剧现象批评”不同,胡尔岩的《我看舒巧的舞剧营造》是就某一特定编导而言的。只是胡尔岩对舒巧系列舞剧创作时段的关注,与叶林前述“新时期舞剧”的时段大致相同,也是10年左右。应该说,胡尔岩是那一时期最有影响的舞评家之一。她的《舞蹈创作心理学》(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年版)曾在北京舞蹈学院首届编导本科班(1985—1989)的授课中,给予那一代编导以极大影响;她的《胡尔岩舞评舞论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也给我国当代舞评界以深刻影响。胡尔岩在《我看舒巧的舞剧营造》一文中谈道:舒巧的舞剧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她先后参加或主创了《小刀会》《奔月》《长恨歌》《玉卿嫂》《岳飞》《画皮》《黄土地》《日月恋》《后羿与嫦娥》《闪闪的红星》等10余部作品,在当时将近30年的岁月里,经由她精心营造与潜心创作,一座“舒巧式舞剧大厦”已然矗立于世,由此她毋庸置疑的大师地位在新中国舞剧发展史上已然坐实;虽然舒巧的舞剧创作丰富多彩,形式风格变化万千,但对于一位成熟的艺术家来说,艺术作品就像是江海上泛起的涛涛浪花,舒巧那具有奠基性的主体内在结构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她的主体内在结构就犹如那江海的河床,尽管一些机遇性的因素会让浪花幻化出千姿百态,但河床却依然能较为稳定地保持着它自身的特性;舒巧作为一位优秀的舞剧创作家,其成功的作品较多,她善于营造作品中的内在结构,她在创作中,每一次都会为自己的内在结构加入一点新鲜元素,同时又汰弃一些相悖于自己审美理想的东西,如此的创作方式能够使她的个人审美及作品中的内在结构得到逐渐的完善,完善后的主体内在结构又将在下一次的创作中得以外延;经此反复,形成良性循环,其内在结构与作品质量也就得到了同步提升,“造心”与“造舞”齐头并进,“舒巧的舞剧营造”便也就在其中显现。②参见:胡尔岩.我看舒巧的舞剧营造[J].舞蹈论丛,1989(1):10—11.然而,这篇文章论述的重点并不在于舒巧如何“造心”,而是聚焦于阐释其如何“造舞”。虽然文章提及舒巧“近30年”的精心营造,但主要论述的还是从《奔月》(1979年)到《玉卿嫂》《黄土地》(1988年晋京演出)这10年间的“舞剧现象”。
胡尔岩谈道:舞剧作为一种感受性的戏剧艺术,舞剧编导是善于在动作上大展身手的动作艺术家,通过人的“物质本体”以展现人的“精神本体”;舒巧舞剧《奔月》的编舞经验,不仅在她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具有特殊价值,而且对我们舞剧创作观念的变革与更新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在创作《奔月》之前,舒巧对自己之前已掌握的古典舞素材进行了整理,她发现虽然我们总在理论上强调戏曲舞蹈遗产的丰富,但在实际的创作实践中,用来编舞的动作其实并不足够丰富;在戏曲动作中,属于“纯舞”的动作是不多的,仅靠戏曲中那少有的“纯舞”来作为舞蹈核心元素的“舞”,是远远不够的;基于此,舒巧便提出了“动作元素分解、变形、重组”的编舞原则,并在具体的编舞实践中积极地尝试与检验,呈现出了不错的效果;“动作元素分解、变形、重组”的意思是分解一个舞蹈动作的若干构成元素(如动态、动律、动力、动速等),并在元素层次上进行变形重组,由此,若干“子体动作”就从一个“母体动作”中被分解变化出来;这种方法不仅使“动作家族”风格的协调性问题得到了解决,也使作品中动作贫乏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更重要的是这种编舞方法根据人物表现的需要,还使动作“质”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根据格式塔心理学派的观点,在元素之间,变化任何一个元素,都会促成一个新的“质”、一个新的“完形”。③参见:胡尔岩.我看舒巧的舞剧营造[J].舞蹈论丛,1989(1):12.当时,舒巧是在其创作实践中暗合了这种原理,并非在实践前就先有了这种知识。总体来说,舒巧在《奔月》的编舞实践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动作组合原则,领悟到了“变”的本身也蕴含着“再变”的可能性,也更使她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既然动作这样小的基本单位都可以变化重组,那么,未经艺术加工的生活原型动作与经过艺术加工的人体动作体系,由小而大、大到舞蹈,这些尚未充分开发的动作领域之间的变化重组,不是也有着可重组性和可变性吗?①参见:胡尔岩.我看舒巧的舞剧营造[J].舞蹈论丛,1989(1):12.舒巧和应萼定在舞剧《黄土地》《玉卿嫂》的创作中,又提出了“在一定的戏剧氛围下,生活原型动作只要具有特定的表现力,对刻画人物性格有必要,此时此地它就是舞蹈动作”的观点,并在创作中实践这种观点,这还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舞剧创作中在“语言”问题上的新话题;《玉卿嫂》中玉卿嫂这一形象端盘、走步等“生活化”的动作,《黄土地》中老农民双手揣在袖筒里的“生活化”的动作,都是他们进行提炼的典型动作;舒巧不断地在探索研究舞剧创作中的“人体动作”,既深入又开放,始终以“向内深入而不求外表的花哨”为核心,而她又有着一种向外开放发展动作的思路走向,并未封闭在现成的素材之中。②参见:胡尔岩.我看舒巧的舞剧营造[J].舞蹈论丛,1989(1):12—14.比较一下胡果刚对“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中舞剧展示和胡尔岩对“舒巧舞剧营造”的分析,可以看出后者明显更本性、更具体、更深邃了。
在分析舒巧对“人体表现力”的探索思路后,胡尔岩进一步关注舒巧对“人的心灵”的开掘。她谈道:舞剧既是一门人体的艺术,更是一门心灵的艺术,是身心一起飞翔的艺术;舒巧并非为了炫耀动作本身才对人体动作展开试验与研究,而是将视点转向舞剧的主要表现对象,即人的心灵开掘,以从中获得表现手段上的解放和自由;舒巧对于剧中人物的心理分析,是将人物的人生经验作为创作的整体背景,但并非仅仅停留在情节发展中人物在此情此景、此时此地下的行为准则和心理活动,而是从确定人物基本的生存状态出发,再进一步分析特定情景下人物产生的特定动机和行为;舒巧对玉卿嫂这个人物的细致分析便是十分典型的一个案例,她认为“中国人在感情上的磨难,在玉卿嫂身上都有所显露”,在对玉卿嫂做了全面且详细的解读后,通过舞剧的独特手段,用内心直视的手法,将主人公独特的情感经历、震人心魄的戏剧性和暗含于内的心理活动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呈现在舞台上,以此将舞剧审美升华到一种不可言说的美妙佳境;总之,舒巧的舞剧营造是建立在两个支撑点上的,其一是对人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其二是对人体表现力的不断探索;用人体动作表现人的心灵激情,又用人的心灵激情去升华人体动作的格调,在身心一起飞翔的舞蹈世界里,实现她的舞剧审美理想—用舞蹈手段表现人、人生、人性!③参见:胡尔岩.我看舒巧的舞剧营造[J].舞蹈论丛,1989(1):14—15.
其实,笔者在对舒巧进行深入访谈和研究后,也先后发表了《舒巧的舞剧》(《舞蹈》1991年第6期)和《舒巧的舞剧观》(《舞蹈》1992年第1期)。这两篇文章本是一篇,即《舒巧的舞剧和舞剧观》,但在发表时因篇幅较长而一分为二。的确,作为“舞剧现象批评”的文章都难免有较大的体量。但其实更显而易见的是,“舞剧现象批评”需要批评者有更宏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