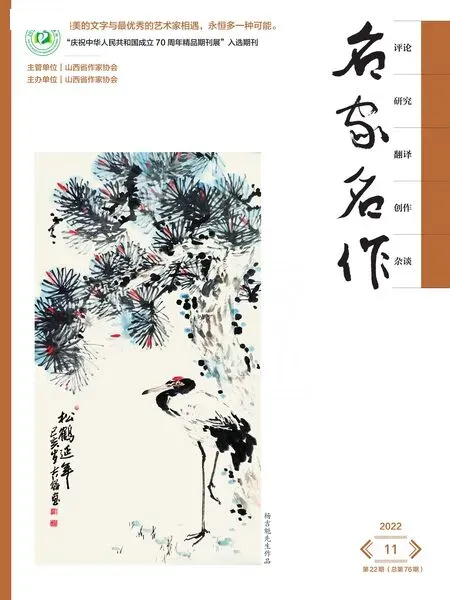《半生缘》的爱情:缘分与人性的挣扎
2022-02-23康洪通
康洪通
一、缘分支撑起《半生缘》中的“缘”
在张爱玲的《半生缘》中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但是在这之中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即文本是围绕着顾曼桢与沈世钧的感情线来逐步展开的。在原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这一句简单的话,道尽了心酸,道尽了无奈。这几个字看似很简单,然而事实可能没有显现的那么单纯,张爱玲想表达的远不止这么简单。这句话字面上想要表达的是曼桢对与世钧的感情现状的冷静且清醒的思考,即便开始是缘分让他们能够相聚,比如原著中这样写道:“是叔惠先认识的她的。叔惠是他最要好的同学。”通过叔惠,沈世钧和顾曼桢有机会相识,首先都在一个厂上班,其次是在过年的时候很多饭店都不开门,好不容易看到了一家饭店还是“半开着门”,于是便遇见了曼桢,这也是世钧与曼桢真正意义上的一次相识,“从这一天起,他们总是三个人一起吃饭”。虽然作者表述的是三个人的关系,但这句话是作者对世钧与曼桢关系的一个暗示,也为接下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书中开头这样写道:“曼桢曾经问他,他是什么时候起开始喜欢她的。他当然回答说: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但笔者认为世钧对曼桢的心意或许不是第一次的相见,而是之后叔惠去找曼桢拿钥匙的那次,叔惠开着曼桢的玩笑,虽然是玩笑,但在世钧的耳朵里那些话是那么的刺耳,在原文中这么写道:“今天他所说的关于曼桢的话,也不过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绝对没有恶意的。世钧也不是不知道,然而仍旧觉得非常刺耳。和他相交这些年,从来没有像这样跟他生气过。”虽然是侧面描写,但我们可以看出世钧对曼桢是喜欢的,否则又怎么连开玩笑的话也听不得。一段缘分的开始总是很美好的,就如四季的春天般美好。
但是在经历了种种之后,这种缘分早已经“变了质”。在这句话的背后,作者其实是在告诉人们,缘分能够让人和人走得很近很近,但亦能将人和人推得很远。缘分是神奇的,它让两个彼此没有交集的人出现了交集并最终在冥冥之中走到了一起,也是缘分的捉弄使这两个人经历种种错进错出的纠缠,最终使得甜蜜美好的感情不可挽回地走向破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有缘无分。”“世钧,我们回不去了”这句话也包含着对之前故事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同时这也是对两个人经历的种种进行总结后而发出的感叹。这就是“张氏”爱情哲学最好的表达。看似是短短的一句话,却能在一瞬间拉近作品和读者之间的距离,甚至还能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又比如:“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半生缘》中充满了悲情色彩,但是读来却又让人产生了某种希望,这恰恰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复杂感觉。有趣的是,在这一生的短短几十年之中,每个人都会有只属于个人的独特经历与表面看上去大同小异实则却完全不同的私人烦恼。然而即便是经历痛苦,即便是浑身是伤,但是依旧能感受到在人间那仅存的一丝阳光。曼桢这样的一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不管你是否感觉幸福,你都要充满期待,没有必要过分忧伤,远处有一个人在等你,你只要知道还有个人在挂念你,你就能在“不圆满”的现状中找到一丝安慰。《半生缘》表层是一个悲剧的故事,比如在李振声、张新颖撰写的简评中就写道:“在《半生缘》里就割掉了多余的尾巴,而且自然地加强了悲剧性感受。”但在悲剧之下,张爱玲用自己的感悟带给读者一丝安慰。
用历史传记式人物分析方法来看张爱玲的人生经历,首先从时间上来看,张爱玲和胡兰成失败的爱情经历在前,而《半生缘》的改写在后。在美期间,1996年她开始改写《十八春》,易名《半生缘》。在张爱玲与胡成兰的爱情中,张爱玲无疑是“失败者”。哪怕得到张爱玲全身心的投入,胡成兰也从未有过满足,反而与其他女人暧昧。假如张爱玲没有之前的种种经历,又何以能在《半生缘》中写出,如:“我们都是寂寞惯的人。”再如:“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却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一样。”这些话语恰恰也能表现张爱玲以独特的视角对爱情和人性的解读。笔者认为,曼桢给世钧的信中的最后一段话,也是张爱玲对感情的认知和对自我的宽慰。张爱玲在遇到胡兰成时,她在自己的照片后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从哲学角度来看,张爱玲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将哲学融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半生缘》中充满了张爱玲的恋爱观点和人生哲学观点。如,曼桢抱着为孩子牺牲的精神,嫁给了自己鄙视和仇恨的祝鸿才,婚后她对丈夫的一再侮辱不闻不问,心如槁木,感觉像躺在污浊的泥里一般,曼桢静寂的姿势让人震惊,这种平静无争,实际上是向社会宣告无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再如,祝鸿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才造成曼桢作为“牺牲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这样的观点:世界观包括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人生观等,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根本观点和态度,人生的理想和抱负、幸福观、荣辱观、苦乐观、恋爱观等,都是人生观的具体表现。 结合张爱玲的感情经历,“总有一个人在等你”,也许是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话,或许是为了宽慰自己而说给自己听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句极具浪漫色彩的话,为这段看似悲情的故事增添了一丝温暖。
从产生的作用和受众角度来看,《半生缘》看似只是在写几个人物爱恨交织的感情纠缠和几个家庭间的家长里短的故事,但是张爱玲的语言既“平常”,贴近生活,让人容易读懂,却又极富哲理意味。比如“曼璐只管沉沉地想着,把床前的电话线握在手里玩弄着,那电话线圆滚滚的像小蛇似的被她匝在手腕上”等。这种表达和思想,在拉近和读者的距离的同时,也能带给读者启发,甚至读者自身的生活经历会使自己对这句话内涵的解读深度倍增。不知不觉中,人们会思考爱情是不是如张爱玲所写的那样,会思考造成这种不可逆转的悲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缘”的影响,还是人性在作怪?在这里,笔者想说张爱玲的感情哲学不仅能引发有类似 “经历”的读者进行思考,甚至在没有类似“经历”的读者身上也同样有效果。换句话说,《半生缘》的受众群体在年龄段的分布上是很广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张爱玲所写的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被学者和评论家冠以女性文学作家或者通俗文学作家的称号而被文学史铭记,但在受众群体的普遍认识之中并不会先验地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任何性别或者雅俗的区分,观众只看能看的,只看好看的。
二、人性造成《半生缘》中的“半”
笔者在此想提出一个问题,在《半生缘》中使曼桢和世钧的爱情充满悲剧色彩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是曼璐一手造成的,是祝鸿才的欲望在作祟,还是缘分使得他们两个人终究无法走到最后,再或者是他们身处的时代和家庭背景注定了两个人根本就没有结果?我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后面的故事结局可能就完全不同了。但无论哪种因素,在《半生缘》这部小说中,“人性”才是造成《半生缘》中的“半”的最为关键的因素。而在曼桢的悲惨遭遇中,曼璐与祝鸿才所展现出的人性是“黑暗的心灵”与“贪婪的欲望”。
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提出了一种见解:女人“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曼璐“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曼桢“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受教育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境遇,新女性也不能彻底与过去决裂,她们与旧的传统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她们的生存状态并不能改变,她们仍要依赖男人。从最早的母系社会到后面的女性地位下降,再到如今人人平等,女人的地位在不断变化,曼桢身处的时代也是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之一,我们不应该把《半生缘》这部小说的悲剧归结为一种原因,恰恰是多方面的问题最后才造成了这一悲剧。
如果说在爱情小说《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想要传达的是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应保持自我,自己才是最靠得住的,而不是一味地顺从男性来获得婚姻的幸福,那么在《半生缘》这部小说中则表达出对爱情、婚姻以及人性的思考。
在《半生缘》中的曼璐一角。一方面她是曼桢的亲姐姐,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而选择当舞女,并且也很疼爱曼桢这个妹妹。在文中曼璐曾这样说道:“二妹现在也有这样大了;照说,她一个女孩子家,跟我住在一起实在是不大好,人家要说的。”曼璐所顾忌的是自己舞女这个身份。曼璐又在祝鸿才“调侃”自己的妹妹时,把镜子往桌子上一拍,大声道:“别胡说了,我算是吃这碗饭了,难道我一家都注定要吃这碗饭?你这叫作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在这些话语描写中可以看出来,曼璐还是很护着妹妹的,并且妹妹曼桢何尝不知道姐姐曼璐去做舞女也是被逼无奈的事。在原文中曼桢就这么评价了曼璐,她说:“舞女当然也有好的,可是照那样子,可养活不了一大家子人呢。我姊姊呢又不是那种人,她其实是很忠厚的。”曼璐为了整个家庭也奉献了很多,曼桢心里是明白的。但另一方面也是曼璐一手造就了曼桢后面的悲剧故事。面对自己的感情,面对自己的人生,曼璐摇身一变,成为“魔鬼”。张爱玲曾在《流言》中这样写道:“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曼桢的一切,是曼璐的“牺牲”所换来的,如果说这里的曼璐还属于是“兽性的善”这一面,那么后面曼璐的表现则展现了“兽性”的本来面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质量互变关系的概念,量变引起质变。 曼璐长年累月的“牺牲”使得她一步一步地变成“魔鬼”。这是人性的本质,也是张爱玲对人性的一种解读,没有人能够一直不停并毫无私心地付出,即便那是姐姐。《半生缘》告诉我们,人有两面,一面是天使,另一面却是恶魔。
随着故事的发展,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关键性人物,这个人就是祝鸿才。如果从祝鸿才这个角度来分析,祝鸿才开始时所表现的是对曼璐一时的顺从和妥协,比如刚开始时“她对鸿才相当冷淡,他却老耗在那里不走”,再比如“好,好,好,依你依你”等。直到两个人结婚,祝鸿才慢慢显露出贪婪的本质,明明曼璐警告过他,但他从最开始就一直有想要“霸占”曼桢这个念头,从原著中我们就能够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在祝鸿才和曼桢第一次见面时,虽然祝鸿才是来找曼璐的,但在见到妹妹曼桢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不断地向曼璐打听曼桢的事,并且还说:“其实……照她那样子,要是出去做,一定做得出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祝鸿才虽然不认识曼桢,但其实打心底觉得曼璐和曼桢是“一样的人”,同时也暴露出思想“肮脏”的一面。所以故事发展到后面,祝鸿才有了妻子曼璐却一直对曼桢念念不忘。在文中其实已经交代了祝鸿才一直以来的那点“小心思”,比如:“从前有一次,鸿才用汽车送她回去,她搽了许许多多香水,和她同坐在汽车上,简直香极了。怎么会忽然地又想起那一幕?因为好像又嗅到那强烈的香气。而且在黑暗中那香水的气味越来越浓了。”以及直接表明了心意对着曼璐说:“曼璐,二妹怎么越来越漂亮了?”在这里男性的贪婪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吃着碗里想着锅里”到最后的“心愿达成”。虽说“曼桢失身”的整件事情是祝鸿才和曼璐一手计划的,但实施计划的终究是祝鸿才本人,而计划这起事件也是因为祝鸿才的贪婪在作怪。曼璐在整件事中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祝鸿才犹豫的时候,曼璐竟然觉得祝鸿才这个男人如此“懦弱”。自古人们对人性就有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性善论与性恶论,但不管我们更倾向于哪一种观点,都不应该一概而论。如果将张爱玲的经历放在其中,那么胡兰成不就是张爱玲笔下祝鸿才的现实写照吗?站在祝鸿才的角度来说,《半生缘》想要告诉我们另一个人性哲理,就是人性是贪婪的,在面对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欲望时,人也可能“兽性大发”而不顾一切,这是贪婪在作祟,同时也体现出作品的戏剧性。我们可以简单地进行假设,假如没有祝鸿才的出现,是否可以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笔者认为,假如没有祝鸿才也可能出现王鸿才、李鸿才等,因为曼璐永远是曼桢的姐姐,而作者的本意是想告诉读者人性是复杂的。正因为人性的复杂才造成了《半生缘》中的“半”。
总之,《半生缘》这部作品是张爱玲最好的爱情观的体现。无论是张爱玲对爱情的解读,还是其对人性的思考,“张氏哲学”无处不在地体现在《半生缘》这部作品中。《半生缘》这部作品中有很多对立的因素,但最大的“对立”则是缘分与人性的对立。纵观全书,《半生缘》中的主人公沈世钧和顾曼桢的爱情悲剧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缘分使然,实则是必然会产生的结果,“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仅仅局限于一方面的思考,这也许是对《半生缘》最好的解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