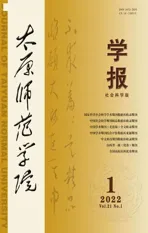论明代墨牡丹与墨梅竹创作思想的趋同现象
2022-02-21李开林
高 帆,李开林
(1.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2.太原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24)
墨牡丹画,指纯用水墨或主用水墨而略施淡彩的牡丹画作。它相对于工笔牡丹而言,二者的创作技法和创作旨趣迥然有别。工笔牡丹明代之前早已有之,但是以水墨作牡丹,却在一开始就遭遇尴尬——它并不像墨梅、墨竹那样在宋、元就盛行画坛。有学者统计,工笔牡丹画作和梅花画作相比,前者在宋以前占居绝对优势。主要原因在于,牡丹象征的是一种富贵雍容之美,非常符合唐、五代及宋初的精神风貌、审美情趣,而宋人逐渐培养起来的内敛淡泊的心境,使得与其心境吻合的梅花艺术创作在宋代流行开来。[1]23伴随着水墨作画的主流趋势,墨梅画在宋代紧随墨竹之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绘画门类,而水墨牡丹创作却姗姗来迟,一直到明代才由沈周、陈淳倡风气之先,并最终与墨梅竹的审美旨趣趋同合一,二者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舍异求同、由分到合的独特历程。
一、“不入时眼久矣”:墨牡丹画作的诞生及其蕴含的调谑意味
墨牡丹画或最早于五代时出现,首创者是被誉为有“野逸之体”的徐熙。明人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记载了徐熙墨牡丹,说其“大有风致,信笔拓成”。[2]4徐熙画法中最知名的是其落墨的笔法。所谓“落墨”,即不采用线条细致勾勒然后设色的作法,而是直接以水墨晕染形象,形成一种没骨效果。徐熙所作牡丹重整体意韵而忽略细节刻画,寓一己个性于其中而不求形象的逼真,“信笔拓成”,展现出特有的落墨风致。詹景凤还说,陈淳作牡丹学得了徐熙之韵,但未得其骨。[2]4陈淳是明代与沈周并称的名家,詹景凤此言跳过宋元径直接入明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徐熙之后沈周、陈淳之前,几乎未有墨牡丹画作流传——墨牡丹在宋元两代并不流行。
苏轼说:“世多以墨画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画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3]1353苏轼本人是书画创作与评鉴的行家里手,但是以水墨画花,他似乎还未有所闻,由此赋诗一首道:
造物本无物,忽然非所难。花心起墨晕,春色散毫端。缥缈形才具,扶疏态自完。莲风起颠倒,杏雨半摧残。独有狂居士,求为墨牡丹。兼书平子赋,归向雪堂看。[3]1353-1354
诗的前八句描述了尹白的墨花面貌,根据诗意推测,尹白所作大概是梅花。元人夏文彦说“尹白专工墨花,习花光梅,扶疏飘缈”,结合苏轼诗意,尹白所绘当是墨梅,非墨牡丹。“狂居士”是苏轼自指。为什么说自己“狂”呢?因为以墨作花本已经十分稀罕,更何况是作牡丹花,大概只有施之以脂粉,出之以描摹,才能表现出牡丹的富贵之态和花王之美。可是苏轼偏偏想看看水墨牡丹是什么样子,所以说自己是“狂居士”。
苏轼的这首诗透露了一些信息,那就是在苏轼的时代还没有人进行墨牡丹创作,连苏轼这样的集文学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天才人物,都以为墨牡丹是不可思议的惊世之作,是造物主的超常手笔,那么墨牡丹在彼时的稀罕便可想而知了。尹白最后有没有为苏轼创作墨牡丹画不得而知,不过宋代有记载的墨牡丹画作留在了某处驿馆的屏风上。许及之的诗《北方馆驲屏风皆画落墨牡丹》记载了这些画作:
停车京洛净风沙,几见屏开落墨花。故国似人犹可喜,秾肌何况谢铅华。[4]28450
“几见”,说明了墨牡丹画作并非只有一幅,而是在所经之地屡次看到。“落墨花”,指以徐熙笔法创作的牡丹画作。最后一句“秾肌何况谢铅华”,以美人褪去妆点为喻,指出了牡丹画作的水墨特性:舍弃了脂粉而以水墨出之,显得十分淡雅素净。除此之外,尚未见宋代其他墨牡丹画作的记载。到了元代,据记载也只有吴镇和边鲁创作过墨牡丹,王毓贤在《绘事备考》卷七中曾记载吴镇画之传世者,墨牡丹图四;边鲁画之传世者,水墨牡丹图四。而卞永誉于《式古堂书画会考》卷三十二也记载了吴镇和边鲁有墨牡丹图各四,但二人画作都已不可见,连明清时期的收藏鉴赏家都未能眼见其真容,从而不知其风貌几何。
墨牡丹画作在宋元两代没有流行开来有诸多原因。单从画面看,以水墨作牡丹视觉上并不美观,甚至会引起一些俗物的联想。因此,水墨牡丹在宋元两代受到了冷落,甚至是带着调谑意味,这须从唐代说起。明人薛逢翔《亳州牡丹史》卷三记载:
唐末刘训者,京师富人。梁氏开国尝假贷以给军。京师春游,以观牡丹为胜赏。训邀客赏花,乃系水牛数百在前,指曰:刘氏墨牡丹也。[5]430
刘训此举显然是戏谑调笑。“墨牡丹”从此以后也成为一个典故,用来代指水牛。牡丹花是富贵典雅的象征,而水牛则是乡村的、俚俗的,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审美鸿沟,正是这种鸿沟造成了一种张力,使“墨牡丹”成为一句笑语。以水墨作牡丹,不管是从视觉形象上还是从想象空间上看,都容易得到“一团黑”的印象,故让人将其与水牛联系起来。宋薛季宣有《复和仲蟠二首》其一,说道:
园荒不减游群鹿,才尽应悲短续凫。有墨牡丹君种否?乡邦能借一畦无。[4]28657
元代戴表元也有诗《次韵答邻友近况六首》,其一道:
十百琅玕接屋山,麦花淡白菜花斑。村园富贵谁消得?更看溪南墨牡丹。[6]485
两首诗里面所提到的“墨牡丹”都是水牛的代指,表现了作者乡间游赏的意趣。其中第二首更是明确地说欣赏溪南的墨牡丹是一种“村园富贵”,可见当牡丹花以水墨的形态展现出来时审美上存在相当的阻力。尽管宋元时人们已接受了以水墨作梅花的艺术,但是对于水墨作牡丹还持一定的保留态度。正如明人宋应昇所言,“刻昔之舟以冀今之获,譬之水墨牡丹不入时眼久矣”。[7]361一方面,牡丹花象征的富贵典雅,不符合宋元人平淡清雅的思想意趣;另一方面,牡丹色彩艳丽,似乎并不适合用水墨来表达。这种认知直到明代才出现了改观。
二、美人之喻和流年之叹:沈周、陈淳墨牡丹诗画创作思想主流及新变
到了明代,水墨牡丹画作真正流行起来,并且伴随着相应的画面题诗。引领这股潮流的是沈周和陈淳。沈周,字启南,号石田。清代陆心源在其《穰梨馆过眼录》卷十六记载了沈石田《水墨牡丹》轴:
纸本长四尺八寸七分,广二尺三寸八分。
正德改元三月二十八日,江阴薛君尧卿见过,适西轩玉楼牡丹已向衰落,余香剩瓣犹可把酒留恋。尧卿索赋《惜余春慢》小词,遂从而填缉一阕,以邀尧卿和篇。词曰:
院没余桃,园无剩季,断送青春在地。临轩国艳,留取迟开,香色信无双美。何事香消色衰?不用埋冤,是他风雨。苦恹恹,抱病佳人,支倦骨酸难起。 尽满眼,弱瓣残须,倾台侧嫣红烂紫,令人可惜。十二栏杆,更向黄昏孤倚。只见东风西乱飞,随例忙忙、何曾因子。慢劳渠,吊蝶寻蜂,知得断魂何许。[8]292
上面这首词为沈周所作《惜余春慢》。他与薛尧卿共同游赏西轩玉楼牡丹,看到牡丹凋落,只剩残香剩瓣,故有此作。“念九日复引小酌,时花遽为风雨净尽,感慨无已,仍倚韵一阕,以既余怀。”[8]293过了几日,沈周又作一首《惜余春慢》,词云:
艳比妃杨,仙疑白李,岂称贫家贱地。东君顾恤,开及茅堂,依旧之才之美。应是书生分悭,故故先飘,纷然红雨。悄西阑,堕者难拈,倾者亦难扶起。
想昨日,羯鼓豪门,山殽池酒。宾朋满紫。今番今日,一体无聊,富贵怅何堪倚。打算荣枯盛衰耳,自有时。□何消筹子。慢填愁,且赋新词,命作惜春还许。[8]293
之后又填《临江仙》词:
昨日把杯今日懒,可堪残酒残枝。埋冤风当玉离披。顿无娇态度,全有病容姿。
恼得吾侪搔白发,带花落地垂垂。此花虽落有开期。不教人不惜,人老少无时。[8]293
前两首《惜余春慢》词牌和词意十分吻合,作者反复咏叹的是因牡丹凋落而引起的年华之思。第一首第三句“断送青春在地”可谓总领全篇。牡丹香消色衰如同抱病的佳人倦酸难起,东风西风乱飞,姹紫嫣红成了满眼的弱瓣残须,饱含着感慨时光流逝、青春不再的惋惜之情。第三首《临江仙》则加入了沉重的历史反思,将牡丹花和唐朝的盛衰转关结合起来。李白曾写了三首杨贵妃的诗,这三首诗把牡丹和杨贵妃交互而写,花即人,人即花,人面花光浑融一片,同蒙帝恩,故后人常将牡丹花来比拟杨贵妃。[9]389沈周第二首《惜余春慢》当中,“想昨日,羯鼓豪门,山殽池酒。宾朋满紫。今番今日,一体无聊,富贵怅何堪倚”,显然是在追忆安史之乱的情景。杨妃深得玄宗宠幸,犹如牡丹花一样国色天香,享受世间无上的荣华富贵,但是一朝羯鼓动地,王朝的繁华转瞬间毁于一旦,沈周因此发出了“荣枯盛衰自有时”的感慨。
沈周出身书香世家,本应走上功名仕途,但是他不求富贵,甘于淡泊,一生布衣。对于富贵荣华的看淡、盛衰有时的认识寓于他的词作与画作中。“此花虽落有开期。不教人不惜,人老少无时”一句透露出作者惜春惜时的心思。容颜凋谢一去不回,人老也再无少时,字里行间表达出沈周对于牡丹花香消玉殒的惋惜之意以及对于人生年华老去的悲情。正如他在给《吴瑞卿墨牡丹》题诗中所说的,“吴生又与花传神,纸上生涯春不老。青春展卷无时无,姚家魏家何足道”[10]5250,同样表达了青春流逝的不可挽留,所不同的是加入了借笔墨为花传神,使青春常驻的努力和乐观。
沈周所绘墨牡丹一朵盛放,似有风拂过,微微摇动,附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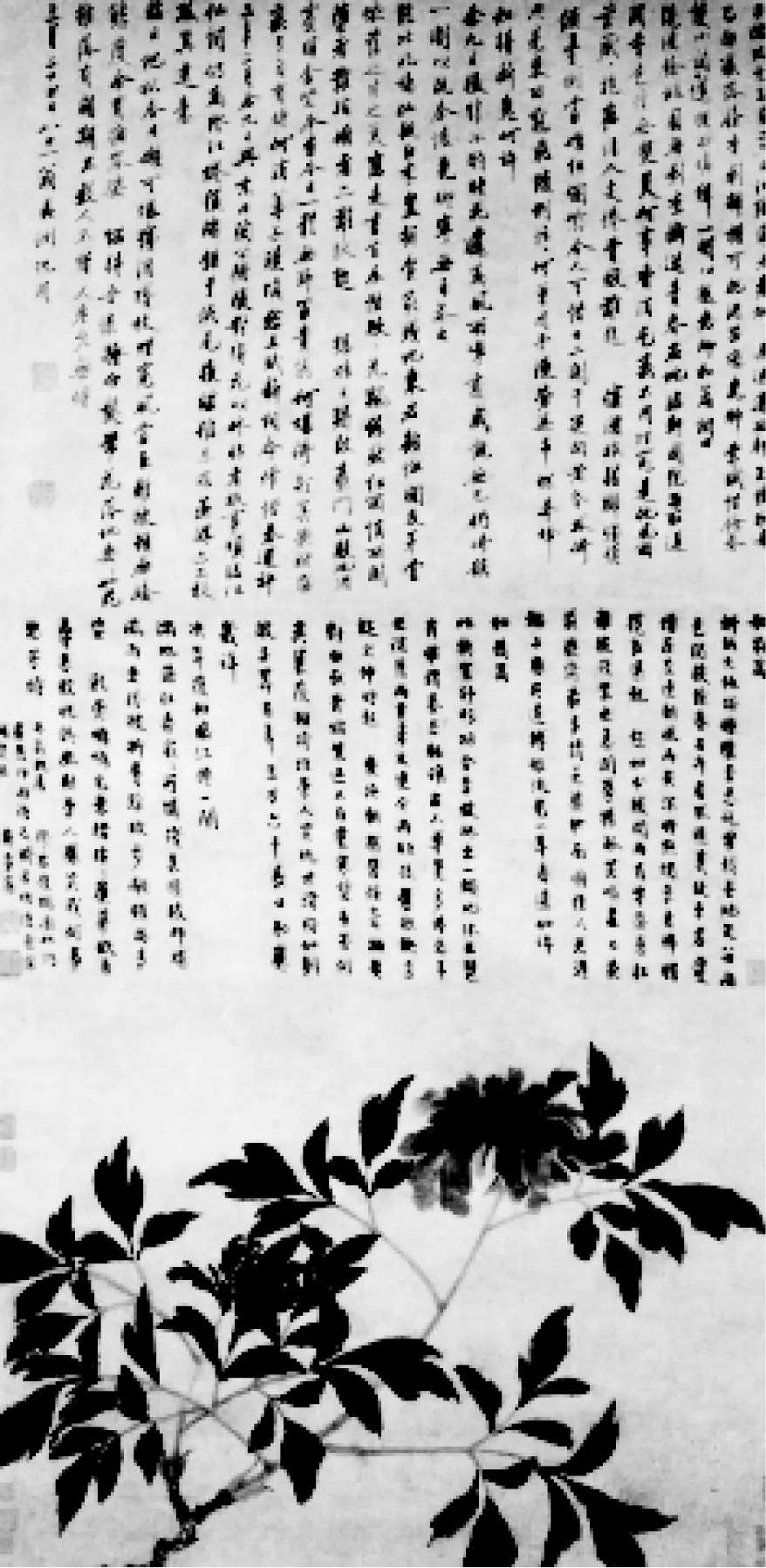
图1 沈周 墨牡丹纸本 水墨纵150.4厘米,横47.0厘米
图1整幅画面显得十分素雅,比较符合沈周淡然处世的人生态度。虽以水墨出之,牡丹仍不失其花王风度,而沈周在诗词中也反复咏叹了牡丹花犹如美人一样的风华,以及对这种风华容易衰减的感叹。牡丹花是富贵之花,是华美之花,和梅花、兰菊等花卉显然有别。这种思想在陈淳那里延续,但是稍稍发生了一些新变。
陈淳是和沈周齐名的大家,胡应麟曾说:“二百年来画花卉,吴中沈周称第一。颉颃并数陈生淳,不事丹青祗水墨。天机一派掌上流,尽扫铅华露风骨。”[11]162陈淳和沈周颉颃并称,而且也以水墨作花。胡应麟在得到陈淳的牡丹画作之后,不无激动地夸赞陈淳画作无以伦比的收藏价值:“为拈老句题册终,跋扈飞扬迥相敌。连城十五差足偿,美锦三千复何惜。卧观旬月仍卷还,笑杀明诚录金石。”[11]162赵明诚极爱徐熙的墨牡丹,但是无奈因卖家索价太高而含恨错失。[12]213胡应麟自信地说自己收藏陈淳的牡丹画作,比徐熙的画还要难得,可见其对陈淳的推重。诗人对于陈淳墨牡丹的认识,仍然基于牡丹的独特之处,即其容姿好似是雍容华贵的杨妃,其凋落则让人深感惋惜。胡应麟说道:“余家藏道复水墨牡丹,纷披老笔而扇头折枝浅绛,丰肌曼色嫣然袭人。”[13]577他遂题一绝:
谁写天真第一枝,盈盈霞色照轩墀。多情错认杨妃醉,亭倚沉香日暮时。[13]577
墨牡丹的风范,就是杨妃之美,也即陈淳笔下的“名花嫣然媚晴昼”:
东风飘飘不绝吟,游蜂舞蝶相追随。名花嫣然媚晴昼,深红浅白纷差池。高堂列宴散罗绮,珠帘掩映春无比。歌声贯耳酒如渑,醉向花前睡花里。人生行乐须及时,光阴有限无淹期。花开花谢寻常事,宁使花神笑侬醉。[14]1010
“人生行乐须及时,光阴有限无淹期”,这两句表达了和沈周墨牡丹题诗相同的含义,而且巧的是,陈淳还表达了与沈周一样的创作心态,即用画笔来使牡丹的风神永驻在画面上,使青春成为永恒:
洛下花开口,妆成富贵春。独怜凋落易,为尔贮风神。[15]671
但是,陈淳墨牡丹诗画所体现出的创作思想还不止于此。随着水墨形态的进一步实践,就牡丹花而言,褪去她的姿色而使用黑白两色以调节浓淡变化,被认为是触及了“国色”的根本特质:国色是不须妆点的,国色的本真是淡雅的,而不是浓艳的;是疏略的,而不是繁缛的。沈周在给《吴瑞卿墨牡丹》的题诗中已经出现了这种思考的端倪。在他的诗中写了吴生、野僧和自己饮酒赏花的乐事。赏花之余,吴生创作了染墨牡丹,并且说“知渠色相本来空,未必真成被花恼”。[10]5250这是借助僧人的禅悟进行的解释:色相本都是空,所以牡丹不管是设色还是墨染都是视觉的幻象,最重要的是要洞察其背后一切皆空的本质。这一点在沈周的墨牡丹诗画里并非主流,但是陈淳则有了更加细致和清醒的认识。他说:“玉情温洁上花枝,低首风前若有思。红紫总能迷俗眼,谁知真色自无施。”[16]467红紫的色彩能够迷俗眼,因为他们不知道真色就是一无所施。在另外一首墨牡丹题诗里,陈淳更是指出,不施脂粉是“素贞”性质的表达。诗曰:“春是花时节,红紫各自赋。勿言薄脂粉,适足表素贞。”[15]691
这样,图画水墨牡丹背后的创作思想,其实已在向原本已经经典化的梅竹创作靠拢。竹子虚心有节,梅花凌寒开放,菊花傲然坚贞,兰花纤尘不染,这些意象在传统文化里都带上了节操德行的寓意,他们的水墨形态,正是所谓的“素贞”之美。而一向被视为带着宫廷身份的富贵之花——牡丹,也渐渐地脱落了她的富贵气和宫廷气,一步步向着“四君子”“三友”的方向走近。
三、“人间究有相逢时”:墨牡丹与墨梅竹创作思想的最终趋同
陈淳尚有水仙、梅花、墨牡丹的合卷,这也是前无古人的创造。这些花卉不仅仅因为水墨的创作技法接近而进入了同一个画面,更是因为她们身上所寓含的德行品性正在一步步趋同。如果说沈周和陈淳的创作思维模式,还处在因物感兴、物我互动的阶段的话,那么到了唐寅和徐渭,墨牡丹的创作其实进入了物我合一、不分彼此的境界。换句话讲,水墨形态、风致洒落的牡丹花,其实是创作者个性特征和人格品性的写照。他们很少再用墨牡丹比拟美人或者杨妃,而是直接指向自己,将那种青春逝去的感伤、富贵逝去的惆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大胆创新的自信,无拘无束的洒脱,以及不媚时俗的孤高。这样的特征进一步使得牡丹和墨梅竹的创作思想合流,最后趋于一致。
唐寅曾为某僧人题墨牡丹,文徵明对此写道:
居士高情点笔中,依然水墨见春风。前身应是无尘染,一笑能令色相空。[17]402
在与僧人交往的过程中创作墨牡丹画,赠僧人以作“清供”,或为僧人题墨牡丹诗,这种情况在明代屡见不鲜。因为僧人的身份和佛法觉悟,这些诗画都触及一个佛教关键词:色空。诗人常以此来区分水墨作牡丹和工笔设色牡丹的根本不同。这首诗中“居士”指唐寅,“高情点笔”指其作画,“无尘染”代指佛门弟子,说唐寅前身是无尘染,意在说明赠僧人墨牡丹画作是因其具有前世佛缘。其谈笑间作画,能看穿色相而还原事物本相,故曰“一笑能令色相空”。乾隆在《御制诗集》里曾夸赞唐寅墨牡丹:
伯虎多能风雅伦,写生犹擅独传真。别成卉里孤高种,羞说世间富贵春。三朵那期归上苑,六如想欲证前身。不衫不履其人似,却得花王自在神。[18]438
此诗可当文徵明诗的绝好注解。“卉里孤高种”指牡丹,“羞说世间富贵春”以及“那期归上苑”,暗喻墨牡丹脱落贵气、不求端庄雅丽的走向。“六如”指唐寅,“证前身”是对文徵明“前身应是无尘染”一句的推衍。诗的最后两句描写了唐寅墨牡丹的基本风貌,以人的不衫不履与画面洒落不羁的写意风神相比拟,也即“自在神”。画牡丹不求展现牡丹的“贵气”,这是创作观念的一大转变。乾隆说唐寅“羞说世间富贵春”,可谓颇有见地。
唐寅也有自题牡丹画诗:“谷雨豪家赏丽春,塞街车马涨天尘。金钗锦绣知多少,多是看花烂醉人。”[19]33这首诗写豪家赏牡丹的热闹场面,车马填街,锦绣琳琅,但是,这些人又知道什么呢?不过是些醉生梦死、娱情声色的庸庸之辈罢了。作牡丹画舍去其“富贵气”,文徵明还有一诗可作注脚:“墨痕别种洛阳花,仿佛春风似魏家。应是主人忘富贵,故将闲淡洗铅华。”[17]402“主人”指作画者,“忘富贵”指用水墨的姿态洗去牡丹的铅华雍容,画出“花王”的别样风神,从而展现画家淡泊素雅的审美情趣。唐寅另有一诗题在其墨牡丹轴上,诗曰:
谷雨花开春正深,沉香亭北昼阴阴。太真晓起忘梳洗,云鬓钗钿未及簪。[20]1089
这首诗同样以生动的笔法展现出“不衫不履”的花王神态来。牡丹的水墨形态,弱化了线条的描摹作用,加上大写意的笔法,使本应端庄雅丽的牡丹画作,带上了率意而为、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其背后所指更多的是具有独特个性的创作者,而不是富贵典雅的皇家气质,即使是以杨太真作喻,其本意也是展现其不衫不履的自在神态,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创作对象身份下移、创作手法上重意忘形、创作风格上追求清雅素贞之美的趋势。
徐渭创作的墨牡丹诗画数量较多而且艺术水准极高。他有一首水墨牡丹的自题诗为其墨牡丹诗画创作奠定了基调:
腻粉轻黄不用匀,淡烟笼墨弄青春。从来国色无妆点,空染胭脂媚俗人。[21]852
“腻”字和“轻”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表现出徐渭对于设色精细,追求富丽精工之作的厌弃。他认为真正的国色从不用妆点就可以倾国倾城,摆弄胭脂只可以迎合俗人的口味和兴趣。一个“空”字点出此类画作缺乏传世的价值,毋宁不作。徐渭还有一诗与此同义:“牡丹难以墨,用墨难以浅。淡淡著胭脂,聊以媚俗眼。”[22]168用水墨画牡丹非易事,为求好看只好施之以胭脂,但是这样只能逢迎俗眼,不能表现真正的国色。因为“国色”无需妆点,美在其神,而不是以贵媚人。
徐渭一生清贫,经历了短暂的入幕生涯之后,潦倒终老。脱去富贵的墨牡丹,可以看作是其自身的写照。其诗曰:“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21]397又说:“不藉东风力,传神是墨王。雪威悲剑戟,鏖战几千场。”[21]836以“墨作花王影”,而以“胭脂付莫愁”,[21]836写出的是牡丹之神韵,而非逼真的形象。这种神韵,非贵非妍,正和象征高尚品节德行的墨梅竹相通。
徐渭曾自言学“彭城写岁寒”,[21]850“彭城”代指文同之作墨竹,“松竹梅”为岁寒三友。徐渭有很多画作将水墨牡丹和梅花或者竹子合卷。清人方廷瑚说,牡丹和梅花虽不同时开放,但是将二者“位置尺幅”中,天机迅发,而画面的题诗,“尤为奇崛,出人意表”[23]836。附图2:

图2 徐渭 水墨牡丹梅花(局部)纸本 水墨纵96.5厘米,横27.2厘米
徐渭的题诗曰:
松烟烧得汝窑黄,墨渖闲涂花里王。更配一梢清似水,俨如光武对严光。[23]836
“闲涂”二字,写出了徐渭创作此画时的率性意趣。“一梢”指梅花,梅花和牡丹开放的时节迥异,但是徐渭却将二者安排在一起,一方面追求一种新奇之感,另一方面要揭示一种关系,即以梅花喻严光,以牡丹比光武。严光事见《后汉书》,他和光武帝是故交,光武曾问计于严光,并许以高位,而严光婉言谢绝,归隐不仕,展现出高洁磊落的节操。有一次,严光就寝将一条腿放在光武帝的身上,光武帝丝毫不以为意,不惊动严光以让其安睡,表现出开阔的胸襟和尊重贤良的谦逊。[24]2763二者的关系可视作是一种君臣之间的完美相处模式,如查揆所言,严光与光武“鱼水最贤”,“但使牡丹开早梅开迟,人间究有相逢时”[23]836,表现出对于君明臣贤的希冀。这种期待其实也是徐渭的理想。方廷瑚说道,此幅画作“命意奇异,运笔古秀,胸中权奇兀奡抱负不凡之致,悉于题句中寓之”[23]836。牡丹和梅花合卷,毕竟是罕见的作法,就像严光和光武之鱼水最贤,可是这种和谐融洽的关系百不得一甚至只是空想而已,所以才显得难能可贵。徐渭曾遭遇科场腐败而屡试不中,后又因胡宗宪案受到牵连,有志难酬。他作墨葡萄画,以葡萄喻明珠,以明珠喻自己的才华,发出明珠不得其用无所售卖的感慨,如:“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21]400又:“数串明珠挂水清,醉来将墨写能成。当年何用相如璧,始换西秦十五城。”[21]401以葡萄喻明珠之才,感慨自己有才而不得为世所用。在《与薛鸿胪》中徐渭说道:“相如词坚,秦璧始岀。葡萄一幅奉上,窃比玉斗谢罪之遗,幸勿碎之”。[21]1024他还将各种不同季节的花卉画入同一画面,并题诗说这是由于“天道差池所致”,[25]234可见徐渭对于科举取士的失望和郁郁不得志的无奈与愤懑。
徐渭还常常将牡丹与竹合画。如《大醉作勾竹两牡丹,次日始得题》:“画也昨日题今朝,酒杯虽冷墨犹潮。湘娥总有凌波色,姊妹江东数二乔。”[21]405《题牡丹竹》:“牡丹须绿叶,春早叶难多。莫道扶持少,新篁捧绛罗。”[21]840《牡丹竹》:“我学彭城写岁寒,何缘春色忽黄檀?正如三醉岳阳客,时访青楼白牡丹。”[21]850附图3、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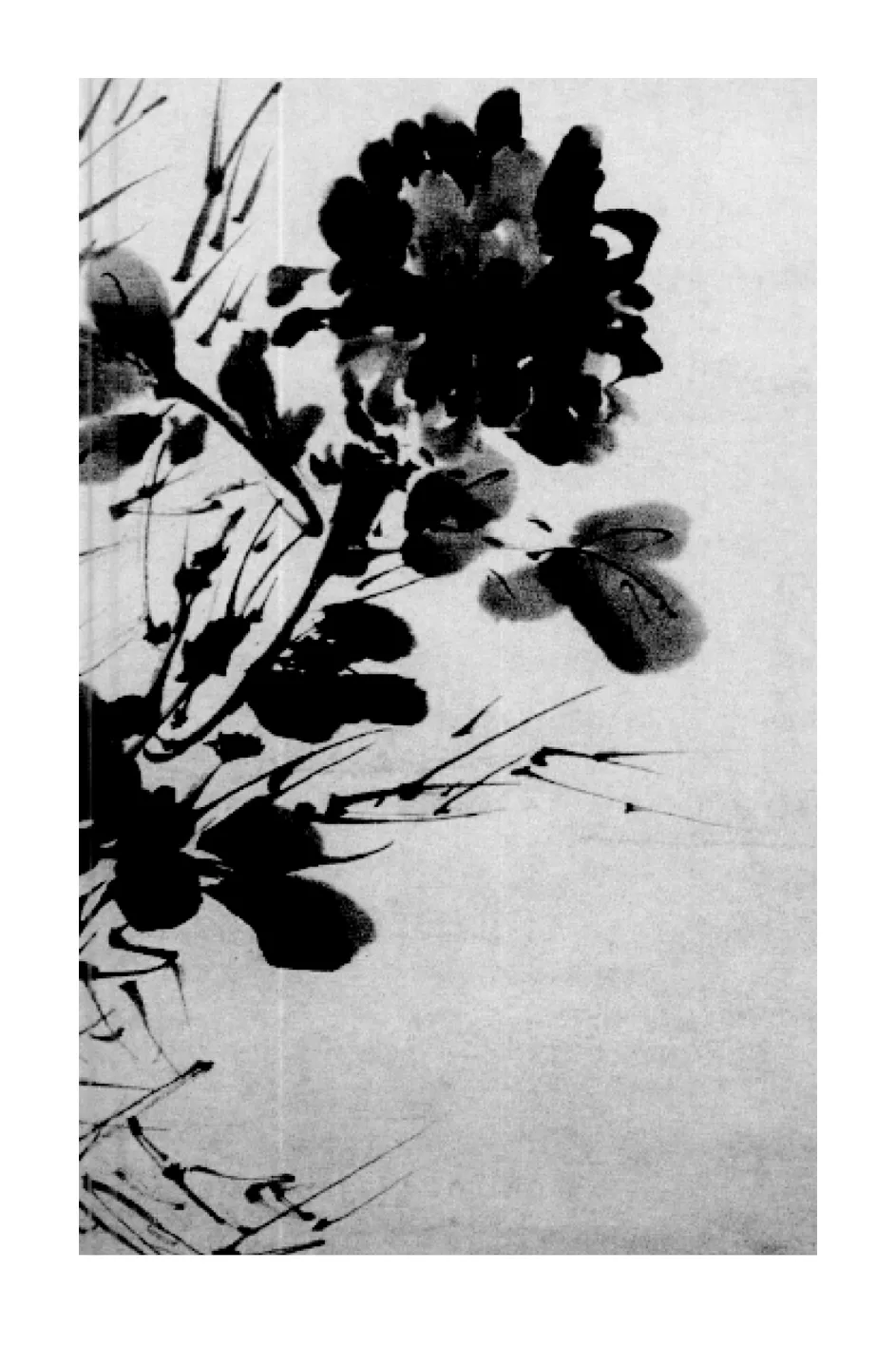
图3 徐渭 花卉图轴(局部)纸本 水墨纵129.5厘米,横32.2厘米

图4 徐渭 墨花九段卷(局部)纸本 水墨纵46.3厘米,横824厘米
徐渭还有一幅画作《墨牡丹飞白竹合卷图》,其创作理念和前面所言牡丹梅花合卷图非常相似。徐渭题诗道:
墨点娇姿小绛匀,笺中亦足赏青春。长安醉客靴为祟,去踏沈香亭上尘。[21]848
这首诗的大意是,我以水墨作牡丹花,在一张纸上就可以欣赏到牡丹的青春风华,而长安醉客则车服华丽地去到洛阳观赏牡丹,沾上了沉香亭的尘土。诗给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翰墨娱情,自由自在,一是追步繁华,混入红尘。诗最后两句说的是李白。玄宗极为赞赏李白的才华,李白因此受到破格待遇,贵妃为之倒酒,力士为之脱靴,可谓盛极一时。但是富贵繁华容易凋谢,不久李白便被赐金放还,纵然才高盖世,也难善终。由此徐渭表达了不慕富贵、淡泊自守的骨气和高尚的节操。这一点与墨梅竹的创作思想完全一致。
这幅图卷之后有题跋,说徐渭为有明第一人:“当日沈青霞君曰,自某某以后若干年不见有此人”。[26]2189青霞为沈炼,徐渭和其关系非同一般。沈炼曾屡次上书揭露奸臣严嵩的罪行,但被严嵩谋害致死,徐渭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作文祭之,为沈炼作《哀沈参军青霞》《与诸士友祭沈君文》。[27]5533既然徐渭有牡丹梅花合卷的画法,并拿光武和严光相比拟,那么这幅牡丹和竹子合卷的图,是否也可以有这样的暗喻:以竹喻己,独立于世外,以牡丹喻大臣沈炼,身居高位,心怀天下,但是一入侯门深似海,刚直的沈炼遭到了奸臣的排挤和陷害。“去踏沈香亭上尘”,表面上看是一种责备,但是结合沈炼的遭遇,与其说是一种对入世合流的指摘,不如说是徐渭对沈炼的同情和惋惜。“国色”可以用来比喻美人,也可以用来比喻这些高洁之士,不是从外貌上评价,而是从内里上判断:真正的国色不用胭脂妆点,而是具有高尚的操守和追求。以墨牡丹之“国色”喻沈炼,恐怕并不为过。
这种以物喻人、物我同一的思维模式,是墨牡丹和墨梅竹最终趋同的根本原因,沟通它们的则是三者共同具有脱落俗气的清容之美和孤高自守的清操之德。如徐渭自题墨牡丹言:“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终不是此花真面目,盖余本窭人,生与梅竹宜,至荣华富丽风,若马牛宜弗相似也。”[28]2徐渭说牡丹本应用钩染烘托之法,方能显出荣华富丽之风,但是这样作画就与自己的本性格格不入,所以才用泼墨为之,以墨牡丹展现梅竹的品格。
另外,这种趋同现象在徐渭那里登峰造极,与徐渭本人作诗作画大胆创新、独具面目的追求也是分不开的。除了墨牡丹和梅竹合卷,徐渭还创作了芭蕉墨牡丹图。他题诗道:
知道行家学不来,烂涂蕉叶倒莓苔。冯伊遮盖无盐墨,免倩胭脂抹瘿腮。[21]405
“行家”是画工之意,“烂涂蕉叶倒莓苔”写出了他创作时的随性率意和自由不羁,这是循规蹈矩的画工所学不来的。徐渭的墨牡丹不染胭脂,脱落掉了世俗之贵气,打破了牡丹开放的时令限制,自言为“墨中游戏老婆禅”[21]184,笔尖如有魔力,像是道士殷七七能遣开非时花,又像是“造化小儿”自由摆弄万物。徐渭在《题牡丹蕉石图轴》中提到:“焦墨英州石,蕉叶凤屋材。笔尖殷七七,深夏牡丹开。”[21]62殷七七为道士,能法术,使开非时花。又有:“牡丹雪里开曾见,芭蕉雪里王维擅。霜色好尖一小儿,冯渠摆弄春风面。”[21]62徐渭自注:“尝亲见雪中牡丹者两。杜审言:吾为造化小儿所苦。”[21]62由此可知,徐渭所言笔尖小儿为“造化小儿”。[21]62清代视远上人曾收藏有徐渭的《墨牡丹》图,査慎行为上人所藏之图题诗,揭示了徐渭这种打破陈规、自成一家的创新精神:
浓墨点双花,枯枝缀一桠。目中无尹白,放笔自成家。[29]1607
诗的前两句是对画面的描摹,后两句所说的尹白是以墨画花的先驱,曾得到苏轼的赞誉。言“目中无尹白”,表现了徐渭不为前人所束缚,特立独行的精神。正因为不师古人,直抒胸臆,才能自成一家,墨牡丹画作带着他强烈的个人色彩。
总的来说,脱落脂粉气的“清容”与以素贞自守的“清操”,体现出明代墨牡丹诗画创作的“清美”追求,这种“清”的境界,也正是墨梅竹要达到的风范。故而在水墨牡丹流行的过程中,三者渐渐走近,产生了创作理念、审美意趣的趋同现象。而徐渭等人的大胆创新,不仅丰富了墨牡丹诗画的精神面貌,而且推波助澜,使墨牡丹一步步向着墨梅竹靠拢,最终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