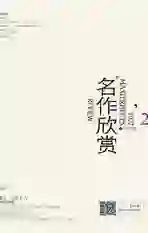全球性视域下东方行者的文图书写
2022-02-19刘璇
摘 要:作为诗人兼画家的蒋彝共出版了13本游记,他始终立足东方行者的审美视野,充分发掘中国诗画丰富的艺术资源,将写意、工笔、白描等绘画技法糅入游记的创作灵思,以画配文,诗画相衬,在诠释西方风景、建筑、服饰等风物的过程中,自觉加入中国书法的艺术形式,营造了文图互释下诗、书、画同构的东方意境,探寻了民族主义立场向世界主义观念的价值转向,体察全球性视域下东西交汇的艺术共鸣。
关键词:蒋彝 文图 画记
蒋彝1903年出生于江西庐山附近的九江,家境优渥,年少时便学习诗词绘画,时逢中国近代时局大变,北伐混战,社会黑暗,胸中抱负难以施展,便于193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政治学,本计划学成归国一展宏图,却在世界局势等种种影响下继续旅居海外,在英生活22年后,于1955年又选择移居美国生活22年。在寓居海外40多年的生涯中,蒋彝共出版了13本游记,题材涉猎广泛,地域横跨欧洲、亚洲、澳洲及美国。其中,8本游记已在中国出版。包括1937年率先在英国出版的《哑行者画记》系列的第一本书《湖区画记》,还有后来出版的《伦敦画记》《牛津画记》《爱丁堡画记》,再到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画记》《旧金山画记》《巴黎画记》和《波士顿画记》。作为诗人兼画家,蒋彝始终立足东方行者的审美视野,充分发掘中国诗画丰富的艺术资源,将写意、工笔、白描等绘画技法与游记创作巧妙糅合,同时将图画、诗歌、书法融合,以横贯中西的笔触解读西方的风景、建筑等风物的特色。他在海外的异乡书写中积极开展文图实践,以图像为媒介,沟通了中西文化的时空对话,自觉营造了文图互释下诗、书、画同构的东方意境。尤其在战争的历史语境中,他既在作品中寄寓了对民族身份、伦理道德的全球性思考,又在不断的旅外异乡书写中,借助文图呼应的视觉经验,蕴蓄着东方神韵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转向中的勃勃生机,体察全球性视域下东西交汇的艺术共鸣。
一、文图互释下诗、书、画同构的东方意境
出生于富裕家庭的蒋彝,6岁时进入私塾读书,“《三字经》是启蒙读物”,接着便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些儒家经典,而后“学习古代儒学大师的评注”,除了读书之外,书法也是他“每天必修的功课”。不仅如此,蒋彝幼年时便对绘画颇有兴趣,“有时也爱涂上几笔”,蒋宅厅堂的墙上挂着许多画作,蒋彝常常协助父亲按季节更换画作。12岁时,“他开始认真地跟着父亲学习绘画”,逐渐“了解中国绘画的历史和一些名画家的轶事”,这不仅为他后来的绘画技艺奠定了深厚的艺术功底,而且激发了他诗、书、画同构创作灵感的产生,使他自觉地在文图互释的创作思路下营造出具有东方特色的诗画意境,并以此来描绘西方国度的自然山水,顺应了全球性文化对话的潮流。
1937年出版的《湖区画记》,是蒋彝《哑行者画记》系列的第一本书,记录了他游历英国湖区瓦斯特湖、德韵特湖、八德连湖等七个湖泊的胜景和感受。全书共配有12幅插图,皆为蒋彝自己的画作,每篇文章均有一两首中国书法的题字,亦是出自蒋彝之手。在绘画技巧上,蒋彝沿袭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风格,借助毛笔“不同的运笔速度及水墨量”,“可在宣纸上画出光和影”。尽管蒋彝的黑白水墨画与黑白照片相似,但二者在本质上却不尽相同,照相机呈现出的风景是“机械的”,“但中国画家则运用笔墨、观察、筛选、重构世界”。“蒋彝是少数试图以传统的中国艺术形式表现西方的先驱,而‘哑行者’系列也证明,他所试验的技法与题材都具扩张性”,因而“他是最大胆且富原创性的作家之一”。这种“以传统的中国艺术形式表现西方”的思路正是糅合了蒋彝诗人、画家、书法家的三重身份,并通过水墨图画的介入、古体诗歌的创作以及中文书法的起承转合,使其统一在文本层面,继而在视觉观感上呈现出诗、书、画同构的东方意境,完成了文图互释下以东方笔触书写西方见闻的异乡人札记。
《瓦斯特湖》一文中,蒋彝记录了自己抵达沃斯谷山岬后的印象和感受,生动地描写了晨雾笼罩下的瓦斯特湖景观。在极目远眺中,作者只见尽头处雾霭缭绕,四周看不见山峦,也不见其他屋子,“细雨微光中,远处白茫茫的海洋映衬着两侧阴郁的树丛”,使作者“不禁想起惠斯勒的画作”,这与文段中的水墨图画相得益彰。图画中,毛笔的黑墨涂抹出远山依稀的轮廓和近处的“苍郁小树林”,中间则以中国山水画的留白技法勾勒出大片圆形的白色湖面,描繪了细雨中瓦斯特湖水宁静无波的景象。在黑墨与留白的衔接处,作者自然地运用浅墨进行渲染,赋予了整个画面微雨朦胧的诗情画意,极具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古典风格。下文中作者在描写狂风骤雨时又以诗入文,对自然展开古典的抒情,采用五言古体诗描述自己的所见。诗歌既与全篇游记的文字排版保持一致,同时又被作者按照中国书法的体式重复地写于该文段之后,使得诗歌与书法浑然一体,诗歌的横写与书法的竖列排版,尽管构成了形式上的对照,却在内容上体现了统一的旨归,蕴含着陶渊明式的田园况味。篇末的图画《瓦斯特湖畔的宜人午后》对自然进行摹写,画中山峦叠嶂,小屋和林木依山傍水,营造了清新质朴、悠然自得的意境,这与先前诗歌、书法中的“倚石自悠然”遥相呼应,促进了文图内容和风格的互释、互动,展现了诗、书、画同构的东方意境。与此类似,在《湖区画记》的其他游记中,蒋彝均将水墨画、诗歌、书法融为一体,不断地进行以中国艺术形式诠释西方自然风景的艺术尝试,在文图互释的过程中探寻中西审美感知的共通性。
与《湖区画记》相较,后来出版的《哑行者画记》系列则与它不完全相同。在绘画技法上,除了《湖区画记》中的水墨写意,蒋彝还在《爱丁堡画记》《波士顿画记》等游记中注重运用工笔、白描等方式模拟现实,丰富了图画的种类。在图画的内容上,他则在其他画记中突破了《湖区画记》中以自然山水为主轴的绘画模式,代之以西方的人文景观,包括建筑、城市、服饰等,拓展了文图互释的文化视野。
二、文图互译下民族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向
近代的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封建王朝的覆灭以及西方列强的侵略,打破了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的生活状态,亦影响着国人的民族观念。蒋彝的民族观念从小受到祖父的影响,他总是听祖父讲“许多有关民族英雄和中国历史的故事”。当他进入中学后,中学的现代教育“开阔了蒋彝的视野和知识面”,“他很快就注意到自己的变化:‘我跟家人说话与以前不一样了。’他开始与外人接触”,还“常常和同学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1918年,蒋彝参加学校组织的一战胜利庆祝游行活动,高呼口号“庆贺世界和平”,欢唱《和平之歌》,“心里感到十分骄傲”,因为在此之前,他无法看到报纸,“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对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也知之甚少,“战争的结束,标志着中国新意识的开始,蒋彝从此开始对政治、现代社会表示关注”a,也愈渐受到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感染。上大学时,“科学救国”学说盛行,蒋彝未听家人的建议选择文学专业,而是毅然选择了化学专业。正如他自己所言:“我那阵子很革命的。”由于接触到了新的思想理念和科学文化知识,大学时代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时期,引发了他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以及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注”。此后,他又在1925年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海南岛》的散文,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开发海南岛、捍卫领土主权的建议。但蒋彝的民族主义热情却在他为官期间屡屡受挫,他发现周围的官员皆是尸位素餐,不顾人民生死,只为自己谋利,于是他萌生了去英国留学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想法。到达英国后,各国的民族情绪在战争的硝烟中持续发酵,欧洲的局部战争、中国故土的反侵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不断地冲击着蒋彝的民族观念,使其突破了出国前守一族之安定保一国之昌盛的民族主义思想,继而转向更为开阔的全球性视域,即以艺术的价值化解种族歧视,打破对立,缓解冲突,不再分殊民族的界限,而是汇通各民族共同情感的世界主义。这一观念的转向成为他文图创作的核心题旨,流露在游记的字里行间,抒发了对民族身份、伦理道德的深刻思考,把握住了战争时期东西交汇下的艺术共鸣。
1936年,“蒋彝的湖区之行前四天,西班牙内战爆发”,“一战”后人们稍稍平静的生活再次掀起万丈狂澜,“不稳定的局势重创蒋彝的心”b,使其在湖区的游览难免笼罩在对战争的忧虑中。面对湖水中的游鱼,蒋彝忍不住发问:“你们也在种族、国籍、语言或所谓的‘文化与文明’间划出界限吗?”c对世界各民族共处前景和人类命运前途的担忧总是萦绕在蒋彝的心头,潜藏于他闲赏山水的豁达背后,奠定成游记隐而不彰的忧患基调。但这种忧思随即又在自然山水的宁静风貌中消散,在古典诗歌的婉转静好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在他看来,“人类的文化感情和思想世界,决不会因为战争的破坏而受到改变”d。因此,蒋彝的文图创作不仅是文学作品在形式上的现代试验,更是他自中国远行至海外后反思战争,由民族主义转向世界主义的观念流变,也是他试图缓和民族矛盾、突破种族界限的艺术探寻,寄托了以文化的认同和情感的共鸣维持世界和平的美好宏愿。
《湖区画记》中的《瓦斯特湖》一篇,作者借助图画《大陡岩山对面的云雾繚绕的岩坡》中的自然景观,抒发了自然面貌相同而人类不同的感慨,图画中山峦与云雾和谐统一,这与作者理想的人类相处状态相呼应,从而暗示了水墨画的象征内涵,拓展了文图互译在情感写意层面的深度。在《伦敦画记》中,作者开篇的献词便直指文本的思想精义,既表达了对兄长的敬意和缅怀,又寄蕴着文学艺术抚慰创伤的意义。而在《风雨中的伦敦》一文中,当作者感受到风雨的哀怨时,不免联想到托马斯·哈代诗歌中被沉重心事压抑的人们,继而联想到来自祖国和欧洲的战争消息,对时局的忧虑成为压在他心头的重荷,喷涌成笔下磅礴的诗篇。诗歌与文中嵌入的书法前后呼应,随着书法字体的由大到小,诗人的抒情也渐入尾声,其难平的心绪在短暂的宣泄之后亦得到了舒缓,整个书法作品构成图画的同时,又与诗歌的情感暗自契合,使得文章从诗、书内容的简单对应层递到诗、画情感的复杂糅合,展现了文图互译下文学作为艺术载体所具备的排遣忧思的功用。在《牛津画记》中,《羞怯的容颜》一文记叙了作者游历港口草原时的所思所感,生动、形象地刻画了马和牛“同享一片草地”,欢快嬉戏,活力充沛的和谐情态。特别是当作者走进马群附近的石南树丛,发现“每匹马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有些安详地小口吃草,有些漫无目的地小跑步,有些则仍成列地相互追逐”e。文字的传神描写照应了文中《港口草原的秋天》这一图画。画面中草原宽广,水流静谧,树木掩映,牛马雀跃,一幅闲适散漫的秋日牛马图跃然纸上,与清新自然的文字共同营造了文图互译的和谐意境。但作者的思绪并不止于此,而是延伸到对港口草原昔日内战场景的想象上,延伸到餐桌上、马背上的“大人物们”。在蒋彝看来,从古至今,腐败君王的身边从不缺乏热衷权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虚荣心和野心早已吞没他们的仁爱道德,使他们对权力趋之若鹜。尽管蒋彝坦言自己也不能摆脱这类知识分子的支配,但他仍然倡导是一种“生命的正直品格”。因此,他认为“人不是为了个人或国家的利益而存在,应该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活”。作者在这里从眼前的和谐画面出发,想象、审视了战争与和平的历史演变,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其世界主义的主张,灌注了其对民族界限与道德伦理的终极思考,试图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深刻挖掘个体自身的价值。激昂的议论之后,作者的语调又回归了先前的平静,补充叙说了“轰炸机飞过之后,这儿仍是如此安详”f,同时,再次呼应了图画中流露的和谐宁静,点明了文图互译的深刻意涵,“在战争中,艺术发挥很大的作用,它提供慰藉,无论是前方沐血奋战的英勇将士,还是后方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的民众”g,而图画和文学作为艺术的载体,正是在世界主义视野的引领下,促进了文图互译的创作实践,昭示了人类未来命运的和平指向,沟通了全球性潮流下中西文化乃至世界各族情感的内在本质。
蒋彝旅居海外四十余年,其《哑行者画记》系列在风格上东西并蓄,内容题材包罗万象,其将绘画、诗歌、书法熔于一炉的创作模式,拓展了以中国艺术形式诠释西方人情风物的深度和广度,展现了全球性视域下文图互释、文图互译的独特思路。
adg 郑达:《西行画记——蒋彝传》,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6页,第189页,第193页。
bc 蒋彝:《湖区画记》(前言),朱凤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13页,第93页。
ef蒋彝:《牛津画记》,罗漪文、罗丽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173页,第175—176页。
参考文献:
[1] 郑达.西行画记——蒋彝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 蒋彝.湖区画记[M].朱凤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 蒋彝.爱丁堡画记[M].阮叔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 蒋彝.伦敦画记[M].阮叔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 蒋彝.牛津画记[M].罗漪文,罗丽如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 蒋彝.哑行者画记(《日本画记》《旧金山画记》《巴黎画记》《波士顿画记》)[M].梁贝特,王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7] 蒋彝.东方杂志(第22卷)[J].东方杂志社,1925(10).
作 者: 刘璇,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杜碧媛 E-mail: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