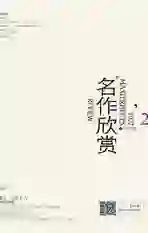《创作月刊》与“五四”新文学传统
2022-02-19杨路宏
摘 要:《创作月刊》是桂林文化城颇有分量的一份文艺月刊,刊物中的文学作品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战争本身,而是立足于现实,更多地向现实深处和民族历史文化维度掘进。这种对抗战、现实生活的深化书写不仅延续了“五四”新文学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人生的传统,而且也接续了“五四”新文学对国民性、民族文化、历史惰性的反思与追问的启蒙、批判精神。
关键词: 《创作月刊》 “五四”新文学传统 抗战书写 后方写真 启蒙精神
《创作月刊》1942年3月创刊于桂林,1943年初停刊,其在桂林刊行的时间虽然仅有十个月,出版期数只有七期,但却成为桂林文化城颇有分量的文艺月刊。主编张煌追求完美的编辑理念使这份刊物的创作、理论与翻译作品都有较高的质量,这就使这份文艺月刊在抗战文学中占有了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抗战初期,“民族意识”“救亡意识”促使文艺界迅速掀起了抗敌救亡的热潮,作家们注重政治宣传与情感宣泄,在文学实现了为抗战服务功能的同时,却使文学脱离了现实,走向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面对更为严峻和复杂的抗战情势,作家们也由狂热到理性。《创作月刊》可以说是在艰难困苦、波谲云诡的战争环境中对“文学的思考”或者“思考的文学”予以集中展示的最为典型的文学空间之一。其文学创作不再单纯地停留于抗战的宣传和呐喊,关注的对象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战争本身。而是立足于现实,更多地向现实深处和民族历史文化维度掘进。这种对抗战、现实生活的深化書写,不仅延续了“五四”新文学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人生的传统,而且也接续了五四新文学对国民性、民族文化、历史惰性的反思与追问的启蒙、批判精神。
一、沉潜的抗战书写
抗战主题的书写是《创作月刊》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创作月刊》各类体裁的创作中,有对爱国志士和英雄的讴歌,有对全民抗战热潮的描述,有对抗战必胜信念的赞颂,还有对民间反战同盟的书写。这些文艺作品在反映中国军民抗战热情的同时,更多体现的是对现实的深入挖掘,对抗战艰难性的理性认识。如吕亮耕的诗歌《给流浪者》(第2卷第1期)理性地认识到抗战的困难和艰巨,告诫人们要想取得抗战的胜利,要有骆驼般的忍耐,苦行僧般的坚毅。茅盾的小说《参孙的复仇》(第2卷第1期)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大利拉和非利士人的狡猾,这让人想起了抗战时期日本假惺惺的怀柔政策,也让我们从中感受到抗战的复杂性。
另外,这些文艺作品在描写战争中的英雄人物时,更关注他们由普通人成长为英雄的思想发展历程,这就使抗战英雄主题的书写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其中比较典型的作品有丰村的小说《北方》(第2卷第1期)、陈波儿的电影剧本《伤兵曲》(第1卷第2、3期)、王西彦的小说《旷野》(第1卷第6期)等。如《北方》描写了村民们在战火洗礼中实现的思想转化和升华。作品没有简单的停留在对老社长、金宝这样的抗日英雄事迹的描写上,而是抓住了村民们思想的矛盾冲突和艰难抉择。如清河抗战信念不坚定,想临阵逃脱。二包皮子自私爱财,一心只想保护自己的财产。但是对残暴日军的痛恨使他们最终都决定参加游击队,在时代的召唤和现实的磨炼中成为敢于反抗、不怕牺牲的真正的英雄。
二、沉重的后方写真
抗战时期,前方的战士在流血牺牲,后方的百姓也在受苦受难,在《创作月刊》中,一些作家以悲悯、愤慨的笔调叙写了下层民众的辛酸苦难的生活处境,并以讽刺的手法揭露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和种种卑琐丑态。如陈纪滢的《边城一夜》(第1卷第6期)中,在民族危亡之际,一些大后方腐败官僚置民族生死于不顾,依然把酒言欢,悠然游走在世俗的、功利性的人情世故之中。青苗的散文《琉璃堡》(第2卷第1期)中,国民党统治下西北的一个地区土匪横行,赋税和苛敛繁重,底层民众的性命贱如蝼蚁,他们在贫穷与饥饿中挣扎,车夫们、卖烧土的、挑粪夫日间靠做苦力赚钱谋生,晚上则从他们日间可怜的收入中抽出一部分寻找刺激和买醉。一些女性为了生存,依靠卖身为生。贫穷阴暗的生活已将他们的廉耻心、同情心消磨殆尽。这里的底层民众毫无信仰和希望的为了活着而活着,冷漠、麻木地挥霍着自己的生命。何其芳的散文《饥饿》(第1卷第1期)描写了国统区下层劳动者食不果腹的痛苦,在成都的一个茶馆里,一个小姑娘看到比一粒米都大不了多少的糖糕掉地上,便飞快地捡起来放进嘴巴里。在成都,经常有衣衫褴褛的小男孩在客人吃饭的时候,用饥饿的眼睛盯着客人的后背,然后拿着一把破蒲扇殷勤卖力地给客人扇扇子,希望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换点客人的赏赐。方敬的散文《磁珠》(第4、5期合刊)中,日军轰炸的警报声一响,大人、小孩向城外飞奔,城外的野地里、土坡前到处挤满了疲于奔命的老百姓。战争使人民生活在苦难和恐怖中。这些文艺作品体现了作家极大的人文关怀和丰富的生命意识,包含着作家对现实社会生活深入的理性思考,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困境并不是民众的错,暴力战争和社会的黑暗统治带来的剧痛才是应该去反思和追问的。
三、理性的启蒙精神
“五四”以来,救亡与启蒙是文学中的两大主题。抗战爆发后,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呼声,但启蒙的诉求并没有消失,在《创作月刊》中就体现了对启蒙精神的延续。
《创作月刊》对启蒙精神的延续首先表现为对抗战时期国民精神上的弱点的批判。如李广田的散文《空壳》(第1卷第2期)批判了一些国民的麻木和愚昧。在文中,一名 “对于法西斯,对于横暴,对于专制,对于一切反民主反进步的东西痛恨到了极点”的大学教授却被称为“神经病”;一名渴望光明、追求真理,对黑暗极端痛斥的女大学生也被称为“神经病”。这些走在时代前列的进步人士,他们思想深刻,风骨卓然,激愤地批判法西斯的暴行,毫不妥协地对一切阻碍民主进步的行径进行无情的抨击,但是这些不同于庸众的有志之士却被愚昧麻木的庸众称为神经病,这一怪现象使作者感到痛心,他尖锐地指出这些庸众是被专制文化洗了脑而不自知的愚昧麻木的空壳人。李广田的另一篇散文《追随者》(第1卷第1期)中,对人云亦云、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莫望尘进行了讽刺和批判。文章中的莫望尘实际上就是李广田在《空壳》中批判过的“空壳人”,因此莫望尘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一类人。作者批判的不是一个莫忘尘,而是一类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国民。钟敬文的散文《石桥塘》(第2卷第1期)对游离于抗战的时代洪流之外,缺乏国家意识的自私麻木的富豪进行了批判。
《创作月刊》对启蒙精神的延续还表现为对民族文化中落后因素的批判与反思。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反省和自我批判才能保持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抗战时期也不例外。李广田的散文《根》(第1卷第4、5期合刊)中,就指出要坚决去掉陈旧的意识和文化,同时也指出陈旧的意识和文化盘根错节,除掉它并非易事。“有一个时候,我还曾经立志要连根拔起,但那根并不是指的这根,那是说旧的意识之类的根,那种妨碍我发扬扩大,妨碍我生得更坚硬更泼辣的根,我真愿把它掘出来,烧毁它。那么我的根也许是不只一条,大概除去一主根之外还有一须根,也许除去地下根之外还有地面上的一气根吧,自然,无论什么根,它们都是互相关联的……”茅盾《随笔二则》中的《关于“北京人”》(第1卷第4、5期合刊)论述了追求文明和进步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一些开倒车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些猿人,终于生存了下来,不但能生存,且能进化。经过慢慢的悠长的数十万年的不断求进,终于从使用粗陋的石器,然后又到了使用铜器,开放了人类史上文明之化,如果这些猿人不求上进,天天只想开倒车,那么我们今天能有这样享福?”作者指出我们的祖先“北京人”不但能生存,而且能进化。作为现代的国人更要追求文明和进步,要“不能不极力反对开倒车”。作者在文中这样写道:“可怜现在有些人却视‘进步’为仇敌,天天在开倒车,比起六七十万年以前猿人‘北京人’来真是不肖的子孙!再说猿人也有不求上进的,他们的后裔一直到现在也还过着猿人的生活……从此可知,我们现在的文明的民族的祖先,当初不但是力求上进而得有今日,也还是因为能够克服了自己的开倒车的份子,所以我们要不为六七十万年前的猿人所笑,不能不极力反对开倒车,不管这些开倒车的怎样!”
总之,作为一份文艺刊物,《创作月刊》很好地体现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对民族救亡的坚定信念和对先进文化的执着追求。它以救亡于启蒙为文化使命,其文学创作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战争本身,而是立足于现实,更多地向现实深处和民族历史文化维度掘进。这种对文学艺术价值的坚守,对现实主义的深化书写,既拓展了抗战文学的表现空间,又体现了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在一定程度上对繁荣和推动桂林文化城的抗战文艺运动以及大后方抗战文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9年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创作月刊》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文學生态研究”(项目编号:2019KY1158)成果
作 者: 杨路宏,文学硕士,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