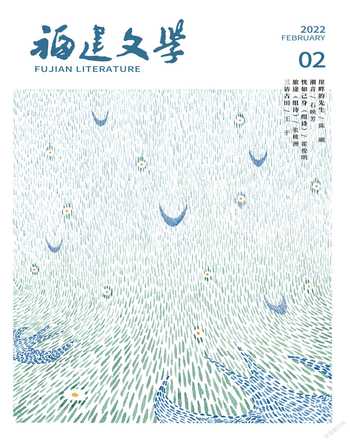读刘翠婵的散文和刘伟雄的诗
2022-02-19朱谷忠
朱谷忠
心灵眼睛的发现
——刘翠婵散文近作浅析
在福建省作家刘翠婵的散文世界里,不管她带我们去乡村还是海边行走,都有一种日常琐碎或意外的路遇,有时是“一杯茶里的风暴”,有时是一地鸡毛的暗流汹涌,有时是一种触手就可以感觉到温度的熟悉的烟火气,有时是一次身体与心灵难得的返璞归真。而更多的时候,或是一种人向自然和季节敞开但又契合的气息,或是一种与物同游、天人合一、相与言语的境界。这其中,她总是天生地从“自我”出发,去观望人生与世界,其作品往往是发自心灵眼睛的投射与发现。
评论家邱景华对刘翠婵有过精准的评介,说刘翠婵的散文,“以感觉的敏锐和想象的奇异见长,它们来自她心灵的凝视,那是用整个生命所凝聚的灵性、感觉和想象,来谛听,来体味,来包容。所以,才有独特的发现:风景不再只是自然的,而是‘第二自然’——凝聚了作者的感觉、想象和心灵,创造出一个生机盎然的艺术世界。”
事实上,过去读到刘翠婵的散文《嵛山岛:瓷器一样的时光》,就发现她的文字,尽管有着女性的深情和依恋,但又有明理达观的一面,那就是她用心灵的眼睛去发现并强调美带给人生和生命的愉悦。
原谅我的阅读错漏,以至迟迟才看到刘翠婵发表于《福建文学》2019年4月号的一组散文——这是我某次向她索要散文新作,她才寄给了我。读罢,我惊异地发现,她的心灵的眼睛,已不单是以过去的“自我”出发,更是以一种悲天悯人之心,去体察社会,感受人生。这无疑是一个女性作家在思想上完成的一次化茧成蝶。
这是一组描摹她的生活视野里的人和事的文字,有三五百字的,有一两千字的,目光所及,指向的都是那一角社会人生,以及一花一草、一虫一鸟,细小毫末、极其普通。甚至她着力描述的都是一些看似卑微的人物。但就是这一切,在刘翠婵看来,都是不可以被忽略、被小看,或视而不见的。
这组散文,比好看的小说更耐读。诸如:某渔村的堂哥因海难死去,获得的赔偿让三十岁的儿子终于有钱结婚了,吉日中最能瞧见喜气的,也许就是“山坡上那堆新垒起的静静的黄土”。再如:表舅的三只羊被偷走,几天后在别人的羊圈里找着,因为他认得羊肚子下做的记号,但人家却说他的羊也做过同样记号。老实了一辈子的表舅,心里憋屈,只好跑到天天牧羊的山坡上偷偷哭了。还有:一位在她心里唤为“真先生”的人与她交往,让她一直难以释然,原因是“先生之真,可以命相许;先生之真,词上亦毕见”。还有:曾经快速城市化导致的一些乡村空心化,致使乡间往事与人们生活現状之间出现窘迫……
在刘翠婵眼里,社会生活里发生的一切都被她记住,除了能抽绎出春天翠鸟的鸣叫,雨水滴落的声音,还有那些可以飞过高山峡谷、却飞不过花海的蝴蝶。除此,她更多的目光,或落在河边收成蔬菜的二三妇女,或落在小区风口处摆小摊卖鞋垫、卖地瓜米的乡下阿婆身上;除此,还有自己名叫木菊的祖母永难忘却的风雨的一生。甚至,市场上不绝于耳的讨价还价,都使她以自己的方式看在眼里,一一收着、捂着。最终,又以自己的方式,尽力呈现最想呈现的那一部分,并且极力去表达和发掘其间温暖的片段,发掘生活里存在的一些矛盾,发掘笔下的劳动者无论命运如何,内心却存有的金子般的光芒。
这种发现,最打动人情愫的便是她对人性切入的角度:不夸张、不丑化,以及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深切追求和深情留恋。用她的话说,自己这样写,就是想寻找并保持某种生活气息,在一种并不辽阔的视野里,保持自己所看到的一种亲切、伤感和熟悉。由此,她在文字上也极力追求简约和精到。的确,在这些作品中,她的一些描写,可以说简约得叫人不忍,但却精到得让人激赏。例如《在天堂,有时只是一个村落》中,她写到这个村子有“巨大的网,从海岸铺到半山,渔民在一张张修补,陷在渔网中的人,像小小的逗点,寒风吹过,逗点会晃”。这种写法,让人想起她在一篇《青青故乡草》中有关青草和女人的描述:“春天一回来,村子……从灰黄转为嫩绿,先是星星点点,没几天工夫,这绿就泛开了,从后院的颓墙根一直到山脚、坡地、田埕、溪畔、菜园。像是村中嫁出去好久的女儿们,择了个良辰吉日,又呼啦啦全回来了。”
而今,刘翠婵眼中的村庄街巷、山岬海边,又汇成一幅幅线条生动的素描,并点点渗出“清、静、绿、凉”的独特意境,让人身陷其中,品咂忘返。而她也以自己一向独特的方式、语言和声音来回应,尽管这样的发现和表述不可能完整,只是她的又一次对社会和人生的观察和体悟,但至少在我看来,这些作品,正是刘翠婵对于生养之地和生命本体的回馈和致意。
献给海洋永恒的爱恋
——刘伟雄组诗《山海霞浦》小析
我一直以为,21世纪以来福建诗人刘伟雄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较以往又有了显著的突破。这就是他自觉地将诗歌中的审美情感同客观物象互感同化,使描写的对象进入一个具有超越性、得以提升和醇化的境界,并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寄托在一个有温度、有意蕴的艺术形式之中,使人读之流连再三,回味不已。
组诗《山海霞浦》(发表于《芳草》月刊2021年6月号)就是这样的一组力作。初读,就像坐在海边的礁石上,感受一阵阵暖风柔浪;细读,就会看到其中含蕴的时光与生命沧桑的独特意象,并赋予作品与众不同的风景;再读,发现他总会自觉地规避那种表演式的乡愁写作,而是通过一个个特定的画面,着力去描摹自然与人生过往中奋斗的艰辛与欢欣,并写出生活的信念与生命的目的。如此,我相信读过这组诗的读者,都会有一种拨云见日般的愉悦,在心灵的澄明中获得一种历史感、时空感,其灵活的表达、凝练的语言、鲜活的内容,对诗人本身来说,都是一次较大的突破和收获。
霞浦,是闽东最古老的县份。尽管这里是一个天地万物丰富多彩的地方,但生于斯、长于斯的刘伟雄,和许多人一样,也经历过生活的磨难、岁月的淬炼。当苦难逐渐沉淀,叹息逐渐远去,他一直追求的温暖、自由、正义,像阳光一样长了翅膀,从他的心里飞到故乡的海岛、海岸、海滩,飞到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朵花和每一种海中生物,成为被着力描写的对象,也成为他献给海洋的一份永恒的爱恋。看得出,他从纯净的心性出发,寓感慨于变化和景致之中,如老家、船只、灯塔、藤壶、海浪和海滩上的族类,让读者把他眼中和记忆中的精彩全部阅览,这与新世纪之前的他的诗中关注的个体命运形成鲜明对照,显示了他的诗歌不仅拓宽了资源领地,更建立了深厚的生态情怀和乡土抱负。在他笔下,可以说对以上每个具象的描述,都饱含着深沉的意味,既有历史反思,又有丰饶的想象力,使抒情、叙事和日常生活语境的糅合,成为他诗歌写作的一种重新定位,从中显现出自然与人生和生命的高度。
无疑,了解刘伟雄生活与社会经历的人,也会从这些诗作里分享到他的一些自传性叙事,分享到他对祖辈亲人和生活过的场所的关注,这种深挚的乡情、亲情和人文关怀,正是诗人的拣选与辨认,同样具有充分的社会意义和不可或缺的历史感。
因而我认为,刘伟雄的这一组诗,词简意丰、凝练深沉、自然淡定,如轻轻的海浪流进我们的情感堤岸,他不但让人看到曾经的那片茶园,“还有祖母驱赶雀儿的身影/ 她招呼鸡鸭猫狗回笼的那个黄昏 /连她飘在风中的银发都成了/ 我在这个世界发呆的理由”;原来,这是“在春天的故乡西洋岛上/ 豌豆花蚕豆花油菜花 /织就了献给海洋的花环/为这一份永恒的爱恋”。而理解物性,与物会通,也是这组诗的一个特色。我们看到,诗人主要是以一个“听者”而不是“言说者”身份倾听万物的心声。由此,在《海滩》这首诗里,“没有船只的海滩/也是海滩/那个少年斜着肩头站在海边/
他要穷尽自己的目光/把海望穿的姿势/真是叫人感动……直到一抹夕阳镀黄少年的脸/苍老的苔藓爬过他的手臂/一尊雕像是以他的形象/站在海滩上/站成了我们的今天。”再如《一个废弃的古村落》:“一个海岛的最早胚胎/笨拙的藤壶伸出柔软的须角/似乎要摸透空气的脾性/
也要弄懂春天来临的意义。”当然,在诗人的故乡,我们还会看到《奔跑的乡村》《唱歌的海葵》,看到《马刺岛的夜》,“岛上无人的时刻/
只有招潮蟹静静地走着……野生的紫菜在月夜的水里/女妖的裙裾一般舞过海滩/红月亮在远海把波光/摊成细细的绸纱……”这一切,并不是诗人在说梦话,而是通过这些看似不动声色的描绘,对天地自然万物保持着一种敬畏之心。
总之,读刘伟雄这组诗,常常被诗中心物合一的意象和深远的内蕴而打动。这些年,我能浏览到的一些诗歌,虽不乏探索创新之作,但仍感觉随意和散漫以及碎片化倾向依然积重难返。我想,这是否需要从观念和细节上实现突破——特别是进行有思想、文化、智慧的深度探索?因而,我个人认为,刘伟雄的这一组诗,也许可以为轻易贴上“乡愁”标签的诗歌创作,在避免模式化和类型化写作方面提供一个有益的经验?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