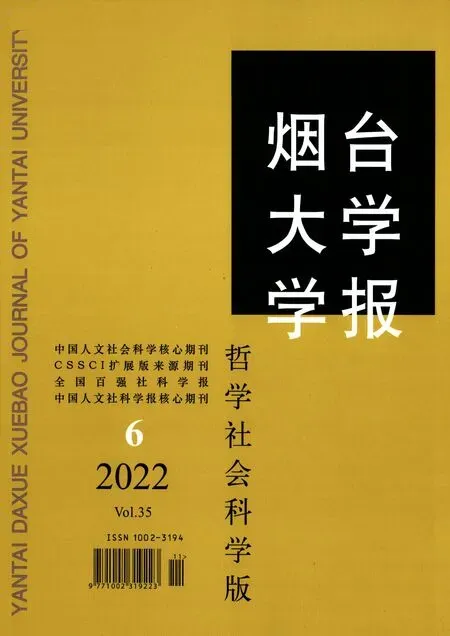论韩国古代诗话的东亚视角与比较批评意识
2022-02-15朴哲希
朴哲希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韩国古代诗话既是民族文化心态和审美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是朝鲜半岛古代汉文学重要的批评样式。事实上,统一新罗时期崔致远(857—?)文集中的部分记述便已颇具诗话形态。在高丽朝初期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历史文化典籍中,也有不少关于文学批评的论述。一方面,这些作品所包含的文人传记及文学史实为后世诗话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材料;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的叙事实践为诗话文体的正式出现奠定了基础。直到高丽朝中后期,随着中国宋代《六一诗话》等诗学典籍的传入,最终触发韩国诗话文体观念的形成,开启了诗论家崭新的审美鉴赏表达方式。
比照来看,虽然韩国诗话与中国诗话有着很强的共通性,但不同的文化心理及叙述视角使韩国诗话具有了不同于中国诗话的鲜明特色:重记事且记事具有史实性;诗歌批评坚守儒家风范,带有儒家正统的功利观念。(1)马金科:《论韩国诗话的史传叙事传统观念及其特殊性》,《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3期。同时,在研读和借鉴中国文学的过程中,韩国古代诗话创作者以中国诗人诗作为参照,逐渐从普泛的文学比较实践及对外交流中梳理出了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批评样式与形态,因而其叙事也具有比较东亚诸区域文学的广阔视野。
放眼当下的韩国诗话研究,国内外学者对诗话起源、时代特征、《东人诗话》等代表性诗话、与中国诗学及儒释道思想之关联、民族主体意识等方面有着系统深入的阐述,研究的焦点侧重于韩国古代诗学本体研究层面及中韩诗话渊源关系的考证,缺乏将东亚作为整体的研究视野和跨文化观照,较少涉及对韩国诗话特殊性的考察,特别是对诗话中所蕴藏的东亚视角与比较批评意识欠缺深层次的阐释。因此,有必要从韩国诗话的书写特色及其演变出发,探寻诗话作者的身份与写作意图。这不仅有助于回顾东亚区域内文学交流的厚重历史,也可以辨识在中国文学辐射之下中韩诗话书写内容、视域的差异,进而实现对于东亚文学整体性和互补性的深刻剖析。
一、韩国诗话书写时的东亚视角
韩国诗话中有很多关于东亚区域及其文化的描写,为今人研究东亚各政权关系以及不同时代的文学风貌提供了有别于官方典籍记述的崭新视角。
关于对日本的诗话记载,最早见于崔滋(1188—1260)的《补闲集》,内容为日本人求取佛教典籍师碑志(《大觉国师碑》)的逸事。关于对安南的诗话记载,则最早见于金正国(1485—1541)的《思斋摭言》,其摘录安南使臣题通州潞河驿门楼壁诗以及使臣阮琳南珍诗,并评价这三首七言诗“体格稍卑弱,然音律铿锵,殊类我国之作,可想其风流文雅”。(2)金正国:《思斋摭言》,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438页。关于对琉球诗话的记载,始见于曹伸(1454—1528)的《謏闻琐录》,其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朝鲜半岛与琉球的距离、琉球的人文和自然面貌等内容。由此可见,虽同处“汉字文化圈”时空,但韩国诗话中形成了不同于中国诗话的特殊样态,即以中韩比较为主,同时兼论其他区域的东亚视野,呈现出一种开放的东亚文学批评精神。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韩国诗话作者对东亚各区域的叙述态度、叙述篇幅有所不同,观察与记录“他者”的目的也自然迥异。总体上看,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高丽朝中后期到朝鲜朝初期(大约为公元13—15世纪)。这一时期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作者通过诗话主要记录一些东亚各区域的见闻、风俗、地理、服饰、诗文等内容。从这些文本的内容上看,多是描述性的汇编,部分内容叙述得相对简略和笼统,具有代表性的诗话作者如《稗官杂记》的作者鱼叔权(朝鲜朝中宗至宣祖时人)。因其有着作为使臣出使的体验和经历,故而在诗话中多记赴燕京见闻以及与中国使节的酬唱诗。又如曹伸(字叔奋,号适庵),其以译官的身份七赴燕京,三渡日本,曾与安南使臣酬唱数十篇。他不仅与日本、安南、琉球等地使臣汇聚于北京,与使臣、文人一道赋诗唱和,同时通过交谈也令使臣之间知晓其他区域的真实情况,充分满足了彼此的好奇心理,展现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文人在异域他乡相见后内心的亲切感和归属感。
黎诗一首云:“三韩见说景偏殊,鸭绿澄澄水色秋。知是江山诗思好,还将句法效苏州(韦应物)。”适庵次云:“嗜鱼熊掌味何殊,我爱君诗淡似秋。温李只要夸富艳,平平端合学苏州。”黎以押苏州字犯唱韵,非和诗体,赠书讥之,又赠一首曰:“马辰遗俗古人殊,世代相移几度秋。耨萨名官何意义,知君礼制异中州。”适庵以书答之,略曰:“……耨萨本是方言,古之云鸟,名官何义哉?交趾岂骈拇之义耶?”黎复书略曰:“……交趾本一郡也。郡之北有南交阙、天址山,故名郡以交址,后误以址为趾,无怪乎君之承讹也。”(3)鱼叔权:《稗官杂记》,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第785页。
由这段文字可知,曹伸与安南使臣黎时举虽然初次见面且语言不通,但显然二人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于是采用笔谈的形式展开汉诗交流,就学诗的倾向、诗中的方言与地名进行深入讨论,以文交友。从地理上看,两人所在的区域距离遥远,往来稀少且不便。然而,两位使臣却在北京相遇了。二人通过此次笔谈,大大增加了对彼此区域语言文化、风土人情的认知。既深化了二人对汉字文化圈内共有文化身份与中华文化的认同,也为后世使臣的继续交往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是朝鲜朝中期(大约为公元16—17世纪)。该时期,从诗话中可见各区域文人间的友谊不断加深。如万历二十五年(1597),李睟光前往北京参加万历皇帝的万寿节。进京后,在朝会中遇见了同来贺寿的安南使臣冯克宽。两人遂往复累度赠诗,分别馈赠对方七言律诗八首,五言排律一首,合计十八首。在两人的诗文唱和中,李睟光写到“今中国逢神圣”,介绍了二人相识的原因,即因共赴祝寿而结缘。同时,他也总结到两国虽“休道衣冠殊制度”,但“却将文字共诗书”。而冯克宽在诗中也表示朝鲜与安南虽地域不同,但“异域同归礼义乡”,强调两地文化“同出一源”,即“彼此虽隔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4)张伯伟、卞东波:《风月同天:中国与东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页。显而易见,他们在学问的渊源上均来自于中国古代圣贤著作,皆信奉礼、义、信、德等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可以说,都接受着同一意义体系,(5)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61页。秉持着相同或相近的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因此,李冯二人在交往中,不仅没有丝毫陌生感、隔阂感,反而深感亲近并找到了深度共鸣和共情。
第三阶段为朝鲜朝后期(大约为公元18—19世纪初期)。本时期,透过诗话可知文学交流更加频繁,东亚诸区域的互动往来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频率上都在历史上鲜有。自以清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形成后,在此后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区域间一直维持着和平的局面。同时,这一时期汉诗繁盛,作品丰富,也恰好迎来了东亚汉文学的鼎盛时期。(6)蔡美花:《中国古典文化是东亚文明走向未来的基石》,《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13日,第3版。18世纪,尹行恁(1762—1801)的诗话《方是闲辑》便为研究东亚文人间的往来提供了一个绝好例证。
我使右议政俞公彦镐诗云:“御苑云常五色新,中开黄幄倍氲氤。香烟暖合三元气,瑞雪晴回万国春。从古东藩承雨露,只今北极拱星辰。频叨法宴皇恩重,余颂椒花愿更陈。”副价户曹参判赵公环诗云:“上元佳节属河清,火树银花贲太平。环海车书昭代化,朝天玉帛小邦诚。恭瞻北阙绵红箓,欣祝南星耀寿觥。携得御香长满袖,东箕万世颂恩荣。”琉球国阮延宝诗云:“弹丸海岛细微臣,元夜随班沐帝仁。玉殿传柑颁御宴,金门桂彩赏王春。绕林烟火辉天上,满砌歌声奏紫宸。瞻仰龙颜惟咫尺,浑身偏洽圣恩新。”其二曰:“上元御苑扬华筵,玉辂龙旗出日边。扈驾王公盈殿下,献芹远价侍阶前。灯联火树银花灿,歌舞霓裳彩色鲜。中外臣僚承宠异,升平共祝万斯年。”(7)尹行恁:《方是闲辑》,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6册,第4915-4916页。
根据材料可见,这则诗话记载了乾隆五十三年春季时,使臣们汇聚于圆明园互相对诗的盛大场面以及当时清朝的盛世气象。尹行恁通过对这一历史场景的生动描述,不仅复刻了这场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还原了当时东亚各区域交往交流的真实情景,也加深了韩国诗话的读者对海外诗歌创作的认识。除了记载彼此互赠的诗歌外,本时期的朝鲜朝文人,或整理前人的唱酬诗,或总结其他区域汉诗的演变历程。如李德懋在《清脾录》中概括了日本、安南等地汉诗的发展史,写作了《芝峰诗播远国》《日本兰亭集》《倭诗之始》《蜻蛉国诗选》等单则诗话;李圭景在《诗论家点灯》中也有《安南国使诗》《安南祥光记闲忙令》《安南使应制团扇诗》《安南陪臣潘武诗》《琉球国诗》等记录。从上述诗话中可知,诗论家的批评对象不再局限于中朝,而是包括了整个东亚地区。而且从诗话主题看,已接近于具体翔实的区域文学研究。这些论诗记事的文本是东亚文学互动的积极尝试与相互照应,构成了韩国诗话的空间范围,拓展了诗史视野和格局,补充了域外汉诗文献,充分展现出韩国诗话较为宏大的观察视域。
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时期韩国古代文人的思维观念与文化心态由传统的“天下一体观”逐步向“民族国家观”过渡,自我与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特别是朝鲜朝末期(19世纪中后期至1910年),东亚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格局发生巨大改变。面对清朝的衰落与日本的渐趋强大,韩国古代文人群体对东亚各区域的情感和态度产生了根本性转变。其渐渐破除华夷观念,去中国中心化,将东亚各区域的文学放置于相同、平等的位置并进行点评。然而朝鲜朝灭亡后,文人很少写作汉诗、诗话,能论及东亚诗歌者越来越少,以写作诗话的形式反映东亚文学交流的情况便趋于消亡了。
二、韩国诗话蕴藏的比较批评意识
在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之下,韩国诗话形成了对比式、影响—接受式的批评形态,并且旨在通过比较,建设、完善并确认其自身的文化。从中体现出一种区域整体意识,而不仅仅是封闭孤立的本国中心观。如从首部诗话《破闲集》的书写中可以看到,李仁老(1152—1220)开篇有言:“读惠弘《冷斋夜话》,十七八皆其作也。清婉有出尘之想,恨不得见本集。”(8)李仁老:《破闲集》,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第4页。其在论诗谈艺中明确地表露出对中国诗话典籍的期待,渴望进行比较的意识业已萌发。具体来说,韩国诗话作者一则不断搜集本地文人对中国诗歌的仿写与补诗,并试图比较、辨析中韩诗作的不同及高下;二则对中国诗体、创作方法进行介绍和点评,并在此过程中加以学习和效仿;三则以中国诗句为依据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增强说服力。总的来看,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学、诗作的内容与主旨基本不出这一范畴。
这可从东亚古代特殊的宗藩制度、地缘关系以及华夷观念等因素中找到答案。如朝鲜朝中期时,文人洪万宗在其诗话《小华诗评》中曾记录下一则柳根、许筠与明使朱之藩之间的对话。“太史(朱之藩)问曰:‘道上馆驿壁板,何无贵国人作乎?’筠曰:‘诏使所经,不敢以陋诗尘览,故例去之。’太史笑曰:‘国虽分华夷,诗岂有内外?况今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俺与君俱落地为天子臣庶,讵可以生于中国自夸乎?’”(9)洪万宗:《小华诗评》,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3册,第2321页。可见,在中韩文人的心目中,两地虽有华夷之别,但汉诗却不分内外。实际上也是如此,古代之东亚实为以中华文化为统摄的文化共同体,彼此之间虽口语表达不同,但却有着共通的文化语境,可以用汉字来进行交流。相同的文字,使得他们深深感受到两地在思想来源及文化属性上具有同一性和相近性,也深深体会到对于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强烈认同感,凝聚起东亚的整体意识,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兄弟般的情谊。而这种共同体意识也正是东亚文人进行文学互动的普遍心理,保障了文学交流的良性循环。
在以封贡关系为背景的传统的中华体系中,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周围区域纳贡朝觐,从中心到边缘一体的世界观、文化观和东亚共同体意识。故而在品评东亚各区域诗文时,韩国古代诗话的创作群体并未因域外文人、域外作品而弃之不录。特别是论中国诗人诗作时,他们在表现出对中国文学强烈认同感的同时,常带有羡慕追随的态度,流露出以中国为中心、朝鲜半岛处于边缘的文化心态。在比较的视域下,自觉呈现出倾慕与崇敬的姿态,在发展本地文学时积极接受中国诗学的思想风潮、审美倾向,在中国诗歌、诗论的对照下主动学诗。
由前文可知,无论是高丽朝还是朝鲜朝,无论是诗话产生的初期还是末期,这种比较批评的意识一直根植于韩国诗话发展的血液当中,成为其有别于中国诗话的重要特征,同时这也正是东亚诗学具有整体性的有力证明。所以,韩国诗话作者在品评各区域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时,没有刻意区分、区别对待,而是把中国文学当作其自身的学习背景予以参照,十分自然地加以叙述和评论,如同讨论本地文学一般。在其所阐释的话语、立场、视角与态度当中充满着比较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已经具有了比较文学的性质。
诗论家作诗多使事,谓之“点鬼簿”。李商隐用事险僻,号“西昆体”。此皆文章一病。近者苏黄崛起,虽追尚其法,而造语益工,了无斧凿之痕,可谓青于蓝矣。如东坡“见说骑鲸游汗漫,忆曾扪虱话悲辛”“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尔远来情”,句法如造化生成,读之者莫知用何事。山谷云“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只此君”“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类多如此。吾友耆之亦得其妙,如“岁月屡惊羊胛熟,风骚重会鹤天寒”“腹中早识精神满,胸次都无鄙吝生”,皆播在人口,真不愧于古人。(10)李仁老:《破闲集》,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第29-30页。
这则诗话的书写表现出李仁老没有排外意识,视中韩文学为一体的潜在心理。他在讨论用事时,既将用事放入中国诗歌发展史中进行纵向考察,分析用事在中国唐宋时期的发展演变;又将用事放入本地视域内进行横向考量,阐述用事在高丽朝的接受。他分别提及、摘录了苏轼的《题〈和王斿二首〉其一》《题〈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其二》,黄庭坚的《次韵〈外舅谢师厚喜王正仲三文奉诏祷南岳回至襄阳舍驿马就舟见过三首〉其三》和《漫书呈仲谋》等多首诗歌作品。根据其文字表述,一方面能够直接感受到诗论家就诗言诗,不分畛域,把中韩文学当作整体的书写心态;一方面也可知,中国诗歌、诗论作为东亚诗学的本源,传入域外后,在域外诗学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李仁老在《破闲集》中,采用摘句、比较等形式记录下很多如“苏黄”等中国诗人之作品,而这则材料仅仅是韩国诗话接受中国诗话影响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在136种韩国诗话中,(11)赵季:《136种朝鲜诗话与中国典籍之关系》,《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2012年辑刊。有着大量关于中韩诗歌比较乃至中韩日诗歌比较的记录。这些诗歌比较的文字展现出韩国古代文人对中国、日本等地文学鉴赏、批评与接受的过程。从中可见,受中国诗歌、诗学的长期沾溉与滋养,文人群体逐渐形成了比较的思维和意识,并作用于诗话的写作当中,令韩国诗话作品带有鲜明的比较文学中接受、影响的性质。
三、韩国诗话作者的身份与写作立场
东亚各区域诗学的发展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在中国诗学的影响下,经过长期的互补、并进、互鉴,进而不断交融,构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独特的东方文学理论体系。(12)马金科:《从诗话批评样式看东亚文人的共同情怀》,《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13日,第5版。诗话作为东亚诗学共同的批评方式自然深度契合东亚诗学的发展历程,但中韩日等区域的诗话又各具特色、和而不同。就韩国诗话而言,由前文可知,诗话作者在分析比较中国、日本、安南、琉球等汉诗时态度各异,使韩国诗话在书写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东亚视角与比较批评的意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我们可从诗话的创作者入手寻找成因。一方面,诗话作者写作时对自身作为中华文化的学习者和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二重身份以及论述的目的是有着清晰的认识定位的;另一方面,在众多诗话创作者的共同努力下,韩国诗话极具内在民族性与外在开放性有机结合的生命力。
从百余位诗话作者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环境上看,他们大多出身贵族,从小耳濡目染接受汉文学教育。从职业构成上看,他们既有很多执掌文衡者、一代名臣,也有不少多次接待或作为使臣出使过中国、日本者。从学缘背景上看,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到过中国,还拜访名士、大儒,并师从中国文人。所以,诗话的作者不仅眼界开阔、见多识广,汉文学积淀也十分深厚。其特有的跨文化交流经历以及掌握中韩乃至中韩日多重文化的背景,使得韩国诗话的书写呈现出东亚视角与比较批评意识。在品鉴东亚不同区域文学时,态度也截然不同,进而显现出其对自身不同的定位。
其一,作为“学诗者”的立场。高丽朝时,崔滋(1188—1260)在《补闲集》中首次提出“学诗者”一词,意味着韩国诗话作者对自身身份有着清醒认识,即自认为是中华文化的学习者,故对中华文化始终要以“学”为主。从学诗的范围上看,不仅学中国诗作,也学本地诗作。
朝鲜朝初期,徐居正(1420—1488)继续沿用“学诗者”一词,他说道:“予尝读李相国长篇,豪健峻壮,凌厉振踔,如以赤手搏乕豹挐龙蛇,可怪可愕,然有麄猛处。牧隐长篇变化阖辟,纵横古今,如江汉滔滔,波澜自阔,奇怪毕呈,然喜用俗语。学诗者,学牧隐不得,其失也流于鄙野;学相国不得,其失也如捕风系影无着落处。近世学诗者例喜法二李,不学唐宋。古人云:‘作法于涼,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何救!’”(13)徐居正:《东人诗话》,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第225-226页。其言旨在纠正学诗者在学诗过程中出现的诗病以及不正之风,并试图及时加以解决。从中可见,徐居正作为域外文人与中国文人相比,在接受中国诗学时具有“主体间性”的差别,即其学习中国诗学是以发展本区域诗学为根本目的。因此,其在诗话的书写过程中自然展现出有异于中国文人群体的特殊关注点。
实际上,关于“学诗者”一词的起源,尹春年(1514—1567)在《体意声三字注解》中的《诗法源流序》中,其偶见严沧浪之论曰:“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路头一差,愈骛愈远。”(14)尹春年:《体意声三字注解》,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第518页。李睟光(1563—1628)在《芝峰类说·诗法》也说道,严沧浪“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又曰:“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鹜愈远” 。(15)李睟光:《芝峰类说》,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第1051-1052页。以此为初学者之法。由此可见,该词最初来自于中国诗学典籍《沧浪诗话》。但该作品在传入朝鲜半岛之后,文人结合自身的接受特点和身份在对“学诗者”一词的认识上又带有了新的变化。概言之,韩国诗话的作者认为学习中国文人的诗作,既要远承中国诗学的传统和思维逻辑,又意在总结经验以指导本地文人学诗。
在学诗者的视域下,韩国文人的叙述对象通常有两个甚至是多个。他们将中韩文学置于同一空间进行讨论,或对比、品评两地诗歌,或解说诗道诗法,或指出学诗的病症并引以为戒,或关注诗风的演变,或阐明诗论家所爱且树立之典范等等,为后世文人写作汉诗提出了原则性意见。诗话创作者广阔的观察视域以及深厚的中韩文学修养,体现出中韩文学乃至东亚文学间的深度交融。相比之下,中国诗话更多关注的是诗歌审美价值、个人风格等内容。(16)马金科:《试论朝鲜诗话话语中的“学诗者”接受视角》,《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金兰丛石亭,山人慧素作记,文烈公戏之曰:“此师欲作律诗耶?”星山公馆有一使客留题十韵,辞繁意曲。郭东珣见之曰:“此记也,非诗也。”非特诗与文各异,于一诗文中亦各有体。古人云:“学诗者,对律句体子美,乐章体太白,古诗体韩苏。若文辞,则各体皆备于韩文,熟读深思,可得其体。”虽然李杜古不下韩苏,而所云如此者,欲使后进泛学诸家体耳。(17)崔滋:《补闲集》,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第81页。
予尝爱晚翠亭赵先生须《咏松》诗:“日斜云影移高阁,风动潮声在半冈。”(18)赵须(朝鲜朝世宗时人)字亨父,号松月堂、晚翠亭,籍贯平壤。太宗元年(1401)文科及第。任兵曹正郎,九年为内赡寺少尹,因细事罢免。《东文选》卷五载其五古一首。后得宋僧《咏老松》诗:“云影乱铺地,涛声寒在空。”赵诗岂祖宋僧乎?赵先生尝咏秋获诗,有“磨镰似新月”之句,语予曰:“韩退之诗云‘新月似磨镰’,吾用此语而反其意,此谓翻案法。”学诗者不可不知。(19)徐居正:《东人诗话》,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第226页。
这两则诗话明显表现出韩国诗人的学诗者属性,所论之旨与其创作紧密相联。第一则诗话为崔滋围绕高丽朝文人的文体之病而展开,并为学诗者指明学习律句、乐章、古体及文辞之典范,引导文人如何入门。第二则诗话徐居正则从赵须诗与宋僧诗、韩愈诗的渊源关系出发,将诗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此为实例,向文人介绍何为翻案法。在崔滋、徐居正等文坛权威的影响之下,诗话创作者在书写时形成了从学诗者的视域出发,在中韩诗学、诗作的比较分析中学习具体实用方法的批评思维。后世南孝温(1454—1492)、李植(1584—1647)、金万重(1637—1692)、洪万宗(1643—1725)、李瀷(1681—1763)、李圭景(1788—?)、李家源(1917—2000)等各代诗坛大家在诗话的行文中皆有此意识,以是否有中华之风作为最高的评判标准之一,从而使得韩国诗话别具特色。
其二,作为中华文化继承和“传播者”的立场。在东亚交流与互鉴的历史文化语境下,韩国古代文人在接受中国文学与文化后,拥有了较高的中华文化水平。因此,在与日本、安南、琉球等地的互动中,身份与立场亦随之发生了转变,在“学诗者”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身份与定位,即其认为相较于其他区域而言,已经继承了正统的中华文化且深谙汉诗创作之道,在汉字文化圈中也具有了话语权。这一转变,一方面使得朝鲜半岛在东亚文学交流中发挥着“中介”和“桥梁”的功能,对促进东亚文学的繁荣和生成东亚文学共同的规律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助于推动各区域文学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韩国古代文学理念在对外交流中得以反思,完善其自身文学批评体系的建构。
清高宗时,安南国阮光平攻逐其君黎维祈,赂乾隆宠臣请封为王,仍入朝。其臣吏部尚书潘辉益、工部尚书灏泽侯、武辉瑨二人从之。庚子,我使适入,亲见潘辉益等赠我使诗。而辉益诗:“居邦分界海东南,共向明堂远驾骖。文献夙征吾道在,柔怀全仰帝恩覃。同风千古衣冠制,奇遇连朝指掌谈。骚雅拟追冯李旧,交情胜似饮醇甘。”武辉瑨诗:“海之南与海之东,封域虽殊道脉通。王会初来文献并,皇庄此到觐瞻同。衣冠适有从今制,缟纻宁无续古风。伊昔使华谁以我,连朝谈笑燕筵中。”二诗声律未畅,堪与日本相上下……(20)李圭景:《诗家点灯》,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8册,第6582页。
嘉靖乙未,琉球国王差臣谢恩,其奏本曰:“琉球国中山王尚清,谨题为谢劳事。伏念,臣僻居海邦,荷蒙圣恩,封臣为中山王,不胜感戴。除具表谢恩外,今有差来使臣二员,正使吏科给事中陈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冒六月之炎暑,冲万里之波涛,艰险惊惶,莫劳于此。小国荒野,无以为礼,薄具黄金四十两,奉将谢意,此敬主及使乃分之宜;酬德报功,亦理之常。二使惧圣明在上,坚不敢受。微臣情不能尽,无以自安。谨令陪臣顺赍贡奉,伏乞天语丁宁,赐被二使,庶下情尽而远敬伸,无任感激之至。”……余读琉球此奏,词意多疵,殆不成章,文献之不逮本国远矣。(21)鱼叔权:《稗官杂记》,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第747页。
以上两则诗话说明,韩国古代文人对日本、安南、琉球三地的用语及立场,其叙述态度与品评中国文人作品时崇拜、钦慕的姿态有着天壤之别。诗话的作者将安南、琉球的汉诗放入东亚视域内与朝鲜半岛、日本等区域诗歌进行横向关联批评。其认为安南使臣的诗声律未畅,与日本是同一层次,而琉球之文章,词意多疵,殆不成章。言外之意,这些诗歌创作能力与水平都远远不及朝鲜朝。换言之,诗话作者认为日本、安南、琉球三地的文学都是需要得到关照与扶助的。这说明韩国文人对他们所学到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准确度及掌握度十分自信,甚至觉得其已经传承了正宗的中华文化,身份业已具有了“权威性”。所以,在韩国古代文人心中一直以“小华”自居,诗话也以“小华”命名(如《小华诗评》等),与安南、日本等地相比自然是十分自豪和骄傲的。而这种“泛中华”观念形成的根本原因便是受华夷观之影响。正如张伯伟先生所言,“以国土面积而言,日本大于朝鲜半岛,但在朝鲜半岛15世纪以下所绘的地图中,其版图是大于日本的。从韩国古代文人的认知开始,‘大’‘小’就不是客观的事实,而是与文化的‘高’‘低’成正比的。故而韩国文人把日本比小国而自比大国,称中国为大国、上国,便是出于这种心理。”(22)张伯伟:《东亚汉文学研究方法》,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01页。
因此,在朝鲜半岛文学理论、汉诗创作高度繁荣的背景下,诗论家在写作诗话时自然在心态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小华”意识下,其评论东亚各区域文学的立场也随之转变。面对中国以外的文人时,他们的身份已不再是“学诗者”,而是中华文化的“代言人”及传播者。即日本、安南、琉球的文人都需要向其学习,需要其帮助与支援。带有朝鲜半岛文学得中国文学之“真传”,以及其强于日本等其他地域的潜在意味和文化自信。
四、结 语
韩国诗话的兴盛得益于诗话创作者对中国诗话的学习借鉴以及东亚之间文化的交流互动。韩国诗话虽然在结构形态、文学理念及审美追求等多方面,与中国诗话具有与生俱来的亲缘纽结,证明了古代中韩“文学共同体”乃至东亚“审美共同体”是存在的,东亚文学具有“共同价值”。但是,在对中国、日本、安南、琉球等东亚各地域文学与文化进行观照与叙述时,韩国诗话的创作群体所建基的观念一直是其本民族的文化立场,通过采用选本、论诗诗以及摘句等多样化的方法,对“他者”文化进行审视、吸收和借鉴。其观点与言论始终是从本地实际出发,考量并比较本地语言、文化、审美意识、文学作品等与其他区域之不同。且在批评的过程中坚持自主性,力图使其对东亚各区域的批评更加全面、客观,对东亚文学有补益之功、补史之效。在东亚文学交流与互鉴的历史语境之下,亦具有比较文学的意义。
同时,由韩国诗话的创作交流可见,汉字作为文化圈内不同语言民族交流的工具,使得跨文化交际成为可能。朝鲜半岛、日本、安南等域外地区都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彼此有着深层次的精神共鸣,是文学同源、制度近似、思想相仿的中华文化共同体。这既保证了东亚文学的交流与互动能够得以有效展开;也使得韩国诗话的书写能够不分畛域,对中国、日本、安南、琉球等地的汉诗均能进行批评比较,展现出韩国诗话的地域特色与本土诗性的眼光。
总之,韩国古代诗话中关于东亚文学交流与批评的书写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特点,既体现出韩国诗话在东亚文学中的独特之处,也为当下东亚友好交往提供了历史依据及可资借鉴的交往路径。通过诗话还原东亚古代文学交流的历史场域,激活历史记忆,不仅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挖掘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真实案例,也有助于重估东亚文学的重要价值,从而为当下探讨东亚文学如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如何走向世界并树立东亚文学的整体形象提供了新的思考。同时,我们也冀望基于古代东亚诗话的研究推向深入,直至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