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狄更斯小说的叙事艺术
2022-02-13杨洪侠
杨洪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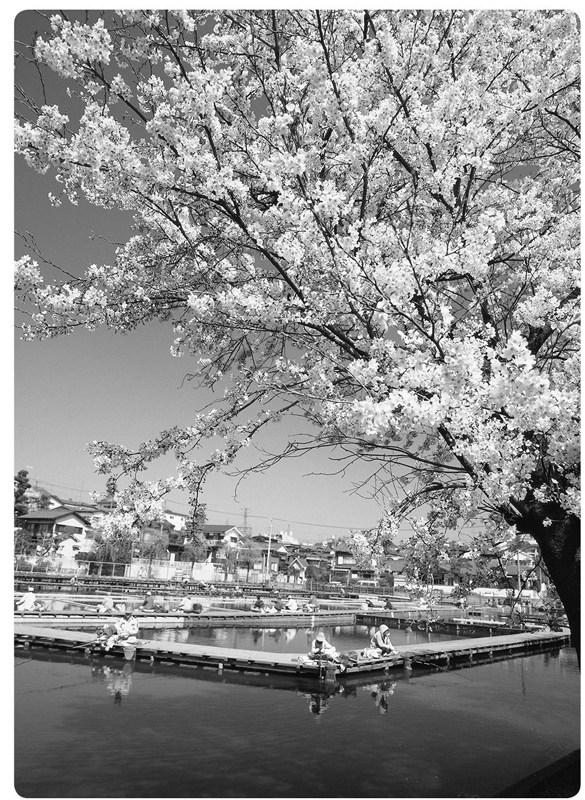
狄更斯以现实主义的写作实现了小说的经典化建构,而其小说的叙事艺术却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技法的阈限,呈现出了现代主义的叙事特质。狄更斯以复杂的叙事视角与隐喻性的叙事空间织构小说情节,以轻松幽默的叙事艺术讲述故事,使小说在现实性意义之外更兼具叙事学价值。
一、复合交叠的叙事视角
狄更斯小说中的叙事视角向来呈现出非单一化的特质,他有意规避维多利亚时期传统小说叙事中固定的全知性叙事视角,转而以复合交叠的多重叙事视角充盈文本层次,以视角的切换抵达不同的叙事效果。叙事视角的转换隐含着创作主体隐秘的叙事意图,使叙事视角在叙事意义之外更兼有表达小说主旨的内容意义。
狄更斯擅于把握内聚焦视角与外聚焦视角的叠加,以内聚焦的视角敞开人物的内在世界,使其情感变动与思想流动引起读者的自我代入,同时以外聚焦的视角讲述小说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陈列小说中复杂的人物关系,使小说的情节推动顺畅而无阻滞。例如,在《荒凉山庄》中,狄更斯以外聚焦的全知视角铺陈了小说的背景,讲述了法庭审理的财产争夺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富豪贾迪斯财产的归属所牵涉的各方利益,使读者在全知视角的讲述下逐渐厘清情节发展线索的同时获得了居高临下的视野,洞悉了上流社会绅士富人们的伪善与贪婪,以及金钱对人性的侵蚀力量。同时,狄更斯也不时地在小说中穿插以埃斯特·萨摩森为叙事者的内聚焦限知视角,以人物的限知叙述遮蔽情节发展中的关键信息,如埃斯特·萨摩森的身世背景、突然销声匿迹的乔及克鲁克遗留下的秘密等。限知性的叙述在文本中制造了迭起的悬念,使平白的情节叙述横生波澜,极大地吸引了读者阅读注意力的集中。与此同时,内外视角的切换也有利于展示事物的不同侧面,揭示不同叙事视角下事物的多义性。例如,在《荒凉山庄》中,外聚焦的全知叙述者将戴德洛克男爵夫人描述成“冷酷得像是尊冰雕,总是摆弄着那副高傲的下颌”的女人;然而在内聚焦限知叙述者埃斯特·萨摩森的叙述中,戴德洛克男爵夫人却是为了丈夫和女儿独自背负着往日的秘密的家庭守护者。她虽然有着冷漠傲慢的表象,在内心深处却对家人怀有温柔而深切的爱意。她并不是平面化的人物符号,而是血肉丰满的立体人物。不同叙事视角下的讲述揭示了人物的多元化侧面,使平面化的人物形象被形塑得生动而立体,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单面化的人物塑造传统。
而《远大前程》中,狄更斯则将同一个人物在不同时期的视角进行叠加,“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的叙事视角的交替揭示了人物的成长轨迹,颇具道德教化的意味。小说以“叙述自我”即老年皮普的回顾视角引入开篇,旋即切换至“经验自我”即少年皮普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其年少时的经历,缩短读者的心理距离,使其在接受的过程中自觉地代入少年皮普的主体经历,与之共同体味生活的百味多姿。双重叙事视角的叠加不仅使小说具有多声部叙事的意味,还让读者在人物“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互照间体验到时光的流逝。幼年皮普视角下的叙述充满激烈的情感流变,带有儿童视角特有的天真与单纯。他在教父的帮扶下从贫困的、遭人冷眼的铁匠学徒变成富裕的、令人艳羡的绅士,然而他深知这种身份的置换犹如绚丽的泡沫,美丽却有着随时碎裂的危险;而成年皮普视角下的叙述则理性而冷静,他已经从一夜之间改头换面的“黄粱美梦”中苏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贪求虚荣所带来的不幸后果。尽管他的确因为金钱获得过短暂的满足,然而最终还是全部失去了,曾让他梦寐以求的艾斯黛拉失去了往日的美丽光辉,他所期盼的“远大前程”也走向了幻灭。“敘述自我”视角下的讲述形成了对“经验自我”视角下的经历的反观与审视,以老年皮普视角对少年皮普作出的论断和阐释充满道德教化的意味,揭示了真正的“远大前程”应当以切实的劳动和进取获得的道理,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面向自我进行审视与内察。同时,不同时空叙事视角的叠加无形间也延展了文本叙事时空的纵深,穿梭于现在与过去的叙事视角令小说具有了时移世易的沧桑美感。
叙事视角的复合叠加产生了迥异的叙事效果,狄更斯着意在不同的文本中采用不同的叙事策略,使其小说因视角组合的多元而折射出不同的风格。且作家对叙事视角的娴熟操纵也使小说情节的织构更为精妙,作家可以有选择性地敞开与遮蔽信息,从而控制读者产生怎样的阅读反应,抵达其预想中的叙事目的。
二、寓意深刻的叙事空间
狄更斯的小说叙事具有浓厚的空间意识,他小说中的叙事空间不仅具有地理坐标与故事背景的意义,还具有浓厚的隐喻意义。空间场景的静态描写喻示着情节的后续发展与人物的命运走向,不同场景的动态切换则构成着小说发展的线索,叙事空间不再具有单维度的表层之意,而是成为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
狄更斯的静态空间中常密集地散布着寓意丰厚的布景,叙事空间中出现的景物往往同小说的深层意蕴有着隐秘的关联,具有浓郁的修辞意义,如《荒凉山庄》的起始篇章中对伦敦街道空间的描述,“拥挤的人群趟过满街的泥泞与飞灰,他们咒骂着不断尝试着四处奔突却无从脱身,只能举着拖沓的脚步前进,浓得化不开的雾将远处的行人包裹成一个混沌的轮廓”。叙事空间中的场景传递着大量的主题意图,在稠密的人群中不断试图脱身的个体象征着在贾迪斯案中试图获取先机的人物们,然而他们日渐陷入这拖沓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获取预想中的利益,反而延宕了自己前行的脚步。而浓雾则象征着事件的复杂及法庭暧昧不清的裁决,事件全部细节因人物各自怀揣的目的而被遮蔽,始终处于云山雾罩的氛围中。而对图金霍恩先生办公室的静态空间叙事则隐喻着人物的内在性格,他的办公室内“凡是能够落锁的地方都扣着锁,到处也找不见钥匙的踪迹”。封闭性的空间与密集的锁头暗示着图金霍恩先生具有严谨小心的行为作风,且他的内心必定隐藏着无数的秘密不想对他者敞开。读者通过文本中的叙事空间形成了对人物的初步印象,从而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试图在之后的情节中印证自己对人物形象的猜想与判断,探寻图金霍恩先生试图隐藏的秘密,从而对小说情节的发展产生了高度的阅读期待。
而《小杜丽》中的城市空间则更富有隐喻意义,不同城市空间的特质揭示着现代性维度上社会阶级秩序的变更,使空间叙事具有深刻的历史写照性。富翁莫多尔位于市中心繁华地带的物舍“实在是漂亮至极,明亮而璀璨的饰物将宅邸装饰得富丽堂皇,走廊上陈列着昂贵非凡的油画,其中的一间屋子悬挂着金色的鸟笼”,华丽却庸俗的装饰象征着莫多尔既富有又流俗的背景,而“金色的鸟笼”则暗示着莫多尔虽拥有无数的金钱,但本质上他也被自己所处的金钱游戏所困,不得不想尽办法维持自己的资产不受影响。而旧贵族巴纳克尔先生居住的宅邸则位居高贵的伦敦城区,那里云集着上流人士的住宅。可是仔细观察巴纳克尔宅邸的细节,读者却能够发现那“宏伟的外墙已经剥落,斑驳的痕迹如同一个麻脸的老人,整栋建筑正在以奇怪的角度倾斜着,像是不自然地塌着肩膀”。宅邸的年久失修与没落象征着旧贵族在工业文明的冲决下已日渐没落,不同空间场景的特征具有深刻的社会隐喻意味,揭示着经济结构的移置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变迁。
在静态叙事空间的隐喻建构之外,狄更斯也常以主人公行迹步履的转换为经在小说中进行动态的空间叙事,使不断切换的空间场景形散神聚地展示社会全貌,构成文本叙事据以延展的线索。例如,在《圣诞欢歌》中,狄更斯借由主人公斯克鲁奇的脚步引领读者观览了伦敦的都市空间,宏伟的皇家剧院金红色的灯光、散发着馥郁的水果芬芳的科芬园市场、堆叠着五彩斑斓的垃圾飞舞的垃圾箱,以及街角商贩热烘烘的小吃摊子,美丽与丑陋、高贵与庸俗、崇高与渺小,它们共同织构了伦敦城市空间的美学经验,传递出狄更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深刻理解。而《远大前程》中的空间叙事更兼具“成长小说”的意味,皮普在不同空间之间的游移不仅成了小说据以发展的线索,还隐喻着皮普身份认同的转化与主体成长史。从破败的铁匠铺与阴森的沙提斯宅邸,到繁华伦敦的贾格思事务所、汶米克城堡与私人寓所,皮普从贫穷学徒变成了伦敦绅士,他的自我认同也在不断地产生变化,从感性走向了理性、从依赖变成了疏离、从善良转化为冷漠,更加适应社会的生存规则。叙事空间的置换暗示着个体的成长轨迹,使空间承载的文化背景与阶层标识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揭示了叙事空间具有的丰富叙事潜能。
三、讽味浓厚的幽默艺术
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立场使狄更斯专注于表现时代现实,然而他并未赓续传统现实主义写作镜像化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写作方式,而是以幽默的姿态介入现实、书写人物并观照世相,以夸张放诞的笔触和恣肆的想象力把握现实。狄更斯小说的幽默艺术具有浓厚的视觉性特征,在温和的戏谑下流露出些微的讽味,具有深刻的现实反思价值。
狄更斯的幽默艺术集中体现在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成功地将视觉性的元素融合到形塑人物的过程中,通过夸张、变形等手段放大人物身上的某些特征以使其偏离常规、远离逻辑,从而产生引人发笑的幽默效果。他将《艰难世事》中的银行家庞德倍形塑为“破铜烂铁制造的圆钢炉被套进了上好的天鹅绒里,同时被塞上了一柄手杖和一只不断喷吐着烟雾的烟斗,于是到处都能听见他破锣般的笑声”,滑稽的形象揭示了庞德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尽管身着华贵但是举止十分轻浮矫狂,尽管跻身于上流社会却并非真正的绅士。而《远大前程》中的郝薇香小姐则被形塑为终日里“披着泛着黄的陈旧婚纱,顶着满头干枯白发”的怪人。人物的荒诞外表结合其种种奇特的行为举止经常带给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惊异的体验,这种形象与行为的反差时常能够引起读者的暗自发笑。这些“乖讹”的人物以直观的视觉形象制造了强烈的感官冲击,幽默形象的视觉性使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有着漫画式的风格,特征鲜明而栩栩如生。
同时,狄更斯在小说的话语叙述中也十分擅用幽默来进行点化,常使用巧妙的譬喻将平实的描述升华为语言的艺术。例如,在《匹克威克外传》中,匹克威克先生的帽子被大风吹去,他不得不狼狈追逐的场景。狄更斯将其描述为“那顶帽子快活地向远处跑去,就如同海里追逐着船只的海豚那样自由,滑溜溜地怎样也捉不住”,一时间头顶的帽子沿街溜走,而匹克威克先生不得不拼命追赶的窘态便跃然纸上,使读者因眼前浮现的生动画面而深觉好笑;《远大前程》中,朴开特先生在遇见棘手的事情时常常“揪住自己圆滑头顶上贫瘠的几缕头发,好像要把自己从这糟糕的泥淖中拔出来似的”,巧妙的比喻带来滑稽的叙事效果,令简单的动作饱蘸幽默的趣味。而当乔去看望已经发迹了的皮普时,他忐忑地等待着皮普的到来,“那顶轻巧的帽子仿佛变作了几十斤易碎的鸡蛋,令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用手擎着”。皮普身份的变幻使乔不得不小心应对,以提着“几十斤鸡蛋”的小心来对待自己破旧的帽子,以期在皮普面前维持有限的尊严。这些令人发笑的窘态背后自有其心酸之处,而狄更斯着意将这些底层人民因现实而窘困的姿态以传神幽默的方式加以勾勒,使读者在为其可笑之处而微笑的同时,油然而产生对他们的同情与体谅,并将批判性的视野置于造成这些现象的社会之间。幽默轻松的语调及其所展示的社会现实之沉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叙事语调与思想主旨之间的不协调生成了浓厚的讽刺意味,凸显了狄更斯的现实主义写作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特质。
对现实的深切观照使他对底层民众有着深沉的关爱与同情,因而他的幽默艺术撇去了其他讽刺性的作品中慣常的浮躁之气。他以夸张的手法塑造人物,以幽默的譬喻描述场面,不仅是为了制造供读者取乐发笑的契机,还是为了借由带有讽味的幽默表征社会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狄更斯幽默艺术轻松愉快的表象下,沉淀着浓厚的反思和感伤情绪,令这些滑稽的小人物引发了读者深刻的同情。
狄更斯在叙事层面推进了英国文学的发展,其复合交叠的叙事视角与寓意深刻的叙事空间极大地推动了现实主义写作的形式变革,使更自由的叙事技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结合,促进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狄更斯讽味浓厚的幽默艺术更使其小说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真正成为“英国传统在文学上的最高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