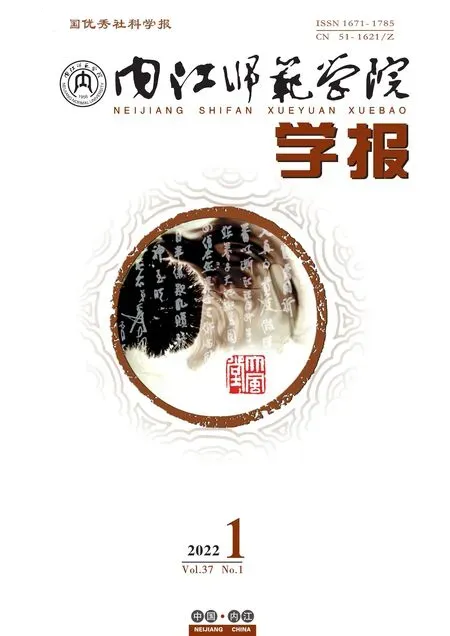从美学到哲学的路径
——兼及潘知常生命美学的学理建构
2022-02-13范藻
范 藻
(锦城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97)
美学与哲学在潘知常的生命美学的学理建构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潘知常的生命美学是如何处理美学与哲学的关系的。这不但是从美学出发去探寻生命美学的哲学原理,而且是从哲学层面上铸就生命美学的美学品格。进而言之,从美学到哲学的路径反思,更是理解潘知常生命美学的一把钥匙。
如果说哲学始于人类仰望遥远星空的一瞬间,那么美学就诞生于人类痛吻脚下大地的那一刻。前者如“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后者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中国唐代的张若虚和陈子昂是当之无愧的诗人式的哲学家和美学家。由此看来,哲学与美学借助于“诗”,也即是艺术的形式,获得了对话的平台和交流的语境。由此令人突发奇想:美学与哲学能否在学科的座位上平起平坐?美学能否取代哲学而凌驾于其上呢?
第一个问题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它们在传统的学科层级上隶属于不同的层级,就像儿子岂能僭越老子。而第二个问题则比较复杂了,美学取代哲学就意味着它是“第一哲学”,是“哲学的哲学”,而第一哲学就是哲学的哲学,又叫元哲学,西方习惯上把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思考的仍然是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力图使心灵摆脱感官而获得确定的知识。尽管用的是散文的笔法,近乎诗化哲学,但距离哲学美学依然遥远。后来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里,因为美学具有审美发生和逻辑理念的双重“优先”而直接称美学为“第一哲学”。在中国,杨春时先生2015年出版了《作为第一哲学的美学》,试图超越意识美学和身体美学,建立体验美学,但距离生命美学仍然是近在咫尺。李泽厚2019年在《美感的两重性到情本体》一书的最后不无感慨地赞同“美学是第一哲学”。但他的立足点依然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着眼于消弭哲学与美学的界限。
潘知常沿着人类生命的起点,依傍审美活动的过程,借助“生命”这个鲜活而神圣的中介,实现了美学与哲学的交融,并阐释了“美学是第一哲学”,更是“未来哲学”和“爱的哲学”的形而上“宿命”般的依据和形而下“诗意”式的表现。
一、本体论:形而上学的追问
本体论是对“什么是什么”这一判断中的“是”又是什么的追问。如果说第一个“是”追问的本体论的概念之“是”,是连接现象和本质的谓词的话,那么第二个“是”则思考的本体论的本体之“是”,即世界背后所蕴藏的高度抽象而又不依赖于现实世界的“理念”“理式”的存在本身,是为本体论之“论”的哲学追问,亦为康德哲学中与“现象界”对立不可认识的“自在物”。毫无疑问,形而上学的“思”就是通往本体论的唯一道路,或者形而上学本身就是本体论的追问。不论是美学追问生命是什么,还是生命反思美学是什么,都正如海德格尔说的那样:“哲学就是在这些问题中看到了自己的真正历史使命。所以,形而上学就是表示真正哲学的别称。”[1]
对此,潘知常说道:“形而上学是美学之母,美学则是形而上学之子。重新确立美学的形而上学维度,就是重新确立审美的至高无上的精神维度,重新确立审美至高无上的绝对尊严,美学也会因此得以光荣‘复魅’。”[2]这不仅是哲学反思的维度,更是生命追问的深度而彰显出人类文明的高度。
如果说哲学是对万物存在之“是”本身的追问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存在比生命存在之“是”更重要和更伟大呢?而将人的生命与审美紧密相连,并在生命美学的理论论证中揭示出“因生命而审美”,这在升华生命意义的同时,也在回归美学的生命视域和紧扣美学的生命领域的同时提升了美学的档次。也就是说,由对生命活动的哲学反思到对审美活动的哲学阐释,使哲学不仅成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理论注释,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美学总结。于是,作为哲学首要性和根本性追问的生命美学具有了第一哲学的美学品格。著名美学家杨春时教授是这样解释“美学是第一哲学”的:“美学是哲学的基本方法论,只有审美才能发现存在、确定存在的意义;审美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回归存在,存在论是审美体验反思的产物,美学为存在论奠基,从而成为哲学论证的出发点。”[3]这个“哲学论证的出发点”当然就是生命——人类自由而美丽的“灵肉一体”的生命。
那么,地球上的生命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同样是生命,驱动其生长的机制肯定是不一样的。植物的生命必然经历由小到大,动物的生命必然经历由弱到强,和人的生命一样,死亡都是它们的共同归宿。面对浩茫的宇宙,尽管人类的生命也是如苏东坡所言“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它还能在“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意义追求中。“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在有限的时空中企及无限的意义,“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这与其说是生命置身的现实情状,不如说是生命向往的理想境界,从而证明生命具有一种超拔的意力和超越的意向,证明“苏轼的诗意人生的生命之美不仅有丰富的旅程、丰硕的成果和丰厚的底蕴, 而且在这矛盾的构体和冲突的结构中, 形成了巨大而无限和复杂而充盈的生命张力”[4]。还有孔子当年在齐国屡次碰壁而不得施展政治才能,闷闷不乐,可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对此,潘知常深有感触地说:“确实,对于人类来说,美就像‘空气’和‘爱’一样不可缺少,追求美,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也是人类尊严之所系,更是人类生命力的源泉。”[5]诚哉,斯言!
于是,回答“生命为何必然走向审美”的理论假设,其实就要证明因生命而审美。这里的生命首先是自然生命,笔者之所以没有采纳美学家封孝伦教授的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三重生命”说的“生物生命”,是因为作为人类的生命,尽管有生物性的成分,如基因、细胞、有机体、染色体等,但这些仅仅是生命的内在构成,或者说是生命的生理要素。仅有这些生物性的成分和构造,只能说明具备了生命的形成因素。但要真正诞生或成为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生物性的内因还必须与自然界的外因发生关系,才能形成人的生命。而人类意义和视域下自然生命则不一样了,它既包括内在生物性的本质规定,也包括外在自然界的环境要素,正是二者的双向合力促使了具有人类意义的生命的诞生和成长。
如植物的生命具有趋光性,动物的生命具有避害性,如此才能保证它们的生长。但植物和动物永远不知道更不会去询问,为何有趋光性和避害性。这种本能性的功能既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因此代的延续和量的叠加就是它们的驱动力,因为它只有一种合乎天性和顺乎环境的生长机制。而人类的生命则不一样了,潘知常说道:
在人类的生命结构中存在着两种机制,即工作机制和动力机制。前者面对的是“世界是如何”,后者面对的是“世界应如何”,前者以大脑、认识、理性为代表,后者则以心脏、价值、情感为代表。而且相比之下,后者更为重要,并且处于动力的、基础的、根本的位置上。无疑,审美活动显然应该属于后者。对于理解审美活动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6]
“世界如何是”的工作机制是结论性的说明,而“世界应如何”的动力机制才是过程性的揭示,这两种机制中的动力机制由于“心脏”器官的存在和作用发挥,因而是其根本性和原发性的机制。心脏日夜不停地搏动而导致血液循环的舒畅感和一起一伏而形成的节奏感,应和着太阳的东升西落的永恒运转、月亮的阴晴圆缺的不变规律。这种宇宙的生命节律与人的生命节律相辅相成而启迪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观点的产生。因为大宇宙诸如“大爆炸”“磁力线”“星云”“黑洞”等动力机制的作用,人类才能产生“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运动感;又因为小宇宙诸如“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和“循环”“呼吸”等动力机制的作用,个体生命才会真切地体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存在感。可见,由于潘知常将“美”“美感”和“审美”定位于“活动”,那么在生命美学研究上,他比封孝伦更具有“动感”。原来封孝伦仅仅是说明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是“生物生命”,而潘知常却要证明生命是一种运动形态。也正是因为这种外对应于“天”,内呼应于“人”的生命运动,将人类生命的“自然驱动力”赋予了“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雄伟气魄和宏大胸襟,从而说明动静结合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既是宇宙的本质,也是生命的本体。
而构成生命本体的“是”,用海德格尔的话讲是“存在”之“亲在”。而显示“亲在”的是如潘知常所谓的“动力机制”,而为这个机制提供源源不断能量的则是情感。最原始的“上邪!”最原本的是“妈啊!”演变为《尚书》的“诗言志”、后来如孔子的“兴于诗”、《毛诗序》的“吟咏情性”,魏晋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唐人皎然的“情在言外”、宋人叶梦得的“缘情体悟”直至明中叶达到高峰,这些统称为“兴观群怨”。这就是感性与情感。为此潘知常在1985年出版的《美的冲突》里称之为“启蒙美学”:“强调人的感性情欲的合法地位和自由表现,强调作家以审美主体的表现为主,直抒胸臆,摆脱束缚”的“启蒙美学独尊感性情欲,开始冲破‘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古典美学观。开始把感性的、充满世俗人情的社会生活推上美的殿堂”[7]。尽管审美的王国不乏义利的考量、价值的追求和伦理的企及,但是情感永远是至尊的国王和伟大的母后。尽管这个王国里也存在着情与理、爱与恨、美与丑和生与死的较量,但胜者的荣耀不是建立在负者的痛苦之上的,负者也非永远是输家,完全可能是“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也会是“美人之美,各美其美”。最起码也是“损人不利己”。这就是经济学称之为的“非零和博弈”。原来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促使生命走向审美、推动蒙昧走向文明的秘密:爱的力量与爱的信仰。
二、关键词:终极关怀的莅临
不论是复杂而丰富的人生经历,还是深刻而多样的学术研究,生命美学都深为服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对“人是什么”的经典解说:“说人是一种力量和软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狄德罗之所以由此陷入巨大的困惑,是因为他关注的是人的此岸世界,是生活情境中的人,属于现实关怀。从认识论上看,生命是一个可以阐释的“为我之物”,但是我们要试图寻找它存在的理由。从本体论上看,生命是一个无法言说的“自在之物”,因此我们要努力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不论是为人找到存在的理由,还是揭开人神秘的面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现实世界的参照毕竟是有限的,常常令我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莫衷一是,每每令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执迷不悟。看来必须“会当凌绝顶”,才能“一览众山小”。前面,我们借助形而上学已经实现了本体论的伟大转型,那么,这里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将本体论生命存在的意义发扬光大,或让本体论在生命意义的思考上再接再厉。由是,终极关怀悄然莅临。将终极关怀由哲学的冥思或宗教的虚幻引入能彰显人类生命存在意义的审美活动,将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凝练为审美形而上学。潘知常早在1991年的那本生命美学的奠基作《生命美学》里就问道:“审美的生命活动呢?它是怎样做出对生命的终极追问、终极意义、终极价值的回答的呢?显而易见,它是用绝对的价值关怀的生命存在方式对生命的终极追问、终极意义、终极价值的回答。”[6]9潘知常有别于以往的哲学家和美学家的是,他紧紧扣住生命活动和审美活动的内在联系,又不拘泥于二者表面的对应关系,而是着眼于从生命与审美的“终极”存在上,试图通过审美来解开生命之谜。
潘知常经过二十多年的思考,到了2019年在《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里将以前《生命美学》里的三个“终极”归结为“终极关怀”,并正式将审美活动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他进一步说道:“由此,审美形而上学把人类精神、人的审美存在方式推到了美学的前台,把形而上学的重建作为自己的美学使命。而‘终极关怀’也是成为审美形而上学的关键词。”[2]449终于把审美由在艺术与生活领域里形而下的体验提升到了存在与意义维度形而上的反思,即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
何谓“终极关怀”?这个概念来自20世纪西方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信仰的动力》:“如果某种至关重要的自称为终极,它便要求接受者完全委身,而且它应许完全实现,即使其他所有的主张不能不从属于它,或许它的名义被拒绝。”[8]这是一个比较保守和消极的终极关怀,因为他面对生命中必然出现而又必须接受的,也是有限的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法则,生活中的我们只能委曲求全或逆来顺受。那么,还有没有超越现实而有必须接受的无限的“生命大限”呢?那就是交织着灵与肉的双重压迫,而又必然降临和必须面对的“生命绝境”,这就是由生老病死引出的焦虑与恐惧、喟叹与哀怨。尤其是生命的终将一死,面对死亡的生命终点而开始的思考,就是终极关怀的最本质性的内容。
在如此死亡阴影下踽踽独行的人类,依然要奋起抗争,用比喻、喟叹和誓言彰显的生命美的方式将中国式的终极关怀演绎得酣畅淋漓。这就是潘知常说的:“终极关怀所坚守和维护的,就是人类生命存在当中的‘必须’与‘应当’。而且,这‘必须’与‘应当’最终究竟是否能够实现,又是完全未知的——尽管可以坚信它必然实现。因此,从终极关怀出发的审美活动事实上就是赌理想的人生存在。”[2]190而要赌赢“理想的人生存在”,即实现生命的“必须”与“应当”,从而更好地体现出生命在这三个方面的意义,也是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在1991年第一期《社会科学战线》刊发的《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考》一文中,对终极关怀归纳的三种类型,在下面的阐释中分别引述。
一是,生命是有限的却又追求无限的存在。如果人类没有终极关怀的莅临,就会如庄子所谓的其“生也天行,死也物化”、浑浑噩噩地生存、懵懵懂懂地生活。而正是因为“终有一死”死亡意识的产生,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卡尔·萨根所说:“人的预知能力是随前额进化而产生的,这种能力的最早结论之一就是意识到死亡。大概人是世界上唯一能清楚知道自己是必然死亡的生物。”[9]这也是王羲之感叹的:“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而要追求长生不死是根本不可能的。“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人类,就开始了抗拒死亡的万里长征,虽然结果依然是死亡,但近者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追求,远者有进入上帝真主佛陀的永恒境界。此之谓张岱年解释的“皈依造物主的终极关怀”。
二是,生命是肉体的却又羡慕精神的境界。肉体的生命就离不开酒色财气,也是恩格斯《在马克思说墓前的讲话》中赞颂马克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在从事的这些社会事务和精神活动中,政治明显地受到时代的限制,科学受到认知的限制,而艺术和宗教则提供了一片自由的疆域,尤其是艺术借助情感的动力,人类的精神生命在这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如潘知常所言,这种审美意义的活动体现于终极关怀,它既维护了世界的完整性、丰富性和多样性,也满足了生命的超越性、创造性和整体性。此之谓张岱年解释的“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
三是,生命是现实的却又向往理想的自由。现实的生命尽管是真实的生命,但不是自由的。就像卢梭说的那样:“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可是自由又是生命的本性和宿命,因为自由的理想、自由的想象、自由的思想而证明了人的生命不同于动物的生命。在自由的三大种类中,自由的想象容易陷入空想,自由的思想受到思想本身的限制,而唯有自由的理想是无羁无绊的,能给人以未来的美好许诺,尽管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因而它具有了终极关怀的价值,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陶渊明的“桃花源”、摩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宗教的“净土”“乐园”“天国”等,这些莫不表明了由于理想之光的照射而使苦难的现实充满希望的期待和获得自由的抚慰。此之谓张岱年的“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
不论何种类型的终极关怀,在其根本意义上都是指向生命的形而上学层面。但由于审美的介入而具有了感性的光辉,从而为生命与审美的合一打通了经由审美活动实现生命活动之目的的“最后一公里”。因为生命的存在或曰生命意义的大彻大悟,美学再也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实践的“自由形式”了,而成了“自由境界”,更是自由本身。于是,借助生命终极关怀的关键词,美学一跃而升至哲学的殿堂,拥有了生命的最高意义和最大自由。就此而言,美学就是哲学,生命美学就是第一哲学。
三、立足点:审美哲学的形成
艺术尤其是诗毫无疑问是审美的典型形态。审美哲学就是要“把哲学诗歌化,把诗歌哲学化,这就是一切浪漫主义思想家的最高目标”[10]。这是恩斯特·卡西尔转述施莱格尔有关诗化哲学的经典而精彩的表达。“诗是绝对名副其实的实在,这就是我的哲学核心。越是富有诗意,也就越是真实。”[11]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的看法与亚里士多德“诗歌比历史更普遍更真实”一样。
当代中国提出这一概念最有影响的是刘小枫1986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他认为:“诗化哲学把美作为个体生存信念的归宿,以审美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最终追求,将感性个体生命归依于审美主义与审美救赎。”因为从古希腊以来盛行的理性主义,加上近代的工具理性、现代的商业理性,使得“普遍的理性化,无异于普遍地遗忘人的感性生存,面对这一历史境遇,诗人出来取代哲学家,就不但合法,而且也是诗人的圣职”[12]。可以说,对生命的关注与思考是所有美学家的共同主题。刘小枫还在《拯救与逍遥》通说中西方诗人的自杀来阐释终极意义的理解:“它恳求所有侥幸活下来的诗人们想一想,什么才是终极的意义和价值;想一想自己所具有的信念是否真实的、可靠的。”[13]就这个意义而言,刘小枫的美学思考无疑也是属于生命美学的范畴。
但是,刘小枫对生命美学的“最后一公里”仍然未能打通,依然徘徊在生命美学的大门口。因为“诗化”毕竟艺术化了,也不能完全涵盖审美活动,而潘知常在《诗与思的对话》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了:
伴随着人类生命活动本身成为哲学本体论的内涵,审美活动本身也无疑会因为它集中地折射了人类生命活动的特征而成为哲学本体论的重要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生命本体论的所谓思与生命的对话,就其实质而言,实际上就是思与诗(审美活动)的对话。[16]24
他又在2002年出版的《生命美学论稿》中阐述这一见解,还在2019年出版的《信仰建构的审美救赎》中说道:“生命美学关注的是:诗与思的对话。……审美形而上学涉及的是审美本体论维度,讨论的是‘诗与哲学’(诗化哲学)的问题。”[2]447
诗或诗歌在西方美学的语境中常常是文学或艺术的代指。在从美学通向哲学的路途中,如果说最具有美学魅力的当属诗学,那么最能体现哲学精神的当数美学。在超越诗化哲学进而审美哲学的命意上,潘知常既沿袭了德国浪漫主义美学借助诗歌来拯救日渐沉沦灵魂的伟大使命,也继承了中国古典主义诗学“诗言志歌咏言”的优良传统,更是扩展了刘小枫的诗歌美学的疆域而成为生命美学的重要话题,并赋予了艺术在生命体验与美学品格、更是哲学反思过程其价值何在的本体论地位。那么,潘知常生命美学视域下的艺术的本体论到底是什么呢?或者说“诗”,其实就是审美如何化为“哲学”的呢?
首先,重新确立了艺术的本体论内涵。如果说哲学因其执着的理性追问精神而理解,其本体论含义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艺术因其不断的情感抒发特质而理解其本体论含义似乎困难多了。其实不然,艺术抒发的情感是人的情感,而人的七情六欲无不是人的生命的重要表征,但是作为高等动物人的情感,绝不是自然的情欲,也不完全是自我的情绪,而是富于高雅而高尚的情感。中国文学向来就追求以情言志和以意传情的“情理一体”。德国现代哲学家舍勒《爱的秩序》就论证了“情理本一体”的见解。而佛洛姆也在《爱的艺术》里说明了“爱是需要学习的”。这些都说明艺术的本体论与其说是理中之“情”,不如说是情中之“理”。当然最好的说法是“情理一体”。这也是潘知常一直看重并反复论证的“诗与思的对话”。
经过这一番对话,不但敞亮了艺术的存在之光,展示了艺术的生命之魅,而且为艺术在美学尤其是生命美学建构的体系中找到了自己最恰当的位置和最合理的存在方式,如宋耀良1988年出版的《艺术家生命向力》和封孝伦1989年的硕士论文《艺术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达》等均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其次,重新强调了艺术的形而上价值。柏拉图为了维护理想国的纯洁而认为艺术“和真实隔着三层”是不真实的,尼采站在艺术拯救人生的立场认为“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海德格尔并不把艺术看成是美学的思考对象,而是从人类“存在”意义的角度,指出艺术与美无关而与美学有关,是人类生命存在状态“恬然澄明”的真理揭示。苏珊·朗格也说:“真正能够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人类生命的方式便是艺术方式。”[14]潘知常感叹道:“不难想象,当代美学把哲学引入美学,意味着美学根本问题的重大转换。过去,我们一般只是从审美活动所反映出的内容的角度来考察审美活动本身的本体论内涵,但是现在我们却意外地发现了审美活动本身的本体论内涵,审美活动本身就是本体论的、就是形而上学的。”[15]审美哲学立足点的形成,使得潘知常的生命美学由内容到本体的递进或嬗变,意味着美学不仅关乎艺术,更关联到艺术所蕴含的生命和生命背后的形而上意义,显然这是实践美学不能回答的问题。
由于审美活动进入了生命的本体视域和存在高地,潘知常的再度强调就有力地突破了中国人熟悉的古典艺术“兴观群怨”功能观和“文以载道”的价值观,使艺术由美学的方面军变成了哲学的生力军,从而使得美学不仅获得了艺术哲学的冠冕,而且戴上了第一哲学的王冠。
最后,重新阐释了艺术的生命力意义。艺术不仅是美学的思考对象,而且是哲学的精神寄托,更是作为第一哲学——美学有关人类生命意义的“恬然澄明”的对象和途径。它不仅是生命力的象征,而且其本身就是生命力的显示,不仅是生命意识的表达,而且其本身就是生命意识的载体。潘知常正是站在生命审美与艺术哲学砌成的高度,用如此深邃的目光,发现了中国艺术除了从《诗经》历经杜甫、辛弃疾到元杂剧再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忧世”传统,还有一条更为深沉而绵延的“忧生”传统,那就是从《山海经》经由庄子和魏晋诗歌、到李煜再到《红楼梦》终于王国维的以“文学为生活”的美学传统。他还对中外的文学艺术经典进行了重新审视,如李煜是“以血书”的词章、《哈姆雷特》诉说的是“我的爱永没有改变”、《悲惨世纪》高倡的是“以爱之名”、《日瓦戈医生》进行的是“爱的审判”。他更是盛赞《红楼梦》是中国的“众书之书”,是“爱的圣经”、文学宝典与灵魂史诗。
正是因为生命力的存在,让艺术家获得了生命的最高存在价值,有如神助,逢凶化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使得本已羸弱的生命在美的烛照下和诗的氛围中,不但返归生命澄明之境,而且登临生命巍峨之峰。
总之,在生命终将走向审美的论题上,潘知常有两个“重要的不是什么,而是什么”的语义模式,从生命的构成和美学的原理上,将“因生命而审美”予以了最简明而精辟的揭示。
一方面,在美与生命的关联上,潘知常经常强调“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或许就审美对象自身的存在而言是内容大于形式,而于审美主体能动的感受而言是形式大于内容。平心而论,映入我们眼帘和震动我们耳膜的首先是对象的形式。这就是柏拉图所谓“形式美所产生的快感”、亚里士多德在“对象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模式或结构”的“形式因”、康德的审美判断是“没有利害关系”的而又普遍令人愉悦的“合目的性的形式”。这种形式之所以令我们愉悦,因为它潜藏着无比丰富而强烈的生命内容。只是人类在审美起始的一刹那犯下了一个“买椟还珠”的美丽错误。如此“一见钟情”,让人类因为对象的“形式美”而获得了永恒的美学生命。
另一方面,在美学与生命的关联上,潘知常还经常强调“重要的不是美学的问题,而是美学问题”。作为哲学问题的生命投射的美学问题,与其说是“美是什么”的“本质”重要,不如说是“美感如何是”的“体系”重要,因为后者与生命的存在和意义息息相关,而同人类的实践作用和价值倒无甚关联。而令人费解的是李泽厚在自己率先建立了实践美学之后,劝诫后学们说:不要去建立什么美学的体系,而要先去研究美学的具体问题。可是,生命美学更相信的是康德的劝诫:没有体系可以获得历史知识、数学知识,但是却永远不能获得哲学知识,因为在思想的领域,“整体的轮廓应当先于局部”。除了康德,黑格尔也说:“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16]这个体系虽然表现于思辨的构架和论理的框架,但它源于人类五官感觉的合理分工和总体协调的组织结构,而哲学则将此提升和梳理为理论的体系。而作为第一哲学的美学,尤其是生命美学必须将这种生命感觉予以恰当和合理的阐释,因此,我们在研究“美学的问题”之前,也不能不首先思考我们对于“美学问题”的思考是否正确,更不能不思考我们自己是否也需要首先对“美学问题”本身去加以思考,否则我们关于“美学的问题”的研究就很可能无功而返。人们常说,要做正确的事,而不要正确地做事。无疑,对于“美学问题”的关注,就是“做正确的事”;而对于“美学的问题”的关注,则是“正确地做事”。
由生命美学到生命哲学,潘知常更是深刻宣示了生命美学截然不同于实践美学。实践美学往往以艺术为核心,追求的也只是精神愉悦。而生命美学不是将审美与艺术活动等同,而是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生命的真正含义,因为作为人的生命它本身就包含了“美”,是原生命与超生命的有机统一。从此,生命美学毅然走出了实践美学的围城,推动着审美回到了人类的生命活动本身上来。
潘知常的生命美学从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建立到终极关怀关键词的确立再到审美哲学立足点的站立,充分证明了从美学到哲学的必然之理。这就是“因生命,而审美”和“因审美,而生命”,昭示的是生命必然走向审美和审美天然拥有生命。由此可见,潘知常确立的审美形而上学,让生命美学完成了由美学到哲学的“华丽转身”,这就是以生命体验为根基,以审美活动为依托,以自由境界为鹄的,向外“天人合一”,向内“身心一体”,开始的伟大而精彩的“诗与思的对话”。它所指向的不仅是富丽堂皇的“第一哲学”的殿堂,而且是光辉灿烂的“未来哲学”和温馨可人的“爱的哲学”,因为“所谓未来哲学,也不仅仅是自由的哲学,而且还应该是爱的哲学”[17]。与其说这是美学通向哲学的必由之路,不如说是美学走向生命的光荣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