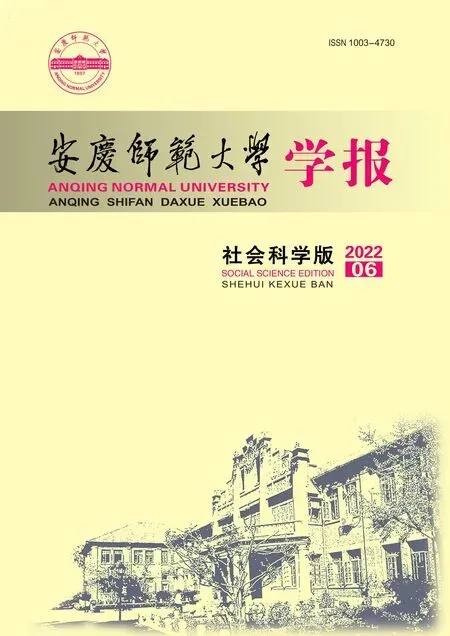《史记》称谓问题考辨二则
2022-02-13张雨涛
张雨涛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宝山 200444)
《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但在历史学方面有着深远影响,同时也作为珍贵的语言材料,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西汉中期的语言面貌,我们可以通过当下的语言学原理对《史记》中的语言问题做出很好的讨论。近如辛德勇先生的《史记新本校勘》,对2013年出版的中华书局《史记》新点校本作出大量校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校勘》中仍存在一些还值得审视的问题,我们择取其中的两则称谓问题,并试图用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再次对其进行分析,以期对《史记》校订的完善,以及加深《史记》中某些语言现象的认识作出一点努力。
一、“我先+NP”及相关称谓问题
《史记·周本纪》: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1]135。
该段所存的疑点在于“我先王”这一组合。《册府元龟》以及宋代公序本的《国语》等版本典籍中所载的都是“昔我先世后稷”,辛德勇(2017)因此推论《史记》原文中的“我先王”的“王”应当是衍文[2]92‐95。
从文献中的事实出发,这里的“王”不是衍文,“我先王”即为正确的原文写法。理由如下。
首先,如“我先王”的语例在当时文献中即为常例,从先秦文献中即为常语。相反,我们没有在典籍中找到“我先”的有关用例。如:
进一步考察后发现,当时语言中后辈称呼自己已故的祖先或先辈,基本上都要在“先”字后加上一个敬语称谓,形成“我先+X”的格式。“X”的内容一般表示生前的地位或者担任的职务,除了上文的“我先王”外,“我先君”也使用较为频繁,如:
此外还有大量的“我先大夫”“我先后”“我先公”“我先人”等语例,都是附缀上相应的敬称以表示对先人的尊重,形成“我先+N敬称+(NP人名)”格式的结构。如:
在少数情况下“先”字后直接跟上先人的名号或者谥号,抑或是先人的来处,我们在《史记》中一共发现3例:
不惟是“我”,当替换成与之近义的“吾”时,其分布情况和“我先”是一致的。文献中我们没有找到“吾先”的用例,而“吾先”后加上各种敬语称谓,同样形成“吾先+X”的格式,如:
(17)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史记·齐太公世家》)[6]1329
综合上面几种情况,无论“先”字后所带的是敬称称谓,还是名讳、谥号等形式,称呼自己的先辈时总要带上相关内容。当“先”字后所带的是敬称类或职务类的名词时,言说者除了表达对先人的尊崇外,还有对自身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出现直接的名讳、谥号、由来的名词时,更多的是加强对所指先人的明确度,提高听话人对说话人内容的识别度。从语境中看,上文中“我先+X”或“吾先+X”的用例大都出现在发言和对话的情形中,如(17)~(19)句,其主观性就较为强烈,说话人的主观情感也更突出。
董秀芳(2016)就已指出,上古汉语中出现的“我+名词”构成的名词短语,这种短语的功能不是表领属,而是表示指示,“我”是一个独立的指示词[7]。既然整个结构的作用就是提高所指的识别性,而单独用“先”这样的类称反而模糊了所指内容,这和本身的名词结构功能是相悖的。总之“先”后的各式名称内容都有自身的语用功能所在,而单独的“我先”则会丧失这些功能。
其次,在文献中我们还考察了另一种“先”的分布情况。当在陈述句中客观说某一人的先祖或先人时,往往写作“其先”。上文中已经提及,“我先”的“我”并非代词,而是一种指示词;同样“其先”的“其”承载的功能也是指示词,两者正好可以类比。
以《史记》文本为例,其中有单独的“其先”的文例,其后并不带上其他的语言成分。如:
(20)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之有德,泽流后世邪?(《史记·三代世表》)[6]450
上文的这些句子,仅单独出现“其先”,并没有提供关于“先”的其他信息。这是因为这些句子中的“其先”并不是句子意义表达的焦点信息,而仅是作为背景信息存在。比如第(20)句中点明的是蜀王所处的地利之好,第(22)句说的是巴寡妇清的财富之巨,先祖在其语境中只起到一种背景介绍的衬托作用,是对人物现况的源流追溯,同样(21)句和(23)句也是类似的情况。
再如有的“其先”后带上相应的名词称谓,形成一种与上文“我先”相似的“其先+NP”类格式的同位结构,如:
(25)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高祖本纪》)[6]281
如上文的(24)句,这里描述郑庄的先人时,就并不简单的作为背景信息存在,其不但是对郑庄的溯源,更是要突出郑庄先人的过往经历,是话语表达的重点信息,因此这里的“其先”后带上了“郑君”这一敬词称谓,其语用功能也透露出作者对郑氏先人的敬重;同理(25)句亦是如此,为了指明汉高祖刘邦出生的传奇性,其母亲先人必须予以表示出来。
更进一步看,还有一类“其先”的组合运用在判断句中,或是点明人物先人的姓名,或是点明人物来源的家族,如:
(26)田叔者,赵陉城人也。其先,齐田氏苗裔也。(《田叔列传》)[6]2727
(27)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李将军列传》)[6]2831
(28)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东越列传》)[6]2985
(29)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列传》)[6]2847
如(26)(28)(29)句,“其先”的功能都是意在说明所述人物的氏族来源,(29)句则直接表示先人的姓名,整个句子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判断句,不过是在其中间插入一句谓语分句。与上文两种情况相比,这里的“其先”显然焦点意味更加突出,其所含的信息重要程度更深。“我先”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上文的第(14)(16)(19)句,都是以判断句的形式表达人物的身世信息。相较于其他形式,这种句子形式承载的语义容量会更大。从汉语常规的话语信息规则来看,在前的部分指代的是旧信息,在后部分是新信息,也往往是语义表达的重点,在篇章语言学有关名词成分与认知状态的理论中,认为如果受话人/读者能够将一个指称形式的所指对象与其他内容区别开来,则说话人/作者就会采用最简易的形式。反之,就会采取较为复杂的结构形式。其由简到繁的等级可以描述为:
零形式>代词>光杆名词>代词/指示词+名词>
限制性定语+名词>描写性定语+名词>关系从句[8]
前文所提及的“其先”分布情况,则大致符合这类等级关系。(20)~(23)句中“其先”并不是作为句子的焦点信息,因此只是单个的组合“其+先”出现,即“代词+名词”的结构,形式较为简单;(24)~(25)句则较之信息程度加深,作者想要表达出一定的所指内容,因此在“其先”后加上相应的名词称谓,构成了“其+先+NP”的格式,即一种“限制性定语+名词”的组合方式;(26)~(29)句则更进一步,其语义信息承载量进一步加大,因此“其先”的功能就涵盖了整个句子,总体上构成判断句的形式。随着话语信息的不断加大,其所呈现的形式也势必趋于复杂,正好构成一条从简到繁的等级链。
本质上看“其先”的分布状态和“我先”是一致的,其背后的驱动原因就是话语信息承载的多寡和语用交际的需要。依照语言的适量性原则,人们在称呼祖先时完全可以以“我先”或“吾先”概之,但文献中存在大量“我先王”“我先公”这类“我先+X”的格式,便是基于语用上传达敬意或明确指代对象的需要。同样,当“其先”所处的语境不同,如果其变为句中的焦点,承担的语用信息越来越大,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也随之复杂,实际就是突出信息,增强指代新的语言手段。
二、“相国+NP”的称谓问题
《史记·秦始皇本纪》: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1]293‐294。
这段文献中值得关注的是“相国昌平君”这一读法,在中华书局1982年的旧点校本和2013年的新点校本都是将“相国”与“昌平君”连文在一起。我们查阅其他的文献,相当多的学者都持这一看法。如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9],现代学人马非百的著书[10],田凤岭等人的论文[11],包括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的记述[12],无一不认为当时的相国即是昌平君。看似“相国昌平君”的读法和释义没有疑问。
但近来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相国”应该和后文的“昌平君”断开,“相国”应该与“昌平君”“昌文君”并列,是三位不同的人物。早时李开元(2013)在《秦谜:秦始皇的秘密》就做过考述,认为先秦时相国拥有独尊且唯一的地位,不可能存在多人。而对于昌平君其人,是随后吕不韦罢相,昌平君才接替成为秦国新的丞相[13]。此外,辛德勇(2017)也认为,这里的“相国”并非指“昌平君”,而是当时尚未罢相的吕不韦[2]323‐329。辛先生认为秦汉时期的“相国”地位十分尊贵,历史上的“昌平君”很可能是楚国在秦国的质子,是不可能担任秦国的相国。
对比以上的两种观点,我们认同后者的观点。“相国”后确实应该和“昌平君”断开,“相国”并非指昌平君,而是当时尚未罢位的吕不韦。在秦汉时期“相国”的地位要比丞相一职更为尊贵,一个国家或王朝不可能会同时存在两个相国。文献中如:
(30)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史记·吕不韦列传》)[6]2425
这里对吕不韦的记述,吕不韦在嬴异人登上秦国王位后就已经封为丞相了,而又在嬴政登位再次升阶成为了相国,可见相国和丞相是两个概念,并不能混为一谈。关于“相国”和“丞相”两者的比较,辛氏在文中已例举大量的考证资料,不再赘述。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该句所使用的文例。如果将“相国”与“昌平君”断开则难以得到文例上的支持。因为旧句读中“相国昌平君”这样的“NP职位+NP人名/称号”格式在文献中是通例,十分常见,这也是为何主流句读都把“相国”和“昌平君”连读的一个主要原因。如:
在《战国策》中多有“相+NP君”的语例:“又遗其后书曰:‘夫赵、魏,敌战之国也。’”(《赵策四》)“秦召,信安君不欲往。”(《魏策二》)相反,像“相国、昌平君、昌文君”这类官职名与人称号并列的句例却非常罕见。本文旨在解决这个矛盾,为何这里能与主流文例相悖,应该写作“相国、昌平君、昌文君”。
我们在文献中可以看到,如果发生“相国”之位的更代或是指代他国之相,都需要在其后附上相关的人名:
当然处在特定的语境中,如果是前面已经出现相应的人名,或者双方语境中已经知道所指的对象是谁,则该处的“相国”就可以单独存在,在对话中“相国”往往就可以不需要带上什么人名称谓:
(36)于是黄歇乃说应侯曰:“相国诚善楚太子乎?”应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原相国孰虑之。”(《春申君列传》)[6]2305
这里的“相国”显然就是指前文已经出现的“应侯”,这是交流双方共同拥有的认识前提。再说某一特定的篇章中,如《萧相国世家》,文中大量地单独使用“相国”一次,都是指代萧何一个人,也不妨碍语言的交流。
从语义特征来看,上文中的“昌平君”“信安君”等一类称号,和“相国”“相”一类官职,虽然同是指代人,但在语义性质上还是存在差异。前者的称号实质上是定指或是特指,其指代的对象基本上是唯一的,因此指别度高,语义指向是明确的;而后者的官职名,本质上是泛指,尤其是可多人担任的官职,除非在特定的语境下,否则语义指向是不明确的,指别度低。因此在一般的语言环境中,出现这类官职类的情况时就往往要带上相应人名或者称号,以明确其指代对象,提高指别程度,否则就会导致语义的模糊而影响信息交流。这就是为何文献中普遍存在“NP职位+NP人名/称号”的格式,“相国”后往往都要带上相应定指称谓。
同时在文献中还存在一类句子,这些句子中的“相国”是没有带上相关的人名或称号的,这里的“相国”单独出现有其一定的语境要求,如:
(40)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绐信曰:“虽疾,强入贺。”(《淮阴侯列传》)[6]2556
上述例子中,(37)句中前文已经出现了“相国公仲连”,提示了“相国”其人是“公仲连”,由于下文两处出现的“相国”都是同指“公仲连”,因此人名也就无需出现,单独写作“相国”也不会混淆所指;同样(38)句中前文提示“相国穰侯”,后文再提及“穰侯”时,单独出现其职务“相国”亦可完成指代功能。往后的(39)~(41)句都是相同的情况。尤其是第(39)句,“相国吕不韦”已经在前文中出现,后文的“相国”依旧指的是吕不韦,对照本文《秦始皇本纪》所讨论语句的时间线,(39)句描述的内容发生在诛灭嫪毐之后,在指明了“相国”是“吕不韦”之后,就可以单独用“相国”指代“吕不韦”。
这些句子都是基于语境铺垫后才有的特殊文例,因为前文已经提示了“相国”的所指对象,在语言适量性原则的驱动下,如果下文还提及同一个人,则就以“相国”单独指代人物,即使官职名在常规情况下承担的是泛指的功能,在此类语境下就可以达到定指的效果。本文的“相国、昌平君、昌文君”正是基于该原理,前文已经有过信息的铺陈,因此在后文的描述中就不必要带上相应的人名,直接以“相国”称呼,与例句(37)~(41)一致:
根据《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嬴政继位的时候,吕不韦已尊奉为相国,因此(42)句中“吕不韦为相”指的就是相国。
如果脱离了这种语境前提,《史记》中在有关“吕不韦”的记述中,强调吕不韦相国身份时往往需要在其后附加上“吕不韦”这一所指内容。如:“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诛之,尽入其国。”(《史记·秦本纪》)“幽王三年,秦、魏伐楚。卒。”(《楚世家》)“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后,甘罗年十二,事。”(《樗里子甘茂列传》)“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舍人。”(《李斯列传》)可见,单独用“相国”类的职务名指代具体人物是特殊语用环境下的现象,与主流的常规用例并不矛盾。
因此,“相国”在本文的语境下可以允许和“昌平君、昌文君”并列,指代的是前文语境中可以推断出的“吕不韦”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昌平君”。
三、结 语
语言的适量性原则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所遵从的重要准则,这尤其表现在称谓结构里,为了保证语言信息的充分和准确,都会相应地增加某些指称信息或省去冗余成分。本文讨论的两则称谓问题都贯穿着这一原则。秦汉时期人们称呼自己的远祖先辈时,基于对先祖的尊崇或者明确先辈的背景信息,不惟单称“我先”,而是在“我先”后附缀各类信息成分,以满足特定的语用需求;文献中在称谓“相国”或“丞相”这一职位时,一般都使用“NP职位+NP人名/称号”的格式,因为官职名为泛指功能,具体语境中需要加上相关的人名才能明确其所指。但如果前文语境已经出现“相国”的具体其人,则后文单用“相国”回指也可以成立,并不影响信息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