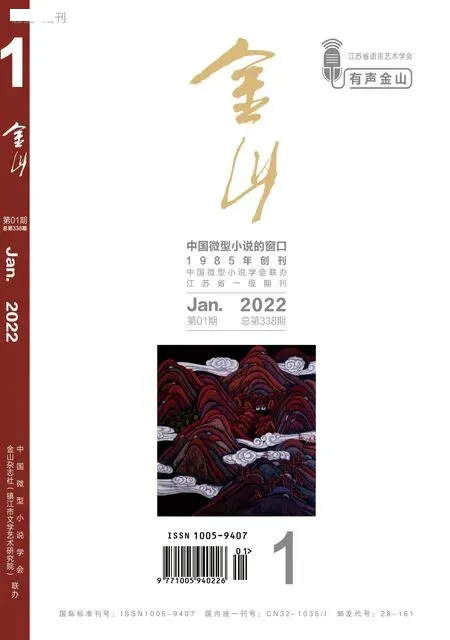《望春风》里的东乡书写
2022-02-13龚舒琴
龚舒琴
编者按:
乡土给予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不论是选择扎根乡土还是离开乡土,乡土的烙印都终将伴随作者一生。乡土的变迁,即是最容易被作者所感知到的时代变迁的缩影;乡土特有的民俗、风物,则是作者身体里挥之不去、永久封存的记忆密码;最重要的还是乡土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它们共同构筑成为坚不可摧的乡土情结,本期我们用文字来一一呈现。
我不是一个喜欢跟风的人。对流量作家或艺人,始终保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感。但作家格非和他的《望春风》却是一个例外。熟悉的场景,熟悉的乡音,熟悉的习俗,熟悉的人和事,一股脑儿地挟裹着我,纠缠着我,一次又一次地进入我的阅读视野。久违了,读书、记录、批注,欲罷不能。
我读格非先生的小说并不很多。
尽管,在拿到《望春风》之前,知道他有《隐身衣》,有《遏色鸟群》,翻过,但都是浮光掠影。坦诚说,我只“认真”读过《人面桃花》。当然,说认真读,是因为很久没有对任何一位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如此认真过,边阅读,边做笔记,边做批注。即使是在阅读曾偶像过的莫言先生的“红高粱系列”、《丰乳肥臀》作品时,也是。
犹记那年,面对《人面桃花》中乌托邦般的“花家舍”,甚至无数次一厢情愿地想象过,这应该就是发生在我东乡圌山坳里某一个乡村的一段似真似幻的故事。尽管我知道,小说只是虚构。
《望春风》不一样。
我固执地认为,这就是格非以故乡为背景的一部“真实”小说。作为从同一方故土走出来的文学爱好者,每一次读,都有一种很自然且强烈的代入感。书中提到的地方,很多我都知道,或者听说过,甚至去过。
我见过东乡“走差人”的神神叨叨;我见过东乡人聚在谁家“山墙下”对别人指指点点、肆意揣测的场景;我见过家家户户都必有的用芦苇秆或竹子围起来的储存有机肥的“茅缸”。我见过东乡奇人为眼睛突遇灰尘的人“翻眼皮吹沙”的精准奇妙;我知道东乡人称呼某些特殊人群都有约定俗成的名词和顺序,比如称专为别人代为书写合同或状词的先生为“刀笔”,比如称某些有特征标志的是“斜白眼宏武”“红头聋子朱金顺”。甚至,我小时候也曾患过的“脊柱结核”就被称之为“瘩背”。当然,这些精妙的称呼,用东乡话读来,更生活、更灵动。
高中阶段,我几乎天天要从便通庵破旧的老房子前走过。这是书中的“我”和“春琴”最终决定落脚的地方。只是,当年的我并不知道,当地人口中的“便当岸”应该被写成“便通庵”。我知道,东乡有儒里赵,有窑头赵,这些村落都是因为名门望族不同的支系聚落而得名。有青龙山,有姚家桥,也有平昌花园和沙港。
我知道东乡人生大病重病去的医院就是德正住的康复医院或者婶子住的江滨医院。我知道东乡人称呼家长为“娘老子”。我也知道东乡一些村落在拆迁遇到阻力时个别村干部们采取的措施和赵礼平之流如出一辙。
太多太多熟悉的生活场景,让我一次一次地陪着书中人“神游”故乡。比如,同彬的妈妈新珍早晨起来在门口刮锅底灰,这是东乡人家天天早晨都会有的此起彼落的“家门口一景”;冬天结了冰碴的乡下路在太阳的暖照下“化冻”,土路变得泥泞不堪,为了保护脚上的鞋子不被弄脏,孩子们不得不跳着走在路边的草窠里,通常此时,家长都会帮着用随手可折的杨树枝“刮干”鞋底或鞋帮上的淤泥;家家墙脚边都搁着一个稻草编的“箩窠”,里面站着一个或笑或哭的半大孩子。而每当父母在村集体“开夜工”回来,就如同书中“我的父亲从青龙山开夜工回来”一样,一进门就幸福地喊“我”起来,父亲带回家一大碗白米饭,那碗白米饭上还盖着一层萝卜烧肉。这曾是我们那个年代多少东乡孩子的集体记忆。那份半夜躺在老屋老式大床上的等待和开心,至今想起,依旧令人口齿生津。
太多太多只有东乡本土人才读得懂的土话和土物的名称,令我一次一次地去回味某个邻居这样说话或做事时候的神态。比如,来骗我同意出让老屋的婶子做饭时系上的是“围腰”,也就是城里人说的“围裙”;我和同彬坐在“腰门口的石阶上”看旧日的村庄,是指东乡老屋几进纵深的中间的门坎;被同彬形容为说话总是“文乎文乎”“一看就是云上翻筋斗的角色”的沈祖英以及那些分不清的各种小动物的称呼。那在太阳光朗照下的“亮豁豁的”巷子口,那太阳映照水面上而呈“亮汪汪”意境的河边,都是我东乡人口中特有的表述。
太多太多的东乡特有的习俗甚至至今仍然延续着,令我一次一次地因为重温而流连忘返。比如,我们童年时代每天在放学回家路上就得开始为家中养的羊或猪找食物的“寻草”;谁家新房上梁时瓦匠师傅大声吆喝着抛糖果、抛馒头、发利市,而村人们如潮水般地跟着东南西北胡乱追逐抢夺的欢腾场景;每当春节临近,几乎每个村落或大队都在上演的“唱花集”“唱麒麟”;谁家有人故去而请和尚来家里“放焰口”;还有那些半夜三更不辞辛苦地躲在新婚夫妻窗下“听壁根”的恶作剧。当然,每当乡干部们敲锣打鼓地到谁家“送喜报”的时候,后面一定会跟着一大群高高低低的孩子们奔跑的身影,那种开心,那种欢呼,仿佛就是自家得到了最大的“喜报”。
真的是太多太多……
记得前年,我的《老东乡》一书问世的时候,乡人和媒体曾热情地称之为第一部系统地介绍东乡人文习俗的“好书”。我也曾沾沾自喜过。但一次一次地阅读《望春风》,这种叙事中随处可见的巧妙地嵌入东乡元素的写法,令人不得不一次次地停下来,回味、品尝、思考。一部小说,能够在当下碎片化阅读的大语境下,给阅读者留下如此印痕,实不多见。
因为《望春风》,我才知道东乡杨树上“七死八活九蹲窠”的是“杨癞子”而不是“洋辣子”。因为《望春风》,我才第一次晓得对一个变得有点“老年痴呆”、不太灵活的人,东乡人说的是“你也快掘墓了”。因为《望春风》,我才第一次晓得人坐在马桶上方便应该写作“正坐在杩子上出恭”。因为《望春风》,我也才第一次晓得说话没谱就是说“没边没沿的话”。这些活灵活现的东乡话,不是东乡人,真的很难体验到格非先生叙事时候的那份随性和惬意。
读着,读着,此刻,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老福奶奶每天黄昏都会温柔发出的呼鸡声:“喔嘘,喔嘘,喔嘘……”